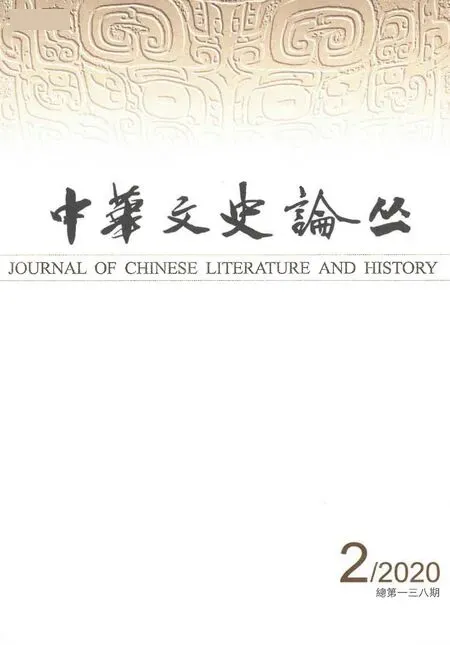論陶詩的力量*
劉 奕
提要: 陶淵明詩歌以自然超妙爲宗,但古今詩人、學者卻不乏陶詩極富力量的各種議論。只是陶詩的力量究竟何在,其存現方式有哪些,卻一直缺少專門論述。其實陶詩同時具有承載包容和超拔絶俗這兩種力量,這源於其人格上曠達深静、疏淡樸拙與憂憤沉鬱、耿介峻潔二者的融合。表現在詩歌上,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其力量的存現: 其一是從風格上的“左思風力”來審視;其二是從“介”與“拙”的自我認同與自我描繪來看;最後則可以從較隱秘的字法、句法、章法上發現這種深厚廣大的力量。
關鍵詞: 陶淵明 陶詩 力量 承載包容 超拔絶俗
一 引 論
陶淵明其人其詩,皆極有力量。對陶詩力量的把握,是判别讀者理解深淺的標準。所謂力量,既指詩歌的力度感、力量感,也指其内在的充實厚重,是就内容、情感、氣韻、風格、語言、技巧等綜合言之,而非單執一端而論之。所以輕盈者可以有大力,豪壯者也可以粗浮不實。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美國講稿》中引用保爾·瓦萊里(Paul Valéry)語云:“應該輕得像鳥,而不是像羽毛。”(1)[意] 卡爾維諾著,蕭天佑譯《卡爾維諾文集》(5),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頁331。羽毛雖輕,無風自沉,蓋其自身無力,完全依憑外物;鳥能飛翔,力大者九萬里風斯在下,力弱者搶榆枋而止,各隨其力而已。瓦萊里的比喻,劉勰早已發之:“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風骨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513。“剛健既實,輝光乃新”,纔能如“征鳥之使翼”。陶詩高翔於天地之間已一千六百年,若無大力,焉能及此。
關於陶詩的力量這一問題,雖然現代研究中缺少系統討論,但先賢時髦對此頗有深刻透闢的見解,可以作爲我們研究的基石。鍾嶸《詩品》最早稱陶詩“又協左思風力”,自是眼力不凡。稍後蕭統《陶淵明文集序》中評價説:“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3)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附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613。他顯然感受到了陶淵明作品所藴含的力量。到宋代,陶淵明成爲一種文化典範,其獨特的質地和意義不斷被討論和抉發。
宋以後人討論陶詩的力量,大致有三個視角: 忠義之氣、人格個性和學養。黄庭堅《宿舊彭澤懷陶令》:“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骯髒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閲江浪。空餘時語工,落筆九天上。”(4)黄庭堅著,任淵等注《山谷詩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5。眷懷晉朝,這是《宋書》以來一貫之論,黄山谷則進而把陶令比作是未得志的諸葛孔明。“骯髒”一詞極能狀出陶公磊落出塵的神貌。後來朱子論陶詩,抉發其豪放之相,其實“骯髒”即豪放也。後人持忠義之論者極多,至清代周春説:“朱子謂《荆軻》一篇,平澹中露出豪放本相,須知其豪放從忠義來,與《述酒》同一心事。”(5)周春《耄餘詩話》卷八,張寅彭主編《清詩話三編》(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542。再次綰合忠義與豪放。
其二從個性立論。《後漢書·逸民傳論》已指出隱士多是“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6)《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755。朱子亦如是觀陶公:“陶卻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7)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327。“有力”、“語健而意閑”二語,可謂洞見。清人延君壽也説:“每聞人稱陶公恬淡,固也。然試想此等人物,如松柏之耐歲寒,其勁直之氣,與有生俱來,安能不偶然流露於楮墨之間。”(8)延君壽《老生常談》,郭紹虞選編,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821—1822。
其三以學養觀陶詩的力量,尤須特識。真德秀云:“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中略)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9)真德秀《跋黄瀛甫擬陶詩》,《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六,《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 商務印書館,1922年,頁2A。真氏意中,“經術”是陶詩力量的根源,“悲涼感慨”則是其表現。清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〇中有一段妙論:“陶公詩雖天機和鬯,静氣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蕩處,實有憂憤沈鬱、不可一世之概,不獨于易代之際奮欲圖報。(中略)蓋所學任天,自與俗異。同時必有貌爲推尊、内實非薄者,必又有多方訕笑、交訌其側者,非具定識定力,何以能不爲之動而卒成所學也。故端居自勵,亦深以懷疑改轍爲警,曰‘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曰‘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曰‘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然則和鬯流溢,學成之候也;憤激沈鬱,刻苦之功也。先有絶俗之特操,後乃有天然之真境。彼一味平和而不能屏絶俗學者,特鄉原之流,豈風雅之詣乎?”(10)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57。
以上三者,雖一致百慮,實殊途同歸。讀陶詩不但要觀其曠達深静,也要觀其憂憤沉鬱;不但要觀其疏淡樸拙,也要觀其耿介峻潔。因爲前二者實由後二者所造,所以它不是閑潭曲水,而是如洋之廣,如海之深,其中有大力存焉。本文則希望在此基礎上,將陶詩細緻展開,觀察其力量的存現方式。尤其是來自人格的力量如何通過藝術的方式,呈現在詩歌之中。爲論證之便,論文擬從三個方面加以探討: 風格上的“左思風力”,介與拙之個性的呈現方式,以及字法、句法、章法。
二 “左思風力”
鍾嶸抉發陶詩的“左思風力”,被學者贊爲“特識”,(11)王叔岷《論鍾嶸評陶淵明詩》,《陶淵明詩箋證稿》附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31。自是陶詩力量最易辨識之處,所以先論述之。前人於此多在比較陶詩與左詩的相類之處。最早作詳細討論的大概是游國恩。在1928年發表的《一千五百年前的大詩人陶潛》一文中,他先評價左思詩“胸次高曠,筆力雄邁”,又舉陶詩《擬古》“辭家夙嚴駕”、“迢迢百尺樓”和《詠荆軻》三詩,説:“這些詩都可以表現陶公慷慨豪邁,自負不凡的氣象。音節蒼涼激越,辭句揮灑自如,拿他們和左思的詩比較一下,纔知道鍾嶸的話不是無的放矢的。”之後列舉了多例,認爲都是陶詩出自左詩的證據。(12)游國恩《一千五百年前的大詩人陶潛》,《國學月報彙刊》“陶淵明號”,1928年第1期,頁136—140。後來王叔岷也有類似的比較之辭,他説:“同是詠荆軻,陶詩三十句,以長勝。左詩僅十二句,以短勝。其‘風力’實不相上下。陶詩之悲壯淋漓,左詩之慷慨磊落,皆令人擊節稱賞!陶公《擬古》之第二、第四、第八,亦見‘風力’之作。鍾氏謂‘協左思風力’,信不虚矣!”(13)王叔岷《論鍾嶸評陶淵明詩》,頁532。
兩先生之説都在理而未融。阮瑀和王粲各有一首詠荆軻的《詠史》詩,陶淵明《詠荆軻》一詩詳細描摹易水送别和刺秦情景,正與阮、王之詩相同,而與左思寫荆軻燕市飲酒之作無關,其淵源顯然在彼不在此。(14)阮瑀詩:“燕丹養男士,荆軻爲上賓。圖盡擢匕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諮嗟,歎氣若青雲。”王粲詩:“荆軻爲燕使,送者盈水濱。縞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揮。”應都是殘詩。然所存片段描摹易水送别,對陶詩的影響顯而易見。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59,88。要説詩歌上明顯借鑑左思的地方,我覺得倒未必是荆軻的題材或者一二激烈的語言,而是左太沖《詠史》的寫作方式。清人何焯在評點張協《詠史詩》時説:“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歎之,隱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抒胸臆,乃又其變。”(15)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893。他將詠史詩分作兩種類型,正體是“隱括本傳”的寫法,左思爲變體,借史以抒發胸臆。本此視之,陶公《詠荆軻》、《詠三良》上承阮瑀、王粲、曹植同題之作,接近正體,而《詠貧士》則屬左思一脈。程千帆總結左思《詠史》有兩個特徵,其一是“雜陳先典,不專一事”,其二是“題爲詠史,實寓衷懷”,(16)程千帆《左太沖〈詠史〉詩三論》,《古詩考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77。即常常在一首詩中詠同一類型的多個人物,借此寄托懷抱;《詠貧士》七首也基本是這一寫法,除了語氣較爲平和内斂外,其他正可視爲太沖《詠史》嫡脈。“左思風力”是否應該這樣理解呢?
以上是從詠史的形式而言,如果以神遇之,而不以形視之,那左思詠荆軻的精氣神在陶詩中並不少見。左思詩云:“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17)左思《詠史》(其六),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297。今存漢畫,荆軻題材集中在刺秦場景,而建安詩歌,則更着力于易水送别,一激烈,一悲慨,都能很好表達荆軻的英雄氣。(18)荆軻題材詩與畫的離合關係,以及阮瑀和王粲二詩的分析,參見劉奕《圖像性的減弱: 漢代詠史詩的一種解讀》,《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頁98—99。左思的詩則迥異於古今同題材作品,他選取的是《史記·刺客列傳》中的另一段記載:“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19)《史記》(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051。爲什麽寫這一場景?前人評述總不外以爲左思藉以表達對豪右的蔑視。此説不錯,但流於表面,未得其深處。英雄之爲英雄,並不要等到他做出了驚人事迹之後纔是。英雄者,恒有其英雄志氣者也。雖然困窮,雖然失路,但其人昂藏不摧。得其時以成其事,其氣勃勃;不得其時不見其事,其氣鬱鬱。鬱鬱勃勃,有時而發,是爲英雄。(20)興膳宏解讀此詩云:“左思卻以‘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有意抹煞了歌中的‘壯士’一語,這等於是部分地否定了司馬遷描繪的悲劇英雄荆軻的形象。可能左思認爲荆軻有勇無謀,過分相信自己的力量,爲燕太子丹泄私憤而去暗殺秦皇,不能算是真正的大丈夫。”左思本意是飲酒燕市時,荆軻還没有做出什麽英雄之事,即“雖無壯士節”,卻英氣勃勃,毫無寒乞相。興膳宏卻理解成了左思對荆軻一生的定評。這個誤讀頗具代表性,故引述於此。[日] 興膳宏《左思與詠史詩》,彭恩華譯《六朝文學論稿》,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53。所以英雄不在乎人知與不知。左思真知英雄,其詩當作如是觀。而陶公也是英雄人,其詩也具英雄氣。(21)古人頗有既看到了陶淵明的用世之心,又看到其卓落不屈之志與兀傲不羈之氣,而以英雄許之的。如陳與義《題酒務壁》詩云:“當時彭澤令,定是英雄人。”白敦仁校箋《陳與義集校箋》卷一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367。案: 此詩爲友人王培軍先生見示。又張以寧《翠屏集》卷一《題海陵石仲銘所藏淵明歸隱圖》云:“豈知英雄人,有志不得豁。高詠荆軻篇,颯然動毛髮。”《明别集叢刊》第一輯(2),合肥,黄山書社,2013年,頁501。又舒位《向讀文選詩愛此數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論其世凡作者十人詩九首》其四:“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詩傳。”舒位《瓶水齋詩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15。
陶詩云:“兀傲差若穎。”(《飲酒》其十三)兀傲自喜,正如燕市之荆軻。而左思則自許“卓落”(《詠史》其一),亦然。馬一浮對《飲酒》其十三正好有一段解讀:
“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屈原對漁父言“衆人皆醉我獨醒”,以爲醒勝於醉;靖節則自托於醉,以爲醉勝於醒。“規規一何愚”,言醒者之計較利害也,“兀傲差若穎”,言醉者之忘懷得失也。“寄言酣中客,日暮燭當炳”,若曰當續飲也。是故其所謂酒,不必作酒看;其所謂醉,不可作醉會。(22)馬一浮《語録類編》,《馬一浮全集》(1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625。
屈原以獨醒爲兀傲,陶公以獨醉爲兀傲,前者意在用世,後者有心逃人,然其不同流俗之意氣卻自相同。“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飲酒》其十二),“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雜詩》其四),這是陶公的傲世語。“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顔”(《詠貧士》其五),這是陶公的安仁處。此類甚多,不煩枚舉,都是不以俗世的標準爲標準,雖不作太沖“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的豪語,但超出塵寰的胸襟氣度正自相同。這樣的詩句,算不算得“風力”之作呢?
不但這類骨鯁嶙峋的詩句有風力,那些温潤深厚的詩作在會心者眼中也是有風力的。如郭紹虞評價《停雲》説:“余嘗謂自來解《停雲》詩者,惟辛稼軒《賀新郎》詞,最爲恰到好處。辛詞云:‘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此數語正得淵明意趣。所謂‘抱恨如何’,所謂‘搔首延佇’者,均可於此春醪獨撫之餘,窺其上下今古獨立蒼茫之感。”(23)郭紹虞《陶集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頁283。這才搔到了《停雲》詩的癢處。如果説詩中前兩章是雨沉天地,所以“舟車靡從”,那麽後兩章明明已雨過天青,那爲什麽陶公只是在家中思念親友,等待他們,卻決不去尋訪?蓋親友正在塵中,義無相尋相求之理。思念不置,是其温厚處;惟思其來,絶不往尋,則是其兀傲處。與辛稼軒充塞天地的塊壘不同,陶詩是其言温潤,其骨則崚嶒。
梁啓超也有類似的體會,他説:
他並不是好出圭角的人,待人也很和易。但他對於不願意見的人不願意做的事,寧可餓死,也不肯絲毫遷就。孔子説的“志士不忘在溝壑”,他一生做人的立腳,全在這一點。《飲酒》中一章云……(筆者按: 下引“清晨聞叩門”一首,略)這些話和屈原的《卜居》、《漁父》一樣心事。不過屈原的骨鯁在外面,他卻藏在裏頭罷了。(24)梁啓超《陶淵明》(1923年商務印書館初版),《飲冰室合集》(12),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3。案:“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語見《孟子·滕文公下》,梁任公記錯了。
一點不錯,陶淵明不是鄉愿,他骨鯁藏得深,但只要涉及獨善的原則,這種深埋的硬氣就會鬱然而怒,勃然而發。“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話説得多麽謙遜,又多麽斬截。(25)延君壽《老生常談》論此詩云:“斬釘截鐵,勁氣勃發,可以想見陶公之爲人。”《清詩話續編》,頁1820。清人包世臣同樣有“彭澤沉鬱絶倫”之語,(26)包世臣《藝舟雙楫》卷一《答張翰風書》,《包世臣全集》,合肥,黄山書社,1993年,頁256。與前引潘德輿“憂憤沈鬱、不可一世”的評價相同。這種深藏其中的氣骨算不算“風力”呢?當然算的。
除了從上述精神氣韻的角度理解“風力”,我們也可以直接觀察到陶詩中有一種峻拔高潔的風格,這種風格即陶淵明不合流俗之氣,也就是“左思風力”的直接表現。“峻潔”的品目,遠出顔延之“廉深簡絜”、“和而能峻”,(27)顔延之《陶徵士誄》,《文選》卷五七,頁791。近則似當出自清人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有云: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28)沈德潛撰,王宏林箋注《説詩晬語箋注》卷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頁164。案: 沈氏《唐詩别裁集·凡例》亦云:“柳柳州得其峻潔。”
拈出“峻潔”,是沈歸愚的見識。峻是高峻,潔是清潔,是潔身自好,這是講陶淵明立身崖岸很高,絶不同流合污,因此詩歌風格也有高潔的一面。以人格論,有傲骨自然能不同流俗。以詩風論,雄豪語、憂憤語、斬截語、磊落語,都是峻潔的表現。除了人所熟知的《詠荆軻》之“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其人雖已殁,千載有餘情”和《讀山海經》之“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之外,潘德輿還另舉過一些例子:
如“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毁”、“賜也徒能辯,乃不見予心”、“擺落悠悠談,請從予所之”、“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迂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我心固非石,君情定何如”、“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蓋所學任天,自與俗異。(29)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〇,頁157。
潘德輿不被衆口一詞的“易代之悲”所束縛,而是由人我關係的角度審視陶詩。引言中曾引及潘氏之言(“蓋所學任天……亦深以懷疑改轍爲警。”)就是峻潔詩風的來源。人言易惑,三人市虎,何況舉世相違,訕笑交加,而仍然堅持故我,那一定是需要極强的骨力和極深的反省砥礪之功的。否則僅僅憑藉少年熱血以行事,往往經不起世事摧折,很容易就改弦易轍而隨波逐流去了。我們看潘德輿所舉,都是《飲酒》、《雜詩》、《擬古》這類晚年組詩中的詩句,可知陶淵明並没有像常人那樣臨老來變得頽喪荒唐,反而骨愈鯁而氣愈盛,便可知潘氏所云“定識定力”絶非虚語。
朱自清據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統計後認爲,陶詩化用左思的句子數量少於《十九首》、阮籍和嵇康詩,所以“左思的影響並不頂大”,“《詩品》的話就未免不賅不備也”。(30)朱自清《陶詩的深度》,《朱自清全集》(3),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0。王運熙也説:“總的説來,陶詩風格的主要特徵是古樸質直。與應璩詩接近,也有與左思詩風相通之處,但左思詩歌雄邁有力的特徵,僅在陶詩少數篇章中見之。從風骨説,陶詩風清(即鮮明爽朗)的特徵比較突出,骨峻(即剛健有力)則稍遜。”(31)王運熙《鍾嶸〈詩品〉陶詩源出應璩解》,《文學評論》,1980年第5期,頁138。如果僅從體現峻潔風格的詩句數量論,二説似可接受。但從内在力量的角度考慮,以“剛健既實,輝光乃新”思之,則朱、王二先生之説猶未達一間。顔延之講陶淵明“和而能峻”,(32)顔延之《陶徵士誄》,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五七,頁791。以及前引辛稼軒、包慎伯、潘四農、梁任公、郭紹虞諸人之論,都可謂洞徹表裏。所以古樸質直是陶詩,沉鬱骨鯁也是陶詩,二者一表一裏,一顯一隱,是渾融焕發的關係,以數量和比例的角度觀察未免失之膚泛。
這一點,近人顧隨恰好有過説明:“陶公調和。(中略)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後,生活一番挣扎之後,纔得到調和。陶公的調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協。”(33)顧隨述,葉嘉瑩記《顧隨講中國古典詩詞》,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70。這個調和,是用了承擔的大力纔得到的。顧隨借禪宗和耶穌作比説:“一個人無論怎樣調和,即使是聖、是佛,也有其煩惱。佛是煩惱,耶穌是苦痛。他不煩惱、苦痛,便不慈悲了。一個大思想家、宗教家之偉大,都有其苦痛,而與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來打破。或問趙州和尚:‘佛有煩惱麽?’曰:‘有。’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麽?’這真厲害。”(34)《顧隨講中國古典詩詞》,頁76。陶淵明能承擔人生的痛苦,他不逃避,不自欺,所以纔能領悟人生的真際,纔知道苦自苦,樂自樂,最終成就其深厚與廣大。他的詩歌質樸自然,是骨鯁其内、風蕩其中的質樸自然,唯其有風力,所以能質能厚能自然;反之,越是質樸深厚,其骨越硬,其氣越盛,二者是相輔相成、呼吸相通的關係,而非主次並列相加的關係。“大用外腓,真體内充。反虚入渾,積健爲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語),這樣來理解“左思風力”,則陶詩無時無處不是風力彌滿的。同理,陶詩無一首不古質,無一首不自然,又無一首不峻潔。
前面詳論陶、左之同,還應補一轉語,稍稍分辨二氏之異。程千帆謂左思“結念在窮通”,《詠史》之作,不過藉以“消釋其内心之矛盾與苦悶耳”。(35)程千帆《左太沖〈詠史〉詩三論》,頁275。張伯偉乃謂:“蓋左思之力,出於其怨,若社會能滿足其願望,則怨亦消失。陶公之力,來自其傲(乃上百年家風鑄造而成),故不屑與主流社會相融。惟其性情淳厚,故其傲在骨不在形。左思屬草根,身懷天才,一心向上爬,屢遭挫折(陸機嘲之爲傖父),乃化爲一股怨氣,不擇地而出。陶公出于貴族,眼見小人得志而忘形,乃遼闊高翔,不屑爲伍。”(36)此爲張伯偉先生書信見告之語。陶、左高下,赫然在目。以風論,陶如春風大雅,左不免飄風之驟。以力論,左如獅子搏兔,貴在一擊;陶則龍潛在淵,深蓄其力。淵明風力近南宗畫和内家拳,左思風力近北宗畫和外家拳,這是二家之異。
三 介 與 拙
陶淵明的自我認知與自我表達有三個有關聯性的關鍵詞: 介、拙、獨,其中以“獨”的使用頻率最高,但具有本質意義的卻是“介”和“拙”。陶詩用“介”字有3例:
總發抱孤介,奄出四十年。(《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飲酒》其十九)
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詠貧士》其六)(37)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219,278,375。
此外,陶淵明偏愛的“固窮”的表達,也是“介”的變形。陶詩用“拙”字有6例,另《感士不遇賦》亦云:“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38)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433。今舉詩中典型者4例: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其一)
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爲拙。(《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雜詩》其八)
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詠貧士》其六)(39)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76,207,353,375。
陶淵明詩文中用“獨”字最多,不算《五孝傳》和《集聖賢羣輔録》,總計有42例。飲酒則獨醉,高歌則獨悲,登臨則獨遊,靈府則獨閑,所盤桓的松是獨松,所遥望之雲是孤雲,孤獨是陶公生命的基調,是陶詩的底色。只是“獨”字所用雖多,卻是“相”而非“法”,只是“介”和“拙”的外顯而已。龔斌説:“他常以孤松、孤雲、孤鳥、秋菊、幽蘭等自況,爲自己耿介狷潔的品格寫照。”(40)龔斌《陶淵明傳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97。此説中肯。陶淵明孤獨,根源於他的介與拙。拙是他的天然厚質,介則是他的德行抉擇。
拙是巧的反義詞。《説文·手部》:“拙,不巧也。”《老子》第四十五章:“大巧若拙。”王弼注云:“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41)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23。拙是順自然、從本性、不造作,所以不論褒義還是貶義,“拙”多從質性上言。如葛洪《抱朴子外篇·行品》:“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42)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547。又如白居易《詠拙》:“所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蠢,我命薄且屯。”(43)《白居易集》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19。陶淵明曰“守拙”,曰“拙生”,其本來如此的意思也很明顯。
介的義項衆多,其中之一是保持操守,特立獨行。《方言》卷六:“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44)錢繹《方言箋疏》卷六,清光緒十六年紅蝠山房刊本,頁11B—12A。《孟子·盡心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45)《孟子注疏》卷一三下《盡心上》,《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5),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6025。又董仲舒《士不遇賦》:“貞士耿介而自束。”(46)《古文苑》卷三,《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頁3B。張衡《思玄賦》:“孑不羣而介立。”(47)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214。“介”是德行,是自我選擇。韓愈《伯夷頌》描述介立之士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反之,“今世之所謂士者: 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48)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65—66。中有所守,唯義是從,而不爲常人是非毁譽所動,這樣纔能特立獨行。這需要的是後天的學習、思考和反省,需要心性錘煉和外在砥礪,並不是天生就會的。從真德秀的“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以下,直到晚清譚嗣同稱陶淵明的境界爲“涵養所致,經術之效”,(49)譚嗣同《報劉淞芙書二》,《譚嗣同集》,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頁14。再到民國梁啓超説“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出都在儒學”,“他做人很下堅苦功夫,目的不外保全他的‘自然’”,(50)梁啓超《陶淵明》,頁13。這些看法都是極有見識的。正源於他們都知道,陶淵明人格中耿介的個性,作品中兀傲的風骨並不是生就如此,就像孟子所言,人心中“義之端”需要後天的培養擴充,纔能一生不動搖。顯然在傳統的思想資源中,這種培養擴充的力量主要還是由儒家來提供的。
陶淵明的拙和介交相爲用。介者與世不諧,在他人眼中自然是“方腦殼”的拙者。(51)錢鍾書《管錐編》第三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二〇《圓喻之多義》”條對古今中西人所述“方腦殼”之語有考述,可參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925。而拙者有三: 不慧之拙,樸厚之拙,耿介之拙。陶公三拙皆備。他天性醇厚,也有狷介特立的傲骨,而從總是短暫爲官的履歷看,他缺乏行政與交際才能當也不假。陶淵明人也妙,詩也妙,這種奇妙正來自他同時具備了天生的拙和砥礪出的介。蓋介者易偏激,易鋒芒顯露而刻薄單寒,唯質性拙朴,所以耿介孤立,卻又寬和樸厚,能傲於骨而不傲於人。分明内省不息,内力激蕩,卻又讓接近他的友人,讓後代讀者沐浴在春風駘蕩之中。後世詩人,在這一點上最像陶淵明的是杜甫,而不是一般人所認爲的王、孟、韋、柳諸人。清初焦袁熹嘗云:“得陶之性情神理者無如杜。”(52)焦袁熹《此木軒論詩彙編》卷四,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頁1B。正與鄙意相同。
如果審視陶淵明的生平,他一生行事,都與世上圓通之輩截然相反。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陶淵明詩文中自述“介”和“拙”是對自己真切地寫照,而非狡獪弄筆的自我塗飾。但“真”的文學並不就等於“好”的文學。厚重的真實所具備的力量仍需要借助詩心詩筆,纔可能轉化成文學的力量感。讀陶淵明的作品時,我們可以感受到“拙”與“介”兩種人格各自的力量和作用,它們浸潤作品之中,倒並不一定非要直接使用這兩個字。
拙在陶詩中的表現是平實厚重,他不在文字上炫技、耍花槍,不刻意追求對偶和繁密的修辭,這都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同時,他的情感深沉穠摯,這是他的作品直擊人心的地方。梁啓超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讀集中《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與子儼等疏》,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間的情愛熱烈到什麽地步。(中略)他對於朋友的情愛,又真率,又穠摯。”(53)梁啓超《陶淵明》,頁7。比如《停雲》,前面已經分析過,這首詩對一班在紅塵中沉浮的親友是有諷喻的,但詩歌又不厭其煩地説:“良朋悠邈,搔首延佇。”“人亦有言,日月於征。安得促席,説彼平生。”“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54)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1。一片深情厚誼,除是鐵石心腸,誰不會爲之心動呢?同樣,友人殷晉安要赴任陶淵明最看不上的劉裕的太尉參軍,常人恐怕早已連朋友都做不成了,可是陶公依然賦詩贈别,最後還説:“脱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55)《與殷晉安别》,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155。其意中始終視殷爲朋友。他人肝膽即秦越,陶淵明胸中卻似乎放得下雲夢之澤,所以作詩時鄭重而纏綿。
此外,“拙”者如頑石,安穩不易動搖,所以容易呈現一種鎮静的風度。李長之説:“高貴和鎮静也體現在陶淵明的身上。”(56)張芝(李長之)《陶淵明傳論》,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頁20。這是就陶淵明的風度而言。那他的詩歌是否也有此風度?自然也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前面部分云:“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佇遥念,一盼周九天。”(57)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227。第三四兩句寫火災,五六兩句寫暫時的安頓,七八兩句寫時間,轉眼已經到了七月,第九句接着寫生活的狀況,第十句以“驚鳥尚未還”從側面補述了當時火勢之大,寫出了家人心中的餘悸,很得含蓄之美。其中“迢迢”二句,寫得恬淡寧静,明末清初人陳祚明特别讚賞道:“燔室後有此曠情。”(58)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13。晚清鍾秀也説:“其於死生禍福之際,平日看得雪亮,臨時方能處之泰然,與强自排解、貌爲曠達者,不翅有霄壤之隔。”(59)鍾秀《陶靖節紀事詩品》卷二《寧静》,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頁11B—12A。的確,前云“一宅無遺宇”,後云“驚鳥尚未還”,並不諱言險難驚懼,難得的是中間卻安放得下恬静的二句,是時序,是景物,更是詩人的胸懷。於人格言,苦難之際,仍有閑情欣賞新秋月色,是有厚重的大力;於詩歌言,在前後危苦中著此清曠之言,便是静遠風味。相比憤怒、呐喊,鎮静是一種更大的力量,人如此,詩亦如此。
陶淵明作品的“拙”,展示的主要是一種承載性、包容性的力量,所謂“地負海涵”,如載川嶽而不虧,如泄尾閭而不盈。而“介”的力量感,則是“淵渟嶽峙”式的,鬱而怒,深沉而高聳。直抒胸臆,表達憤懣,所以高聳;下筆沉着,詩思深曲,所以深沉。試以《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爲例,作一分析: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絶。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悦。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誰能别?(60)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206—207。
癸卯歲是晉安帝元興二年(403),這一年陶淵明三十九歲,正丁母憂服喪在家。去年,荆州、江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三月,占領建康,“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61)《晉書》卷一〇《安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55。到了本年十二月,桓玄篡位稱帝,遷安帝于尋陽。(62)《晉書》卷一〇《安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56。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晉書·五行志》載:“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爲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63)《晉書》卷二九《五行志下》,頁876。這是詩歌的背景。
只就詩歌本身看,詩中的傲岸之氣已是鬱怒如飛。首四句大有頓挫。從意思上講,正常的語序是“寢迹衡門下,荆扉晝常閉。顧盼莫誰知,邈與世相絶”,但這樣就平順無奇。現在一顛倒,便有傲氣中人。陳祚明注意到這一點,他説:“起四句,一句一意,一意一轉,曲折盡致。”(64)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三,頁402。這一訣竅,後世要杜甫纔能深知。同時,顛倒後形成的首二句别有作用,即規定了詩歌主題的正反兩面,正面講自己的隱居,反面講自己對人世的拒絶。歲暮之風、經日之雪,本來嚴酷,但是詩人卻在嚴酷中有深會於雪之精神。大音希聲,真正的力量並不靠高聲呼喝證明自己。皓已潔,其純潔的力量足以籠罩山河。“勁氣”兩句語意轉折,雖然美好,卻也嚴酷,詩人不粉飾不躲避,只是接受。然後遞進,由嚴酷而痛苦: 因貧困而痛苦,更因孤寂而痛苦。軟弱者寫痛苦,是自戀自憐,是咀嚼把玩,於消沉無可奈何之際獲得一種沉淪的快感,更是乞求别人的關注與憐憫。固執强硬者寫痛苦,那就只是痛苦,正如快樂只是快樂。痛苦之來,既能承擔,也有反抗。“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悦”,是承擔。下面再一次轉折,“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這便是反抗。世中的人看不上,没有人值得尊重,論交當世,難免失望,尚友古人,纔能撫慰詩人鬱鬱之心。所謂固窮守節,孔子是這麽説的,也是這麽做的,那“我”現在也這麽説這麽做,古之烈士應該與“我”相視而笑了吧?“非所攀”,是謙辭,“深得固窮節”卻又極見兀傲。陶淵明不煉字嗎?“深”字何等傳神而有力。因爲傲氣被唤起,詩人便忍不住反問: 不順着你們所謂的通津大道走,棲遲隱居,這就是你們所謂的拙嗎?(65)陳祚明謂:“平津,平道也,人所共由,信不由之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三,頁402。意思爲一轉折。可知開篇所云“邈與世相絶”,既是世人疏遠詩人,更是詩人棄絶世人,兩相憎,兩相絶。最後,詩意再折回,詩人轉頭對堂弟説:“我的深意都在言外,誰能與我契合而辨别呢?”這就是對“邈與世相絶”的遥相呼應。明末黄文焕説:“無一可悦,俯首自歎;時見遺烈,昂首自命。非所攀,又俯首自遜;苟不由,又昂首自尊。章法如層波疊浪。”(66)黄文焕析義《陶元亮詩》卷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187。分析得真好。但如前面的揭示,詩歌一直處於跌宕起伏的轉折和遞進之中,並不是只有這四處轉折。所以方東樹《昭昧詹言》中説:“一直敍去,而時時頓挫開合,筆勢起跌,無平直病。”(67)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頁105。
如果再聯繫背景解釋,對詩歌的理解又會更深一層。陶淵明不久之前還是桓玄的屬官,現在桓氏稱帝,一般人都會覺得這是從龍的大好機會,那詩人强調固窮,會没有針對性嗎?最後他説,“寄意一言外”,誰是我的同志而能明白我的苦心呢?所謂的不理解,第一個當然是一般人不理解他爲什麽不出來做官。第二可能是少數人覺得陶淵明不出來做官也是爲了討好桓玄。何以見得?《晉書·桓玄傳》載:“玄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並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68)《晉書》卷九九,頁2593—2594。陶公自然不屑不齒桓玄的禄位,可會不會有人以小人之心猜度陶淵明,以爲他是眼紅皇甫希之,也想當桓家的隱士?縱觀今古,想來這樣的議論彼時一定少不了。此際的陶公,他要“與世相絶”,要“固窮”,要“棲遲”,就是敲擊自己錚錚之骨,鏗鏗然作響,要讓世人聽聽。其憂深,而出之以憤歎,想要平和也難。
以上分析可見,個性上的“介”要轉化爲藝術上的“介”,寫作時就不能平鋪直敍,或一味平淡,而是要富於變化和轉换,通過關鍵字的錘煉,通過句内和句間的轉折、斷裂、遞進等方式,在語意承接上造成頓挫、突兀的感覺。
前人常説陶淵明無意作詩,只是胸次的自然流露,那麽這種“介”感的形成是這種自然流出的無意行爲還是詩人的有意爲之?從全部陶詩看,陶淵明常能熟練運用類似的寫作技巧,這顯然不能用偶然性和自然寫作來解釋。那爲什麽會有那麽多陶淵明無意作詩的看法呢?我認爲拙與介的交相爲用所形成的獨特的詩歌美學效果是非常關鍵的原因。語言的平淡自然,常見修辭密度的降低,這是給人的直觀印象。同時,由樸拙的本性、樸素的語言、真誠的情感所帶來深厚感又無處不在,即便在詩人最憤激的時候,仍然能保持一顆温潤的詩心。如在“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和“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這樣晦暗苦痛的時刻,他依然能發現雪的神韻——“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無聲故莊嚴,皓潔故坦蕩,他已經將人格全部表現出來,所以這兩句一直被後人讚歎不置。其寫作手法也正與《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相同。於是,兀傲的“勁氣”和有意識的表達被深藴于樸實厚重之中,如峻骨藏於豐肌,纔讓人容易産生無意爲詩的印象。
四 字法、句法、章法
前以提及,陶詩中存在着一個字法、句法、章法的隱秘世界,他們藴含着飽滿的勁氣,形成頓挫有力的藝術質感。或許有疑問,六朝詩是否可以講字、句、章法。只是想一想陸機《文賦》和劉勰《文心雕龍》,便覺得可以放心去討論。至於陶詩,固然是六朝詩中的異數,但所謂“深人無淺語”,無論陶公當初作詩時有意與否,顯然通過字、句、章法的分析,可以幫助讀者更清楚了解詩中深意,似無需置疑。明人焦竑《陶靖節先生集序》云:
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懷得失,每念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69)焦竑《澹園集》卷一六《陶靖節先生集序》,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70。
“因拙得工”、“發奇似易”是對陶詩風格極好的把握,也是文本着力分析之處。焦文中更注意的地方是他認爲“譬之嶺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即陶詩的佳處源自陶淵明的人格、胸襟、氣韻的超妙,並非他刻意營造鍛煉而出的。反面言之,既有超妙之言,就應當審視陶詩是如何做到兼有拙易工奇之境的。這時,字句章法的角度,當不可少。
朱熹具有敏鋭的藝術感受力,引言中引用的他“語健而意閑”的評價,正是他對這種藝術質感的深切體認。近人潘伯鷹也説過:
陶詩之美,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自然”的意思並不是説平澹,隨便,乃是説由苦心經營而出,以其真力的彌滿,練習的純熟,而泯去了一切烹煉的迹象。(中略)陶詩我們粗粗看去,似乎不經意,但一細加涵詠,便知轉折瀏亮,安章用字的精穩,無不恰到好處,令人不能復易。昭明所謂“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實爲知言。(70)鳧公(潘伯鷹)《陶詩小識》,《中法大學月刊》1933年第2卷第3、4期合刊,頁76。
陶詩的力量感雖然不像樸素自然的風格一望可知,但從蕭統到潘伯鷹,不能説没有知音。概括言之,陶詩的力量體現在用字上主要是準確厚重,造句是樸拙與高奇,安章則是頓挫曲折。下面分别做一討論。
(一) 字法
黄庭堅評價陶詩,有名言曰:“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71)黄庭堅《題意可詩後》,《黄庭堅全集》(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529。涪翁之意,陶詩的拙與放不是庸人所理解的笨拙與疏放,而是有智慧與道存乎其中,誠可謂知言。焦竑説陶詩“或因拙以得工”,所見正同。前一節已經概述了陶詩“拙”的特色,這裏再單從字法的角度做一討論。
如果論陶詩字法的拙和放,可以看到,動詞和形容詞的使用效果偏向於拙,而虚詞的使用效果則是放。在前者,陶淵明偏好用口語的、常用的動詞、形容詞,而且會有較高頻率地重複使用,不像其他詩人那樣精挑細選,又儘量避免重複。這當然是笨拙的表現。但是一旦告别了南朝貴族“巴洛克”式文學的語境,後世讀者越來越發現這種笨拙樸素具有更豐富廣大的包容力,更深沉厚重的承載力,可以爲詩句提供更豐富的解讀的可能。
比如“在”字。我們用國家圖書館藏汲古閣舊藏南宋初年刻《陶淵明集》十卷本(曾紘跋本)作底本,統計詩歌中使用的“在”字(不計小序和異文),一共有54例。再用明萬曆沈啓原刻《謝康樂集》作底本統計,謝靈運詩中“在”字有16例。用《四部叢刊》景宋本《鮑明遠集》統計,鮑照詩中有18個“在”字。陶淵明對“在”的使用頻率顯然遠遠高於他同時的謝、鮑等人,這一特點的成立基本不受異文的影響。“在”字句是漢語最基本、最口語的句式,其生命力從先秦延續至今,從未衰歇。任何一個詩人,都無法避免“在”的使用,但是如果可能,他們會選擇别的表達方式,以避免“在”的大量出現,唯獨陶淵明是例外,他看似毫不在意、漫無節制地使用着“在”字,這樣給人的第一印象當然是樸素,甚至是笨拙。但如果我們分析這些例句,會發現很多時候,陶詩中“在”字句既準確,也包含更豐富的意藴、更深沉的力量,有種不假安排而恰到好處的天機意趣。
比如《飲酒》其二:“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此處“在”字有個異文:“飢”。王叔岷認爲“飢”於義較備,但“在”音節較佳,而且陶詩喜歡第三字用“在”。(72)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280。王先生論“在”的優點不錯,但“飢”於義較備嗎?恐怕不是這樣。訓詁上,“飢”和“餓”的意義有區别。“飢”是不飽,所以《飲酒》其十一稱榮公“長飢至於老”,就是總吃不飽。超過不飽的程度,表示完全没東西吃、無食之意,則爲“餓”。這一點古人的用法區分是很清楚的,如《論語·季氏》:“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莊子·盜蹠》:“餓死于首陽之山。”《史記·伯夷列傳》:“餓且死。”以及《淮南子·説山》:“寧一月飢,無一旬餓。”《淮南子》的例證尤其顯明。陶詩云“夷叔在西山”,是餓死意,非不飽意,所以王説不確。“飢”不但訓詁上不準確,而且直露淺白。“在”字就不同,它既不存在訓詁不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包孕萬狀,涵渾有力。“在西山”,並不是只指餓死一事,同時也包含了上西山的原因,在西山的堅持,以及最後的作歌和餓死,凡此都統攝在了“在西山”三字之下,如此與前一句“積善云有報”纔有充分地呼應和强烈地對比。其實“飢”也爲陶淵明所常用,但使用時意思都很妥帖安穩。《飲酒》其十“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其十九“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飢爲食不足,還没到餓之將死的地步,卻終究不能堅守家園,而出仕求“一飽”,其中愧意已隱然可見。又其十一“榮公言有道,長飢至於老”,榮啓期壽過九十,雖然長飢,終不至於餓死,“飢”字用得很準確。《有會而作》“老至更長飢”也是如此。而“夷叔飢西山”卻並不準確妥帖,自不如“在”。選字造句看似散淡實際精嚴,正是陶詩特色。此處“在”與“飢”之辨,也當以這一特色審視之。
又比如《飲酒》其八首句:“青松在東園。”老大一句白話。漢魏晉詩人提到松柏,總是免不了一番形容。比如《古詩十九首》的“青青陵上柏”,劉楨《贈從弟》“亭亭山上松”,左思《詠史》“鬱鬱澗底松”,袁宏“森森千丈松”。(73)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513。後來謝朓《銅爵悲》也説:“寂寂深松晩。”(74)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91。準擬前人,完全可以寫成“青青東園松”,或者“寂寂東園松”等等,可陶公掃卻形容,直截地説“青松在東園”,這是何等自信。因爲詩歌後面“衆草没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五句都在描寫這棵松樹。“衆草”句,見其幼弱。“凝霜”二句,則一轉,雖然幼弱,淩霜之性卻没有分毫減損。“連林”二句又進一步狀其孤獨。所以這棵松青翠、堅韌、孤寂,用任何一個疊音詞去形容它都無法同時包孕這三層意思,轉不如直接説“青松在東園”,反得其簡勁之骨。《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的“在”雖然是介詞,但其效果,正與此例相同。
再如“交”與“懷”。《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卻讓後世讀者讚不絶口。如蘇軾説:“非古人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75)《題淵明詩二首》,《蘇軾文集》卷六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091。宋人張表臣稱“淵明之句善體物也”(76)張表臣《珊瑚鈎詩話》卷一,何文焕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59。。清代薛雪讚云:“其妙處無從下得着語,非陶靖節能賦之,實此身心與天遊耳。”(77)薛雪《一瓢詩話》,丁福保編《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704。稍後洪亮吉《北江詩話》也稱:“余最喜觀時雨既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藴。古今詩人雖善狀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節之‘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庶幾近之。(中略)他人描摹景色者,百思不能到也。”(78)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洪亮吉集》(5),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243。二句究竟好在何處呢?平野之間曰“遠風”,即風從遠方來之意,曰“交”,則有四方之意,是天地皆在我意中。曰“良苗”,是眼中無不善者。曰“懷新”,是春風滋養之意,更是宇宙生生之德與欣欣向榮之景皆在目中。劉熙載認爲這是“物亦具我之情也”。(79)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55。詩人未必有意,但盈溢胸襟的是天地無窮、萬物化生之境,所以筆下自然便以十字寫出無限,寫出生長和希望。潘德輿稱之爲“化工兼畫工”,(80)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〇,頁158。良有以也。可見,胸中有元氣,筆底自然化平凡爲神奇。二程盛讚石延年“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以爲能形容宇宙生生之意,其實石詩猶是我觀物,而陶詩則純然物我渾融,境界更高出一層。
陶詩在形容詞的使用特色上與動詞相同。比如《和劉柴桑》中“良辰入奇懷”一句中,“良”與“奇”都是陶淵明喜歡用的形容詞。陶淵明詩文中“良”字一共有31個用例,其中以形容詞“良”作定語構成定中結構的詞語有17個21例: 良朋、良朝、良由、良友、良話、良辰、良對、良日、良月、良才、良苗、良弓、良人、良晨、良價、良絲、良田。同時謝靈運的詩文中“良”字出現了28次,更多是用作表“的確”、“很”的副詞,作爲形容詞構成的雙音詞僅8個11例: 良田、良工、良遇、良辰、良游、良時、良覿、良吏。從修辭的角度看,這意味着謝靈運的重複率低,修辭多樣化,而陶淵明就相對樸拙了。但前面分析“良苗亦懷新”時已提到,新苗自有良莠之分,在詩人眼中卻都是“良苗”。無需自我誇飾,一個“良”字,自然見出包孕萬物之胸懷。“我見青山多嫵媚”,大概這就是詩人鍾愛“良”的緣故吧。當然,“良”字聲音的響亮也是需要考慮的原因。《擬古》其一“中道逢嘉友”,“逢”字已經是ng韻尾,再用“良”,不免有音韻沉澀之弊,换用“嘉”字,便自然瀏亮。可見陶淵明並不是一味蠻用“良”字,所謂“化工”,自是詩心洗練的結果。
至於“奇”字,也爲陶詩所喜用。如《和郭主簿》其一“陵岑聳逸峯,遥瞻皆奇絶”,《連雨獨飲》“雲鶴有奇翼”,《飲酒》其八“連林人不知,獨樹衆乃奇”,《桃花源詩》“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等等,用得最好的,還是這裏的“奇懷”。清人延君壽説:“‘奇懷’字是自家覺得於無奇處領會出來,他人不得而知也。”(81)延君壽《老生常談》,頁1821。在他人平淡無奇的一天,在陶公,卻能引發“奇懷”。有“奇懷”,自然有“奇情”、“奇想”、“奇思”、“奇感”,鬱鬱壘壘,撑拄胸間。劉柴桑居然想要招邀這樣的人參禪打坐,禮拜淨土,叫他如何忘卻喜怒哀樂、兒女情長?一個“奇”字,便暗示了詩人情感的豐富,不用直言拒絶,會心者已然明白。所以詩歌後文“無歸人”、“見廢墟”是哀,“春醪解饑劬”是樂,“共相疏”是拒絶,“耕織稱其用”是接受。陶淵明説:“劉公啊,看看我這百折千回的奇懷吧,對我來説,春酒可撫,人間可樂,叫我如何去修道呢?”平淡一字之中,卻藴藏萬千,“一芥子中藏三千大千世界”的手段,陶公可謂當仁不讓。
有學者敏鋭地指出陶詩有力,但卻認爲這是因爲詩中多有“鋒芒畢露”的“狠重的字眼”,(82)魏耕原《陶淵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82。似乎過猶不及。偶爾,如“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其二)的“擲”和“騁”,如“崩浪聒天響”(《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其二)的“崩”與“聒”,的確煉字之迹明顯。但更多時候,陶淵明用字拙中見奇,淡而彌厚,是自在樸素而包孕深廣。故惠洪説:“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83)惠洪《冷齋夜話》,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3。王世貞説:“淵明托旨沖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84)羅仲鼎《藝苑卮言校注》卷三,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頁130。類似意見還有很多,不贅引。除了前面提到的例子,再譬如“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時運》)之“翼”, “中夏貯清陰”(《和郭主簿》其一)之“貯”,從這些廣爲前人稱道的字句入手體會,恐怕更能瞭解陶詩的真際。這樣,也就不會産生“見南山”“在藝術表現力上,似均不及‘望’字突出”的想法,並以此肯定“悠然望南山”了。(85)鍾書林《隱士的深度: 陶淵明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188—189。另范子燁也有類似看法,見范子燁《悠然望南山——文化視域中的陶淵明》,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頁327—328。
至於字法上“放”的特色,主要來源於陶詩對虚詞的運用。這一點錢鍾書《談藝録》中已論及,魏耕原舉證尤詳。(86)魏耕原《陶淵明論》,頁197—200。今引證錢默存語於此:
唐以前惟陶淵明通文於詩,稍引厥緒,樸茂流轉,别開風格。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孰是都不營,而以求其安”;“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日日欲止之,今朝真止矣”;其以“之”作代名詞用者亦極妙,如“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87)錢鍾書《談藝録》一八,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頁177。
“樸茂流轉”,正是放逸之意。
(二) 句法
陶詩句法的力量感有兩種,一種樸拙,一種高奇。明代許學夷説:“靖節詩,語皆自然,初未可以句摘,即如東坡所稱(中略)等句,亦不過愛其意趣超遠耳。非若靈運諸公,用意琢磨,可稱佳句也。”(88)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105。因此這裏所謂的高,不是修其辭之高,而是意思上的不俗不凡和表達上的自在輕盈,如方東樹評《移居》二首云:“只是一往清真,而吐屬雅令,句法高秀。”又評《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云:“‘開春’已下,照常敍説,只爭句法秀出耳。”評《贈羊長史》:“高妙疏遠,筆勢騫舉。”所謂“高秀”、“秀出”、“高妙”、“騫舉”等等,都是對“高”的描述。而“奇”,是更在“高”之外,有特出之見識與風度,也可以借用方東樹對《飲酒》二十首的描述,即“人有興物生感,而言以遣之,是必有名理名言,奇情奇懷奇句,而後同於著書”。(89)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頁107,108,109,111。這類“奇”句,如方氏所言,在《飲酒》詩中俯仰即是,無煩多舉例。
樸拙之句與高奇之句在陶詩中相融相生,其關係正與前述“拙”與“介”的關係相同。蘇東坡語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90)惠洪《冷齋夜話》,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3。將這一特色説得極明白。所以句法的力量感常常由樸拙之句與高奇之句的交織來實現。這種交織大概有三種情形: 一是字面樸拙而意藴高奇,《飲酒》、《雜詩》、《擬古》、《詠貧士》等組詩往往如此。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三有云:“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 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驅,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91)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三,《歷代詩話》,頁507。二是在前後娓娓如家常語的詩句中嵌入一二高句奇句,二者互相生發,便知平淡中原自有高情深致,使讀者不至誤以爲只是淺淡。清人馬位《秋窗隨筆》:“人知陶詩古淡,不言有琢句處。如‘微雨洗高林,清飇矯雲翮’,‘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詩固不於字句求工,即如此等句,後人極意做作不及也,況大體乎?”(92)馬位《秋窗隨筆》,《清詩話》,頁827。此處所舉各句正可作爲例證。第三種情形則可視爲第二種的鏡像,即前面已經提及的,在動蕩、憤懣中着一二静淡之語,而詩人的胸次、詩歌的境界全出。
(三) 章法
前面分析《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詩時已經可見,陶詩並不像一般所想象得那樣平鋪直敍,無論是有意經營的結果,還是出於他“奇懷”的流露,總之陶詩存在高明的章法。通過開展、收束、斷裂、轉折、遞進、分承等各種方法,詩歌正如“龍躍天門,虎卧鳳閣”的王右軍書法一樣,夭矯舒卷,變化多端。明明語言是樸拙的,但章法的奇縱,卻讓樸拙的用字造句生動無比。所以論陶詩的力量,也一定要結合字法、句法、章法三者而觀之。
清人丘嘉穗在分析《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詩時説:“陶公詩多轉勢,或數句一轉,或一句一轉,所以爲佳。余最愛‘田家豈不苦’四句,逐句作轉。其他推類求之,靡篇不有,此蕭統所謂‘抑揚爽朗,莫之與京’也。”(93)丘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246。這裏即以此詩爲例,作一分析。詩云: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顔。遥遥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94)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227。按,“耒”字,袁本作“禾”,誤,今從蘇寫本改之。
第四句“自安”是詩之眼,卻不開門見山,而是從“歸有道”説起,便是高處落筆,自然不凡。由衣食爲道,到衣食需營,是順承,而自營始能自安,就是遞進。於是詩歌便自然生出兩層意思,一是以自營衣食爲歸之道,“開春”句到“風氣”句,正是寫這一層。“開春理常業”二句是概説,即春耕秋收之意。如何是“常業”?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所以是常業。後面四句就是對“常業”的具體描繪。“晨出”二句是一天的勞作情景,也是每天不變的狀態。寫了一日,再寫四時,“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早晚都比平地上冷,春天暖和得遲,秋天冷得早。然後總結前四句説“田家豈不苦”。但詩歌馬上轉折,“弗獲辭此難”,這就轉出詩歌的第二層意思,也是中心的意思: 自安。“四體誠乃疲”,轉折,説明“苦”;“庶無異患干”,再次轉折,解釋何以“安”。下面再用具象來説明“自安”的生活狀態:“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顔。”後二句,再遞進,求知己于古人,這是“自安”的心理狀態。最後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即以“自安”作結。全詩意思有層層遞進,有轉折,結構上層次分明,寫法上有概括有描述,有分有合。章法靈動多變,並不是流水賬的平鋪直敍。思想上看得透,行動上做得出,語言上甘於樸拙,這是陶詩質厚處;而詩歌内在的流動變化,正是詩心的流動變化,則讓詩歌透出剛勁婀娜之氣韻。蘇軾稱讚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真是獨具法眼,無愧陶淵明的千古知己。
何以陶詩章法能如此夭矯頓挫呢?顧隨曾説:“詩人有兩種: 一爲情見,二爲知解。中國詩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見的路。”“陶公之詩與衆不同,便因其有知解。”(95)顧隨《駝庵傳詩録》,《顧隨講中國古典詩詞》,頁79。這是極富洞見的區分和判斷。顧先生解釋説:“情見就是情,知解就是知。”(96)同上。“情見”和“知解”大約近于我們常説的感性和理性。一般詩人偏感性,陶淵明則偏在理性一邊,又不缺感性。在中國詩歌的源頭處,這種區分就很明顯。《頌》、《大雅》和部分《小雅》是知解的,而《國風》與《楚辭》是情見的。鍾嶸《詩品》中,上品詩人除了阮籍源出於《小雅》外,其他詩人的源頭不是《國風》就是《楚辭》,足見顧隨所言不虚。除了情感的一面,魏晉以來詩歌還有另一個重要源頭和創作特徵,就是曹植開創的賦法鋪陳的寫作方式。黄節《曹子建詩注序》論曹植詩:“驅屈宋之辭,析揚馬之賦而爲詩。”(97)黄節《黄節注漢魏六朝詩六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317。此説最爲有見。所以六朝詩重鋪陳,鋪陳就是横向地在描寫平面上的展開。
陶淵明的詩歌卻不同於情見的和鋪陳的詩歌,他章法上的源頭應該是阮籍。這一點上,方東樹最有慧眼:“阮公、陶公艱在用意用筆,謝、鮑艱在造語下字。”(98)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頁110。阮籍、陶淵明的詩,都是以意運章,所以篇章佈局是順着詩人相對理性的思考來展開的。思想的開合頓挫,必然造成章法上的開合頓挫。因此陶詩的章法是線性的,在曲折回繞的過程中湧動向前。
五 結 語
本文分三方面論述了陶詩的力量的來源和呈現方式。陶詩深藏大力,當可無疑。貫串三方面的是一個基本特徵,即平實樸拙與沉鬱耿介的交織互生。前者提供承載包容之力,後者提供超拔絶俗之力。而尤需注意,二者的關係是相融相生,使質樸中深藏兀傲,憤懣時不失深厚,這纔是陶詩力量的最顯著特色。清人李懷民《紫荆書屋詩話》云:“凡詩於諧處看其傲岸,朱子所以謂陶公是負性帶氣人也。”(99)李懷民《紫荆書屋詩話》,韓寓羣主編《山東文獻集成》(47),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97。大是知言。而王夫之《俟解》中有段話,可以作爲陶詩力量的注腳:
堂堂巍巍,壁立萬仞,心氣自爾和平。强如壯有力者,雖負重任行赤日中,自能不喘,力大氣必和也。毋以簞豆竿牘爲恩怨,毋以婦人稚子之啼笑、田夫市販之毁譽爲得失,以之守身,以之事親,以之治人,焉往而生不平之氣哉!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卑下之必生於慘刻也。學道好修之士,自命爲豪傑,於此亦割捨不下,奚足以與於仁!(100)王夫之《俟解》,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85—86。
以人觀詩,可以看到陶詩的力量;以詩觀人,正可以説這種力量是陶淵明爲仁人的明證。
陶詩的力量,申説如上。更進一步,除了研究陶淵明其人其詩,本文還有另一層目的。我始終認爲,文學史的研究當以文學研究爲歸宿。當學者試圖巨細無遺地指認並勾勒出文學史上的每一條線索時,試圖發現並填補文學史的每一個空白時,我們不能忘記,這樣做的目的是理解文學、研究文學,而不是遺忘文學。傑出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應當占據文學史研究的核心位置。經典作家作品的影響絶不僅僅局限在文學上,他們早已全面浸潤在本民族文化,甚至一些異民族文化的肌理經脈之中。從語言、審美到人生態度、言行方式,甚至草木之欣賞,飲食之烹饌,無不回蕩着經典的聲音。對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果不能深切地理解,那也談不上傳統的繼承,更加談不上發展出新。程千帆先生曾强調文學作品的核心地位説:“文藝學與文獻學兩者有個結合點,那就是作品,首先要把作品弄得很清楚。”(101)徐有富《程千帆先生談治學》,《文獻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方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使作者的心靈和它所依托的時代浮現出來。就是要認識作品真正的美。(中略)我們無論用哪種方法從事研究,都必須歸結到理解作品這一點上。”(102)《訪程千帆先生》,鞏本棟編《程千帆沈祖棻學記》,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93。張伯偉總結並引申程千帆先生的學術理念説:“所謂文學研究的方法,其區别于哲學或史學研究方法的關鍵,就在於其研究對象離不開文學作品本身。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學的歷史和理論;不深入理解作品,文學的歷史和理論就只是表層現象的描繪或似是而非的議論。”(103)張伯偉《“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程千帆先生詩學研究的學術史意義》,《文學遺産》2018年第4期,頁164。陶詩這樣的典範作品,自然應該得到文學上最充分的討論。拙文致力於此,至於所得深淺如何,敢請方家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