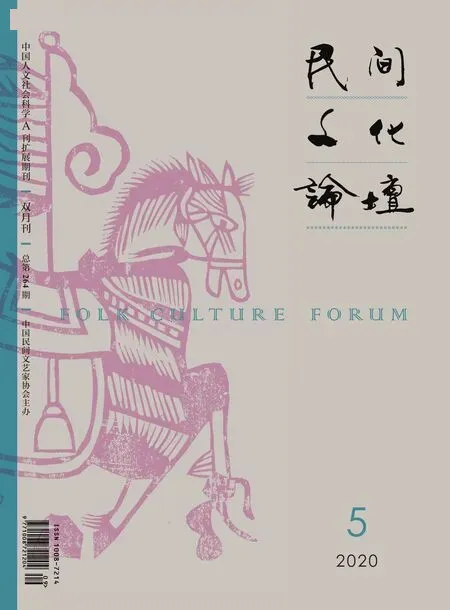《格萨尔》的故事*
降边嘉措 口述 王素珍 周利利 整理
一、两个故事——红军长征的故事和《格萨尔》故事
我出生在康巴地区,即四川甘孜州巴塘县。巴塘县就在金沙江边,过了江就到了西藏。我们家乡地处茶马古道核心地段,过去号称“五省通衢”。西康省解放后并入四川省,就是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那里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交汇的地方,也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人们常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难与悲壮,雪山、草地都在我的故乡,我的家乡也是《格萨尔》广泛流传的地方,我是听长征的故事和《格萨尔》故事长大的。
我出生的时候刚好红军从我们那儿过去,留下了许许多多关于红军的传说和故事。受此影响,我写过这方面的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红军从我家乡过》。
我从小就爱听大人唱歌、讲故事。大家都说,藏族是“歌舞的海洋”。藏族人会走路的时候就会跳舞,会说话的时候就唱歌,民歌、歌舞非常丰富。我觉得在这个“歌舞的海洋”里,最主要的民间艺术有三种:一种是热巴舞,再一个就是藏戏,第三个就是《格萨尔》说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三种流浪艺人里,《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生活最苦、社会地位最低。《格萨尔》说唱艺人被称作“乞丐”,是真正的流浪艺人。农奴制度很残酷,所有农奴生下来的孩子都有主人,都要交人头税,热巴艺人也好,藏戏艺人也好,都要交,但是《格萨尔》说唱艺人不需要交“人头税”。他们交什么呢?乞讨税。后来我到了北京,也有机会去世界别的国家和地区,发现世界上很少有乞讨的人还要交“乞讨税”的。可见在封建农奴社会,《格萨尔》说唱艺人地位是非常低的。
藏族地区山高水深,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土匪很多,社会不安宁,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部落仇杀、武装械斗。说唱艺人要自己一个人云游四方,说唱《格萨尔》,是很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危险的,因此他们常常跟朝佛的香客、热巴艺人或者马帮走。马帮给他点儿吃的,他就给他们演唱。我从小就听艺人讲《格萨尔》故事,这是我和《格萨尔》的渊源。
另外,我对艺人的生活、对马帮也有一些了解。我的外公就在一个马帮,我和他们接触得比较多。马帮的生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种浪漫,也是很苦的。所以,我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化艺术的熏陶,对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有比较深的了解,感同身受。这两件事情后来对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格萨尔》研究小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很重视。早在1952 年,青海省文联就成立了《格萨尔》研究小组,开展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青海省文联是在五省藏区里成立最早的一个文联,文联主席就是程秀山同志。程秀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和贾老他们一起,都是在周扬同志领导下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是我们党内第一批从事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
1955 年,我第一次到北京。1956 年,我到北京参加“八大”的翻译,并留在中央民委翻译局工作,专门翻译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后来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合并了。
1958 年民研会要搜集整理《格萨尔》,中宣部批准民研会的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关于《格萨尔》工作的第一个文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58 年搜集整理《格萨尔》,作为1959 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的献礼。同时还开展了“新民歌运动”,民研会组织收集采录新民歌。民研会当时就两件事大:一个是新民歌;一个是《格萨尔》。
1958 年藏族新民歌收集得很多,民研会在领导和组织这个工作。民研会没有懂藏文藏语的人,主要靠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和西藏公学(即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的学生搜集新民歌,并决定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我爱好文艺,领导上就把编辑出版藏族新民歌的任务交给了图旺同志和我。图旺同志是一位很优秀的翻译,曾经给毛主席当过翻译,我给周总理当翻译,他翻译水平很高,也比我大几岁。我们翻译、编辑藏汉对照民歌,我们国家的第一本藏族的民歌《藏族新民歌》,就是1959 年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工委书记张经武写的序言。藏族新民歌很多是翻身农奴唱的,有些也不是。大量的还是藏族民歌,是群众自己创作的,其中也包括仓央嘉措的情歌,与新民歌一起收集。那时候毛主席号召“采风”,郭沫若和周扬编《红旗歌谣》,我们把《红旗歌谣》翻译成藏文。民研会的规格很高,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是周扬、钟老(钟敬文)他们这些德高望重的大家名家。
《格萨尔》的收集整理工作是1952 年开始的,1958 年达到高潮。中宣部颁发的两个文件,现在看来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一个是要求有关部门组织编写《藏族文学史》,另一个是要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搜集整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格萨尔》工作在五省藏区,加上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涉及范围几乎包括半个中国。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当时西藏还没民主改革,编写《藏族文学史》的任务就交给了中央民族学院。青海比较有基础,收集《格萨尔》的主要任务就交给了青海,其他藏区配合。青海文联负责,主要是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蒙古族)、文联主席程秀山两位主持工作。我的老家四川藏区即康巴地区,是《格萨尔》广泛流传的地方,也开始收集,收集了很多资料。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意识到民间说唱艺人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收集了一些手抄本、木刻本,然后组织翻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参与这个工作,到青海发现有《赛马称王》《英雄诞生》《霍岭大战》等二十多部、七十多本“异文本”。“异文本”这个概念首先是西北民族学院的王沂暖教授提出来的。就是说,同样一部《赛马称王》,有西藏的艺人讲的,也有青海地区、四川藏区的艺人讲的,故事内容基本相同,但又有差异,各有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所以称作“异文本”。
这一时期《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出版工作,由民研会指导,主要在青海进行,取得了很大成绩,具有开拓性、开创性的价值和意义,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尊重。
1959 年,我们国家下了很大的工夫,为建国十周年国庆献礼,最后献了什么?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半部《格萨尔》藏文本。从1958 年发文件到1959 年,才整理出版《霍岭大战》上部,因为《霍岭大战》篇幅很长,分上下两部。下部经过二十多年,在改革开放后才出版,可见工作之艰难。
回顾新中国以来的历史,我认为我们《格萨尔》的事业与我们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运昌盛,《格萨尔》事业就发达兴旺。
三、到社科院从事《格萨尔》研究
1979 年中央主持召开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人们普遍认为四次文代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很多老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说:文艺的春天来到了。我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但不是代表,我给参加会议的藏族代表担任翻译。
当时钟老好像还没落实政策,但是他出席会议了。民研会的代表主要是贾老(贾芝),马老(马学良),马老后来担任民协的副主席,又是我们少文所的副所长。还有王沂暖教授和西藏等地的藏族代表,他们在这个会议上一起提出,要为《格萨尔》平反昭雪,得到周扬等领导同志的支持。“文革”期间受到批判的作品很多,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在全国的文代会上,大家一致提出要求平反的只有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这也说明《格萨尔》有它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影响面很广。
1979 年的文代会意义十分重大、十分深远,民研会是在这一年恢复工作的,少数民族文学所也是这一年酝酿筹备,于1980 年成立的。贾老是我们所的第一任所长,副所长是马学良和冷拙。那时民研会和少文所的物质条件很差,连办公地点也没有。两个单位的主要领导是重叠的,业务上有联系,关系十分密切,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我认为80 年代初是我国民间文学的黄金时期,也是《格萨尔》事业的黄金时期。
我是1980 年报考社科院的。当时社科院面向社会招生,这是社科院成立以来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招聘科研人员。当时我们报考的人有八九个,借中央民族学院少语系教室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主任是格桑居勉,他是中央民族学院少语所的教授,成员有贾芝、马学良、马寅,还有刘魁立。马寅是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司副司长,是延安来的老八路,也是民族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兼少文所筹备领导小组成员。我报考的是副研究员,答辩进行了三天,我被录取了,成了当时我们国家藏族的第一个副研究员,也是我们所的第一个副研究员。
贾老和马老问我的打算。我说:“我过去长期从事翻译出版工作,业余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我还是想一边搞文学创作,一面搞当代文学研究。”我也知道,在文学所不搞研究是不行的。贾老说:“你有从事翻译的经验,自身的经历也很丰富,写小说是可以的,这是好事儿,我们支持。但是你了解藏族史诗《格萨尔》吗?”我说我知道《格萨尔》。贾老和马老让我讲讲。我就汇报了我对《格萨尔》的了解和认识。
贾老说:“让你研究《格萨尔》行不行?”我说:“我搞不了。”我知道《格萨尔》精深博大,很难,在过去24 年的时间里,我翻译了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也看过黑格尔等西方学者关于史诗的论述,所以,我对西方文化,希腊史诗、印度史诗也并不陌生。我就知道研究史诗是很难的。
后来贾老就问:“如果组织上要你搞,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格萨尔》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真的是很伟大,我从小就听艺人讲,印象很深。中国有史诗,而且是很伟大的史诗,我们应该做好收集整理工作。这个工作解放初期就开始进行了。现在西藏师范学院(即西藏大学的前身)的旦真他们几位老师就把扎巴老人找来,成立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格萨尔》研究所。旦真老师是马学良先生的学生,他们正在记录整理《格萨尔》艺人扎巴老人的说唱本。据说,扎巴老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说唱艺人,在峨眉会议上,被称赞是“国宝”。旦真他们提出要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格萨尔》学。我们相处几十年,经常交换意见。我认为他们讲得很有道理。因为我翻译过马列著作,而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藏文的第一版是我参与翻译的。所以,我在他们的意见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发挥,当时我就提出,应该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
贾老他们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有很深的了解、有深厚的感情。他们都认为我关于建设《格萨尔》学的设想很好,有创造性,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贾芝是少文所所长、马学良是副所长,好像我已经是所里的人,开始给我布置任务了:以后来所了,要深入研究,不断完善。
社科院向全国招聘人才,当时作为一件大事,新华社发消息,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文中提到:降边嘉措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学体系是很有建树的,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①1980 年9 月26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社科院向社会公开招聘科研人员的消息,其中特别提到,降边嘉措提出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学科体系的观点,很有创见性,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消息。
我看了报纸以后赶紧跑到民院去,对马学良先生说:我说得很清楚,这不是我提出,是西藏师范学院的老师们先提出的,我只是按照我的理解做了一些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学体系”的发明权是西藏师范学院的。马老说:“说是你提出来的,也没有错。你提出这个观点是好事,评委给予鼓励也是应该的。”
我就这样被录取了,胡乔木院长亲自签署聘书。1 月8 日我就到院部报到,10 日贾老和马老就找我谈话,任命我担任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他们两位都是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的老人,强调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立的第一个专门从事藏族文学研究的机构,说明社科院和国家民委领导对藏族文学事业非常关心和重视。
两位领导讲得很对,我也是“老民委”,知道他们谈话的分量。少文所的藏族文学研究室不但当时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藏族文学研究室,40 年的时间过去了,就是在现在,也是唯一一个。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至今也没有专门从事藏族文学研究的“藏族文学研究室”,都是在别的部门兼顾着做一点。就这样,他们郑重地把研究《格萨尔》的任务交给了我。
四、80 年代《格萨尔》研究
(一)“做好抢救工作,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贾老和马老对我说:“做好抢救工作,是当前的第一要务。”1980 年4 月,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被称为“峨眉会议”。西藏的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开展搜集整理的情况,特别汇报了扎巴老人的情况,说他是一位著名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他的演唱内容非常有特点。萨空了和贾芝充分肯定了西藏同志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称赞扎巴老人是一位国宝级人物,应该很好地加以保护,做好扎巴说唱本的记录整理工作。“峨眉会议”以扎巴老人为例,强调了做好搜集整理工作的迫切性。
贾老说:为了加强对全国《格萨尔》工作的指导,经中宣部批准,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和社科院成立全国《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国的《格萨尔》工作,办公室就设在我们所。其范围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7 个省区,学术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贾老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开展了,《格萨尔》不但是藏族文学室的重点,也是我们所的重点课题,也是民研会的重点工作之一。贾老和马先生都是民研会的副主席,而周扬同志既是我们社科院的副院长,又是中国文联主席兼民研会的主席,直接领导两个单位。
不久,院里正式任命贾芝同志担任全国《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任命我为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藏族文学研究室和《格萨尔》协调小组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
我1 月份报到,3 月底就去拉萨,到西藏大学,那时还叫西藏师范学院。我找扎巴老人,采访他们,还有玉梅,一位著名的女艺人。当时西藏社科院没有成立,西藏大学也没成立。我们1980 年就开展工作,一方面收集整理《格萨尔》,另一方面协助、帮助各地建立协调小组,并开展工作。
概括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救人,重新组织队伍。按当时的政策,允许用招生的办法来调干部,解决户口问题。我们所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格萨尔》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这在《格萨尔》事业发展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50 年代初是《格萨尔》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第二个黄金时代是80 年代初期和中期。所以说,《格萨尔》事业和国家的命运真的是连结在一起。
(二)《格萨尔》研究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983 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第一次把哲学社会科学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这一次规划会议是在桂林开的,被称之为“桂林会议”。我参加了桂林会议,遵照周扬副院长的指示,我们在会上提出,建议把《格萨尔》纳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马学良先生说,编写《藏族文学史》很重要,中宣部早有指示,还专门发文件,建议把《藏族文学史》的编写任务,也纳入国家项目。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的审议,一致通过。当时全国关于少数民族学科,纳入“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的就这两项:一是《格萨尔》研究,另一个是《藏族文学史》。
1984 年中宣部发了文件,决定成立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刘魁立担任组长,我为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关鹤童(文化部民族文化司司长)、殷海山(国家民委文化司司长)、陶阳(民研会书记处书记)担任副组长。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7 个省、区都有人参加。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就从那时开始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了工作。
桂林会议之后,1984 年我们在拉萨召开了7 省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大会,这是全国第一次召开《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会,影响很好。
(三)《格萨尔》走向世界
1985 年2 月是芬兰著名英雄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 周年,民研会组织代表团,贾老是团长,成员有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绳武(他负责主持翻译《卡勒瓦拉》汉文版工作),还有民研会一个翻译一起去了芬兰。
贾老在大会上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我讲《格萨尔》说唱艺人,主要介绍了扎巴和玉梅,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芬兰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我们代表团的活动,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①芬兰报纸在介绍记者招待会的情况时说:“各国记者只向中国代表提问。”《土尔库报》《晨报》《赫尔辛基报》等各大报纸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中国代表的发言,并配发贾老和我的照片。芬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反复播放有关信息,说:“中国是一个史诗宝库,史诗在中国还活着。”评论说,“这是一个使人们感到极大振奋的新消息。”
我们参观了芬兰少数民族学会、他们的档案馆、关于《卡勒瓦拉》的资料。《卡勒瓦拉》资料当时也很多、很重要,保存得也很好。那次会议上,有一位教授叫杭柯,另一位叫海希西,他们对贾老和我说:“你们的《格萨尔》很重要,《格萨尔》应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两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术委员,可以提供帮助。”海希西当即邀请我到波恩大学参加中亚史诗研究。
回国后,我立即向院领导和钟老汇报,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件事。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世界非遗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6 年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的教授,他到美国访问以后,知道有世界非遗公约,认为很重要,回国后他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说我国应该加入。那位教授只是建议,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但提出建议,而且写了具体方案,并且得到我们院领导和钟老等民协领导的支持。②1985 年上半年,在我院领导和钟老、贾老等专家学者支持下,我正式提出应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格萨尔》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但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学领域里的第一份“非遗”报告,就全国来说,也是继侯仁之教授之后的第一份。《格萨尔》在很多方面真的是走在全国民族民间文学和藏学研究的前面,起到了引领和带头的作用。这是《格萨尔》本身的价值,西藏问题有其重要性也是一个原因。
1986 年,《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昔日乞丐,今日国宝,扎巴老人昂首挺胸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嘉奖,他老人家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高兴。
(四)民研会与《格萨尔》事业
民研会即现在的民协,成立至今整整70 年了。我自己觉得,民研会的工作与我国的《格萨尔》事业有着密切联系。从50 年代开始,全国的《格萨尔》工作就是在民研会的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我们少文所,实际上是三重领导,即国家民委和社科院直接领导,给经费,给编制,而民研会在业务上给予指导。这与当时的领导人有很大关系,周扬同志既是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又是文联主席,民研会主席;还担任我们社科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这几个部门都归他直接领导。钟老、贾老、马老三位老同志也在这几个部门担任领导。
钟老对《格萨尔》工作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他多次说过:《格萨尔》不但是我国藏族同胞的,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人类的文化遗产。他晚年在友谊医院住院的时候还把我叫去,让我汇报工作。钟老对《格萨尔》的翻译工作非常关心,语重心长地说:降边,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格萨尔》的翻译,你要把这个工作负责起来。你现在在编精选本,藏文《格萨尔》精选本40 卷,你要把它翻译成汉文。后来钟老口述,让我的博士生周爱明③周爱明现任《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记录,给中国社科院、国家民委等几个部门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翻译工作。贾老也很关心和重视翻译工作,生前抱病给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
因此,那时是我们《格萨尔》工作的黄金时期,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