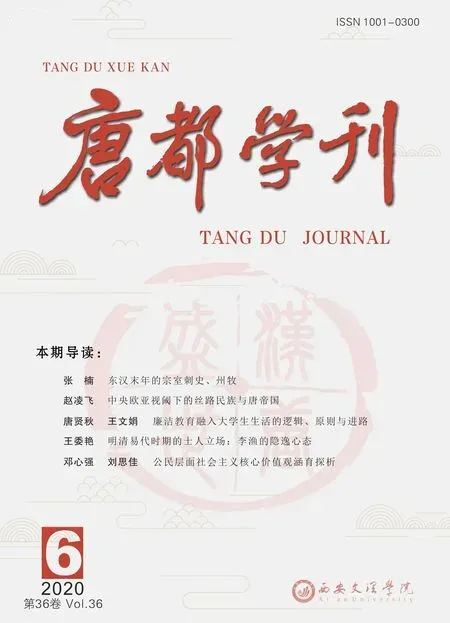明清易代时期的士人立场:李渔的隐逸心态
王委艳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在朝代更替之际,尤其是在汉族政权与外族政权鼎革之际,对于来自旧朝的文人来说,摆在面前的选项并不多,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拼死抵抗,为旧朝死节;二是归降新朝并为其服务;三是采取与新朝不合作态度,隐逸。在明清鼎革之际,上述三种方式都有所表现。在文学创作中,表现这种“易代心态”之作便形成一种创作倾向,“即以清初而论,异族入主带来了强烈的心理震荡,故文坛形成了汉族(特别是江南)士人孤愤兴寄之作的创作主潮。而随统治者政策的张弛,以及士人个性的差别,此类作品或慷慨或低徊,或显豁或隐晦,手法与风格千姿百态。”[1]陈洪的文章写于1998年,很显然,他注意到了发生在17世纪的明清鼎革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而对于17世纪的通俗小说而言,由于小说的文体特征,无法如诗歌直抒胸臆,“易代心态”的表达也更为曲折隐晦。
如果说《型世言》中道德说教的增加说明了明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以及作者对明末社会道德问题与时代危机之间的关联的思考,那么易代之际在李渔话本小说中则表现了另一种情况:隐逸心态。
一、《连城璧》:李渔的“中间人”心态
李渔(1611—1680),浙江兰溪人,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在明末参加童子试,以五经见拔,后参加乡试屡挫。后经历清兵江南屠杀,劫后余生,作《丙戌除夜》:“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明清鼎革之后,李渔便绝意仕进,自谋生路了。在古代,对于离开土地的读书人来说,生存是非常艰难的。李渔采取各种方法谋生,小说创作、戏剧创作、搞家班、刻书卖书等等。同时,游走于官绅之间以获取资助。此多为后人诟病。李渔与仕清、抗清者不同的是,他所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既不仕清又不抗清,绝意仕途,采取隐逸态度以表明立场,生存上又不得不依靠新朝廷中人来获取资本。因此,李渔的“中间人”心态是其易代心态的突出表现。既要显示自己对旧朝的忠,又要在新朝获得生存空间,这对于李渔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没有张岱的家底,没有王夫之的名望,只有满腹才情。李渔在明朝只是一介布衣,没有一官半职,而后人之所以对他有苛责要求,完全是因为他的才华与成就。李渔不食禄于明朝,却依旧为旧朝守节,虽不彻底但与那些降清的明朝文臣武将相比,其行为已经可圈可点、难能可贵了。李渔忍辱偷生于改朝换代之际,不但用诗歌记录了战乱之际南方遭遇的天灾人祸,记录了清军过处的烧杀抢掠、屠城民死的现实,并因此被称为“诗史”[2],而且其小说也曲折反映了李渔的“易代心态”。
经历明清易代的李渔,对于易代之际社会上各色人等的表现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对于他们选择的对待新朝的态度,也有自己的明确立场。李渔在《连城璧外编》卷1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议论:
话说忠孝节义四个字,是世上人的美称,个个都喜欢这个名色。只是奸臣口里也说忠,逆子对人也说孝,奸夫何曾不道义,淫妇未尝不讲节,所以真假极是难辨。[3]185
时代鼎革,各色人等有各种表现,鱼龙混杂,难辨真伪。李渔借评论被虏妇女对各色人等的表现进行了个人的价值判断,他把守节而宁死不屈者尊为“最上一乘”;把勉强失身,自悔投河者做“中上”;把“身随异类,心系故乡,寄信还家,劝夫取黩”者为“中下”;而对于那些依附新贵,抛弃旧主者则为“最下一流”。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判断。李渔小说集《连城璧》刊刻于清朝初年,这些小说均取自明事,其用心昭然。李渔应该非常清楚,对于他个人来说,做到“最上一乘”或者“中上”是非常难的,在这篇小说(“落祸坑智完节操 借仇口巧播声名”)中,李渔塑造了一位“虽不可为守节之常,却比那忍辱报仇的还高一等”的耿二娘形象,耿二娘用各种技巧和智慧使掳掠她的强盗不能行奸淫之实,并且利用自己的智慧将强盗打死复仇,并借强盗之口证明自己没有失节。可谓智勇双全。但李渔非常清楚,耿二娘虽然保全了贞洁,但并非全节,除未被奸淫外,其身体也已经被强盗猥亵。因此,在叙述故事之前,专门提醒“看官”莫以“《春秋》责备贤者之法”苛求。按照李渔的观点,“末世论人”是不能苛求的,能保全最基本的贞操就已经非常难得了。在明清易代、生命朝不保夕的时节,目睹清兵屠城惨祸,又目睹多少明朝文臣武将屈节仕清的社会现实,李渔对于生存的艰难是有非常清醒认识的。能够保持最基本的节操,在“末世”已经难能可贵了。因此,李渔基本走了一条中间路线:既不屈节仕清,又要忍辱偷生。
李渔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表达自己的这种“中间”路线。在《连城璧》子集“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中,谭楚玉和刘藐姑追求婚姻自由而不惜跳江殉情,被莫渔翁救起,谭楚玉发奋读书,终于中举做官。这应该是一个大团圆结局,但李渔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叙述谭楚玉做官期满进京、拜访莫渔翁的情节。小说这样叙述谭楚玉思想的变化过程:
谭楚玉原是有些根器的人,当初做戏的时节,看见上台之际十分闹热,真是千人拭目、万户倾心,及至戏完之后,锣鼓一歇,那些看戏的人竟像要与他绝交的一般,头也不回,都散去了。可见天地之间,没有做不了的戏文,没有看不了的闹热,所以他那点富贵之心还不十分着紧;如今又被莫渔翁点化一番,只当梦醒之时,又遇一场棒喝,岂有复迷之理?就不想赴京去考选,也不想回家去炫耀,竟在桐庐县之七里溪边,买了几亩山田,结了数间茅屋,要远追严子陵的高踪,近受莫渔翁的雅诲,终日以钓鱼为事。[3]17
人生如戏是李渔一生坚持的价值观。以戏场点化人生,曲终人散、人走茶凉,这种人生境遇对于李渔来说已经看破。谭楚玉的退隐无疑是李渔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既要为旧朝守节,又要在新朝生存,对于李渔来说并非易事,经营家班,奔走于权贵之间以取得秋风之资,搞创作、搞刊刻、搞画谱、搞园林等等,无不为获取生存资本而为之。因此,李渔的“中间人”路线有着难以回避的人生境遇和社会现实。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4]“绝意浮名”,不仕清,也许是李渔坚守的对于明朝最底线的“守节”之举,对于饱读诗书的李渔来说,不参加新朝科举是需要勇气,也需要付出代价的。“明清鼎革不仅改变了李渔的人生道路,而且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虽然清朝文网甚严,李渔还是勇敢地将他对明清鼎革的认识和态度比较曲折、隐晦地写进了他的话本之中。”[5]
李渔在其小说中,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的这种不屈节又要生存的“中间人”心态,可以说,这种取中心态是李渔在鼎革之际采取的基本行为方式。也许李渔这种不屈节仕清不能完全将之归入为明朝“守节”,因为对于李渔来说,在经历家乡金华被屠城,“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1)参见李渔《婺城行吊胡仲渊中翰》。“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2)参见李渔《婺城乱后感怀》。,这种经历是惨痛的,是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对于李渔来说痛彻心扉。因此,李渔是宁肯乞讨也绝不触碰人生底线(屈节)的。在《连城璧》寅集“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中,指出家国乱离之际,乞丐中也“尽有忠臣义士、文人墨客隐在其中”[3]27,李渔也许怕读者看不明白,把正话故事放在了崇祯末年,而且加以强调故事发生的年代:“那个忠臣义士,去今不远,就出在崇祯末年。”[3]30李渔将明末鼎革之际的文武百官与乞丐进行对比,来说明自己对于当时人各种行为的看法,显然,李渔更赞成不屈节而不得已忍辱偷生的乞儿,而不是“尽皆逃窜”的文武百官。联系李渔类同乞儿的人生经历,不难体会,李渔借小说舒块垒的复杂心态。
李渔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他的这种“中间人”态度。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写“冬青”“不居名”“不矜节”“不求人知”[6],也许正是李渔之追求。“不屈节”和要“生存”在行动上表现为“不合作,不抵抗”,颇受误解,“而他又不能明言,于是只好借助于文学作品,把真实的自我(或者说是‘自认为的真实自我’)通过借题发挥包装后表达出来;同时也把不被理解之苦闷,用文学的手法加以抒发”[7]。
二、《十二楼》:李渔式隐逸
根据李渔年谱,顺治十三年(1656),《无声戏》(后作《连城璧》)一集问世,顺治十五年(1658),《十二楼》问世。如果说《无声戏》中对于明清鼎革之时明朝文臣武将、士人等的立场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议论,对自己个人的“不屈节、不抵抗”的处事哲学有一个明确的立场,那么两年之后至《十二楼》,这种立场则缓和许多、也隐晦许多。从《李渔年谱》中可知,就在这两年间,顺天、江南、河南等地接连发生科场弊案,多人被流徙、抄没、问斩,这在清初对于读书人来说震动相当大的[8]。在《十二楼》中,少了《无声戏》的锋芒,多了游戏人生、隐逸为乐的闲情逸致。相比于《连城璧》中女性和小人物居多,《十二楼》中多文人雅士,他们的生活更加具有个人趣味,同时,李渔也更多表露心迹,将自己的个人趣味、道德追求寓于描写之中。在对个人追求的辩驳与自辩之中表现出自赏,并欣然自得。
杜濬为李渔《十二楼》作序时指出:
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殆老泉所谓“苏张无其心,而龙比无其术”者欤?夫妙解连环,而要之不诡于大道,即施、罗二子,斯秘未睹,况其下者乎!语云“为善如登”,笠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厥功伟矣![9]
杜濬从三个方面评价《十二楼》:鼓吹经传、接引顽痴、为善。并指出三个方面并非板着面孔说教,而是以通俗的语言、入情啼笑的方式进行。这与易代之际其他话本小说较多宣扬道德有所不同。这固然是李渔《十二楼》的写作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十二楼》和《连城璧》一样,蕴含着李渔不能明言的块垒,和对自己立场的辩解。李渔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其行为方式和处世之道备受指责。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大可不必对此求全责备。因为对于一介布衣的李渔来说,能够做到“中间人”状态,能够做到“不屈节、不抵抗”,采取与新朝廷不合作态度,已经难能可贵。当然,李渔也有自身缺点,如恃才傲物、游戏人生、携姬为乐等等,李渔在自己的作品中毫不掩饰自己对享乐、美姬的爱好,这就会更多给后世论者口实,或者会得出与李渔期望相反的评价:所谓守节,只不过是游戏、享乐人生、以妻妾成群为乐的遮羞布而已。但无论如何,李渔带给后人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受。
在《十二楼》中,李渔塑造了几个隐逸者形象来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在《合影楼》中,李渔塑造了路公路子由这一角色,李渔对路公这样描述:“管提举有个乡贡同年,姓路,字子由,做了几任有司,此时亦在林下”,指出路公性情:“在不夷不惠之间”[10]12。在小说中,李渔对路公的智慧倾注了大量心血,很明显李渔对于处于“不夷不惠之间”的路公持赞赏态度,因为这契合了同样在“林下”而又以智慧自得的李渔的人生哲学。李渔不愿意过清苦生活,又不愿意出仕新朝,“他希望凭藉自己的才华和他人的援引,在过上较好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能够保有自己的独立,得到社会的承认”[11]。李渔的这种“中间路线”招致世人对他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在李渔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进行辩驳。同时,李渔对于那些在鼎革之际首鼠两端、作壁上观的士人进行了辛辣讽刺,在李渔的观念里面,他是有自己做人底线的,但在文网渐密的清初政治环境中,这是不能明言的。在《十二楼》之“夺锦楼”中,李渔针对男女婚姻有这么一段议论:
未许之先,若能够真正势利,做一个趋炎附势的人,遇了贫贱之家,决不肯轻许,宁可迟些日子,要等个富贵之人,这位女儿就不致轻易失身,倒受他势利之福了。当不得他预先盛德,一味要做古人,置贫贱富贵于不论,及至到既许之后,忽然势利起来,改弦易辙,毁裂前盟,这位女儿就不能够自安其身,反要受他盛德之累了。这番议论,无人敢道,须让我辈胆大者言之,虽系末世之言,即使闻于古人,亦不以为无功而有罪也。[10]30
这里最后一句议论显得非常突兀,所谓“末世之言”与上论所及之男女婚配实风马牛不相及。但可使人联想明清鼎革之后世人对待新朝所采取的一些态度。很明显,李渔对那些趋炎附势、首鼠两端的没有信义可言的人是持鄙夷态度的。其背后的潜台词是,能够在时代剧变之中坚守志向是非常不易的。
在《三与楼》中塑造了一个“喜读诗书不求闻达”的高士虞素臣形象,此人绝意功名、寄情诗酒,又喜好构造园亭,这简直是李渔自身的翻版。此人尊奉“弃名就实”,所谓“三与楼”,即与人为徒、与天为徒和与古为徒,谦逊、隐逸、弃虚就实。这符合李渔的性格特征,是李渔对人生的一种期许。虞素臣及其子虞继武都是光明磊落,与人为善之人,与唐玉川父子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李渔所推崇的理想人格。
明清鼎革之后,李渔放弃举业,但他必须生存,必须养活家人,尤其是李渔举家移居杭州之后,生存问题一直是李渔面临的首要问题,而李渔择业是有选择的。他在《十二楼》之“萃雅楼”中,借人物之口写道:“我们都是读书朋友,虽然弃了举业,也还要择术而行,寻些斯文交易做做,才不失文人之体。”[10]133在这篇小说中,李渔把“书铺、香铺、花铺”说成是“俗中三雅”,再加上“古董铺”凑成“俗中四雅”。这无疑是想在市井之中寻求某种心理慰藉,在朝堂之外做些稻粱谋。“李渔虽为文人,自从移居杭州之后,实际上是行走在市井之中,先是与书坊、戏班打交道,后来是自己开书坊刻书、卖书,组家班打抽丰,市井之中尽有文人之营生,花铺、书铺、香铺、古董铺,乃‘俗中四雅’,此乃李渔人生经验之总结。”[12]也许不能简单地说这只是李渔的生存之道,而是更有“隐于市”的味道。
在李渔的小说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些处于半隐状态的高人。不想做清苦的“隐于野”,而选择更能发挥自己才华、更接近自己性格的“隐于市”,并在笔墨之中寻求心灵的安顿,也许后世不应该对李渔式的“隐逸”做过多苛求。李渔的这种“中间人”姿态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十二楼》之“奉先楼”中,他劝人吃半斋:“何谓半斋?肉食之中,断了牛、犬二件,其余的猪、鹅、鸭不戒也无妨。”[10]252那么,为何不能吃牛、狗呢?因为二者都是“大德于人”,而人不可负义忘恩。接着李渔这样议论:“即以情理推之,也不曾把无妄之灾加于有功之物,就像当权柄国,不曾杀害忠良,清夜扪心,亦可以不生惭悔。”这无疑让人联想到明末时局。而在《十二楼》之“归正楼”中,对于偷儿回头,李渔也不忘逸出笔墨,议论一番:“可见国家用人,不可拘限资格,穿窬草窃之内尽有英雄,鸡鸣狗盗之中不无义士。”[10]127联想到《连城璧》寅集“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中对乞丐中不乏高人的论述,明显是李渔借小说表达自己对时事的看法。
《十二楼》之“闻过楼”是李渔集中反映自己易代心态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李渔通过塑造顾呆叟形象来表达自己鼎革之后的理想行为方式。本篇小说叙事简单,正话前有大段议论和诗词,其中心意思是表达山乡隐居之乐。小说中,顾呆叟放弃举业,退隐山林,乡绅仕宦与之结交均为听其箴言、遵其教导,并自愿出钱为其建造别业。这无疑是李渔心目中的理想生活。隐逸但不全隐,结交乡绅仕宦以获取生存之资,但不主动结交,而是以自己的才华吸引乡绅仕宦登门“求教”。顾呆叟形象无疑是李渔的理想人生,但李渔却未必有顾呆叟那样的人生境遇。
李渔通过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处世哲学和人生趣味,以半隐姿态来实现自己在“不屈节、不抵抗”和生存之间的协调。可以说,李渔的生活方式是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一种无奈选择,在明代,李渔只是无名布衣,没有张岱、王夫之的声望,因此,也不可能过张、王式的遗民清苦生活。而李渔有传统文人的基本气节,不仕清、不屈节对他来说是保持操守的底线。为了生存又不得不依靠新朝权贵,如果能够做到如顾呆叟那样让权贵主动登门“求教”,也许是李渔的梦想,这一方面可以守住节操尊严,一方面可以理直气壮地宣扬这是难以拒绝的事,不存在折节之事。但李渔很难做到。
总之,隐逸心态是17世纪明清鼎革之际,由明入清的士人多少都有的心理情结,只不过针对不同个体,其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有的完全隐逸,不与新朝合作,如张岱、王夫之;有的采取半隐,以“中间人”自居,不屈节、不抵抗,以各种方式在新朝获得生存,如李渔;有的则观望,在时局稳定之后出仕为官。17世纪白话通俗短篇小说的繁荣,很多原因来自于下层文人在时局动荡之际采取的生存之道。同时,他们的思想也就会随其创作而蕴涵其中。正如陈洪所言:“以小说的形式表现自我,是清代小说与明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不同;特别是自我指涉的成分,清代小说远远多于明人作品,如《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而李渔则是肇其端者。”[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