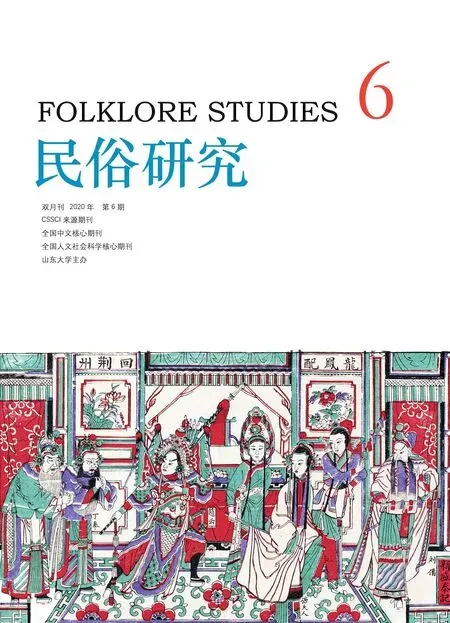柳田国男的民俗艺术研究
——以《民俗艺术》杂志与民俗艺术丛书为中心
李常清
一、前 言
“民俗艺术”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学者视野,始于“民俗艺术之会”(1927-1932)的成立及其机关杂志《民俗艺术》(1928-1932)的创办。在学会和杂志存续期间,柳田国男作为指导者之一,陆续在该杂志发表论文10篇(1)具体篇目包括:第一卷第一号的《发刊词》《提线木偶杂考》,第一卷第三号的《关于诸国祭祀日历》,第一卷第六号的《岛的历史与艺术》《八重山岛歌舞合评》(合著),第二卷第四号的《蚕神与人偶》,第二卷第六号的《风流与趣味》,第二卷第十号的《假面所见一二》,第三卷第一号的《狮子舞考》,第四卷第四号的《从钩占到儿童游戏》。,所探讨的话题涉及人偶、风流、假面、舞蹈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是由普通民众创造、享受并传承至今的民俗艺术事象。此外,《民俗艺术》杂志发行一年半以后,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俗艺术的研究,杂志主编北野博美策划出版了“民俗艺术丛书”。这套丛书共有四卷,柳田所著的《民谣之今昔》为第二卷。该著作基于丰富的资料和柳田对于民谣的深刻理解,细致考察了民谣的变迁,希冀借此了解普通日本民众的心性。在“民俗艺术”概念存续期间,柳田主要通过《民俗艺术》杂志与民俗艺术丛书之《民谣之今昔》,从民俗学的视角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如影相随的艺术进行阐释。
20世纪40年代,“民俗艺术”开始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论著中,如常任侠《民俗艺术考古论集》、岑家梧《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但此时尚未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20世纪后半叶,“民俗艺术”概念的界定一直处于混沌状态,直至21世纪,中国学者在构筑民俗学和艺术学的交叉学科之时,才开始界定“民俗艺术”等概念。在探讨“民俗艺术”时,中国学者意识到邻国日本在该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陶思炎在构筑“民俗艺术学”时指出,“民俗艺术”作为学术概念首见于日本1926年(2)实为1927年——笔者注。成立的“民俗艺术之会”,此后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在学术界。(3)陶思炎:《民俗艺术研究的历史回顾》,《民族艺术》2011年第2期。另外,吴衍发、季中扬在对民俗艺术研究史进行溯源回顾时,都提到“民俗艺术”研究起源于日本1927年成立的“民俗艺术之会”。(4)吴衍发、徐子方:《常任侠与中国早期民俗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3期;季中扬:《现代性的两面性与民俗艺术的传承困境、机遇及其应对——以湖州石淙蚕花为例》,《民俗研究》2018年第5期。
相较于中国所接受的日本民俗艺术方面的信息,日本国内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柳田国男对民俗艺术的确立所起到的奠基作用。例如,三隅治雄在民俗艺能学会成立总会的纪念讲演中,回顾了近代民俗艺能研究的历史,认为“民俗艺术之会”及《民俗艺术》杂志的出现是整个日本民俗艺能研究中的重要一环(5)[日]三隅治雄:《民俗芸能研究の歴史と現状と展望》,《民俗芸能研究》1985年創刊号。;桥本裕之追溯并分析了柳田和折口民俗学初创以来的民俗艺能研究轨迹,探求现代民俗艺能研究的可能性(6)[日]橋本裕之:《民俗芸能研究という神話》,民俗芸能研究の会/第一民俗芸能学会:《課題としての民俗芸能研究》,ひつじ書房,1993年。;鹤见俊辅将《民俗艺术》杂志的创刊与柳田国男的临界艺术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7)[日]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四巻 芸術》,筑摩書房,1975年。,视角颇为新颖;菅丰在回顾民俗学视角下艺术研究的学术史时,指出20世纪初叶,民俗学视角的艺术研究成为重要课题之一,包括“民俗艺术”在内的相关学术探讨,体现出学者对艺术民众性和日常性的关注。(8)[日]菅豊:《アートの民俗学的転回、民俗学のアート論的転回》,现代民俗学会网,http://gendaiminzoku.com/meeting.html,发表时间:2019年12月15日,浏览时间:2019年12月20日;[日]菅丰、雷婷:《民俗学艺术论题的转向——从民间艺术到支撑人之“生”的艺术(vernacular艺术)》,《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但菅丰致力于探究民俗学视角下艺术研究理论与创新,因此对于柳田的民俗艺术研究仅在学术史回顾中一笔带过,并未细致论述。
大致看来,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民俗艺术的研究较为零散,并未深入展开。虽然进入21世纪之后,在新时期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之下,中国学者在“艺术民俗学”“民俗艺术学”等领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在追溯艺术和民俗的关联时,都提到日本学者在近似领域所做的探索,但从关键人物柳田国男切入,对日本民俗艺术的学术史研究仍需要加强。另一方面,总结日本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柳田国男与民俗艺术的关系也仅仅是在回顾民俗艺能史时被一笔带过,止于概说性的总结,而从柳田的具体著述切入,深入论述其“民俗艺术”论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鉴此,笔者将基于《民俗艺术》杂志中的10篇论文和民俗艺术丛书之《民谣之今昔》,结合具体文本,对柳田民俗艺术论的特点及其折射出的思想史内容进行分析。
二、肯定普通人的民俗艺术
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目的,柳田在《民俗艺术》匿名写作的发刊词中指出:“我们为了学习古今亿万人共同体味过的生存方式,并不想仅仅遵循少数智者的卓识。因此,我们想首先确切地记录眼前丰富的事实,使之尽可能成为更多人的共有知识。然后整理与比较这些材料,基于自然而然显现的共通现象,如果有法则的话,想试着提炼出世间的法则。”(9)[日]柳田国男:《創刊のことば》,民俗芸術の会:《民俗芸術第一册》,国書刊行会,1973年,第3页。显然,柳田尝试从田野调查资料中总结世间法则,复原普通民众生活史与民族史的学术追求,而并非仅仅满足于根据少数智者的卓识去判断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
柳田的民俗艺术研究强调研究“普通人”“无名常民”的艺术活动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在他的相关著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民谣之今昔》一书中,他对由平民创作、平民传唱的民谣进行了细致研究,将民谣视为普通百姓创作的珍贵的民俗艺术。因为在文字尚未普及的古代,普通民众表达所思所感时,歌声往往更具感染力。民谣具有无作者性,“是在共同的气氛、共同场域中产生的,在这过程中很多人都会参与其中,这一点有别于印刷文艺”(10)[日]柳田国男:《民俗芸術叢書第2巻 民謡の今と昔》,地平社書房,1929年,第13页。。为此,柳田把民谣产生的条件总结为五点:“第一,民谣的用词是当地俗语,其他地方传来的词语也会转换成当地方言来唱;第二,仅歌唱与眼前情景有关的题材;第三,互相调侃,无所顾虑地唱出会话中难以启齿的事情;第四,妙语连珠;第五,笨拙的作品、粗制滥造的作品较多,仅有部分作品被记忆下来,并传承至今,这五点是所有古民谣都具备的特征,与文人笔端的民谣截然不同。”(11)[日]柳田国男:《民俗芸術叢書第2巻 民謡の今と昔》,地平社書房,1929年,第20页。
然而,到了近代,民谣急遽消失,一些惜古之人努力记录,使得民谣这一较为晚近的学问迅速成长起来。然而,实际的采集工作却出现了一定的混乱,自大和田建树的《日本歌谣类聚》问世以来,民谣集的数量不断增加,但看似繁荣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不少问题。如各地重复的内容太多,年代出现了混乱,照搬古文献中的记录,罗列一些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歌谣等。鉴于此,柳田从全国收集来的数量庞大的作品中,把作者明确的疑似民谣排除在外,并进一步区分整理为元歌与转用歌,以此解释作为普通民众艺术的民谣发展法则。与此同时,反对所谓的专业人士跨越边界对乡野百姓的辞藻进行无谓的改造。
除民谣外,在柳田看来,民间和乡野中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也是普通民众心声的真实映射,蕴藏着日本文化之根源。因为普通民众的民间记忆是真实的、纯粹的,相对于带有大量汉文化痕迹的古文资料,口承的民俗艺术更蕴含着重构日本民族史的可能性。对此,柳田在研究中多有论述。如在《假面所见一二》中,关于如何具体研究假面的历史以及假面所折射出的民间信仰,他认为从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切入,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在历史上,假面信仰在日本广泛存在,且至今仍在某些地区活态传承着,搜集整理信仰转化为传说或者其他文艺形式之前的传承过程,既可以读出现代生活的横断面,同时又能厘清假面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另外,在《狮子舞考》中,柳田认为狮子舞与动物耳冢传说密不可分,通过这一口承传说可以追溯至历史久远的生祭习俗。(12)[日]柳田国男:《獅子舞考》,民俗芸術の会:《民俗芸術第五册》,国書刊行会,1973年,第253页。虽然古代民间信仰的本意在传承过程中被渐渐遗忘,最终徒留其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完全被遮盖,世代流传的某些传说之所以至今仍为普通民众所讲述,是因为其中隐藏着可以探究日本固有信仰的重要线索。
除上述口承文艺之外,柳田也对舞蹈、假面、人偶等从祭祀中分化出来的艺术事象有所着墨,相关论述透露出他对普通民众艺术创造的赞赏。如《假面所见一二》中,柳田在探寻假面的研究方法时发现,假面的制作者分为专业手工艺人与业余手工艺人两个系列,其中业余手工艺人更忠于传统。(13)[日]柳田国男:《仮面に関する一二の所見》,民俗芸術の会:《民俗芸術第四册》,国書刊行会,1973年,第1014页。由此,柳田指出研究假面民俗的关键,是多关注乡下朴素的业余手工艺人所制作的工艺。关于专业手工艺人与业余手工艺人的分类和对比,反映出他对由非专业艺术家创作、并由非专业受众享受的民俗艺术的重视。
此外,儿童游戏也进入了柳田的考察视野,成为他探讨信仰起源的重要切入点。如在《从钩占到儿童游戏》一文中,柳田指出信仰有时会演变为儿童喜欢的趣味游戏。如儿童在游戏中拿着蚕神人偶揉着旋转的动作,很可能就是模仿了从前盲人巫女占卜时的做法。信仰和儿童游戏具有一定的关联,儿童在观察父母兄长虔诚地祭祀神灵时,他们会非常敏捷地模仿其中有趣的动作,因此宗教信仰中的某些动作渐渐演变成了儿童游戏。
总之,不论是民谣、传说、故事等口承文艺,还是舞蹈、假面、人偶等与身体表现有关的艺术事象,柳田都从普通民众的艺术出发,肯定此类艺术事象的重要价值。因为据此可以追溯纯正的精神资源,进而重构日本的本土文化。
柳田关于民俗艺术的开拓性研究,为后世的艺术研究做了铺垫,形成一种有特色的艺术论体系。从其想法获得启发,竹内胜太郎的《艺术民俗学研究》、折口信夫的《日本艺能史六讲》等著作相继问世。(14)[日]竹内勝太郎:《芸術民俗学研究》,立命館出版部,1934年;[日]折口信夫:《日本芸能史六講》,三教書院,1944年。另外,肯定普通人的民俗艺术这一视角,也触发了鹤见俊辅的“临界艺术论”(15)所谓临界艺术,是指由非专业的艺术家创作并由非专业鉴赏者欣赏的艺术。它与由专业的艺术家创作、由专门鉴赏者欣赏的纯粹艺术,以及由专业的艺术家创作、大众欣赏的大众艺术形成对照。参见[日]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四巻 芸術》,筑摩書房,1975年,第5页。,且近年来仍有学者对此进行关注,如福住廉对21世纪临界艺术进行了理论探索与艺术实践(16)[日]福住廉:《今日の限界芸術》,BankART1929,2008年。。菅丰在民俗学学科艺术论转向的相关著述中,提出Vernacular Art等崭新的艺术研究视角(17)[日]菅丰、雷婷:《民俗学艺术论题的转向——从民间艺术到支撑人之“生”的艺术(vernacular艺术)》,《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其中具体的研究笔者将另文撰述。
三、重视民俗艺术的传承与传播研究
普通民众的民俗艺术是在传统乡土语境中孕育出来的,乡土群体的内部知识通常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值得注意的是,民俗艺术一直处于流变过程中,因此,柳田反对将民俗艺术作为一成不变的凝固镜像来看待,而是重视民俗艺术的传承与传播研究,提倡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对其进行把握。民俗艺术只有不断与外来的要素相融合,适应新的变化,才会在传承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关于民俗艺术的传承与传播研究在柳田的著述中多有体现,如在《民谣之今昔》中,柳田言及民谣与流行歌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流行歌是民谣的源泉之一。远方的流行歌传入之前,平凡朴素的民谣作者的视野是极其有限的,想象空间也不甚宽广。民谣的形式虽然尽可能追随前代,但内容却在不断地吸收流行歌的元素。因此,民谣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同一首民谣在不同地方会呈现不同的表达方式,重要的是适应各个地方,表达当地民众的情感。虽然歌手主观上认为自己歌唱的是自古以来民众的心声,传唱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实际上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有时歌谣的传承与传播被迫中断,使得部分歌谣被渐渐遗忘。即使侥幸存留下来也因内容变得陈旧,难以继续传唱。等到世间太平以后,普通百姓会重新创作歌谣,以表达劳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心声。因为所知题材有限,他们会主动借鉴远方传来的歌谣。另外,“口口相传不存在文字出版那样的版权问题,每次歌唱都是一个版本,歌手可以根据情况自由地增删,因此民谣会伴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哪怕是曲名发生变化,曲中有新人物登场,听众依然会惊叹某个奇迹,在悲欢与快乐之间徘徊”(18)[日]柳田国男:《民俗芸術叢書第2巻 民謡の今と昔》,地平社書房,1929年,第137页。。
柳田国男强调不仅口承文艺如此,舞蹈、流行等民俗艺术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流动变化中不断吸收新要素。在《狮子舞考》中,柳田认为狮子舞是内外习俗杂糅的产物:自域外传来的舞乐等要素渐渐融入本土固有宗教的祭礼,日本固有的信仰通过外来的技艺得以保存至今。狮子舞自域外传入以前,日本本土已经有了鹿舞,这与用鹿头祭祀的信仰习俗密切相关。关于鹿头的传说至今仍然在日本其他地方有所流传,其中奥羽地方传说中相邻两村互斗,输的一方会将鹿头埋入地下形成鹿冢。柳田据此推测,“鹿舞的主要目的是让灾害远离自身领地,但对于邻村而言,这或许会侵犯到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经过协商在村界建鹿冢”(19)[日]柳田国男:《獅子舞考》,民俗芸術の会:《民俗芸術第五册》,国書刊行会,1973年,第246页。。顺着这样的线索会发现,在一些传说中还有关于不同权现(20)“权现”,是指佛或菩萨化身为日本的神出现。参见[日]金田一京助等编著:《新明解日汉词典》,邓子丹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795页。的争斗过程中,有一方耳朵被另一方咬掉的内容。耳朵被咬掉的地方被称作“耳取桥”“耳取岭”“耳取路”等。柳田在某个耳取桥,发现有将灵性的鹿头供奉在祭祀仪式中的情况,由此推测割耳的内容或许与供奉牺牲的习俗有关。割掉兽类或者人的某一器官作为记号,表示对其占有,自古以来在家畜或者俘虏身上多有发生。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习俗渐渐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仅保留在某些祭神仪式当中。后来中国的狮子舞传入,因为日语中“狮子”和“鹿”发音的相似,鹿舞渐渐附会成狮子舞。直到现在仍有很多地区的狮子头上长着角,并将一些歌咏鹿的歌谣用在狮子舞表演当中。
在《风流与趣味》一文中,柳田指出,“风流”的原意是指室外技艺的变化,艺人每年都会想方设法添加新趣味,以此吸引观众。而风流得以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是其形式越来越丰富,能捕捉到更多人的兴趣。风流传播开来,“进入各个村落之后,会再次固定下来,以统一的形式支配民众的心性”(21)[日]柳田国男:《風流と我面白》,民俗芸術の会:《民俗芸術第三册》,国書刊行会,1973年,第720页。,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换言之,风流与趣味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缺一不可。风流离不开趣味,风流因为有趣才会代代流传,无趣之风流会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趣味也离不开风流,不断发生变化的表演形式,会增加趣味性,让群体内部产生愉悦的心情,并渐渐与地方生活融为一体。
民俗艺术的流动性特征同样适用于冲绳岛的相关艺术事象,在《岛的历史与艺术》中,柳田提到,虽说八重山群岛的普通百姓至今仍把歌唱与舞蹈当做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放松方式,但岛上近世二百年或者一百年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有的表现形式不断融入各种新要素。柳田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趋势,因为不论歌词、曲调还是服饰、乐器,自本岛经由冲绳传入八重山之后,都发生了内外、新旧的融合。直到今日岛上的歌谣舞蹈等艺术依然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不仅会为日本一国的艺术融合做出贡献,也会融入世界音乐的和谐乐章中”(22)[日]柳田国男:《島の歴史と芸術》,民俗芸術の会:《民俗芸術第一册》,国書刊行会,1973年,第502页。,为世界艺术的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柳田对固守所谓的传统,忽视民俗艺术流动性特征,缺乏传承与传播研究视角的做法持批判态度。如《蚕神与人偶》中,柳田在文末以批判的视角指出:“风俗会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或者进化,不论是何种奇风异俗,将其作为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事象去追溯其源头的做法都是错误的。”(23)[日]柳田国男:《おしら神と人形》,民俗芸術の会:《民俗芸術第三册》,国書刊行会,1973年,第337页。
总之,普通民众所创造的民俗艺术是流动变化的,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因此,其知识结构并非恒久不变,而是在内外、新旧的融合中,朝着多元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并在某些阶段、某些地方留下痕迹。在研究一种艺术事象之时,通过收集分散于各地但属于同一系统的艺术活动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理清一种艺术是通过怎样的路径从最初的形态慢慢演变成当今的形态,并依旧在普通百姓中富有活力的传承。
四、批判民俗艺术的舞台展演化倾向
大正时代,在大正民主主义和“民间”热潮的影响之下,国家层面意识到民俗艺术在触发国民乡愁、激发民族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再一味推崇西方文明,开始认可本国民俗艺术,并注重自上而下地引导。大正三年(1914),文部省文艺委员会刊行了《俚谣集》,这是在国家层面把民俗艺术作为文化遗产来认知,并将其记录在案的突破性举措。在劳作机械化不断推进,各地传统劳作所孕育出的民谣不断消失的背景下,国家层面号召收集民谣的举动显得异常珍贵,从而带动了民间的民谣采集活动。同时,各地区的民俗艺术被视为民俗资料,展现出民俗艺术传承作为民俗研究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之下,1925年日本青年团的大本营——日本青年馆在东京青山成立。开馆的纪念活动——“乡土舞蹈与民谣之会”在会馆大厅揭幕。作为组织者的青年团不但是各地方社会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参与民俗艺术文化保护的主要推动者。他们致力于普及和传承民俗艺术,搜集隐没于民间的乡土舞蹈和歌谣并将其置于舞台上公演。柳田协助公演的策划,并作为学术顾问参与其中活动。借助乡土舞蹈与民谣之会的舞台,民俗艺术让背井离乡、在东京奔波的人们感受到一种乡愁,因此他们希望每年都能如期上演。自此,乡土舞蹈与民谣之会的公演几乎每年都会定期组织。(24)[日]鈴木正崇:《『民俗芸術』の発見―小寺融吉の学問とその意義》,《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2015年复刊第52号,第31页。以此为契机,不少民俗学者、舞蹈家、音乐家或前往地方调查研究,或努力学习歌舞知识,而《民俗艺术》杂志也成为他们发表观点的重要阵地之一。
民俗艺术是挖掘普通民众心性的重要材料,然而若把民俗艺术从乡土时空中分离出来,仅仅局限于舞台上的表演,长此以往民俗艺术将渐渐失去民间传承的生活根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舞台上的表演,将民俗艺术从其赖以支撑的民间信仰中剥离出来,使得民俗艺术极易成为表演者哗众取宠的道具,而与原本由普通民众创造并由普通民众享受的民俗艺术迥然有别。对这种展演化倾向,《民俗艺术》杂志的另一位指导者折口信夫在观看了第四次乡土舞蹈与民谣之会后,对表演活动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为了到东京进行展演,很多地方的民俗艺术作了较大修改,已不再是原有的姿态。因此,折口希望不要过于追求舞台效果,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持民俗艺术的原汁原味。此外,折口阐明对艺术的态度,“这次活动仅仅是作为一个造型艺术的展览会就可以,而不要将艺术性作为目标,这样演出者会更为轻松,观看者也可以体味到过去的真正的生活”(25)[日]折口信夫:《感謝すべき新東京年中行事》,民俗芸術の会:《民俗芸術第三冊》,国書刊行会,1973年,第709页。。
对民俗艺术呈现出的展演化倾向,柳田也在相关论文中提出了批评。如在《风流与趣味》中,柳田在观看了第四次乡土舞蹈大会上的表演后敏锐地意识到,艺人虽然出自农家,但其表演已成为一种展演性质的工作,不再像从前那样因为兴致而自由表达。更有甚者,艺人为了得到东京人的褒赏,将此前未受东京统摄的本土艺术改造成东京风格。在此背景之下,一年一度的乡土大会上,来自地方的舞蹈与民谣纷纷登上绚丽的舞台。然而,在表演的过程中,观众和表演者的兴趣点各不相同,这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因为生活和工作节奏较快的东京观众疲于生计,无暇学习乡土舞蹈和民谣的相关知识,他们追求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更喜欢华丽、炫目的舞台以及热情洋溢的演出。如此会出现一种矛盾,朴素的乡土舞蹈如若保持原汁原味,会在观众那里失去吸引力。而为了迎合观众,对舞台进行装饰,改成华丽的背景,乡土艺能则不再是原生态艺术。
民俗艺术的复合体——祭祀的展演倾向也愈加强烈,对此柳田曾言:“日本祭祀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节点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观赏群体的出现,即祭祀的参加人员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具备共同信仰,可以说是站在审美的角度观望仪式活动的人群。”(26)[日]柳田国男:《柳田国男全集13》,筑摩書房,1998年,第382页。大正、昭和时期,有些大型祭祀,把艺能从乡土时空中分离出来,仅仅局限于身体表现,虽然能够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村町由当地民众悄悄举行的小型祭祀更应受到重视。“因为大祭基本接近于表演秀,已经成为大众艺术,而小祭一直保持着临界艺术的功能”(27)[日]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四巻 芸術》,筑摩書房,1975年,第15页。,因此柳田提倡复兴小祭,避免大祭展演化趋势的扩大。
由此可以看出,柳田对过分迎合观众趣味,将民俗艺术从最初的乡土语境中剥离出来,置于舞台上进行展演的倾向持批判态度。然而在国家收集乡土色彩浓厚的地方民俗艺术的政策之下,地方民俗艺术的舞台展演并没有因为柳田、折口等学者的批判而中止。各府县依然会认真遴选符合条件的艺术项目,并推荐至乡土舞蹈与民谣之会进行表演。虽然乡土舞蹈与民谣之会曾在二战期间一度中断,但是战后得以再度复兴。自1950年开始由文部省主办,发展成为“全国乡土艺能大会”,1959年起改名为“全国民俗艺能大会”并持续至今。(28)[日]鈴木正崇:《『民俗芸術』の発見―小寺融吉の学問とその意義》,《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2015年复刊第52号,第33页。民俗艺能也成为必须要在观众面前通过身体进行表演的艺术,艺人的表演和观众的观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75年,国家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这一制度框架问世以来,为了记录和保存面临消亡危机的民俗艺术,学界与政府合作,共同推进民俗艺能的保护工作,有些学者甚至参与了文化财保护的相关工作,二者的合作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推助了艺能的展演化倾向。
五、柳田国男与《民俗艺术》杂志、民俗艺术之会的疏离
在《民俗艺术》第四卷第四号以后,柳田再未在此发表过相关论文,实际上这是他疏离学会与杂志的一个重要信号。柳田疏离《民俗艺术》杂志和民俗艺术之会,既有他本人研究理念的影响,也与学科研究领域划分和人事关系,乃至当时整个时代的社会思想背景的影响息息相关。
其一,柳田研究理念的影响。柳田把普通民众创造的民俗艺术视为探寻日本人的民族心性、纯正日本文化的重要材料。基于这一研究理念,在他的支持与引导下,“民俗艺术之会”成立,《民俗艺术》杂志创刊。柳田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普通百姓创造的各种民俗艺术,唯有如此才能掌握更丰富的研究资料,从而更好地探讨“共通法则”。然而,纵观《民俗艺术》杂志总48号可以发现,《民俗艺术》杂志整体偏重于祭祀与艺能的考察,而一般艺术尤其是造型美术并非其研究重点,仅有第一卷第十一号是造型美术的特辑。对此,负责本号编辑工作的今和次郎有所担忧:“无形方面的民俗艺术研究进展地十分顺利……而造型美术方面只能寄希望于未来。”(29)[日]今和次郎:《編輯後記》,民俗芸術の会:《民俗芸術第二冊》,国書刊行会,1973年,第1088页。换言之,发刊以来,学者对无形艺术示以浓厚兴趣,却鲜有人关注有形艺术。以至于《民俗艺术》最后偏于对神事中祭礼和艺能的研究,柳田最初关注的各种有形艺术渐渐从学会成员的研究视野中消失。其结果是有形艺术进入民艺的研究范畴,最终民俗艺术的研究对象仅剩下无形文化——艺能。而艺能愈演愈烈的展演化倾向,使其脱离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柳田提出,应该将艺能排除到民俗学的范畴之外。(30)[日]吉越笑子:《芸能研究と柳田国男》,鎌田久子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会:《民俗的世界の探求 かみ·ほとけ·むら 鎌田久子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慶友社,1996年,第427页。
其二,学科研究领域划分和复杂人事关系的原因。虽说“民俗艺术之会”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成立的组织,《民俗艺术》的发刊词也是由柳田亲自匿名书写的,但他并不能完全主导该学会。民俗艺术之会的成员学科背景复杂,折口信夫、早川孝太郎、小寺融吉、吉田衡吉、竹内胜太郎、金田一京助、今和次郎等人都曾积极参与加入,他们横跨民俗学、考现学、演剧学等各领域,研究视角各有不同。因此,学会和杂志的学术走向不是柳田一人所能控制的。实际上,在日本民俗学界,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柳田起着主导作用,由于其势力过于强大,很多声音都被遮蔽。在这样的人事背景之下,民俗艺术之会之外出现了诸如民俗艺能之会、口承文艺学会、民艺协会等独立的学术组织,其未能成为一个统括各个近似分支的学术组织。
其三,社会思想的缘故。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力倡导“脱亚入欧”,全盘西化,而“脱亚入欧”的实质在于“脱中入欧”。按照柳田的观点,日本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化严重,因此有必要重新建构本土真实的日本史。唯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优于中国的文化独特性,步入欧洲先进文明之行列。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之下,需要通过民族主义构建日本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意识。因为大量古文资料已留有汉文化的痕迹,这些记忆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只能靠民间记忆去重构历史。因此,柳田故意避开汉文化痕迹明显的古文资料,试图通过民间和乡野传承的民俗艺术,找寻普通民众生活背后真正的日本文化。柳田所关注的民俗艺术是生活在民间、乡野的普通百姓创造的,其中蕴藏着真正的日本文化之根。然而,民俗艺术研究后来局限于艺能这一狭隘的无形文化之范畴,无法从根本上探寻日本文化之根。加之有些艺能过分倚重于掌门人个人的力量,超越了柳田民俗艺术学关注普通民众历史的范畴。
另外,大正至昭和初期,日本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在军国主义的禁言时代来临之前,诸多不属于大学、官学体系的学问登上学术舞台,鹿野政直称之为“民间学”。日本的民俗学就属于民间学的一种(31)[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の民間学》,岩波書店,1983年,第7页。,而与民俗学密不可分的“民俗艺术”,也是这种社会思想的产物。“民俗艺术”这一外延宽泛的统合概念,既包含了折口信夫民俗学性质的艺能研究、小寺融吉的舞蹈与演剧研究,也吸纳了今和次郎的考现学研究。而柳田国男主要关注的是由普通人创造并享受的民俗艺术。
事实上,柳田尝试对民俗艺术进行探索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对应的正好是日本民俗学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他积极挖掘隐藏于民间的艺术事象,试图通过研究民俗艺术来把握普通人的风俗习惯及生活文化,以服务于柳田民俗学的整体构想。置于柳田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中去探讨民俗艺术可以发现,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各地的民俗艺术曾被柳田视为民间传承的一个领域,成为民俗学研究的素材,涉及口承文艺、造型艺术、信仰仪式、艺能等方面。然而,在研究后期,柳田将最初被涵盖于民俗艺术之下的艺能排除在民俗学的范畴之外。柳田对艺能的否定性态度不仅直接刺激了民俗艺术之会与《民俗艺术》的没落,而且对此后日本民俗研究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932年,民俗艺术之会解散,《民俗艺术》杂志停刊,经历了短暂摸索期的民俗艺术逐渐为“民俗艺能”这一概念所替代,最终退出了学术舞台。尽管民俗艺术之会和《民俗艺术》杂志时期萌发的艺术视角,在其后的民俗学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但柳田在民俗艺术诞生伊始的开拓性研究,仍然继续发生影响。1952年“民俗艺能之会”成立,继承并复兴了“民俗艺术之会”。(32)[日]三隅治雄:《民俗芸能研究の歴史と現状と展望》,《民俗芸能研究》1985年創刊号,第13页。伴随着“民俗艺能之会”的成立,“二战前的乡土舞蹈、乡土艺能、民俗舞蹈、民俗艺术、民间艺术等说法在二战以后被统一称为‘民俗艺能’”(33)[日]鈴木正崇:《『民俗芸術』の発見―小寺融吉の学問とその意義》,《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2015年复刊第52号,第35页。。1984年民俗艺能学会成立,于1985年发行会刊《民俗艺能研究》,并持续至今,在民俗艺能研究方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学术研究热潮。
整体看来,柳田在民俗学初创时期所提出的民俗艺术论极具启发性和创见性。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柳田本人还是后继者,对排除艺能之后的民俗艺术所进行的具体研究极少。仅有鹤见俊辅、菅丰等人有意承继并创新柳田所提出的民俗艺术观,其结果是“民俗学当中,社会传承、经济传承、仪礼信仰传承方面是研究的重点,‘艺术’和‘娱乐’则是周边性的民俗……甚至可以说在民俗学这一学问之中,‘艺术’‘娱乐’等分类概念不过是权宜、表面的分类标签,没有必要将其提升至包含实际内涵的概念”(34)[日]小松和彦:《総説 芸術と娯楽の民俗》,小松和彦、野本寛一編:《芸術と娯楽の民俗》,雄山閣,1999年,第6页。。
六、结 语
20世纪30年代左右,柳田国男在《民俗艺术》杂志和民俗艺术丛书中,对民谣、传说、舞蹈、人偶等诸多民俗艺术事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柳田将普通民众创造的民俗艺术作为一个体系进行理解,高度评价非专家或普通人的艺术活动,这在当时具有开拓意义。同时,他强调民俗艺术所具有的流动性、开放性特征,认为这是民俗艺术能够突破相对稳定的结构,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吐故纳新、兼收并蓄,从而得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关键。
柳田之所以关注普通人的民俗艺术,是冀望循此线索,探讨不同地区普通民众背后的生活历史,进而溯源真实的日本史,重构大和民族的民族认同,这在日本现代艺术论中属于开拓之举。这种通过普通百姓的艺术探寻日本民族精神的研究方法,为其后期“一国民俗学”等思想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学术铺垫与知识储备。
——学院派民俗学的世界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