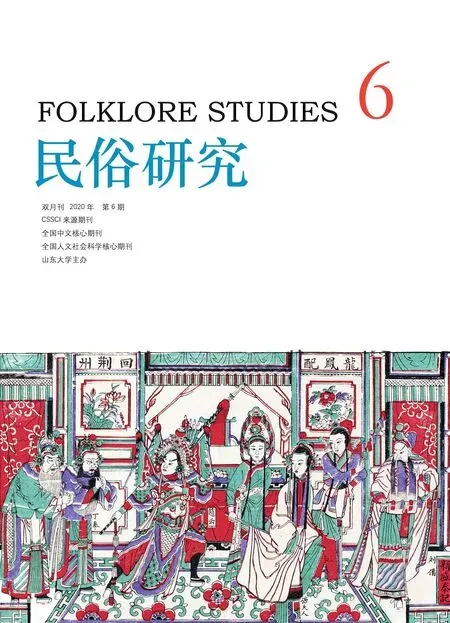深描“中国本土信仰仪轨传统的文化底蕴”
张志刚
引言:作为前沿课题的信仰仪轨传统研究
从国际学术界的研讨动向来看,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象征理论”的影响推动下,“仪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日渐成为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的研讨热点、前沿课题。这一前沿课题吸引着一批著名学者,力图超越以往的“宗教仪式的现象描述”,进而深究“信仰仪式的文化意义”。
例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宗教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的研究成果表明,信仰仪式在行为和观念上均充满“象征”,人们之所以执着于这样或那样的“信仰仪式象征”,就是因为它们深含“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与文化功能”。他深入田野,通过观察非洲赞比亚地区的恩登布人(Ndembu)的生活发现,当地古老的信仰仪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生命危机仪式”(life-crisis rituals),如青春期仪式、丧礼等;二是“生存困扰仪式”(rituals of affliction),此类仪式均旨在禳解人生的种种困苦或灾难。(1)参见[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再如,美国民族学家、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基于扎实的田野考察和透彻的个案研究,从学理上把“宗教”视为“一个文化体系”,提出了“文化意义深描理论”,以求更具体、更深入地阐释“作为象征性的意义体系的宗教传统”,是何以积淀为某个文化区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族群或社群生活的心理倾向和行为动机的。在他看来,“一种宗教就是:(a)一个象征体系,其作用在于(b)在人们当中营造出强有力的、普及的和持久的情绪与动机,其方式在于(c)系统阐述关于整个存在秩序的诸多观念,并且(d)赋予这些观念以实在性,此种氛围致使(e)前述意义上的情绪和动机看似是唯一真实的”(2)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3, p.90.。
学术乃天下公器。以上两位国际著名学者所提出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东方信仰仪轨的文化底蕴及其现实意义,显然是有学术启发的。东方的信仰仪轨传统,乃是东方文化传统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无疑承载并传承着东方的文明特质与文化精神。从方法论来看,我们能否假设:越是“原生态的且不失生命力的民间信仰仪轨”,或许愈发有助于寻根溯源,使今人深刻认知“某种本土文化传统”的本相、特质、来龙去脉呢?本文试以比较研究的学术视野,着重以土生土长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仪轨为例证,与方家一起探讨,如何深描“中国本土信仰仪轨传统的文化底蕴”,有无可能据此拓展与深化“东亚文化圈的信仰仪轨传统研究”?从比较宗教学的观念来看,笔者以为,较之西方以基督教为主导的仪式传统,中国的信仰仪轨传统主要有下述三个显著的特性。
一、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人本特性
如果说西方以基督教传统为主导的信仰仪式是“神本主义”的,中国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信仰仪式传统则更注重“以人为本”。基督教仪式所体现的“神本主义”,充分流露于其一般仪轨和重大节庆,如基督教的信仰仪轨主要包括“洗礼、礼拜、圣餐、祷告”等,其重大节庆主要有“基督降临节、圣诞节、复活节”等,皆以“造物主——上帝”为崇拜对象,以“耶稣基督”为信仰目的,除此之外,绝不能崇拜任何其他偶像。因而,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寇克斯(Harvey Cox)指出:基督徒生活于“两种时空状态”,即“世俗年”和“礼仪年”(或称“教会年”);作为人类成员,他们生活于一年四季;身为基督徒,他们则是根据“教会历法”来安排生活的。(3)参见[美]哈维·寇克斯:《基督宗教》,孙尚扬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相比起来,中国的信仰仪轨传统的确更为彰显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人文精神。如“祖先崇拜”,可谓中国人自古以来所传承的“底线信仰和礼法规矩”,也就是说,无论“儒、释、道”还是“民间信仰”,也无论有无专门的祭祖仪式,若不遵奉“祭祖规矩”,便触犯了“做中国人的底线”。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如楼宇烈先生所释:中国人所崇敬的“神”常常是祖先,在甲骨文里,“帝、上帝”等主要是指“部落的祖先或英雄”,他们死后会保佑子孙。所以,“祖先崇拜”可以说是“圣贤崇拜、英雄崇拜”。到周代,这种信念开始演变,“祖先神或圣贤神”并非盲目地保佑子孙,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有德”,于是出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思想;春秋时,前述思想进而发展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神之主也”。这就在西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文化传统。(4)参见楼宇烈:《探求合乎东亚文化传统的宗教学研究理论》,张志刚、金勋主编:《世界宗教评论》第1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关于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人本特性,或许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梁启超所做的阐释更为全面,也更耐人寻味。他在晚年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时强调,中国传统里根本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及其崇拜仪式”,中国人只有“崇德报功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贯彻于中国人的所有祭祀行为,如祭父母、祭天地、祭动植物神、祭各行业神、祭英烈人物等。
祭父母,因父母生我养我;祭天地,因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于人,则凡为国家地方捍患难建事业的人也要祭;推之于物,则猫犬牛马的神也要祭;如此,“报”的观念便贯彻了祭的全部分。这种祭法,和希腊、埃及的祭天拜物不同。他们是以为那里面有甚么神秘,乃是某神的象征,并不因其有恩惠于人而去祭他。老实讲,中国所有的祭祀,都从这点意思发源。(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第171页。
在梁启超看来,若是把中国人所供祀的神灵一一根究来历,大抵没有不是由人变来的,而考释这些神灵受祀范围的广狭、年代的久暂,以及一般民众的祭祀心理等等,便能成为中国宗教史的精彩篇章。
二、中国信仰仪轨的兼容并包传统
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仪轨传统,信仰者“只能崇拜上帝,不能敬拜其他任何偶像”。西方基督教仪轨传统的这种鲜明的“唯一性、排他性”,在“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etiquette disputes,约17-18世纪)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中国礼仪之争,又称“中西礼仪之争”,直接起因于,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的教会内部纷争,其争论内容主要有三:第一,能否把天主教的崇拜对象(Deus)译为中国典籍里的“上帝”?第二,如果一个中国人皈依天主教,能否“祭孔”?第三,如果一个中国人皈依天主教,能否“祭祖”?(6)关于“中国礼仪之争”,可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由此可见,这场礼仪之争实质上引发了中西方信仰传统的根本冲突,因为所谓“译名之争”关乎前述中西方信仰仪轨传统的根本分歧——“神本主义”还是“以人为本”,“祭孔之争”所挑战的是“周孔教化”形成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传统(7)梁漱溟有如下论断:“两千余年来中国之风教文化,孔子实为其中心。不可否认地,此时有种种宗教并存。首先有沿袭自古的祭天祀祖之类。然而却已变质;而构成孔子教化内涵之一部分。再则有不少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然试问:这些宗教进来,谁曾影响到孔子的位置,非独夺取中心地位谈不到,而且差不多都要表示对孔子之尊重,表示彼此并无冲突,或且精神一致。结果,彼此大家相安……在确认周孔教化非宗教之时,我们当然就可以说中国缺乏宗教这句话了。”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1-92页。笔者以为,梁先生关于“中国缺乏宗教”的说法,或许言过其实,但他对中国文化主流传统的定性,仍不失参考价值。,“祭祖之争”则触犯了“做中国人的底线”。因而,这场旷日持久的中西礼仪之争,注定以康熙皇帝的一道“禁教谕旨”为悲惨结局。
与西方基督教“唯一性、排他性的礼仪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信仰礼仪传统可谓“和而不同,兼容并蓄”。这一点在中国本土的道教仪规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为了表达虔诚,祭祷者要清洁身心,奉行仪轨,于是便有“斋戒”。从形式上看,“斋”有“设供斋”“节食斋”“心斋”等,其中尤以“心斋”重要;所谓“心斋”,其要义就是“敬诚专一,心无二想”。虽然道教戒律有“上、中、下”三品之分,有“三戒”“五戒”“八戒”以及数十上百种戒,但就内容而言,其基本精神是与儒教伦理、佛教戒律相会通、相融合的,如仁爱、慈悲、孝亲、敬师、忠君、报国、勿贪、不淫等,同时又不失道教斋戒的自身特性,如“皈依道、经、师”、不毁谤道法、不轻泄经文、不污漫静坛、不贪睡误课等。(8)关于道教斋醮科仪,参见牟钟鉴:《道教》,张志刚主编:《宗教研究指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笔者之所以在此首举“道教斋醮科仪”为例,就是由于“以道家哲理智慧为根脉”的道教,是在中华文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不但更能体现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本质特性,而且对林林总总的中国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仪轨产生了深广影响。关于这一点,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魏乐博(Robert P. Weller)的田野体验,或许要比中国学者的描述与解释更客观、更有说服力。
自攻读博士学位起,魏乐博便投身于中国宗教仪式,尤其是民间信仰仪式的田野考察。据他本人回忆,到中国从事田野考察之前,他脑子里装的都是“一些抽象的理论知识”,即西方人类学界的大量概念、理论与方法;但到中国进行田野考察之后,他却发现中国人的宗教状况特别是普通百姓的信仰习俗,与西方学者的理论想象相去甚远。譬如,按照特纳、格尔茨等人的“解释人类学”观点,田野考察的目的在于,解读“某种仪式的地方意义”,但他到处访谈当地老百姓的结果却是,很多人并不十分清楚仪式的意义,而有些人干脆回答: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做的!这使他意识到,中国老百姓对于宗教仪式的理解,并非“统一的”而是“多样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民间信仰非常重要。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察的切身经历,给他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一神论”与“多神论”的巨大反差。在美国,如果遇到一个摩门教的传教士,他会对你说:“不要相信其他的宗教,那些都是骗人的”;而另一位长老会的传教士会对你讲:“其他的宗教,比如摩门教,肯定是不对的,不要相信它们。”而他在中国碰到的很多老百姓则会说:“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教人做好事、劝人为善的。”魏乐博坦率承认,这是他所碰到的“真正的多神论”,只有运用人类学的比较方法,才能如实发现不同文化的鲜明差异,且体会到这么强烈的文化冲击。(9)参见卢云峰:《宗教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本——访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魏乐博教授》,《中国民族报》2008年9月19日;龙飞俊:《主体、多样性与仪式:我的中国人类学研究——魏乐博教授访谈》,《当代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张士闪、[美]魏乐博:《当代中国民间宗教研究要“接地气”——波士顿大学魏乐博教授访谈录》,李生柱译,《民俗研究》2017年第5期。
论证至此,笔者要对魏乐博教授所用“多神论”概念加以修正或纠偏,因为在许多国际学术同行看来,相对“一神论”而言的“多神论”,按照来自西方背景、长期流行的“世界宗教史的进化论解释套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含有“贬义的”,即主要是指“原始的或初级的宗教信仰形态”。这无疑是“西方学界一神论倾向的宗教研究”的一大偏见。其实,一方面,我们不妨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心意,把所谓“多神论”诠释为“多多益善”,即“凡是好的、善的神灵,都不妨拜一拜、求一求”;另一方面,我们倒不如说,越是“原生态的、扎根民间的且有生命力的信仰传统”,愈发能使我们真正认识“信仰仪轨传统的本相与特质”。假如这一判断基本上能够立论,那么,中国土生土长的且对民间信仰有深广影响的道教斋醮科仪,便堪称“诠释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典型例证”;更何况,前述道教斋戒所折射出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特征,既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又是顺应世界宗教之发展潮流的。
三、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圣俗融合
国际学界专业化、学术性、交叉性的比较宗教研究,现已形成诸多颇有影响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假如我们从中首选一对最有影响的“分析范畴”,恐怕非“神圣”与“世俗”莫属了。例如,社会学暨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人杜尔凯姆(又译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认为,已知的一切宗教现象,无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把全部事物(现实的或理想的)一分为二,划为两大类——“世俗的”(profane)和“神圣的”(sacred)。因而,他强调:“把世界分成两个领域,一个包括所有神圣的事物,另一个则包括所有世俗的东西,这是宗教思想独具的特色。”(10)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p.52.虽然杜尔凯姆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比较研究的学术视野来看,这种“圣俗二分法”主要适用于西方宗教传统研究,却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研究。
谈及“中西方信仰观的异同”,著名史学家、儒学家钱穆曾刻意强调两点:一是,两种不同的信仰方式,西方宗教传统重视信仰,中国人也不轻视信仰,但相比之下,西方人“信在外”,即“信仰者”与“信仰对象”分别为二;而中国人则“信在内”,“重自信、信其己、信其心”,“信仰者”与“信仰对象”和合为一。二是,两种不同的神性观念,西方人所崇拜的“神”是“惟一的、绝对的、外在的”,中国人也信奉“神”,但“神”并不只指“天”或“上帝”,也包括人与物。在中国人的信念里,“圣”与“天、神”也是和合为一的。(11)参见钱穆:《略论中国宗教》,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9页。
虽然钱穆先生的上述观点主要立论于儒家思想,但对我们探析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另一个主要特性,无疑是有学术启发的,笔者将此主要特性概括为“圣俗融合、百姓日常生活为重”。例如,道教做道场时,总是将“斋戒”与“坛醮”结合起来。所谓“醮”,就是设坛祭祷,主要内容有三:上供祭神,谢罪忏悔,上章祈祷,并伴以念经、礼拜、鸣鼓、奏乐等神圣气息。“醮仪”的一般程序包括:设坛、上供、烧香、升坛、礼师存念如法、高功宣卫灵咒、鸣鼓、发炉、降神、迎驾、奏乐、献花、散花、步虚、赞颂、宣词、复炉、唱礼、祝神、送神等,共同营造出神圣氛围。所谓“坛醮”主要分两类:一为“清醮”,如祈雨消灾、祛病延年、传戒受戒、护国安民、祝圣庆诞等;二为“幽醮”,如摄召亡魂、破狱破湖、炼度施食等。如上种种形式与内容,可谓“圣俗融合”,其主要功能是“为百姓日常生活服务的”。
著名汉学家、美国宗教学家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潜心研究中国民间教派长达数十年。他颇有心得地解释道,在中国民间信众看来,诸种神明是“道德秩序建构的象征”。从根本上说,“民间世界观”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人类社会都要遵守的宇宙秩序,因而民间神明崇拜可以支撑社会道德准则。这在庙会的娱神戏里表达得特别明显,如善恶正邪,黑白分明等。民间善书也教导人们孝亲睦邻之道,谁要不遵守这些道德准则,拜神也没用。中国民间信仰的道德价值观,可用一句俗语概括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国民间教派,最初大多是由当地百姓自愿结社的,它们举办的各种仪式几乎都是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如祛病、平安、长寿、家庭和睦、家族兴旺、早生贵子、五谷丰登、生意兴隆、学业有成等等。因为普通百姓相信,他们所祭拜的诸神,就是作为神灵的“大善人或大能人”,能够为他们解决一切生存需要。这显然表明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实际性”。只要哪位神有求必应,老百姓就供奉。这样一来,信仰仪式便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了。(12)参见[美]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的秩序与内在理性》,赵昕毅译,《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通讯》1998年第3期。
关于中国信仰仪轨传统的圣俗融合特性,有必要澄清一种常见的理论误解,这就是不少中外学者简单照搬“神圣与世俗”概念,且以西方基督教传统为参照,以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因其“现实性或功利性”而“缺乏神圣性”或“神圣性不足”。譬如,中国人常言:“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灵则还愿,不灵不再拜”等。笔者认为,看到类似的说法,切忌“望文生义”,而要“听话听音”。从整个世界宗教史来看,古今中外各大宗教传统的信众主要就是普通百姓,他们之所以寻求信仰、参与仪式,就是为了有所依靠、有所指望,能够帮助他们消除艰难困苦,过上美好生活。譬如,若对西方基督教平民信徒的日常祷告有所观察,他们所祈求的种种内容岂不与中国民间信众一样,从生老病死到日常琐事,无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或功利性”吗?
再从学术角度来看,正如法国汉学家、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专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所尖锐指出的,由于专业化的比较宗教研究是一门萌生于西方的“学科”(science),因而首先有必要反省与质疑的,就是那些在建构“中国宗教”这一研究领域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概念范畴。具体地说,自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西方学术界对宗教的定义大都隐含“潜在二元论”(underlying dualism),即把“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神圣与世俗、教会与国家、灵魂与肉体、超自然与自然等)对立起来,这显然属于西方“非此即彼的逻辑”(either/or logic)。而中国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所谓“中国宗教”在传统上是归属于“礼”范畴的。因此,若要真正理解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就要尽量少用“西方的范畴和逻辑”,而应对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予以“整合性的、合理性的演绎”。(13)详见[法]劳格文:《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领域的转变、启迪与中国文化》,李凌翰译,《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通讯》1999年第4期。
关于“礼”对中国社会、国家政治、宗教文化、民间习俗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根据长期的田野考察,深究“礼俗互动关系”,明确地把“礼与俗”界定为“自古及今中国社会的某种普遍现象与社会思想的一般特征”,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实践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14)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齐鲁书社,2019年,第1页。这一新近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反思西方宗教学“二分法的概念范畴”对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包括本土信仰仪轨传统研究的偏颇影响。
四、余论:拓深东亚文明与仪轨传统研究
尽管笔者学识有限,仅能着眼于国际学术界的晚近动向,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仰仪轨研究”视为学术前沿课题之一,初步探讨了中国本土信仰仪轨传统的三个主要特性。然而,假若这种粗浅的学理思考在方法论上不无收益,有助于我们探究“本土信仰仪轨传统所深含的文化底蕴”,那么,这便初步论证了“东亚文化圈的信仰仪轨传统研究”的重要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日、韩三国乃东亚文明的“文化重镇”,不但拥有相近的文化传统,而且富有深厚的本土信仰仪轨传统,皆可称为“礼仪之邦”,皆为东亚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我们既有条件、更有必要加强学术合作,通过比较与对话,拓展与深化“东亚文化圈的信仰仪轨传统”这一重要课题的整体性研究。如何展开“文化比较与文明对话”,包括“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仰仪轨传统的比较与对话”,尚是摆在国际学术同行面前的前沿课题,东亚学者无疑要有担当,为之做出努力和贡献。具体就“东亚文化圈的信仰仪轨传统”研究而言,我们能否从整体上分析论证,中、日、韩三国悠久深厚的信仰仪轨传统既各自饱含东亚文明的文化底蕴,又共同传承“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圣俗融合”的文化生存、文明发展的价值理念呢?在前文论证的三个主要特性中,笔者以为,“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共存理念之于当今世界纷争、人类文明前景尤为重要。如果我们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基本共识,并在日后通过拓展与深化“东亚文化圈的信仰仪轨传统”研究来印证前述三大特征及其核心价值理念,那么,本文所浅尝的学理论证便达到主要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