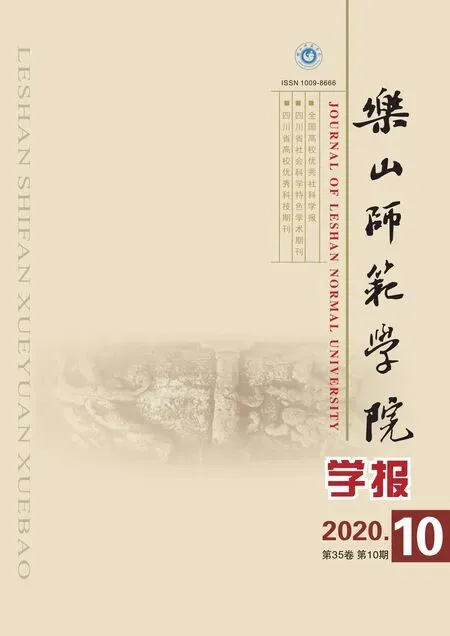横放杰出:论苏轼词开阔丰盈的空间感
宋学达
(香港浸会大学 中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999077)
苏轼词历来被视为词之“变体”,是在唐宋词艺术的发展史中突破“花间范式”而另立门户的第二种审美规范,即所谓“东坡范式”。王师兆鹏先生最早提出唐宋词演变史中的三大范式:“一是由温庭筠创建的‘花间范式’,二是由苏轼创立的‘东坡范式’,三是由周邦彦建立的‘清真范式’。”[1]139并总结“东坡范式”相对于“花间范式”之“变”,凡四端:其一为主体意识的强化,即“词的抒情主人公由‘共我’向‘自我’的转变”[1]139;其二云感事性的加强,即“由普泛化的抒情向具体化的纪实的转变”[1]145;其三乃力度美的高扬,即“词的审美理想由女性化的柔婉美向男性化的力度美的转变”[1]149;其四则是音乐性的突破,即“词从附属于音乐向独立于音乐的转变”[1]153。在“东坡范式”的这四端变化之中,前三者皆关涉到词作文本空间的艺术呈现。其中第一和第三两点,正是促成苏轼词之文本空间形成独特艺术呈现的关键所在:主体意识的强化,使得苏轼旷达的精神气质与博大的胸襟抱负被熔铸到词作之中,从而打造出一种因气势壮大而开阔的文本空间,完全区别于花间词之狭小与精致;高扬的力度美,则赋予苏轼词之文本空间一种向外的张力,使其极具充实的丰盈感。总此两端,可谓苏轼词之文本空间具有“橫放杰出”的艺术表现。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晁补之论词言论有云:“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2]125这里的“横放杰出”一语,原本是针对苏轼词“不谐音律”及“曲子中缚不住”之特点而言的,属于“东坡范式”之第四点变化范畴内的问题。但借用这四个字形容苏轼词文本空间的特点,也是恰切的:“横放”言其开阔,“杰出”谓其丰盈。
一、士大夫词文本空间之“气象”的扩大
苏轼词之“变体”,并非横空出世的突变,而是“士大夫词”的艺术经验在词史中不断积淀所形成的一种进化结果。“士大夫词”肇始于李煜,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2]4242邓乔彬先生在《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中曾指出,王国维所谓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当是指李煜之词不是如‘花间’那样为歌妓演唱而作,而是自我抒情的、以气象见长之词。”[3]357所谓“自我抒情”“以气象见长”,正是“东坡范式”中主体性增强与力度美的雏形。刘扬忠先生在《唐宋词流派史》中则对王国维所谓李煜词之“眼界始大”与“感慨遂深”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所谓“眼界大”,指的是艺术视野开阔,题材范围扩大,面向整个人生与社会,塑造深美闳约的艺术境界,而不仅仅局限于温庭筠以来的花前月下、闺房庭院的小范围;所谓“感慨深”,指的是由狭隘地“缘情”(儿女柔情)转向深广地“言志”(天下国家之志、人生重大问题等),具有深沉的宇宙人生的思考和超逾一己闲愁浅恨的大悲哀与大感慨。[4]97
“深美闳约的艺术境界”与“深沉的宇宙人生的思考”皆表明由李煜所开启的“士大夫词”,在文本空间方面与花间词的狭小精致有着相反的艺术表现,不仅突破了闺阁庭院的“小范围”,走向开阔的现实世界,而且藉由文人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慨将文本空间的规模向着无限的宇宙境界推衍开去。李煜亡国后的名篇,确实大多具有此等特质,如《虞美人》一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兰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5]25
这首词具有三个层面的文本空间:第一层乃直观的空间场景,即囚禁词人的“小楼”;第二层是词人回忆之中的“故国”;第三层则为经由人生感悟而衍化出的无限宇宙时空。前两个层面在词中皆有直观的语义表现,比较容易把握,而第三个层面,则需要透过物象去体会李煜所寄寓的深层感慨,如开篇的“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句,虽然源自对昔日帝王生活的怀念,但这一叹问所包含的人生况味却并不止于李煜的个人身世,而是接通了古往今来的无限时空,将文本空间的体量铺展到包蕴万有的宇宙格局上去了。正如刘扬忠先生所言:“李煜亡国后的词,已经不仅仅是自道个人身世之悲,也不仅仅是南唐一隅和五代之末的感伤基调的代表者,而是更有了代表人类某种普遍情感的意义。”[4]87-88是以王国维《人间词话》谓李煜词乃“以血书者”,誉之“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2]4243。“普遍的人类情感”“担荷人类罪恶”,这种大格局、大气象,自然是花间词无法比拟的,而格局与气象的扩大,也必然会使得词作文本空间的体量得到扩充,呈现出一种宏阔、博大的空间感。
叶嘉莹先生曾指出:“诗人的关心面如果深广,则其作品中之意境自然便也会随之而加深加广。而且这种感发生命还不仅是关系于诗人一己之性情襟抱而已,同时也关系于外在时代之背景与生活之经历。”[6]388而李煜词能够成为“士大夫词”的开端,则正是源于其“外在的时代之背景与生活之经历”,这其实是颇有偶然意味的。如果李煜没有经历从帝王到阶下囚的人生落差,便不会有“将前期享乐的声色之词,变为亡国后的血泪之作”[3]199的创作历程。也就是说,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发生在李煜身上,本质上是其特殊人生经历所造成的一种不得已的结果,而并非具有明确意识性与目的性的艺术选择。同时,也由于李煜的特殊人生经历,导致其词作中接通宇宙的人生感悟无不伴随着悲凉凄惨的意态情绪,这同样会导致文本空间内质的柔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空间感缺乏向外扩张的力度。
“士大夫之词”发展至北宋,出现了晏殊和欧阳修这两位极具代表性的词人。晏、欧历来被视为南唐词风在北宋的接续者,同时二人又都是饱读诗书、富有学养的文人士大夫典范。因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也无论二人如何看待词的文体功能,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都会自然而然地流入其词作之中,使之具有一种同样能代表人类普遍共同情感的“生命意识”。孙立先生在《词的审美特性》中曾指出:“宋词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所意欲超越自然生存、追求身心相对自由的人生终极目标。”[7]105这种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生命意识”,自然也会体现出一种接近宇宙无限性的空间格局。且看晏殊那首著名的《浣溪沙》词: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8]21-22
这首词与李煜《虞美人》词一样,其文本空间同样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其一,直观的“小园香径”;其二,由此刻而回忆的“去年天气旧亭台”;其三,推衍向无限宇宙的人生思考。第三个层面的人生思考,主要通过“夕阳西下几时回”之一问与“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两叹传达出来,即有限人生与无限时空的矛盾,感慨个体生命面对广袤宇宙的渺小与无奈,是以陈廷焯于《词则辑评·大雅集》卷二谓之“有一刻千金之感”[9]2146。这种极富哲学意味的人生感悟,无疑带给词作一种更大的空间格局,恰如孙虹先生所言:“晏殊词作中出现最多的主题是自然与人类,永恒与无常的对峙中,岁月如流,青春不再的咏叹,其中寄寓了人类生存中最深切的徒唤无奈之情。在晏殊之前,这也是唐五代词不变的旋律,但是,唐五代词特别是《花间集》,它自限于表现女性情感的狭隘空间,并且,一味地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10]136
欧阳修词中的优秀作品,同样大多体现出有限个体生命面对无限宇宙时空的不满足感,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之“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11]31、《采桑子》(十年前是樽前客)之“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与“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11]30,等等。对此,叶嘉莹先生认为:“欧词在其表面看来虽有着极为飞扬的谴玩之意兴,但在内中却实在又隐含着对苦难无常之极为沉重的悲慨。赏玩之意兴使其词有豪放之气,而悲慨之感情则使其词有沉着之致。这两种相反而又相成之力量,不仅是形成欧词之特殊风格的一项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支持他在人生之途中,虽经历挫折贬斥,而仍能自我排遣慰藉的一种精神力量。这正是欧阳修的一些咏风月的小词,所以能别具深厚感人之力的主要缘故。”[6]97-98
晏殊、欧阳修将得自现实人生经历中的思考与感悟写入词中,虽然较之李煜多少有了一些自主性艺术选择的意味,但在本质上依然更多是时代背景促成的结果,如刘扬忠先生所言:“北宋前期文官政治的确立、上层士大夫地位的优越稳定和这个阶层风雅娱乐活动的需要,决定了晏欧词派的产生。”[4]213同时,晏、欧二人有意写入或无意流入到词中的思考与感悟,以及由此带来的愁绪,实际上并不可谓之深刻,因为这些哲理性的内容并非来自对人生苦难的反思与领会,而是一种贵族式的、略带学院派气质的精神思辨。对此,谢桃坊先生在《宋词概论》一著中对晏殊的论述是极具代表性的,“(晏殊)根本没有必要佯为沉湎歌酒以逃避政治斗争的目标,因为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巨大动荡,他也未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12]170,因而在他的词中出现的“愁”,大多是“属于那种安适的生活里暂时的寂寞所引起的淡淡的闲愁。这种闲愁是贵族士大夫们有时感到无聊而产生的”[12]164。故而,“晏殊的词固然包含某些人生哲理,我国古代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这种现象,却不能据此认为他们就是理性的诗人”[12]175。
总之,晏殊与欧阳修虽为北宋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词人,但在“士大夫之词”的艺术发展史中,却尚未臻于极致,是“士大夫之词”之中间阶段而非完成状态。因此,在文本空间的建构及呈现上,晏、欧词也同样没有完全达到“士大夫之词”真正的艺术巅峰,正如孙立先生所言:“晏、欧词理性层的表现,仅是对生命如水、人生苦短的感发与哀叹,人生的悲患意识并不强烈,只是生活优裕的士大夫文人在酒后茶余、观景赏春时自我心灵所流衍出的人生喟叹,词的空间形式尚开掘不深。”[7]168但是,从李煜到晏、欧,“士大夫之词”文本空间的“气象”之大也无疑得到了初步展现,在他们的创作中所逐步累积的空间艺术经验,最终传递到苏轼手中,绽放出“横放杰出”的空间奇观。
二、“东坡气质”造就的“天风海雨”之势
“东坡范式”最显著的特点,即作者将其主体性注入词中,表达自我的襟抱、意绪与思想,从而有别于“花间范式”及南唐词人所习惯使用的“代言体”。郑园先生在《东坡词研究》中曾专门对苏轼词中的第一人称进行探讨:“考察东坡的全部词作,其中,‘我’出现了65次,‘吾’出现了19次,表示主体‘我’的‘余’出现了3次,作为自称的‘东坡’出现了17次。这样的数字不能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创作个性。”[13]145是故,苏轼笔下的很多词作,特别是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之后的作品,都可以体现出一种特有的“东坡气质”,正如南宋汪莘所言,有一种“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14]906,亦如近代词学家叶恭绰《东坡乐府笺序》所言,“盖东坡之词,纯表其胸襟见识、情感兴趣者也”[15]35。而苏轼之为人,又特以襟怀坦荡、乐观旷达著称,因此那些彰显着“东坡气质”的词作,几乎都能在直观感觉上带给读者一种开阔博大的空间感,甚至会有“天风海雨”扑面而来一般的巨大气势。
“天风海雨”一词,是陆游对苏轼词的评价,出自《跋东坡〈七夕词〉后》:“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16]197陆游并没有说明这首《七夕词》具体是苏轼的哪一首作品,但一般都认为是自带“天风海雨”一语的《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①,盖如马亚中先生所言:“苏轼词集中专咏七夕之作有四首,《鹊桥仙》两首,《渔家傲》一首,《菩萨蛮》一首。唯《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一阕最合此跋意境。”[16]197且看其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首《鹊桥仙》还是写在“乌台诗案”之前的作品②,此时的苏轼还处于“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17]134(《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的意气风发时期。而在遭遇“乌台诗案”之后,“魂惊汤火命如鸡”[19]999(《狱中寄子由》其二)的命悬一线之危以及伴随而来的巨大精神摧残促使苏轼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般的精神蜕变。一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青年才子、有为官吏,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样一个被监管的罪臣,这一接近李煜的巨大人生落差无疑使苏轼在思想层面同样得以接近“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的高度。加之获罪后“心存余悸,不敢轻易写诗”[20]的心态,使得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之后所写的词作,能够体现出更加深刻的人生体验与思考,“东坡气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与深化。如此,则词作所传达出的空间感也往往更为宏阔、辽远。最典型的例证,当属《临江仙》一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7]467
这首词除了“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这一大的写作背景,还有更加细致的小写作背景可循,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了这首词的本事:
子瞻在黄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有语范景仁于许昌者,景仁绝不置疑,即举袂大恸,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赒其家。子弟徐言此传闻未审,当先书以问其安否,得实吊恤之未晚。乃走仆以往,子瞻发书大笑。故后量移汝州,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未几,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21]261-262
在这一则本事记载中,苏轼面对有关自己“传以为死矣”的流言而“大笑”,说明此时他已基本走出了初到黄州时迷茫、抑郁与低落的情绪,因此他在词中可以用“夜阑风静縠纹平”这一景物描写暗示内心之愤恨与悲伤的平息,更咏叹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深刻人生体验,而这两句词中所包含的感慨、反思与精神升华,可谓历代经历过重大挫折之人所共同面对的人生命题。由此,这首词在思想层面也就上升到了人类精神普遍性的高度,使得词作之文本空间具有了融通上下四方和古往今来的宇宙格局。词在“长恨”两句处,已藉由深刻的思想内涵获得了极大的空间气象,而结尾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则将这种宏大的气象进一步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推远开去。同时,通过本事记载中“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的结局,可知此二句所写只是苏轼在精神层面的远游,并非在现实中真的“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而正因为这一时空维度上的“推远”只是在精神层面,也就使得“推远”的范围脱离了现实世界的限制,走向无限。
苏轼这首《临江仙》可以呈现给读者如此气象恢弘且有着无限宇宙格局的空间感,可以说是完全得益于其中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倘若只从物象层面考察这首词的文本空间,会发现其时长不过自“三更”至“夜阑”,而其地点除了结尾的想象之辞,也仅仅是在自家门前这一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而这恰恰说明,这类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词通过深刻的思想性所晕染出的空间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物象描写的束缚,在文本空间的构建中做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苏轼的词作中,最能体现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作品,应当是赠予友人王巩家姬柔奴的一首《定风波》:
谁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17]579
词之上片基本上是对柔奴这一人物形象的聚焦式描写,而下片则主要是苏轼与柔奴的对话,盖其词序有云:“定国(王巩字)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17]579单从这一层面的写作背景看这首词的文本空间,其格局无疑是非常有限的。但倘若将王巩贬官等大写作背景纳入考量,则会发现“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一句所包含的人生感喟与生命思考,同样具有宇宙格局。虽然这首词在表面上是苏轼与柔奴的对话互动,但其内在本质还是写给王巩的,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对王巩贬谪遭遇的记述,正可视为这首词的大写作背景,文曰:
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22]318
所谓“以余故得罪”,指的是王巩在“乌台诗案”中因与苏轼有交游而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在所有“乌台诗案”受牵连者中贬所最为偏远,而“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的境遇,也是十分凄惨的。词中“岭南应不好”之问,正是针对王巩贬谪境遇而发。但是,即便是遭遇如此苦难,王巩所作诗歌却依然“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这一乐观旷达的心态,也正与“此心安处是吾乡”相合。结合王巩的贬谪苦难这一大的创作背景来看这首《定风波》,可以发现这首词在思想内涵层面上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其精神核心已触及到如何面对人生失意以及如何看待命运不公这一极具人文关怀意义的终极命题。由此,苏轼将一个极其有限的空间场景内发生的一段简单对话,与宇宙人生的无限空间相接通,在对作品空间感的塑造上实现了以“四两”之笔力拨“千斤”之体量。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笔下具有开阔、宏大空间感的文本空间,并非主要借助具体空间物象的描写来实现,而更多是以其哲人气质在思想内涵层面赋予词作文本空间一种大气象与大格局。元好问将苏轼的这种哲人气质称为“性情”,其《新轩乐府引》论曰:“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23]1383-1384而苏轼注入到词作中的“性情”,用孙虹先生的话说,就是其“耿介直谅、奇伟狂狷的人格精神在笔下的折射,所表达的是士君子得志与不得志,群居与独立,或茂而不骄,或瘁瘐而不辱,不倚不惧、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高雅不俗的人格境界。所以,词可以横放杰出、倾荡磊落、幽洁悲壮、成天地奇观。”[10]180-181可以说,正是因为苏轼之精神气质具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大格局、大气象,他的词作中才能出现具有宇宙格局与气象的宏阔文本空间。正如蔡嵩云《柯亭词论》所言:“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2]4910
三、“运气入词”的空间构建手法
那些体现着苏轼特有人格精神与哲人气质的词作,其文本空间不仅具有无限宏阔的宇宙格局,更往往具有一种向外的巨大张力,也就是一种空间内部的丰盈感。比如苏轼词中那些“四两拨千斤”式的空间建构,其最表层的空间场景一般是有限的,但其深层的思想内涵却可以接通天地精神而生成一种宇宙格局的大气象,冲破表层空间场景的局限。这种深层内涵对表层空间的冲破,无疑会呈现出一种向外扩展的张力美,且力道极强。胡寅《酒边集序》描述阅读苏轼词的观感,称其“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24]403,如果借用这一描述对苏轼词的文本空间艺术进行阐释,可以将“尘垢”理解为苏轼词的表层的空间场景,而超然乎其外的“逸怀浩气”则正是基于“东坡气质”的深层思想内涵。无形的“逸怀浩气”冲破有形“尘垢”的限制,不仅扩大了文本空间的体量,更造就了一种满溢的丰盈感。
当然,对“逸怀浩气”作以上理解仅能针对苏轼词中的一小部分。在苏轼具有“变体”意义的词作中,并非每一首都具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深刻思想。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词作的文本空间就会坍缩至“花间范式”下的狭小。这一方面是因为“变体”词本身即具有以阳刚之气变“本色”词之阴柔之美的意义,由阳刚之气的力度美所支撑的文本空间,其体量自然会大于被阴柔之美弱化的文本空间,正如杨海明先生所言:“‘变体’词中另又增添了很多表现愤怒感情和狂放意态的辞语,这就更使其风格变得遒劲有力和男性气十足。”[25]425又云:“‘变体’词内既因吐发英雄豪杰之志气而充实着坚实丰厚的人格力量,又因较多采用直抒胸臆、任情挥洒的写法而充盈着洪大强盛的气势,故在风格和美感方面,就‘弸中彪外’地呈现出雄健豪迈的阳刚气貌”[25]461,所谓“弸中彪外”,正是一种对刚性、扩张性的空间感的描述。另一方面,单就苏轼“变体”词的艺术特质而言,其相对于花间词等“本色”之词,又处处体现出一种丰沛而源源不竭的“文气”。这种“文气”在苏轼笔下,则正是那份可以“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24]403的“逸怀浩气”,其流为词作中的文字后,自然也会给人一种“登高望远”一般的开阔空间感。
最能体现苏轼强大“文气”的词作,当属在密州创作的《江城子·猎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17]146-147
这首词往往被视为苏轼“变体”词风的典型代表,而且是由苏轼本人认定的。在给友人鲜于侁的尺牍中,苏轼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22]1560(《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无柳七郎风味”与“自是一家”,正是苏轼在创作“变体”词这一意义上出现自觉的体现,正如刘扬忠先生所言:“苏轼这里既然是把它作为与柳七风格相异的‘自是一家’之作列举出来的,则此词就无疑具有代表苏轼新词风、显示苏轼改革词体之方向的典范意义。”[4]190-191苏轼自己用“壮观”二字描述这首“变体”词作的整体艺术风格,而从空间意义上讲,“壮观”同样是一种对宏阔空间感的描述。但是,如果我们在词作原文中寻找直接描述空间的语辞,所得仅有“千骑卷平冈”“西北望,射天狼”这两处,虽然这两处空间描写的确具有开阔、宏大的特点,但似乎尚不足以将整首词的直观空间感推向“壮观”的程度。
那么,这首《江城子》究竟“壮观”在何处呢?纵观全词,可以发现虽然这首词以郊猎为题材,但苏轼所书写的重点并不在于描绘狩猎的场面,而是将最多的笔墨放在了对“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样一种自我形象的塑造上。诸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等词句,都是对自我形象的聚焦式描写。聚焦式描写所塑造的空间感,原本应该是极其狭小的,但是苏轼在这首词中运用聚焦手法所描绘的,是郊猎的场景中英武飒爽的“太守”形象,浑身散发着阳刚之气与豪迈之风,使读者同样可以感受到仿佛“天风海雨”般的巨大气场。因此,这首词所呈现出的空间感之“壮观”,正在于苏轼所塑造的自我形象所散发出的阳刚豪迈的气质风神,其文本空间并非仅仅借助带有空间信息的物象描写而建构,更多是由苏轼与生俱来的那种刚强而奔放的“逸怀浩气”晕染而成。苏轼这种以“文气”作词的手法,被杨海明先生总结为“运气入词”,并视为“变体”词的特有美感:
宋代词论本身并不丰富,而对苏、辛“变体”词的赞词则更不多见;但就在这为数很少的后一类词论中,竟又随处可见这个“气”字,这就说明:“变体”词那富有男性阳刚气概的风格和美感,便在很大程度上与词人平素的“养气”、“蓄气”和写词时的“运气入词”密切相关。[25]440
“运气入词”,也就是跟随“文气”的流宕去布置词作的行文脉络,往往是随作者之“心”而动,“心”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体现出一种不求工而自工的自然与自在。正如邓乔彬先生曾指出的:“苏轼以诗为词……因才大气盛,其长调之作多为才气所运,难见精心结撰的人工痕迹。”[3]489而以这种方式所构建出的文本空间,其中物象亦往往被赋予浓厚的作者主观色彩,如《八声甘州·寄参寥子》开篇云:“有情风、万里捲潮来,无情送潮归。”[17]668“有情”或“无情”皆源于苏轼的主观情志,正如叶嘉莹先生的解读:“此词开端二句写万里风涛,气象开阔,笔力矫健,外表看来似乎极为超举,然而在其‘有情’‘无情’与夫‘潮来’‘潮归’之间,却实在也隐含有无穷感慨苍凉之意。”[6]177又如《水调歌头·快哉亭作》之结尾两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17]483,“风”之所以能有“快哉”之感,是源于苏轼自己的胸怀中存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是苏轼特有的豪迈胸襟所赋予自然物的主观属性,明杨慎《批点草堂诗余》点评云:“结句雄奇,无人敢道。”[9]302正是看到了此句乃脱胎于苏轼独特的个性气质,他人难以学得其精髓。
总之,这种“运气入词”的写法,在文本空间的构建方面具有不局限于物象以及主观色彩浓厚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也恰与苏轼在《自评文》中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相合拍,文曰: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22]2069
虽然《自评文》所论乃针对文章这一文体,但苏轼作为众体皆擅的文学家,其创作思想与写作手法应当是大体相通的。杨海明先生在《唐宋词史》中即曾指出:在苏轼词中“‘情性’就象滔滔汩汩的泉水一样,从胸中奔涌流泻而出,又‘随物赋形’地构筑成了不同的词境;‘文字’在他笔下,就像驾轻就熟的骏马一样,横奔突驰在抒情的原野上,却又‘中含法度’、‘纵勒有节’。”[26]313这一解说正是借用《自评文》中的文论去解说苏轼的词体创作。如“滔滔汩汩的泉水”的“情性”,也就是苏轼用以晕染出词作之文本空间的“逸怀浩气”,充溢于《江城子·猎词》中的强大气场,难道不正如“不择地而出”的“万斛泉源”吗?而这种有如“万斛泉源”的“逸怀浩气”,以主观的方式对文本空间进行“随物赋形”,在词作中构建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的宏阔文本空间。
苏轼能够通过“运气入词”的手法使其词作呈现出气势磅礴的空间感,其根本原因依然在于他身上那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质。换句话说,是因为在苏轼的性格中本身即富有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所以才能够有充足的“文气”注入词中,从而形成具有开放格局的“大气”文本空间。而正源于此,导致这种“运气入词”的空间构建手法很难被其他词人所取法继承,因为要实现这种手法,首先必须具有接近于苏轼的气质个性。因此,“运气入词”这种文本空间构建手法,更多与词人的天赋气质有关,并不是可学而至的,故而在苏轼之后,除了武人出身的贺铸与辛弃疾,以及南北宋之交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主战派词人,便很难见到同样以巨大的气势晕染出宏大文本空间的作品了。
注 释:
① 邹同庆、王宗堂二位先生将陆游此跋文编入《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一词之“参考资料”,未知何据。见《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18-620页。
② 邹同庆、王宗堂两位先生认为《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作于熙宁七年(1074),这距离“乌台诗案”发生的元丰二年(1079)尚有五年时间。参《苏轼词编年校注》,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