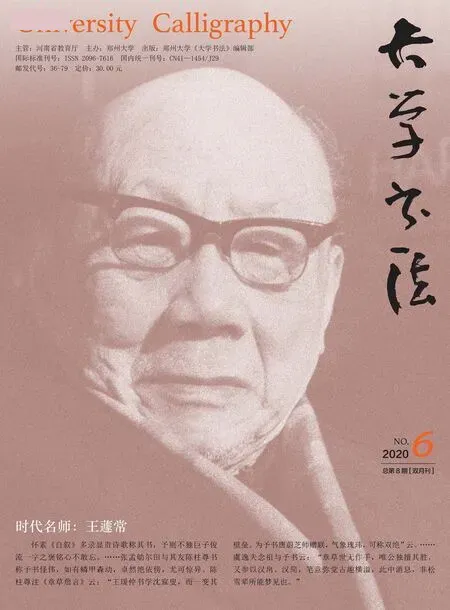“书卷气”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规约
——论苏轼书法品评的建构与意义
汤传盛
引言
众所周知,黄庭坚曾评苏轼之书云:“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黄庭坚将苏东坡书作中流露出的所谓“学问文章之气”,作为评判苏轼书法相较于他人书法较高一筹的原因。显然,在黄氏看来,学问文章与书艺水平的高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自此以后,苏轼的书法在后世接受的过程中,“书卷气”是不可或缺的品评准绳之一,苏轼书法也打上了“书卷气”的深刻烙印。此外,就历代文人书法而言,“书卷气”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品评标准为人们所不断阐释。那么为何书法作品需要“书卷气”?“书卷气”的内涵是什么?“书卷气”作为一种精神气质如何在书法作品中予以表达?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对于书法中“书卷气”的内涵,已有众多学者对其进行探讨。[2]然学界虽对于“书卷气”的理解有着各自不同的阐释,也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但是普遍理解均从“书卷气”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气质的角度去考察。那么“书卷气”自宋以后成为一种品评标准,书法作品“书卷气”的外在形式与内在要求具有什么样的联系?需要我们思考。
一、“气” 与“书卷气”的文化分疏
所谓“气”,说文解字释:“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外历代都对“气”有着诸种不同的阐释,于此不再赘引。可以说,“气”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实为古人常论,从具体的对自然状况的描述到抽象的万物之本源,都蕴含着“气”。可以说,“气”一字本身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巨大的阐释张力,而随着历史对“气”的不断演绎,对于“气”的内涵也延伸到书画理论中,产生了诸多与“气”相关的美学范畴,如气韵、气势、气象等。对此论述,不胜枚举,就近而言,如余绍宋言:“书法应重气韵,历来无持异论者。盖作字不讲气韵,则必成为世俗应用的符号,而非美术;作画不讲气韵,则必成为工匠应用之图案,亦不能称为美术,其理正相同耳。”[3]
就艺术中的“气”而言,一方面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自身所具备的风神气质,另一方面是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内在韵味。就创作主体而言,“气”一方面指艺术家本身的先天禀赋,难以对其进行模仿与指实,如董其昌言:“气韵不可学。”另一方面是指艺术家自身在成长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后天修养。如魏晋时期,曹丕便提出“文以气为主”,把“气”与文学艺术的创作联系在一起,他提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4]。他从创作角度,对“气”进行了辨析,同时说明了在艺术创作时,主体的能动性作用,“巧拙有素”的表现形式与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性也同样有所联系。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无法将这种先天禀赋与后天修养完全割裂开来,理应辩证地去对待。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时,将主体之禀赋、气质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外化于作品,观者通过对作品外部特征的把握,从而理解作品所体现的精神气质。
而当我们论及书法时,由“气”这一元范畴也延伸出诸多相关子范畴,诚如刘熙载所言:“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 皆士之弃也。”[5]综言之,正如北宋张载所言:“凡可状者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
然当我们谈及“书卷气”,在现代语境中,我们都明白其与“腹有诗书气自华”之异曲同工。《汉语大词典》中释云:“书卷气,指说话、作文、写字、画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读书人的风格与气质。”[6]自宋以前,在文艺理论中似乎并未言及此论,但在早期文论中,已有表现对才学的重视,如《荀子·劝学》中云:“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可以知道,在早期文艺理论中,虽强调读书为学之重,但“书卷气”并未被拔高至艺术品评范畴之中,在宋以前也似乎并没有以学养、读书来评判书法艺术之高下。那么为何从宋代开始,以“学问文章之气”来看待书艺高下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呢?如果我们熟悉宋代历史,便可从中窥知一二。
据《宋史》记载,太祖赵匡胤提倡文教,宰相“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以至于铸成错事,遂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宋史·文苑传序》[7]也记载,宋太祖“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此后,宋代帝王之“重文”传统沿袭而下。虽说,这不免充斥着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意味,但也对宋代学术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而“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尹,无不擢科”,使整个宋王朝“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以至于朱文公(熹)颇有微词:“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如此度日而已。”另一方面,宋代科举取士之政策的独特性,“取士不问家世”,使宋代教育规模逐渐兴盛,无论官学、私学都达到顶峰,大大地激发了平民文人士子对学问的追求、对进取功名的狂热。从汪洙那著名的诗句中我们便可知宋朝朝野内外的读书、治学之风气:“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人对“学问”的追求,读书、治学之风气的浓厚,远超历代,从宋代流传诗歌中均可找寻,而这种对学问文章的推崇也在书法品评中予以推崇,如黄庭坚:“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义高妙,似非吃人间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8]“士大夫三日不读书, 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 。”[9]“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致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10]“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11]李昭玘:“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终不能见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12]
可以说,整个宋代书法品评观念弥漫着对学问的追求,这与特定时期的文人眼光有着紧密关联。从钱锺书先生所言“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有一种从以作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探讨艺术家气质为中心的倾向”[13]可以知道,苏轼乃至宋代文人,不再对书法艺术的外在形式予以过度拔高,而逐渐转向于对艺术家主体之精神气质的向度。而学问修养在整个宋朝的无限拔高,使书法的品评开始走向对于“学问文章之气”的追求,以致后来“书卷气”在书史的长河中逐渐成为一种书法品评的美学范畴。
随着书法艺术的历史性发展,对于所谓“书卷气”的论述亦有所嬗变,诚如李彤先生所言:“书法品评标准是书法品评所遵循的艺术评价尺度,但其实质则是审美主体对书法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因而其虽有客观性的一面,但在书法艺术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的不同,每一时代的品评标准往往会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相对性。”[14]如董其昌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俗,自然五壑内营。”[15]清代苏淳元《论书浅语》在论及书法艺术的技法与学养的关系时说道:“书虽手中技艺,然为心画,观其书而其人之学毕见,不可掩饰,故虽纸堆笔冢,逼似古人,而不读书则其气味不雅驯,不修行则其骨格不坚正,书虽工亦不足贵也。”[16]可以看出,苏淳元对书法的技道关系有其独特的见解,书法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一种技术性的体现,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是人心灵之物化,从书法作品中可对书家学养得以体会。作为技法的书写训练,在形而下的层面虽然可做到技艺精熟,但如若缺少学养的支撑,则气味、骨格等便不够雅正,因此这种艺术作品“书虽工亦不足贵也”。从苏淳元的话语中,我们也可看出,其论点的逻辑起点在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书家,换言之,书家的修养是决定书法作品是否雅驯、坚正,具有“书卷气”的第一要素。李瑞清则说:“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17]马叙伦《石屋余渖》:“鲜于伯机书以雅胜松雪,张伯雨不及伯机而尤雅于松雪……余所谓雅者,以山林、书卷为主要对象。有山林、书卷之气韵,书自可目。”[18]客观而言,赵孟頫书法可谓精熟之至,而为何马叙伦在评赵氏书法时,认为其雅不及鲜于枢和张雨?而其批评赵孟頫书法不雅之时,也道出了其做出这种判断的标准,很明显,马叙伦认为赵氏书作气韵不够,是由于“书卷气”不足为世人所诟病。
二、苏轼艺术思想中的对“书卷气”的追求
如前文所述,在宋代文人眼中,对书法的评价尺度逐渐游离于书法技法本身,开始转向对创作主体精神气质的品评,而具体的表现之一则是对读书、治学等字外功夫的推崇。北宋艺术史上的典型代表无疑是苏轼,无论在书画、文章或道德层面均成就卓然。那么苏轼眼中之“书卷气”是如何呢?
首先,就书法认识而言,苏轼对于书法的认识是基于对晚唐之后的书学凋敝的立场上的,他对晚唐五代时期的艺术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19]他以贯休和亚栖为例来抨击诗词与书法,认为这时的艺术粗野鄙俗,且不留余地地概括了唐末五代之艺术“大率相似”,可见,他对于唐末五代以来的艺术风气极其反感。那么,随着对于当时艺术的抨击,他也展开了自身对书法艺术的认识,“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20]。可以说,苏轼的艺术思想尤其是书法思想,首先是站在批判唐末五代书学的基础之上,在抨击这种现象之后,再慢慢道出其自身的思想:“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1]苏轼以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四人为例,来说明对于艺术中的技法问题,随着时代的演绎,至唐代,几乎已经完备。在这样一种层面之上,苏轼进而便认为:“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苏轼对古人书论有着一定的继承,同时对书法中的“工”与“不工”有了独到的认识。
就书法实践而言,苏轼不崇尚对形的过度模拟,从苏轼对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的赞赏中我们可知:“颜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此言也。”[22]我们看到,苏轼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不在于其字形或大小的准确,也就是说,书法外在形式并不是其对于颜真卿书法赞赏的标准,其对书法的气韵更加看重。那么,气韵可能较为虚空,从何可知呢?他说道:“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从这句话,我们便可知道苏轼对于颜真卿书法的欣赏,必先知其为人。那么,我们便可知道,苏轼所谓的“气韵良是”,在一种层面上便是知其为人后,由“人”所散发之风神气骨。苏东坡在论诗文与绘画创作时也有诗曾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对于艺术中的书卷气流露,我们并不能完全以形式美的要求来予以概括,毕竟作为审美范畴的其中一个标准来说,书卷气是一种精神气质的显现,完全将其落归实处难免有失偏颇。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来说,一方面,艺术作品中书卷气的流露必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这种标准决定了我们对艺术作品欣赏时所产生的审美共识;另一方面,书卷气作为一种精神气质,它从一定程度上既是书家对艺术作品的先天“赋予”,也是欣赏者对艺术作品的后天“追认”。
就书法艺术的欣赏而言,苏轼也同样持有独特的理解,并提出“外枯而中膏”的审美理想:“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我们知道苏轼在艺术中崇尚“平淡天真”,而所谓的“淡”,即以他认为的“外枯而中膏”为佳,乃是抛除艺术外在形式,或者是视觉效果的单纯品鉴,进而是对艺术作品所生发的气韵的把握,这种把握的重点则在于艺术家自身精神气质的涵养。那么如何涵养气质,则在于学问与道德。“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乎书……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间其为人邪正之粗云。”[23]苏东坡认为“君子小人必见于书”,并且直接以“以貌取人”否定了“以貌取书”的论断,从中也可看出苏轼对书法的欣赏不仅仅桎梏于笔墨的外在形式亦即书法艺术的直观呈现效果,而是更为推崇笔墨之外的气韵。因此,后来他又说道:“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书家并不将书法的笔墨技法作为评价书法作品的标准,而在笔墨之外的学养、人品等则是判断书法优劣的重要标准。这与前文所述一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代风气对书家群体的影响。
从我们对苏轼艺术思想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苏轼对书法艺术之品评,首先不拘泥于书法作品的外化呈现,但同时也不否认书家对于书法艺术之形式技巧的追求与模拟的学书历程。一方面艺术不仅仅是技术,另一方面技法对于任何艺术而言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就书法艺术的品评而言,对于书法之欣赏,工与不工,实则非艺术欣赏之核心把握,而应“在笔画之外”把握书家、书作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如何体现,则须要“论书兼论其平生”。而论其平生的一个重要尺度则在于书家亦即创作主体本身的学问与道德。在笔者看来,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后世为何总以“书卷气”评价苏轼书法的重要原因。主体的精神气质是宋代文人对于艺术把握的重要标准,正如李之仪所说“凡书精神为上”的思想渊源与时代因素。
三、“书卷气”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规约——苏轼书法品评的建构与意义
可以认为,苏轼作为宋代书坛的代表人物,其弟子门生均不同程度地对其思想有所承继,正如李之仪之言:“东坡帖,乃其子迈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苏氏诸子,源同派异,种种皆有过人处。”从宋代文人对苏轼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思想对其自身艺术成就的影响:“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东坡)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24]
可以说,自苏轼之后,书家对苏轼的艺术评价皆统摄于其思想的前提之下,不以工拙论其书,不以形式论其书,而更加注重的则是书艺之外的书家本体的精神气质与学养,从而逐渐确立其书法具有“书卷气”之说。
有学者认为:“以书卷气评书,既忽略了学养如何渗透进笔墨,也忽略了作品的内形式如何转化为外形式,只是凭欣赏者的经验直觉,因此,尽管它有很大的合理性,却无法言之于人。”[25]的确,对于书卷气的理解,无法言之于人,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从“书”之外对书法作品的判断对于后世、对于当下的艺术评价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书卷气的追求是我们对书法艺术的一种接受,如果我们承认书法艺术的发展是由诸多因素所造成的,那么对于书卷气这一笔墨之外的审美趣味则是需要我们在不断接受中去不断丰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彰显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与张力。对于“书卷气”的追求是一种对人生历程、人生体悟的涵养,正如苏轼所言:“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少年时期书法艺术的呈现必然需要经历技巧的锤炼,诗、书等呈现的“气象峥嵘”,随着自身精神气质的涵养,随着人生体悟的增加,“渐老渐熟”,得之“平淡”,看似平淡,实则不是,“绚烂之极也”。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严格地来说,看见东西的并不是眼睛,看见东西的是大脑或心灵。”就艺术而言,我们对书法作品的鉴赏与判断,与其说取决于作品呈现的直观效果,还不如说最后要归结于作品背后所显现出的悠长而深沉的“气韵”。对于这种“书卷气”的把握便需要艺术家、作品以及欣赏者三者的高度统一,虽然这样难免使书法艺术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不也正是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吗?
当然,苏轼作为书史上一个经典的建构,其因素有很多,但是同时期及后世对其书作的评价均从其自身的艺术思想出发。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认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立,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到证实”[26]。如果说,“二王”经典的建构是后世对其在不断接受的过程中逐渐完善,那么,苏轼经典的构建则直指苏轼自身,苏轼自身的艺术思想、艺术地位、艺术成就使苏轼的艺术打上了“书卷气”的烙印。我想,这也是苏轼成为艺术史上一个经典所体现出的范式意义吧。
结语
对于书法“书卷气”的评价,我们应赋予其客观的评价:宋代书法中“书卷气”作为一个品评标准而影响后世,与宋代强调读书治学之风气有关;苏轼书法在宋代及以后被打上“书卷气”的烙印,亦有其必然的一面。此外,对于苏轼的书法称为一种经典,也正由于苏轼学养、涵养的丰富,与其成为书史上一个经典人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欧阳修所言:“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久。”
自宋伊始,“学问文章之气”在文艺理论中开始强调,可以说,宋以后,对于书法品评不再以技法论高下,“文人书”“文人画”亦不再以工与不工为唯一尺度,书法的评价逐渐向形式外之诸因素游离,可以说,其影响直至今日,也为我们品评当下文人书法寻找到了突破口,当然,也为一些“名不符实”之文人书作找到了拔高自身的“借口”。可以说,“书卷气”的产生,从好的一面来说,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利于我们更为客观地看待书法艺术之主体的精神气韵,从另一层面来说,也使书法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使书法的欣赏具有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就“书卷气”的审美范畴而言,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也有着一定的嬗变,但总的来说,在更广的层面中则直指“韵”的要求。一方面,“书卷气”的过度拔高,难免使我们理解书法时增加了一些难度,但是也使我们对书法艺术的阐释赋予了更为广阔的张力;另一方面,完全就形式美而言,对于“书卷气”的理解必然有失偏颇,毕竟艺术不仅仅是技术,但完全将“书卷气”置之于一种精神气质也未免过于人云亦云。“书卷气”使书法自宋代以后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气质与神韵,虽然,对“书卷气”的品评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书家、书法作品本身,但它却毫无疑问地高于作品本身,正如那句著名的诗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注释:
[1]黄庭坚.山谷集:卷29[G]//集部,别集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历来研究者的论述中主要有几点:一、书卷气并非书法美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而是人们对书法美的某些具体形态的一种综合性的判断与评价。(陈方既《气息论》)二、刘正成在谈及书法中的书卷气时指出:“所谓书卷气,是指文人书写、书法家书写时所留下的审美特征,其书法墨迹所留下的是书法家书写时的心理特征和感情态迹,即‘意’和‘神’的运动轨迹,这是一种非制作的美,一种‘灵’的美。”(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1.)三、山东大学郑训佐先生言:“所谓‘书卷气’,是书家的文化性格在书法创作中艺术化的折射,其中含有社会信仰、伦理原则、美学风范等层面的内容。但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卷气’具有不同的内涵。以恋古心态看‘书卷气’,只能使之面临被遗弃的尴尬,而完全将‘书卷气’视为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的古典原则,无疑又会造成现代书法文化意蕴的缺失。”( 郑训佐.论书卷气的文化内涵[J].山东社会科学,2015:37—38.)曾有法国学者也谈及书卷气:“书卷气是读书人有别于不读书人的一种气氛、一种优势、一种平直,除了认识世界、分析问题、批判能力方面高人一筹,还有独立和自由的渴求,以及善于接近人、善于表述、令人产生好感等之外,他还能给人一种见多识广,站得高看得远,有过人的智慧和高尚品味的印象和形象。” (小土.字外功夫·书卷气·意境——关于“书法书卷气”问题的思考[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7(4).)
[3]余绍宋.余绍宋集:国画的气韵问题[M].浙江: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136.
[4]曹丕.典论:论文[G]//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5.
[5]刘熙载.艺概:书概[M].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6]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873.
[7]脱脱,等.宋史[G]//史部,正史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黄庭坚.山谷集:卷29[G]//集部,别集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黄庭坚.山谷集:卷29[G]//集部,别集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黄庭坚.山谷集:卷29[G]//集部,别集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黄庭坚.山谷集:卷29[G]//集部,别集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李昭玘.乐静集:跋东坡真迹:卷9[G]//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128.
[13]钱锺书.苏东坡的赋:序[G]//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11.
[14]李彤.申情尚意趋雅重韵:北宋书法品评刍议[J].中国书法:书学.2018(4).
[15]董其昌.画禅室随笔[G]//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256.
[16]苏淳元.论书浅语.[G]//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866.
[17]李瑞清.玉梅花庵:书断[G]//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095.
[18]马叙伦.石屋余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39.
[19]苏轼.东坡全集:书诸集伪谬[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苏轼.东坡全集:书诸集伪谬[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苏轼.苏轼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759.
[22]苏轼.苏轼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813.
[23]苏轼.苏轼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818.
[24]黄庭坚.山谷集:卷29[G]//集部,别集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楚默.书卷气的几个重大问题——兼评“论书卷气”[J].书法研究,2006(123).
[26]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浦元,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