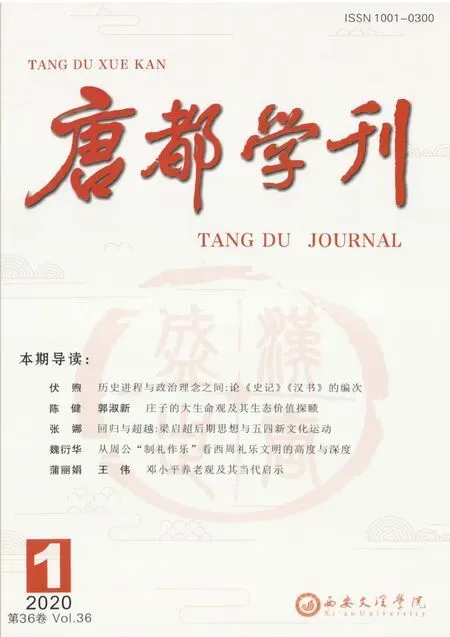王充教育经历新证
李 浩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近几十年来,受惠于徐复观、钟肇鹏、蒋祖怡、任继愈、林丽雪、大久保隆郎、周桂钿、吕兆厂(1)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钟肇鹏《王充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蒋祖怡《王充卷》,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林丽雪《王充》,台湾大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大久保隆郎《〈後漢書〉王充伝質疑について》,福島大学教育学部論集(人文科学部門),1983年;周桂钿《秦汉思想研究(2 王充评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吕兆厂《王充生平和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前修时彦对王充生平问题的不断求索,学者们廓清了很多误解,达成了不少共识,但在涉及经典命题的细部研究时,仍有可资探讨之处。以王充的教育经历为例,它对王充知识构成、话语表达、思想视阈影响之深远,毋庸赘言,然诸如王充“是否有过受业郡国的经历”“曾否赴洛阳求学”“曾否师事班彪”等问题,学人至今莫衷一是。他若王充幼年之学习经历,或因受制于文献,至今亦鲜见细致的梳理。有鉴乎此,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前揭问题重加考辨,以期进一步澄清误解,凝聚共识。
一、王充早年学习经历考
王充幼年习业乡塾,接受了典型的汉代经学教育。这段经历主要见于《论衡·自纪篇》(下文引《论衡》各章仅称篇名),其辞云:
六岁教书……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1]1188
《自纪篇》篇幅虽繁,但详于托主客问答以自辩,生平行事反倒着墨不多。且该部分叙事时间跨度较大,不免令读者有跳跃之感;加之行文间杂俪辞偶句,殊不易解。不过,借助旁证材料,我们还是能够了解王充早年的学习内容与大致的学习进度。《自纪篇》的三个关键点——“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手书既成”都与练字、识字有关,它们是幼年王充最重要的学习任务之一。考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2]1721
由此可知,经由汉代知识精英的不断改造,至王充时代,“字书”已经逐渐褪去秦代“以吏为师”的旨在培养帝国行政人员的极端功利色彩,成为辅助士子阅读儒家经典、培养具有儒家道德理想的“师吏”的工具。举凡《汉书·艺文志》中所言,班固所续字书幼年王充自不及见,扬雄《训纂篇》从成书到普及亦需要一个过程,那么,王充幼年在书馆习字的教材主要应是《苍颉》《爰历》《博学》和《急就篇》。又,观《论衡》曾引用且大段阐释《尔雅》中《释宫》《释鱼》《释天》诸篇之内容,可知王充年岁稍长后亦曾研习辞书《尔雅》。复考崔寔《四民月令》“正月”条云“砚冻释,命幼童人小学,学篇章”,崔氏自注:“幼童,谓十岁以上至十四;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3]。然则识字、习字而外,幼年王充尚需学习《六甲》《九九》。《汉书·食货志》谓“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2]1122亦印证了此点。这里的“六甲”指“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指“九州岳渎列国之名”,“计”与“九九”则指“计数之书,若今算经也”[2]2824。《太平御览》卷385人事部26“幼智”条引《会稽典录》云:“王充,字仲任,为儿童游戏,不好狎侮。父诵奇之,七岁教书数。”[4]1781学者或以为此记载与前引王充自述“六岁教书”说相龃龉,但参诸前揭《四民月令》《汉书·食货志》之引文,可知二者断不必以矛盾视之。盖幼童之启蒙本非一蹴而就之事,此点《自纪篇》已然揭橥,更何况《会稽典录》叙述王充的蒙学经历时增一指代“计数”之学的“数”字,似反而更接近汉代教育的实际。
此外,考虑到“汉人读书,《小学》与《孝经》同治,为普通之平民教育”[5]91,则王充早年亦曾深入研习《孝经》。尽管统观《论衡》全书,王充在客观上未能做到《孝经》所提倡的“显父母”“恐辱先”[6],他本人对儒家“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等行为亦颇不以为然,但《孝经》对王充的影响仍不容小觑。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云云,因与王充《无形》《龙虚》《奇怪》《量知》《别通》《状留》《辨祟》等篇的言说立场契合,几乎成为他处理许多问题时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他若《开宗明义章》《丧亲章》《感应章》《诸侯章》亦间为《论衡》所征引[7]276。
详细梳理王充早年的学习经历,印象有二:其一,王充《自纪篇》回顾幼年学习经历时已开始进行形象的自我建构。如以“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突出“异于众人的我”[8]22-29,以“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暗合“知室家长幼之节”[2]1122的儒家幼学教育理想等等。但若将王充从“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到“手书既成”间的表现与“七岁能通《论语》”[9]862的马续、“七岁通《春秋》”[9]1241的张霸或《太平御览》卷384、385人事部26“幼智”条记载的其他汉代神童相比[4]1773-1782,仍略显逊色。然则王充所承受之家庭背景、身处“古荒流之地”的地域环境等因素对其生平之影响与限制,在此时已有所显现。其二,王充早年接受的是典型的汉代教育。王氏所习基本典籍与东汉的王公贵胄(2)《后汉书·皇后纪》载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18 页;又谓顺烈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38 页。、士人精英、底层胥吏[10]相比并无根本性差异。它决定了无论王充的思想在今人看来如何“特异”,却没有“一人独有之,而同时之人,绝无与之互相出入者”[11]886的可能。近代以降之论者,“或以为(王充)千古一人,或以为(王充)并时无两”[11]886, 恐非平情之论。
二、“受业郡国”说驳议:再论王充曾赴洛阳求学
结束小学、初级算术和《孝经》学习后,王充赴京师洛阳深造,进入“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1]1188的新阶段。对于这种进阶教育,赵翼《陔余丛考》卷16“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云:
士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12]
将其与《后汉书·王充传》“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后汉书》李贤注引《袁山松书》“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9]1629合观,我们认为,对活跃于东汉早期的王充而言,游学京师是其问学的不二选择,《自纪篇》“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正是对此期求学经历的真实写照。
不过,学界对此尚有不同看法。汉代教育里的《论语》“在小学似随意科,在大学似预科”,“故有从闾里书师即已读《论语》者,有从当代经师先读《论语》后习专经者”[5]91。《论语》这种可上可下的定位,加上《自纪篇》将《论语》《尚书》牵连言之,使得部分论者对王充本阶段的学习经历产生了误解,认为王充完全有可能在郡县学习《论语》《尚书》,不一定非得到京师太学[7]18。此种说法推至极致,便是完全否定正史中“王充曾赴洛阳求学”的记载[13]。表面看来,将王充“受《论语》《尚书》”的地点定在郡县似亦可通,班固《两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2]1386,可证郡国学之兴盛;梅福、隽不疑、盖宽饶、诸葛丰、张禹等名流都曾“以明经为郡文学”[2]2917,3035,3243,3248,3347,一似郡国学师资力量颇为雄厚;《汉书·王尊传》更载尊“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复召署守属治狱,为郡决曹史”[2]3227,是为直接佐证。
不过,持此论者似未意识到:其一,地方官学兴衰无常,多数时候其兴废均系地方长官的个人行为,中央政府对此不甚在意。加之官学兴废与东汉地方官员个人升迁黜陟的关联不太大,留意于此者多为“循吏”群体,职是之故,汉代地方常有“郡学久废”之事,《两都赋》所言是出于文学审美的考虑,并非实情。其二,地方官学的郡文学、五经卒史品阶太低(3)《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帝后与功臣诸侯宴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785 页。郡文学博士实际地位与社会认同之低由此可见一斑。,对我们前面提过的知识精英而言,年轻时因“明经”屈居此职仅仅是以之作为察举征辟的跳板,任期均甚短,故郡国学的师资并无保障。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无从属关系,除非地方长官自行采取鼓励措施,否则地方官学的学生出路无保障,因此,地方官学教、学双方的积极性均不高。其三,统观两《汉书》,似王尊这般以“郡学生”出身的极其罕见,尤其是当该人的学习目的意在扩充知识而非作为任“文吏”之资质时,其最理想的选择只能是京师太学而非主要承担奖进礼乐、推广教化功能的地方官学(4)详参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版,第189 页;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 年版,第270-271 页;祝总斌《东汉士人人数考略》,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45 页。。
以上是从宏观的角度释难者之疑,若具体到王充个人,尚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补充说明:
其一,在西汉末东汉初年,会稽郡仍是个只有在“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时才能“颇称多士”的偏远地区[9]2460,到了王充要“受《论语》《尚书》”时,东汉政权已逐渐稳定下来,先前避乱者或返回原籍,或“抱负坟策,云会京师”[9]2545,会稽并无名师硕儒,不具备向私人请益的条件(5)会稽曲阿人包咸曾因避乱在东海郡“立精舍讲授”,且一度归乡里,不过他在教了会稽太守黄谠的儿子后随即“举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重新回到了政治文化中心。而且看包咸本人“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的经历,也恰恰佐证了赵翼“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的观点。参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570 页。。
其二,《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9]1241,《华阳国志》卷10“蜀郡士女”条亦谓霸“为会稽太守,拨乱兴治,立文学,学徒以千数,风教大行,道路但闻诵声,百姓歌咏之”“德澹会稽,道崇辟雍”[14],今案东汉光武、明、章诸帝在位期间世既承平,又是所谓儒学大盛之时[9]2545,知此处“拨乱兴治”云云系指张霸永元年间(89—105)“立文学”“崇辟雍”之事,然则此前会稽未有郡学甚明。职是之故,卒于汉安元年(142)的会稽余姚人黄昌可因“居近学官,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遂就经学”[9]2496-2497,而活跃于西汉末、东汉早期的会稽士人严光[9]2763、包咸[9]2570、张武[9]2681、郑弘[9]1155(6)关于郑弘师事之人的籍贯,学界尚有争议,见马宗霍《论衡校读笺识》,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10 页。不过,即便我们不采纳《后汉纪》的观点,而是认同《后汉书》“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之说,亦不妨碍我们的观点,因为郑弘显然是到外地师事焦贶的(此点观包咸答太守黄谠以“礼有来学,而无往教”即可窥见一二,参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570 页)。、澹台敬伯[9]2573、赵晔[9]2575、顾奉[9]2581(7)如前文所引,顾奉是张霸在永元年间表用的处士,然考《后汉书·儒林传》“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云云,知顾奉受业亦是在外郡而非会稽。与王充则只能远赴外地或京都洛阳深造。
综上,王充到京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是合乎情理的,前贤于《自纪篇》内在时间线索跳跃处偶有失照,遂疑王充系受业于郡国学、未尝至洛阳,恐于义未安。
三、王充与班彪、班固父子交游始末重勘
王充游学京师期间,与班彪、班固父子过从甚密。王充始至洛阳之时间,文献无证,论者多定在王充父丧服除后。今考廉范“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诣京师受业”[9]1101,张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京师”[9]1100,知此说可从。唯王充之父王诵未必死于建武十四年(38)的会稽大疫,王充受业京师之年龄亦不必非系十五(8)班固《白虎通义·辟雍》、崔寔《四民月令》、王粲《儒吏论》皆持十五岁入太学说,然此不过理想之状态。或十八岁,凡此等处似不宜过拘。今人能够确定的是,王充至迟在18 岁时已“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9]1629,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游学生活(9)汉明帝永平二年(59)时,王充尚在洛阳,故言十数年,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629 页。。《后汉书·班彪列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曰:“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9]1330马总《意林》卷4引《抱朴子》云“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儿必为天下知名’”[15],可为佐证(10)班彪是在建武十二年(36),亦即王充10 岁那年回到洛阳的。又,王充生于建武三年(27),比班固年长五岁。。不过,对于上述记载,尚有必要做三点补充说明:
第一,前人常以班彪不曾任教太学为由,否定班彪与王充的师生关系。然考马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9]840、郭玉师事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9]2735,知汉人谓“师事”某人,所学不限“七经”。再观傅燮“少师事太尉刘宽”[9]1873、蔡邕“师事太傅胡广”[9]1980,知其“师事”之人不必为太学博士。复考符融“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9]2232,戴封“诣太学,师事贸阝令东海申君。还京师卒业”[9]2683,知求学者“师事”之人可与己之太学学业无涉(11)当然,如果学生“师事”之人本身就是太学博士,则另当别论,如东汉初年的帝师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参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570 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可以”一词。。是故,建武三十年(54)班彪辞世、班固“归乡里”,王充并未停止游学洛阳之举,且于永平二年(59)“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9]1629。准此,王充“受业太学”与“师事扶风班彪”判然两事(12)周桂钿先生已指出,博士、太学、讲授并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说详氏著《王充评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13 页。吴从祥先生亦对此事有所考辨,然与笔者的论证进路有所不同,详见氏著《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97-104 页。,不得以班彪未尝任教太学否定《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的真实性。
第二,部分学者认为王充绝无师承,所学全系自修得来[16],此说亦难以成立。王充《论衡》透露过自己师承的事,除却《自纪篇》“谢师而专门”这一关键时间点外,最明显的要属《量知篇》的这段话:
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以郁朴之实,不晓礼义,立之朝庭,植笮树表之类也,其何益哉?……人无道学,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犹丧人服粗,不能招吉也。[1]552
我们知道,《量知篇》的立意上承《程材篇》,下启《谢短篇》,是王充“鸿儒”形象自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即通过抨击文吏与普通儒生来凸显“异于众人的我”[8]22-29,因而其所设立的评骘标准都是王充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量身打造的。王充敢于用“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以郁朴之实,不晓礼义,立之朝庭,植笮树表之类也,其何益哉”“人无道学,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犹丧人服粗,不能招吉也”[1]552等话抨击文吏,足以证明他是有老师的。至若《自纪篇》云“未尝履墨涂,出儒门”,盖如马宗霍先生所言,“虽仲任设为或者之词,然《论衡》之作,欲于儒、墨两家之外自为一家,其微旨可见矣”[17]394。此观全书屡以“孔、墨之材”“材贤孔、墨”[1]539,540,1204并称可知,非自认无师承也。另一个重要证据是,王充自视甚高,屡屡抨击郡守、长吏、博士、郡文学,甚乃“有所发擿,不避上圣”[1]1253,但对班彪、班固却抱有相当之温情。如《超奇篇》云: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1]616
“班马优劣”是千秋聚讼的问题,王充此处未作论证,径借观读者之口断言班彪之书优于《史记》。更重要的是,班彪所续《太史公书》只是今本《汉书》的蓝本,连其子班固都觉得“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9]1333,但王充不唯许之以“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还顺带称赞了班固,其对班彪之态度可见一斑。当然,若仅就《超奇篇》而言,论者亦可将王充对班氏父子的谕扬理解为“话语”工具,即王充甲班彪乙太史公不过意在暗示东汉政府——今人,尤其是王氏本人的著作不可忽视。此说固然有理,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王充对班氏父子并未停留在作为言说“话语”的层面。举例言之,王充曾出于自我建构的需要在《佚文篇》称赞司马相如、扬雄[1]864,在《宣汉篇》《须颂篇》《案书篇》高度评价班固的赋颂[1]822,851,1174,但当《定贤篇》需要否定汉赋时,则仅仅批评司马长卿、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1]1117而不及班固。又如,班彪、班固父子无疑合乎王充“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若专城之苗裔,有世祖遗文”[1]1115等通人的标准(13)班彪“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见《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4205 页。又,王充曾许班固为“通人”,见《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604 页。,但当他在《定贤篇》贬抑“博览通达”的通人时则仅举司马迁与刘向,不及班氏父子[1]1115。综上,前贤言王充叙及班彪时“没有丝毫师生的意味在里面”[13]346-348等说法无法成立,更不可以据此否认班彪、王充二人的师承关系。
第三,对前揭文献中“王仲任抚班固背”的记载,我们认为,《论衡》能够大量征引班彪尚未流传的《续〈太史公书〉》[7]312-324,足证班、王二人关系密切,王充与班固有所交流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详玩葛洪《抱朴子》、谢承《后汉书》所载王充抚班固背并大加称赞之事,似以前者较为可信。盖就班彪在当时学界之地位及王充的现实身份而言,谓“此儿必为天下知名”属于正常夸奖后辈的话,而云“此儿必记汉事”,则颇有“后见之明”的嫌疑。这是因为,在王充心中,续写《太史公书》是班彪本人业已完成之事(14)见《超奇篇》《佚文篇》《案书篇》《对作篇》的相关论述,亦可参看周桂钿《王充评传》的引用与简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15 页。,直到王充50 岁之后[18]作《案书篇》,犹云“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1]1174。由“虽无篇章”等表达可知,几十年后,王充仍不知晓班固在其父《续〈太史公书〉》基础上撰写《汉书》之事(15)王充不知道是时间差的原因。班彪卒于建武三十年(54),而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是“父彪卒,归乡里”后之事;等到永平五年(62)班固以校书部的身份回到洛阳、受诏著《汉书》,王充已返回会稽家乡了;及至《汉书》撰写完成,已是章帝建初年间,远在东南一隅的仲任更因关山阻隔、讯息不畅难以得知。以上系年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376,391-392页。,又怎么可能在18 岁时说出班固“必记汉事”的话呢?不过,谢承《后汉书》的记载同样渊源有自。《汉书·高帝纪》云:已拜,上召谓濞曰:“汝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顿首曰:“不敢。”[2]76刘邦预言40 多年后的吴楚七国之乱,这种“奇异”的记载显然出自执笔史家的后见之明。套用马克·布洛克的话来说,它不过是历史学家的一种“技艺”[19]。谢承《后汉书·班固传》载王充抚班固之背并将王氏的称赞之语坐实为“此儿必记汉事”的预言,盖亦同于《汉书·高帝纪》,纯系史家固有的程式化叙事笔法。谢承没有选择葛洪《抱朴子》“此儿必为天下知名”式的宽泛表述,而一定要让王充“预见”班固“必记汉事”,是因为三国时班固的《汉书》已风行天下,而王充又是谢承的“乡里先辈”,故而谢承“务欲矜夸,不知其乖谬也”[20]。但必须指出,王充称赞班固之事细节虽或容有修饰,但王充曾亲见班固这一事件主体却无容悬拟,与王充无乡邦之谊、甚至曾与王充商榷天文学观点的葛洪亦记载此事即为明证。前辈学者因谢承“矜其乡贤”[21]之故,遂全盘否定王充与班彪、班固父子的交谊,恐非笃论。
多方证据表明,王充与班彪、班固父子关系密切,《论衡》不仅常引二人言论、行事以为论据,且字里行间对他们充满了温情,“王充未尝师事班彪”“王充与班固未曾谋面”等说法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