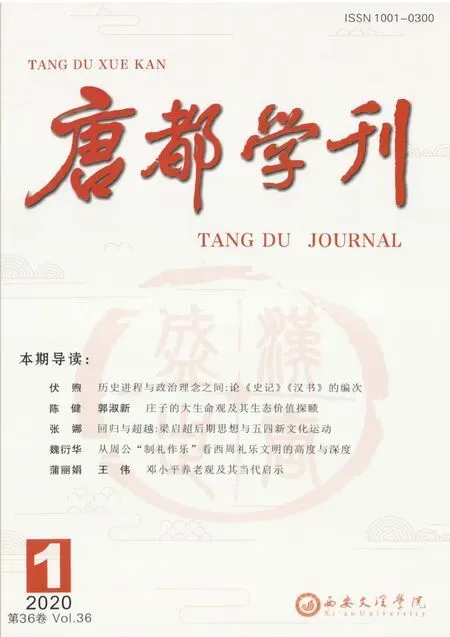回归与超越:梁启超后期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张 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1919 年5 月4 日爆发的全国性爱国政治运动被称为“五四”运动,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不能仅以这一天来界定。其实,早在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就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历时十余年。这场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革新运动,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梁启超生命的最后阶段,梁启超后期思想回归传统、趋向保守,被五四新文化阵营所排斥,并被视为五四新文化的对立面。然而,就连发生在1919 年5 月4 日的爱国学生运动其实也与梁启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和一元的,而是多元和立体的,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和对人物的价值评价,都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历史结构中进行。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只有主导方一个声音,其他方面如辜鸿铭、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他们的观点绝不能被简单地视作新文化的对立面,他们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被当时的众声喧哗所掩盖,但现在这些声音的价值应该被重新评估并肯定。本文拟以梁启超后期思想为例,来分析其看似与五四新文化思潮相悖,而实则也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一环的思想价值所在。
一、“不合时宜”的批判和“不随潮流”的回归
《欧游心影录》通常被作为梁启超后期思想转变的代表作,主要记录了梁启超等一行七人从1918年12 月底从天津启程前往欧洲、直至1920 年初回国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段时间,国际上正值“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新的国际同盟正待形成,而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所以,这样的时代背景也就决定了《欧游心影录》不可能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旅行记录,实际上,它是梁启超站在欧洲近代文明前,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对东西文化所做的思考,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价值判断,以及对中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整体考量。文中既有对战后欧洲惨淡的描写,也有对大战的反思;既有对物质文明破产的感慨,也有对精神文明重建的期待;既有对科学万能的否定,也有对科技进步的肯定。所以,《欧游心影录》并非只是对欧洲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单纯否定,其中包含着辩证的分析、正反的论说。但当时蓬勃发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楷模,作为运动中的“楷模”通常总被夸大为完美无瑕,不容被指责和怀疑。而此时梁启超对西方近代文明诸多弊端都给以辛辣批判,显然,这种客观理性的批判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同时,梁启超后期思想被五四新文化阵营诟病的原因之一还在于他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五四新文化运动正热情地张开双臂迎接西方新思想,并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而此时梁启超却开始饶有兴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系统研究,包括对老子、孔子、墨子、荀子、陶渊明、杜甫、孔尚任等,梁启超都有过专门的著述。在五四那样一个高扬西方新思想的时代,梁启超回归传统的行为便很容易被认为是开倒车、落后时代潮流。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判断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首先,如果能对梁启超一生的思想有一个整体把握,就会发现,梁启超一生从未彻底否定传统文化,除了批判“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糟粕外,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乐观的,并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不论是他被后人视为思想进步的前期,还是思想退步的后期,他的著述中都有肯定传统文化的论述,不同之处只在于比例问题,即他在后期对于传统文化的投入比前期更多。这只是他著述方面的偏重问题,而不能说成是他思想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实际上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梁启超的思想基本是前后一致的。因此,也就不存在开倒车之说。并且,梁启超一生中对吸收引进西方文化始终抱着积极的态度,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始终如是。所不同的是,由于眼界知识所限,他在前期对西方文化的弊端尚没有直观清楚的认识,而随着眼界的开阔和知识的增多,特别是欧游所带来的直观感受,让他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所以在他后期思想中对西方文化的弊病有了更多的批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现代文明的信心,在他看来,“这种现象,连我们有时也看得讨厌,有人说,这不是叫社会向上,倒是叫社会向下了。其实不然,一面固是叫旧日在上的人向下,一面仍是叫旧日在下的人向上。然而旧日在下的人总是大多数,所以扯算起来,社会毕竟是向上了。”[1]67
其次,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判断,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评价标准有直接关系。在当时西学东渐、西风强劲的背景下,社会上对于思想进步与否、观念正确与否的评判依据大多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评价标准,即西方优于东方,新思想优于旧传统。但平心而论,这样的评价标准过于简单和草率,结果就将许多有益的思想文化给屏蔽掉了。同样,梁启超后期思想也需要进行重新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启蒙民众,其方法是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这种想法本身固然没错,但落到实际层面却出现了极端行为,如“彻底西化”“全盘西化”等。全盘西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全盘否定自身传统文化,对自身进行大换血,这固然是不可能的,但实际带来的弊端却显而易见。即便是那些大谈西化的人,在梁启超看来,“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2]409显然,在梁启超看来,这些所谓的“西化”,也不过是些形式的成分,而缺少实质的精神和内容。他所希望的,始终是一种东西文明的融通,他说: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3]
有人批评这仍然是一种“中体西用”的认知形式。这里且不谈“体用”的问题,单就梁启超对东西文化的态度而言,他的广大开放胸襟彰显的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更表明了对异域文化的极大包容和欢迎,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阵营中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精神的体现。
二、理性看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启蒙民众思想,梁启超后期思想虽然与五四运动主导方的具体口号和做法存在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和指向却是一致的。并且,梁启超在很多方面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助益,这是以往研究所容易忽略的地方,也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着力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宣扬西方民主、科学,这是梁启超前期思想所大力宣传的方面,也是他前期思想为人所称道的原因所在。然而,后期他的思想被认为转向了复古落后,并在《欧游心影录》中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进行了无情挞伐,而他所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也正是当时五四运动所大力讴歌和倡导的,他这样“不识时务”地“逆潮流而动”,也让他的后期思想蒙受了不公的评价。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以一位历史旁观者的身份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笔者认为,梁启超后期思想不仅没有落伍,反而更加深刻;不仅没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悖逆,反而从不同的方面给予新文化运动以很大的支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梁后期思想遭受众多非议的一个方面在于他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上。五四主流思想采取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所谓“不破不立”,要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新文化。所以,但凡与传统有关的事物,都要坚决废除,“打倒孔家店”“线装书应当抛在茅坑里三千年”等口号屡见不鲜。虽然,鲁迅、胡适等后来曾指出,这种激进的口号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但也侧面证实了这种彻底否定传统的口号和行为在当时社会上的号召力。与这种彻底否定和重建式的启蒙不同,梁启超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调适型的启蒙。他从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特别是在生命的后期他致力于传统文化的钻研,挖掘传统文化中关乎人类情感、道德等具有超越时代价值的东西。但梁启超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是在对东西方文化反思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再思考,他肯定的是传统中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东西。对于保守派为传统而传统的态度,梁启超向来十分反对,他说:“旧者流侈然俨然以道德为其专卖品,于是老官僚老名士之与道德家,遂俨然三位一体之关系,而欲治革命以还道德堕落之病者,乃迳以老官僚老名士为其圣药,而此辈亦几居之不疑。”[4]
他反对将传统文化视作卫道的外衣,他推崇的是传统中有益于精神升华的精髓实质,而非传统中的条条框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以西方为发展的楷模,西方在物质方面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但相较于物质方面,其在精神方面的发展则明显滞后,并且由于精神、情感、道德等的缺失而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前车之鉴,梁启超希望能够从西方社会的发展中总结一些经验,以便使中国在转型的道路上避免错路、少走弯路。那么,如何避免?在欧游之前,他曾寄希望于西方,然而欧洲战后的一片惨淡,西方有识之士寄托东方文化来救拔他们的想法,使梁启超更加坚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他看来,利用传统文化非但不会阻碍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有助于新文化运动的顺利进行。
其次,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主义的批判,也成为梁启超后期思想被指落伍的原因之一,对“科学”的态度成为判断是否是新文化阵营的标准。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就以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声光电气等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并成为国人效仿的目标。国家富强固然离不开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但如果将其发展到极端,则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梁启超对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和科学万能主义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他在欧游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让他在面对发达的物质和科技文明时,不会头脑狂热,而能客观辩证地看待一个事物,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个事物。同样,也不能将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对“科学万能主义”的批评,视作他对科学本身的反动。梁启超显然已预感到他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能会招来非议,故在文末专门做了注,以表明他的实际立场,“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1]64。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因对待科学问题上的理性态度,而遭狂热“西化”者的鄙薄,并成为判断他落伍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梁启超后期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科学和科学精神,坚信科学的价值。他在《美术与科学》的演说中认为,西方现代化成就应归功于科学,“现代化文化根底在哪里?不用我说,大家当然都知道是科学。”[5]并认为,在中国即使是最顽固不化的人,现在也绝无法否认科学的价值,他说:“近百年来科学的收获如此其丰富,我们不是鸟,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诸如此类,哪一件不是受科学之赐,任凭怎么顽固的人,谅来‘科学’无用这句话,再不会出诸口了。”[2]408他认为,中国要发展进步,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培养国民的科学精神,并给“科学精神”以系统的解释,即“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2]410他希望国民能够人人存一科学精神,并运用普及之,那么中国文化必定会再放异彩。正是出于对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和对科学价值的认同,他积极参与当时中国最大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并在1923—1928 年先后五次出任科学社的董事。除此之外,他还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大力宣传科学和科学精神,鼓励国人要做“科学的国民”。显然,梁启超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服膺者、鼓吹者,而非反对者;五四时期乃至后来不少人之所以对他在科学问题上的观点产生非议,主要症结在于他对“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我们认为,对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正反映了梁启超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6]。
再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是新文学运动,欧美文学成为新文学运动重要的引进译介资源和效仿对象。众所周知,梁启超最早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身体力行地支持白话文运动,他创作的《欧游心影录》可视为同时代白话文的上乘之作。但与前期注重文以载道的文学政教思想不同的是,梁启超后期思想更加注意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突出文学的艺术和美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欧美短篇小说时,梁启超却对这种文体提出了批评。他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说道:“现在他们的文学,只有短篇的最合胃口,小诗两句或三句,戏剧要独幕的好。至于荷马、但丁、屈原、宋玉,那种长篇的作品,可说是不曾理会。因为他们碌碌于舟车中,时间来不及,目的只不过取那片时的刺戟,大大小小,都陷入这种病的状态中。”[7]52要知道在此前,为了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梁启超正是这种短篇政治小说的提倡者和鼓吹者(1)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客观事实,即便是在梁启超鼓吹短篇政治小说的前期,他也从没有否定中国或西方古典文学的魅力和价值,虽然间或对中国古代小说有所批评,但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和分量是很低、很轻的。。而此时,他更强调古典文学的长处和优点,批评现当代西方文学寻求一时的感官刺激,缺少永恒的艺术价值。实际上,梁启超对短篇小说的批评是有所指的,五四时期的小说多以短篇为主,并且“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作为当时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将的胡适就十分推崇短篇小说。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称:“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我们简直可以说,‘写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8]而梁启超认为,这恰恰代表了一种文化快餐式的病态。“在日益忙碌、机械化的现代生活中,中国的青年,因为现实政治社会的不安,精神无所寄托,只能需求短篇文学体裁以作片刻的刺激和发泄,梁启超认为这不过是‘在惶惶求所以疗治之法’。”[9]而古典文学中那些滋养人类情感和灵魂的文字却全然被忽视了。
当时国内很多作家还积极提倡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强调对人的启蒙和“人的发现”,因此更加注重客观性和真实性。自然主义文学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启蒙载体。茅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生派”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文学的作用,一方要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一方也要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10]希望借助自然主义“求真”的特点,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缺陷,以激发起改造社会和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但梁启超对自然主义文学过分揭露社会黑暗的表达方式十分不满,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这样写道:“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之后,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分别,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1]65梁启超的担忧不是毫无道理的。自然主义文学不论是受其译介的影响,还是由于其文学创作手法,其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积极改造社会和乐观面对人生的初衷,而是走向了其对立面。
虽然,梁启超对新文学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反对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百花齐放”更有助于增强新文化运动的活力。文化本就是多样的,同为儒家学说,其中也分为多种学派,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显然就很不一样,但并不妨碍它们同属儒家学说。所以,今天我们再评价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不能因为他对短篇小说和自然主义文学的批评而否定他在整个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
三、思想启蒙与文化交流
梁启超在很多方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带来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并在国民启蒙和思想解放方面做出了诸多积极贡献。
第一,梁启超从政多年,积极致力于国民性改造,注重自己在国家政治、经济层面的实际作为,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典型路径。然而,沉浮宦海多年,他发现再好的制度都需要人来执行运作,如果人的素质有问题,再好的制度都形同虚设。所以,他决意要弃政从教,希望能从教育方面为国民性改造做些实际具体的努力,因而出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启蒙民众的宗旨完全一致,只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或者说是路径上有所不同。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启蒙民众思想的方式寄托于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并以欧美小说作为重要的载道方式之一。而梁启超虽然对欧美现代小说注重感官刺激的快餐形式颇有微词,但仍认为文学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路径。他在《〈丽韩十家文钞〉 序》里曾明确表示:“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筦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世者,殊非夸也。”[11]
所不同的是,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关乎人性修养的超时空价值,精神、道德修养是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面,所以传统经典需要重新被挖掘和重视。他弃政从教,就是希望能从教育方面为国民性改造做点实际的事情。他认为,情感、道德教育是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面,欧游的见闻触发了他很多感想,在知识科技理性日益飞涨的西方,其国民的情感、信仰和道德则明显干瘪滞后,欧战爆发也多与此有关。国家要富强,人的情感也需要和谐,并且情感、道德等是否和谐,是国家富强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所以,当他看到国内对知识、科技、理性的狂热追捧,就不免希望能在理性和情感的天平上有所平衡,以避免国民在理性和情感上的失衡。那么,这就涉及情感、信仰和道德是效法西方还是取法中国传统的问题?梁启超向来在东西文化方面都十分开通,世界的格局、开阔的胸怀都让他并不唯传统是为。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了《情圣杜甫》的演讲,其中讲道:“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发展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12]传统中既然有价值可取,又何妨接受呢!近代的西方和日本,“传统文化透过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供给他一种内在自发的动力,驱使他勤奋努力的工作;这就是西方人所谓的勤劳的工作精神(work ethic)。没有这种精神,现代化不会在西方出现,而日本的经济成长也不会有今天这种惊人的成绩。重要的是:在这两个地区,勤劳的工作精神都是以传统为源头。”[13]相较于西方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更合乎中国国民的习惯和心理,有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存在其中,传统是国民凝聚力的重要力量,任何企图打破传统的行为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西方现代社会的富强也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在此之前,中国文化一直在世界中处于强势地位,不能以传统文化在低潮期的回应而否定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其实,相比于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高调立场,五四新文化阵营中不少人对传统文化的复杂心理也不难发现。就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在五四后期开始整理国故,他虽将此说成是在传统文化中“捉妖打鬼”,这实际是充当了整理国故的幌子,他一生都对“国故”有着难舍情感。周作人也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主张将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结合,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是东西两种文明的融合,只是所引进的西方文化处于显性的地位,而传统文化处于一种隐而不显的潜意识当中。直至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传统在我们文化中的底色地位,只是底色的深浅程度不同罢了。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是一种简单地吸收。他刚刚经历了一年的欧游,他所主张的对传统文化的吸取,是站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对立联系上考虑的,是以一种立体、深刻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看似是回归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对传统的超越。
第二,梁启超重视传统文化,并非意味着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思想有所抵牾,在西方先进思想的介绍方面他同样是不遗余力,可以说五四新文化阵营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在欧游回国不久后,于1920 年4 月联合众多社会名士在北京成立了共学社,其宗旨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将翻译外文图书和派遣留学生作为工作重点。此前,他已向时任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的张元济提出“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的主张,并获张元济支持。梁启超认为,“无论何种学说,只要是有价值的,我们都要把他输入,令各方面的人,对于那一种有兴味,就向那一种尽量研究。表面上看来,所走的方向,或者不同,结果总是对于文化的全体,得一种进步。”[14]217共学社通过梁启超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地位,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编译出版了大量外文图书,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哲学、科学、文学等多个方面,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思想,这些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
为了进一步增强与国际间直接的文化交流,1920 年9 月,梁启超又联合蔡元培、张元济、林长民、熊希龄等社会名流成立了讲学社,其目标是每年邀请一名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讲学社先后邀请了四位国际名流来华访问讲学,有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著名学者杜里舒,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讲学社还拟邀哲学家柏格森、倭铿,经济学家凯恩斯,科学家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但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作为讲学社的创立者,梁启超积极筹划组织,甚至亲自出面邀请这些世界名哲。梁启超曾在《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会上演说词》中讲道:“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因为现在全世界,已到改造的气运,在这种气运里头,自然是要经过怀疑的试验的时代。所以学派纷纷并出,表面上不免有许多矛盾,但各有开辟将来局面起见。总之各有各的好影响。就学问的本质说,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为中国现在计,说是那种绝对的适宜,那种绝对的不适宜,谁也不能下这个断语。”[14]217无疑,四位国际学者的到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久违的生机,他们将先进的思想介绍给国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扩大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围和影响,使中国思想界在更多的领域得以解放和革新。共学社和讲学社的这些贡献,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梁启超从中所做的努力更不应被淡化甚至被遗忘。
四、小结
梁启超曾经说过:“我们中国因为近来社会进步比较的慢,欧洲先进国走错的路,都看得出来了,他治病的药方,渐渐有了具体的成案了。”[14]217可见,梁启超在他生命的后期,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系列行为,都基于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都出于国民性改造和国家富强的考虑。在他诸多看似保守的思想行为背后,我们能看到他对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深切关注,这是他鉴于欧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之所思,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启蒙”的宗旨一致。尽管梁启超在此前的不少文章中也有对于人本精神的讨论,但后期对此问题的讨论显然更加深刻,这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西方近代文明在传统社会前显示了多方面的发展优势,但“一战”的爆发也暴露了西方近代文明发展中的一些弊病,其中就包括人的异化问题、精神信仰的空虚问题等。其二,此时中国正以西方近代文明为发展楷模,而如何能避免上述弊端,显然是梁启超关心的重点。其三,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非常注重人本意识问题,所以,此时讨论人本意识问题也是对东西文化能否汇通融合的思考,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能否补益西方近代文明这个问题的思考。
梁启超当时尤其重视人本问题,也与新文化运动有关。梁启超针对“什么是新文化”这个问题,给出了他的理解,他说:“要讲新文化,必有两个先决的要点:一、在知识上要有科学的理解;二、在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15]419其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之一 ——“科学”,其二是关系到情感和道德的问题。在五四之前,人们尚可按照传统的一套礼仪规范行事,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彻底反传统行为则容易使人心无所安放,行为无所规范。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而旧的道德规范已被打碎,这样很容易使人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境地,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他严正指出: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7]53
梁启超希望那些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们,“要作新文化运动,应当要‘知识上,非做到科学的理解不可;在道德——品格——上,非做到自律的情操不可!’”[15]42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就是“民主”和“科学”,所以,“科学”的重要性已逐渐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同(2)梁启超对于“科学”的理解,相较于同时代的很多人要深刻得多。他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讲到“科学精神”要分三层意思说明:一是“求真智识”,二是“求有系统的真智识”,三是“可以教人的智识”。他认为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很多病症,如“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等。所以,他认为倡导科学,绝非只是表层的枝叶,而是要学习其精神。。但对于伦理道德这种于国家富强目标看似并无太多直接关系的因素,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历史证明,伦理道德这种软实力才是支撑一个国家发展强大的基石。因为“知识的发展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受制于社会环境,而道德显然是造就不同社会环境的一种重要力量。所以,道德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互相交织,甚至在社会功能上有一定的替代关系,这个道理不难理解。”[16]172
梁启超后期看似回归传统的保守行为,其实是一种先觉意识,是经过审慎的思考和总结。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谁会认为过时落后呢?墨子的“兼爱”“非攻”,谁又会否认其价值?新旧并非绝对对立,新思想通常是在旧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新旧思想通常有相当多的重合部分。梁启超对传统的回归,并不是对传统文化道德绝对的、无条件的赞同,而是对传统文化道德的超越。他认为,道德的目标不外二者,即“发展群性”和“发展个性”[17]。也就是说,在发展群体力量的同时,也要保证个体的发展。那么,“这样的道德原则与传统道德原则是不同的,因为传统道德原则只顾及了前者,而没有顾及后者。”[16]19显然,梁启超所主张的道德公准与传统并不完全相同。同样,对于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他也不是简单地亦步亦趋,而是在旧有文化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打破了两千多年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桎梏,也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准备。我们在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地位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需进一步讨论。事实证明,“全盘西方”不仅绝无可能,反而危害甚大,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传统社会文明的积淀,是几千年文明的见证,应汲取其中优秀的文化因子,进行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转化。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适应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化会越来越普遍,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真理始终是真理,作为世界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同样,梁启超后期思想中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是出于对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的肯定。在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得以彰显,而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正是源于他坚信传统文化中具有能够补救西方现代文化的积极因素。所以,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不应流于简单粗疏,而应该看到其在“解放思想”“启蒙民众”“引进西方思想”等方面的贡献绝不亚于五四新文化阵营中的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