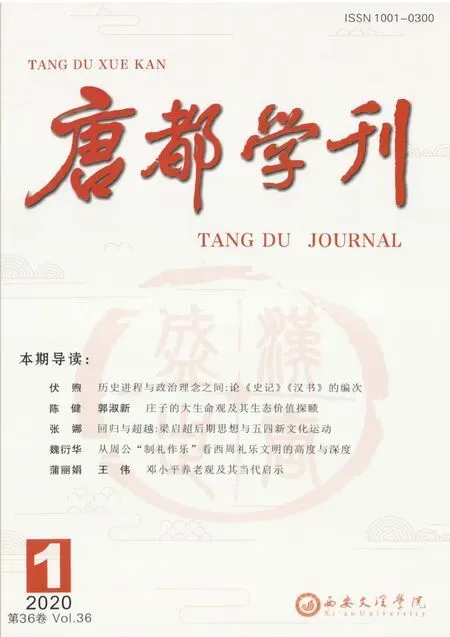“算赋”与两汉王朝的崩溃
马天祥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一、“算赋”与小民的破产
算赋,是一种依据人丁征收的人头税,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讲包括“口赋”(口钱)和“算赋”(算钱)。究其根本而言,口赋和算赋是对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时期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据《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春正月条下注: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条下注:《汉仪注》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又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补车骑马。”
《汉书·孝惠帝纪》六年冬十月条下注: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
翻检文献可知这种税制肇端于西汉高祖四年(前203)。高帝四年冬十一月条:“八月,初为算赋。” 且该条注文:“《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此后,这一针对人丁课税的方式一直绵延至东汉末年。可以看出东汉平民在七岁到十四岁期间须缴纳每人每年二十钱的“口钱”;在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期间须缴纳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算钱)(1)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常制是经过漫长变动而最终确定下来的,当然即便常制已经确定,但随年景丰欠、国用绰约还会出现一定的涨落。可参看加藤繁《关于算赋的小研究》一文,详见《中国经济史考证》( 上) 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并且,这种税制对妇女并不网开一面。既往研究对此并未说明,现特将《后汉书·孝章皇帝纪》卷三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摘引于此:《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
由此可见,东汉王朝已有旧令在先,妇女生产后可免去三年算赋。章帝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增益,对怀胎妇女赐予一定数量口粮,并免去其丈夫一年算赋。这些法令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对没有怀胎和生产的女性还是要征课算赋的。因史传中皆以“算”字表述,且未予额外说明,妇女之算似当等同于男丁所征课之数目,故以常理推知:五口之家,如有三个成年人、两个未成年人,就得出400 钱。此外,还有更赋。据《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春正月条下注: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曰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也。
又《后汉书·孝明皇帝纪》中元二年秋九月条下注:
更,谓戍卒更相代也。赋,谓雇更之钱也。《前书音义》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有一月一更,是为卒更。贫者欲得雇更钱,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古者天下人皆当戍边三日,亦名为更。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当行者不可往即还,因住一岁,次直者出钱三百雇之,谓之过更。”
可知更赋包括卒更、践更和过更。卒更、践更皆属徭役范畴,过更当属兵役范畴。按照国家要求,成年男丁都有为国家服徭役一个月的义务——卒更,如果不想亲自服徭役可花钱雇人代替自己来服一月徭役——践更。然而,雇佣他人的价格政府已经明确制定为两千钱(2)此项费用对小民而言颇为巨大,且属自愿而非强制,故小民多服徭役而少缴纳钱款。。另外,成年男丁有都有服兵役戍边三日的义务,但由于诸多原因导致“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所以还要花钱雇人代替自己服三日兵役。雇佣他人的价格政府明确指定为三百钱。这样一来,一个五口之家若有两个成年男丁,那么每年至少又要缴纳六百钱,加之之前的四百钱算赋就是一千钱。
无论年景好坏,什么事情也没有,就得上缴1000 文左右的钱款给政府。本来小农脆弱,天灾人祸都可以使之破产。现在又这样1000 文大钱横在那里,小农就像站在深过下颌的水流之中,一有风浪就面临灭顶之灾。[1]
根据汉代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拥有七十亩耕地来计算(3)该家庭类型和土地数量均采自许倬云《汉代农业》中第三章《农民的生计》所推算之数目,见许倬云《汉代农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57 ~ 80 页。,理论上每亩土地的收入按《昌言》中推算的平均值:“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2]拥有七十亩土地的农户每年收入的粮食当为二百一十斛左右。许倬云将文字材料和居延汉简所提供的信息相结合,对一个五口之家的口粮消耗做出了如下统计:
一个成年男子一个月的粮食消费量为3斛,一个成年家属为2.1斛,一个未成年人1.2斛。据此,我们在上面虚构的那个五口之家,每一个月要消费粮食11.4 斛,或者说每年约消费140 斛粮食。[3]
也就是说,在全部二百一十斛粮食中必须扣除这用于糊口的一百四十斛。所剩仅七十斛而已。而这七十斛中还要在拿出一部用于折钱去缴更、赋之钱,如果按在正常年景下一斛粮食可以换得六十钱,那么一千钱就要折掉将近十七斛粮食。至此,这个五口之家在完税之后所剩粮食只有五十三斛了。如果进行纯粹理论层面的推算,这个五口之家在之后的一年中没有遇到任何地方政府发起的宗教祭祀活动(4)这一点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据班固《汉书·食货志上》“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之语,可知宗教祭祀当为小民一年中不可避免之支出。,没有任何婚丧嫁娶、衣服器用采购、疾病、生产工具更新或维护,没有任何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滥征徭役,且还需按最少数额为来年每亩留足一斗的粮种后,这个五口之家所剩粮食只有四十六斛。
然而,盘剥并未完结,这些还只是这个家庭缴纳了更、赋之费后的剩余。此时,所剩粮食本已不多,但还需缴纳直接以实物形式征课的“三十税一”的田租。按照二百一十斛的收入,应该缴纳七斛。此时,这个五口之家仅仅就剩下三十九斛粮食了。辛辛苦苦劳碌一年所得的收成除了缴纳各种赋税和保留全家口粮外,仅余三个月的口粮可做他用。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理论层面的推测。此外,还需要注意另一问题,每年岁末官吏催科之急又会加剧大量粮食在短期内集中抛售,《后汉书·孝安皇帝纪》元初四年条下注:《东观记》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
可知,每年在秋收临近之时地方官吏都核查户口,统计人口数目,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准确掌握人丁数目以便按人头征税。又《后汉书·百官志》有“岁尽遣吏上计”之文,且该条注引卢植《礼注》:“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上计”实际上是一种地方向中央定期汇报制度,据《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注引用颜师古语“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而汇报内容又据《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注:“受郡国所上计簿也。若今之诸州计账”可知,地方郡国每年要在八月秋收之前对当地的人口数目进行核定,而后在粮食收获之后按人丁征课各种赋税,租税征收完毕后,将所辖地方的人丁数目、田亩面积、征课钱粮数目一一登名造册,而这一切都要在农历九月结束前完成。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小民要完成粮食收获、缴纳田租、以粮折钱、缴纳算赋等事项。纵然地方政府在办理过程中尽最大限度节省时间,尽最大可能不征发徭役,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小民被迫将大量粮食集中投放市场用于换取货币,在这一环节中虽然没有了赤裸裸的盘剥和压榨,但地方豪强势必会凭借其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优势,一次次地上演着另一种隐性的盘剥。东汉时期丰年本就不多,但即便是丰年足岁小民还要遭受“谷贱伤农”的困扰。因此,两汉时代真正摧垮脆弱小农经济的幕后黑手正是汉代的赋税制度,而绝非摆在台面上的天灾频仍。一些单纯基于文献的研究认为,导致汉代小民大量破产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频发,这种说法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在两汉王朝这种畸形的赋税制度下,小民是注定要走向破产的,在这种境况下天灾只不过依仗着“税祸”成为压垮小民的最后一根稻草。破产之后的小民出于生计的考虑,为躲避人头税的盘剥,多寻求豪强庇护成为豪强的佃农乃至奴隶。这样一来,以人丁课税的制度便失去了征课对象。要之,汉代社会的小民既是物质生产者,又是国家财富的提供者:“自耕农是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阶层,一方面他们是土地的直接生产者,一方面又是政府赋税徭役的主要提供者。”[4]
法国学者弗朗斯瓦·魁奈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农业社会中长久以来存在的“人头税”的弊端:
据说在中国,除了土地税以外,还有某些非正规的赋税,诸如一些地区的关税和通行税,以及一种人头税形式的对人身征课。如果这些说法属实,则表明在这一点上,这个国家对于他的真实利益,尚未真实明了。因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来自土地,而上述这些赋税破坏了税制本身从而对国家税收造成危害。这一事实可以用数学方法无可置疑地显示出来,不过却难以用推理方式加以把握。[5]
这也许就是长久以来困扰两汉王朝“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怪圈产生的根本原因。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供求关系等经济规律已开始发挥作用,畸形的赋税制度凭借强硬的国家意志不容挑战,而小民只能任人压榨。就好比一部简单的杠杆式榨油机,供求关系等经济规律构成了它的支点,依靠国家意志推行的畸形税制是它的强硬杠杆,而小民便是容器中等待压榨蒸炒之后的大豆。国家并没有糊涂到要把小民压扁、榨干,但兼具官员和商人身份的豪强,利用了畸形税制的强硬杠杆和经济规律的有力支点,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毫不留情地按下了杠杆,而后不仅分得大量油水,还要将那些压扁、榨干的“豆饼”施放到自家土地用来“肥田”,于是疯狂壮大的豪强阶层最终葬送了两汉王朝。
二、本可省减的“算赋”
如何才能为汉代的小民寻得活路呢?至少在理论层面上,其实方法很简单:税、赋分化——将征课实物形式的税与征课货币形式的赋分化开来。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赋税,分别向两种身份不同的人去征课。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开始出现,“钱”和“粮”分别扮演着国家财政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国家在征课赋税时又必须兼“实物”和“货币”这两种形式。国家对粮食的需求,直接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小民征收实物形式的田租,其他概不征课,让小民只承担物质生产的职责,而不再额外负担将粮食、布匹等折取货币的职责,进而免遭奸商压榨。那么国家对“钱”的需求又如何解决呢? 答案同样很简单——商业。国家应该像从农业中直接抽取实物形式赋税一样,对工商业征课货币形式赋税。这样不仅减轻了小民的负担,更可以依靠税率的杠杆调节促进商业的良性发展。其核心思想合于《管子》所言的“轻重之术”。当然,这只是一种基于汉代社会做出的理想假设。
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历代王朝对赋税的征课都是以“便国”而非“便民”为宗旨的。庞大而低效的政府只会采用对自身最为便捷的征收办法,而不会考虑它是否是百姓最为憎恶的手段。其次,西汉开国以来仰仗中央“无为”政策蓬勃发展起来的民间工商业,在武帝一朝受到了重大打击。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政策,对民间自由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给予了沉重打击。用强硬的行政手段将曾属民间经营的大宗工商业统统收归国有,纳入行政体制之内。朝廷税源虽然暂时充足了,但却扼杀了一度繁荣的民间经济,最终导致国家收入锐减。
然而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又只是表象而已,因为两汉财税制度在设立上就是借为国家广开税源之名,行为帝室聚敛财富之实。西汉以来,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是彼此相互独立的(至少在形式上)。天下的田租和算赋(不包括口钱)归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管;而“山泽鱼盐市税”则由少府掌管(5)其中征课仍不都以货币形式,大宗之物亦皆以实物形式征课。,口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汉王朝帝室的私财[6]25-126。经历两汉鼎革的桓谭在《新论·谴非》中曾记录: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6)此处“八十三万万”似当为“入十八万万”之误。,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又有《汉书·王嘉传》载录西汉末年王嘉在奏折中曾言: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从桓谭到王嘉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国用之财与帝室之财的消长变化:
武帝时,盐铁的收入移归大司农,因此,少府的收入暂时减少,可是,因为口赋的创设,很多公田池御的设立,并且随着一般经济的发展,市税、矿山税、鱼业税的收入也增加起来,结果,少府的收入更加增大,到汉末元帝时,少府、水衡的剩余钱数超过了大司农的剩余钱数,它的收入也几乎可以和大司农匹敌。[6]124
这些分析都在说明着一个深刻的问题——纯粹就财政的收支而言,西汉中期以后国家完全有能力依靠从工商业等货币流通领域征课货币形式的赋税,用以弥补国用。然而,从工商业等货币流通领域征课上来的钱,却直接被用来满足帝室日益膨胀的开销,乃至“国家财政有时虽告穷困,但帝室财政却是富裕的,拥有巨额的剩余钱数。”[6]124要之,在国用与私用之间,帝室从来关注的都是自己如何生而不在乎小民怎样活。因国用不足而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不愿削减帝室收入而额外盘剥小民的名目罢了。东汉以来,虽然光武省官节用,将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合并为一。但这种财政制度,在君主清明时固然有益国用,然而一旦遭逢庸主,那么国用之财便注定难逃被帝室大肆侵吞的命运了。一切分析都旨在说明,帝室本就不具备真正意义上为小民计之精神,更何尝设身处地为小民改革赋税制度呢?纯然在财政数字层面上本来可以省减的“算赋”,却因为帝室的私欲而未被省减。
且前文所言少府收入之增加,并非源于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实是源于帝室统制经济规模的扩大,以致民间有交易而无贸易,有地主而无富商。在史传中的鲜明表象便是《史记》有《货殖列传》、《汉书》尚存《食货志》,然而《后汉书》及现存诸多后汉史料中皆无民间从事大宗贸易与工商业巨贾富商之笔墨。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权力形成的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西汉末年,豪强林立的局面已经确立,东汉光武帝开国曾有借“度田”推行土地改革的尝试,然而举国叛乱的风潮使其不得不退回到原有制度上来,在兼顾豪强和小民的两难中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开国之主尚且如此,似乎倾颓之势已然注定。所以,至东汉各地豪强依托坞壁割据一方时,已经几乎不存在什么民间的自由经济了。即便朝廷改革赋税制度,而征课对象也已然消失殆尽。两汉王室皆自中期之后国用开支日益庞大,使得赋税连年增加。尤其是东汉中期之后,由于羌患频仍、国用不足,加之帝室挥霍无度,以致赋税日益繁重。使东汉王朝在税制弊病重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已无力另图更生之建树了。
三、汉末曹操推行的全新税制
两汉税制积重难返已无价值可言,于是汉末曹操从现实出发制定了简单有效的全新赋税制度。《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了建安九年(204)曹操在河北冀州地区推行了全新的赋税制度: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
该条下亦有注文:《魏书》载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定。……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据此可知,建安九年袁氏大势已去,冀州之地即将平定。曹操为收复民心、恢复生产,制定了全新的租税制度。曹操的赋税政策已经完全不同于两汉旧有之税制。首先,田租更轻。两汉实行“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而曹操推行的“田租亩四升”政策比汉家还要轻。以《昌言》中亩收三斛的平均值计算,可知曹操征课田租的比例接近“百一而税”,可谓至轻!其次,征课形式由粮食、绢帛和棉等实物形式构成,小民在缴纳赋税时不再担心有折换货币之盘剥。最后,绢帛、棉等实物的征课又都是以户为对象,而不再以人为对象。这一办法不仅有利于小农家庭的手工业发展,更有利于该类家庭的人口增殖。曹操此番改革,可谓一举多得。如果暂且抛开尚存的豪强问题,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困扰两汉王朝的土地兼并及赋税制度问题都被曹操的新政一并解决了。
综上所述,两汉王朝直接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小民征收大量货币形式的赋税。沉重的赋税本已可憎,而沉重的货币形式赋税更将小民推向了无底的深渊。为了缴纳货币形式的赋税,小民的社会身份都被迫要从直接的实物生产者转化为商品的出售者。国家重农“禁民二业”,实则在畸形的赋税制度下小民都被迫兼具物质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双重身份。由于小民自身社会地位的卑微,导致其往往无从享受这双重身份带来的积极因素,却常常背负这双重身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