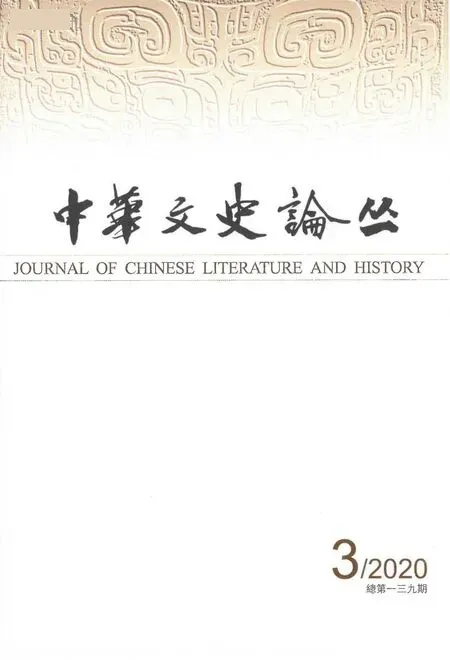中國典籍所載女人國傳説研究
張緒山
提要: 女人國傳説見於記載甚早,其突出特點是女子羣體獨立存在,無性繁殖(入水懷孕、窺井懷孕、飲水懷孕、感風而孕),男嬰不存活。不同時代的女人國傳説總是指向華夏邊緣或“域外”的某一地區的族羣,地域方位的變動意味着華夏族人對域外關注點的變化,而傳説相關内容的變化則反映了受關注的“域外”族羣的特殊性,同時緣於中介傳播者的差異。女人國傳説提供了與華夏族人迥然不同的異族形象,是華夏族羣自我認同所需要的“他者”,是不可或缺的參照物。
關鍵詞: 女人國傳説 《山海經》 華夏
女人國傳説是見諸華夏典籍的衆多傳説之一,歷來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在以往衆多研究成果中,有兩種明顯的傾向,一是將包括中國女人國傳説在内的世界各國不同淵源的女人國傳説視爲一個體系,進行綜合性研究,試圖從中提煉出一條普遍適用的規則,其結果是方枘圓鑿,不得要領;(1)陳廷瓚《女人國考》,《貴州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李衡眉《女兒國的來歷》,《社會科學戰線》1992年第1期,收入氏著《先秦史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頁161—169;詹義康《“女國”釋》,《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2期;林樹明《“女人國”父系意識形態鏡像》,《外國文學評論》1993年第4期;王青《女兒國的史實、傳説與文學虚構》,《南京師大學報》2008年第3期。一是認爲“中外關於女國者之紛説甚夥,實皆子虚烏有,殆姑妄而聽之也”,(2)楊博文《諸蕃志校釋》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31。實際上是認爲不可能對它進行深入的“歷史性”研究。在世界範圍内,女人國傳説見諸一些民族,其起源頗爲不同,各自擁有獨特體系,是各族自身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看,具有較完備體系的女人國傳説至少有三: 中國、希臘與印度。這三大體系之間間或有所交叉,但結構明顯有異,流傳範圍不同;混同研究不僅難度極大,而且往往顧此失彼,難以融通。本文以中國古代有關女人國的傳説爲獨立研究對象,而將希臘與印度淵源的女人國傳説作爲潛在的比較對象,具體研究則另文進行。
一 唐代及以前的女人國傳説
中國古代有關女人國(或女兒國)的傳説起源甚早。在早期傳説中,女人國是居於“域外”的族羣,位於華夏之西。《山海經·海外西經》:“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3)袁珂《山海經校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頁201;楊帆、邱效瑾注譯《山海經》,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16。“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4)袁珂《山海經校注》,頁201;楊帆、邱效瑾注譯《山海經》,頁316。同時又提及“男人國”:“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5)袁珂《山海經校注》,頁199;楊帆、邱效瑾注譯《山海經》,頁314。《山海經·大荒西經》亦云:“大荒之中……有女子之國……有丈夫之國。”(6)袁珂《山海經校注》,頁337—338;楊帆、邱效瑾注譯《山海經》,頁422—423。《山海經》所記多取東夷傳説,(7)參見劉宗迪《失落的天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553—563。女人國傳説乃東夷族人對西方“域外”的一些女性族羣的認識。其他記載亦可爲佐證。《淮南子·墬形訓》記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女子民、丈夫民”,東漢高誘注:“女子民,其貌無有須,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黄衣冠,帶劍。皆西方之國也。”(8)《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44。
關於女人國人口的繁衍方式,郭璞注《山海經》“水周之”條云:“有黄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繞也。”(9)袁珂《山海經校注》,頁201;袁珂《中國神話傳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頁271。郭注表明,感水而孕之説在晉以前早已形成,其後襲用。梁元帝蕭繹所撰《金樓子·志怪篇》云:“女國有横池水。婦人入浴,出則孕,若生男子,三年即死。”(10)許逸民《金樓子校箋》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153。《太平御覽》卷三九五引《外國圖》云:“方江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黄水,婦人入浴,出則乳矣。去九嶷二萬四千里。”(11)《太平御覽》卷三九五,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1826上;袁珂《山海經校注》,頁201。
很顯然,在早期女人國傳説的雛形(prototype)中,除了女人國位於西方這一地理方位限定外,還有三個重要特點: 一是女人國“居於水中”,與“男人國”並立。此一環境元素在後來的傳播中演化爲海島,目的是凸顯女人國與外部世界隔絶所形成的封閉性。二是感水而孕,無性繁殖。三是生男嬰不能生存,故其“純女”特點得以保持。在這三個特點中,無性繁殖之説尤爲重要,是中國傳統女人國傳説中一以貫之的核心元素,與古希臘傳統的女人國傳説形成鮮明對照。(12)希臘淵源的女人國傳説亦有三個主要元素: 一是女人國婦女尚武與好戰;二是女人國婦女與鄰近羣體的男子結合以繁衍後代;三是所生後代只留養女嬰而不留男嬰。中國與希臘兩種女人國傳説雖在構架上涇渭分明,但相同的特點是,在流傳過程中,其中之某一特點可能被突出出來,總體特點始終保持不變。見張緒山《希臘“女人國”傳説在歐亞大陸的流傳》,待刊。在希臘傳統中,無性繁殖偶或見諸記載,但不居主導地位。(13)唐代杜環在751年怛羅斯之戰被阿拉伯人俘虜,於地中海東部世界遊歷十年後回國,寫成《經行記》,其中説:“又聞(拂菻國)西有女國,感水而生。”依夏德的看法,杜環所説的意思可能是“生於水”,如賽普勒斯島流行的維納斯崇拜(Venus Anadyomene of Cyprus)。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Leipsic & Münich, Shanghai-Hongkong, Kelly & Walsh, 1885, p.204.如此,則與女人國無關。中國淵源的女人國傳説在後來的流傳演化中,基本上由這三個主要素構成其核心,有時只突出其中的某一特點;但無論如何,其潛在的用意都在强調女人國獨特的習慣風俗,以及與“域内”華夏族人所熟悉的自身習慣風俗的明顯不同。
自戰國以來,東夷地區即流行頗多域外傳説。《史記·封禪書》云:“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14)《史記》卷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369—1370。秦崛起於河西,初并力西向,與西戎爭霸,及并吞六國,始勠力東指,東夷神仙傳説,漸爲始皇所迷。《史記·封禪書》曰:“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15)《史記》卷二八,頁1369—1370。隨着秦始皇的海上尋仙行動,東海虚無縹緲之傳説逐漸風靡。但東夷淵源的女人國傳説,還没有進入秦人的“神仙”傳説系列。
兩漢及三國時期,朝鮮半島北部處於中原政權控轄之下,成爲“域内”之地,半島以遠的地區成爲華夏族人關注的“域外”,逐漸與“女人國”結緣。女人國轉移到東海,應在這個時期,但具體日期,則不可確知。《後漢書·東夷列傳》:“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其耆者)又説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16)《後漢書》卷八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816—2817。所謂“闚井生子”雖與“感水而孕”稍有不同,但均與“水”有聯繫,屬於同一範疇。可以説這一時期“東大海”中“無男人”的女人國,乃是《山海經》女人國的翻版,只是背景舞臺隨華夏族人注意力在地域上的變化發生了轉移。女人國被置於東海的“海島”之上,其社會封閉性及海島地理的封閉性,與《山海經》所記女人國“水周之”的環境協調起來;而其“無男人”的特性,藴含着兩層意義: 一是成年男子的不存在,二是男嬰的不成活,即《山海經》所謂“生男三歲則死”之意。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記載,女人國位於沃沮國東界的海島上:
毌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宫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宫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王頎别遣追討宫,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17)《三國志》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847。
毌丘儉(?—255)是曹魏後期的重要將領,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正始五年(244)至六年兩次率兵征討高句驪。正史記載:“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六年,復征之,宫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18)《三國志》卷二八,頁762。《三國志·魏書》將“女人國傳説”與歷史記載相混雜,一並鑲入東海這一背景中,完成了地理方位上的轉移。
兩漢三國時期,沃沮部落居於朝鮮半島北部,分爲北沃沮與南沃沮,南沃沮即東沃沮。《後漢書·東夷列傳》:“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19)《後漢書》卷八五,頁2816—2817。東沃沮大致位於今朝鮮的咸鏡道,北沃沮大致位於圖們江流域。由此而言,沃沮耆者所説的海島女人國傳説的舞臺應是日本。在日本古代的“邪馬臺國”時期,2世紀末發生内亂,各國推立女子卑彌呼爲王。卑彌呼女王治下的邪馬臺國是三十多個倭人國家的盟主。這種女人做主的傳統以及相關傳説,可能有助於女人國傳説的形成。(20)《三國志·魏書·倭傳》記載: 卑彌呼死後,“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三國志》卷三,頁858。據此可以認爲,當時部落中男子地位尚不及女子,男性爲王掌權就會造成“國中不服”,女性爲王則“國中遂定”,十三歲的女孩因爲是前任女王的“宗女”,也可以爲王。可知母女繼嗣的女系原則在當時還深入人心。
魏晉南北朝時代,女人國傳説的内涵變得蕪雜起來,其主要變化有二: 一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内容被納入其中,二是背景舞臺不是確定於一個方向,而是呈現多樣化分佈。《梁書·東夷傳》記載:
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産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21)《梁書》卷五四,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809。
慧深是南朝梁人,《梁書》所載乃其499年前後的敍述。慧深所記“女國”並非傳統上之“女人國”,因其國中亦有丈夫存焉;其“食鹹草如禽獸”的所謂女人,也並非真實的女人,而是海獅,所食之“鹹草”即海帶。(22)G. Schlegel, Problémes géographiques: 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 les historiens chinois, III: Niu kouo, le pays des femmes, T’oung Pao 3, 1892, pp.495-510;譯文見希勒格著,馮承鈞譯《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97—306。慧深所述扶桑究爲何地,久有聚訟,迄今未有定論,(23)扶桑國之考證歷來聚訟紛紜,有日本説、美洲墨西哥説、澳大利亞説等等。早期的研究者希勒格認爲慧深所指乃千島羣島的情況。“慧深既未至千島,僅據蝦夷之傳聞,故其説中事實與神話兼有之”。希勒格著,馮承鈞譯《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卷,頁297—306。故其東千里的女人國究指何地,亦難以確知。但無可懷疑的是,慧深所記與傳統女人國傳説多不相符,唯一相符合者僅在所謂二、三月間“入水則任娠”一節,實際上是將殊方異域之奇説與中原流行已久的女人國傳説聯繫起來。此時的背景舞臺仍在東海這個方向上。
此類將某動物附會於人類的記載也見於其他民族史册。如公元1世紀的羅馬作家梅拉(Pomponius Mela)曾記載一地“女子獨居,全身有毛,浴海而孕,其俗蠻野,爲人所捕者,用繩縛之,尚虞其逃走”。(24)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204.10世紀左右的阿拉伯作家伊卜拉希姆·本·瓦西夫(Ibrhīm Bin Wsif)所著《印度珍異記述要》也記載:“海女種族,被稱之爲水中之女。她們具有女性之外表,髮長而飄動,有着發達的生殖器,乳房突起,講一種無法聽懂的語言,伴有笑聲。一些海員説,他們被大風抛到一個島上,島上有森林和淡水河川。在島上,他們聽到叫喊聲和笑聲,便偷偷靠近她們,没有被發現,他們當場捉住兩個,並把她們捆綁起來,和她們生活在一起。海員們去看望她們,並從她們身上享受到快感。其中一個人相信了自己的女伴,爲其解開捆繩,她便立即逃到海中,從此再也没有看見她。被捆的另一個則一直呆在其主人身邊,她懷了孕,並爲其主人生下一男孩。海員把她和孩子一起帶到海上,看到她和孩子在船上無法逃跑,便有點憐憫之情,於是給她鬆了綁,但她卻立刻離開孩子,逃進大海。第二天,她出現在海員面前,扔給他一個貝殼,貝殼裏有一顆貴重的珍珠。”(25)見費琅著,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上册,頁157。以此例彼,可認爲慧深所言只是對女人國傳説的牽强附會。
東晉南遷以後,南朝各代仍以正統自居,但疆域局促,與外部交通不甚暢通,所獲消息多屬道聼塗説,本屬於華夏邊緣“故事”的女人國傳説,與四面八方傳來的消息附會結合,衍化出各種新的説法。《梁四公記》記南梁傑公與諸儒論方域之事,所論女人國遍佈華夏邊緣地域,其方位更加複雜:
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四川東部)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絶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臺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昔狗國之南有女國,當漢章帝時,其國王死,妻代知國,近百年,時稱女國,後子孫還爲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國,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論。(26)張説《梁四公記》,車吉心主編《中華野史》(先秦至隋唐卷),濟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頁846。
《梁四公記》爲小説體裁,據信爲唐代張説所作。張説(667—730/731),字道濟、説之,洛陽人。睿宗至玄宗時三度爲相,封燕國公,詩文皆顯名。《梁四公記》記載的“女人國”大略有三類: 一是以女子爲君長,或女尊男卑的氏族、部落或國家(如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板楯之西);二是以猿猴、鬼、蛇爲夫的羣體(如昆明東南之絶徼、南海東南);三是純女無夫的聚落(如勃律山之西女子浴水而孕)。説法雖變得五光十色,光怪陸離,但有一點是恒定不變的: 與女人國相關的族羣都是華夏族人眼中的“蠻夷”。
隋唐兩代是中原王朝對外交往的繁盛時期,典籍所記諸“女人國”基本上是現實存在的國家,與中原王朝存在朝貢關係。隋開皇四年(584),靺鞨及女國並遣使朝貢。靺鞨,隋唐時代居於我國東北之黑水白山間,此處“女國”與靺鞨並列,其地顯在東方。唐貞觀八年(634),龜兹、吐蕃、高昌、女國、石國遣使朝貢。“女國”與西域諸國相提並論,明顯位於西方。由於隋唐時期中原王朝之疆域經營的重心在西域,“西域”已成中原王朝關注的華夏“邊緣”,故女人國諸傳説均被置於西域。
此一時期之西域女人國有二,其一位於葱嶺之南。隋煬帝經略西域,裴矩主其事,當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交市,裴矩誘令諸商胡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記西域四十四國風土人情,其中即有女人國之消息。《西域圖記》序稱:“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27)《隋書》卷六七,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579。《西域圖記》已佚失,但其材料多爲《隋書·西域傳》所取。(28)任乃强《隋唐之女國》,見《任乃强民族研究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頁213。《隋書·西域傳》云: 女國“在葱嶺之南”,(29)《隋書》卷八三:“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内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見《隋書》卷八三,頁1850。又於《于闐傳》中云: 于闐“南去女國三千里”。(30)《隋書》卷八三,頁1852。玄奘《大唐西域記》云:“此國(婆羅吸摩補羅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稱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31)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08。以其地理位置論,女國應在喜馬拉雅山以北,于闐以南,拉達克以東。(32)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四,頁409。吕思勉亦認爲:“其地明在今後藏。”見《吕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079。任乃强:“婆羅吸摩補羅國,在恒河上游,當今尼泊爾西境,德里之東北。以喜馬拉雅山脈與女國爲界,即所謂大雪山是。玄奘遊印時,吐蕃國西界達岡底斯,與女國接。……北接于闐,當係以昆侖山爲界。”《隋唐之女國》,《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頁215。道宣《釋迦方志》曰:“(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大雪山,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國(言金氏也),出上黄金。東西地長,即東女國。非印度攝,又即名大羊同國。東接土蕃,西接三波訶,北接于闐。其國世以女爲王,夫亦爲王,不知國政。”(33)道宣《釋迦方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7。《釋迦方志》明言即“大羊同國”,所述地理位置與《大唐西域記》同。此“女國”位於中原之西,卻被稱爲“東女國”,是因爲唐人從中亞民族獲知西方世界有“女人國”,故以方位區别,稱之爲“東女國”。(34)任乃强《隋唐之女國》,《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頁216—217。玄奘瞭解希臘羅馬世界的“西女國”:“(波剌斯國)西北接拂懍國……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貨,附拂懍國,故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産男,皆不舉也。”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一,頁943。拂懍即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同時,他也知道印度傳説中的“西大女國”。“僧伽羅國”條記“執師子傳説”: 師子與南印度王女結合生育一對子女,其子殺獅父暴露身分,因其乃畜類所生,被各以一船送走,其子到達僧伽羅(師子國),“其女船者,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魅,産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一,頁868—870。
另一个女人國則位於川西。(35)《新唐書》卷二二一:“(東女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6218—6219。吕思勉認爲,此種記載實際上是“揉兩説而爲一,而不悟其地之相去數千里也”。見《吕思勉讀史札記》,頁1079。有學者認爲,《新唐書》所記“東女國”實際上是葱嶺之南擺脱吐蕃政府威力而遷徙到青海東南、四川西北的蘇伐剌拏瞿呾羅國。見張雲《吐蕃絲綢之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62—65。《舊唐書·西南蠻傳》:“東女國,西羌之别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俗以女爲王。東與茂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及白狼夷。其境東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36)《舊唐書》卷一九七,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277。隋唐史册記載的這些西域“女國”,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女人國”。《隋書·西域傳》:“其國代以女爲王。……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内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37)《隋書》卷八三,頁1850。《大唐西域記》:“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稱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38)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四,頁408—409。《釋迦方志》卷上《遺迹四》:“其國世以女爲王。夫亦爲王,不知國政。男夫征伐種田而已。”(39)道宣《釋迦方志》,頁37。這些國家只是盛行女子當政掌權、女子地位高於男子的女權社會,不同於傳統所説的浴水而孕、“純女無男”的女人國。吕思勉認爲,隋唐史籍混淆了兩種“女國”,“以有女自王,而稱女國,則杜撰史實矣”。(40)吕思勉《吕思勉讀史札記》,頁1083—1084。母權制社會的存在是歷史事實,但將它們稱作“女國”顯然是僭用傳説中的“女人國”之名,屬於文化傳播中常見的“同名異實”,即由於理解上的意義偏離,同樣的名稱被用來描述不同的事物。隋唐時代的“女人國”以如此面貌呈現,説明女人國傳説不僅隨時代而與不同地域結緣,而且也隨時代與地域出現意涵上的變遷。
二 宋代的女人國傳説
南宋以後中國經濟重心南移,中原華夏族人與南海的聯繫增多,目光遂轉向南海。中原王朝遷都汴梁以後,長安失其首都地位,加之西夏阻其梗塞,聯繫西域的陸路交通衰落;與此同時發生的重大變化是海路的日漸興盛,尤其是指南針之應用,更爲海上交通增勢。在海路呈現繁榮,阿拉伯商旅進入中國貿易規模擴大的環境中,女人國傳説的背景舞臺也開始轉移至南海。
12世紀中後期,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海外諸蕃國”條:“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奠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闍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人世。”(41)楊武泉《嶺外代答校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74—75;校注者以闍婆之東的“東大洋海”指澳大利亞以北海域,與下文“女人國”條不符。“東南海上諸雜國”條:“東南海上有沙華公國。其人多出大海劫奪,得人縛而賣之闍婆。又東南有近佛國,多野島,蠻賊居之……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嘗有舶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咸生女也。”(42)楊武泉《嶺外代答校注》卷三,頁111。
《諸蕃志》是趙汝適任提舉福建路市舶時所作,宋已南渡,諸蕃惟市舶僅通,故所言皆海國之事。《諸蕃志》材料多采周去非《嶺外代答》,可與《嶺外代答》對觀。其“闍婆國”條:“又名莆家龍,於泉州爲丙巳方;率以冬月發船,蓋藉北風之便,順風晝夜行,月餘可到。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43)楊博文《諸蕃志校釋》卷上,頁54。“海上雜國”條:“沙華公國,其人多出大海劫奪,得人縛而賣之闍婆。又東南有野島,蠻賊居之……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常有舶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即生女也。”(44)楊博文《諸蕃志校釋》卷上,頁128,130。但《諸蕃志》又記“西女國”:“西海亦有女國,其地五男三女,以女爲國王,婦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女子貴,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生子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與大秦、天竺博易,其利數倍。”頁130。
南宋以後的女人國故事,與此前頗爲不同。在此一時期的女人國傳説中,背景舞臺已經發生轉移。三佛齊,唐代稱室利佛逝,乃Srivijaya之對音,在今之蘇門答臘東南部;闍婆即爪哇島;沙華公國在加里曼丹島,或即Sawaku島之古名,或即Sembakurq之對音。(45)楊武泉《嶺外代答校注》,頁112;楊博文《諸蕃志校釋》,頁129。如此,則其東的女人國應在蘇拉威西島。(46)有學者列出兩説,或指蘇拉威西島布吉斯(Bugis)人居住地,或在澳大利亞北部。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彙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54。前説是,後説非。依《嶺外代答》、《諸蕃志》所記,更應注意者有三點: 一是女人國的生育方式由“感水而孕”轉變爲“感風而生”;二是外來船舶飄落其國的男子,被“羣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即存在虐殺男子現象;三是落難於其國的智者盜船逃走,遂使女人國之風俗傳播於外的傳奇。此前未見記載的這些細節均非傳統説法。
這些新增加的元素,已見於稍早時期的阿拉伯文獻。10世紀左右,伊卜拉希姆·本·瓦西夫《印度珍異記述要》記載“女人島”:“該島位於中國海最邊緣。據説全部島民皆女人,由風受精繁殖,而且只生女孩;又傳説,女人們因吃一種果實而受精。還傳説,在該島上,金子像竹子一樣生長,呈杆狀,島民以金子爲食。有一次,一個男子落入她們之手,女人們要殺死他,但其中的一個可憐他,把他拴在一根梁上,投入大海,海浪和海風一直把他帶到了中國。他去見中國國王,向國王談起該島的情況。國王隨即派船前去尋找;但是航行了三年,卻没有找到,連一點蹤迹也没有。”(47)費琅著,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上册,頁175。中國海在哪裏呢?據作者説:“過了占婆海,就是中國海。”(48)費琅著,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上册,頁163。占婆、闍婆,同名異譯,即爪哇。很顯然,阿拉伯文獻中的“中國海”即中國文獻中的“南洋”覆蓋的海域。阿拉伯人雖然在此一時期主導了東西方海上貿易,但對他們而言,“南洋”仍是一個有所瞭解、總體上陌生的“邊緣”地區。
在趙汝適(1170—1231)及其隨後的時代,這個版本的女人國傳説在阿拉伯世界仍在流行。卡兹維尼(Kazwini,1203—1283)《各國建築與人情志》中記載:“中國海中的女兒島。人們發現那裏都是女子,絶無任何男子的蹤影。姑娘們靠風受孕,生下來的也是和她們一樣的女子。還有傳説認爲,她們是靠吃一種樹的果子而受孕的,而這種樹就生長在本島之内。她們吃果受孕之後也生育女兒。有一位水手敍述説,他有一次曾被大風吹向了此島。他説:‘我發現到處都是女子,没有一個男子和她們生活在一起。我還看到此島的黄金如泥土一樣豐富,金蘆葦長得如竹子一般。她們想把我殺死,但其中之一把我藏了起來,然後又置我於一塊木板上,放在海中任其飄蕩。大風將我吹向了中國海岸,我向中國皇帝報告了有關此島的情況,並對島中遍地是黄金的景象作了稟奏。’中國皇帝便派人前往探險,走了三年也未能找到該島,只好一無所得地空手敗興而歸。”(49)費琅著,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上册,頁340。伊本·瓦爾迪(Ibn al-Wardi)的《奇迹書》(1340年左右寫作),(50)“女兒島是一個大島。據傳聞,島上從來没有男人。傳説這裏的女人是靠風受孕的。懷孕後,她們也生下和自己一樣的女子。某些人還聲稱這個島上有一種樹,女人吃了這種樹上的果實以後即懷孕。……相傳,有一個男人受天命支配而來到這個島上,島中的女子們想將他殺死,但其中一位頓生憐憫之心,將他裝在一艘小船上抛到海裏。他逐浪顛波而漂泊到中國的一個島上。他向這個島的國王講述了本人在女兒島上的所見所聞,講到了島上的居民以及豐富的黄金。於是該國王就派遣了一些船隻及一部分人(包括此人在内)前往。爲了尋找女兒島,他們在海裏航行了許久,卻始終未見蹤影。”見費琅著,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下册,頁464—465。顯然取自同樣的資料。及15世紀初巴庫維(Bkuwi)《關於考證强大國王古迹和奇迹的書》,都敍述了同樣的“女人島”故事。(51)“女兒島。它與中國毗鄰,島上只住有女子。傳説這裏的女子是以風受孕,或者是吃島上的某種樹的果實而懷胎。”見費琅著,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下册,頁517。16世紀初麥哲倫環球航行時,他的參與者皮戛費特在航海記録裏也記載了這個傳説。1522年,他們從馬魯古海抓來一個做領航員的當地老人,告訴他們説,在爪哇島後面有一個阿洛島,島上的婦女就是由風受孕的;如果有男人膽敢登上這個島,女人就會殺死他。(52)謝苗諾夫著,蔡俊生譯,沈真校《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60—161。各方傳説均指向“南洋”這個地區,説明人們將這個傳説與這個地區存在一些符合女人國傳説的事實聯繫起來,將女人國傳説的背景舞臺轉移到了這一地區。
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無論中國記載還是阿拉伯記載,其中所謂的“男人至其島輒死”即女人虐殺男人這一情節,似乎染有印度傳説成分。這個情節最典型地見於印度流行的“僧伽羅傳説”。傳説講述的是: 古印度僧訶劫波城有一位名叫僧伽羅的商人,帶領五百名隨從來到名爲“寶島”的斯里蘭卡。登岸後,被住在一座鐵城中的女妖(羅刹女)所誘惑。這些女妖化作嫵媚的婦女,把他們當作丈夫看待,並準備不久後把他們吃掉。僧伽羅得到神的警告和指點,不爲所動。但他的同伴迷戀女色,不相信會有殺身之禍,結果被羅刹女全部吃掉。僧伽羅隻身逃回僧訶劫波城。羅刹女王懷抱一名嬰兒追尋而來,向國王告狀,要求僧伽羅與她破鏡重圓。國王不但不聽僧伽羅的申訴,反而被羅刹女王的妖豔所傾倒,將她收入後宫。羅刹女於夜晚召來其他女妖,把王宫内的人全部吃掉。民衆推選僧伽羅登基爲王。僧伽羅率軍剿滅女妖,並在島上定居下來。他們的後代稱爲僧伽羅人。此傳説亦爲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一所載。(53)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一,頁873—875;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88—89。
自唐代以來,海上交通之主導勢力爲波斯人,宋代則爲阿拉伯人。南宋以後,陸上交通梗塞,阿拉伯人東來皆循海路。印度、南海島嶼爲阿拉伯人必經之地,阿拉伯人往來東西方從事的貿易,規模空前。阿拉伯人集合印度、阿拉伯傳説,成爲阿拉伯典籍及《嶺外代答》、《諸蕃志》等此一時期中國典籍域外材料的主要供給者。周去非、趙汝適所記與阿拉伯傳説兩兩相對,遥相呼應,清楚地表明二者之間的聯繫。
不過,宋元兩代中國典籍在記載傳自南海的女人國傳説的同時,仍保持着對中原傳統女人國傳説的記憶。北宋劉斧撰《青瑣高議》,其卷三《高言》記一人“殺友人走竄諸國”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外逃的殺人者北走漠北,南及海外,遊歷大食及其南面的林明國,林明國南又有一國,其國東南有“女子國”,云:“聞東南有女子國,皆女子,每春月開自然花,有胎乳石、生池、望孕井,羣女皆往焉。咽其石,飲其水,望其井,即有孕。生必女子。”(54)劉斧《青瑣高議》,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27。《青瑣高議》乃小説家言,所言域外之事,多異想天開,其實不過串綴舊典與時聞之域外異聞。在我國史書中,“大食”是阿拉伯的稱號,自唐代與中國交通漸多,頻頻見諸中國典籍。所謂大食國之南有林明國,林明國之南又一國,其國東南有“女子國”,這類地理次序完全出自臆想;所謂“女人國”故事中的懷孕方式,除了在“望其井”之外增加“飲其水”的想像,在總體上都是舊典舊説,並無新獲材料。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異聞類聚”篇仍保持舊説:“他如女人國,視井而生育。”(55)蘇繼廎《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79。
周致中《異域志》“女人國”條云:“其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尺許,桃核長二尺。昔有舶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遂傳其事。女人遇南風,裸形感風而生。”這顯然是宋代新獲之知識,與周去非《嶺外代答》及趙汝適《諸蕃志》所記同出一轍,但同時也提到:“又云與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國無男,照井而生,曾有人獲至中國。”(56)周致中《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54。奚部源出鮮卑宇文部,南北朝時自號庫莫奚,隋唐簡稱爲奚。奚人初居於土河(今老哈河)上游一帶,隋唐之際,擴散到今山西、河北北部地區,臣服於突厥。小如者部見於《通典》、新舊《唐書》,爲室韋之一部,居於嫩江流域以北。把女人國傳説與奚部小如者部聯繫起來,這樣的記載顯示了新舊知識的混合。
三 明代作爲小説題材的女人國傳説
元代以後,“女人國”傳説不再作爲域外的社會現實爲涉外史籍所關注,而成爲新發展起來的雜劇、小説等文學形式表現的重要主題之一。元末明初的雜劇家楊訥(約1333—?),一生所作雜劇近二十部,今存《劉行首》、《西遊記》兩種。其中《西遊記》記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長達六本二十四折,是吴承恩所著《西遊記》小説的一個重要依據。(57)鄭振鐸主編《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4年。《西遊記》雜劇所敍主題,是唐僧西天取經路經女人國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人國是“千年只照井泉生,平生不識男兒像”。其中第五本第十七折《女王逼配》以女王本人口吻介紹其國情形:“俺一國無男子,每月滿時,照井而生。俺先國王命使,漢光武皇帝時入中國,拜曹大家爲師,授經書一車來國中。至今國中婦人,知書知史。立成一國,非同容易也呵!”這種説法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沿襲了《後漢書·東夷列傳》所謂東海女人國“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的傳統;二是介紹了女人國與中原王朝的歷史淵源,上溯至漢代的班昭(曹大家),承認所受中原文明之影響,顯示出中原中心主義的敍事原則——這是中原華夏族人的族羣意識的一種本能反應,故在説明域外女人國“蠻夷”族性特徵的同時,不忘説明他們對“天朝上國”的傾慕以及攀附心態。
將同一主題發揚光大,使之成爲一個遐邇聞名、膾炙人口的故事的,當推明代吴承恩(約1500—1583)所著《西遊記》。《西遊記》所展示的中原視角更爲明顯。對女人國的描述首先是突出中國傳統女人國傳説所固有的封閉性。其中第四十八回的描述是: 大雪封河面之後,三藏與一行人到了河邊,勒馬觀看,見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問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裏去?”陳老道:“河那邊乃西梁女國,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我這邊百錢之物,到那邊可值萬錢;那邊百錢之物,到這邊亦可值萬錢。利重本輕,所以人不顧生死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數人一船,飄洋而過。見如今河道凍住,故捨命而步行也。”(58)吴承恩《西遊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頁357。去往女人國需要“飄洋而過”的説法,實際上是《山海經》以來女人國“水周之”之説的曲筆。
其次是將傳統的“感水而孕”改造成“飲水而孕”,顯示了宋代以後的傳説演化的一個特點。《西遊記》第五十三、五十四回描述: 唐僧師徒四人來到西梁女國,唐僧與八戒飲了子母河之水而感覺肚疼,遇見幾個半老不老的婦人,向她們説明情況,希望找些熱水喝。幾個婦人望着玄奘“灑笑”。孫悟空大怒,催逼老婆子去燒熱水。那老婆子驚嚇之餘解釋説:“我這裏乃是西梁女國。我們這一國盡是女人,更無男子,故此見了你們歡喜。你師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條河唤做子母河,我那國王城外,還有一座迎陽館驛,驛門外有一個照胎泉。我這裏人,但得年登二十歲以上,方敢去吃那河裏水。吃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若照得有了雙影,便就降生孩兒。你師吃了子母河水,以此成了胎氣,也不日要生孩子,熱湯怎麽治得?”幸賴悟空到解陽山取得“落胎泉”之水,化解了二人的懷胎危機。(59)吴承恩《西遊記》,頁390—404。
在西梁女國,雖然“農士工商皆女輩,漁樵耕牧盡紅妝”,但男人仍被視爲人口繁衍的一種途徑。一個事實可説明這個問題: 當女人們看到走在街道上的唐僧師徒時,一齊鼓掌歡笑道:“人種來了!人種來了!”很顯然,在這國中,男人仍被視爲繁育後代的“種子”之源。所以女人國女王聽説唐僧前來,不曾見面早已是“滿心歡喜”,芳心暗許,對衆女官説道:“我國中自混沌開闢之時,累代帝王,更不曾見個男人至此。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賜來的。寡人以一國之富,願招御弟爲王,我願爲后,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卻不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聞聽女王説法,也是個個“拜舞稱揚,無不歡悦”。(60)吴承恩《西遊記》,頁398—399。最終多虧悟空施計,四人方纔走脱。在傳説中,西梁女國“陰陽配合,生子生孫”這條暗線已經脱離了傳統“女人國”故事的構架,顯示出印度女人國故事影響的痕迹。(61)還有一些徵象説明印度故事的影響。西梁女國設有接待外國使者的“迎陽館驛”,唐僧師徒四人在子母河附近的村舍投宿時,曾被老婆子取笑道:“還是你們有造化,來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們也不得囫圇了!”八戒哼哼:“不得囫圇,是怎麽的?”婆婆道:“我一家兒四五口,都是有幾歲年紀的,把那風月事盡皆休了,故此不肯傷你。若還到第二家,老小衆大,那年小之人,那個肯放過你去!就要與你交合。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兒哩。”見吴承恩《西遊記》,頁395。“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説明西梁女國裏存在“虐殺男子”的習俗,這與印度僧伽羅傳説相同。這是以往研究者通常所不注意的元素。
明代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基本上沿襲《西遊記》的套路。其中第四十六回寫鄭和下西洋的船隊經過女兒國,元帥鄭和喬裝打扮後,前往王宫討要降書與降表、通關牒文,被女王看中欲行匹配,無奈鄭和乃太監之身,難遂其願,女王羞惱成怒,監禁鄭和。鄭和麾下劉先鋒領兵五十人前往搜尋,路過一座大橋時,向橋下一泓清水觀望,覺得肚疼,以爲是中了瘴氣,便舀了橋下清澈的流水來喝,肚子隨之大了起來。一位當地的女百姓被兵士捉到,領到軍中王爺面前,告訴明軍:“我這國中都是女身,不能生長。每年到八月十五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到這個橋上來照。依尊卑大小,站在橋上,照着橋下的影兒,就都有娠。故此叫做影身橋。”王爺道:“那橋底下的河,叫做甚麽河?”女百姓道:“叫做子母河。”王爺道:“甚麽叫做子母河?”女百姓道:“我這國中凡有娠孕的,子不得離母,就到這橋下來,吃一瓢水,不出旬日之間,子母兩分。故此叫做子母河。”明朝官員從百里外山中的“頂陽洞”取得聖母泉水,纔摆脱尷尬處境。(62)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上册,頁600—606。
如果説《西遊記》中的“飲水而孕”是傳統“感水而孕”、“窺井生子”的演化,則《西洋記》所謂“照泉懷胎,喝水生子”之説,則應是中原傳統“窺井生子”傳説與宋代以後衍出的“飲水而孕”説法的結合。如果説在《西遊記》中,“照泉”這一因素只是輔助性的因素(證明是否懷胎),那麽在《西洋記》中則被提高到主導地位,而喝水則被改造成輔助(助産)因素。如果説《西遊記》利用了唐代玄奘印度巡禮的背景舞臺(西域),《西洋記》則借助同時代(明代)鄭和下西洋的背景舞臺(南洋)。但無論如何,無性繁殖這一主線仍然歷歷可見。(63)清代李汝珍所著《鏡花緣》也描寫了一個“女兒國”的故事,但這個“女兒國”與《西遊記》中的“女兒國”有所不同,其中有男人存在,只是在這個“女兒國”中陰陽反背、男女顛倒,女人是社會的主導,處於强勢地位,從國王到各級官員都是女人,而男人則居於從屬地位。這個類型與隋唐女人國傳説框架相同,脱離了傳統“女人國”傳説。見李汝珍《鏡花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可以説,無性繁殖是遠東“女人國”傳説中最傳統且固定的主導元素。(64)關於唐代“女國”的討論,見Jennifer W. Jay, “Imagining Matriarchy:‘Kingdom of Woman’ in Tang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6. 2, 1996, pp.220-229.
四 女人國傳説的文化意涵
從起源上,“女人國傳説”的出現,乃是華夏文明圈内族衆與邊緣區部族社會交流互動的産物。它所反映的是華夏族人對邊緣區部族社會的認識,或者説,是周邊部族社會的信息通過某種渠道,裊裊縷縷地傳播到華夏文明中心區後,在華夏族人心中形成的帶有想像性的“知識圖景”(或曰心理認知痕迹)。這種“知識圖景”逐漸演化爲一種標識性的族羣符號,爲華夏文明圈内的族衆所接受,又反過來被用來標識新的邊緣部族,自身邊緣的“他者”。隨着華夏族人活動重心的變化,其所關注的域外族羣也發生變化,“女人國傳説”的背景舞臺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轉移,有關女人國的“知識圖景”也隨之發生轉移。因此,“女人國傳説”所代表的是他們對邊緣區部族的“他者”異己性的認知,對邊緣區部族的身分特徵的“認定”。
女人國的最大特點,是封閉性的女性羣體的存在;與這種女性羣體並立的,還有獨立的男性羣體。《山海經·海外西經》有“女子國”與“丈夫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女子之國……有丈夫之國。”《淮南子·墬形訓》所記海外三十六國,西北至西南方諸國中,有“女子民,丈夫民”。在傳統的女人國傳説中,“丈夫國”始終是一個隱形的存在;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女人國傳説中的這個隱形元素逐漸退居幕後。
女人國傳説中的女性單性别羣體的存在,反映的是初民社會一定階段上的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源於原始人類的“禁忌”。在關乎原始羣體生存的禁忌中,最重要的禁忌之一,是進行生産時的“性禁忌”,尤以狩獵活動過程中的“性禁忌”最爲重要。(65)謝苗諾夫著,蔡俊生譯,沈真校《婚姻和家庭的起源》,頁78—84。在原始羣體中,最初的狩獵具有自發性質,但後來有組織的狩獵成爲決定羣體生存的重要活動;能否使狩獵活動有效,狩獵羣體的組織和準備至關重要;需要完全戒除和禁止一切成員之間的摩擦、衝突,而衝突的主要根源往往是非規範的性關係。爲了避免衝突的發生,當時唯一可采取的辦法,就是節制性關係,即狩獵以及準備期間嚴禁性關係的發生;禁止男女間的交往,違者被處死。在性禁忌規範要求下,由全體成年男子組成的狩獵隊在遠征前離羣索居,並且時間越來越長。這一“禁忌”使原始羣體逐漸呈現出兩個獨立存在的性别羣體: 一是包括全體成年男子;一是包括女人與孩子。男子外出從事狩獵,婦女從事其他生産活動。(66)謝苗諾夫著,蔡俊生譯,沈真校《婚姻和家庭的起源》,頁136—139。一些原始族羣的捕魚活動也有同樣的風俗存在。無論是捕魚還是狩獵,一般都有很長的季節。這種風俗習慣本來出於生産活動的實用目的,但在長期發展中逐漸演變成爲宗教性禁忌,從而獲得頑强生命力。(67)漁獵活動開始前限定的時間内,不僅要禁絶與婦女發生性關係,而且要徹底同異性隔絶。這在未開化民族中是常見現象,被稱之爲“獵人和漁夫的禁忌”。見詹·喬·弗雷澤著,趙陽譯《金枝》,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275—278。
當氏族内婚姻被禁止而進入兩合氏族婚姻後,不僅不同氏族的男人與女人分開居住,而且同氏族的男人與女人也分開居住。於是原始羣内形成彼此隔離的男人羣體與女人羣體。一個氏族内的男、女羣體與另一個氏族的異性羣體形成經常的、鞏固的婚姻關係;而本氏族成員之間卻完全隔斷了性與婚姻關係。如鄂温克人中,一個氏族分成男女兩個部分,男人羣體稱作Kul(苦魯),女人羣體稱作Mu(木),男女兩個羣體不通婚,其丈夫、妻子屬於另外無血緣關係的氏族,這個氏族同樣分成男女兩個羣體。(68)吕光天《論古代鄂温克人的羣婚家族及氏族的産生》,《考古》1962年第8期。在這兩種情況下,兩個羣體生活上被隔離開來,發展爲居住地上的分離狀態。這種獨立的女性羣體的存在,構成了中原華夏族人中流傳的“女人國”傳説的基礎,女人國傳説反映了這種現實。
浴水而孕、窺井而孕、飲水而孕、感風而孕等相關傳説,屬於感生神話的範疇。感生神話是初民社會的基本思維特點之一。在初民社會的思維中,世界呈混沌朦朧狀態,人與自然緊密交織在一起,萬物融爲一體,人神互感、天人相感、物我相感,通過直接或間接、整體或局部的交感而孕育生命。對於一切生命而言,水與氣是兩種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一年四季中春季雨水帶來的萬物復蘇,植物隨雨水而成長,生物隨雨水的降臨而出現,很容易讓初民社會的人類認爲水中藴藏着生命的種子。對於個體生命而言,氣的存在是“生”的徵象,没有了氣,生命便告結束;對於采摘草木果實的民族,春風帶來的草木復蘇,也必然使人産生風與生命關係的聯想;對於農耕民族而言,農作物在春天中發芽,夏天中成長,秋天中收穫,冬天中儲藏,都與時令變化、四季風向密切關聯。季節變换下的風向變動與植物生長、成熟的密切聯繫,使人類産生聯想,認爲人類生命隨風而來。這種感風而孕的傳説,至今在我國雲南楚雄彝族女兒國神話中仍完整地保留着。(69)《搓日阿補征服女兒國》流傳於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其中講到: 在女人國的女人們於每年三月,跑到花頂山上,迎風站幾天,回來就懷孕,生孩子。見李子賢《東西方女兒國神話之比較研究》,《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頁41—48;又見李子賢編《雲南少數民族神話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8—55。將生命的孕育與水、風聯繫起來,是初民原始思維中的“生殖聯想”。
浴水而孕、窺井而孕、飲水而孕、感風而孕等感生神話,顯然也曾經存在於中原族人中,但在父權制確立以後就完全消失了。(70)黄帝母見雷電繞北斗身感有孕;禹爲其母吞食神珠薏苡而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周之先祖乃其母踏巨人足迹而生,等等,可能是這種感生神話的衍化。《山海經》郭璞注“婦人入(黄池)浴而孕”是往昔觀念的遺存。女人國傳説所反映的,是父權制原則下的華夏族人對早已消逝了的社會習俗的記憶,但由於這種社會習俗在華夏社會早已没有對應的實際存在,故而將這種習俗當作周邊異族的奇異特徵。在華夏族人對域外的活動中,一旦發現邊緣地區或域外的某個族羣呈現出某個特徵與女人國傳説的某個重要元素相符合時,存在於華夏族人記憶中的這種格式化的傳説便被啓動,運用到他們身上。不同時期出現的女人國傳説在地域背景上的變遷,在根本上反映了中原王朝對域外族羣關注點的變化。
女人國傳説之不斷見諸華夏典籍,源於“華夷觀念”支配下的華夏族人對邊疆異族的持續關注。華夏族人從很早就有强烈的“華夷”情感,“華夷之别”是華夏族人源遠流長的强大意識之一。中華古人自稱“中國”、“華夏”、“中華”、“九州”、“神州”等,與此相對應的是“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其文化優越感很早就已存在。(71)當然,中華族人的華夷觀念的發展傾向是重文化過於種族,即韓愈《原道》所謂“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春秋時代華夏族人的“四夷”意識已經非常明確,諸侯爭霸的口號是“尊王攘夷”。管仲説:“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72)《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一,《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2009年,頁3876上。(《左傳·閔公元年》)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73)《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六,頁4664下。(《左傳·定公十年》)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74)《論語注疏》卷三,《十三經注疏》,頁5356上。(《論語·八佾》)由這種内外之别的“華夷”觀念構成的華夏意識,包含互爲對照的兩個方面,一是自我族羣意識,一是基於自我族羣意識的異族觀念。
華夏族人的族羣認同,集中表現在由文教禮儀制度爲核心的族羣優越感上。《戰國策·趙策》云:“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75)劉向《戰國策》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391。唐代爲中國歷史上的黄金時代,氣魄恢弘,胸襟開闊,有海納百川的氣度,但“華夷”觀念仍很清晰。杜佑雖承認“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但仍堅持華夏文明、四夷荒蠻的觀念,認爲四夷“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76)杜佑《通典》卷一八五《邊防一》,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4970—4971。唐太宗謂:“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朕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77)《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26。唐太宗是否做到了“愛之如一”,平等對待華夏與夷狄,姑且不論,但自古華夏族人“貴中華,賤夷狄”,則是不爭的事實。“華夏”與“蠻夷”的對照與對立,是華夏族人族羣認同感的極重要的媒介元素;華夏族人的自我認同在這種對立中得到强化。
這種“華夷”意識之下的“内外”觀念,在地域上表現爲“域内”與“域外”。流行於華夏族羣中的女人國傳説所表達的“女人國”特質,屬於域外“夷狄”的特徵,與“域内”華夏族的族性特徵形成對照。所以,我們看到的一個一以貫之的現象是,在“女人國傳説”的歷史上,“女人國”總是被置於“域外”——華夏文明圈的外圍。從春秋戰國時代以後,諸如《山海經》、《穆天子傳》之類充滿異域傳説的作品,以及正史中專涉中原與外族交往及域外知識的“四夷傳”,固然反映了中原族人與域外交通的事實,以及對周圍世界的强烈探求欲,但更藴含着一個文化現象,即通過對華夏文化圈邊緣區“其他”族羣異質性的“蠻夷特徵”的刻畫,凸顯中原族人的同一性,强化中原族人對自身族性同一性的認同。“女人國”是中原華夏族人記載的域外族羣之一,屬於“蠻夷”族羣範疇,其“純女無男”、“感水而孕”、“感風而孕”等生育方式屬於與華夏迥然不同的“奇風異俗”,帶有蠻夷族羣特徵的烙印。對華夏族而言,“女人國”是一個異己性的“他者”,這種“他者”存在的客觀作用之一,是讓華夏族人在與“夷狄”特徵的對照中,認識到自身典章制度的優越性,凸出華夏族人自身的族羣意識。
在春秋戰國到漢代華夏邊緣的形成、擴張中,被包含在“邊緣”中的各地中國人雖然逐漸凝聚許多共同性,然而在文化上仍有相當的差異,他們需要通過强調“異質化”的邊緣族羣,來强調在此邊緣内人羣間的共同性與同一性。域外的“珍異土産”及異族的“奇風異俗”成爲可以利用的資源,被用來强化與凸顯域内人羣的同質性與一體性。春秋至漢代出現或流行的許多作品,如《逸周書·王會》、《山海經》、《淮南子·墬形訓》以及史書中的“四夷傳”等,都是以他族的異質性來凸出域内的同質性。(78)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羣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04。所以,只要華夏族人的自我認同過程存在,作爲參照物而與之相伴的外族的異質性就不可能消失。隨華夏族人的活動重心不同,表現“域外”不同地區的族羣異質性的女人國傳説被一再提起,這一事實所反映的是華夏族人自我認同的需要。明代以後女人國傳説被納入雜劇、小説等,以更爲通俗的流播,可謂與時俱進,使華夷觀念更廣泛地深入民衆意識。女人國傳説在中華典籍上綿延不絶,斑斑可稽,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