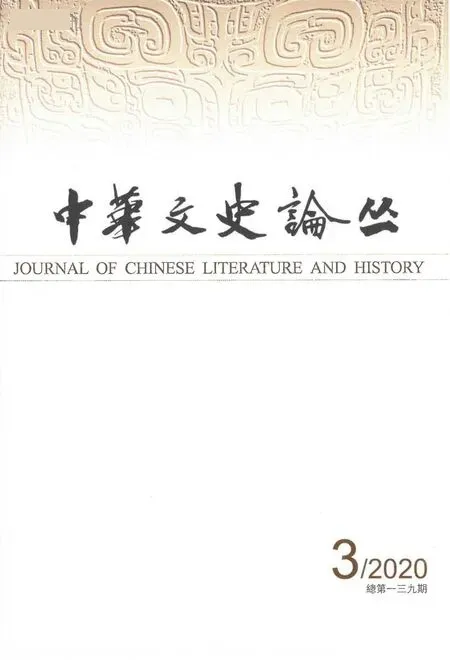禮制與情欲: 唐代婚禮的儀式書寫與文學表達❋
楊爲剛
提要: 敦煌遺書中保存了大量唐代婚禮文獻,其中包括官方編修的禮書和用於婚禮的口誦詩文。通過對這些婚禮書寫進行分析,以及與存世婚禮文本比讀可以發現,唐人的現實生活中,婚禮程式並没有完全被儒家禮制束縛,而是表現出世俗化、功利化的傾向,以富貴與情欲爲主題的婚禮文學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産物。唐代婚儀禮書與文學表達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魏晉以來的貴族文化,從唐前期到唐後期,婚禮書儀與婚禮文學的書寫羣體從宫廷文臣轉移到官僚文人,婚禮書寫與文學創作表現出世俗化、儀式化的特點。唐代婚儀書寫與表達方式的演變軌迹,成爲中古時期從貴族社會到官僚社會、從貴族文學到官僚文學變革的一個縮影。
關鍵詞: 儀式 書儀 書寫 文學表達
前 言
婚姻是建立在生物性特徵基礎上的社會行爲,婚禮是婚姻獲得合法性與合“禮”性的儀式與程序,既是一種體現社會意識形態的禮法制度,也是一種約定成俗的風俗習慣。從歷史發展看,婚姻儀式與其他儀式一樣,是一種與原始宗教有淵源關係的表演形式,去掉巫術色彩的婚禮是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重要過渡儀式。從儀式的構成要素看,婚禮儀式是一個社會文本(social text),是由多種表意手段構成的符號系統: 包括作爲儀式場所的空間佈置、内部裝飾與器物陳設,有一套體現儀式參與者身分的行爲表演,以及配合儀式進行的口誦文本。從儀式展開的過程看,婚禮具有時間、地點、人物與情節等要素,具有開始、發展、高潮、結束的完整過程。作爲歷史現場的古代婚禮很難全面地還原,我們對於古代婚儀的瞭解或想象,基本上通過文字以及少數圖像材料。
最早的系統性婚儀記載保留在《儀禮》與《禮記》中。一般認爲,這兩種儒家經書中保留了周代的婚姻制度。秦漢以來,這套體現儒家倫理觀念的婚儀文獻成爲官方與民間舉行婚禮的指導思想。唐代時期,有四種形式的婚儀書寫值得注意,一是中央政府制定的禮典,以《大唐開元禮》爲代表。一是地方政府編修的禮書,如敦煌遺書中的婚禮書儀。一種是婚禮舉行過程中的口誦文學,如敦煌遺書中的婚嫁詩文。最後一種是存世文獻中的婚儀文學,以公主婚嫁詩文爲代表。
各種文體、文類中的婚儀書寫是婚禮的文字表達形式,受到文體功能的限制,不同的文體或文類只能表達婚禮的某一面向。因爲唐代婚禮無法進行田野考察,圍繞婚儀儀式,官方制定的禮典、地方禮書與文人文學創作如何來書寫與表達,它們之間又存在何種關係?本文嘗試在這幾方面進行探析,以求證於方家。
一 禮制與風俗: 官方書寫中的婚禮
婚禮儀式的産生可以上溯到殷商時期甚至更早,遠古時期的婚儀因爲没有文獻記載而無法詳考。(1)關於婚禮的起源,參看王玉波《中國婚禮的産生與演變》,《歷史研究》1990年第4期;黄浩《昏禮起源考辨》,《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儀禮·士昏禮》是現存最早關於婚儀儀式的文獻,一般認爲出現在春秋、戰國之間,對婚儀思想進行解釋的《禮記·昏義》時間還要晚。(2)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沈文倬《菿闇文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1—27。《儀禮·士昏禮》中的婚禮儀式一共有十四個儀式單元,主體歸納爲六項,即爲納采、納吉、問名、請期、納徵、親迎等“六禮”。儀式空間設置在宗廟,儀式在“敬慎、重正”的祭祀氛圍中展開,主持者是家長。作爲當事人的新郎、新娘在最後的“親迎”環節出現,“同牢合巹”儀式標誌着婚禮的完成。
通過對儀式時間、空間、參與者及其行爲的規定,《儀禮·士昏禮》製造出一套符合儒家家庭倫理觀念的儀式敍事,婚姻的倫理與教化功能得到突出强調。《禮記·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3)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416。婚禮目的是締結兩家姻親關係,賦予男女雙方傳繼香火與繁衍子孫的角色定位與責任擔當。(4)葉國良《〈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與執禮時之三項基本禮意》,《嶺南學報》復刊第3輯,頁1—10。《禮記·昏義》:“(婚姻)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别,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 昏禮者,禮之本也。”(5)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418。婚禮儀式圍繞家庭(族)與社會關係的生産、維係與傳遞來進行設置。因此,士昏禮是體現儒家婚姻理想的儀式敍事,作爲婚姻生物學基礎的,與個體享受與快樂有關的内容都被有意識地消解或者遮蔽。(6)李安宅《〈禮儀〉與〈禮記〉的社會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40—42。焦傑《附遠厚别防止亂族强調成婦: 從〈儀禮·士昏禮〉看先秦社會婚姻觀念》,《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漢代儒生整理的《儀禮·士昏禮》是否在兩周時期得到嚴格執行,有學者表示了質疑。(7)陳筱芳《周代婚禮: 六禮抑或三禮》,《文史》2000年第4輯。但是,這套體現周禮婚義的儀式書寫卻是漢魏以後婚禮儀式的綱領性文獻。魏晉南北朝是禮學大發展的時期,吉、凶、軍、賓、嘉五禮制度逐步確立。唐代禮制集前代之大成,形成了成熟的五禮體系,《大唐開元禮》的編纂是標誌性成果。作爲營造盛世的産物,《開元禮》被視爲唐代的《禮記》。對於《開元禮》中諸禮的制定與行用,儘管學術界存在不同看法,(8)關於《大唐開元禮》的行用問題,相關研究甚多,代表性研究成果參看劉安志《關於〈大唐開元禮〉的性質及行用問題》,《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吴麗娱《營造盛世: 大唐開元禮的撰作緣起》,《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但是就婚禮儀式而言,《開元禮》的指導思想與古禮一致,婚禮儀式圍繞家庭與社會關係的生成與傳承,設置了包含“六禮”在内的十二項儀式。儀式的主持者是雙方父母,新郎、新娘在最後親迎環節出現,到拜姑舅禮結束。與古禮相比,《開元禮》的等級尊卑差别更加細化,婚儀分爲皇室與仕宦階層兩類,仕宦階層又分爲三品以上、四品至六品、六品以下三類。儀式空間更爲具體明確,禮儀在宗廟或者家宅中進行,大門、寢門、階阼、庭院與正寢(中堂)及其附屬空間構成儀式展演的主要場域。
與《儀禮·士昏禮》一樣,没有證據證明這套時間冗長、程式複雜、儀節繁瑣的《開元禮》婚禮儀式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嚴格遵循,更可能的情況是作爲一種指導思想貫徹於婚儀實踐中。分析儒家經書、國家禮典與實踐層面上婚禮儀式的關係,需要具有實踐品格的婚儀書寫,敦煌遺書中的婚禮書儀提供了這方面難得的材料。
書儀是書信的程式與儀範,産生並流行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書儀包括書信的書寫規範與相當於儀注的禮儀規範兩部分内容。(9)陳靜《書儀的名與實》,《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1期。杜海《書儀源流述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文獻記載中只存目録的唐代書儀在敦煌遺書中有大量發現,根據使用對象,這部分書儀分爲朋友書儀、吉凶書儀與箋狀表啓三類。(10)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二)》,《周一良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44—468。記載婚嫁儀節的吉凶書儀源於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家禮、家訓。唐代吉凶書儀在繼承東晉南朝書儀基本特徵的基礎上,(11)史睿《敦煌吉凶書儀與東晉南朝禮俗》,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95—421。關於東晉書儀與唐代書儀的關係,參看祁小春《唐代書儀與王羲之尺牘之關係》,《中國書法》2015年第11期。與士族家禮、國家禮制以及民間習俗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與實踐品格的書儀。(12)姜伯勤《唐禮與敦煌發現的書儀——〈大唐開元禮〉與開元時期的書儀》,《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425—441。其中的婚禮書儀成爲研究唐代婚姻禮俗的重要文獻。
按照編修過程與使用範圍,敦煌吉凶書儀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中央政府組織編修並且通行全國的書儀,有盛唐時期杜友晉編修P.3442《吉凶書儀》及其簡約本P.3849《新定書儀鏡》,還有中唐時期鄭餘慶編修S.6537v《大唐新定吉凶書儀》。一類是在通行書儀基礎上增删修訂的地方性書儀,如S.1725《大唐吉凶書儀》,據趙和平考證,認爲“不晚於開元時代”。(13)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頁420—422。還有P.3284、P.2646、P.3886 大中年間張敖修訂的《新集吉凶書儀》。除了書信範式外,具有儀注性質的書儀有S.1725初唐《書儀》與張敖《書儀》。對於婚禮儀式書寫,應從書儀規範與禮儀規範兩方面進行分析。
無論是古禮經還是國家禮典,都没有提及婚禮儀式中的書函,婚禮書函的出現應該與吉凶書儀出現同步。敦煌寫本中時間最早的唐代婚禮書儀是P.2619杜友晉《新定書儀鏡》殘卷。此寫本收録的六首婚禮書儀,分别是《通婚函書》與《答函書》、男女雙方的《祭祖文》與男女雙方的相慰問語。這六首書儀貫穿於婚禮締結的始終,包含通婚、成婚與完婚三個主要程序。作爲婚禮的固定設置,六首書儀也見於張敖《書儀》,其中男女雙方《通婚書》及《嫁娶祭文》四首在張敖《新集諸親九族尊卑書儀》也有收録。張敖《書儀》的藍本是鄭餘慶《書儀》,鄭氏《書儀》則以杜友晉《書儀》爲法。鄭氏《書儀》中的婚禮書儀没有存世,通過比較張敖《書儀》中的六首書函與杜友晉《新定書儀鏡》可以發現,兩者書信内容體式與文字表達基本一致。如杜友晉《新定書儀鏡》之《通婚函書》曰:
(往來皆須以函封,無函者可用紙。)名頓首,闊展既久,(雖近未久,答書准此。)傾展良深。孟春猶寒,體履如何?願館舍清休。名第某息名(弟云厶弟兄,隨時稱之。)未有伉儷,(亦云婚媾)承第若干女,(厶弟兄之子任言)令淑有聞,願托(亦云取希,敢結)高媛,謹因某官姓名,敢以禮請。名諸弊少理,言展未由,惟增翹軫,願敬德遣,白書不具。姓名頓首。(14)本文涉及到的敦煌書儀以及婚禮詩文没有特殊標注外,均引自譚蟬雪《敦煌婚姻文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同時參校向達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頁27)
《新集諸親九族尊卑書儀》之《通婚書》在《新集吉凶書儀》基礎上進一步簡化:
厶頓首頓首!闕敍既久,傾矚良深。時候伏惟,體履如何?館[舍]清休。即此厶蒙恩,厶第幾男,未有伉灑(儷),伏承第幾娘子,令淑有聞,願托高援。謹因媒人厶乙,敢以禮請。厶限以官守,展敍未由,伏增翹咏,謹遣白不宣謹狀。厶月厶日厶郡厶乙狀厶官位閣下。(頁29)
杜氏《書儀》延承了魏晉尤其是南朝以來的書寫傳統,因此,就書函構成的婚禮程式看,自東晉南朝到唐前期再到唐後期,儘管社會性質由貴族社會轉變爲官僚社會,書儀製作者的身分也由世家大族轉變爲地方判官書記。(15)吴麗娱《敦煌書儀與禮法》第二章《書儀的類型遞變及製作傳播》,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55—82。但是,體現貴族好尚與家法家風的婚禮書函格式没有發生大的變化,建立在經學基礎上的儒家禮度始終爲吉凶書儀所保持與遵守。例如對於女方的描述“令淑有聞”,符合“婦順”的禮義要求。《祭祖文》通過告慰祖靈顯示婚禮的莊重與神聖。雙方家長相慰問語中,“不勝感愴”“深助感慰”的話語秉持了“婚禮不賀”的古義。
由此可見,以文辭表達爲中心的書函構成唐代婚禮儀式中最能體現儒家禮義的部分,也是東晉南朝至唐代婚儀設置中最穩定的内容。但是,婚儀儀節繁瑣複雜,内容絶非六首書儀所能涵蓋,其中具體的儀節與程式需要通過書信之外的儀注來分析,S.1725初唐《書儀》與張敖《書儀》提供了這方面的材料。
S.1725初唐《書儀》以書信交换爲線索,可以分爲定婚、成婚兩個階段,相當於六禮中的納徵與親迎。納徵的時間是上午,男方給女方送去彩禮和“納徵版”,表示婚姻成立。然後是親迎,女婿前往女方家,附帶財禮與“親迎版”。女方在家中庭院與中堂舉行儀式後,新婦來到男方家,在男方庭院舉行“同牢合巹”禮,然後引入青廬。第二天,在中堂與庭院舉行成婦禮,拜見姑舅,婚禮結束。親迎成婚是婚禮的重心,成婚儀式在男方家完成,但文中又提到:“近代之人,多不親迎如室,即是遂就婦家成禮。”(頁7)可見,當時還有女方家中成禮的婚俗。與官方禮典中的婚禮相比,S.1725初唐《書儀》在遵循古禮基本禮義的基礎上,簡化了禮制性程式,增加了世俗化内容。這些變化在張敖《書儀》中有進一步的體現。
張敖《書儀》是在鄭餘慶《書儀》基礎上“采其的要,編其吉凶”而來,其主導思想源自古經。(16)陳韻《敦煌寫本書儀之昏儀昏義研究(一): 〈新集吉凶書儀〉昏儀昏義與〈儀禮·士昏禮〉昏儀昏義之比較》,《中正中文學術年刊》1998年第2期。“先王制禮,後代行之。是以男女有婚姻之禮,以成夫婦之道,俾無紊於人倫。”(頁16)儀式氛圍延續了古禮秉持的肅穆與莊重的要求,强調“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動樂,思嗣親也。”(頁16)張敖《書儀》以書信往來的方式進行議婚、訂婚,“親迎”成婚是婚禮的高潮,與初唐《書儀》比較,出現了幾點值得注意的變化。
首先,符合禮制的成婚儀式應在夫家舉行,但是初唐《書儀》提及有“婦家成禮”的習俗。張敖《書儀》中,儀式跨度從親迎到同牢合巹,没有拜姑舅禮,儀式舉行場所是夫家還是婦家没有特别説明,成婚地點表述比較含糊。譚蟬雪認爲張敖《書儀》中的成婚禮是在女家。(頁169)吴麗娱認爲《書儀》有意識地模糊成婚地點,旨在使得儀式適合男女兩家。(17)吴麗娱《唐代婚儀的再檢討》,《燕京學報》2003年新15期。不管是成禮在女家還是男家,兩種書儀都可以證實,唐代時期存在女家成婚的禮俗,而且到中後時期有普遍化傾向。
其次,《新集》中出現了娱樂性節目。如男方到女方迎親時,要“向女家戲舞”,這種戲舞在古禮中應是一種宗教儀式,後來演變爲娱樂性習俗。敦煌壁畫婚嫁圖中多處出現類似的樂舞,如盛唐時期445窟北壁,畫面中央有一紅衣小兒在舞蹈,旁邊還有六人組成的樂隊伴奏。這些變化説明,主於敬畏與思親的婚禮開始向歡快與熱鬧的方向發展。
再次,除了體現古禮的傳統儀式,如奠雁、同牢合巹外,兩種書儀都提到了禮經與禮典中没有的儀式,如入青廬、撒帳、去花、去扇等。這些世俗化的喜慶儀節取代了禮經中的祭祀儀式,成爲婚儀的主要構成部分,並且上流社會同樣流行。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五《花燭》提及“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婿、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又有卜地、安帳並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18)趙貞信《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43—44。
最後,在書信之外,儀式書寫還包含其他文體,如張敖《書儀》提到“如夜深即作催妝詩”。行同牢合巹禮後,儐相“咏去花詩、去扇詩三五首”。另外,還有配合儀式進行的咒願文,如張敖《書儀》中的撒帳儀式上提到一段咒願:“今夜吉辰,厶氏女與厶氏兒結親,伏願成納之後,千秋萬歲,保守吉昌。五男二女,奴婢成行。男願總爲卿相,女即盡聘公王。從兹咒願之後,夫妻壽命延長。”下注:“此略言其意,但臨時雕飾,裁而行之。”(頁15)與口誦詩歌一樣,咒願文也是用於婚禮的應用性文體。這些婚嫁詩文一般都是文人創作,具有鮮明的文學色彩,其表達的基本思想也與經義不同。
儘管儒家禮經與官方禮典中的婚禮儀式的倫理教化功能得到强調,但是,婚姻儀式的制定與展開並没有完全否定或忽視個體情欲的存在。(19)關於傳統婚禮中儒家思想與性情的關係,參看顧濤《論古典婚禮根植於人之情性》,《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敦煌書儀中的婚儀設置延續了儒家禮經、官方禮典的價值設定與禮義表達,體現出儒家化的主導思想。同時,又包含了一些不見禮經、禮典的儀節設置與表達方式,這些内容多來自民間習俗,體現了婚儀在實踐層面上的品格。因爲吉凶書儀的重心是書信,因此對於婚禮儀式書寫並不周全。張敖《書儀》最後指出,“令略具之,亦未周細,但君子祥(詳)而行之,則無誤耳。”(頁16)進一步探究唐代婚禮的多種面向,還要借助其他書寫文本來分析。
二 富貴與色相: 婚禮中的口誦詩文
唐代婚禮的進行過程中,存在多種配合儀式進行的口誦詩文辭賦。這種應用性的文學作品在敦煌書儀、唐人文集與小説筆記中都有發現。但是,存世文獻中的婚儀文學多是片段性的。敦煌遺書保存的《下女夫詞》則是一組完整的婚禮詩詞,現已發現十七件,其形態功用從作爲私人文書到童蒙習字教材都有體現。(20)宋雪春《敦煌本〈下女夫詞〉的寫本考察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學輯刊》2017年第4期。對於這則文獻的性質,一般認爲是用於配合婚禮儀式舉行的口誦詩詞。同時,作爲流行於敦煌地區的文學作品,收録向達等人編撰的《敦煌變文集》中。(21)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273—284。還有研究者認爲這是一件敦煌古劇的腳本,(22)關於下女夫詞的研究,參看宋春雪《敦煌本〈下女夫詞〉研究綜述》,《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2—45。屬於説唱文學的範疇。要認定文本的性質與功能,要把文本置還到婚禮現場與文學書寫傳統之中進行解讀。
《下女夫詞》包含男女對答韻文與五言、七言詩歌兩部分,時間貫穿整個“親迎”環節,從新郎上門開始,到成夫妻禮結束。從婚禮程式上看,各部分内容時間前後相接,關係緊密。譚蟬雪根據抄寫形態、内容與體裁的差異,指出《下女夫詞》只是對答部分,第二部分是《論女婿》,第三部分則是《婚嫁詩》(23)譚蟬雪《敦煌婚姻文化》,頁42。伏俊璉認可這一看法,參看伏俊璉《敦煌文學總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461—467。。我們認爲《下女夫詞》三部分作爲一個整體没有問題,但是爲了適應儀式需要,整體上分爲三部分來表達也有道理。因此,爲了方便討論,我們采用三分法,按照儀式進程對其内容進行分析。
第一部分是男女對答的四言韻文,儀式空間是門内與門外,男女主人公的關係設定爲互不相識。爲了得到女方的接納,新郎被塑造成一位出身高門、富有才學的地方長守。如:“通問刺史,是何抵當……本是長安君子,進士出身。選得刺史,故至高門。……三史明閑,九經爲業。……本是三州遊弈,八水英賢。馬上刺史,望在秦川。……並是國中窈窕,明解書章。……刺史乘金鐙,手執白玉鞭。”(頁35)這些身分都是程式化的表述,其官籍、郡望以及任職地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來隨意設定。如在寫卷Дх.11049V+Дх.12834R中,“馬上刺史,本是某鄉”中的“某鄉”其他寫本中均作“敦煌”。(24)宋雪春《〈俄藏敦煌文獻〉中四件〈下女夫詞〉殘片的綴合》,《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因爲寫本發現於莫高窟,儀式的舉行地是敦煌地區,所以任職地爲敦煌周邊最能體現職權的有效性;又因爲長安是政治文化中心,所以籍望選擇長安又能顯示出身的優越感。
第二部分《論女婿》,男主人公被允許進宅,對話體改爲五言詩歌。詩歌吟誦者應該是新郎或者儐相,描寫重點是宅第。新郎延續了對答部分的身分,從大門、中門、庭院到中堂的這一區域,每到一處都要吟誦一首詩歌。這一場域是宅第的公共禮儀空間,也是禮書規定的儀式空間,但是,揖讓周旋的禮儀展演並没有出現,詩歌的書寫重點是豪華的宅第空間,如《至中門咏》有“困金作門扇,磨玉作門環”句。《至堂基詩》有“琉璃爲四壁,磨玉作基階”句。《至堂門咏》有“屏風十二扇,錦被畫文章”句。與新郎的高貴身分一樣,宅第的描寫也是虚擬的,以此顯示主人的社會地位。這一部分相當於過渡儀式,通過咏詩,新郎升堂,爲“入室”行禮做好身分準備。
第三部分儀式空間由廳堂轉入婚房,與第一部分誇飾新郎的社會身分不同,這部分詩歌的描寫重點是新娘的美貌與身體。詩歌美化新娘的修辭手法有兩種,一是用花來比擬,《催妝二首》之一“自有夭桃花菡□(或釋作顔、面、萏),不須脂粉污容顔”句。《去花詩》有“一花卻去一花新,前花是假後花真”句。《去扇詩》有“青春今夜正方新,鴻(葉)開時一朵花”句。一是用神仙來比擬,如《去花一首》詩有“神仙本自好容華,多事旁人更插花”句。比擬的神女出自神話傳説中的婚戀題材,如《催妝二首》之一有“今霄(宵)織女降人間,對鏡匀妝計已閑”句,《咏繫去離心人去情詩》之一也有“天交織女渡河津,來向人間只爲人”句,把新娘比作私自來到人間與凡男結爲夫婦的織女。同題詩之二有“更轉只愁奔兔月,情來不要畫蛾眉”句,又暗用了嫦娥奔月的傳説。《合髮詩》有“本是楚王宫,今夜得相逢”句,用的是巫山神女與楚襄王遇合的故事。
通過對三部分内容的分析可見,男女主人公的身分描寫都是虚擬的,但是描寫的重心不同,對於男主人公强調其出身地位與文采學識,對於新娘的描寫則是强調其如花美貌與神仙資質。這種身分書寫與禮經、禮典中的婚義表達不同,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根據經書中的婚儀表達,婚姻目的之一是“合兩家之好”。這種表述既没有提及締結婚姻的條件,也没有説明兩家之“好”指代的内容。然而,在傳統等級社會,婚姻締結有明確的階層差異,門當户對是婚配的首要條件。漢魏以來,隨着門閥士族社會的形成,婚姻與門第結合起來,婚媾成爲門閥士族壟斷和獲取社會資源進而結成聯盟的手段。婚姻重門第的觀念一直延續到唐代,隨着貴族社會的衰落與官僚社會的興起,門第婚姻又與科舉取士制度聯繫起來,出身名門、富有才華、仕途遠大的新興文士階層成爲士庶嫁女的首選。同樣,門第清華、權高位重的貴族顯宦之女也是年輕士子爭相攀附的對象。對於婚嫁者來説,無論是個人還是家庭,理想的婚配對象意味着上流社會的生活品質,《下女夫詞》虚擬新郎的出身與才學就是這種社會心理的體現。
把婚姻與現實身分的改變與生活品質的提升聯繫起來,凸顯了婚姻的功利化功能,這一點似乎容易理解,研究者也有論及。那麽,對於新娘美貌尤其是比擬爲神仙的書寫目的是什麽呢?
儒家婚姻思想把子嗣的繁衍、倫常的維係與情欲的滿足對立起來,禮經婚義重婦德不重婦貌。然而,《婚嫁詩》中,對於新婦的女德並不在意,書寫重點是新娘的容貌。當婚禮進行到洞房階段,隨着作爲社會身分的最後一種標識——服飾的脱卸,男女主人公只有體現生理特徵的身體。這時候,渲染新娘豔麗外貌明顯具有性暗示與性挑逗的成分,這種情欲化的男女關係又通過神女的隱喻進一步表達出來。在進入文學書寫之前,織女、嫦娥、巫山神女都是遠古時期神話傳説中的人物。漢魏以來,隨着民間信仰的發展,神話中的女神經過祠神化轉變,出現了神仙與凡間男子發生婚配的民間傳説。李豐楙研究指出,這種人神婚是另一種形式的冥婚習俗,原爲遠古時代已經存在的巫俗信仰。(25)李豐楙《魏晉神女神話與道教神女降真神話》,載《仙境與遊歷: 神仙世界的想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55。人神接遇的民間信仰經過知識階層的改造,産生兩種不同的人神婚戀敍事。(26)關於兩種不同敍事中的女神形象,參看Zhang Zhenjun, Two Modes of Goddess Depictio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2017, 3(1), P.117-134.在道教文本中,人神婚配是夫妻合氣進而長生久視的修煉方式,(27)柏夷《天師道婚姻儀式“合氣”儀式在上清、靈寶學派的演變》,《道教文化研究》第16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頁241—249。以杜蘭香嫁張碩、成公智瓊嫁玄超改編的故事系列爲代表。在文人創作中,悟道成仙的神仙追求轉變爲表達男女情欲的文學題材,如題名宋玉《高唐賦》與《神女賦》、曹植《洛神賦》等表現人神接遇的辭賦,以及記敍人神遇合的志怪小説。(28)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神婚戀小説的表現形式,參看楊爲剛《經驗與想象: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祠神信仰與人神婚戀小説》,《國學研究》四十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23—344。把《下女夫詞》三部分連綴起來,構成了一則完整的婚戀敍事。一位身分高貴、才華横溢的年輕士子偶遇一位貌若神仙的女子,兩人情投意合,由此發生婚配或者性愛關係。這一情節完全符合魏晉以來形成的人神婚戀敍事模式,尤其在唐代小説中多見。周一良較早注意到敦煌書儀與《遊仙窟》等婚戀小説都具有“就婦家成禮”(頁7)的特徵。(29)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俗》,《文物》1985年第7期。程毅中認爲張鷟《遊仙窟》是根據《下女夫詞》改編而成。(30)程毅中《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文學遺産增刊》1962年第10輯。張鴻勳又進一步指出《遊仙窟》就是《下女夫詞》的禮俗化。(31)張鴻勳《〈遊仙窟〉與敦煌民間文學》,《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429—459。《遊仙窟》的創作是否受到《下女夫詞》影響暫且不論。從情節設置看,兩者的相似緣於兩則敍事都屬於魏晉以來文人化的人神婚敍事,建立在性本能基礎上的情欲表達是這一敍事傳統的重要特徵。
在諸多《下女夫詞》寫本中,通過詩歌表達的男女情欲比較含蓄。榮新江在英藏敦煌文書中發現了編號爲S.9501+S.9502v+S.11419+S.13002 的《下女夫詞》殘卷。(32)榮新江《英倫所見三種敦煌俗文學跋》,《九州學刊》1993年第4期。這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寫本,綴拼後,内容首尾不存,不見男女對答部分,所存文字都是五、七言詩。與其他《下女夫詞》比較,此寫本不但詩歌順序不同,還多出一部分詩歌。其中一部分詩歌内容大膽直接,如一失題詩曰:“昨夜忽驚眠,論情是惡憐,被人抛郍(那)畔,郶(部)又落誰邊。隔是無藏地,從他笑我天。惟將兩個手,遮後復遮前。”這是新娘脱光後的“戲婦”情節。還有通過人神遇合來直接暗示床笫之事,如“□答詩”云:“脱衣神女立陽臺,夜亡更蘭(闌)玉漏催。欲作綾羅步千造,玉體從君任看來。”(33)張鴻勳《新獲英藏〈下女夫詞〉校釋》,《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407—428。這些描寫與敦煌曲子詞中文人狎妓的歌辭接近。具有猥褻意味的詩歌爲什麽能夠在以儒家思想爲主導的婚禮現場進行吟誦?這需要從儀式設置與表達需要來進一步分析。
按照儀式人類學的觀點,“在許多儀式中,特别是那些重大的與複雜的大儀式,往往一個‘主幹儀式’係由多個不同的‘分支儀式’共同構成,從而使‘主幹儀式’事實上成爲一個由某一個確定的主題所主導下的儀式羣。特納稱之爲生長茂密的‘儀式樹’(mudyi tree)”。(34)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頁209。婚禮儀式並不是一套單一的表意體系,而是由多種儀式構成的儀式組合。把《下女夫詞》三部分内容置於敦煌書儀所構建的婚禮儀式中,可以清楚顯示婚禮儀式通過多種“次要儀式”來表達婚義的儀式設置與儀式書寫。首先,以書函爲中心的婚儀文書貫穿婚禮始終,延承了禮經與禮典的婚義設定,屬於禮制層面的婚儀表達。《下女夫詞》三部分内容相當於親迎環節,其前半部分體現了婚姻成立的社會因素與物質條件,體現了婚姻的功利化傾向。後半部分表達了建立在原始本能基礎上的情欲需求,體現了婚姻的生物性功能。因此,敦煌寫本中的婚禮儀式至少表達了婚姻的三種功能: 傳宗接代、追求富貴與滿足情欲,與之對應,形成了禮制性、功利性與情欲化三類書寫表達方式。這三種婚儀表達方式相輔相成,構成了文字層面上的婚禮儀式的敍事功能。婚禮儀式設置與儀式書寫的對應關係可以通過咒願文等其他口誦文學進一步佐證。
咒願文的體式類似俗賦,這種口誦文體在初唐《書儀》中已經出現。敦煌寫卷中發現二十餘首咒願文,從咒願對象上,分爲針對新夫、新婦或者夫婦二人三種。與婚嫁詩詞一樣,咒願文也是配合儀式進行吟誦的文體,但不同於《下女夫詞》通過一組或者幾組詩詞來表達。咒願文是一首獨立辭賦,限於親迎禮中的某個環節吟誦,如上引S.1725初唐《書儀》中的咒願文,在撒帳儀式吟誦,其他還有用於新人入門、拜堂或舉行酒宴等。對於咒願文的内容,研究者更關注其功利化的表達傾向。(35)關於咒願文的研究,參看譚蟬雪《敦煌婚姻文化》,頁162—168;武漢强《唐宋民間婚禮祝詞敦煌本“咒願文”研究》,《蘭州交通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實際上,其内容表達與儀式進程有關,因此與《下女夫詞》一樣,具有多面向的書寫傾向。如 P.3608《咒願文》:
冬穴夏巢之時,不分禮樂;繩文鳥迹之後,漸制婚姻。或因地封官,或因官得姓,爰及姬漢,聲教鬱興,女辭家以適人,臣蒙恩而事主。隴西令族,吴郡高門,鳳凰和鳴,宫商叶律。男僅弱冠,女才成笄。綢繆束芻,三星在户,窈窕淑女,百兩迓之。蕭史降於鳳臺,姮[娥]下於兔月。邯鄲緩步,官立錦箜,桃妁仙容,隔於羅扇。笙客遍□(座),行觴數巡,二儀悦懌,九族歡忻。花黄片落,濡襪生塵。逶迤南國,婀娜東鄰,飛願雙翥,處同一身。紆青拖紫,曳組腰銀。生男尚主,育女榮嬪。富貴百代,榮華萬春。功業繼世,刀筆絶倫。邦國之寶,室家之珍。皇華奉使,同受諮詢。享□將久,日暮君□。獻酬□祝,以酢主人。伉儷並退,門外送賓。(53頁)
這是酒宴即將結束之際對於夫婦兩人的祝福,此時,婚禮基本結束,夫妻關係得到確認,因此願文内容符合儀式進展的需要。儘管文章開頭提及婚禮的禮制淵源,但這不是表達的重點,文章的主題部分體現爲對新人的身分誇讚與世俗祝願。例如,對於婚配雙方的身分,虚飾其高貴出身,如“隴西令族、吴郡高門”句,這也是《下女夫詞》前半部分的表達手法。對於女主人公,則是誇飾其貌比天仙的外貌,“桃妁仙容,隔於羅扇。”這又是《婚嫁詩》的修辭策略。同樣,對於新郎與新娘的結合;一方面表達富貴生活的現實願望:“紆青拖紫,曳組腰銀”、“富貴百代,榮華萬春”,體現婚姻的功利化功能;另一方面,又把兩人的結合比擬爲人神遇合的神仙伴侣,如“蕭史降於鳳臺,姮[娥]下於兔月”,表達不受禮俗局限的情欲滿足。
對於不同的儀式關節,不同的祝願對象,咒願文都有固定的文學修辭與内容表達與之對應。受到文體與程序的限制,《下女夫詞》中屬於不同儀式、多組詩歌表達的内容,在這則咒願文中被壓縮爲一篇,出現了體現婚姻不同功能的表達集中在一篇文章中的現象。只有瞭解婚禮的儀式設置及其對應的文體書寫,才能理解這類文體的表達方式與儀式功能之間的關係。如P.2633《崔氏夫人訓女文》是女兒出嫁之前母親的告誡,教導女兒如何處理家庭關係。母親的話語體現了“婦順”的傳統婚姻觀,因此既不會出現富貴的主題,也没有表現情欲的色相描寫。
敦煌婚禮寫本中,詩詞文賦的運用使得婚禮儀式具備了文學化特徵,適應了婚儀儀式世俗化、情欲化的表達需求。這種文學性的表達傳統如何形成,是敦煌地區特有,還是源於唐代婚儀書寫的普遍模式?這些問題的解答需要從唐代婚禮儀式與文學書寫的大背景中探討。
三 宫廷與市井: 文人創作中的婚禮書寫
存世文獻保存的婚嫁詩文中,數量相當較多的是公主婚嫁詩文。在皇帝時代,公主是一個特殊的羣體,一方面,她們擁有高貴的身分與無上的權勢。另一方面,與普通女子一樣,她們没有婚姻決定權,而且她們的婚姻更容易被充當政治砝碼,用來平衡皇室與權貴之間的權利分配。作爲皇帝之女,公主出嫁的婚禮要比士庶女子婚禮更爲隆重體面。(36)關於唐代公主婚禮儀式,參看郭海文《唐代公主的婚姻禮儀》,《社會科學評論》2009年第3期。但婚嫁屬於家庭事務,公主嫁爲人婦,仍然要遵守以家庭關係爲核心的婚儀程式。
在國家禮典與官方公文中,公主婚嫁有固定的儀式設置與書寫範式。《開元禮》有“公主降嫁”禮,與士宦婚禮比較,公主降嫁禮增加“册公主”與“公主受册”儀式。儀式舉行場所是太極殿與長樂門,這是顯示皇帝嫁女的儀式空間,也是體現公主身分的儀節。除此之外,儀式程式沿循禮經的禮義表達,把公主納入儒家化的婚姻程式,强調其作爲人婦的身分。如新郎進宫親迎前,父親訓導兒子的言辭,“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37)《大唐開元禮》卷一一六《公主降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551。與士庶婚嫁表述相同。
與册公主儀式相配合,册公主降嫁文則是昭示天下的“王言”。從保存下來的册公主文來看,典雅莊重的文風是一種“被需要的文體”。(38)關於古代“王言”的文體特徵,參看周劍之《論宋代駢體王言的政治功能與文學選擇》,《文學評論》2013年第3期。這種程式化的册文在宣示皇權神聖的同時,又標榜家國一體的禮治思想。如《册平昌公主出降文》:
維天寶五載,歲次庚戌,十二月戊申朔,九日丙辰。皇帝若曰: 於戲!婚姻之序,人倫爲大。家道以正,王化乃貞。諮爾平昌公主,性質閑婉,襟靈敏悟,柔順外徹,和惠内融。公宫道訓,備聞勤儉之則;女史箴規,克慎言容之範。頗聞圖象,既習紘綖。方修中饋之儀,式從下嫁之禮。罽車遵路,巹庋在庭。歸爾好仇,申兹寵典。今遣使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右相吏部尚書晉國公李林甫、副使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李暐,持節禮册往,欽哉。爾其虔修令德,祗服厥訓。循於法度,宜爾室家,可不慎歟!(39)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03。
這種册文一般包含兩方面内容,一是强調女子品德對於婚姻家庭、禮教王化的重要性。“三綱以正,王化是先。二姓之合,人倫式敍。下嫁之禮,厥惟舊章。”(40)宋敏求《唐大詔令集》,頁202。(《册樂成公主出降文》)二是公主作爲人婦的品德準備。“孝敬閑婉,朗然夙成。法度言容,資於内訓。詞禮是則,令淑增華。”(41)宋敏求《唐大詔令集》,頁203。(《册晉寧公主出降文》)與敦煌婚嫁詩塑造新娘的方法一樣,册文中的公主形象也是虚擬的,典雅的語言對應禮典中的儀式,製作出符合儒家婚姻理想的“標準”公主形象。
現實生活中,唐代公主不但很少具備官方標榜的女德,而且禮典規定的婚禮儀式也很難嚴格執行,可以以太平公主、安樂公主的婚禮與婚禮詩歌爲代表進行分析。太平公主嫁薛紹的婚禮規模盛大。“假萬年縣爲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毁垣以入。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樾爲枯。”(42)《新唐書》卷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650。與盛大婚禮相配合,唐高宗作《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詩》,其中有“華冠列綺筵,蘭醑申芳宴。環階鳳樂陳,玳席珍羞薦。蝶舞袖香新,歌分落素塵。歡凝歡懿戚,慶葉慶初姻。暑闌炎氣息,涼早吹疏頻。方期六合泰,共賞萬年春”句。(43)《全唐詩》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21。富麗典雅的修辭延續了南朝以來宫廷宴飲的儀式書寫程式,(44)關於南朝宴賞文學的書寫程式,參見林曉光《王融與永明時代》第六章《宫廷禮儀中的王融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48—272。詩中没有禮經婚儀所表現出來的教化意味,也没有肅穆與莊嚴的氣氛,更像是一場以皇帝爲中心、羣臣參與的節日盛宴。劉禕之、任知古、元萬頃、郭正一等有奉和詩存世,表現出相同的風格特徵。如任知古《奉和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詩》曰:“帝子升青陛,王姬降紫宸。星光移雜佩,月彩薦重輪。龍旌翻地杪,鳳管揚天濱。槐陰浮淺瀨,葆吹翼輕塵。”(45)《全唐詩》卷四四,頁543。這種拘謹空洞的詩風在安樂公主的婚禮詩中有所改變。
安樂公主有兩次婚禮,第一次是以郡主身分嫁武三思子武崇訓,時間是長安三年,地點是洛陽。第二次以公主身分改嫁武延秀,地點是長安。兩次婚禮中,第一次有詩文存世。《舊唐書》卷一八三《武崇訓傳》記:
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時,封爲高陽郡王。長安中,尚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朝,欲寵其禮。中宗爲太子在東宫,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内行親迎禮,歸於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彦伯、張説、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宗楚客兄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有新句。(46)《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4736。
這次婚禮轟動京城,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其一,郡主的婚禮具備甚至超過公主出嫁的排場;其二,當時政壇與文壇的核心人物不但參加婚禮,而且都創作了詩歌。張説、宋之問的《花燭行》保存下來。兩首詩歌描寫的情景都屬於親迎禮,儘管有繁簡的差異,但内容與修辭相近。張説詩長達42句,288字,宋之問詩作文辭相對簡省,録文如下:
帝城九門乘夜開,仙車百兩自天來。列火東歸暗行月,浮橋西渡響奔雷。龍樓錦障連連出,遥望梁臺如晝日。梁臺花燭見天人,平陽賓從綺羅春。共迎織女歸雲幄,俱送常娥下月輪。常娥月中君未見,紅粉盈盈隔團扇。玉樽交引合歡杯,珠履共蹋鴛鴦薦。漏盡更深斗欲斜,可憐金翠滿庭花。庭花灼灼歌穠李,此夕天孫嫁王子。結褵初出望園中,和鳴已入秦簫裏。同心合帶兩相依,明日雙朝入紫微。共待洛城分曙色,更看天下鳳凰飛。(47)陶敏、易淑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416—419。
根據儀式進程,詩歌可以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的儀式空間是從皇宫到婚宅,這段迎親路程是洛陽城最具禮制意義的空間。在這個公開的禮儀空間中,公主婚禮成爲全民參與的公共儀式。浩浩蕩蕩的儀仗僕從,眼花繚亂的娱樂活動,萬人空巷的觀禮場面,這些描寫既是儀式現場的真實寫照,也是作者迎合婚主炫耀權勢心理的文學修飾,婚姻的功利化與政治性特徵得到充分顯示。後半部分,儀式空間由廳堂轉向婚房。芙蓉帳、鴛鴦薦等物象既能顯示主人身分的高貴,又暗示了夫妻生活的美滿。“紅粉盈盈隔團扇”、“娥娥紅粉扇中開”描寫新娘美貌。“共迎織女歸春幄,俱送常娥下月輪”句用織女與嫦娥暗喻新娘下嫁,“和鳴已入秦簫裏”句又用了公主弄玉與簫史成仙的典故。從修辭風格看,這部分内容儘管有虚飾的成分,但符合公主作爲“天子之女”的特殊身分。從世俗富貴的表達到神仙生活的追求,兩部分内容合起來,情節與《下女夫詞》三部分内容相同,屬於魏晉以來的人神婚戀文學傳統。
作爲皇帝之女,公主有足夠支配的權力與財富,同時,奢華的生活又符合世俗世界對於神仙世界的想象。榮華富貴與神仙追求最能表現上流社會的生活品質,與這兩種生活品質相對應的文學資源是南朝以來的宫廷文學傳統。(48)商偉《宫廷文學與市井文學——從一個側面看南朝詩歌的發展趨勢》,《文史哲》1986年第2期。可以通過《初學記》進行分析。
《初學記》是玄宗爲皇子創作詩文時檢查事類而命人編撰的類書。此書卷一四《禮部·婚姻第七》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敍事”與“事對”屬於婚儀婚義的内容,選取的話語全部出自儒家經典,體現了正統的儒家立場。第二部分“賦”“詩”屬於文學書寫部分,選取了自東漢以來與婚姻有關的文學作品。顯然,引用的文學作品並不對應儒家婚姻觀念,更多的是世俗化、情欲化的表達。比如收録的陳朝詩人周弘正《看新婦詩》云:“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婿顔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卻輕紈扇,傾城判不賒。”(49)逯欽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462。此詩是吸收南朝民間情歌基礎上創作的宫體詩,重情欲的傾向不符合儒家化的婚義表達。收録的唐代文學作品中,除了唐高宗與羣臣唱和的婚禮詩外,還有五首市井婚禮詩: 楊師道《初宵看婚詩》、褚亮《咏花燭詩》、陳子良《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詩》、鄭翼《看新婦詩》、李百藥《戲贈潘徐城門迎兩新婦詩》。相對於宫廷婚禮詩的富麗堆砌,這些文人創作的詩歌更顯示出世俗化的書寫傾向。如楊師道《初宵看婚》:“洛城花燭動,戚里畫新蛾。隱扇羞應慣,含情愁已多。輕啼濕紅粉,微睇轉横波。更笑巫山曲,空傳暮雨過。”(50)《全唐詩》卷三四,頁459。顯然,這些缺少道德與説教主題的婚禮詩文一方面延續了魏晉以來宫廷文學創作傳統,一方面也吸取了市井文學世俗化的特徵,由此構成了張説、宋之問等人製作安樂公主婚禮詩歌的範式。顯然,世俗化的情欲表達違背了儒家婚禮的基本禮義,由此招致宋代史官的指責也可以理解。《新唐書》卷二六《武崇訓傳》:“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宫,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51)《新唐書》,頁5840。
婚禮詩歌是配合婚禮儀式而作,宫廷婚禮詩歌表現出世俗化傾向與婚禮儀式的世俗化有直接關係。《資治通鑑》卷二九記景龍二年(709),唐中宗在宫中主持婚禮,把皇后乳母嫁給御史大夫竇從一,儀式臨時而設:“俄而内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卻扇詩》數首。扇卻,去花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52)《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6630—6631。這場具有遊戲色彩的婚禮中,没有官方禮制規定的儀節,都是世俗化的儀式。可見,中宗時期的宫廷婚禮已經表現出世俗化的傾向,延續到德宗建中年間,唐德宗不得不要求禮儀官奏改公主、郡主的出降婚儀,“將以化行天下,用正國風。”(53)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頁1529—1530。禮儀使顔真卿提出恢復公主拜姑舅禮,停觀花燭、障車、下婿、卻扇詩等世俗禮,禁止聲樂娱樂活動等一系列措施。從奏請的舉措看,其改革對象主要針對婚禮中的世俗化内容。但是,行政干預並不能改變婚儀世俗化的趨勢,越到後期,宫廷與民間的婚禮與婚禮書寫越表現出趨同的特徵,盧綸的詩作可以説明。
盧綸有《王評事駙馬花燭詩》四首,記貞元二年德宗女義陽公主嫁司徒王武俊之子王士平所作,詩曰:
萬條銀燭引天人,十月長安半夜春。步障三千隘將斷,幾多珠翠落香塵。
一人女婿萬人憐,一夜稠疏抵百年。爲報司徒好將息,明珠解轉又能圓。
人主人臣是親家,千秋萬歲保榮華。幾時曾向高天上,得見今宵月裏花。
比翼和鳴雙鳳皇,欲棲金帳滿城香。平明卻入甘泉裏,日氣曈曨五色光。(54)劉初棠《盧綸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210—214。
同樣涉及到世俗化與情欲化的内容,詩歌没有唐前期宫廷婚禮詩歌那麽富麗堂皇與鋪排堆砌,表現出篇什短小、内容淺俗的特點。然而,就是因爲淺近通俗的特點,這組詩遭到王漁洋與四庫館臣的嘲笑與指斥。作爲一種具有禮儀性質的詩作,婚禮詩歌表現出來的特點與作者身分以及詩歌用途都有關係。盧綸有長時間的幕府生活經歷,晚年進入宫廷,此時的宫廷詩人是以權德輿爲代表的一批有幕府經歷的年輕詩人構成。盧綸作爲大曆元老,頗受詩人推重。在令狐楚爲憲宗編撰的《御覽詩》中,盧綸選了三十二首,僅次於李益三十六首。其中就有這組婚嫁詩的第三首。除此之外,具有儀式性質的詩歌還選了《皇帝感詞》四首、《天長地久詞》二首、《宫中樂》一首。可見,盧綸這種淺俗而實用的詩歌適應了宫廷需要,以至於唐憲宗與唐文宗都曾遣人訪求過盧綸的詩文。(55)蔣寅《論盧綸詩對中唐詩壇的影響》,《文學遺産》1993年第6期。盧綸的婚嫁詩顯示出此時的宫廷婚禮文學創作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隨着婚嫁詩創作羣體的下移進一步顯示出來。
唐代後期,宫廷大臣創作的公主婚儀詩文在存世文獻中難以見到,留存下的只有普通文士創作的婚嫁詩。范攄《雲溪友議》卷中《吴門秀》記,吴中文士陸暢以辭藻聞名:
初爲西江王大夫仲舒從事,終日長吟,不親公牘。府公微言,拂衣而去。……及登蘭省,遇雲安公主下降劉都尉,百僚舉爲儐相。詩題之者,頃刻而成,其詩亦麗也。《咏簾》詩曰:“勞將素手卷蝦須,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踟躕。”《咏行障》詩曰:“碧玉爲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强遮天上花顔色,不隔雲中語笑聲。”詔作《催妝》五言詩一首曰:“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柏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曉霞。”内人以陸君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宫大咍,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56)唐雯《雲溪友議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83—87。《唐詩紀事》卷三五《陸暢》條也有類似記載,文字稍有不同。
《全唐詩》卷四七八所録陸暢六首婚嫁詩分别是《雲安公主出降雜咏催妝二首》、《坐障》、《階》、《簾》與《扇》,這六首婚嫁詩與存世文人的婚嫁詩文可以比讀。
可以確定作者的文人婚嫁詩文存在多首,黄滔有三首婚嫁詩,分别是《卷簾》、《啓帳》與《去扇》,李商隱有《代董秀才卻扇》詩一首,徐安期有《催妝詩》一首,司空圖有《障車文》一首。此外,還有數首見於小説、筆記,也屬於文人創作。楊明璋從形式、内容以及創作者等幾個方面,對存世文獻與敦煌遺書中的婚禮詩文進行了細緻的比讀,認爲存世文人婚禮文學與敦煌婚禮詩文没有本質的差别,存在的差異只是前者的文人化特徵明顯,表現出獨誦的特點,後者的口頭表演與對答的特徵明顯。(57)伏俊璉主編《敦煌文學總論》第十一章《敦煌婚儀文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477—496。因爲都是普通文人創作,他並没有把陸暢的公主婚嫁詩作爲一特殊類别。根據他的分析,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斷,唐代後期,以宫廷爲中心的上流社會與中下層社會不但使用了程式基本相同的婚儀儀式,而且與這種儀式相對應的文學樣式基本也是出自市井文人之手,陸暢婚禮詩作被宫女廣爲傳唱也是這個原因。
進一步把公主婚禮詩文置於整個唐代文學創作的背景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唐前期與唐後期的婚禮文學發生的諸多變化。首先是詩歌的内容與體式的改變,儘管都是配合儀式過程的創作,前期婚禮詩歌的體式與内容相對自由,後期的婚禮詩文進一步儀式化、程式化。保存下來的婚嫁詩文基本都是配合婚禮展開的儀禮文本,體式以七言絶句爲主,題目與内容都相對固定。與文體變化對應的是創作羣體的變化,唐前期的婚禮書寫以宫廷爲中心,創作羣體是宫廷大臣,張説、宋之問等人都是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唐後期的婚禮詩歌轉向市井與地方,創作主體是中下層官僚文人。安史之亂之後的文人幾乎都有入幕的經歷,雖然盧綸被列爲臺閣詩人,但是他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在幕府與地方上度過。其他陸暢、李商隱、黄滔、司空圖等人都有在地方鎮守擔任掌書記、從事等文職的經歷。富有文才,擅長筆劄文書是這類文士的共同特徵。如《舊唐書》卷一九《李商隱傳》記,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58)《舊唐書》卷一九,頁5078。這種誄奠文章與婚嫁詩一樣,屬於吉凶禮儀中的應用型文體。又《唐摭言》卷一:
湯篔,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闐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篔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制,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恚而卒。(59)王定保《唐摭言》,《唐五代筆記小説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668。
湯篔能在頃刻之間完成四本《障車文》,並不能證明他有多高的社會地位,相反,這只能表明他作爲下層僚屬的身分,婚禮詩文的創作成爲這類文吏應該具備的技能與熟悉的業務。通過司空圖《障車文》我們可以看出,只要具備了一定的文學基礎,這類程式化文體的創作並不難爲。
陸暢與湯篔的經歷説明,唐代後期,隨着新興文士羣體成爲文學創作的主體,源於宫廷的婚儀文學經過中下層文人的改造後,形成了具有生活情趣與世俗追求的書寫模式,這些儀式化的婚儀文學隨着文人的宦遊而廣泛傳播,成爲宫廷與民間、中央與地方共同接受與模仿的對象。(60)關於唐代幕府文人的文學創作,參看戴偉華《唐代幕府與文學研究》第三章《幕府中的文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59—93。從這個意義上講,敦煌婚儀文學的源頭既不是地方民間藝人,也不是當地的知識階層,而是來自漢魏以來的中原文學傳統。進而言之,與張説等人《花燭行》同時代的《遊仙窟》不會受到《下女夫詞》的影響,相反,《下女夫詞》的淵源更應該是魏晉以至唐代的文人文學傳統,甚至可以説以張鷟《遊仙窟》爲代表的中原文人婚戀文學的創作影響了《下女夫詞》的創作,(61)關於《遊仙窟》敍事文體文人化特徵的生成與承延,參看康韻梅《遊/神仙窟/文章窟—〈遊仙窟〉敍事文體探析》,《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頁397—430。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與韋瓘《周秦行記》在敦煌寫卷中發現就是證明。
四 小 結
遠古時期的婚儀儀式是一種宗教儀式,表現出巫文化的特徵。兩周時期,隨着巫覡文化向禮樂文化的轉變,婚儀儀式的宗教性質淡化,倫理教化的功能得到强調,漢代儒生根據周禮整理的《禮儀·士昏禮》就是代表。從書寫的角度看,《禮儀·士昏禮》是建立在禮制空間與家庭身分相對應的儀式表達,確立了儒家化婚儀書寫的基本範式,無論對婚儀實踐還是婚儀書寫均産生深遠影響,魏晉以來,國家禮典中的婚儀就是禮經婚儀禮制化、制度化的産物。然而,無論是古禮經還是國家禮典,其中的婚儀禮儀只是理想化的制度設計,相當一部分内容停留在文字層面上,所以要對婚儀及其表達進行分析需要更具實踐品格的婚儀文獻。
魏晉南北朝是婚禮理念與實踐大變革時期,屬於士族家禮、家訓的婚姻禮俗被廣泛接受並且上升到官方禮儀的層面。體現士族身分與學養的書函成爲婚禮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書函的實用,禮經與禮典中的部分儀式展演約化爲文字表達,提高了婚儀儀式的實踐性與實用性。程式化的書儀更容易模仿與流傳,所以能夠代替禮經與經典,爲社會各個階層所使用。婚禮書儀的出現與普及意味着重經義與重文辭的貴族風尚結合起來,婚禮儀式具有了文學化的表達方式。
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唐代婚禮文本清楚地顯示了唐代婚禮表達的文體特徵。口誦詩文最能體現婚禮的文學性,這些婚儀書寫對應世俗化的儀式設置,表達了婚姻功利化、情欲化的取向,與體現儒家婚姻理念的書函一起,構成了婚禮多層面的表達方式。婚禮儀式的文學化,意味着婚禮儀式具有了文學化的表達方式,與之對應,進入婚禮儀式的文學傳統必須因應儀式的表達需要而做出調整。比如《下女夫詞》本屬於人神遇合敍事傳統的一個完整故事情節,但爲了儀式表演需要,其情節不得不重新設定,由此形成了與儀式進程相關、表達方式不同的三部分内容。清儀式展演與文學表達之間的對應,可以更直觀地觀照儀式與文學之間的淵源關係。(62)關於文學與儀式的關係,參看伏俊璉《文學與儀式的關係: 以先秦文學和敦煌文學爲中心》,《中國文化研究》2010年冬之卷。
從唐前期到唐後期,從中央到地方,從宫廷到民間,吉凶書儀的製作日益官牘化,以至於最終被表狀箋啓類文書所代替,與之對應的是書儀製作羣體從名士貴宦到書記文吏的轉變。(63)吴麗娱《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33—82。婚儀文學的變化軌迹與禮儀書寫的變化軌迹同步,隨着禮制與文學的下移,以及官方禮儀的簡約化、士庶化,(64)姜伯勤《唐禮與敦煌發現的書儀》,《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425—439。中下級官僚文人成爲婚禮文書與婚禮文學創作的承擔者。這些沉浮遊弋於社會上下層之間的文人官僚既是文學製作者,又是文學的傳播者,由此決定了婚禮文學表現出新的時代特徵,這一變化軌迹可以認爲是中古時期從貴族社會到官僚社會、從貴族文學到官僚文學變革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