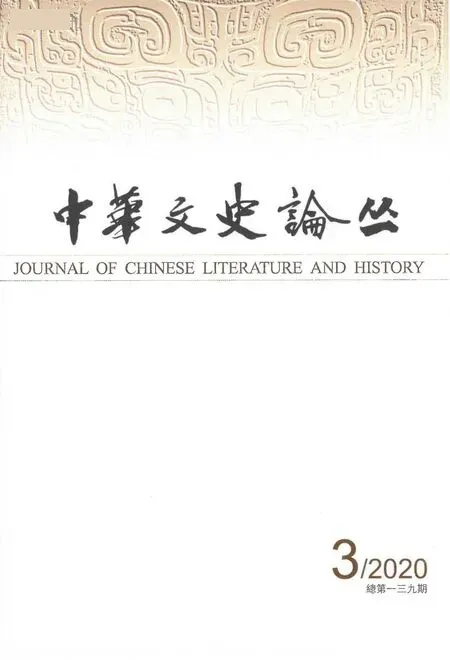走進“錢學”
——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
王水照
提要: 作爲《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一書序言,介紹了成書緣起、内容結構和寫作求真宗旨,討論“錢學”研究中資料使用和有無體系兩大疑點。尤以論韋莊《秦婦吟》、論牛李黨爭、論楊貴妃入宫、論韓愈、論杜詩“欲往城南望城北”句五个例證説明錢鍾書、陳寅恪兩先生學術交集及其意義,指出錢氏的“打通”與陳氏的“詩史互證”的不同,闡述錢氏堅持以文學爲本位,堅持文學—文化—文學的學術理路。這是貫穿他全部著作的一個“系統”。
關鍵詞: 錢鍾書 打通 陳寅恪 詩史互證 文學本位
2020年是錢鍾書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一位朋友在病中與我通電話,建議我把這些年來所寫的有關錢先生的文字彙輯成集,以作紀念。我十分猶豫。我和錢先生相識相交算來共有三十八年,前十八年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跟隨他治學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棄愚鈍,對我的成長花費不少心力,他是我學術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後二十年雖分隔京滬兩地,仍不時請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壽之際,理應奉上一瓣心香。然而,自審已經發表的文字,對錢先生的人生經歷瞭解不深,對他的學識涵養、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門徑,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業,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經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錢鍾書與宋詩研究”,雖已結項卻未成書;打算撰作的《錢鍾書學術評傳》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對先生。但畢竟如今得親炙於先生者,已爲數不多,我還是有向年輕學子述説自己感受的衝動,似乎也是一種責任。
《錢鍾書的學術人生》内容大致包含錢先生其人、其事、其學三項,釐爲四輯: 第一輯涉及生平經歷和學者日常風範,第二輯記述與學術有關的事件,第三、四兩輯則關於“錢學”,又大致依《宋詩選注》、《宋詩紀事補正》、《錢鍾書手稿集》幾部著作爲重點展開,尤傾力於《手稿集》的研讀,特立專輯。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學,兼及唐代文學。爲便於讀者閲讀,又增設若干小標題,以醒眉目。這一設計希望能使原先零散無序的文章,略具條理性和系統性。各輯分類容有不當,錢先生的人生本來就是有學術的人生,他的學術又與生命息息相關,是不容截然分離的。
有位年輕朋友當面對我説:“你寫的有關錢先生文章是‘仰視’,我們則認爲應該用平視的視角。”我欣賞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氣。我也聽懂他話外的意思: 一是切勿隨意拔高,二是力求敍事真實。這確應引以爲戒。我曾作過一次《記憶中的錢先生》的講座,題目是主辦方出的。這個題目,錢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認可: 他既反對别人研究他,又對“記憶”作過調侃:“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1)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重印本序》,《人·獸·鬼》,《錢鍾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頁134。魯迅也寫過回憶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説:“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2)魯迅《朝花夕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2。魯迅的“現在只記得是這樣”,不失爲可以踐行的一條原則,也不算違背“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吧。本書所記不少是我親見親聞,自信力求真實,即使是傳聞之事,也經過一些考查。至於“仰視”云云,則情形比較複雜。我不能花兩個星期温一遍《十三經注疏》;不能看過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作過筆記;不能讀遍明清人别集,“余父子集部之學,當繼嘉定錢氏史學以後先照映”;(3)錢基博《〈讀清人集别録〉小序》,《錢基博集: 序跋合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05。不能按照圖書館書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閲讀;更不能留下多達四十幾卷的手稿集……僅此數端,“仰視”視角自然形成。裝作“平視”甚或“俯視”,不是太不自然了嗎?當然,不要因“仰視”而影響論析的客觀性、科學性,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節,一位研究宋代文學卓有成就的朋友給我來信,鄭重而認真地對錢先生學問提出全面質疑。信函多達四頁,暢所欲言,略無避諱,“自來與兄坦誠相見”,令我十分感動。他講了六點意見,概括起來是兩條: 一是錢先生只是資料羅列,知識堆積;二是缺乏思想,更無體系,“縱觀全部著述,没有系統”。這兩條實是互爲表裏,互證互釋的。我一時無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後所寫的有關錢先生文字中,内心始終懸着這兩條,循此而與他進行討論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罷了。這次編集本書時,我躊躇再三,決意全文公布錢先生給我的一封論學書簡和兩份學術檔案,也是爲了繼續討論和探索這兩個問題。
1984年秋,我應日本東京大學之邀,去該校授課。離國前曾去北京教育部辦理手續,並向錢先生話别,談了一個上午。一是日本學者的中國學研究,二是關於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傳》(他有對此書的評注本)。他告誡我在外面不必過於謙抑。我到日本後,除授課外,主要精力放在去各大圖書館訪書。原以爲不會有多大收穫,不料偶然見到兩種中土久佚而仍存彼邦的我國古籍: 一是《東坡先生年譜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二是《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朝鮮活字本)。我寫信向他彙報,他習慣性地誇獎幾句後,即寫下一大篇關於不要迷信資料、死於句下的文字,是有關資料與研究辯證關係的極重要的精闢論述,也可以視作對他某種質疑的一次回應。他説:“學問有非資料詳備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資料詳備而已可立説悟理,以後資料加添不過弟所謂‘有如除不盡的小數多添幾位’(《宋詩選注·序》)者。”資料是研究學問的前提和基礎,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必迷信資料,片面貪多務得,成爲資料的奴隸。他接着講了兩個親歷的故事: 一是他論述《老子》中神秘主義基本模式,並不“求看”新出土之馬王堆漢寫本《德道經》;二是參觀美國國會圖書館,發出豪語:“我亦充滿驚奇,驚奇世界上有那麽多我所不要看的書!”没有博覽羣書、海量閲讀的底氣,這番驚駭現場的豪語就會變成狂言了。“雖戲語,頗有理,告供一笑”。在研究工作中理應詳細地占有資料,但切忌買菜求益,唯多是求,這個“理”是嚴肅認真的。然而,信的末尾,他又筆鋒一轉,告我新本《談藝録》即將問世,“偶檢存稿”,發現“可增删處往往而有”,至少論但丁和梅堯臣兩處應補意大利人博亞爾多和蘇東坡的相關材料。足見念兹在兹,資料是基礎和前提這條根本法則是不容動摇的,重要的是實現對資料的自主占有和駕馭。
粗讀錢先生的著作,總會感到引證繁複,不免目迷色眩,但細加覆按,他的排列和選擇是有内在理路的。《宋詩選注》的注釋,精博富贍,乃他人不可及之處,卻被稱爲“挖腳跟”,實在是種誤讀。他送給我該書1962年再版本,我曾與初版本加以對勘,光是詩例引證一項,至少有三種形式: 一是按時代順序排列,有些平列感;二是從比較中點評各個詩例的特點;三是引例後發表大段議論。尤其是撤换了大量例證,個中原因,大堪玩索。僅舉開篇鄭文寶《柳枝詞》“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兩句,他先説此詩很像唐韋莊的《古離别》,但比韋詩“新鮮深細得多了”,這是講承前。接着講啓後: 周邦彦《尉遲杯》詞是整首改寫鄭詩,石孝友《玉樓春》把船變爲馬,王實甫《西厢記》把船變爲車,陸娟《送人還新安》又把愁和恨變成“春色”。尤其令人尋味的,删去初版蘇軾等六個詩例,那些詩例也是披沙揀金、辛苦搜集到的。這只能説明,資料在錢先生手中,是自由挪捏、依理驅遣的活材料,而不是死於材料之下,這纔是對資料的正確態度。
錢先生説,獲取資料是爲了“立説悟理”,從資料到知識,再到思想和體系,應是研究工作的一般進程。匡亞明先生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有個重要主張,凡是對人類文化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必有傑出思想甚或思想體系,因而他不僅收入傳統意義上的“思想家”,還收入衆多舊時只能進入“疇人傳”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傑出人物。他在叢書“總序”中作過深刻的説明。錢先生存世的文化遺産可謂洋洋大觀,怎麽成了“縱觀全部著述,没有系統”的思想碎片的彙集?這是我的困惑和焦慮。我在悼念錢先生的《記憶的碎片》中寫道:
(錢先生)没有給出一個現成的作爲獨立之“學”的理論體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紛呈卻散見各處,注重於具體文藝事實卻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經過條理化和理論化的認真梳理和概括,纔能加深體認和領悟,也纔能在更深廣的範圍内發揮其作用。研讀他的著述,人們確實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統一的理論、概念、規律和法則,存在着一個互相“打通”、印證生發、充滿活潑生機的體系。感受不是科學研究,我無力説個明白。(4)拙撰《記憶的碎片——緬懷錢鍾書先生》,《鱗爪文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頁8。
這段文字寫於錢先生逝世後第三天,似乎給我自己定下了一個努力目標。雖然也作過一些謀劃,然而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大都未能完成,愧悚不已。也提出過《宋詩選注》的“四種讀法”,從《容安館札記》梳理錢先生的南宋詩歌發展觀,“晚唐體”是把握南宋晚期詩歌風格的核心概念等個别問題,都未能從全局上解決問題。
我想可以擴大思路,從多種角度去探討所謂“體系”問題。這裏提出一個錢先生與陳寅恪先生學術思想觀點的交集問題,或可從中抽象出一些系統性的問題。
陳先生長錢先生整整二十歲。吴宓先生在清華工字廳提出的“陳錢並稱論”,其着重點在於極度推重錢氏,若推測當事人的内心反應,陳先生或許一笑了之,而在錢先生那裏,可能頗爲微妙了。後來學術界逐漸發現兩人學術觀點多有差異(主要是錢質疑陳),但出於對他們的尊重和禮貌,並未展開討論。近年來討論纔熱烈起來,形成了“陳錢異同論”這個極有學術價值的議題。本來,展開平心靜氣的學術爭辯是正常的現象,大學生時代的錢鍾書就富於挑戰權威的精神,與周作人關於新文學源流的爭論,就是著名的事例。他還在暑期夜晚納涼與父親錢基博先生論爭陳澧《東塾讀書記》與朱一新《無邪堂答問》的高下問題,父崇陳而子重朱,幾個回合,最后以陳爲經生之書、朱爲烈士之作而勉强取得一致(見錢基博《古籍舉要序》)。我在復旦大學講授宋代文學,也戲向學生出個論文題目“當朱老遇到錢老”: 朱東潤先生推重梅堯臣和陸游,爲他倆各貢獻了三種著作,錢先生的《談藝録》等著作卻對梅、陸多有苛評,其間的區别大概也有志士和才子不同立場的投影吧。陳先生和錢先生最直接、最根本的不同學術取向,乃是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的區别。作爲歷史學家,陳先生觀察世上的萬事萬物都是“歷史”,“詩”也是史料,於是“以詩證史”、“詩史互證”成爲他倡導並運用成熟的研究範式;錢先生卻在“打通”的基礎上,强調“史必徵實,詩可鑿空”、“史藴詩心”,甚至想寫一部哲學家的文學史,由此形成他若干一以貫之的思想原則。
我這次編集本書時,全文收入錢先生給我的兩篇審稿意見,一論韋莊,一論唐詩,卻不約而同地向陳先生發出質疑,就包含上述内容。
我的《韋莊與他的〈秦婦吟〉》一稿,討論對象是向迪琮先生所編的《韋莊集》。錢先生説,此書“始托‘詩史’之名,藉以抬高韋莊”,“抬出與杜‘詩史’並稱”,韋莊一生“崇奉”杜甫。這裏“崇奉”、“抬高”、“詩史”三個關鍵詞,其實都或明或暗地針對陳先生。錢先生明確寫道:“憶陳寅恪先生《秦婦吟箋釋》即以‘浣花名集’爲韋崇奉杜之證……同一捕風捉影,文學批評中之‘考據’必須更科學,更有分析。”這是迄今所見錢先生第一次點名批評陳氏的文字,且係給《文學評論》編輯部的審稿意見,應屬半公開性質的。錢先生對陳氏“崎嶇求解”(張載語,見朱熹《詩集傳·詩傳綱領》)的歷史考據方法的非議是不假諱飾的。陳氏《韋莊秦婦吟校箋》(見《寒柳堂集》)中論定《秦婦吟》“爲端己平生諸作之冠”,又以“生平之傑構,古今之至文”十字評賞之,可謂“抬高”之至;而錢先生在《容安館札記》第789則卻又詳細指摘此詩藝術上缺失之處,如“支蔓失剪”、“詳略失當”,結尾“令人悶損”等,(5)《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3),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2488。兩者對照鮮明。至於“詩史”一語,錢先生從根本上加以擯斥。《管錐編》云:
蓋“詩史”成見,塞心梗腹,以爲詩道之尊,端仗史勢,附合時局,牽合朝政;一切以齊衆殊,謂唱嘆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詞。遠犬吠聲,短狐射影,此又學士所樂道優爲,而亦非慎思明辯者所敢附和也。學者如醉人,不東倒則西欹,或視文章如罪犯直認之招狀,取供定案,或視文章爲間諜密遞之暗號,射覆索隱;一以其爲實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經,一以其爲曲傳時事,乃一代之皮裏陽秋。楚齊均失,臧穀兩亡,妄言而姑妄聽可矣……苟作者自言無是而事或實有,自言有是而事或實無,爾乃吹索鈎距,驗誠辨誑……專門名家有安身立命於此者,然在談藝論文,皆出位之思,餘力之行也……康德論致知,開宗明義曰:“知識必自經驗始,而不盡自經驗出。”此言移施於造藝之賦境構象,亦無傷也。(6)錢鍾書《管錐編》(4),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390—1391。
詩是詩,史是史,兩者雖可用以互證,卻各有其本質屬性,不容混一。於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的區别,大暢其旨,具見錢先生着眼所在。在《宋詩選注·序》中,他又有一段論述:
“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内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裏來鑑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7)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頁3。
陳先生是否有對“詩史”的直接論述,待考。但錢先生此處所言,仿佛都有其影子在。陳先生論《長恨歌》,於賜浴華清池那段絶妙好辭,指責時間不合,應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時節”,且“其旨在治療疾病,除寒祛風”,而非“消夏逭暑”;於“六軍”謂數字不合,考當時唐皇室軍隊實只有四軍;於“峨嵋山下少人行”句,又謂地理有誤,唐明皇未行經該地,但此例尚“不足爲樂天深病”,算是網開一面;而華清池之長生殿,乃“祀神之齋宫,神道清嚴,不可闌入兒女猥瑣”,這就是白居易的“失言”了。(均見《元白詩箋證稿》)錢先生所談的“吹索鈎距,驗誠辨誑”,“專門名家有安身立命於此”,用愛克司光透視人體美等語,不免令人聯想到陳先生的身影。錢先生批判“詩史”概念,對他與陳先生在詩學觀念上的根本分歧,作了深刻的闡述。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一例。
我在《唐詩選·前言》中,從士族、庶族的社會身分分野,論述唐代進士科“以詩取士”,進而探討唐代一般詩人的社會身分,以及唐詩繁榮原因,都深受陳先生論史的影響。以門閥士族和寒素家族的對立論史,是他史學的基石,近年出版的萬繩楠《陳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講演録》(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全書即以此爲中心線索予以論述。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寫道:“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時牛李兩黨以科第而分,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寅恪案: 乙盦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識。”(8)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86。而牛、李兩黨,其社會身分即各爲“庶族新興階級”和“門閥世族”,牛黨所重“科舉”即特指進士科,李黨所重“門第”,即世家大族。陳先生很少在著作中稱引當世學者見解而自重,此處乃爲特例;且推重爲“卓識”,無疑也是對己説的自信和自許。對於這個陳先生自以爲“卓識”的見解,錢先生卻表示異議。他在審稿意見中寫道:“……與鄭覃事合觀(抬出《詩三百篇》來抵制文宗“詩博士”之舉),便知讎視‘進士’不僅是世家子弟反對選舉,還包含着自周、隋以來經學對詞章的讎視,即‘儒林’對‘文苑’的讎視(在宋如道學家之於詩文人,在清爲考據家之於詞章家,在現代歐美如科學家之於人文學家,所謂“兩種文化之爭”),此點文中不必詳説,但措辭須稍減少簡單化,除非能證‘明經’派都是貴族世家。韓愈《答殷侍御書》可以一讀。殷即殷侑,大經學家——是徵‘進士’和‘經書’是兩門學問,但‘進士’與‘明經’不一定是出兩個社會階層(殷當時已官爲侍御)。”在錢先生看來,認同或貶斥進士科之爭,不是牛、李兩黨之爭,也不是士族和庶族兩個社會階層之爭,而是“兩種文化之爭”,這與陳先生頗異其趣。
陳先生的這個觀點在學術界引起過討論。對於牛黨出於庶族、李黨出於士族,中外學者多從成員的個案調查結果來加以反駁,如同在中山大學任教的岑仲勉先生和日本京都大學的礪波護等。然而,陳先生的見解有其材料的堅實基礎和理論上的自足性,不是簡單方法就能完全駁倒。他首先説明,“牛李黨派之分野在科舉與門第”這是個“原則之大概”,但“牛李兩黨既産生於同一時間,而地域又相錯雜,則其互受影響,自不能免”,牛党可以變李,李党可以爲牛,但不影響這個大判斷。接着又分析三種複雜情況: 一是牛李兩黨的對立,根本在於山東舊族(華山以東的王、崔、盧、李、鄭等士族)與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而李唐皇室原屬關隴集團,與山東舊族頗有好感,但唐中葉後,其遠支宗室地位下降,已大别於一般士族,處於中立地位;二是有的號爲山東舊族者,門風廢替,家學衰落,此類“破落户”已與新興階級同化,無所分别;三是凡牛黨或新興階級所自稱之門閥多不可信。凡此種種,單用實證主義户籍調查式的考辨方法就無濟於事了。
錢先生卻從“兩種文化鬥爭”的角度質疑,可謂另闢蹊徑。這是一個頗有歷史穿透力的大判斷。論述未暢,留下許多未發之覆,可供後輩進一步探討。錢先生也不是一般地反對文學羣體與社會身分相繫聯,比如對南宋“江湖派”,他就提出“江湖詩人之稱,流行在《江湖詩集》之前,猶明末之職業山人”(見於給我的信),與江湖派起於陳起編印《江湖集》的舊説相左。他認爲這是一個“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的社會羣體,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詩派。(9)可參觀《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一文,收入即出之拙撰《錢鍾書的學術人生》。説唐代進士問題之爭懷疑其存在士族、庶族的社會階層背景,説江湖詩人卻承認此乃一游走江湖的社會羣體,在文學與階層的關係上,一截斷,一相聯,均反映出錢先生論學的文學本位立場。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二例。
1978年9月,錢先生在意大利參加歐洲研究中國協會第26次會議,第一次以“不點名而點名”方式公開對陳寅恪先生發出質疑。他説:
文學研究是一門嚴密的學問,在掌握資料時需要精細的考據,但是這種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讓它喧賓奪主,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
他接着舉例説: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宫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麽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爲是嚴肅的文學研究。(10)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人生邊上的邊上》,《錢鍾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179。
話題是楊貴妃宫闈隱秘,批評確是嚴肅的。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是“四人幫”粉碎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派往國外的,由四位副院長(包括錢先生)組成,規格甚高;陳、錢兩先生,兩度同在清華,卻無交往;僅有一次是後來陳先生主動將《元白詩箋證稿》寄贈於錢,而楊貴妃問題恰恰就在此書第一章論《長恨歌》中提出。這表明錢先生並不因私誼而放棄自己的學術理念,旗幟鮮明地向一種研究風氣進行挑戰。
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法是他運用純熟、新見迭出、影響深遠、廣受好評的研究方法,《元白詩箋證稿》即是代表著作。錢先生的“打通”法也是他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的詩史互證也獲得豐富的精彩成果。然而,兩位同擅“詩史互證”法,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及考證風格卻大異其趣。錢先生的不滿,簡言之有二: 一是“喧賓奪主”,文學是“主”,歷史考據是“賓”,歷史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他在批評中,處處突出以文學爲本位的原則。他判定考據楊貴妃入宫事是“無謂的問題”,是嚴格限制在文學範圍之内的,連舉的兩例(濟慈喝稀飯,普希金抽煙),也是兩個文學家的“話柄”。二是“深文周納”,“以繁瑣爲精細”的考證風格。其實早在“文革”中成書的《管錐編》裏,已表示對討論楊貴妃入宫事的厭煩。該書第一四五則論中寫道:“閑人忙事,亦如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五《書〈楊太真外傳〉後》、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一《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外傳後〉》以來之爭辯‘處子入宫’,煙動塵上,呶呶未已。”(11)錢鍾書《管錐編》(4),頁1227—1228。陶潛因有二子“不同生”詩句,引發爭論陶潛私事(有一妻一妾,或喪妻續娶,或爲孿生),“推測紛紜”;“處子入宫”事與其相提並論,均爲“無謂的問題”。此時尚未及陳先生,足見錢先生一貫的貶斥態度。
從陳先生立場來看,此事又當别論。首先,這不是一個僞問題。若放在歷史領域中,可能别有意義。正如替陳先生辯護的學者指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開宗明義即引朱熹之語:“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12)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1。因而值得考辨,從中可以窺見“李唐皇室的家風”,就是説,在文學領域以外,這就不是“無謂的問題”。這個辯護自有理據。但也必須指出,陳先生本文中並無涉及此點。他認定的性質是“宫闈隱秘”,是一場“喜劇”。
其次,從學術史而論,陳先生説,這是“唐史中一重公案”。他細心地梳理正方(主張“處子説”)諸家,在杭世駿、章學誠、朱彝尊等人中,認爲“朱氏之文爲最有根據”,其他人不過沿承朱説,因而把朱彝尊作爲駁難的主要對象。他的反駁,論證細密,剖析毫芒,長達七八頁,足爲“非處子説”定讞,“了卻此一重考據公案”。
第三,陳先生明言,他辨明朱氏之誤,“於白氏之文學無大關涉”,表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在文學之外討論此事。而且實際上與文學亦非毫無關係。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我們文學所的《唐詩選》在注釋《長恨歌》“楊家有女初長成”、“一朝選在君王側”句,有一長注:“開元二十三年,册封爲壽王(玄宗的兒子李瑁)妃。二十八年玄宗使她爲道士,住太真宫,改名太真。天寶四年册封爲貴妃。”這不是陳先生那一大篇考據文章的提要嗎?他的考辨成果已被錢先生也參與過的唐詩選本所吸取。再説,我們讀李商隱的《龍池》、《驪山有感》等詩,陳先生的成果也會産生文學性效果。“新臺之惡”畢竟不符合我國傳統悠久的道德標準,朱熹的“不以爲異”的説法值得考慮,只是不像唐以後那麽看得嚴重罷了。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三例。
陳先生《論韓愈》一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對韓愈的推崇超邁宋儒,世所僅見。他把韓愈定位在“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爲新關捩點之人物”,即“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在這個前提下,他高度肯定古文運動:“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這裏把“唐代古文運動”和“宋代新儒學新古文運動”,視作一脉相承的關係,語氣決斷,“不容置疑”。所謂“新儒學”,他又説:“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説,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儘量談心説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爲體,華夏爲用,退之於此以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傑,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13)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88。這些著名的觀點,錢先生均提出異議。
錢先生首先指出韓愈雖標榜“文道合一,以道爲主”,實際上他的“文”和“道”是“兩橛”的,並不等同於“文”必然服從、附庸於“道”。在《中文筆記》第十册中,他舉李漢《韓昌黎文集序》説,此文以“文者,貫道之器也”發端,但一路寫來,只見李漢光推重韓愈之文而不及其道,所謂的“摧陷廓清”,也是指文:“先生之文摧陷廓清之功”。最後錢先生説:“皆分明主‘文’”,“可見昌黎爲文學道,分爲兩橛”。韓愈在“儒學”上並未獨立成家。這一觀點,在《容安館札記》中有更詳盡的發揮。如第720則云:
《進學解》云“觝排異端,攘斥佛老”,即《原道》之説也。然自道其學爲文章則云:“下逮《莊》、《騷》,太史所録。”《送孟東野序》又云:“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詞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合之《送王秀才序》云:“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足徵昌黎以“文”與“道”分别爲二事,斥莊之道而稱莊之文,如《答李翊書》、《送高閑上人序》即出《莊子》機調。(14)《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3),頁1769。
接着也分析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與《中文筆記》相似)後,他又説:
證之昌黎《答竇秀才書》“專於文學”、《上兵部李侍郎書》“性本好文學”、《與陳給事書》“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等語,乃知宋人以昌黎入道統,尊之而實誣之也。近人論韓,更加夢囈矣!(15)《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3),頁1770。
錢先生的有關論述還有很多(16)可參觀《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一文,收入即出之拙撰《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不贅述。
錢先生的立論可以明顯看出,是從文學本位立場出發的。“古文運動”本來是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個概念,據目前檢索到的資料,殆始見於胡適在1927年由北京文化學社出版的《國語文學史》,(17)《國語文學史》次年改名爲《白話文學史》,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後出的各類文學史多沿其説,遂成重要研究論題。古文運動是借助於儒學復古旗幟而推行的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還是如陳先生所言,是新儒學新古文的文化運動,這是根本認識上的歧異。
陳先生的《論韓愈》發表於1954年《歷史研究》,是他建國後最早問世的少數重要史論之一,論文高屋建瓴,議論縱横,大氣包舉,透露出學術自信與自負。僅如“天竺爲體,華夏爲用”的提法,就與通常所説“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不同,似有深意存焉。高深學問常常易於被人誤解,我們後輩實不宜對陳、錢二位宗師説些不知深淺之語。事實上,目前不少學者研究唐宋古文運動,還在沿承陳先生的路數,强調其思想史方面的性質。問題應是開放性而非終結性的。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四例。
錢、陳觀點交集中,也有相反相成,或可互補互融的一面。兹舉對杜甫“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的不同解釋爲例。
陳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論《賣炭翁》“回車叱牛牽向北”句時,從長安城市建置特點,即“市在南而宫在北”出發,認爲杜甫此句“望城北”亦指望皇宫,意謂詩人“雖欲歸家,而猶回望宫闕爲言,隱示其眷念遲回,不忘君國之本意”。(18)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251。
文學研究所《唐詩選》杜甫部分是我注釋的,當年曾把此句作爲“難點”提出集體討論。我總結討論意見,最後寫道:“‘望城北’有三種説法: 一説‘肅宗行宫靈武在長安之北……望着城北,表示對唐軍盼望之切’;一説‘唐代皇宫在城北,回望城北,表示對故國的眷念’;一説‘望即向,望城北即向城北之意’。”(19)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頁244。結論是:“後一説較妥。當時作者百感交集,憂憤如焚,一時間懵懵懂懂地走反了方向,於情理或更切合。”第二説就是陳寅恪先生的意見,第一説解爲盼望在靈武的肅宗與唐軍,實際上與陳氏同一思路,把詩意引向對“故國”、“唐軍”的期盼,突出杜甫“每飯不忘君”的意義。第三説只從“情理上”揣摩詩人其時之心理狀態,或許與詩意更貼切些。這主要是吸取錢先生在討論會上的意見。後來他在《管錐編》中卻有更深入的發揮。他説:“杜疾走街巷,身親足踐,事境危迫,衷曲惶亂。”並引五條書證: 張衡《西京賦》所謂“喪精亡魂,失歸忘趨”;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王安石集杜句;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言皇惑不記孰爲南北也”;《敦煌掇瑣》之《女人百歲篇》“出門唤北卻來東”;李復《兵餽行》“一身去住兩茫然,欲向南歸卻望北”,“即用杜句”。並拈出“向”以與“望”爲互文,“望”可作“向”解。(20)錢鍾書《管錐編》(3),頁988—989。
一位是着眼於安史之亂、國破家亡、皇權失墜的記憶,“每飯不忘君”的杜甫思想定位等歷史因子;一位是超越於特定的歷史時空,而聚焦於文學是人學、對一般人情、人性的熨帖,注重於詩性的因子。兩説各有所長,但仍體現出不同的學術趨向。
我們注釋《唐詩選》時,遇到存在異説而需下斷語時,常用“某説是”、“某説較勝”、“兩説並存”三種形式。我在注釋杜甫此句時的按語是第三説“於情理或更切合”,來表示傾向於錢先生之説,但也承認陳先生説“可備一説”。白居易“回車叱牛牽向北”之“北”,指涉是確定的,確指皇宫,因該篇主旨乃“苦宫市也”;但杜詩此句的“北”,没有足夠的證據徑斷爲皇宫方位。然而反過來説,也同樣無充足證據斷其爲非。綜合兩説,可以擴大對詩歌的理解空間,所謂“詩無達詁”有其正當性。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五例。
以上五例,觀點歧異,涇渭分明,都有錢先生的文字爲依據(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談之語),表明陳、錢兩位論學旨趣的差别。錢先生也是主張“打通”的,他説過:“吾輩窮氣盡力,欲使小説、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爲一家。參禪貴活,爲學知止。”(21)錢鍾書《談藝録》,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352。所説五例,論韋莊,論楊貴妃入宫,論杜詩三則屬“詩史互證”,論韓愈,論門第排斥進士科,則各與哲學、社會學有關,借用錢先生自己的話來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詩選注·序》中的一段論述:
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迹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没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抛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像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説詩歌、小説、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22)錢鍾書《宋詩選注》,頁4。
這是對文學研究與歷史考訂區别的説明,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文學與哲學、文學與社會學研究。文學是“人學”,必然與各個學科發生關聯,因而,單純地從文學到文學的研究路線是不足取的,必須同時進行交叉學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須堅持文學的本位,文學始終是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堅持從文學—文化—文學的路線,不能讓其他學科代替文學研究本身,這是貫穿錢鍾書先生全部著述的一個“系統”,對當前我國古代文學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啓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