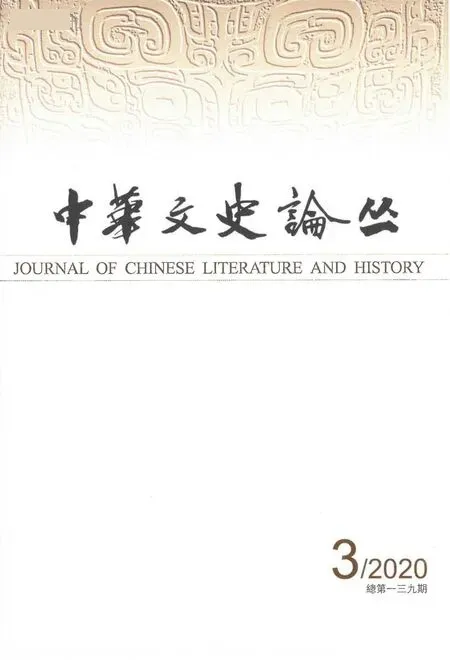北宋仁、徽兩朝的“太平敍事”與宋人文化記憶
夏麗麗
提要: 在南宋人的集體記憶中,宋仁宗、徽宗兩朝分别代表了兩種北宋“太平”敍事。邵雍的《伊川擊壤集》堪稱仁宗朝的“太平吟”,而推崇仁宗“嘉祐之治”的宋代士大夫在後世更將其盛贊爲“幾至三代”的“本朝盛時”。另一方面,徽宗朝堂所時興的“太平文體”在文獻層面建構出“太平盛世”的人爲景觀,其内容包括宋徽宗的宫詞創作、朝臣的應制帖子詞,以及與宣和御畫兩相映襯的君臣題詩。宋徽宗追求“豐亨豫大”的帝都中心觀,而恭儉的宋仁宗則代表了天下無事的太平治世,兩者在後世的形象對比,實則反映了宋人的文化記憶對北宋盛世的事後反思與理想化追述。
關鍵詞: 宋仁宗 宋徽宗 太平敍事 太平文體 《伊川擊壤集》 文化記憶
南宋人喜言“本朝故事”,而今人對北宋的歷史認識,得益於南宋人對中原文獻的涓滴存留與時事論定。可以説,追憶北宋幾乎成了日後南宋士大夫的共同特徵,清人翁方綱在《石洲詩話》中如此評價南宋詩:
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1)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23。
這些“可資考據”的紀事詩歌,(2)關於宋詩的紀事功能及其敍事性,可參考周劍之《宋詩紀事的發達與宋代詩學的敍事性轉向》,《文學遺産》2012年第5期,頁74—86。恰恰反映了南宋人對前朝的集體記憶。而在南宋人集體撰寫的多重“詩史”中,筆者發現,“太平”敍事在他們的北宋追憶文學中頻繁出現,尤其在涉及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兩朝時有突出表現。據相關學者研究,“太平”觀念最初在漢代流行開來,尤其在緯書中被廣泛使用,而東漢公羊學家何休很可能受到讖緯的啓發,結合西漢董仲舒的《春秋》“三等”之説而開創了“三世説”,其中“太平世”意指“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大同理想“治理圖示”。(3)邱鋒《何休“公羊三世説”與讖緯之關係辨析》,《天津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頁130—134。此後,“太平”一詞的内涵逐漸泛化,或在早期或中古宗教語境下指代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或在世俗政權中象徵聖王出世的清明之治。(4)關於東漢晚期出現的《太平經》和早期道教組織如太平道、天師道,可參見余英時《東漢生死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中有關《太平經》與道教的部分,以及Anna Seidel, “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 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A. Stein,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1983): 291-371;有關中古宗教與政治領域,可參考孫英剛《“太平天子”與“千年太子”: 6—7世紀政治文化史的一種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頁42—50。到了宋代,“太平”話語同樣充斥在帝國官方輿論中,如宋太宗(976—997年在位)將其第一個年號定爲“太平興國”,又主持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官方大型類書的編纂,以宣示大宋治世的到來;而宋真宗在位年間(997—1022)對天書、符瑞、封禪的愛好,都是其力圖打造“太平盛世”的文化表徵。但本文所指的兩種“太平”敍事則專指宋仁宗與宋徽宗時期的政治—文化話語,這是因爲二者不僅在文學層面的表達更爲集中,而且具有當時特定的“時代精神”(Zeitgeist),並構成了明顯的對抗關係。筆者試圖結合宋人的文學創作與歷史認識,從而論證當“太平”這一超驗的觀念術語被宋人移植進當下的現實史事中時,它既抽象爲理想化的文學圖景,也隱含了歷史龜鑑的道德意藴。
一 仁宗朝:“幾至三代”的百年治世與邵雍的“太平吟”
今人通過宋代文獻所認識的宋仁宗,並没有什麽驚人之舉、蓋世之功,但他與君臣之間的交流互動卻爲人所津津樂道,並以此奠定了這位皇帝在後世眼中“治世之君”的形象。尤其是仁宗朝學統四起、人才濟濟,有涵育君子之功,《宋史》亦贊曰:“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5)《宋史》卷一二《仁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251。良有以也。
實際上,當時的現實政治並非没有弊端,但宋仁宗的形象在後世卻經歷了一次“升格”。史家對宋仁宗最常見的評價就是“守成之君”,而他作爲“祖宗”典範的形象實際上是後來舊黨士大夫的重新闡釋,他們以仁宗恪守“祖宗家法”作爲抗衡新黨的政治話語,這幾乎成爲了南宋士大夫的標準歷史敍事。(6)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 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又見張林《熙豐變法與宋仁宗形象的提升》,《史學集刊》2015年第3期,頁4—10。與此同時,這樣一個充滿憂患、積重難返的仁宗之世,卻被日後的宋代士大夫建構爲理想治世典範的“嘉祐之治”。(7)參見曹家齊《“嘉祐之治”問題探論》,《學術月刊》2004年9月,頁60—66。關於仁宗朝的“因循末俗之弊”,可參考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載《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524;司馬光《謹習疏》,載《司馬光集》卷二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606;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臨川先生文集》卷四一,載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801—803。
在推崇仁宗之治的後世文化記憶中,邵伯温(1056—1134)的筆記《邵氏聞見録》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作爲元祐後人,邵氏筆記中處處可見新舊兩黨、“君子”與“小人”的對立,而書中對前朝故實與洛陽風俗的記述亦持有明顯的舊黨立場。值得注意的是,邵伯温還寫下了另一種“太平”敍事,和宋徽宗時期歌舞昇平的盛世景象迥然異趣: 書中每以仁宗朝爲太平治世,如“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8)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9)《邵氏聞見録》卷二,頁14。“仁宗生長太平,尤節儉”。(10)《邵氏聞見録》卷三,頁23。這其中當然不乏溢美之詞,甚至帶有神化色彩,其中一則記載便聲稱仁宗曾夢見一位道教神人,之後:
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摇首,而時和歲豐,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 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彦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吕誨云。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11)《邵氏聞見録》卷二,頁15。
在這條記載中,邵氏一方面力圖將宋仁宗刻畫爲尊崇無爲思想、“垂拱而治”的聖君,另一方面,又間接把太平治世的成效歸功於“祖宗法度”與一批治國能臣,並在最後不無誇張地將之目爲超越歷史的理想政體。
但若仔細推究,邵伯温對仁宗朝故事並非目見,而多有耳聞,親歷徽宗朝的他將宋仁宗有意識地理想化。其“太平”觀無疑受到其父邵雍(1012—1077)的影響。邵雍曾盛贊“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 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12)《邵氏聞見録》卷一八,頁196。“本朝五事”另見邵雍《觀盛化吟》(其二)詩注,《伊川擊壤集》卷一五,載《邵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21。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將本朝(尤其是宋太祖至宋仁宗時期)比隆三代的説法在北宋不乏其例: 司馬光在仁宗嘉祐年間上呈的《進五規狀·保業》中即言“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13)《司馬光集》卷一八,頁539。此後的元祐朝臣亦云“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14)見《宋史》卷三四《吕大防傳》,頁10842—10843。又如陳師錫在上書宋徽宗的諫言中説:“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羣臣,賢必進,邪必退。……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爲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15)陳師錫《上徽宗論任賢去邪在於果斷》,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93),卷二三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頁253。楊時的《上淵聖皇帝疏》亦與之同調:“貞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效也。”(16)《全宋文》(124),卷二六七五,頁82。一個“本朝盛時”、“幾至三代”的“嘉祐之治”便由此被建構出來。
反觀邵雍,其生平覆蓋了整個仁宗朝,他自己也將那個時代推許爲太平盛世:“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極矣。以前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17)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九,頁215—216。與此相應,“太平”之象在其詩集《伊川擊壤集》中更是俯拾皆是,邵雍化身爲名副其實的“擊壤老人”,在“太平世”中生老病死,在洛陽“安樂窩”裏終老此生,如:
太平自慶無他事,有酒時時三五杯。(18)邵雍《閑居述事六首》其一,《伊川擊壤集》卷四,頁237。
太平身老復何憂,景愛家園自在游。(19)邵雍《後園即事三首》其一,《伊川擊壤集》卷五,頁240。
此時不向樽前醉,更向何事醉太平。(20)邵雍《東軒消梅初開勸客酒二首》其二,《伊川擊壤集》卷六,頁262。
生長太平無事日,又還身老太平時。(21)邵雍《清風短吟》,《伊川擊壤集》卷六,頁269。
太平自慶何多也,唯願君王壽萬春。(22)邵雍《安樂窩中四長吟》,《伊川擊壤集》卷九,頁317。
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23)邵雍《插花吟》,《伊川擊壤集》卷一,頁332。
此身生長老,盡在太平間。(24)邵雍《歡喜吟》,《伊川擊壤集》卷一,頁335。
天下太平日,人生安樂時。(25)邵雍《太平吟》,《伊川擊壤集》卷一,頁337。
俗阜知君德,時和見帝功。況吾生長老,俱在太平中。(26)邵雍《自慶吟》,《伊川擊壤集》卷一一,頁362。
太平之盛事,天下之美才。人間無事日,都向洛中來。(27)邵雍《里閈吟》,《伊川擊壤集》卷一一,頁368。
太平無事日,得作白頭翁。(28)邵雍《白頭吟》,《伊川擊壤集》卷一二,頁370。
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29)邵雍《觀盛化吟》其一,《伊川擊壤集》卷一五,頁421。
太平文物風流事,更勝元和全盛時。(30)邵雍《履道吟》,《伊川擊壤集》卷一七,頁455。
而他的臨終絶筆詩《病亟吟》更以平白的詩句做出最直接的表露:
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老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
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31)邵雍《病亟吟》,《伊川擊壤集》卷一九,頁514。
而若我們進一步細究邵雍的詩集名,我們可以注意到,邵雍的“太平擊壤歌”是在伊洛之地吟唱的。邵雍之子邵伯温曾記載王拱辰、富弼、司馬光等人合力出資,爲“先君子”購置了天津橋附近的房産,並事後感嘆“洛陽風俗之厚,人物之盛,此不可見矣”。(32)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八,頁194—196。邵雍《喜樂吟》曾言“生身有五樂,居洛有五喜”,其自注云:“一樂生中國,二樂爲男子,三樂爲士人,四樂見太平,五樂聞道義;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體。”(33)邵雍《喜樂吟》,《伊川擊壤集》卷一,頁335。其中,“居洛五喜”囊括了人情、物事與風景,而所謂的“大體”,或可以“京都國大體雍容”釋之。(34)邵雍《天津閒步》,《伊川擊壤集》卷七,頁274。洛陽的園林山水與名士雅集相互映襯,使得西京士族的閒適生活成爲美談。而與堯夫的“洛社”唱和相對應,邵伯温還將元豐年間文彦博首倡的耆英會、同甲會,以及司馬光組織的真率會推許爲“洛陽太平盛事”。(35)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頁104—105。關於北宋士族在洛陽的起居生活與文化風尚,可參考程民生《宋代洛陽的特點與魅力》,《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5期,頁10—17;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構成》、《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係》、《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宋詩新貌的孕育》,載《王水照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31—197;周寶珠《北宋時期的西京洛陽》,《史學月刊》2001年第4期,頁109—116;Xiaoshan Yang, “Old Men at Home: The Rhetorics of Joy and Leisure,” in his 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 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197-242。有若干學者業已指出,開封與洛陽在北宋後期更隱然成爲新、舊兩黨的地理分野。(36)參見[日] 木田知生《北宋時代の洛陽と士人達: 開封との對立のなかで》,《東洋史研究》1979年38卷1號,頁51—85;葛兆光《洛陽與汴梁: 文化重心與政治重心的分離——關於11世紀80年代理學歷史與思想的考察》,《歷史研究》2000年第5期,頁24—37。而“洛陽名園”作爲有别於“東京夢華”的另一幅追憶圖景,其背後的歷史主體也判然有别。
二 徽宗朝:“太平文體”所打造的盛世文本圖景
相比於宋仁宗,徽宗皇帝的形象帶有强烈的個體存在感,而徽宗廟堂上歌咏昇平的應景之文在現存文獻中也隨處可見。筆者在北宋後的士人文學創作中發現,他們往往通過將歷史詩意化的表達,來形容“宣政風流”的徽宗朝盛世。從某種程度上説,“太平盛世”是徽宗朝君臣主動謀求的人爲景觀,而“豐亨豫大”之説則是觀念上的集大成者,並成爲當時朝廷的指導綱領。方誠峰進一步指出,“豐亨豫大”之説“表達了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37)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90。一言以蔽之,“豐亨豫大”意謂聖人出世,天下太平,並有聖朝“制禮作樂”的文化工程與之配套。
與“豐亨豫大”的盛世氣象相應,徽宗朝的廟堂也充斥着頌美文學,不啻爲當時的“太平文體”。“太平文體”一語出自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原指效仿徽宗朝時興的儷偶之文,而“所謂太平,則崇觀宣政時也”;(38)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748。筆者在此則借題發揮,將這一術語引申爲崇觀宣政時期所有以潤色太平爲宗旨的文學創作,故而並不局限於駢儷時文這一種體裁,而主要就其歌功頌德的功能和華麗鋪張的風格而言。關於當時諂諛文風的盛行,沈松勤、姚紅先生寫有專文,從崇寧黨禁的角度加以闡釋,(39)沈松勤、姚紅《“崇寧黨禁”下的文學創作趨向》,《文學遺産》2008年第2期,頁65—76。但鑑於其基本文獻取材自士大夫詩文,筆者在此則主要着眼於宋徽宗自身的宫詞創作以及臣僚的應制帖子詞,其與詩文的區别在於,它們作爲表達載體天然地適合於文飾“太平”。
宫詞作爲一種特定的詩歌體式,有其自身形制特點。(40)詳見俞國林《宫詞的産生及其流變》,《文學遺産》2009年第3期,頁131—139。俞先生認爲宫詞在形制上應是“七言絶句的連章”,並且多爲入樂傳唱的“歌詞”,内容上,它以當事人(無論是外臣還是帝妃)敍寫宫闈中事爲“宫詞之正體”。而宫詞的描寫性與紀事性在宋代被進一步加强,並以雍容華美的風格見長,而“風諫”之義漸少,俞國林先生將之概括爲“歌舞昇平,揄揚嘉瑞,藻飾萬物,歌功頌德”(41)俞國林《宫詞的産生及其流變》,頁136。——宋代宫詞被稱爲“太平文體”可謂實至名歸。現存的宋徽宗早期作品即以宫詞爲主,艾朗諾(Ronald Egan)對此有專文論述。(42)Ronald Egan, “Huizong’s Palace Poems,”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361-394.具體而言,徽宗宫詞多涉及宫内起居、嘉符祥瑞、御書御畫、花石綱、大晟樂等繁華空前的宫廷景觀,體現出富貴風流的皇家氣派以及“天下一人”的帝王自我形象。有的詩篇展現四方的珍貴花木被移入宫苑,如洛陽牡丹、杭越花果、江南楊梅、二浙枇杷、閩中荔枝,皆深得京都地氣,開得十分繁茂(43)如宋徽宗《宫詞》其六六:“江浙秋橙入上都,深宫培植向庭除。金丸磊磊尤珍異,均錫臣鄰侑樂胥。”《宫詞》其七三:“楊梅澤國最榮昌,此歲移來入上方。造化想知偏借力,結成繁實勝江鄉。”《宫詞》其九三:“二浙枇杷得地榮,移來丹宇倍生成。天心賦與偏繁盛,珍物由來出太平。”《全宋詩》(26),卷一四九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頁17047,17049。又,宋徽宗《宫詞》其四:“洛陽新進牡丹栽,小字牌分品格來。魏紫姚黄知幾許,中春相繼奏花開。”《宫詞》其五:“杭越奇花異果來,未分流品未堪栽。苑中别圃根荄潤,移入珍亭一夜開。”《全宋詩》(26),卷一四九二,頁17050。又見宋徽宗《保和殿下荔枝成實賜王安中》、《宣和殿移植荔枝》,《全宋詩》(26),卷一四九五,頁17071,17072。——這些奇珍異寶作爲貢物皆被安置於艮岳,而這座皇家園林更成爲了囊括天下四方景致的縮影;(44)關於艮岳在徽宗朝作爲文化象徵符號的獨特意藴,可參考James M. Hargett,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 Monumenta Serica 38 (1988): 1-48。另一些則描寫大晟樂及其引來的瑞鶴,(45)宋徽宗《宫詞》其八:“雅樂方興大晟諧,均調律吕貫三才。廣庭度曲笙鏞間,羽翮翺翔赴節來。”《宫詞》其五三:“大晟揄揚逸樂音,躬行律度革窪淫。長門羽鶴來翔舞,正雅方知上欲歆。”《全宋詩》(26),卷一四九一,一四九二,頁17048,17053。並以此作爲太平盛世的徵象;(46)藝術史學者石慢(Peter Sturman)在對《瑞鶴圖》的闡釋中便突出其“瑞應”語境,參見Peter C. Sturman, “Cranes above Kaifeng: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 Ars Orientalis, vol.XX (1990): 33-68。除此之外,徽宗對祥瑞的執迷也反映在《宫詞》中,甚至到了“瑞物來呈日不虚”的程度,(47)《全宋詩》(26),卷一四九二,頁17051。詩中又説“乾崇來上新祥瑞,幾夜黄河徹底清”,(48)《全宋詩》(26),卷一四九二,頁17053。按,此句模仿宋白於宋真宗年間創作的《宫詞》其二:“近臣入奏新祥瑞,昨夜黄河徹底清。”簡直不似人間;而佞臣們甚是知趣地投其所好,後人諷刺當年“丞相(王黼)自言芝産第,太師(蔡京)頻奏鶴翔空”。(49)劉克莊《讀崇寧後長編》其二,辛更儒《劉克莊集箋校》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230。仔細想來,徽宗對祥瑞的津津樂道恰是爲了證明自己親手打造的太平之象——“珍物由來出太平”,(50)宋徽宗《宫詞》其九三,《全宋詩》(26),卷一四九一,頁17049。超常的神奇物事也只能出現在一個極盛的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中的祥瑞實物不僅被寫入宫詞,還被視覺化爲藝術圖像: 現存的所謂徽宗御畫以花鳥作品爲主,但又與一般的花鳥畫不同,御畫多以四方進貢的奇花異石、珍禽瑞物爲描摹對象,並處處滲透着道教神仙思想,在畫風上别具一格,致使後世有“宣和體”一説。(51)“宣和體”一詞最早見於鄧椿《畫繼》卷六“花竹翎毛”一條:“李誕,河間人,多畫叢竹,筍籜鞭節色色畢具,宣和體也。”載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2),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頁713下。不寧唯是,從現存的徽宗御畫和文學創作來看,每幅花鳥祥瑞圖往往有對應的御筆題詩,(52)參見《全宋詩》(26),卷一四九五中所涉及的宋徽宗題畫詩,頁17069—17080。致使文學與書畫成爲記録反映太平盛景的雙重見證。這從宋徽宗的兩首《宫詞》中也可見一斑:
嘉禾呈瑞已爲殊,更有靈芝拱翠趺。通進剡章知異物,翻傳繪畫作新圖。(其九)
瑞物來呈日不虚,拱禾芝草一何殊。有時宣委丹青手,各使團模作畫圖。(其一三)(53)《全宋詩》(26),卷一四九一,一四九二,頁17044,17051。
此外,這些以描摹祥瑞爲能事的宣和御畫自有其政治隱喻,(54)如藝術史學者畢嘉珍(Maggie Bickford)便將宣和御畫與皇權(emperorship)相關聯,强調“御筆”是宋徽宗君主權力的象徵,藝術品則化身爲傳達政治、文化權威的外在媒介,詳見Maggie Bickford,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ship,”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pp.453-514。王應麟《玉海》記載:“宣和中,獲鳥獸草木之瑞,凡十五種,繪爲《太平睿覽圖》一卷。御撰序文、詩章,各冠圖右。”(55)王應麟《玉海》卷二“慶曆龍圖天章閣觀三朝瑞物”,上海書店出版社,1987年,頁3668。湯垕《畫鑑》的記載與之類似,而其畫册則題爲《宣和睿覽集》。(56)《畫鑑》原文如下:“當時承平盛時,四方貢獻珍禽、異石、奇花、佳果無虚日。徽宗作册圖寫,每一板二頁,十五板作一册,名曰《宣和睿覽集》,累至數百及千餘册。度其萬機之餘,安得暇至於此,要是當時畫院諸人仿效其作,特題印之耳。然徽宗親作者,自可望而識之。”湯垕《畫鑑》,馬采標點注釋,鄧以蟄校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頁44。如果説上文分析的徽宗宫詞力圖呈現文本中的昇平氣象,那麽宣和御畫則創造出圖像中的盛世景觀。周紫芝《書陵陽集後》引韓駒題御畫詩,由是云:“國家承平日久,朝廷無事,人主以翰墨文字爲樂。當時文士操筆和墨,摹寫太平紛然。如韓子蒼《題何太宰御賜畫喜雀詩》,有‘想得雪殘鳷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之句,不動斤斧,有太平無事之象,以此知粉飾治具者固不可以無其人也。”(57)周紫芝《書陵陽集後》,《全宋文》(162),卷三五二二,頁190—191。韓駒詩見《陵陽集》卷三,題爲《臣以御畫鵲示臣某謹再拜稽首賦詩》二首,其一云:“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翅(原校: 一作羽)爭巢並語時。想見春風鳷鵲觀,一雙飛占萬年枝。”其二云:“舍人簪筆上蓬山,輦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烏鵲,爲傳喜色到人間。”《全宋詩》(25),卷一四四一,頁16618。如此,無論是《太平睿覽圖》所存録的宣和御畫,還是韓駒等文人“粉飾治具”的詩篇,它們都成爲了那個太平盛世的絶佳寫照,而宋徽宗正是通過將這些藝術創作轉化爲政治—文化資本,從而達到“摹寫太平紛然”之效。
而除了歌咏昇平的宫詞及其對應的宣和御畫,宋代帖子詞亦可納入筆者所指稱的“太平文體”。(58)關於宋代帖子詞的全面論述,詳見張曉紅《宋代帖子詞研究》,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2010年博士論文。又可參張曉紅《宋代帖子詞體制考論》,《甘肅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頁89—92。實際上,有學者已經指出帖子詞與宫詞的連屬關係,王珪文集便將《宫詞一百首》與《立春内中帖子詞》、《端午内中帖子詞》等合爲一卷。(59)參見王育紅《中國宫詞觀念之嬗變》,《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頁178—179。只是與宫詞傳統不同,帖子詞是宋真宗時期初創的詩歌體裁,並屬於翰林學士的應制之作,但兩者的内容都以描狀宫廷生活見長,辭藻華麗,可見宋人是以宫詞體式來創作帖子詞的。清人趙翼言宋代帖子詞,亦稱其“莊麗可誦,見太平景象”。(60)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四“帖子詞”條,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頁484。徽宗時期的帖子詞儘管存世不多,但同樣以富貴華美著稱,故劉克莊批評周邦彦的代制帖子詞“平平無警策”。(61)劉克莊《後村詩話·後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5。一些士大夫由此不滿於這樣的“太平”風格,周煇《清波雜志》有“春帖子”一條,先抄録了司馬光的帖子詞,之後評論説:
春、端帖子,不特咏景物爲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蘇東坡亦然。司馬温公自著《日録》,特書此四詩,蓋爲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誇,殆若唐人宫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着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62)周煇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卷一“春帖子”條,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425。
不難看出,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人納諷喻於帖子的“玉堂之楷式”,恰與宣政之時“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誇”的類宫詞創作形成對比,從而不妨視爲對徽宗朝“太平文體”的抵觸與矯正。
反觀徽宗朝的文學風尚,我們不難看出,“太平文體”的泛濫實與宋徽宗“太平豐亨豫大”的政治主張息息相關,集體頌美文學的另一面恰恰是廟堂的言論禁忌,而這又來自於皇帝親手頒布的詔令,《東都事略·本紀》卷一一載:
(政和六年,1116)秋七月庚子,詔曰:“朕嗣先帝盛德大業,法成令具,吏習而民安之。休祥薦臻,四方蒙福。生齒日衆,本支蕃衍。蠻夷納土,開疆寖廣。興事造功,制禮作樂。四方之遠,人材之衆,倍蓰於前遠矣!挾奸罔上者,於太平豐亨豫大之時,欲爲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朕若稽古訓,審而後行,而施之罔極,豈有改作?蓋害成之人,敢行私智,爲臣不忠,罪莫大此。可令御史臺覺察糾奏。”(63)王稱《東都事略》,《二十五别史》(13),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頁83。
類似説法又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64)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八載政和六年(1116)七月:“詔豐豫盛時,毋爲裁損計。”下有小注:“詔戒羣臣挾奸罔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爲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榜朝堂,刻石尚書省。”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716。此外,《宋史》記載侍御史黄葆光論朝廷吏員猥雜之弊,徽宗亦答以此言。(65)見《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頁4361。又見《宋史》卷三四八《黄葆光傳》,頁11028。而無論哪種情況屬實,此語都出自宋徽宗本人無疑。
由此可見,“豐亨豫大”的論調顯然是蔡京等人爲了迎合道君皇帝、文飾“太平”而精心炮製的宣傳標語,而“太平豐亨豫大之時”的另一面恰恰是諱言時弊、道路以目,這在日後也成爲臺諫批判徽宗朝政的口實。(66)如孫覿、程瑀於靖康元年上呈的奏章,文中都批判“豐亨豫大”的施政綱領,並將新法置於“祖宗法度”的對立面。參見汪藻撰,王智勇箋注《靖康要録箋注》卷三“靖康元年(1126)二月二十六日”、卷九“靖康元年七月十日”,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86,907。到了南宋,士人更將“豐亨豫大”的徽宗朝時風裁定爲招致金兵入侵、鼎祚傾覆的直接内在禍因,逐漸成爲了歷史公論。後來朱子在論《易》《豐》卦時也順帶言及此:
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騎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羣臣創爲‘豐亨豫大’之説。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爲因陋就簡之説。’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爲,而大禍起矣!”(67)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七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860。
從很大程度上説,徽宗朝的“昇平”圖景是活在文本中的世界,而其載體正是時興的“太平文體”。宋徽宗在宫詞中便道出了其本質屬性:“六宫閒燕多餘樂,索寫新詩頌太平。”(68)宋徽宗《宫詞》其一二,《全宋詩》(26),卷一四九二,頁17050。而就其詞臣而言,“大梁詞隱”(69)見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雞漫志校正》卷二,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41。文中提到,万俟咏詞在當時極受歡迎,甚至出現了“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的情況。万俟咏日日歌吟“太平無事,君臣宴樂,黎民歡醉”,(70)万俟咏《醉蓬萊》,《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051。蔡京有聯句“君臣燕衎昇平際,屬句論文樂未央”,(71)《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賜宴聯句》,《全宋詩》(26),卷一四九五,頁17073。其子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記載當時“朝野無事,日惟講禮樂、慶祥瑞,可謂昇平極盛之際”,(72)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8。那個時代被一再地踵事增華、粉飾敷衍,以至於在文獻層面留給後人“太平盛世”的錯覺——不難想見,這些頌揚“昇平極盛”的“太平文體”不過是皇帝授意、朝臣奉命的應制之作,是人爲强行建構出來的文本世界。“慶雲翔鶴誤聲詩”,(73)晁説之《上元前再題南莊壁二首》其一,《全宋詩》(21),卷一二一一,頁13787。當時新舊黨爭背景下的政治語境擠兑了原本預留給負反饋信息的文本空間。而“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爲五季變亂裁損之計”的詔令在彼時無疑代表了道君皇帝至高無上的絶對性權威,它意味着廷臣只能書寫頌揚太平的阿諛之文,若流露一絲居安思危的諷諫規勸之意,便會被冠以“敢行私智,爲臣不忠”的罪名。如此,廟堂上當然僅剩趨炎附勢的弄臣了。是以後人感慨説:“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74)《朱子語類》卷一三,頁3129。而如若不得言危、言亡、言亂,那麽當然只有“日惟講禮樂、慶祥瑞”了。這從宣政時期的文獻上看就是一片歌功頌德之聲,以及批評諷諫一方的集體沉默,朝野上下呈現一派“醉太平”的景象,“導致了參政主體和創作主體的沉淪”,(75)參見前揭沈松勤、姚紅《“崇寧黨禁”下的文學創作趨向》,頁67。如陸游形容其時“以剽剥頽闒熟爛爲文”,並目之爲“元祐體”的反面;(76)陸游《曾文清公墓誌銘》,《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2302。朱子則批評宣政間文章“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77)《朱子語類》卷一三九,頁3307。彼時文獻也如同整個時代的風氣那樣,充斥着自我膨脹式的浮誇。
三 作爲宋人文化記憶的兩種“太平”敍事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在宋代文獻中看到了兩種“太平”敍事: 既有舊黨筆下“太平無象”的仁宗治世,也有徽宗朝“宣政風流”的“太平”景觀。事實上,南宋人不乏將宋徽宗與宋仁宗作比較的例子,前文已多有涉及,而筆者將其議論概括爲三點: 一是以仁宗之恭儉反襯徽宗之鋪張奢靡,二是借兩位皇帝討論藝術才華與治國能力的矛盾衝突,三是突出宋徽宗“天下一人”、勞民傷財的帝都中心觀,與之形成對比的則是仁宗朝天下無事、與民同樂的治世氣象——這些共識在後世也逐漸凝聚爲兩者“明主”與“昏君”的形象對照。
關於第一點,南宋初的兩部筆記可堪注意。朱弁的《曲洧舊聞》記載了劉太后開奉宸庫,勸勉宋仁宗引以爲戒:“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帑藏,今日觀之,正可爲鑑戒。若取以爲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宗垂訓之意也。”(78)朱弁《曲洧舊聞》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97—98。有趣的是,蔡絛的《鐵圍山叢談》同樣提到了徽宗朝君臣對奉宸庫的態度和處置,筆記中對宫廷秘庫如數家珍的逐一品賞,與朱弁《曲洧舊聞》的記載形成鮮明反差。《鐵圍山叢談》卷一載:“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内諸司務,在奉宸庫古親涎事中。”(79)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頁18—19。按,“在奉宸庫古親涎事中”一句似有脱誤。又見卷五:“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1114),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内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從以杖直手焉,大内中諸司局大駭懼,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内藏庫。”(80)《鐵圍山叢談》卷五,頁97。耐人尋味的是,蔡絛的兩則相關記載都聲稱“述/踵藝祖故事”,認爲宋徽宗處置奉宸庫寶物的做法是正當合理的——但事實上,“藝祖故事”卻是另一番情形: 開寶五年(972),宫内人曾勸宋太祖“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黄金裝肩輿,乘以出入”,而太祖回答説:“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8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開寶五年七月甲申”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86。“不以天下奉一人”的藝祖之訓到了道君皇帝那裏,卻成了“以自奉養爲意”,如此數典忘祖的事例讀來令人唏噓。
除了富極而奢這一點,後人在言及宋徽宗本人時,最常見的批評是他空負藝術才華而不宜治國爲君。王士禛《池北偶談》中有一則筆記題爲“仁宗徽宗”,便將這兩位宋代皇帝作比較,而其切入點就是藝術與治國的無法兼容:
元臣巙巙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爲君耳。”《炙輠録》記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此語在巙巙之前,可謂絶對。(82)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02。
而筆者發現樓鑰有詩《題林宗魯校書所藏宣和御畫》,説的也是同一層意思:
周公多藝孔多能,徽廟才高更倍增。除卻萬機都不會,至今遺老話昭陵。(83)樓鑰《題林宗魯校書所藏宣和御畫》,《樓鑰集》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48。
此詩巧妙地將徽宗與仁宗作對照,更以仁宗的善政否定了徽宗的才華。儘管宋徽宗給後人留下了瘦金體書法、宣和御畫等藝術瑰寶,堪稱史上獨一無二的才子皇帝,卻也因此被後人視爲玩物喪志的昏君,如王夫之即感慨説:“徽宗如彼也,蔡京如彼矣,蔡攸、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時人士相趨以成乎風尚者,章醮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畫也。清歌妙舞,狹邪冶遊,終日疲役而不知倦。”(84)王夫之《宋論》卷八《徽宗五》,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54。這倒也契合了宋太祖對李後主的評語:“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85)蔡絛《西清詩話》卷中,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04。而後世的通俗故事甚至將宋徽宗視作南唐李後主轉世。(86)如馮夢龍《醒世恒言》中載《勘皮靴單證二郎神》,其開篇即言:“北宋太祖開基,傳至第八代天子,廟號徽宗,便是神霄玉府虚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這朝天子,乃是江南李氏後主轉生。父皇神宗天子,一日在内殿看玩歷代帝王圖像,見李後主風神體態,有蟬脱穢濁、神遊八極之表,再三賞嘆。後來便夢見李後主投身入宫,遂誕生道君皇帝。”見馮夢龍《醒世恒言》卷一三,1627年金閶葉敬池刊本,葉1a—1b。歷史的反諷總是引人深思。
然而,最近的學術研究則更傾向於將宋徽宗的藝術成就與他的政治佈局勾連在一起,並指出當時耗費巨大的文化工程無疑是其政治“盛世”圖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方誠峰即强調徽宗“御筆”、京師土木工程與祥瑞體系的政治象徵意義;(87)詳見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相關研究又可參見前揭Bickford, “Huizong’s Paintings”;以及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譯本參見[美] 伊沛霞著,韓華譯《宋徽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包弼德(Peter Bol)則將宋徽宗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稱號與自創的“天下一人”花押視爲“君主獨裁的一種形式”。(88)Peter K. Bol, “Emperors Can Claim Antiquity Too: Emperorship and Autocracy Under the New Policies,”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pp.173-205.實際上,徽宗朝的宫廷文化藝術强烈地輻射出當時的帝都中心觀: 一面是祥瑞珍寶、奇花異卉從四方進貢内廷,“從今閉向深宫裏,莫學江湖自在開”;(89)吕本中《邵伯路中逢御前綱載末利花甚衆舟行甚急不得細觀也又有小盆榴等皆精妙奇靡之觀因成二絶》其二,《東萊詩集》卷六,載《東萊詩詞集》,合肥,黄山書社,1991年,頁88。一面是三舍取士法、玉清神霄宫、大晟樂等禮樂制度自中央向地方全面鋪開。(90)相關研究可參考Patricia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Shin-yi Chao, “Huizong and the Divine Empyrean Palace Temple Network”; Joseph S. C. Lam, “Huizong’s Dashengyue,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dom”;載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pp.229-274, 324-358, 395-452。這根本上反映了宋徽宗及其臣僚“以天下奉一人”的聚斂心態,或即所題“天下一人”的密意。蔡京曾形容宋徽宗乃“人主主人翁”,(91)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記事”“對徽宗詩句”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359。可見整套政治文化工程的主導動機來自於那位風流天子的强烈個人意志。
與積極發揮“主人翁”精神的宋徽宗不同,“百事不會”的宋仁宗在他四十二年的主政時期看似無足稱道,卻在日後被反復追念。南宋年間流傳着一首題寫於宋仁宗永昭陵寢宫旁的無名氏詩,它最早見載於吴曾《能改齋漫録》,又數見於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阮閲《詩話總龜》、陸游《家世舊聞》等南宋文人筆記中,足見其流行程度。詩歌本身則反映了時人對仁宗的理想化追念: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92)《能改齋漫録》卷一一“記詩”“題寢宫詩”條,頁305。
此詩頭兩句的基調不禁讓人想到歐陽修爲宋仁宗所寫的《永昭陵輓詞三首》其三:“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93)歐陽修《永昭陵輓詞三首》其三,《居士集》卷一三,洪本健《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16。相應地,詩中的民生“不擾”、邊事“無功”、吏治“不能”,似乎着力於刻畫一個“無爲而治”的君主形象。最後,此詩也出現了“夢覺”一詞,但已非宣、政事盡的“東京夢華”,而是“太平無象”的後知後覺,乃至“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無知無覺。
誠然,宋人對仁宗朝的贊許不外乎太平日久、海内晏然、百姓安樂,以及培育出一批以天下爲己任的士大夫。王啓瑋便着眼於慶曆士大夫在地方如何作爲百姓與皇帝之間的溝通紐帶,造成“郡必有苑囿與民同樂”(94)談鑰《嘉泰吴興志》卷一三“苑囿”條,載《宋元方志叢刊》(5),頁4739。的景象,並將之等同爲“太平之效”。(95)王啓瑋《論北宋慶曆士大夫詩文中的“衆樂”書寫》,《文學遺産》2017年第3期,頁68—80。與宋徽宗時期朝臣的頌美文學不同,仁宗朝士大夫位居廟堂之時則發出憂患之辭規諫君主,而身處江湖的時候,卻用文學渲染出天下無事的衆樂治世景象——而文風本質上可説是當時士風的風向標。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後世的通俗文學中,兩位宋代皇帝的形象也有鮮明對照。《大宋宣和遺事》前集開篇歷數自古以來的無道君主,有夏桀、商紂、周幽、楚靈王、陳後主、隋煬帝、唐明皇,之後緊接着便是宋徽宗:“今日話説的,也説一個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96)《新編宣和遺事》前集,《士禮居黄氏叢書》本,揚州,廣陵書社,2010年。而日本學者澤田瑞穗指出,後世包公案説唱詞話的開場白常有“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的套語,(97)澤田瑞穗《「四帝仁宗有道君」—明代説唱詞話の開場慣用句について—》,《中國文學研究》第4期(1978);中譯文見澤田瑞穗著,前田一惠譯《“四帝仁宗有道君”——論明朝説唱詞話的開場套語》,載《中國古典小説研究專集》第3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頁69—87。可見在後人眼中,宋仁宗在位之時無愧爲太平盛世。
宋人之所以能夠平行建構出以宋仁宗、宋徽宗爲代表的兩種“太平”敍事,正得益於一種帶有“詩性智慧”(mythopoeic)的“文化記憶術”。人類學家揚·阿斯曼(Jan Assmann)開創了“文化記憶”(kulturelle Gedächtnis/cultural memory)理論,(98)參見[德] 揚·阿斯曼著,金壽福、黄曉晨譯《文化記憶: 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5—46。又,關於上述“集體記憶”的兩種類型,詳見該書第一章《回憶文化》第二節《集體回憶的形式——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頁41—61。而文化記憶本身介乎個體遭際與宏觀歷史之間,“元史學”也早已解構了所謂絶對客觀、真實、權威的歷史編纂,而揭示出任何歷史書寫背後的權力操縱及其“情節化”(emplotment)的敍事機制,(99)詳見[美] 海登·懷特著,陳新譯《元史學: 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可惜世人大多“只知詩具史筆,不解史藴詩心”。(100)錢鍾書《談藝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頁104。正是宋人的文化記憶完成了對北宋歷史的情節化建構與焦點轉换,才出現了後人對北宋盛世的事後反思與理想化追述,而南宋人的紀事詩文與歷史書寫便是其表達媒介或曰“編碼”。作爲“太平”敍事的執筆者,宋代士大夫或許最終掌握了比君主更大的話語權,在把本朝歷史升格爲“太平世”的同時,也將褒貶之辭隱含在“詩史”紀事與“春秋史筆”之中,流傳於後世任人評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