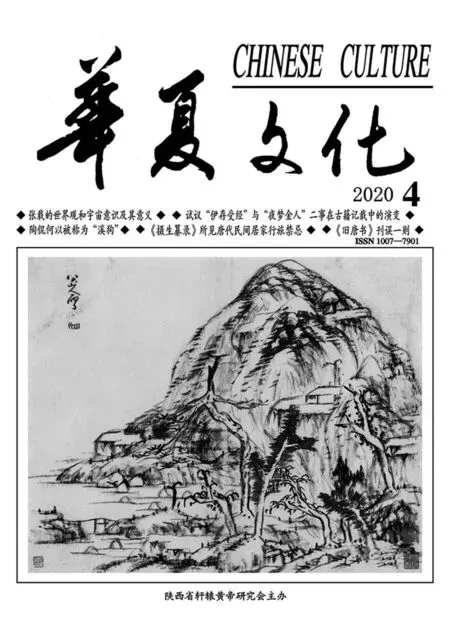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周代“封建”再论
□刘 黎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历史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载体作用。周代的“封建”对其以后中国历史中关键的“宗法—家族”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精神要义。
一、政治统治意识的转变
牧野之战“小邦周”革“大国商”之“天命”,但随后武王之弟管叔、蔡叔与殷商遗臣、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三监之乱”,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周公平定叛乱后,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亲情不可靠的结论。周公“制礼”,摒弃“亲亲之议”,向“尊尊之议”转变,“尊尊之议”即君臣双方订立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分散的、在具体场景中制定的诰命契约文书,最终实现了周的天下构造原理的转变。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进行了再次分封,此次分封与武王分封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周公主导的第二次分封是通过文书的形式进行的,即“册名为制”,如围绕册封康叔为卫候,以周公为核心的周王室发布了三道文书,即《康诰》《酒诰》以及《梓材》。君臣之间产生一个类似于“诰”文体的文书,文书中不带有血缘关系的感情色彩,在这种文书中所体现的是康叔治理卫国的权力是周天子赐予的,体现了臣下对天子“敬”的态度。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里的“文”即册名文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文书的形式确立的,这是周文明相较于夏商文明一个质的跃迁。这使得周的君臣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熟人社会(血亲氏族社会)的“陌生化”,这是人心智的一种巨大飞跃。这种变化推动了整个“君子”(精英)群体内部君臣关系的文书化,这样的文书化造就了礼制的完善。周文明的最高成就或深层的核心是“礼”,周代通过“册名”分封诸侯,制定出一整套关涉君臣权利和义务的规则体系,“礼”是一整套系统完善的律法体系。
周代各诸侯国都有“春秋”,即历史记载,“史”所存的不是简单的档案文书,而是相当于现代意义下实体化的法律汇编。天子以史为其顾问,“礼”最后不能自我执行就会出现“以兵为刑”的局面。周代的军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野战军队,换言之,战争就是司法活动,有一系列的规则。“礼”相当于一种习惯法的自我执行,即礼的基本作用是确定君臣的权利和义务,并予以保障。
二、差序格局下的君臣关系
周天子和诸侯之间并不是后世那种绝对的君臣关系,周人通过文书建立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上人与人关系的巨大飞跃,治理秩序的可扩展性也是空前的。一般研究认为,“封建”包括土地和名位,土地在周以后的“封建”中是首要因素,但在周的“封建”中,“名位”是首要因素,周的君臣关系是一种多中心的差序格局。商代有频繁的国都迁徙现象,周代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商的数次迁徙没有导致其“亡国”,周代郑国最初被分封于关中一带,其后迁往河南,鲁国最初在河南,后来迁到山东,这表明“封建”制度下社会组织形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周天子有三重身份,即天下第一大夫、天下第一诸侯和天子,诸侯、大夫在封地内亦如此。君向臣提供名位和保护,臣的义务一是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二是在京畿任职,辅佐天子。差序格局的结构使得周天子对天下事务做出决断时要征得诸侯的同意,社会权威呈现出分散性。周“封建”的根本特征是共同主义,故有所谓“共和行政”的历史现象,但君臣间是有等级差异的,不得僭越礼制。在君臣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既是理性的,也充满情感。君臣之间的关系,即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任何一方享有权利的前提是履行对对方的义务。一个君要享有权利,必须履行对臣承担的义务,否则,臣可以解除对君的效忠。周的“封建”下君臣关系是分层次的。
三、政治统治原则:“敬德”与“保民”
商亡周兴,周公得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的政治观点。商前期的繁荣稳定是因为“……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尚书·君奭》)商的灭亡则是因为德行的丧失,为了体现周王室的德行,周公做出“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尚书·多士》)的政治决策。所以,还特地凸显了周王室先祖的德行,“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尚书·康诰》)。周公这是告诫卫康叔要以商不重德行而亡的教训为鉴。
以商亡为诫,周公虽然表示仍要“敬天威”,但更要重视“尽人事”,强调贤能之人对王朝兴亡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尚书·君奭》)这就把商代统治者所谓的“天命论”思想彻底推翻,强调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即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因为在武王伐商战争中,商王军队中大批奴隶临阵倒戈,这让周公感到了民众的巨大威力,所以,“保民”构成了周公德政思想的核心。在《尚书·康诰》中,他对康叔提出“……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书·多士》)的要求。
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基本上贯穿着周以来的保民传统,汉初,“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汉书·刑法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中有:“……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末尝不背也。”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精髓所在。
五、周代“封建”的演化
周的宗法制分封,实现了政权、族权和神权的三合一。周的“封建”不能简单地以西方历史文化的框架进行生搬硬套,要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进行具体的研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周代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封建”已不能在思想文化和制度上管理疆域庞大和人口众多的大帝国。在周代的“封建”结构下,最有实力的是大夫阶层,在这种权力框架下存在着一个权威下移的现象和过程,所以出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现象。公元前221年,秦的建立采用了李斯的郡县制建议,摒弃了封建制。但在技术没有突破或展开的情况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帝国治国的主要原则是以道德笼罩于其政治框架之上,企图使全国以一种均衡和相似的姿态进行“静止”的统治,所以,“封建”的形式还是不同程度地在被各个王朝开国初期所采用,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调适与过渡的需要。周的“封建”经历秦汉的发展,从“名位”转向“土地”,是为了适应“小国寡民”社会向大一统帝国转型的需要。
周的“封建”在战国的金戈铁马声中走向了终结,秦建立后采纳李斯的郡县制建议,但秦历二世而亡。汉兴刘邦再次进行分封,实行郡国并行的治理格局,到汉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汉武帝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行“推恩令”,封国又变成了郡国。西晋大封同姓宗室,结果爆发了“八王之乱”,大一统的格局就此中断,引发了持续三百年之久的大动乱,大量汉族人南迁,成为引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南迁的开端。唐代安史之乱后推行的变相分封——藩镇,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唐一百五十余年的国祚。明初亦实行了大规模的分封,但朱元璋去世后朱棣发起“靖难之役”,推翻其侄建文帝后亦大力削藩,分封制最终淡出历史舞台。
六、封建—宗法与家族:现代化的社会基石
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对周代“封建”的再认识,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政治一统、文化多元进行深入理解,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促进各民族间文化心理层面的信任,加强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西方自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契约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质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外剥削、发动战争的恶果,时至今日,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周代的“封建”是建立在人文关怀之上的文书契约关系,既具有理性精神,又充满了人文关怀。
周的“封建”与后世“封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周“封建”的核心是建立在一种相对平等的文书契约关系上,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后世的“封建”则是一种纯粹的赐予与接受,强调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周代的宗法制得到儒家的大力发扬,从两汉的世家大族到宋明的宗族都是宗法制的演化结果,即社会结构不断下沉形成平民社会,平民社会所形成的家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石。
七、结语
运用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的思想框架研究中国历史,才能对中国历史做出客观、具体的研究,而不能以西方的历史文化理论简单地套用于中国历史文化上。否则,无法对中国历史文明做出清晰的认识,也就无法对中国历史文明来自何处——发展状态如何——将要去向何方形成一个系统和客观的认知和理解。周代的“封建”是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重要原点所在,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对周代“封建”的再认识,对明确中国历史和文明本身的形成、发展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