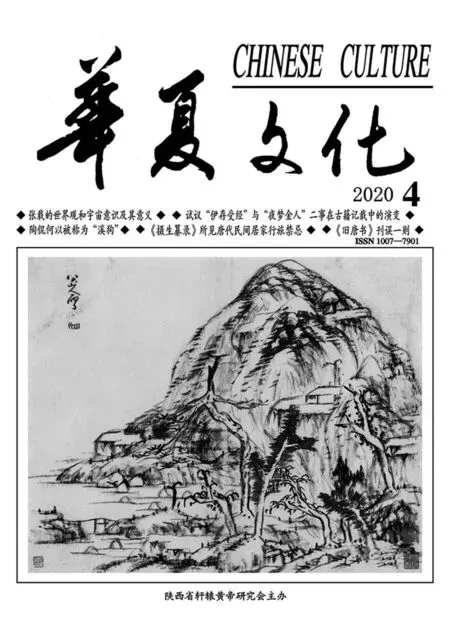试议“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二事在古籍记载中的演变
□卢克寒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先生曾与陈垣先生就《四十二章经》是否为汉代译本,“浮屠”与“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四十年代,季羡林先生则在《浮屠与佛》一文中指出,伴随着西域各国的佛教人士进入中土,汉末三国时期应是“浮屠”一词转为“佛”的关键时期。之后,很多学者陆续围绕着《浮屠经》的语源、佛教具体传入中国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而事实上,这些问题都与“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这两条关于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史料紧密相关。
一般认为,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夜梦金人,从而促生了派遣诸使出使西域拜佛求法之事,从此佛教得以在中国流行。但裴松之注本的《三国志》曾引《魏略·西戎传》所言:“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闲、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汉哀帝元寿元年为公元前2年,距汉明帝永平年间已去六七十年, 足见在汉明帝夜梦金人之前,佛教已经在汉王朝的统治下进行传播了。况且,汉明帝夜梦金人这一说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夜梦金人”一事是否为真,在学界仍有一定争议。不仅如此,后世诸多典籍对于“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二事的记载也多有不同,极有可能存在引据与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的情况。在此,本文拟从诸典籍对于二事的文本记载入手,梳理“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的原始史料出处,并通过此二事在古籍中的文本演变,分析佛教典籍对于正史记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
一、汉明帝夜梦金人真伪考
一般认为,关于汉明帝夜梦金人一事最早记载于佛教典籍《四十二章经》。吴焯先生曾在《汉明帝与佛教初传——对于中国佛教史一段历史公案的剖析》中梳理讨论了隋以前关于汉明帝感梦求法一事的著述,并倾向于认为《四十二章经》应是最早记录明帝夜梦金人的典籍。其文中提到有学者认为袁宏《后汉纪》应是最早记录其事之书,《四十二章经》系晚出。事实上,这种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可能性,本文在此不做赘述。但是《四十二章经》中关于汉明帝夜梦金人一事的记载,确应是永平之后的佛教徒另加增补润色过的。
下文为《四十二章经》中对于汉明帝夜梦金人一事的记载: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金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建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四十二章经》)
大致来说,上述记载有三处值得商榷,也正是这三个问题使得汉明帝夜梦金人一事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首先,张骞出使西域是西汉武帝年间之事,此处记载明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应为误作,而《出三藏记》中的记载与《四十二章经》中所记基本相同,应是直接对《四十二章经》进行抄录所致。
其次,根据《后汉书》中对于傅毅的记载,“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后汉书》卷八十),显宗是明帝之庙号,这段史料说明了在孝明帝时期,傅毅应是十分不得志的,故而作《七激》诗来劝谏明帝。而时至汉章帝时,傅毅才被授予兰台令史等职。因此,傅毅又怎可能于永平年间在明帝面前回答佛事呢?在此基础上进行推断,永平年间的傅毅应尚处于在政治上默默无闻的时期,其才华也并未被明帝发现。而《四十二章经》的记述之所以引傅毅为明帝回答西方佛之事,是因为其当时已在文学与政治方面有了一定的影响。足见这段文字并非记于永平年间,应是明帝之后伪作。
再次,《后汉书》对于明帝所派遣之秦景、王遵等人未有任何记载。既无其本人列传,也未见其出现于他人传述当中。按照《四十二章经》的记载,秦景既是汉羽林中郎将,又承担着出使大月氏的国家大事,本应在正史中有所记载。而《后汉书》对于担任羽林中郎将者的记载仅有耿弇、冯鲂与桓典等几人,《汉书·西域传》中在谈到汉明帝夜梦金人一事时也仅仅说之后“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后汉书·西域传》),并没有任何关于秦景的记载。因此,秦景其人存在的真实性也有着很大疑问。
综上所述,汉明帝夜梦金人之事在发生时间、在场人物多个方面都有着值得商榷之处。而《四十二章经》又是传入汉地的第一部佛教经典,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夜梦金人一事是否是佛教徒为了借助皇权提高佛教地位而编造出来的。此外,在《四十二章经》之后,“夜梦金人”开始更多地出现于史料里,并逐渐与汉哀帝时期的“伊存受经”一事相结合,广泛地出现于正史与佛教典籍对于佛教初传入中国的记载之中。
二、“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在正史与佛典记载中的演变
前文已经提到,“伊存受经”一事最早载于《三国志》引鱼豢著《魏略·西戎传》。《魏略》的成书年代在三国时期,较《三国志》更早,且该段记载出自鱼豢对于西域记载的章节,并无任何主观捏造的动机,其记载应比较可靠。但由于《魏略》原书已佚,因此对于《魏略》其书的考证便十分重要。
从体例上看,《魏略》属于鱼豢编著的私史。《史通》记载:“魏时京兆鱼豢,私著《魏略》,事止明帝”,又说其“异闻间出,其流最多”。可见《魏略》在刘知几眼中的史料价值不如其他官修史书。同时,《法苑珠林》、《法显传》等佛教经典也曾引《魏略》之记载。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质疑《魏略》关于“伊存受经”一事的记载呢?事实上,根据清代史家的辑佚,《魏略》记载确多异闻,然其异闻多关于魏国皇室贵族,如《法显传》引《魏略》载许攸称曹操为“某甲”一事,便属于典型的异闻,难知其真假。但《魏略》在《西戎传》中对于西域各国的记载却应是最具有史料价值的。首先,鱼豢所处的年代,对于西域风土的记载并不会被政治所干扰,也不涉及作者忠于司马氏或曹氏的立场问题;其次,虽然引用《魏略》的典籍多而杂,包括《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史料,以及《法苑珠林》等佛教史料,但其引用大多是关于西域的记载。尤其是对于佛典而言,对于流传既广史料的引用有助于使佛教的传播更具有真实性。例如《法苑珠林》就在其《感应缘》篇援引《魏略》作为说明迷迭香产自大秦的佐证。这足以见得《魏略》对于域外各国的记载广为人所接受,无论史家还是释家。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相信《魏略》对于“伊存受经”一事的记载。
如果说《魏略》与《四十二章经》中的记载分别是“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的原始史料来源,那么后世所见的对于该事的记载应皆出于此。但是在历代史官转引的过程中,对于二事的记述开始逐渐与原始材料发生偏差。按照时间线索梳理,北齐人魏收所著的《魏书》作为距《魏略》时代较近的正史,首次将“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两事以时间先后顺序合于一起被录于《魏书·释老志》一篇之中。如下则引其原文:
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魏书·释老志》)
与《魏略》之记载相比,《魏书》虽承认“伊存受经”之事的真实性,但是却认为此时的佛教尚未对中土文化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魏略》中的“景卢”之名已被记作“秦景宪”。而在之后对于“夜梦金人”一事的记述中,《魏书》则说“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与《四十二章经》中的记述相比,《魏书》虽然删去了有着明显纰漏的“明帝使张骞出使西域”一节,但是所谓的“郎中蔡愔”同样并未出现于《后汉书》的记载中,而秦景的形象也已经由羽林中郎将转变成了博士子弟。
《隋书》对于二事的记载大体与《魏书》相似,但却将《魏书》中的“秦景宪”误作了“秦景”。这导致《隋书》对于“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的记载中出现了两个“秦景”,一个是哀帝时期的博士弟子,另一个却是明帝时期出使天竺的使者。很明显,哀帝元寿年间至明帝永平年间存在着六七十年的跨度,两个秦景必不可能是同一人,存在讹作的可能。
相较于正史中的记载,佛教典籍对于明帝“夜梦金人”一事的记载大致与《四十二章经》相同,其中纵有些许出入,也大多集中于秦景“博士弟子”或“羽林中郎”的身份分歧上。值得注意的是,纵观对于“夜梦金人”一事记载的佛教典籍,皆以汉明帝永平求法一事为佛教之初传,而并不对“伊存受经”有任何记述(该类佛教典籍有《高僧传》、《法苑珠林校注》、《出三藏记》、《释迦方志》等)。
根据上文,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正史中对于“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的记载之所以会出现较大程度的变化(如最初将景卢讹作为秦景宪,后又讹作为秦景),很明显是受到了佛教典籍的影响。《四十二章经》作为最初记载“夜梦金人”一事的典籍,是后世史家在编纂佛教史时所必不能忽视的。从正史文献的演变上来看,“伊存受经”的主人公“景卢”频繁被史家冠以不同的名称,但“秦景”出使大月氏却成为了大多数史料的共识。这不仅说明正史在编纂时可能受当时佛教经典的影响,似乎也可以推测,“夜梦金人”一事在史家编修史料时拥有更多的材料支持,并被更多的人所认同。而“伊存受经”一事因为古籍资料记载甚少,因此在史料编修过程中才会经常被误作,并出现将“秦景”之名“张冠李戴”于“伊存受经”一事之中的情况。
三、正史与佛典记载异同之原因
中国古代的史家修史以力求真实为准则,而佛教典籍的集成目的则以传播教义为核心,故而其对于同一件事的叙述重心也必不相同。可以看到,“夜梦金人”一事在佛教文本最初的记载中出现了诸多不符史实的记载,但是后世史家却仍援引如旧,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帝遣使出使西域应确有其事,而《四十二章经》中对于“夜梦金人”的描述则更多地带有神话色彩。总体来说,汉明帝时期应确实出现过一次以汉王朝官方为主导的出使西域的事件。但由于正史与佛典在书写侧重等方面的不同,才使得对于佛教初入中国的记载出现众多版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教众与寺院数量增长迅速,佛教发展可谓空前兴盛。太和四年,在北魏当时的都城大同就已经有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魏书·释老志》)。这还未包括“四方诸寺”的僧尼人数,足见其当时佛教之兴盛。与此同时,魏晋至隋唐佛教典籍的编纂也如雨后春笋一般,《高僧传》、《弘明集》、《历代三宝记》等佛教著作的相继问世,进一步扩大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为了给佛教的传播铺陈道路,佛家在叙述汉明帝“夜梦金人”一事时往往愿意将明帝塑造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形象。但事实上,《后汉书》中明确崇信佛教的楚王刘英最终因谋反被明帝处死,而佛教在明帝时期也并未获得长足的发展。即便如此,“夜梦金人”的传说仍然给了佛教徒很大的发挥空间,以至于在很多佛典中会出现诸如明帝遣张骞出使西域之类的谬误。且从内容上看,“夜梦金人”一事不仅故事性远胜于“伊存受经”,还更有益于佛教利用皇帝的影响力,更能够达到传播佛教的目的。因此,佛教典籍也便更愿意以明帝遣使求法作为佛教初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同时,《魏略》作为“伊存受经”的唯一史料出处,所叙述的仅仅是博士子弟与佛教发生的关系,并没有记录皇帝与汉王室对其的回应,甚至此事是否为皇帝所知都难以明确,且口授佛经直接导致佛经的内容并没有明确的书面记载。而“夜梦金人”一事,不仅使《四十二章经》最终作为求法的成果被保留了下来,还兴建了洛阳白马寺。因此即使《四十二章经》中的记载有诸多与史实不符之处,却确实提升了“永平求法”一事的可信度。最终,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正史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记载也只能大部分采信佛典的说法。
四、结语
“伊存受经”与“夜梦金人”作为佛教传入中国早期阶段的文化现象,深刻地烙在了中国佛教史上,也为后学研究佛教初传中国提供了重要材料。虽然从史学的角度上讲,斯人已逝,往事千年,我们很难根据现有材料去考据事件的真伪;但从文化意义上说,二事在后世的流传加深了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加速了汉地佛教的形成,积极地促成了以儒家基本精神为内核的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因此,无论是史家还是释家对于佛教初传的记载,客观上都对佛教文化向内渗透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