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期来华留学生微信群会话语码选择的统计分析
余一骄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湖北武汉,430079)
前言
生活在沉浸式的汉语环境中是长期来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突出优势。除了面对面的汉语交流,留学生还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开展交际活动。汉语国际教育研究者先后从如何利用微信平台辅助汉语教学、调查留学生网络交际中如何使用汉语等角度展开了研究。第一类研究注重通过微信平台,给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推送学习资源,要求学生按时提交作业、共享学习经验,从而提高汉语学习效率[1];或要求留学生在微信群里提交口语作业,安排助教在群里及时对口语作业进行点评,促进留学生准确地使用汉语词汇和语法[2]。第二类研究注重分析留学生的微信交际语料,统计他们使用汉语、英语等不同语种发言的频次,分析其语码选择的优先级。由于收集大规模微信会话语料比较困难,已有成果中所观察的留学生数量较少,语料规模偏小,例如有的研究只对两名留学生的298条语料进行了分析[3]。被观察对象太少,不利于反映更多留学生使用汉语的特征。
语码是指人们用于交际的任何符号系统, 它既可以是一种语言, 也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4]。言语交际中,会话人使用何种语码,通常是出于特定的心理动机与交际目的,而不是随意选择。在微信会话中,汉语与英语混用,文本与图像、动画表情、音频、视频混用都极为常见。长期来华留学生是典型的多语者,他们在微信交际中更是存在汉语、英语、韩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混用的现象[5]。研究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微信会话中的语码混用现象及语码转换动机。例如,为何动画表情在微信会话中被高频使用[6];大学生用户使用汉语、英语中不同语体的词汇、句法的动因等[7]。来华留学生在微信会话中是否积极运用汉语、是否频繁使用汉字、什么时候可能使用学生的母语等语码选择态度,值得长期观察、定量分析。
2018年,30名来自东南亚、东亚、中亚、东欧、中美洲的留学生来到武汉某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8年9月,他们建立了一个班级内部的微信群,用于开展班级内部、非面对面的交流。本文研究的语料是自该微信群建立之日起,至2020年3月的聊天记录。通过统计分析来华留学生为期一年半的微信群会话语料,期望揭示更多关于留学生在网络交际中运用汉语的特点。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统计留学生使用文本方式、非文本方式的发言次数,分析留学生对多模态发言方式的选择偏好及对中国网络交际文化的适应程度;第二部分研究留学生在什么语境会选择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会话;第三部分讨论留学生对汉字和拼音的选择偏好;最后总结全文。
一、文本方式与非文本方式的选择
针对来华留学生汉语运用状况的研究大多是依据文本语料,例如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的语料。微信允许用户使用文本、图像、动画表情、视频、语音、地理位置、红包、名片等多种方式进行交流。在微信会话中,文本方式并不是用户发言的唯一选择。因此,首先有必要了解留学生到底是趋向使用文本方式进行交流,还是非文本方式进行交流。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留学生在该微信群发言3221次,其发言方式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非文本方式发言频繁,但文本方式发言还是占绝大多数。留学生以文本方式发言2280次,占总次数的70.79%;以非文本方式发言941次,占总次数的29.21%。非文本发言方式包括图像、动画表情、红包、地理位置、网页等,但没出现视频、语音方式的发言。余一骄 统计了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期间42个微信群(群内成员均为中国人)的会话语料,发现其中使用文本方式发言的占比为82.96%,使用非文本方式发言占比为17.04%[8]。29.21%与17.04%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可知,这30名来华留学生比以上中国用户更乐意使用非文本方式发言。
在微信交际中,夸张、搞笑的动画表情使用得特别频繁。设计有创意、有吸引力的动画表情和图像已成为一门产业,微信用户可以购买独特的动画表情,部分微信用户甚至还有斗图行为。留学生们在微信群里特别喜欢发动画表情、图像。对他们而言,利用动画表情、图像等来回应其他人的发言,不仅可以省去思考语句、输入汉字等较为繁琐的操作过程,还有可能因为动画表情、图像的内容夸张,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但利用动画表情、图像等方式发言,其交流内容极为受限。发言者如果只需要简单地表明赞扬、感谢、佩服、羡慕等态度,用动画表情、图像等方式来发言,交流效率会很高。但如果是咨询学习或生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还是得依赖文本方式交流。文本方式发言不会被非文本发言方式完全取代,它依然是微信群成员之间完成最有价值信息传递的首选方式。
第二,来华留学生在微信群里频繁发动画表情,较多地发微信红包,反映出他们较好地适应了当代中国的网络交际文化。在传统风俗中,亲友之间大多是节日期间才面对面地发红包。自从微信提供在线发红包功能之后,随时都能一对一或一对多地跨地域发红包。30名留学生来中国不到一年,却在群里累计发了25次红包。留学生发红包的具体时间分布如下:2018年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发了15次红包,并产生7次与红包有关的会话;2019年中国农历春节期间,尽管大多数留学生都回国度假了,但仍在群里发了9次红包,并产生2次与红包有关的会话;2019年清明节发红包1次。发红包及讨论红包的学生来自东南亚、东欧、东亚等地的多个国家。平安夜、圣诞节是国外的节日,来华留学生中利用发红包来庆祝,比较容易理解。春节期间,留学生也发红包来庆祝,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春节风俗有较多了解,但清明节在群里发红包就不大符合中国的风俗。用户在选择自己的网络交际语码时,往往会主动顺应网络交际环境。留学生乐意在群里发红包、使用动画表情等非文本交际方式,是对当前中国网络社交模式的主动顺应。
二、汉语与留学生母语的选择
来华留学生较多地利用多种语言在微信朋友圈进行交流。在本文研究的留学生微信群文本会话中,既有完全用英语、泰语、越南语、俄语发言的现象,例如“Thank you 3 time”,也有汉语与英语、泰语、越南语等外语混用的现象,例如“OMG 海底捞昨天我还说想去吃”。在2280次文本发言中,留学生独立使用母语发言30次,使用汉语与母语混合发言3次,二者合计33次,仅占文本发言总次数的1.45%;有172次发言是用阿拉伯数字(常用来描述电话号码)、英文字符(常表示英语句子、汉语拼音等)或其他非汉字符号,占文本发言总次数的7.54%;有2075次文本发言使用汉字来表述,占文本发言总次数的91%。“语言和语言使用的语境之间是一种相互顺应的关系;语言选择塑造着语境,同时也被语境所塑造。”[9]该微信群里会话的主题大多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相关,全体留学生都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语境与汉语水平共同决定了汉语是该微信群交际的首选语言。
虽然母语为泰语的学生在群里占比为53.3%,但纯泰语发言仅12次;母语为越南语的学生占比为20%,纯越南语发言16次;母语为俄语的学生占比为16.7%,纯俄语发言2次。母语是波兰语、韩语、西班牙语的学生均只一个,可能因为缺乏与之交流的同伴,于是没有出现使用波兰语、韩语、西班牙语的发言。用泰语、越南语发言的次数相对较多,且集中出现在少数话题中。话题1是一次关于寒假回家购买机票的讨论,其中出现了5次越南语发言。话题1至话题4括号内的中文句子是对学生外文发言的翻译。本文所列举语料中的汉语发言是留学生的原始发言记录,笔者未对其中的汉语表述错误进行更正。
话题1:
F:我想问一下
F:有没有人订票回国了?
F:怎么我不能支付呢?
T:我定了~
T:可是我有公司买机票
F:外国的支付宝不能支付吗?这么奇怪呀?


F: Uhh chs í(嗯,我也不懂)
F: Okiee(好的)
B:去哪儿网好像可以支付
F:我刚试试定在淘宝也不能了
越南留学生F在网络上购买机票遇到困难,于是在群里提问。泰国学生T选择使用汉语进行回答,但未有效解答其提问,于是F继续用汉语追问。在第4个话轮,越南留学生W用越南语回答F用汉语提出的问题。能否顺利地买到机票,对F很关键。F和W用共同的母语来表述会更准确、高效。第5至第8个话轮均使用越南语,是F和W相互顺应对方的语码选择结果。第9个话轮中的“Okiee”不是规范的越南语,而是越南人用英语开玩笑的说法。学生B在第10个话轮参与讨论,虽然他也是越南学生,但他使用汉语发言,F随即改用汉语对B进行回复。F不断顺应其他发言者的语码选择,这既显示出她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又是顺应论在留学生语码选择中产生作用的例证。
话题2:
F:有没有人知道如果坐飞机超过公斤要加多少钱?
D:比提前买贵五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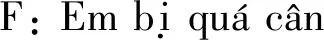



在首个寒假回越南前夕,话题2中的越南学生F用汉语提问“有没有人知道如果坐飞机超过公斤要加多少钱”,该提问的汉语表达不够清晰,不容易确定F是想了解“行李超重时,是否需要额外收费”还是“对行李的超重部分,按什么资费标准进行收费”。在第2个话轮,她的越南同胞D用汉语回答“比提前买贵五倍”,是对行李超重部分的资费标准的回答。无论是第1个话轮的提问,还是第2个话轮的回答,其汉语表述都令人费解。可能F和D都感受到了用汉语来表述自身不太熟悉的内容,交际效率低,于是在第3至第8个话轮中,F和D利用越南语进行交流。他们用越南语对话,虽然每次的发言都很简短,却帮助F知晓了关于行李超重的收费规则。话题2中用越南语发言的交际效率比用汉语高。
话题1和话题2是来华留学生在微信群内集中使用越南语发言的两个典型案例。当留学生遇到重要事件,用汉语表述存在障碍或表述效率较低时,他们会选择使用母语进行发言。当问题解决后,他们切换为微信群中全体学生的共同语来进行交流。遇到涉及安全、健康、财务等重要事件的处置,如用外语表述存在准确、熟练程度不足等问题,留学生往往考虑转为使用母语,这在其他语种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运用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另外,当某个留学生使用自己的母语发言,来自同一国家的其他留学生可能顺应其语码选择结果,从而出现多人、多次使用非汉语表达。
话题3:
L(01:40:34): wow(哇)
在话题3中,L和S均是来自泰国的女生。武汉下雪了,L很惊讶。L先用英文单词“wow”表示惊喜,然后泰语和阿拉伯数字串混用,发出下去玩雪的倡议。“5”在汉语中和“呜”字谐音,在汉语网络交际中多个“5”连写表示大哭。在泰语中,“5”的发音是“ha”,和笑声相近,因此在泰语网络交际中多个“5”连写表示大笑。只懂汉语,不懂泰语的人看到话题3中的“55555555555”,很可能出现跨文化交际障碍。S对L的倡议不仅不支持,还根据客观条件不满足的事实(此时是凌晨1点41分,留学生宿舍已经锁门,不能下楼去玩雪),提出了反问。L的倡议没被同胞积极回应,只好尴尬地发了“呵呵”。
话题4:
Y: 我们班有没有人叫张三和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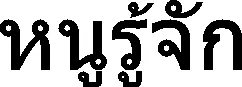
(我知道李四,周一和周二下午与我们一起上课。)


(我的中国朋友问。我说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不敢决定。)

(那我告诉他那不是我们的室友像小孩子一样讲,告诉阿姨。)

话题4是发生在泰国留学生之间的讨论。在不影响语料阅读的前提下,此处对语料的中文人名用“张三”和“李四”做了替换。在第1个话轮中,Y用中文提出问题,其中包括两个中文姓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泰国,涉及人的信息大多比较敏感,因此Q在第2个话轮中,2次用泰语发言,回答Y的提问。在第3个话轮中,Y向Q解释为何她提出第1个话轮中的问题,以及将如何处理Q提供的有效信息。在第4个话轮,Q用泰语向Y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话题4是一次达到了交际者预期的会话,因为Q有效回答了Y的提问,Y也向Q解释了为何要提出这个问题。Y和Q使用泰语交流,减少了能看懂该话题内容的学生数量,较好地保护了张三、李四的隐私。
以上4个话题中,均有多位学生使用了自己的母语进行交际。其他使用越南语或泰语的发言,要么比较零散,要么是同一位学生多次使用。话题1和话题2与生活中的关键事件高度相关,因此留学生使用了自己的母语进行交际,从而可以快速地达到交际目的。话题3和话题4,可能是出于保护谈话内容的私密性,适当地降低谈话内容的传播范围,而使用了会话者的母语。以上4个话题实例,有代表性地展示了来华留学生在公共微信群里,如何使用自己的母语作为会话语码。尽管群里的泰国、越南学生数量较多,但他们考虑到了该微信群是班级群,不宜过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聊天,避免让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感到尴尬。
三、汉字与拼音的选择
熟练掌握、运用汉字是外国留学生深入学习汉语的前提。留学生比较容易掌握那些常读、常写的汉字,对非高频读写的汉字则较难掌握[10]。长期来华留学生不仅要多记汉字,更要在真实的汉语交际环境中准确地使用汉字。有汉语国际教师反映:部分来华留学生对汉字学习积极性较低,尤其是在电脑或手机上写汉语时,喜欢用拼音,而不是汉字。虽然用拼音也能达到交际的目的,但却不利于学生深入地学习汉语。在本文研究的微信群会话中,2075次汉语文本会话使用了汉字来表述,21次汉语文本会话使用拼音(未标声调)来表述。该微信群中有一个学生来自东亚国家,却多次使用汉语拼音来发言。相反,群中6个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学生没使用拼音来发言。以下给出3个话题实例,从中观察留学生遇到其他人用拼音表述时的语码选择态度。
话题5:
Z:@M zenme le?
M:就是需要帮忙,新年前买票的人很多,所以要抢票
Z: oh buzhidao zenme bangzhu
M:按一下那个蓝色的就可以啦
话题5的讨论包括4个话轮,涉及2名学生,Z是来自东亚的学生,M是来自东欧的学生。有人在群里发了一个非文本形式的通知,Z没看懂,于是点名问M。话轮1中,“zenme le”虽然没标声调,但容易理解为“怎么了?”。在话轮2中,M的回答包括三个分句。虽然M的母语是俄语,在拼音表述方面有优势,但M没有顺应Z用拼音发言,而是用汉字写句子进行回复。在话轮3中,Z继续用拼音的方式来提问。注意:话轮3中的第一个词“oh”不是拼音,而是英语单词,相当于汉语中的“哦”。“oh”之后应有标点符号,把英语单词和后面的汉语拼音分开。在话轮4中,M依然坚持用汉字表述来回答。在两问两答中,M表现出了优秀的拼音理解和汉字运用能力,Z却始终未用汉字表述自己的提问。
话题6:
Z: Dajia gangcai meiyou Wifi de fangjian, xianzai liandeshang ma?
Z: Buzhidao shibushi zhiyou women fangjian haimei huilai
V:有可能你们的流量用完了
S: 学校网络的力量一个月能用4GB
话题6包括3个话轮,4次发言。Z是话题5中的东亚学生,V是来自东欧的男生,S是来自东南亚的女生。Z先后提出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询问其他同学房间里的无线网络现在是否能连得上?第二个问题中的“huilai”让人费解。估计Z想表达“恢复”,但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词语来表达,从而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房间还没回来?”的表述结果。V没有直接回答Z的第一个问题,而是告诉他房间不能上网的可能原因是Z的网络流量已超限额。从V的非直接回答来看,V所在房间的无线网络正常,且V熟悉网络计费规则。S在V发言的基础上,进一步给予补充信息(其中“力量”应该是“流量”。估计是用拼音输入“liuliang”时掉了一个u,误输为“liliang”,然后被汉字输入法软件选为“力量”)。V和S热心地为Z提供帮助,Z既未表示感谢,也没继续提问,也许Z没看懂V和S的回答。
在话题5和话题6中,M、V、S虽然热心回答了Z的提问,但实际的帮助效果存疑。对Z用拼音表述的问题,M、V、S始终用汉字写句子进行回答。Z既没声明看不懂同学的回答,也没请求同学用拼音写句子。因此,“合作原则”“语言顺应论”等在话题5和话题6中均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Z在群里共发言143次,其中用拼音发言20次,仅在话题7中被其他同学用拼音回应。在该微信群会话语料中,仅有话题7是在一个话题内部,出现多人使用拼音进行发言。
话题7:
Z: Nimen fangjian Wifi zenmeyang?
Z: Shibushi turan lianbushang?
V: Nigoule
Y: Wi-Fi很好的呀
F:对
F: wifi不好
Z: tianna haimeiyou zuowan
F: wo ye shi
F: =))))
M:我也设
Y: 不想做作业了

F:在做的时候突然没有网
F:连不上
D:天意
F:对啦、反天意的话会犯罪
F:那就不做作业吧
D:反老师的意更惨
Q: 你们再试试wifi好像好了。
F:还没有的
在第1个话轮,Z因为房间无线网络故障,在群里主动用拼音发起提问。V用“Nigoule”进行回复。“Nigoule”既不是英语单词,也不是正确的汉语拼音。由于它在微信群会话语料库中只出现一次,笔者难以推测V想用它来表达什么意思。在第3和第4个话轮,Y和F选择使用汉字进行发言。但F在发言中使用了字母词Wi-Fi,Wi-Fi是该群中使用频次最高的字母词。在第5个话轮,Z又用拼音写句子告诉大家自己的作业还没完成,该发言很快在群里引起了共鸣。第6个话轮中,F用拼音“wo ye shi”对Z进行了回复。在整个语料库中,除了Z之外的留学生,仅有这一次使用拼音发言。在第7个话轮,M参与讨论,但M选择用汉字来表述。此处的“我也设”应该是“我也没”,估计是用字形输入法软件输入汉字时出现了错误。在第8个话轮,Y不受前面已有多次拼音表述的影响,继续使用汉语发言。在第10至第15个话轮,D和F恢复用汉字进行表述,Q亦用汉字写句子参与讨论。
有部分汉语教师担心留学生相互之间频繁用汉语拼音进行聊天,从而会阻碍他们合理使用汉字。但从话题5、6、7的会话过程来看,即使在讨论中有少量学生使用拼音表述,其他长期来华留学生还是坚持以汉字为语码进行回复。在长期来华留学生的微信交际中,使用汉字表述是绝对的主流。
结语
本文采集了一个长期来华留学生微信群的真实会话语料,从发言类型、学生母语的使用、汉字或拼音使用次数等角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统计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生比中国人更喜欢用动态表情包、图像等非文本方式来发言。从留学生也喜欢发红包、讨论红包可知,他们较好地适应了当代中国的网络交际文化。长期来华留学生在班级微信群里积极地使用汉语进行交际,极少出现同一种母语的学生频繁地用其母语交流的情况。在汉语交际中,即便有个别学生使用汉语拼音进行提问,其他留学生大多坚持用汉字写句子去回应。这说明多用汉字、少用拼音的理念已在长期来华留学生的日常汉语交际中得到贯彻执行。长期来华留学生频繁地写汉字、用汉语开展日常沟通,用当代中国人常见的网络交际方式进行交流,这说明他们乐意接受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动机增强了,其汉语学习主动性、学习效率都会随之提高。
虽然本文所观察的留学生来自8个国家,但其中泰国学生占比超过一半,有4个国家的留学生只有1人。各生源地国家的学生人数不均衡,可能导致缺乏同胞的留学生不得不使用汉语和其他同学开展会话。如果来自每个国家的留学生人数都超过2人,也许会有更多留学生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发言,从而利用汉语发言的比例会略有降低。未来如能收集到更大规模的留学生微信会话语料,可以就此问题深入研究,定量分析不同母语类型的长期来华留学生使用汉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注释:
[1] 王卓玉:《微信平台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研究》,《开放教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3~119页。
[2] Qi Xu, Hongying Peng, “Investigating Mobile-assisted Oral Feedback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ComputerAssistedLanguageLearning, No.3-4, 2017.
[3] 牟蕾、吴勇毅:《多语者新媒体话语研究——以外国汉语学习者微信朋友圈话语为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51~160页。
[4] 李经纬、陈立平:《多维视角中的语码转换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337~344页。
[5] 牟蕾、吴勇毅:《多语者新媒体话语研究——以外国汉语学习者微信朋友圈话语为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51~160页。
[6] 范莎莎、方美思:《浅谈“表情包”在大学生群体中走红的原因及影响》,《文化与传播》2018年第3期,第54~58页。
[7] 程伟:《基于顺应论的网络交际语码转换现象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2期,第44~49页。
[8] 余一骄:《微信文本会话的语言风格统计与分析》,《华中学术》2017年第2期,第94~101页。
[9] 于国栋:《语码转换研究的顺应性模式》,《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1期,第77~87页。
[10] 郝美玲:《高级汉语水平留学生汉字认读影响因素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第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