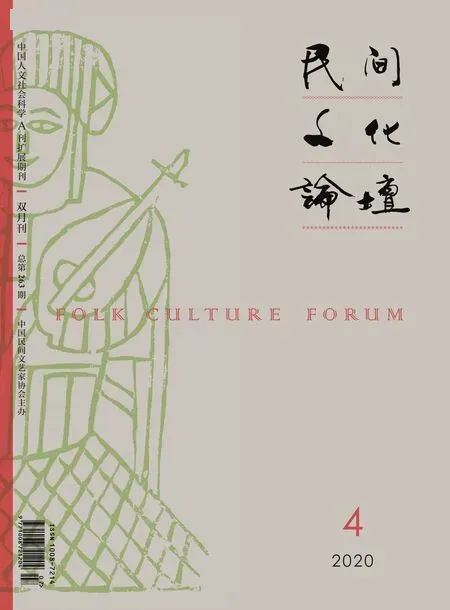天生神物:《山海经》中的上帝与众神
刘宗迪
宗教的核心是祭祀。对于上帝以及天地山川等自然神的祭祀,是除祖先崇拜之外,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主要内容。其历史源远流长,及至秦汉时期,关于上帝和天地山川之神的祭祀逐渐制度化,《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后汉书·祭祀志》对秦汉时期的宗教祭祀制度言之甚详,但商周时期的宗教祭祀制度,却文献缺略,并无系统记述。商代甲骨文为占卜之辞,百余年来,发现甲骨累计虽有十数万片,其中与祭祀相涉者数量众多,且祭祀卜辞多详列祭祀的对象、祭品、仪式名称,为了解商代宗教祭祀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然而,卜辞所载仅是占卜所及者,其已经制度化,而无待于占卜的祭祀行事,则不见于卜辞,如卜辞中关于至上神“帝”的祭祀仪式就罕见涉及。且卜辞仅寥寥数语,其卜问之辞和验辞均就事论事,而不涉及卜问之事的背景,据以很难了解商人对某位神的具体看法,故仅据卜辞所载实不足以呈现商代宗教祭祀制度和宗教观念的全貌。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又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生值东周,且身居鲁国,“周礼尽在鲁”,对周礼自是熟稔于心,然而,孔子及其后学并没有留下关于周代宗教祭祀制度的系统记述,号称“礼经”的《仪礼》所载只是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仪式场合宾、主升降揖让的动作规范,而无及于祭帝祀神之礼。《左传》《国语》以及《礼记》的《礼运》《礼器》《郊特牲》《明堂位》《祭法》《祭义》《祭统》《月令》等篇多言祭礼及其意义,但这些文献多出自战国时期,《礼记》中更有晚至汉初的材料,且其言夏、商、周祭礼,既缺乏系统性,又多为战国秦汉之际知识分子依托之说,殆非上古宗教祭祀制度的本来面目。《周礼》,尤其是其中的《春官宗伯》篇,对祭祀之礼有系统的记述,但亦为战国文人依托之作,尽管不乏现实的影子,却非基于对上古祭礼的真实写照。故虽然自汉代经学以来,礼学即成专门之学,清代学者对古礼考证尤详,然而对于先秦时期宗教祭祀制度,仍是言人人殊,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更是臆说纷呈,令人难得其真相。
实际上,在传世古书中,有一部书记述上古帝、神崇拜,其翔实可靠远非其他先秦文献可比,这就是《山海经》。
由于《山海经》多载闳诞迂夸之言、怪异荒僻之物,被视为齐谐、志怪之书,故历来为考古史者所不屑。实则,《山海经》并非齐谐志怪之书,更非胡编乱造之作,其记物叙事自据章法,所载神怪异物俱有来历。《山海经》包含《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前者分东、南、西、北、中五方记述了数百座山的名称、方位及各山的物产,包括草、木、鸟、兽、蛇、鱼以及金、银、铜、铁、玉等各类矿物,是一部典型的地理博物志。《海经》包含《海外经》和《大荒经》两部分,两者分别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记述,按照东、南、西、北、内(中)五方,记述了四方海外的山川、方国、族类。惟因其书来历甚古,记物叙事之法别具一格,且其中《海经》诸篇为述图之文,后人不解《山海经》的成书过程和记述之法,读不懂书中内容,故视之为荒怪之书。
《山经》在记录众山的地理物产的同时,还往往记录栖息出没于某些山、川中的神灵,以及诸多以“帝”命名的山丘,这些以“帝”命名的山丘当与上帝崇拜有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山经》每篇的末尾,皆有一段专门记述该篇诸山的山神祀典。《海经》则更是在记述山川、方国等地理景观之外,记录了众多的帝和神,并往往详述其诡谲之形、祭祀之礼、献祭之物。要之,《山海经》一书保存了丰富的上古时期上帝、众神崇拜与祭祀的史料。由于《山经》内容皆据实录,非如《海外经》《大荒经》那样经过从图画到文字的转换,转换之际很可能已经羼杂了述图者的解释甚至篡改,故《山经》所载与帝、神相关的内容,当更能保存古人观念的本色,为我们了解上古时期的神学观念,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有见于此,本文拟对《山经》a本文引《山海经》,皆据宋淳熙七年(1180年)池阳郡斋本《山海经》,今有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本。中关涉帝、神崇拜的内容做一番勾稽、分析,以备学界同行了解、研究古代宗教所共鉴。
一、《山经》中的帝迹
(一)帝之下都
上帝作为至上神,在古人的心目中,应该住在天上,故《诗经·大雅·云汉》称“昊天上帝”,《尚书·召诰》称“皇天上帝”,其实,“上帝”之称,已寓帝居于上天之义。惟因上帝住在天上,高高在上,方能鉴临人间,无所不见,明察无隐。但是,正如身居紫禁城的人间帝王也常常要走出禁宫,巡查四方,并在各地设有行宫一样,高居天庭的上帝也要时常降临地上,巡查人间,于是,人间就需要有上帝的行宫。《山经》的群山中,即有多处上帝在人间的宫殿。
《山经》记载了多处以“帝”命名的地名,即为上帝在下界的离宫别馆所在,其中,以《西次三经》所记最典型,如下列诸条:
1. 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䍃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丘,东望䗡渊。
2. 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
3. 槐江之山: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
4.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昆仑之丘。昆仑为中国神话和古代地理学中的名山,古书中关于昆仑神话景观的说法,可谓争奇斗艳,异彩纷呈,而以《淮南子·地形训》所载最为全面。古人致力于求索昆仑之所在,大都认为它是一座位于中国西垂、黄河上游的高山,而对其具体所在,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昆仑的最早出处即《山海经》,昆仑除见于《西山经》外,还见于《大荒西经》《海内西经》等篇,《山海经》所记才是昆仑的本来面目,后来各种昆仑异说,无非由《山海经》的昆仑说曼衍而来。
经文称昆仑之丘为“帝之下都”,“帝之下都”,顾名思义,即上帝在下界的都城或宫殿。《海内西经》亦以昆仑为“帝之下都”:
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昆仑之墟 “在八隅之岩”,即高居于四四方方的基址之上;“面有九门”,每一方面各有九座大门;“面有九井,以玉为槛”,每一方面还有九口水井,皆以玉石为井栏。昆仑之墟显然是一座人工建筑物,其实就是祭天的神坛。a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93—522页。人类借祭祀与上帝、群神沟通,祭天之地即为上帝、群神降临之所,因此,昆仑成为上帝、群神在人间的宫殿,故得名“帝之下都”,为“百神之所在”。上帝在天上的都城位于天极,在地上的都城位于昆仑,故在古人的宇宙观中,昆仑上应北极,两者共同构成天地之中轴。
《西次三经》说昆仑之神陆吾“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天之九部”当指天之九野。古人分大地为九州,相应地,分天穹为九野,《吕氏春秋·有始》云:“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并详列九野、九州之名,其实就是按照九宫格的方位将天穹和大地分别划分为九个对称分布的区域。
“帝之囿时”,“时”,郝懿行《笺疏》校订为“畤”,《史记·封禅书》云:“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索隐引《汉旧仪》云:“畤,如种韭畦,畤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畤。”畤为祭祀上帝之所,其构造如同种菜的田畦。所谓“帝之囿畤”,即上帝的苑囿,当为上帝在下界的花园。
《西次三经》中,与昆仑之丘相邻,为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圃即菜圃、蔬圃,则槐江之山为上帝在下界的菜园子。槐江之山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此说与昆仑之丘上“万物尽有”(《大荒西经》),皆表明其山饶有各种金玉珍宝,当为献祭上帝、天神之物。
《西次三经》所记群山中,不仅有上帝的蔬圃和花园,还有上帝的动物园。经谓崇吾之山“西望帝之搏兽之丘”,搏兽即猎兽,此座位于崇吾之山以西的帝之搏兽之丘,为上帝在下界的兽苑,是上帝打猎的地方。正如后世帝王的上林苑,既有奇鸟异兽,亦有奇花异草,兼具动物园与植物园的景观,《西次三经》所呈现的这片群山之中,同样既有上帝的动物园,又有上帝的植物园,其宗教功能可谓完备。
植物园可以植草木果蔬,动物园可以豢养鸟兽,实际上,它们都是供祭祀时献祭上帝之用。除此之外,《西次三经》所记群山中还有上帝采玉之地。经云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有而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这一段文字金声玉振,声情并茂,其文学意味在《山经》中独一无二。古人崇玉,不仅因为玉石质地细腻可玩,而且还因为佩玉可以辟邪,食玉可保长生,故古人亦以玉祭神,《山经》每篇的篇末祀典中,即屡见以玉祭神的记述。峚山所出的丹水出产白玉,且有玉膏,玉膏为黄帝所食所飨,玉膏年久则成玄玉。黄帝 “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峚山盖为黄帝采玉之地。黄帝在《海经》中屡见,在《山经》中则唯此一见,黄帝盖即上帝,亦即《山经》屡屡提到的“帝”。黄帝采玉于峚山,以峚山的玉膏为食,当意味峚山所产玉膏和白玉是祭祀上帝之物,峚山可谓上帝的玉田。
可见,在《西次三经》所记载的以昆仑为中心的群山之中,有数处上帝在地上的设施:昆仑之丘是帝之下都,为上帝的宫殿;槐江之山是帝之平圃,为上帝的菜园;昆仑边还有帝之囿畤,为上帝的花园;有帝之搏兽之丘,为上帝狩猎的兽苑;峚山则为上帝采玉的玉田。这一系列上帝的宫殿苑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宗教地理学体系,昆仑之丘及其周边群山,当为古人祭祀上帝的一系列圣地所在。
昆仑为“帝之下都”,无独有偶,《山经》还记载了一处“帝都之山”。《北次三经》有一处泰泽,“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广员百里,无草木,有玉金”。泰泽即大泽,当是一处水面广阔的泽水,泽中有山,名曰帝都之山,此山方圆百里,山上无草木,有玉石、黄金。帝都之山,很容易让人想到作为帝之下都的昆仑,此山当与昆仑一样,亦为祭祀上帝的祭坛所在。《史记·封禅书》云:“天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a今本作“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地”原当作“天”,涉上下文而误。《史记·封禅书》记齐地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上云祭天主于天齐渊,是祠天于泽中,下云祭地主于泰山下小山梁父,是祠地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正与“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之说相悖,太史公行文不当如此自相矛盾,故知此文“天好阴”当作“地好阴”,“地贵阳”,当作“天贵阳”。“天”、“地”二字互舛,原文当作:“盖地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天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天贵阳而地好阴,方合乎天高地卑、天处阳而地处阴之理。帝都之山在大泽之中,当即祭祀天地的圜丘,山上的玉石、黄金则为奉献给上帝的祭品。
《西山经》中,除《西次三经》所载帝迹之外,《西次一经》有一座天帝之山,此山名之为“天帝”,亦当因其为祭祀上帝之地而得名。
(二)帝台
除《西次三经》外,《中次七经》亦记载了数个与上帝有关的地名:
1. 休与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其状如鹑卵。帝台之石,所以祷百神者也,服之不蛊。
2. 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也。
3. 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䔄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
4. 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囷。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叶状如杨,其枝五衢,黄华黑实,服者不怒。
5. 讲山:有木焉,名曰帝屋,叶状如椒,反伤赤实,可以御凶。(均见《中次七经》)
休与之山上的石头,有美丽的五彩纹理,圆润如鹑卵,大概就像如今南京所产雨花石之类的玛瑙石。将此石佩戴在身上可以辟除蛊毒,可见其深得古人的珍视。古人将此石献给上帝,故被称为“帝台之石”,因其圆润如棋子,故被称为“帝台之棋”。大概在古人的心目中,上帝也是要下棋解闷的。
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也”,觞谓饮酒,觞百神谓以酒醴献祭众神。古人在隆重的宴饮场所或祭祀场合,都要以乐舞伴奏,即所谓钟鸣鼎食,谓之“侑觞”。鼓谓敲击,钟为乐器,“鼓钟之山”,顾名思义,其山当为奏乐起舞之地,奏乐起舞的目的则在为帝台侑觞献祭众神。
以上两条均提到“帝台”。“帝台”,顾名思义,即上帝之台,当指祭祀上帝的祭坛。《中次七经》中,休与之山与鼓钟之山为相邻的两座山,休与之山的五彩之石被用为帝台之棋,鼓钟之山为在帝台献祭众神时奏乐宥觞之所,则帝台亦必与两山相去不远,或即两山中的一座。“帝台”之名,表明这里是一处祭祀上帝的宗教圣地。
《中次七经》中,在休与之山、鼓钟之山附近,还有一系列与上帝相关的地名,当皆为与上帝之祀有关的地理印记。
姑媱之山上生长着一种䔄草,女人将此草的果实佩戴在身上,就能取媚于人,得到男人的欢心,传说这种草是上帝的女儿死后所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地方风物传说,大概当地女性有佩戴此草以为姿媚的习俗,故当地人编出这个故事解释此种风俗的来历。由此故事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天上的上帝跟人间的帝王一样,也有妻子儿女。上帝不死,但其女儿会死,但上帝的女儿毕竟不同于凡人,故死后化为美丽的䔄草得以永生。
少室之山上草木葱茏,山上有一棵树,名曰“帝休”。这棵树枝繁叶茂,五根粗大的树枝伸向四方,一定会投下浓重的阴翳,可供行人驻足休憩乘凉。此树名为“帝休”,意味着在当地人传说中,这棵树是上帝休憩的地方。
《中次七经》中,与少室之山相邻为泰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叶状如蔾而赤理,其名曰栯木,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状如,白华黑实,泽如蘡薁,其名曰䔄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泰室之山上也有䔄草和美丽的石头。“泰室”即“太室”,历史上,太室山指今天的河南嵩山,少室山则是嵩山附近的一座山,故前人均认为《山经》的太室、少室之山即河南嵩山。实际上,华夏历史久远,地名叠经变迁,《山经》中地名非常古老,其所谓太室、少室是否就是今天的嵩山,并不能因其名称相同而骤断,对此问题,姑且不论。不过,“太室”“少室”的名称却耐人回味。太室亦即大室,古人称宗庙为大室,古书和金文中屡见,大室为祭祖之所,商、周祭祀的惯例,祭祖与祭天(帝)并举,以祖宗配享于天帝,故宗庙当与帝台所在不远,明乎此,可知太室之山、少室之山或当为宗庙建筑所在,亦为宗教圣地。
与太室之山相邻为讲山。讲山上长着一棵树,名为“帝屋”。此树的叶子像花椒,枝上生棘刺,棘端内曲(“反伤”),结子赤色,很可能就是花椒树的一种。花椒因气味辛香郁烈,且树生棘刺,故古人相信其不仅可以治病,且可以驱邪除秽,故经谓之“可以御凶”。此树名为“帝屋”,颇耐人寻味。谓之“帝屋”,或因上帝曾在此树下居住,或因为此树生长于上帝之屋附近,不管此树缘何得名为帝屋,其以“帝”为名,足见其地为上帝足迹所及。
《中山经》中,除《中次七经》记载多处帝迹之外,《中次十一经》亦有四处与“帝”有关的景观:
其一,帝囷之山,其所出之水名曰帝囷之水,《说文》云:“囷,廩之圜者。”囷即圆形的粮仓,“帝囷”盖谓上帝的粮仓。《吕氏春秋·九月纪》云:“是月也,……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帝藉即藉田,为祭祀上帝众神而设的农田,藉田收获的粮食专门用于献祭上帝众神,神仓即储藏藉田收获的粮仓,“帝囷之山”一名,暗示其地为上帝的粮仓所在。
其二,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台之浆也,饮之者不心痛”。所谓“帝台”,当与《中次七经》的“帝台”同义,亦为上帝之祭坛。高前之山上有一处泉水,其水清冽,称为“帝台之浆”。《周礼·天官冢宰》云:“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释名·释形体》云:“浆,水也。”“浆”谓饮用水,“帝台之浆”当为献祭上帝的神水。因为此水为上帝所饮,故当地人信其有神效,饮之能疗心痛。
其三,与高前之山相隔三座山,为毕山,毕山所出之水曰帝苑之水,“帝苑”盖即上帝的苑囿,此水得名为“帝苑之水”,当因此水流经帝苑,为帝苑灌溉草木。
其四,该篇还有一座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柎,名曰帝女之桑。”此树名为“帝女之桑”,或因此桑为上帝的女儿们采桑的地方,或因此桑为上帝的女儿死后所化,如同《中次七经》中的䔄草为帝女死后所化一样。不管是何种缘由,当地必定有关于此桑的传说。帝女之桑当是古人祭祀蚕神的神桑。a《海外北经》云:“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一个女子跪在树上呕丝,此女子即蚕神,三桑长百仞,盖亦即帝女之桑之类。《原化传拾遗》(《太平广记》卷479引)记载的马头娘故事,谓女子被马皮所裹而成为蚕女,类似故事又见《搜神记》卷14、《中华古今注》卷下,皆以蚕为女子死后所化,当皆为上古帝女之桑传说之流亚。
《中次十二经》为《山经》最后一篇,其中有一处阳帝之山,此山称为“阳帝之山”,且在《山经》地理格局中位于南方,“阳帝”之名当与南方、夏天或太阳有关。《海外南经》云:“南方祝融。”《礼记·月令》谓夏天“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祝融为南方和夏天之神,又为火神,炎帝亦为火神,其实就是阳帝。惟《山经》记载简略,此阳帝是否即祝融或炎帝,无从考证。
综上所述,可见《中山经》所记群山多处为古人祭祀上帝的宗教圣地所在,为上帝频频光顾,故在其地留下了一系列印记,有祭祀上帝的帝台,有上帝对弈的棋子,有为上帝奏乐侑觞的鼓钟之山,有供上帝休憩的帝休之树,有上帝的女儿死后变成的美丽䔄草,有被称为上帝之屋的花椒树,有上帝粮囷所在的帝囷之山,有专供上帝饮用的甘泉帝台之浆,有灌溉上帝苑囿的帝苑之水,有帝女之桑,为上帝之女采桑之树,或上帝之女死后所化的神桑。关于这些与上帝有关的圣迹,在当地一定有相关神话传说流传,䔄草传说只是其吉光片羽而已。
(三)帝之密都
《中次三经》有一处青要之山,为“帝之密都”所在,此山景观十分引人注目:
青要之山,实维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鴐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仆累、蒲卢。䰠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齿,而穿耳以鐻,其鸣如鸣玉。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鸟焉,名曰鴢,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其状如葌,而方茎黄华赤实,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
此山称为“帝之密都”,可与昆仑称为“帝之下都”相呼应。此山北望河曲,河曲即黄河转弯之处。河曲之地必定水流缓慢、水面广阔,且有大片的滩涂薮泽,故经文云此山“北望河曲,是多鴐鸟”。鴐鸟为天鹅、鸿雁之类的大型水鸟。其地有水禽栖息,足见此河曲之地必多水草和水生物,故下文云此山附近的墠渚“多仆累、蒲卢”,仆累、蒲卢即螺、蚌之属,俱为水禽喜食之物。青要之山的所在,依山临水,河曲水流潺湲,草木丰茂,水禽翔集,环境开阔而优美,古人祭祀上帝群神必选择风景宜人之地。由青要之山不仅为帝之密都所在,而且还是禹父之神和武罗之神所栖,可知此地必为一处重要的宗教圣地。
经谓青要之山“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禹父即鲧,《海内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因窃帝之息壤填土治水而被上帝处死于羽郊(或作羽渊),鲧死后从腹部生出了禹(或说鲧化为黄熊),类似说法亦见《左传》《国语》《天问》等书。鲧是男性,男性不能生子,但鲧却在死后生出了儿子,经文所谓“禹父之所化”,当即指鲧死后化生禹(或化为黄熊)一事。鲧死后何以还能生子?这一问题从来无人问及。实际上,鲧死生子的秘密,正在他盗窃的“息壤”。“息”有生息之义,《周易·革卦》:“水火相息”,王弼注:“息者,生变之谓也。”《释名·释言语》云:“息,塞也,言物滋息塞满也。”“息”有生息之义,故妻子称“息妇”,以其能生养;子女称“子息”,以其能继香火;投资获利为“利息”,以其为钱所生。则所谓“息壤”“息土”,即能生殖之土。息壤为生命的源泉,而鲧拥有息壤,故鲧虽死而犹能生育。由此可知,古人对鲧的崇拜,不仅与土地有关,而且还当与生殖有关。土地为生命的源泉,故在古人心目中,土地亦为人类生殖能力的源泉,所以古人不仅求丰年于社神,亦求子息于社神,此兼具求年与求子功能的神祀,即所谓高禖。《礼记·月令》云:“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高禖为古人求子之所,即生殖之神。鲧造地,鲧为土地之神,亦即社神,明白了这一道理,则知鲧可兼为高禖之神。
明白了鲧为高禖之神、生殖之神,而青要之山为鲧之神祀所在,则青要之山得名“帝之密都”的缘由也就可得而详了。“密都”当即高禖,《诗经·鲁颂·閟宫》云:“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毛传云:“閟,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孟仲子曰是媒宫也。” 閟宫为鲁人祭祀先妣姜原之庙,又称媒宫,媒宫即高禖。“密”“秘”“閟”通,陈梦家指出,《山经》“帝之密都”即高禖之所在。a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清华学报》,1937年第3期。婚媾求子,男女欢愉之事,故需行之于清静隐秘之所,故谓之“閟宫”“密都”。可见,所谓“青要之山,实维帝之密都”,实谓此山为高禖之神所在。
其实,不仅鲧为高禖,禹亦为高禖。《淮南子·泛论训》云:“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可见禹为社神。《世本》云:“鲧取有莘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a《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高密即禹,“密”“禖”音通,“高密”即高禖,禹既为社神,社与高禖为一体之二面,故禹又被冠以“高密”之号。
鲧祀称为“墠渚”,亦非无故。《说文》云:“墠,野土也。”《风俗通义·封泰山禅梁父》云:“下禅梁父,礼祠地主。……禅谓坛墠。”坛、墠均为祭神之所,坛高而墠下,墠以祀地,故低于祭天之坛。“墠”“禅”音同,其字从土,表示筑土为之;从示,表示祭神之地。鲧为土地之神,故祀之于“墠”;渚为水中洲渚,设祭坛于水泽之中,故谓之“墠渚”。祭鲧于墠,即后世称祭地为“禅地”的缘起。
明白了青要之山为高禖所在而得名为“帝之密都”,则经文关于此山景观的涵义就容易理解了:
经云“是山也,宜女子。”“女子”意为“子女”,“宜女子”即谓此山有利于生儿育女,青要之山为高禖所在,是女性求子之地,自然“宜女子”,正如当今民间娘娘庙、观音庙等女性求子、拴娃娃之所亦有利于生儿育女一样。
经云青要之山所出的河流畛水中,“有鸟焉,名曰鴢,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凫即野鸭,此鸟状如野鸭而青身(羽翼青绿色)、朱目(虹膜或眼眶为红色)、赤尾(尾羽红色),可能就是鸳鸯;“食之宜子”,即谓吃了此鸟(或此鸟的卵)有益于生儿育女。吃鸟卵或鸡蛋能够促进生育,这种观念至今在民间还有流传。至于鸳鸯,因其双栖双飞的习性,更被民间视为美满婚姻的象征。
经又谓青要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葌,而方茎黄华赤实,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葌即兰,荀草为兰草之类香草。“服之美人色”,谓佩戴此草可令人颜色悦怡,秀媚可亲,《郑风·溱洧》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即谓青年男女以兰草相互悦媚。《楚辞》中香草美人的诗句更是俯拾即是,人类以花草芳馨取悦异性之俗,发乎情性,由来久矣。女性至青要之山求子,并取山上香草佩带于身,以取悦于男子,达到生儿育女的目的,即所谓“服之美人色”。
青要之山上,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无疑是武罗之神,经云武罗䰠“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齿,而穿耳以鐻,其鸣如鸣玉。”“䰠”字仅见于《山经》,即“神”字,但此处改从示为从鬼,必有深意存焉。武罗神的形象更是非同凡响,他身穿豹皮之衣,腰身修长,牙齿白皙,双耳戴金环,声音清越如同鸣玉之声,俨然是舞台上一位风姿绰约、嗓音浏亮的俊美小生,在《山经》所记众多形貌诡谲的神灵当中,武罗神可谓独一无二。这位英俊的武罗神是为上帝司掌青要之山的,青要之山是帝之密都,来此朝山者都是女性,女性眼里的神当然要仪表俊美,况且他还是一位与男女姻缘有关的神,更需有高颜值。
可见,青要之山作为高禖所在,山上的景观、草木、鸟兽无不与婚姻和生殖有关,如果说,昆仑作为“帝之下都”,相当于上帝在下界的朝廷,那么,青要之山作为“帝之密都”,就是上帝在下界的后宫。
二、《山经》中的众神
(一)天神
《山经》尽管记载了众多的上帝之迹,上帝的宫殿苑囿散布各地,但是,上帝在《山经》中却不见出场,综观《山经》全书,通篇不见关于上帝的正面记述。
这一点其实不难解释,在古人心目中,上帝作为至上神,居于天宫神殿,轻易不会露面,更不会亲力亲为从事具体的事务。上帝既然不会现身在场,因此,《山经》中就看不见对上帝形象、事迹的直接描述,而只是记录了众多上帝的居所。上帝无需时时事事在场,上帝的居所就是上帝存在和权能的见证。
正如人间帝王垂拱而治,不必每事亲躬,具体事务自有朝廷各个部门负责,上帝的具体事务亦有其下属之神代劳。《山经》即记载了多位各司其职的上帝下属之神,《西次三经》中,“帝之下都”昆仑周边的群山之中,即有多位神灵居住:
1. 槐江之山: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
2.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
3. 蠃母之山:神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状如人而犳尾。
4.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5. 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磈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
6. 符愓之山: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风云之所出也。
7. 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
8. 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
9. 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婴短之玉,其阳多瑾瑜之玉,其阴多青雄黄。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
槐江之山为英招之神所司,英招之神主管帝之平圃。昆仑之山为陆吾之神所司,陆吾之神主管帝之下都、天之九部和帝之囿畤的神。帝之平圃即上帝的蔬圃,天之九部指天之九野,帝之囿畤即上帝的苑囿,对此,上文已有详论。
蠃母之山为长乘之神所居。长乘之神司掌天之九德,天之九德为哪九种德,其详目不得而知。“德”有恩惠之义,《玉篇》云:“德,惠也。”《尚书·盘庚》云:“施实德于民。”即谓施惠于民。“天之九德”,盖指上帝施与人间的九种恩惠。
玉山为西王母所居。西王母又见《大荒西经》和《海内北经》,《大荒西经》云:“有西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琁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又云:“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沃之野场景位于《山海经》世界西方,对应于秋天。沃之野即沃野,沃野之上,凤鸾起舞,百兽共处,珍品美味无所不有的场景,所呈现的实为秋收庆典景象,出现于这一场景中的西王母实为丰收之神。a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69—578页。
秋收同时意味着万物凋零,生命衰微,故丰收之神同时也是死亡之神。a丰收意味着死亡,故丰收之神同时也是死亡之神,此义弗雷泽《金枝》论之甚详,举证綦多。《西次三经》说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天之厉指天上的厉鬼,五残指五残星,《史记•天官书》云:“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丈。”正义云:“五残,……见则五分毁败之征。”五残星为出没无常的妖星,当为彗星、流星之类。五残出现预兆毁败,可见五残亦与死亡有关。
长留之山为少昊之神所居。少皞为主管西方和秋天之神,此山又为员神磈氏的宫殿所在。此神主司反景,反景即返景,指日落西山时投向东方的影子,则此神实为落日之神。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之言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挚即少皞,《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帝王世纪》云帝喾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也。”则帝挚少皞为常仪之子。“常仪”又作“常义”,《大荒西经》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义,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则常义为月神。义(義)、仪(儀)与我、娥,形近音通,常义亦即嫦娥。《西次三经》中,与少昊所居的长留之山相邻之山,名为“章莪之山”,“章”“常”音近,“義”“莪”形音皆近,章莪之山盖即常义之山,即少皞之母所居之所,故《西次三经》中,少昊所居的长留之山与章莪之山相毗邻。
符愓之山为江疑之神所居。“是山也,多怪雨,风云之所出也”,谓此山风云变幻莫测。山区地形复杂,导致气象变化无常,所谓油然作云、沛然作雨,风雨阴晴瞬息万变。此山多雨,或为古人祈雨之地,江疑之神盖为风雨之神。
騩山为耆童之神所居。耆童即老童,《大荒西经》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老童为颛顼之子、重黎之后。经文未言此神所司之事,此神声如钟磬,盖为音乐之神。
天山为帝江之神所居。此神混沌无面目,却能歌善舞,或为歌舞之神,正与耆童之神相呼应。《左传·文公八年》云:“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浑敦”,《史记·五帝本纪》作“浑沌”。“江”“鸿”字通,帝鸿氏之子名曰“浑沌”,帝江“浑沌无面目”,故或以为帝江即帝鸿氏之子浑沌。实际上,《山海经》谓帝江“浑沌无面目”,只是说其面目模糊、不具五官而已。“浑沌”作为形容词,而并非帝江之名,且帝江通晓歌舞,而帝鸿氏之子浑沌则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坏蛋,安能混为一团?
泑山为蓐收之神所居。蓐收为秋天之神,《礼记·月令》云秋天“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少皞和蓐收共同掌管秋天和西方。此山西望落日,落日为红光之神所司,红光与长留之山主司反景的员神磈氏一样,均为落日之神。日落西方,故落日之神与主司西方和秋天的少皞、蓐收同处一山,皆在《西山经》中。
以上诸神之所司,多与天文、日月、气象、时令有关,当皆为天神,亦即上帝的下属,他们各居一山,各有所司,正如人间朝廷由职责各异的官府组成一样。《西次三经》所记这些各有所司的众神,居住于昆仑之丘周边群山中,昆仑为帝之下都,则这些环绕在昆仑周围的众神之山,就是上帝在下界的各个官府,它们与帝之下都昆仑之丘一道,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各有所司的万神殿。神因祭祀而临在,《西次三经》记载的诸神所居之山,实际上就是古人祭祀这些神灵的圣地所在。
(二)土生土长之神
《西次三经》之外,《中山经》也记载了多座神灵所居之山。与《西次三经》所记诸神皆为替上帝掌管某种事务的天神不同,《中山经》所记诸神皆为土生土长、掌管一方水土的山神。
1. 和山:实惟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其状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萯山之阳,出入有光。泰逢神动天地气也。(《中次三经》)
2. 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风雨。(《中次七经》)
3. 骄山:神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雎漳之渊,出入有光。(《中次八经》)
4. 光山: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中次八经》)
5. 岐山:神涉处之,其状人身而方面三足。(《中次八经》)
6. 丰山: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中次十一经》)
7. 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中次十二经》)
8.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中次十二经》)
和山之神泰逢,人身虎尾;堵山之神天愚,多怪风雨;骄山之神围,人面羊角虎爪;岐山之神涉,人身方面三足;光山之神计蒙,人身龙首;夫夫之神于儿,人身而身操两蛇;洞庭之神帝之二女,除帝之二女以外,尽皆形象诡异。而且,诸神出没,常伴有异象,泰逢神、围神、耕父神、于儿神“出入有光”,能令天地气象为之变色;计蒙神、洞庭女神出入则伴有飘风暴雨;耕父神一旦出现,会给国家带来败亡之祸。
以上诸神当皆为居于一方,掌管当地风雨水旱、年景丰欠的土著之神,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而非如《西次三经》所记众神,为上帝下属天神,他们原居于天界,其所居之山只是天上官府在人间的投影而已。不过,居于洞庭之山的风雨之神名为帝之二女,被当成上帝的两个女儿,表明这些原本土生土长的神,也可以与上帝续上家谱而跻身于上帝的宫殿之中。
《山经》记载的这些土著之神表明,在古人观念中,神的存在与自然环境和地理景观密不可分。上古时期,人烟稀少,草莽未辟,高山深谷、广渊大泽受复杂地理条件的影响,阴晴晦明,变幻无常,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令人难以捉摸,再加上道路未通,野兽出没,因此,在人们的想象中,高山背后必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所在,神灵即隐居其中,飘风骤雨、雷鸣闪电的背后,即是山间的神灵在兴妖作怪。如果遭到冒犯,就会给人间带来天灾人祸、兵灾瘟疫,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对高山大川充满敬畏之心,将之作为神灵予以崇拜和祭祀。《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山经》关于山中神怪及其出入异象的记载,即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于高山大川的神秘想象和崇拜心理。山神水怪自属无中生有,但这些记载却足以说明,人们对山神水怪的想象却是基于真实的自然环境,并非巫师之流独出心裁的杜撰。山川崇拜跟关于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自然知识一样,也源于古人对其自然环境的真切感受和长期经验,因此也是其地理知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借助这些知识,我们才能认识到,古人心目中的自然世界,与后世王朝地理学视野下或现代科学地理学视野下的自然世界具有全然不同的面目和意义,他们的地方感和地理学,与王朝地理学经略天下的政治治理术或现代地理学的经济发展观主导下的舆地观和地理学具有大相径庭的内容和格局,这些山神水灵的知识,在今天尽管已经失去了其认识自然的科学价值,却是引导我们走进古人的心灵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津梁。因此,《山经》的这些记载,貌似荒诞迂夸,却为我们了解古人的自然观和宗教感、了解神灵由自然环境和地理景观中自然而然、土生土长的发生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结语:山川、宗教与神话
《山经》详细记述了数百座山及其所出河流的名称、方位以及山川所产的草木、鸟兽、蛇鱼、金石矿物等自然物产,并详述各种物产的形态、功用(尤其是医药功用),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部典型的地理博物志。在古人的观念中,山川大地,不仅是草木鸟兽栖息的家园、金石宝藏的府库,同时也是神灵的居所。
大自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既能造福于人类,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故古人对高山大川、大泽广薮、密林深谷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投射到这些对象之上,即将之赋予神性,成为神灵现身之所,于是就有了对于山林、川谷、丘陵的崇拜,而山林、川谷、丘陵等自然景观则因此成为神灵栖息的圣地。既然在古人的心目中,山林川谷为神灵的家园,则《山经》在博载山川物产宝藏之同时,兼载山中圣地以及栖居这些圣地的神灵,实为题内固有之义。
《山经》中记载了众多“帝迹”,有帝之下都、帝之平圃、帝之囿畤、帝之搏兽之丘、帝之密都、帝台、帝苑,这些都是上帝在下界的朝廷、宫殿和苑囿;有帝台之棋,为上帝游戏之具;有帝休之树、帝屋之树,为上帝休憩之所;有帝台之浆,为上帝饮用之泉;有帝苑之水,为浇灌上帝苑囿之水;还有数处以“帝”命名的山,即天帝之山、帝都之山、帝囷之山,这些山亦为“帝迹”所及;众神散居于群山之中,有为上帝司掌宫殿苑囿的天神,如英招、陆吾、长乘诸辈;有日月、风雨、歌舞之神,如江疑、耆童、蓐收、红光、磈氏诸辈;有土生土长、专司一方水土的山神,如泰逢、天愚、围、计蒙、耕父诸辈。上帝、众神的宫殿苑囿,错畤列布于群山之间,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功能齐备的万神殿:昆仑之丘作为万神殿的中心,位居众山之巅,环绕于昆仑周围的群山之中,有多处上帝的离宫别馆和群神栖居的山丘渊泽,居于昆仑的上帝统领群神,个性分明、形象各异的众神各司其职,各居一山,呈现出一幅波谲云诡的神国景象。这一景象比起希腊的奥林匹斯神殿毫不逊色,其规模之恢弘壮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希腊诸神只局促于一座奥林匹斯山巅,而《山海经》的众神则分别居住在位于十数座山的离宫别馆之中,山中除了上帝的都城,还有上帝的兽苑、菜圃、花园和秘宫,群山中蕴藏着金、玉、丹粟、雄黄等各种宝藏和灵药,栖息着形形色色面目诡谲的神兽怪鸟,大大小小的河流从这些山间发源,流向四方。可以说,《山经》的山川大地,就是众神的宫殿,《山经》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山川交织、众神列布的宗教地理学版图。
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人云亦云的成见,即华夏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重伦理而轻宗教,重历史而轻神话,重理性而乏想象,因此,缺乏一个像希腊神话、印度神话、北欧神话等等那样完整的神话体系,或者认为华夏先民并不乏想象力和宗教性,上古时期肯定也曾有过足以与希腊、印度、北欧相媲美的神话体系,只是因为历史沧海桑田的变迁,导致中国的神话体系已经失落于漫长的时间洪流之中了。其实,没有哪个民族,在其文化发轫时期,能够离开宗教,中国先民并不缺乏宗教创造力,中国的原始宗教体系也没有失落,它就原原本本地记录在《山海经》中,只是后人眼界狭窄,古书旧志尽管历历在目却一直熟视无睹。
至于神话,则只是附丽于宗教体系之上的叙事和话语而已,神话原本只是一些用以解释宗教制度、仪式、圣迹、圣地景观等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各各依附于其赖以生发的对象而存在和流传,经历岁月消磨之后,大部分消失了,小部分借最早的文献记录而流传了下来。这些故事原本就是一些短小的故事和话语碎片,诸如《山经》中的黄帝采玉于峚山的传说、炎帝之女溺亡后变为精卫鸟的传说、帝女死后变为䔄草的传说、钟山之神的儿子被上帝处死后变为鵔鸟的传说等,即属此类,这些传说散漫而不成体系,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存在、自成一体的神话体系,就像现在流传在各个地方的民间传说构不成一个完满自足的体系一样。
希腊神话、印度神话、北欧神话等看似体系完备的神话,其实并非自古即然,它们并非原始宗教的产物,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历代诗人、文人、文献家摭拾、汇辑古代传说故事片段,运用文学想象力和历史编纂学技巧熔炼和再创造的产物。在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北欧萨迦成书以前,并不存在一个叫做希腊神话、印度神话、北欧神话的自在的神话体系。至于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像希腊神话、印度神话、北欧神话那样的体系完备的神话,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北欧埃达那样的神话编纂活动,而中国之所以没有神话编纂活动,则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传统。从《尚书》《竹书纪年》《逸周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以至于《史记》《汉书》以降的浩如烟海的史书,较之那些主要依据口传史料编纂而成的史诗,更真实地保存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因此华夏民族根本不需要神话史诗,也根本没必要为缺少像希腊、印度、北欧那样的神话史诗而感到缺憾甚至自卑。
其实,通常所谓“神话”,不过是指一些关乎创世、人类起源、国家起源之类的宏大话题的古老传说、故事和观念而已,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与传说、故事、歌谣等传统文体相并列的、自成一体的“神话”文体。神话可以各种文体形式而存在,甚至可以图画、符号、建筑、地理景观的形式而体现,神话从来就是各种各样的观念和话语“碎片”,碎片化才是神话的本真状态,作为体系的神话概念(mythology),只不过是一个现代的理论发明,对于这一理论发明,现代神话学尤其“功不可没”。a参见[美]柯克著:《希腊神话的性质》,刘宗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
《山经》呈现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以天地山川群神为主体、以祭祀为表达形式、以地理景观为依托的原始宗教地理学体系,根据《山经》的记述,即不难窥见与这一宗教地理学体系相伴生的原始神话的存在样态。
《山经》记载的众多的上帝栖居之地和众神司掌之山,都是上古宗教祭祀的圣地,是古人祀神祭天的地方,这些场所被古人选作圣地,自然源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景观。圣地一旦被选定,就被赋予了神圣性,这种神圣性需要被标识,以与周围广袤的山川大地区别开来,作为世世代代朝圣、拜祭的场所。对于圣地的标识,可以藉由祭坛、神庙、碑石等人工建造的方式,使之永久性在空间中被标识出来,但是,圣地的具体意义,却离不开话语和叙事。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错综复杂的根系,联系着一个民族的世界和历史。唯有语言,才能将独标孤立的圣地和神迹与更广大的世界、更久远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并将之融汇于族群的共同记忆之中。圣地的意义诉诸语言,以叙事和话语的形式而流传,就是所谓命名和传说。命名,追本溯源,就是对神圣之物意义的保存,而传说则是对神圣之物意义的解说。尽管凡俗之物也需要命名和解说,但是,任谁也不得不承认,能够历经沧海桑田而依然留在大地上的地点和地名,大都是圣地或名胜遗迹,而流传于世的传说也更多是从圣地、神庙、遗墟等神圣景观生发出来的,因为唯有神圣之物才最为人珍视,最值得命名和言说,唯神圣的意义最值得保存和流传。命名与传说皆为意义的自然表露,因此,命名和传说往往密不可分,有命名,必有解说与之相伴,而解说流传既久,即为传说。可以说,命名只是凝练的传说,而传说则是展开的命名,两者都植根于被命名和传说之物的意义。传说大多只能以口头的形式在当地土著、宗教团体中世代流传,随着时过境迁、族群瓦解,这些传说大都烟消云散,消失于时间的长河之中,但只要那些地点还在,这些地点的地名还在,其意义就会被铭记其中,与之相关的传说就不难被后人重新“回忆”起来。正是在此意义上,大地山川的记忆,较之人类的记忆更为坚固和恒久。宗教地理景观(圣地)以及散落于这些景观中的地名和传说,而不是从开天辟地开始说起、按部就班展开的创世叙事,才是“神话”的原始形态。狭义地讲,最初的神话形态,就是传说。《山经》记载的一系列上帝之迹(帝之下都、帝之密都、帝之搏兽之丘、帝之平圃、帝之囿畤、帝台之棋、帝台之浆……)、群神之名(英招、陆吾、长乘、江疑、耆童、蓐收、红光、泰逢、天愚、围、计蒙、耕父……)、神祀之号(天帝之山、帝都之山、阳帝之山、帝囷之山、帝苑之水、帝休之树、帝女之桑……),以及黄帝采玉于峚山、炎帝之女死后化为精卫、钟山之子化为鵔鸟、帝女死后化为䔄草、鲧窃帝之息壤死后化生等传说,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些以圣地、地名和传说形式存在的神话。这些以圣地、地名和传说形态而存在的神话,依托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景观而生发和流传,像草木一样植根于大地,土生土长,它们才是神话的原始形态。
《山经》中除记述了众多散居群山的土生土长的神之外,还于每篇的末尾记载了一系列统领该篇群山的山神及其祀典,如《南山经》三篇后的祀典记述为:
凡䧿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
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稌。
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
尽管各篇之神形象各异,祭品、祭器和仪式的品类和数量不同,记载的详略也多有参差,但其记述的内容和体例高度形式化。每一山列之山少则数座,多则数十座,绵延的里程少则“数百里”,多则“数千里”甚至“上万里”,却由一神或二、三神统领,每一山列的山神形象各不相同,但祀典和祭品却大同小异。如此地域广阔、纲纪严明的山神祭祀制度,显然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自发性的地方崇拜,而只能是出自统一的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意味着这些统领群山的山神,并非基于当地自然环境或地理景观而自然生发出来的土著之神,而是人为的构建。这些山神祀典或许正是主持《山经》的知识团体所筹划的国家性山神祭祀制度。
与散居群山、土生土长的地方性山神皆有专名不同,这些统领群山的神均无专名可以称道,这是这些人为造作的神与上述土生土长的神之间最大的不同。命名基于意义,土生土长之神即源于一方山水对于当地人们的意义,山神栖居的圣地即为意义和神性充盈之域。为了标识、保存、传承这种意义,就必须为之命名,命名在将意义保存于语言和记忆的同时,也为这个地方打上了印记。上文提到的那些土生土长之神各有名号,其所栖居的山丘也各有其名,而且,我们可以想见,在当地必定有相关的神话传说在当地流传。相反,《山经》各篇山神祀典所记的这些无名之神,还只有官方制度安排赋予它们的功能,却尚无令当地土著心领神会的意义,因为没有意义,故无需命名,因为没有名字,这些无名之神也就无法进入语言,更无法生成神话传说,它们就像死后没有墓碑、不会被人纪念的无名灵魂,只是偶尔略过的阴影,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周易·系辞传》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神和神话都植根于天地自然、孕育于宗教、经由“圣人”命名而流传于语言,离开苍天大地的恩惠和启迪,脱离宗教祭祀的滋养,没有命名和语言的意义加持,就不会有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