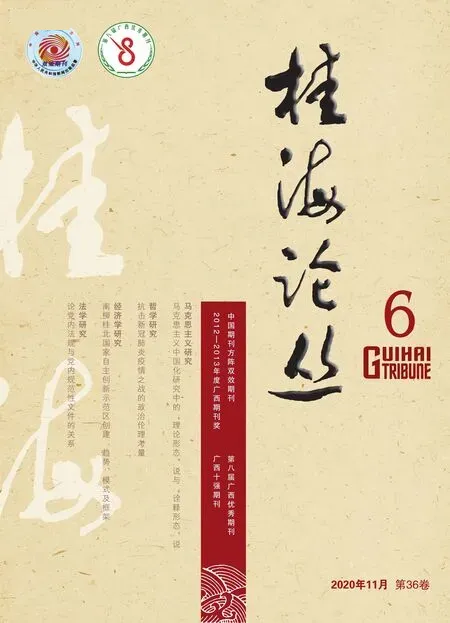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理论形态”说与“诠释形态”说
□周全华,马爱云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
一、“理论形态”说概述
“理论形态”说认为,一个思想体系可以产生出若干个不同的理论表述体系,也即“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成熟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内部的系列范畴、价值内核、重要概念、推理方法、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按其理论逻辑的内在关系,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思想结构[1]。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一个思想结构体系都因时空环境的差异、历史实践的差异、话语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多种理论表述形式,即不同的“理论形态”。后生的理论形态与原初的思想体系,在价值内核、逻辑形式、思维方法、概念、范畴、基本观点、基本原理上,没有原则性的差异,只是在实践方法途径、实践规范、重点选择、话语表述上有若干创新。当然理论形态也可能会有某些思想上的创新,但没有超越原初思想体系的框架。如中国儒学历史上的各流派都没有给孔子增加多少新思想,只丰富了理论表述形式,董仲舒给了它一个泛神哲学的表述形式,朱熹给了它一个思辨哲学的表述形式,王阳明给了它一个唯心哲学的表述形式。如果只是借原初思想资源而发展出全新的思想,那就不是原初思想的新理论形态,而是一种异于旧思想的新思想。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西方的文艺复兴,都是旧瓶装新酒。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就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表达形态。原初思想体系与后生理论叙述体系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而且往往是一源多流。理论体系的建构者除开思想家本人,还有不断相承的后继者。
研究理论形态,并不只是无聊的学术命题。因为原初文本里的思想并不会自动发生历史效应,而思想的多种理论表达形式是出于时代的需要并直接参与现实斗争,这样才可能释放原初思想的潜能量。形式不是消极的,而是能动的,它的能量来自理论形式的构建者,是他们将前人文本中的思想投入新斗争。他们是政治实践者或为政治实践服务的理论家。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先后出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个“理论形态”。依据这种“理论形态”说的分析方法,可以给马克思主义流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特定理论形态予以恰当的历史定位。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世界上先后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叙述形态就有:德国左翼社会党理论形态、列宁主义理论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托洛茨基左倾理论形态等等。
理论形态的研究,亦有学者以文本学方法进行,令人耳目一新。西方马克思学就是以文本学研究取胜。文本学研究文本的所有版本形态、文本的流行路线、文本的改制形态、各不同文本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经典作家,及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著述版本,可以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细微差异。
以流溯源和以源察流,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本,对后来衍生的各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形态进行梳理并揭示其质的属性,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巨大工程。“理论形态”说就是依据马克思原初思想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发生的变化,以内容实质来划分源与流、流与流的差异。理论形态研究者重点是对这些差异,进行其“质”的属性的研究。即质变与未质变。未质变是指保留了原思想体系的本质内核和基本原理,是源“化”为流、根“化”为枝,源流和根枝属于同质的关系。质变是指仅保留马克思原初思想的若干结论和话语风格,而删除马克思原初思想的灵魂。现今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判断,即认为它们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异质的。而对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定性判断则几经反复,现在主流看法是,苏联社会主义因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而日益僵化、需要加以改革,但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形态。其他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东南亚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都是保留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而作时代化和民族化的变通,尤其对其理论叙述体系作了更大改造,赋予更明确的民族形式和时代特征。虽然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有高下、成败、功过之分,但应承认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源流所衍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
以“理论形态”说的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进行研究,目前有几种路径。一是内部比较研究,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关系研究。二是纵向比较研究,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与原典马克思思想体系作“源”与“流”的关系研究。三是横向比较研究,对各民族、各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形态,作“流”与“流”的关系研究。
二、从“理论形态”说中析出“诠释形态”说
如前所述,对同一思想体系,根据不同的时代场域、历史“前见”、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而产生不同理解、并作出不同解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诠释形态”是一个新的概念,是从“理论形态”概念派生而来,本意是要弥补“理论形态”解释力的不足。二者区别在于:“理论形态”属于“建构式解释”,而且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而“诠释形态”属于“注经式解释”,有的可能有影响力,有的可能默默无闻,所以后者没有成为“理论形态”,而只是“诠释形态”。“诠释形态”可以有一定建构,但只是个别创见,没有自成体系。“诠释形态”是指不稳定、不成体系、而又互相关联的“一套解释话语”,它是处于前“理论形态”的东西,还没成形为“理论形态”。而“诠释形态”的“一套互相关联的解释话语”,又与一般的“零散解释话语”不同,后者可以是一次性的,可以是每次有不同的说法甚至矛盾的说法,而“诠释形态”已经形成“一套有内在关联度的解释话语”。不少学者把“诠释形态”归在“理论形态”之中,不加区分。而且除“理论形态”的命名之外,还有五花八门的其他命名:有的称为“范式”,有的称为“拟范式”,有的称为“理论模式”,有的称为“思维方式”。究其实质,大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诠释,根本没形成所谓“范式”“模式”“方式”。
例如,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分为几个发展阶段,认为各发展阶段都产生了各自的“理论形态”,都有各自的理解和解释特征,并分别以“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几个标签,来命名这三种“理论形态”[2]。它们其实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形态”,都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解释话语”,只能归属于“诠释形态”。而“诠释形态”如果要升华到“理论形态”的高度,是有条件限制的:一是必须对马克思原初思想,作出建构性解释和理论的重构;二是具有实践性,即产生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而不纯是书斋里的理论产品;三是产生过重大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四是如果满足了以上三条,但是却走向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则不能算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形态”了。以此标准度量,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形成的“理论形态”,只能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论形态”,则还有列宁主义、欧洲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如果把不同时空下、不同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把这种“诠释形态”,都看作是“理论形态”,那将发生思想史的混乱和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混乱。按照上述学者的观点,如果以“诠释形态”的分析框架来概括,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梳理方法。他们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依次走过的三个“哲学形态”:“理论哲学形态”“实践哲学形态”“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形态”,下面以“诠释形态”说方法作如下改叙。
第一,他们所谓“理论哲学形态”,不宜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的第一个“理论形态”,而只能称为“诠释形态”。它只是一套书本式的解释话语,具有教条主义的特征。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热情的介绍并宣布为自己的信仰,这种解读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这只是一种书本式的“诠释形态”,还远未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形态”。以李达为代表的一批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文艺理论各领域,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但主要是以“理论哲学”思维方式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作出巨大贡献。而王明等取得革命实践领导权的教条主义者,则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可生搬硬套的教条,用于瞬息万变的现实斗争,给革命造成损害。他们实质上亦是以“理论哲学”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斥为“食洋不化”。而毛泽东等实践派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教训,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科学,摒弃了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融入革命实践和中国文化,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哲学”仅仅是对马克思原初思想的书本解读,只能算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形态形成之前的一个铺垫,即有功亦有过的“诠释形态”。
第二,他们所谓“实践哲学形态”,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形态”。这是因为他们把所谓“理论哲学”,当作第一个“理论形态”而不是“诠释形态”所导致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没问题,但以历史逻辑和思想史逻辑来看,则是轻重不分了。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形态”,终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知与行、认识论与历史观、理论与实践的分裂。所以“‘实践哲学’诠释形态”不必另立,更合乎思想史习惯。
第三,他们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形态”看作第三个理论形态,也是不合适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生长,学者们尝试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质,实践被上升为本体的地位,试图替代物质本体论,以与机械唯物论最后划清界限;并以实践的物质性,来与唯意志论划清界限。他们所谓“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标签,只能是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新理解和新解释的一种尝试,只能是一种“诠释形态”,还不是“理论形态”。改革开放后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理论形态”,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用“诠释形态”概念梳理几个有影响的“标签”
用“诠释形态”概念来解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些动向,可以澄清一些滥贴标签造成的混乱。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领域,目前出现了四个“拟范式”,并将这几个“拟范式”分别标签如下:一是学界将以前中国学者不参与世界对话、甚至不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意见对话的、封闭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称之为“以马解马拟范式”。其实“以马解马”毫无创新和建构,不能称为“范式”或“理论形态”,只能归属于对文本的注经式解说、宣讲,有普及之功,但算不上是一种“诠释形态”。二是某些学者自谓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最新高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称为“以新解马拟范式”。多数学者不以为然,认为尚在起步走向严格学术规范的研究是不必如此虚张声势的。“以新解马”是凌虚蹈空口号,没有学术根基,并未达到“诠释形态”的功夫。三是以现代西方各种哲学尤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近四十年来渐成气候,其成果广泛分布于国内各重要刊物,学界不少人认同其是“以西解马拟范式”。“以西解马”打开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视野,活跃了研究思路,开拓了多种解释和比较的可能,逐渐形成多种各自为学、互不相联、极不稳定的准“诠释形态”,但还远未达到定于一统的“理论形态”的高度。四是一批有国学功底的学者,尝试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点,研究二者对接的可能性,被称为“以中解马拟范式”。有些学者认为“以中解马”的“拟范式”可以成立。如冯契就曾自评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已经和中国传统结合了,因此不能越过它,而只能经过它,才能前进”[3]。冯契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智慧说三篇》(人的自由和真善美、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被学者认为“有自己的范畴和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4]。冯契有自己的创见,有体系建构,超过许多一般的诠释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但以前述“理论形态”的几个标准,如“实践性”和“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等等来看,则难以定论冯学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
也有不少学者们认为高清海有过四次重要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苏联哲学教科书解说范式的批判,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解说范式”。但这些贡献仍未达到建构新“理论形态”的高度,而只能归属于更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诠释形态”。高清海在80 年代初期改革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第一次作为是大胆颠覆了“苏联哲学教科书诠释形态”,但还未建构新的“诠释形态”。他的第二次作为是在80 年代中期提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的确是提出了新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诠释形态”。他的第三次作为是在90 年代提出“类哲学”思想,重新认识人,但这是至今尚未完成的“人学的诠释形态”。他的第四次作为是在本世纪初又提出“中华民族需要自己的哲学”的民族主体思想”其意图是要建构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理论”,而不再是限于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或“诠释形态”[5]54。这仅是提出了一个口号,并未建构实质内涵。
学者们跟进高海清的思路,纷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诠释形态”作进一步描述,有的学者继续嗜好冠以“范式”的标签。其一,他们说建国头三十年是“教科书范式”,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统一标准,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包括中国历史、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学、法学、伦理学、文学史、文艺思想史和美学等几乎全部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研究多半只是做简单裁判——唯物论的还是唯心论的?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进步的?人民的?还是反动的没落阶级的?自以为只要给所有文化遗产贴上了上述标签,就算完成了研究。这种给古代先贤扣帽子式的研究,遇到不少矛盾却又视而不见。这不能算是“范式”,而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械唯物论倾向的诠释形态”。其二,他们说20世纪80年代为“教科书改革范式”,突出“实践”这一核心范畴,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历史规律与人的意志等根本问题的意涵。这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论诠释形态”,但不能高估为一个新“范式”。其三,他们说20世纪90年代后为“后教科书范式”,马克思哲学研究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如人学问题、异化问题、卡夫丁峡谷问题、亚细亚社会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等等。“后教科书范式”就是没有“范式”——实质是没有统一的“诠释形态”。他们引用库恩的“新旧范式交替时期”概念,即旧范式失范而新范式又未成的“危机时期”[6]。其实更切实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处于新旧“诠释形态”交替之际,尚未形成新的公认一致的“诠释形态”,而不宜动辄使用“范式”之类的大词。
也有学者以“思维方式”的标签,论说建国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依次走过三个“思维方式”。一是所谓“实体性思维方式”,突出世界的物质本体性,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困在认识论之中。这仍是机械唯物论倾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诠释形态”。二是所谓“主体性思维方式”,突出“实践”的地位。这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诠释形态”。三是所谓“后主体性思维方式”,“实践”成为本体性范畴,此前对实践与理论关系的理解,易走向“理论与实践合一”的实用主义立场[5]52。这个“后主体性思维方式”实际仍未超越出“实践唯物主义的诠释形态”而是寄生于其内。
还有学者继续用“理论形态”的标签,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依次走过了三个“理论形态”。一是“实事求是理论形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二是“主观能动性理论形态”,是企图超越客观规律和历史阶段的“主观能动性”论。三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形态”,这主要源于市场经济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7]。
另外还有学者以“理性模式”的标签,“从理性自身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看到三个“理性模式”的切换[8]。的确,“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进步和变革,都是以理性的解放和批判为先导的,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以理性审查一切,二是对理性自身的审查。”[9]
一是“信仰理性模式”,其特点是崇尚神圣、权威、经典、传统。“信仰理性模式”导致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哪一部分是救国的科学工具,哪一部分属于理想社会的信仰。“李大钊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成为组织群众运动的‘宗教的权威’,他预言: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体的运动所风靡。”[10]直到毛泽东才明确区分了信仰与科学,他把马克思关于行动指南的那部分叫做科学。二是“认知理性模式”。毛泽东运用“认知理性”,区分“从实际出发”与“从教条出发”这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诠释形态”纠正为“实事求是诠释形态”。三是“反思理性模式”,“信仰理性”审视信仰,“认知理性”审视真理,当着理性审视理性自身时,这就是“反思理性”了。“反思理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为审视对象。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科学理性再度觉醒,恢复了实事求是路线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诠释形态”,然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形态”——“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学界又从“认知理性”前进到“反思理性”,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破除对原“教科书哲学”的迷信,从“唯上”“唯书”不“唯实”的思维定式解放出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作重新定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诠释形态——“实践唯物主义”。所谓实践唯物主义也仅仅是一种“诠释形态”而非“理论形态”,但可以为继续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服务。“实践唯物主义的诠释形态”的出现,也不仅仅是“反思理性”的贡献,其间仍有“认知理性”和“信仰理性”的共同作用,没有“认知理性”对实践困境的探究和对实践经验积累的提炼,没有“信仰理性”所提出的理想追求和实践要求,就不会有从理论到理论的“反思理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