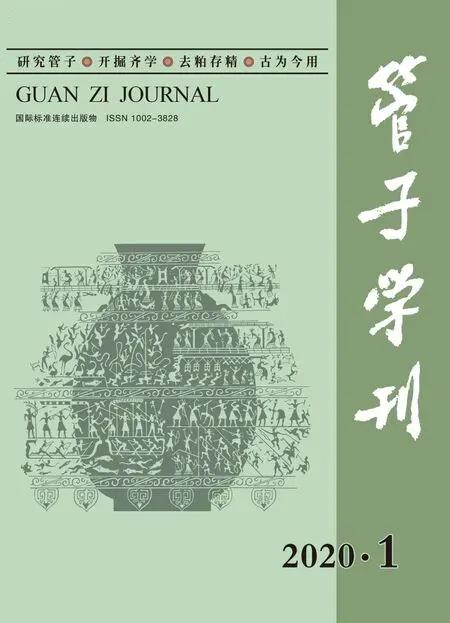法家学说与先秦秦汉反腐败制度创建
邱 涛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中国由原始社会开始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还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过渡时期,对私有财产日渐增长的追逐,在有限的社会资源面前,就已导致贪贿的产生。早在黄帝时,就有“庶人之贪者”蚩尤作乱,后来到尧舜时期又出现了著名的“四凶”,其中缙云氏的饕餮“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1)《左传·文公十八年》。“四凶”,是指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氏族首领中出现的与“大道既隐”相适应的、践踏元社会道德风尚的“不才子”。他们是帝鸿氏(一说黄帝)的浑敦、少昊氏的穷奇、颛顼氏的檮杌和缙云氏的饕餮。,与后世贪贿、聚敛者的形象相契合。当然,维护公正的原始道德与原初的贪贿行为作斗争,在这时主要还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与对统治权力的掌控斗争交织在一起。
中华民族早期的政治伦理,既承继了去古未远的原始道德遗风,也在于人们逐渐认识到贪贿淫逸之危害,小则身败名裂,大则亡国灭族。有贪贿的发生,必然就会有反贪贿的行动,必会产生提倡清廉勤政、贬斥贪贿暴敛和骄奢淫逸的思想。舜就说:“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表明自己做人要正直清明的心迹。并告诫臣下:“朕塈谗说殄行!”他这是在明确表示自己厌恶贪残暴行。他还教导夏禹,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虞夏书·舜典》)。上行下效,舜提倡并践行勤政清廉,他的下属也有同样的言与行。伯益说,要“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皋陶说,要“直而温,简而廉”“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他还总结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治)而敬,扰(顺)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实),强而义”。(《尚书·虞夏书·大禹谟·皋陶谟》)可谓一套完满、辩证的道德格言,也反映出当时一定的社会现实,为先秦的反贪思想以及到秦汉的制度创建奠定了基础。
一、先秦反贪思想传统
针对夏商西周,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政以贿成”的状况,不少正直有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不遗余力地谴责贪贿淫逸、横征暴敛的行为。他们的言论构成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百家争鸣中,创造了中国早期民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从理论上说明贪贿的反常理、非礼非法性;指出贪贿的涡国殃民、贪贿者破家亡身的必然性;掲露、谴责暴敛的严重程度及其丑恶行径;提倡淸廉勤政,树立清高勤苦的人物典型。
孔孟、老庄把贪贿暴敛比作盗贼。春秋前期鲁国对宫室有“丹楹刻角”之举,受到当时人们的非议,孔子批评臧文仲早年“不仁者三,不智者三”,其中有“废六关,妾织蒲”“作虚器”,就与此有关,尤涉聚敛问题(《左传·文公二年》)。 “废六关”亦作“置六关”,是设置六关以征税;妾织蒲,卿大夫之家与民争利,古为一禁;“作虚器”指私蓄大龟并作室以居。故孔子说:“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因蔡国出产大乌龟,臧文仲收藏大乌龟壳是为了占卜求福之用。臧文仲私自把大龟藏住在一间屋子里,屋内有雕刻山形花纹的斗拱和画水藻纹的梁上短柱,这与天子为占卜求福、藏大龟的“丹楹刻角”的豪华庙堂一样,自然属于奢侈淫逸之类(《论语·公冶长第五》)。
孔孟的“仁政”学说与贪贿不两立,孔子留存的言论虽不多,然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春秋后期,季氏当政,重聚敛。一次,季康子忧虑盗贼多,问政于孔子。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一句话把好聚敛的季康子和盗贼摆在同一位置上,季氏如能节制自己的贪欲,上行下效,百姓也会知耻而不去干偷窃之事(《论语·颜渊第十二》)。季康子在鲁哀公十一年“欲以田赋”,即在宣公十五年实行的“初税亩”基础上再对农田征军赋, 增加一倍赋税。季康子派自己的家宰、孔子的学生冉有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以“丘不识也”为由,不回答,但私下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让冉有劝季氏不要太过贪婪,否则最后按亩征税也会不满足的。但季康子还是专横地实行了征“田赋”,而冉求不听师言,协助季氏征田赋,很令孔子生气。对此,孔子坚持批判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2)《左传·哀公十一年》《论语·先进第十一》。引文中“如是则以‘丘’亦足矣”,指成公元年“作丘甲”所定一丘出赋之数,“以丘”就是按丘征税,征田赋按丘征就可以了。《礼记》中也记载了以前孟献子说过的当官不能聚敛、不能与民争利的规定:“畜马乘(士人初晋为大夫者),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卿大夫),不畜牛羊;百乘之家(拥有采邑的大贵族),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礼记·大学》)孔子认为那些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聚敛钱财的大臣连盗贼都不如。
战国时代,反贪思想进一步发展,持续揭露、谴责暴敛贪利的行径。
老子以简要而切中要害的语言告诫统治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生之厚,是以轻死”。 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老子指出聚敛是违反天道的,是无道。老子反对统治者的贪欲巧诈,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是看透了当时政治的诈伪贪欲的一面。他说:“朝甚除,田甚荒,仓甚虚;服文采, 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盗竽非道也哉”!这是把聚敛财货比作盗首(3)《老子》,第五十七、七十五、七十七、五十三章。。庄子则把国家统治者比作窃国大盗,“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箧第十》)墨子也有类似比喻:“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墨子·耕柱》)
孟子的学说,开宗明义就告诫统治者不正当的“利”的危害:如果国君一味地考虑“何以利吾国”,大夫们一味地考虑“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则一味地考虑“何以利吾身”,那就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为什么呢?一方面,“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另一方面,就如他所尖锐地谴责的王者一样:“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因此,孟子强调“仁政”,只有仁者才应该居于统治地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没有法律制度,朝廷不守道义,工匠不守尺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 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这是极言最可怕的状况,无礼无学而“贼民”者即贪欲无厌坑害人民的官吏得势猖獗,那么国家的灭亡就快了(《孟子·离娄上》)。孟子不限于揭露、谴责贪贿暴敛,还提出消除这种状况的理想方法,他规劝统治者恢复周文王治岐时实行的王政,回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大同”;“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人们都讲道德,即便用棍棒也能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他提出的仁政项目和提出实行的井田制,都包括反聚敛、薄赋税的内容,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孟子所说的这一内容:“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4)《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滕文公上》。先公后私,这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这是孟子恢复井田制主张背后所要强调的一个核心价值。荀子则指斥:“乱世则不然,汙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綦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虺,恶之如鬼。”(5)《荀子集解》卷七,《王霸篇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47页。这是深刻地揭露贪贿盗窃和权谋之害民,必然招致人民深恶痛绝。
韩非揭露为臣而奸邪者有“八术”“八奸”,其一为“养殃”,透露了当时官吏们“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是为了“娱其主而乱其心”,这是“上下交征利”的一种,就是迎合君主奢淫享乐,而“尽民力,重赋敛,顺其所欲”,以便自己“树私利其间”。韩非还揭露当时出现的卖官鬻爵之弊:不论贤与不肖、有无功劳,只“用诸侯之重,听左右之谒,父兄大臣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勤,有功者堕而简其业。此亡国之风也”(6)《韩非子集解》卷二,《八奸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6-39页。。这就指出卖官这一战国时期新出现的贪贿花招,其恶果会导致亡国。韩非子在《五蠹》篇里,更深刻地论述了行贿、买官鬻爵会导致政治沦为市道,奸商横行,生业荒废,会使国家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行货贿而袭当途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于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结果,“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财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7)《韩非子集解》卷十九,《五蠹第四十九》,第350页。。有外敌时没有人去打仗,平时没人生产,国家怎能不危险?这是韩非子要摒除的“五蠹乏民”之种种恶相,千载之下,犹可为镜鉴。
韩非子还指出:“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俸重无前,俸重无前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解决之道是“任事者毋重,使其宠必在爵;处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禄。故民尊爵而重禄”,“则国治(8)《韩非子集解》卷十八,《八经第四十八》,第337-338页;卷三,《十过第十》,第40页。”。韩非又提出政治上的“十过”,其“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四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他认为没有禄外的私利,才能消除官吏贪贿腐败,“处官者无私,使其利必在禄”,“故下明爱施而务赇纳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利以弍主威,行赇纳以疑法。……故君轻乎位而法乱乎官,此谓无常之国”。韩非子认为“有道之国”必须使“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9)《韩非子集解》卷十八,《八经第四十八》,第337-338页;卷三,《十过第十》,第40页。。这是从理论上说明臣吏贪贿、求私利对君主权力的危害,是法家学说中的精华。
在揭露、谴责贪贿聚敛的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也注意弘扬正气,从正面倡导和清廉勤政的品质,树立廉洁勤政人物典型。这里既有往溯上古大禹、伯夷、叔齐等先贤,也有表彰时贤如鲁国季文子、楚国令尹子文、齐国的晏婴等。孔子把伯夷、叔齐与齐景公作对比,清浊分明。他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徳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孔子又称赞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也!”孔子自己也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后来,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视恶声”,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尽心下》)
楚国的令尹子文的廉政勤政就为人所盛赞。后人斗且说:“昔令尹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 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10)韦昭注:《国语》卷十八,《楚语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七年刊本,第8页。孔子称赞说这就是“忠啊”!
春秋战国时期,构成反贪倡廉思想传统的,并非只有那些著名思想家的学说,也有许多政治家的言行。晏婴竭力批评和防禁齐景公的贪欲暴敛,他本人则是一生节俭、清廉的楷模。晏婴也是第一个提出“廉政”命题的人。他说“廉政可以长久”,好比“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接着又以石比喻廉政不能持久的道理。当时齐景公问“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晏婴“对曰: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当时传颂晏子节俭,他对古人极为重视的自家丧祭都极为俭约:“一狐裘而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擀衣濯冠以朝”。孟子说“晏子以其君显”,是对晏子廉俭并谏诤制约齐景公的贪欲聚敛、使其政权不至于在当世崩溃而说的(11)《晏子春秋》卷四,《内篇问下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2页;《礼记》中的《檀弓下》《礼器》《杂记下》;《孟子·公孙丑上》。。春秋后期,楚国令尹、司马等热衷聚敛。令尹子常 (囊瓦)是出名的一个。一次,他问大夫斗且“蓄货聚马”之事,斗且未答,回头对他弟弟说:楚将亡吧!或者令尹将完蛋,因为“令尹问蓄货积实,如饿豺狼焉!”“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死无日矣!” 他认为“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害民之财用”,并将令尹子文的廉与子常的贪做对比,指斥子常作为楚王的辅佐,却在诸侯间没有好名声,“民之赢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瑾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蓄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12)韦昭注:《国语》卷十八,《楚语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七年刊本,第7-8页。这是透彻说明贪贿“蓄聚”和“蓄怨”是成正比发展的至理名言。
当然,春秋战国是流传下来的也并非都是反贪倡廉的思想。战国末年,贪贿腐败风气日趋严重,一些统治者的执政思想也出现扭曲。《吕氏春秋》记载:卫嗣公“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对而人民的不安。卫嗣公说:这些老百姓“民甚愚矣”!征敛粮食是为人民的,他们自藏粮食和把粮食藏到国库,“奚择”,有什么需要选择的呢?这并非笑话,因为战国时加重征敛是常事。不过卫君所谓的“民愚”,倒不如说是他本人“利令智昏”(13)《吕氏春秋》卷十八,《审应览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18-219页。。辩士中也出现了同流合污的言论,策士苏代对燕国君说:“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14)《战国策》卷二十九,《燕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七年刊本,第15页。这是将“进取”与“廉”、“仁义”对立起来,反映当时颓风严重,连辩士们也为贪贿张目,也可谓是一种千古“妙”论!
战国时期反贪的言论如此尖锐、深刻,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可知当时社会尤其是官府贪贿成风,乃至前代所无的卖官鬻爵事件亦不少,只是失之记载或是有所记载而没有流传下来而已。
二、先秦监察机制的初立
上古三代直接脱胎于原始社会,多沿用习惯法。尤其到了三代,处理或监督各种非法行为常用“刑”,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禹刑》《汤刑》《九刑》,就是夏、商、周的刑律。今天可见商代甲骨卜辞中记录的用刑很多,就是明证。
夏朝刑罚,《禹刑》规定主要为死刑和赎刑,“昏、墨、贼”构成死刑,其中“贪以败官为墨”,就是以贪污腐败而败坏官事,就是犯了不廉洁的“墨”罪。这是古代将贪污腐败称为“贪墨”的源头之一(《左传·昭公十四年》)。
商代刑法,在《汤刑》中规定对“总于货宝”,即贪财之罪用“大刑”,重惩。而且臣下对国王有“三风十愆”的恶习“不匡”,要处以“墨刑”。
到西周初年,从《尚书》的《康诰》《费誓》等篇中,可以看到以“常刑”处罚盗窃劫掠一类的行为。到周穆王时的《吕刑》才出现一定的诉讼程序,刑罚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化,不过当时断案仍有一定的随意性。到春秋中期后,少数诸侯国才正式制定、颁布刑律,仍遇到阻力。郑国铸刑书,遭到晋国名臣叔向的批评;晋赵鞅铸刑鼎,遭到孔子的反对。孔子、叔向认为,刑法只能掌握在官府、贵族手中,“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否则,人民掌握刑书,“将弃礼而争于书”,并按刑律与统治者争论,反而难办。所以要坚持礼治,沿用习惯法。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旧制度的坚冰终被打破,此时终究出现执法的事例,如反对“铸刑书”的叔向还是按刑律原则惩处了叔鱼(即羊舌鲋)等人贪贿不轨的行为。
春秋晚期,我国开始颁布成文法。公元前536年郑子产“铸刑书”,将刑法铸于鼎上,公示于众。公元前513年,晋国赵简子“铸刑鼎”,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律铸于鼎上公之于众。到战国时期,各国推行法制,以法治国。在诸子百家学说中,也以法家最盛,代表人物多被统治者任用以变法图强。法家主张摒弃“不为刑辟”,要求“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15)《韩非子集解》卷十七,《定法第四十三》,第304页;《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2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战国初年李悝颁布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法经》。其中第五篇《杂律》就涉及对“借假不廉,淫侈”等贪贿行为的惩处(16)李悝《法经》早已失传,篇目留存于《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刑法》。。
这一时期,监察官员的机制,正如《尚书·梓材》说“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说明自古就有监督,并要求监察官员公正不偏颇。
在夏代,就有负责监察之官——“啬夫”。啬夫又有区分,“吏啬夫为检束群吏之官;人啬夫为检束百姓之官”(17)《左传·昭公十七年》;尹知章:《管子注》,转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5页。。 到周代,除了监察官员外,还有两类监督贵族、官员贪贿盗掠行径的机构:一是司法系统——司寇,一个是财政会计系统——大宰。
《周礼·秋官·司寇第五》记述大司寇的职能:一是“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以圜土聚教罢民”,即把“坏人”关入监狱进行教化。二是以“五刑纠万民”、“五罚”分治野、军、乡、官、国,其中“四曰官刑,上能、纠职”。大司寇下属的士师又以“五禁”分治上述区域,“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治之”,都是治理官员包括惩治贪贿行为在内的。《尚书·周官》记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与《周礼》的记载相呼应。而在西周金文中多见司寇协同司土(徒)、司马(合称“三司”)执行政务。春秋时期几个主要诸侯国设有司寇,少见专门治理狱讼,而承继自夏朝以来的传统,由“理”官治狱。据记载,晋国有司寇,而断狱则为“理”官;齐国的断狱官也称“理”官或“大司理”(18)韦昭注:《国语》卷十四,《晋语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七年刊本,第3-4页;《管子·小匡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5、129页。据记载,从夏代开始,治狱官就称为“大理”“理”。《礼记·月令》注:“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处理朝官的案子,西周和东周都是由当政大臣裁断。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大司徒“帅其属而掌邦教”,即掌教谕和考察官员,分三年大比和年终考绩的两种情形。其中正岁命令教官:“各共尔职,修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实施对官吏的监督。小司徒根据大司徒职权来管理其属官,“及三年则大比”,岁终有考核和赏罚,“令群吏正要会政致事”。正岁率属官学法令,宣告“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并“修法、纠职”。
对于哪个部门应该职掌百官的监察,《周礼·春官》中虽载有“御史”,但《左传》中并无记载,而《周礼》一书成于战国晚期,可见在战国晚期以前,对于监察部门并无明确记载,这时的监察制度在官制系统中的位置较为模糊,反映出国家机器还在逐步完备的过程中。而这时有刑无法,“国有常刑”是针对被统治阶级,针对贵族、官吏不过是一句套语,当时就有明文规定对王族及勋贵的减刑办法。《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交给天官甸师职内处理。还定有“八辟”之法,凡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人可减罪。这样,对官员的纠察便大有自由裁量的伸缩余地了。
根据《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西周由专设的财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国家的贡赋等常规收入和支出,规定“以九式均节财用”,将用财的节度、开支分作九类。大宰之下专设“司会” 一职,负责掌管收入来源和调度、节约开支;掌握各处官府钱财出纳所登记的副本,作为考察群吏办事成绩的依据;还要负责把下属“司书”税敛的记录、“职内”的赋入和“职岁”的赋出,相互参校,按旬、月、年做出统计。另设“外府”一职,掌管“邦布之入出”即货币的收入,按制度供给各项“邦用”,“岁终则会”即年终作一次结算。这样的财政管理,对春秋战国及以前时代而言,颇为严密,如能严格执行,能极大地杜绝贪贿的发生。不过,这种严密制度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然是一个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完备的,且多含有理想化的成分。而前述的众多贪贿事例,几乎都是在制度外发生的,统治者公然以财物乃至土地行贿,也不是一般财政制度和财政部门所能制约的。以公家钱财办私事的贪污贿赂,典型者如春秋晚期陈国辕颇“赋封田以嫁公女,有馀以为己大器” 一事,倒是能从财务记录中查出来。
战国时期,设置有主管财务的职官。《史记·赵世家》记载,徐越向赵列侯建议“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符合统治者的要求,而被任命为内史,“所与无不充”。可见,内史在战国时期是负责财务、税收的官员,从上述内容看,负有监督财政出入的责任。
战国晚期,在前述两大监察系统之外,又出现了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为国君掌握百官万民的行为动向,以保障国家法律、政策的实行。《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载有“御史”,其人员配置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共计192人。《周礼》中记载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随侍国君左右,掌书记、法令。《史记》记载的一段著名史实:公元前227年,赵惠王与秦昭王会于渑池,秦昭王要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王受辱,其臣蔺相如端一瓦盆力逼秦王“击缻”助乐,“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明证。
战国时期,秦、齐、赵、魏、韩等诸侯国均有御史,御史掌文书、法令,中央各部门、地方各郡县的文书均集于其手,使御史成为最了解全国情况的官员,自然就日渐成为国君了解全国情势的耳目而带有监察的职能。为了行使监察职能,御史须随时派属员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荀子就说:“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19)《荀子集解》卷八,《君道篇第十二》,第161页。这不仅是说到国王应通过御史了解各地情况,而且国君还要派可信任的“便嬖左右”,到各地去了解“国君耳目”所不能达到之地的民情。战国时期,御史监郡县的制度已经出现。《战国策》中就记载了魏国原国都安邑(魏惠王迁都大梁后,置安邑为县)监郡县御史的递补情况:“安邑之御史死,其次(副手)恐不得也。输人为之谓安令曰:‘公孙綦为请御史于王,王曰:彼固有次矣,吾难败其法’,因遽置之。”(20)《战国策》卷二十八,《韩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七年刊本,第12页。就是说当时的体制,御史的任命由副手依次升补。
为了规范御史人员出使、监督各地的行为,防止出现滥用经费或接受地方宴请馈遗的情况,当时还规定了御史部署出差的伙食标准。据《云梦秦简·传食律》记载:“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分升一,菜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除了规范之外,从中也可见御史的属官有在秦国属第五等爵的大夫(秦制,爵大夫以上,主一车,属员三十六人,“令与亢礼”,即县令须以对等的礼节来招待),第六等爵的官大夫,普通属员“卒人”。
综上可见,无论是行政监督还是财政制度的监管,在上古三代时期都不完备或诸多实际不能执行的情况,到春秋以后才出现了某些制度,形成了一定的机制。这些都是由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社会发展程度所决定的,为中华制度文明之初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秦汉时期对先秦法家反贪思想和监察机制的继承与发挥
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后,法家思想就长期居于秦国政治的主导地位。法家思想在战争年代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的力量去争取胜利,但存在过于刚强而少弹性的理论缺陷,故在和平发展年代,不宜作为国家政策的唯一指导思想。只有文武并用,方能长治久安。秦汉长时段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不过,法家政治文化在法治反贪领域,有儒、墨学说难以比拟的理论建树。
首先,法家较早意识到官吏腐败对国家的严重危害性。《商君书·修权》明确指出:“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21)《商君书·修权第十四》,第25页。这是把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大臣、“秩官之吏”,比作社会的蠹虫,指出其存在必将危及国家安全,应及时清除。
其次,法家认为不能把各级官吏视为理想的圣君贤相、道德完人,尤其是在那个“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22)《韩非子集解》卷二,《有度第六》,第24页。的时代,故强调借助于法律和刑罚的力量来清除贪官污吏。韩非就说:“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23)《韩非子集解》卷二,《有度第六》,第26页。法家思想认为,好利和私欲是人性之本能,君臣关系本质上不过是利益交换关系,奢望官吏们不去追逐私利、自觉廉洁奉公是很难的,“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只能以严刑酷律震慑官吏,使他们不敢去贪污受贿,“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24)《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开塞第七》,第39、17页。。为了使刑罚对官吏真正具有威慑力,法家提出了轻罪重罚和加罪两项立法原则,企图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秦律·法律答问》对行贿一钱即处以“黥城旦”重刑的规定,正是这一原则在反贪领域的运用。在秦统治者眼中,重要的不在于行贿数量多少,而在于是否为行贿、受贿的性质,对官吏贪赃枉法、触犯刑律的都要加重处罚,对官吏贪贿行为的威慑效力是明显的(25)法家思想代表作品之一的《商君书》中就已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参见《商君书·赏刑第十七》,第29页。。
第三,法家主张“不分贵贱亲疏,一断于法”,强调“刑无等级”。《商君书》说:“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6)《商君书·赏刑第十七》,第29页。《韩非子》也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7)《韩非子集解》卷二,《有度第六》,第26页。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在惩治贪贿时不能因贵废法,法外施恩,尤其要防止君主亲近者、女宠说情, 干扰反贪贿。韩非子反复强调:“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女妹私义之门不待次而宦”(28)《韩非子集解》卷四,《孤愤第十一》,第59页;卷十七,《诡使第四十五》,第317页。。如果听任权贵请托之风盛行,想控制住腐败是不可能的。二是功是功,过是过,不因功废法,不以功抵罪。对依仗功绩而滥行贪贿者,依法严惩,不因其以前的功绩贡献而心慈手软。为了避免官吏中出现逾越法律约束的特权阶层,法家强调君主也不能任意越法行事,《商君书》说:“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9)《商君书·修权第十四》,第24页。虽然封建专制社会的特点是有凌驾于社会制约力量之上的特权者存在,但这种守法意识对于加强反贪是极为宝贵的。
秦王朝虽然很快就崩溃了,但它集战国政治改革之大成而创建的政治体制,正如司马迁所说是“法后王”,为中国各封建王朝所承继,而不仅仅是汉承秦制而已。在监察体制上,秦已初步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由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郡守(兼)、县令长(兼)、县御史(主吏掾)等构成的较为完备的监察机构,制定了确保各级官吏廉洁奉公、惩处贪污腐败的监察法规。
秦中央监察机构的最高首脑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官始于秦。”《汉书》记载:“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缓,掌副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御史大夫的职权比较宽泛,包括代皇帝起草诏令、受皇帝差遣完成重要使命、辅佐丞相处理军国大事等,但其职责并不是一般地协助丞相处理政事,而是负有对丞相的监督和牵制之责,监察、纠劾百官是其最主要的一项职责。御史大夫的设置,是秦王朝监察机构发展的重要标志。秦御史大夫的属官很多,最重要的有二丞:其一为御史丞,其二为最重要的御史中丞,“殿中兰台,秘书图籍在焉,而中丞居之”(30)《宋书》卷四十,《志第三十·百官下》。。由于御史大夫职尊权重,主要精力往往在帮助和监督丞相总理国政上,因此公署居于宫廷之中,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御史中丞便统领众御史,具体执行对朝廷内外高级官吏的举劾案章,行监察大权。秦汉体制均是如此。
侍御史,史籍中简称御史,秦代重要的中央监察官员,掌管中央的奏章、文书、档案、图籍和地方的上计簿籍等,具体执行监察百官的任务。其权力还不止此,郡、县等地方长官“岁雠辟律于御史”(3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尉杂》,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页。,说明秦御史有监察朝廷律令实施状况的权力。侍御史在制度上归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统辖,但实际上往往以皇帝特使的身份直接承皇帝之命处理重大事项,如秦始皇坑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公元前211年(始皇三十六年),东郡民有于陨石上刻“始皇死而地分”者,“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3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这都表明了秦御史作为监察官的重要地位。
秦王朝以严格的监郡御史制度来实行对地方的监察。秦王朝在每郡皆设一名监郡御史,其官秩虽仅六百石,但权力颇大,是一郡中最重要的监察官,对郡守和郡府其他官吏都可行使监察权,监郡御史不时向朝廷汇报,使朝廷对该郡情况了如指掌,起到强化统治的作用。《史记》记载: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3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及裴骃《集解》。。同时,监郡御史还拥有监察以外的其他职权,如领兵作战,刘邦起事后,率义军据丰,“秦泗川(郡)监平将兵围丰”;如开凿渠道,当秦始皇命屠睢进攻越族时,奉命修建灵渠以运军粮的就是监郡御史禄;如举荐人才,秦泗水郡的监御史就曾举荐萧何到朝廷做官(34)《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第九》。。显然,监郡御史的设置是战国以来监察制度的发展,是秦始皇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其作用在于监察和牵制郡守,以防止其权力“太重”及以权谋私(3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四,《汉制依秦而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161页。。
郡守作为秦代最重要的地方官,不仅握有本郡行政、司法大权,而且有监督下辖县、乡各级官员的监察职能。两汉郡守以“行县”方式实施对辖区的监察权,就是源于秦制。
县令、长,也是秦代重要的地方官,不仅握有本县行政、司法大权,而且有监督下辖县乡等各级官员的监察职能。秦代各县还有辅助令、长行使监察权的县御史,如秦简中记载墓主喜在秦王政(始皇)四年任安陆(今湖北安陆北)御史(36)《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第6页。;主吏掾也是县中执行监察职能的僚佐,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办之”,“文无害,有文无所枉害也,律有无害都吏”(37)《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及司马贞《索隐》、裴骃《集解》。。尤其是主吏掾的职掌:无害都吏,即汉代负责监察的郡督邮的前身,如《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秦末,萧何担任的主吏掾一职,就与无害都吏性质较为接近。
从秦的监察机构的组成可以看出,秦王朝已经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网,居于中心的是独揽帝国专制权力的皇帝,御史、监郡御史等则是他的主要耳目。但郡、县两级监察机构相对薄弱,是秦代监察系统的问题所在,直到汉代确立刺史察郡、督邮察县、廷掾察乡制,这一缺陷才得以弥补。
秦代不仅设置了监察机构,配备有数量较多的监察官员,而且有细致、严厉的监察法规,以残酷的律令来慑服各级官吏,避免陷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腐败泥潭。从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代虽没有专门的监察法规, 但各种法律文书中均有较丰富的监察内容。
《置吏律》是有关任免官吏的专门法典,秦王朝通过这些法典对担任官吏的年龄、经历、学识等条件,作出了不少限制性规定。《法律答问》中规定,对不执行朝廷政令的“犯令”“废令”官吏,都要处以流放以上的惩罚,即使已经免职或调任,也要再加追究。此外,还有大量处罚官吏贪贿违法行为的具体规定(38)《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4-95、165-166、171、175、178、211-213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规定,不准私自挪用官府资金,见“府中公金钱私貣用之,与盗同法”。《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规定,禁止官吏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侵吞官府财产。秦代法律规定,要对各地官府仓库定期进行检查,新旧官吏职务交接时,也要依据籍簿开仓核实。如有不符的,就要处罚。如“计校相谬也,自二百廿钱以下,谇官啬夫;过二百廿钱以到二千二百钱,赀一盾;过二千二百钱以上,赀一甲。人户、马牛一,赀一盾;自二以上,赀一甲”,就是希望通过严格的检核措施,防止官吏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家财物(39)《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5、125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规定,处罚断案不公正,乘机收受贿赂,即“论狱何谓不直?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在官吏上下其手的断狱过程中,往往意味着行贿、受贿行为的泛滥,故秦对断狱不直者要“致以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时就“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40)《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1页;《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赎罪,即秦代赎耐、赎黥一类可缴纳钱财赎免的罪,官吏判这种罪不公正,往往存在贪污舞弊行为。《法律答问》规定,“赎罪不直,史不与啬夫和,问史何论?当赀一盾”,可见秦律对此类行为处罚之严。
秦律禁止官吏私自调用官府人力、物力牟取私利。《秦律杂抄》上载:“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就是对自佐、史以上官吏利用驮运行李的马和看守文书的私卒为个人贸易牟利的行径,要处以流放的严惩。《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匿户及敖童弗傅”“傅籍不实,匿户匿田”,往往涉及隐匿户口和田地,以躲避摇役,不缴纳户赋、田租等问题,多是官吏与豪强勾结,徇私枉法的结果,故法律规定当禁止并严加惩处(41)《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33、222页。。
秦律对行贿、受贿的处罚极严。行贿者应受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甲诬乙通一钱黥城旦罪,问甲同居、典、老当论不当?不当”。这一条律文说明行贿一钱应判处黥城旦之刑罚。又规定,“知人通钱而为藏,其主已取钱,人后告藏者,藏者论不论?论”,即是规定替行贿者保管财物的也要论罪而受到处罚。受贿者应受的处罚更重,《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明确说“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就是警示官吏不应贪图不正当的富贵,否则难免杀身之祸,这是对贪官们最有震慑力的警告(42)《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30、282页。。
秦王朝以强有力的专制皇权来保障其监察机制的运转,皇帝不仅授权各级监察官厉行监察,还经常亲自巡行帝国各地,检查地方吏治和民情,督促监察系统的高效运行,被视为秦监察机制的有机补充。故秦王朝监察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往往与专制君主的执政能力、政治道德紧密相关。当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主政时,能够通过高效、有力的监察系统牢固控制全国,而当胡亥、赵高之流主政后,监察机制迅即瘫痪,很快就陷于天下皆叛的灭顶之灾中。
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奠基并走向成熟的开端,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堪称一代盛世。然而,贪污腐败的问题始终伴随着帝国的历史进程。尽管秦汉帝国都曾大力反贪,为澄清吏治做出过努力,也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却无法从根本上扼制贪污腐败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吏治崩溃和政权瓦解。纵观秦汉时期反贪的历史,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留给后人珍贵的启示。
贪污腐败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危害。秦商鞅,韩非,汉董仲舒、贡禹、王充、王符、仲长统等思想家,都反复指明了贪腐侵蚀国家政权的严重性。秦二世而亡,秦末的腐败猖行,与兵徭征发等暴政、急政,都是关键因素。西汉和东汉后期,社会经济并未到崩溃边缘,然而王朝崩溃了!其根源是政治的腐败黑暗、官吏的贪渎横行,这直接导致了民众离心离德的社会大危机,进而演变为王莽代汉和东汉张角黄巾大起义、董卓篡权、军阀混战,促动其统治走向瓦解。道理很简单,吏治腐败的直接受害者是广大无辜民众,民众对官吏的贪腐最敏感也最痛恨,他们会在忍让承受、寄望于政府处理的同时,以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一旦统治政权缺乏对贪官污吏的有效控制能力和诚意,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反抗必起,终必汇成雷霆之势,荡涤一切官场丑恶,秦汉王朝的倒台,莫不如此,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要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力避因王朝覆灭而带来的巨大社会破坏,统治者必须始终对贪污腐败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不懈地抓好反贪工作。
建立严密有力的监察机构是有效反贪的必备条件。秦汉反贪的主要经验就是大力投入、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完整严密的监察网络体系,并配备相当数量的监察官员。实践证明,在政治环境比较健康时,秦汉监察机制确能收到澄淸吏治的良好效果。秦汉监察体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不彻底。郡守、县令是地方长官,同时兼辖区内最高监察官,集地方行政与监察权于一身,不但容易造成监察与行政的互相干扰,更重要的是监察权经常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使得秦汉时代的监察效能大大削弱。督邮、廷掾等既为监察官,又为郡、县长官的属吏,他们在行使监察权时须秉承行政长官的意志,难以避免使监察权屈从于行政权。历史经验证明,监察权不独立,特别是行政权对监察权的支配在本质上会妨害监察的正常运行,这种体制根本不可能防范吏治的腐败。
必须依靠法律反贪腐,有法必依。《秦律》中就规定有详细的以惩治渎职和贪污腐败官吏的法规,对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用法律明确规定了“轻罪重罚”的标准,对贪官污吏有着巨大的震慑力。此后,《汉律》继承了《秦律》的精神,加大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此外,两汉还规定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项监察法规,有针对性地惩治各种贪贿行为,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情况则时好时坏,西汉武帝和宣帝、东汉明帝时,基本能做到有法必依,既不以贵、官抵罪,也不因功废法,保证了法律反贪的权威性。不过,更多时候法律受到皇帝、贵戚、宠臣们的破坏。尤其西汉中期以后,儒学理论导入汉代法律,既有积极意义,也带来有罪不罚或同罪异罚的所谓“八议”之条(议亲、故、贤、能、功、责、勤、宪),严重削弱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使贪官污吏可借各种名义逃脱惩罚,加剧了腐败之风的蔓延。后世应汲取这一历史教训。
官府不得以改善财政收入为由直接经营工商业,这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内容。官员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往往会损公肥私,大肆侵吞,与商人勾结出卖经济情报或操纵买卖,谋取一己私利;官吏直接经营工商业,会严重败坏官员的形象,污浊吏治空气。汉武帝时期,在强化反贪的情况下,仍难以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府经商政策。王莽新朝吏治的迅速腐败,一发不可收拾,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统治阶级奢侈享受之风,不仅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也是贪污腐败的根源之一。在任何一个政权中,官吏的合法收入总是相对固定和有限的,一旦奢侈享乐形成风气,官吏们为了满足奢侈享受之欲,难免会走上贪污受贿、谋取不义横财的绝路。西汉、新莽、东汉中后期的数次吏治腐败高潮,都与皇帝、王侯外戚带头掀起来的奢侈歪风有关,在享受贪欲的刺激下,贪官污吏会层出不穷,直至吏治彻底崩坏。因此,反贪腐必须与有效控制奢侈享乐配合,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民众参与是反贪污腐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秦汉反贪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制度上保障民众参与反贪、揭发贪官污吏的权利的重要性。两汉都有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言变事”制度,许多贪腐大案就是在民众的揭发下败露的。东汉时还把“民诵”(民间舆论)作为黜陟官吏的重要依据。道理很简单,贪官污吏们无论怎样遮掩贪污腐败的事实,可能会逃脱上级的监察,但难以逃脱民众的眼睛。关键是要在反贪过程中避免单纯依赖有可能官官相护的官僚队伍,鼓励民众在法制范围内参加到反贪行动中去。这样,无论隐藏多深的贪腐丑行,也会大白于天下。
表彰廉吏、提高官吏自身修养,是保持官员队伍的廉洁奉公的必要内容和条件,但不能高估甚至迷信其作用。秦汉历史表明,品质优异、自觉廉洁奉公的官吏毕竟是少数,要求官僚队伍整体上达到这样的道德水准是不现实的。汉宣帝反贪,特别重视表彰廉吏,这是对的,但他希望全体官吏们都能以此为榜样,自觉清廉,就太过天真,效果自然不佳。一方面,贪官污吏不会按照榜样的标准来矫正自己,在利益驱动下仍会照贪不误;另一方面,会出现许多钓名沽誉的伪君子、伪装清廉的贪官,正如王成、黄霸等“伪廉吏”清廉美行的谎言被戳穿后,只能加剧腐败问题的恶化。
秦汉王朝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贪腐既要从制度建设、强化法制入手,也要从提高官吏的自我修养、道德约束入手。同时,既不要过多寄望于贪官污吏们在道德教化下会洗心革面,也不要以为有了法制,就必能根除贪腐,执法者不行,好法也会变坏。还应双管齐下,“治法”与“治人”并重。
秦汉反贪皆以失败而告终,证明了在专制皇权体制下,想要解决好吏治的贪污腐败问题是很难的,往往只能取得局部、阶段性的成果。这正是古代中国不断上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王朝周期律的一大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