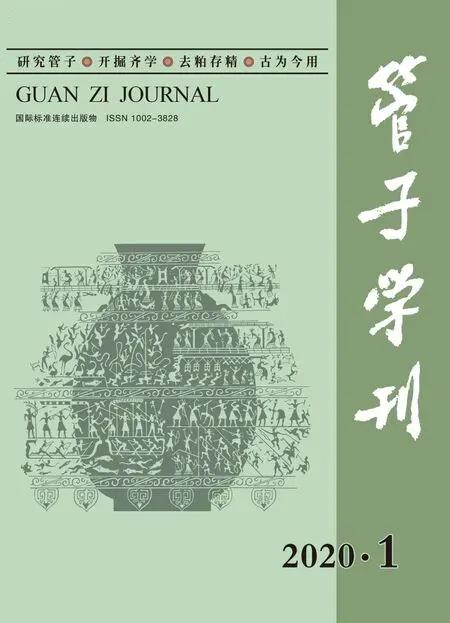《管子》中的法思想
[日]金谷治 著,于 淼 译,邓 红 校
(1.日本东北大学,日本 宫城仙台 980-9577;2.北九州市立大学 文学部,日本 福冈北九州 802-0841)
《管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分类为道家,从《隋书·经籍志》以后的各种书目中被分类为法家。而《韩非子·五蠹篇》称之为“商管之法”,和明显的讲法的商鞅之书并列。《管子》一书内容混杂不纯,以政治经济为中心,其他学派的思想也参杂其中,但一般认为其和法家思想有关联。尽管如此,对《管子》中的法思想仍缺乏特别深入的研究(1)例如木村英一的《法家思想的研究》并不包含《管子》,武内义雄的《诸子概说》以《管子》为杂家。。我想其理由在于《管子》一书内容的时代性不太明确,再就是《韩非子》和《商君书》才被看作是法家思想的典型。
诚然,《管子》中与法有关的语言折衷了一些儒家式的道义和道家式的道思想,缺乏所谓法家思想的纯粹性。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法家思想到底是什么,是否可以仅仅认为是与韩非子相似的思想呢?从中国古代法思想的发展来看,《管子》中的法思想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意义。马王堆出土的《经法》等四篇成为道法折衷的新资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中便有着一些和《管子》类似的语言。我想,《管子》中的法思想也有必要从这方面加以探讨。
本文首先探讨有关法思想的语言在《管子》中是如何得到表现的,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考察,究明其思想史的意义(2)法或者法思想,与制度问题有关。众所周知《管子》在这方面也有重要的资料,但本文只限于直接的法思想,不涉及制度。。
一(3)原文无分节,只是隔开了一行。为了方便阅读而加以分节,数字标题是由译者添加的。
众所周知,《管子》全篇可分为《经言》等八类。虽然对《管子》的文献批判应该从这八类入手,但是考量的结果,未必能得到明确的结论(4)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论述。八类指《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短语》十八篇、《区言》五篇、《杂》十三篇、《解》五篇、《轻重》十九篇。。现今即使从各篇的内容加以考察,也很难明确把握这个分类的意义。概而言之,《经言》是比较古老的资料,《外言》是仅次于前者的重要资料,其他的《内言》《管子解》《轻重》等部分思想有些模糊不定,而此外的部分甚至没有一个主题思想。认为《经言》相对古老的理由在于,《管子解》对《经言》中的四篇做出了解释,这和《经言》一词的意思是相对应的,且到汉初为止的引用语都限于《经言》部分。同样,在《经言》中也混入了可看做是解的文章,篇的成立前后也有所不同。这里暂且将这一部分作为整体,从中举出一些材料来加以说明。
从篇名来看,《经言》中的《七法篇》和《版法篇》和法似乎有关联。两篇都以法命名,但从整体上看很难说都是法家的文章。《七法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的“七法”认为,如果不能很好运用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的话,政治就不能取得成功,在对这七项的说明中,只有关于“法”的说明才明显是法家式的表现。譬如“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不能“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聚”。不过,这前后的六个说明中,如基于天地的气、寒暑的和睦等一样的法则性叫做“则”,说“义也、名也、时也……谓之象”等话,从广泛意义来看表现的是法则性,但并不一定只是法家的思想。由此可见,以尺寸、绳墨等度量衡作为法,不是表现技术性的客观性的法家式常规比喻,也可以仅从字面上去加以理解。“七法”这个词只出现在标题并没有在正文出现,即使作为原标题,这个“法”字也只是表现了广义的一般性法则。
《七法篇》第二章之后的部分离开七法而加以论述,在第二章“四伤”的赏罚论里可以看到和法家有关的主张。如果“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爱法于民”(5)本文的“民”字原称“人”,后根据《管子集校》许维遹之说而改。以下根据《集校》校正的地方会标注△。另外在此前后,用同样的表现来讲“令”“社稷”和“威”的重要性。,那么就是“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也就是“有罪者不怨,爱赏者无贪心”。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对超出个人主观性的法律客观公平性的关注。而且“四伤”的主张也在《版法篇》里多次出现。《版法篇》从整体上具有浓郁的古风韵味,被理解为是在版本上写下应该作为常法的东西,但“版法”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出现在正文里,整体上也不是叙述法思想的。其认为不能只凭君主的喜怒之情进行赏罚,讲“正法直度,罪杀不赦”之类的严刑,是与法家赏罚论相关的主张,主要思想与前面的“四伤”一致。
这个信赏必罚的赏罚论实际上经常贯穿整个《经言》。譬如最初的《牧民篇》,以“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为《十一经》中的两个必要条件之后,解释了“严刑罚”“信庆赏”;在《权修篇》中将“禁末产”和“信赏罚”联系在一起加以说明;《立政篇》中提到“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且“令必行”在讲严正赏罚时被频繁提及。在《牧民篇》中,也提到了《十一经》这一章,将“下令于流水之原”作为十一中的一个而提出,讲“令从民心”的必要性:在《国颂篇》中,有“四维张,则君令行”之说,在《形势篇》中,有“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之说。因此,在各篇中随处可见“令不行”或“令行”之类的语言。
总的来说,“令”当然有着法的意义,不过与广泛的一般意义上的“法”相比,作为个别具体的禁令、训令的意义更强一些。也可认为“令”在古代本来就和“命”是一个字。《经言》重视这样的“令必行”,“法”这个词自然就少了。而在《修权篇》中,说“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认为“令”与赏罚密切相关。只是在《经言》中看不到《外言》《重令篇》中的“行令在乎严惩”这样表示与严惩直接有关的语言。相反,《牧民篇》则以“刑罚不足以畏其意……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说明了省刑的必要性。虽然这里体现了《经言》与《外言》以下各篇的差别,但关于“法”与“令”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相同的。《外言》的《法法篇》中有“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等,明显是以“法”为中心的词汇,但除了《经言》里《权修篇》末尾的一段以外,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的语言。在《权修篇》末尾的一段中,集中表现了“法”,反复强调了“法不立则令不行”这一主题思想,但是这一段以“凡牧民者”开头的一段文章,和前面所说礼义廉耻一段文章相同,都可说是混入了《牧民解》的文章(6)《牧民解》在《管子解》中只剩下篇名,原文已丢失。武内义雄《诸子概说》(全集第7卷122页)有“通过查阅现在残存于《权修篇》中”,认为应该是指与“凡牧民者”连在一起的后半部分的文章。这个末段的意思符合上面提到的《法法篇》,也符合后面叙述《管子解》中其他篇章关于法令的考量的话,更加证明了这个事实。。
总而言之,《经言》中关于“法”本身的论述还没有清晰的形式,主要是重视个别具体的“令”的现实作用,并与赏罚的严正并列在一起。与法家有关的语言,还需进一步考察《经言》。《立政篇》所说的“德不当其位,功不当其禄,能不当其官”,让人联想到法家所说的刑名论,同一篇中提到的“布宪”和“宪籍”与之前的“宪令”一样,被认为与成文法的公布有关,《七法篇》中提到的“人君泄则危……言实之士不进”,让人想到申不害的“术”的秘密性(7)关于这个问题,《牧民篇》认为君显现好恶与得到引导民众的贤者的帮助有关。笼统地说,与申不害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幼官篇》记载了南方夏政中明确上下尊卑的立法,北方方外中法令的重要性等,但都是片断的。以上大多不是关于“法”的考察,整体上也完全看不到以“法”为中心的色彩。
反之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即使重视“令”和”赏罚”,即使存在着法思想,这些都是和法家的主张相反,从主张道义的立场加以了折衷的。“令必行”不是通过严罚推行,而是主张省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刑罚),根据民心来实行“令”。 《七法》也是一样,被列为狭义之法的其他六法,譬如“化”说的是渐习教化,《心术》根据诚和恕来布令,《权修篇》讲赏罚的言词等,都和爱利和智礼并列。《牧民篇》中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是讲孝悌与礼义廉耻,可见《牧民篇》明确主张将民众经济上的充足和道义联系在一起,法令才得以实施,因此才有国家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经言》中的法思想就显得比较薄弱,其关于“法”的考察,可以说从总体上还没走出适应现实的朴素阶段。
二
以上考察了《经言》诸篇,下面想考察一下《外言》。《外言》在很多方面可看作是对《经言》的敷衍,不过也有积极地说明“法”的文章,从而可以观察到法思想展开的迹象。所以可认为《外言》诸篇表现了法思想。下面我们想详细考察一下《外言》。
首先,《外言》第一篇《五辅》中的“公法行而私曲止”“公法废而私曲行”等重视德、义、礼等的折衷性句子,表现了对“法”的重视。因为在《经言》里看不到把“法”作为公共性的事物看待,并将之和私相对应这样的思想(8)在前面提到的《版法篇》的资料中,有不能根据喜怒之情进行赏罚;在《七法篇》的资料中,有不能为了爱民而曲法等。虽然都是有关的思想,但不是什么积极说明“法”的公共性质的资料。,而《外言》以下的篇章经常强调这样的思想。同样,在《外言》的《八观篇》中有“私情行而公法毁”,《法禁篇》中有“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短语》的《君臣上篇》中有“人君不公,常慧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区言》的《任法篇》“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甚至表现了明确的公私论,在此之上又说“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由此可以看到将“法”和“私”加以对照的定义。
其次想讨论一下前面对《经言》的考察时也言及过的“法”和“令”的关系。《经言》中除去《权修篇》末的一段外,都没有疑问,在《外言》的《法法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法”是“令”的依据。同样,在《短语》的《君臣上篇》也有“君体法而立,君据法而出令”的说法,这样重视“法”和“令”的地方还很多。《八观篇》中有“置法出令,临众用民”,《任法篇》阐述了“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的重要性,《杂》的《七臣七主篇》对“法”“律”“令”进行了说明,在此之上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管子解》的《形势解》中也说“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9)《形势解篇》的这句话是对《经言》的《形势篇》的解说,值得注意的是,《形势解篇》将《形势篇》中的“令”或者“政令”和“法”加以联系。。与法制和法度等词汇并列的法令也很多。
在《经言》中“令”受到额外重视,在《外言》以下将之与“法”联系起来进行说明,这是因为对“令”进行了反省,其“法”的性质自然而然得到了加强。《经言》中的令必行需要上下和睦,遵循民情的主张,在前述《形势解篇》的例子中得到了原封不动地的继承,而《法法篇》和《重令篇》加重了只有严惩才能执行“令”的法家倾向。这无疑加强了与“令”和“法”的联系。《法法篇》讲“令”不依“法”(令不法)是不好的之后,说赏罚必信,特别是提出“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强调了排除恩情的严惩主义。这里可以看到类似于法家的严刑主义的东西。
此外,《经言》中经常提到“令行”和“令不行”,《外言》的文章提到了“令”的轻重。这些也和对“令”的反省以及与“法”的结合有关。例如在《八观篇》中有“上令轻,法制毁,则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在《重令篇》中有“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令”的轻重就是指“令”的尊卑。也就是说,“令”的法的控制力的强弱就成了一个问题,《重令篇》说的就是支持严刑。
其从各个方面对“法”本身,譬如“法”的定义等也进行了说明。如在《经言》所看到的那样,只有《七法篇》中的把“尺寸”“绳墨”“规矩”等作为法来看,其他的除了《权修篇》末尾的一段就没有关于“法”的定义。《权修篇》末尾说“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用民力(或能、死命)者也”,这些都是讲的“法”的目的,这和令行也有关系,这和《外言》以下讲“法”的语言有类似。其原本是《牧民解》的文章,大概是根据《牧民篇》四顺一章“令不行”的解而写成的吧。
下面想看一下《外言》中关于“法”的定义。
《外言》的《法法篇》说“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法者,民之父母也”,有很多大赦的“惠”反而会招来祸因此被说成“民之仇雠”,因此刑罚的意义很强。
《短语》的《心术》上篇有“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10)第一句的原文是“简物小未一道”,意思难以理解。现在假设根据丁士函把“未”改成“大”的话,我认为“一道”二字是衍字,应当排除在外。另外,这一段文字是夹在一段前后押韵的文章之间,似乎是后来的窜入。,仍然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可谓事物鉴别的标准。这个定义与道、德、义、礼的定义并列。还说“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讲的是“法”的根本的统一性和必然的规范性。
《短语》的《正》篇有“如四时之不貣,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还提出“当故不改曰法”,都是指适用“法”的一定不变性。这是为了遵守“法”的客观性的重要条件。这里把道、德、法、刑、政五个并列起来定义。
《区言》的《任法篇》中有“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与之相对的是“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阐述了从政者政治策略的性质。“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也有这个意思。此文之上有“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这句话强调了“法”的严格的绝对性质。
《杂》的《七臣七主篇》的“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有与赏罚有关的意思。将之与“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对照,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
《杂》的《禁藏篇》中的“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和《管子解》的《明法解》篇中的“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11)原文是“吏者,民之……”,但是与《禁藏篇》的文章相比较,将“者”字当作衍字排除在外。,民之所悬命也”都是指相同的东西。所谓“仪表”或“程式”是指作为公的客观标准的性质。在主观的私人感情中,这是对发生过的事划分是非的标准,所以决定了百姓吏民的命运。而“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则对“害公正”“私意”加以对比说明,但同时也具有预防邪恶的性质和稳定天下国家的功能。
以上是对“法者”或“……是法”这一形式的对“法”本身的直接说明。当然,这里没有全部列举出《管子》中的“法”的性质,但显而易见的是,《外言》诸篇把“法”作为考察的对象并从多个角度加以了热心的讲解。与此并列的是对“法”的根源、基础,以及起源的考察。《短语》的《心术》上篇中的“法出乎权,权出于道”和与之并列的“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相比,更明确地指出了“法”的根本是道。类似的话在《外言》的《枢言》篇中也有,如“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再加上上文的“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把“法”发生的原因归结于人心。关于这一点,以后在讲道法思想问题的时候还要详细考察,这里仅仅是想指出其对“法”的考察有了进展这一事实。
我们已经大致理解了与《经言》不同的《外言》各篇的特色,下面想叙述一下关于“势”的思想。重视君主的权势或权威,是与《韩非子》相似的法家思想的重要主张。《外言》的《法法篇》中有“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都是确立“威权”的主张。《杂》的《七臣七主》篇有“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讲的是应该明确上下之分。《明法解》又说“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所以才强调“必治之势”。然而在《经言》类,《形势篇》的篇名带有“势”这样的文字,在整体上却看不到“势”。《形势篇》以前好像是《山高篇》(12)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作为《管子》的篇名可以看到《牧民》《山高》等,查《集解》引用刘向《别录》的记载,《山高》又名《形势》。“山高”是取篇首的二字。,如果去掉这个,在《七法篇》中只能看到“用兵之势”一词。只是,从《形势篇》的内容来思考一下把它命名形势的理由,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说顺应自然秩序,所谓的形势恐怕指的是自然的形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当然是一种势,但是这种势与《明法解》中看到的与权势和权威有关的“必治之势”显然不同。《经言》和《外言》以下关于势的思想也是不同的。
三
综上所述,《经言》诸篇对“法”的考察比较薄弱,而《外言》诸篇对各种各样的“法”进行了定义。还强调了“法”具有针对个人感情性的客观公共性,对《经言》所重视的“令”和“法”的关系也有提及,并出现了韩非式的“势”思想,具有法家性的东西。不过,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到底可不可以把《外言》各篇都考虑在内。《管子》现存76篇,《经言》9篇之外的从《外言》到《轻重》的共7类、67篇。而各篇都有自己的特色,其并不一定都在讲“法”(13)出现与法令有关的语言的篇章大致如下:《外言》中的《五辅第十》《枢言第十二》《八观第十三》《法禁第十四》《重令第十五》《法法第十六》,《短语》中的《君臣上第三十》《君臣下三十一》《心术上第三十六》《白心第三十八》《势第四十二》《正第四十三》,《区言》中的《任法第四十五》《明法第四十六》《正世第四十七》,《杂》中的《七臣七主第五十二》《禁藏第五十三》,《解》中的《形势解第六十四》《版法解第六十六》《明法解第六十七》。。也即根据每篇的中心意思,有讲“法”的有不讲“法”的。这么看来,上面那些关于“法”的言论,不仅仅要看其是不是总括性的提出,在上下文中是怎么说的,还有必要进一步仔细研究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
外篇讲“法”和“令”的篇章主要是《外言》的《法禁》《重令》《法法》这连着的三篇,以及《区言》开头的《任法》《明法》连着的两篇,再加上《管子解》的《版法解》《明法解》连着的两篇。下面想逐次斟酌这些内容,并加以分析。
《外言》的《法禁篇》强调“法制”,认为“刑杀”和“爵禄”统率下民是治国的要务,这里说只有“一置则仪”百官才能守其“法”,下民也不能立“私”,按顺序列出了“圣王之禁”等项目,篇名就来源于此,“圣王之禁”的内容里有“枉法以求于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也举出了“以亲为本”“诡俗异礼”,最后一段有“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之类的话。可以说是有折衷圣王道德的意思。
在接下来的《重令篇》中,有“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行令在乎严罚”,认为下民批判“令”是不应原谅的。其次解释了“朝之经臣,国之经俗,民之经产”,说“令必行”。但是,这里折衷了“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的思想,有一种偏离篇名之感,还有一段说的是“天道之数”的“至则反,盛则衰”。
在接下来的《法法篇》中,首先提出了在“令”的基础上确立“法”的主张,根据严刑思想认为“法者,民之父母也”, 反复强调“令行”这一中心,说明有必要“确立法”和“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政者,正也”讲“是故圣人一精一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因不正当行为“法”也受到侵犯,可以看到以“主与大臣之德行”作为道义性的折衷性的思想。此处又说,“宪律制度必法道”,承上所说“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也讲“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好像是建立在“法”之上的思路(14)《法法篇》末尾有一段被看作是《参患篇》的错简,最后又以重出的形式附加在了篇中。。
上面考察了《外言》的三篇,虽然在法、严刑、势的主张等方面有法家的倾向,但还是继承了《经言》的主张,在彻底贯彻“令”与赏罚并重的同时,在道义立场上与天道等的折衷,这些都是其特色。那么,《区言》方面又如何呢?
首先在《任法篇》中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这与“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并列,而圣人要“守道要,处佚乐……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则是道家式的语言。虽然也讲尧和黄帝等帝王的无为政治,但篇中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等,都是在讲法至上。至于“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则是讲以君权为中心的法。在此可以看到道法折衷的色彩和法至上立场的加强。
下面的《明法篇》虽然与《韩非子》的《有度篇》的内容重复,但仍然重视君臣之分和君权,讲不立法乃招致亡国,强调“以法治国”。在这里也有“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等类似道家无为之治的语言。《区言》的这两篇与前面《外言》的三篇相比,贯穿着道法折衷的主旨的,但没有强调道义性,与之对应的是法治主义的加强。
最后是《解》的两篇。《明法解》的主旨是讲“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带有强烈的法至上的语言,“必治之势”这句话也重视确立君主的“威势”。而《版法解》则是对《经言》的《版法篇》的主旨进行解说,其中有“威立而令行” “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等,这些都是《版法篇》末尾“法天合德,象法无亲……”这一说法发展而来,所谓“版法”就是指天地四时用“法”治理天下,这是对自然法秩序的强烈尊重。这一点接近同样是“解”中的《形势解》,与之前的《明法解》则完全不同。
以上是对《外言》以下主要篇章“法”思想的考察,下面想讲述一下结论。最显著的是,各篇之间的折衷立场有着强弱或有无的差异。例如,《明法解》几乎是纯粹的以法为中心的政治论,这里看不到对道义的顾忌和道法折衷的色彩,但《重令》和《法法》等篇则把它们混在了一起。比较接近《明法解》的是《明法篇》了,但这里的折衷性也很微弱,《任法篇》的道家性语言只有一部分。因此,相对于折衷性的减弱,这些篇章强调了“法”的绝对至上性。《外言》的三篇也讲了“法”,其中有与《经言》不同的特色,但对道德的顾虑和道法折衷的强烈削弱了现行“法”的客观性,可以说《区言》的“法”的主张是软弱的。也就是说,其讲客观性“法”的语言,包含着现实道义上的正义,具有强烈的贯彻始终的自然法立场。
其实在《经言》中也体现了这个折衷性和自然法的立场。在那里可以看到相对于“法”讲“令”,“令必行”和赏罚一起宣扬尊重道义的重要性,而《形势篇》有顺从“天之道”的政治论,即所谓“上无事,则民自试”。换而言之,《外言》各篇清晰地呈现了法思想的倾向,但它所包含的折衷色彩,实际上是直接继承了《经言》的立场。尽管《经言》诸篇相对古老,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其折衷性只侧重于“法”的主张的纯粹性,必然是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后才出现的。当然,要证实这一点,还有必要对之进行思想史的考察。以上概括了《管子》中有关法思想的表述,接下来想简要地考察一下思想史的流派。
四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尽量避免超出《管子》的范畴围,但这里似乎有了论述的必要性。
首先,《明法篇》的内容明显与《韩非子》的《有度篇》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关于这种关系,罗根泽认为《明法篇》是从《有度篇》中节选出来的,郭沫若断定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即是秦王嬴政二十六年以后的秦文(15)罗根泽《管子探源》(《诸子考索》)第五章。郭沫若等《管子集校》下册第768页。《有度篇》中有讲齐、燕、魏灭亡的文字,表示其成立的上限。郭氏据此说是秦王嬴政二十六年以后。但是,《明法篇》中没有这样的文章。。仔细推敲一下,这个说法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16)只在《有度篇》中有强调“先王之法”的文章,《有度篇》有可能是它和《明法》两种资料的合成。,但不管怎样,两者并没有太大的时代差距。且更重要的是,《明法篇》的法家言很纯粹,而事实上《明法解》则更加彻底。《有度篇》有“先王之法”讲折衷性,这就是它不是韩非子的东西的理由(1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365页以后,容肇祖《韩非子考证》第九等。,但《明法篇》没有这一点,这是韩非的法至上的立场。而且可以看出在《明法解》中的“必治之势”这一概念,体现了与韩非子的亲近性。
《韩非子》中被认作是韩非自著的《显学篇》和《五蠹篇》,提到了“势”和“威势”的重要性。与此相对,也可以看到《难势篇》中对慎到的“势”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吸取。据韩非所言,慎到的思想应该称为“自然之势”,这是把它转变为“人之所得设”的人为之势的必要。所谓人为之势,就是不管统治者的贤愚如何,都必须要人为地创造出能够顺利统治的威势,也即“必治之势”。这是从慎到进化到韩非的新思想(18)参照拙稿《有关慎到的思想》(《集刊东洋学》第七集,1962年)。。《明法解》完全继承了这个思想。此外,前面我们提到与《明法篇》和《明法解》并列的《任法篇》有着强烈的法至上的思想。可以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部都接近于韩非的法思想。
但在《明法篇》和《任法篇》中也出现了与道家的无为思想有关的词语。《明法篇》的有些微弱,而《任法篇》则是部分存在。而这种表现方式被认为会助长以法中心的立场。例如,《明法篇》所说的“法而择人而不自荐”,是指立公“法”要不被私情所迷惑,《任法篇》中也有道家式的语言,总之就是“任法而不任智”,都是在强调作为“天下之至道”的客观法。所以即使说有道法折衷的色彩,也可以说那不是本质性的。
《外言》的《法法篇》则不然。所谓“宪律制度必法道”,是以客观法为基础来考虑“道”的。与此同时还有“道法”一词(19)这一段话在《任法篇》里也有,但在那里被读作“道从法”,与《法法篇》不同。。“道”是基于“法”的意思。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便可知道它们所谓的“道”是什么,道法思想的实际状态如何。
其实,“道法”这个概念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那是由于在马王堆发现了古佚书。这些被称为《经法》、《十六经》(20)最初被称为《十大经》,在1980年3月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里被纠正为《十六经》。、《称》、《道原》的四篇,是与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有关的道法折衷的资料。关于其内容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笔者也曾研究过(21)拙稿《关于古佚书〈经法〉等四篇》(《加贺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文史哲学论集》所收)。。就结论而言,四篇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大都是战国末期到秦汉时期的作品,其特色是自然法色彩较强的一种特别的道法折衷思想。可见这个道法思想与韩非的核心思想是不同系统的,这里产生了探究道法思想的历史的课题,所以需要对《管子》内容进行综合考察。
众所周知,古佚书《经法》有“道生法”,在《管子》的《心术》上篇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话。前面我们也指出过“法出乎权,权出于道”,中间除了“权”之外没有别的。其结果是和“道生法”一样。另外在《外言》的《枢言篇》也有“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这仍然是以“法”为“道”,让人联想到这是同样的思想。显而易见,这与讲“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的法至上的《任法篇》的立场不同。与《心术篇》相同的《短语》,以及《君臣》上下篇有讲“道法”的语言。而且,在上篇中有“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和“是故别一交一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把这个定义为“道”,另外还有“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也。……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这里的“道”,虽然用“理”的语言加以说明,但还有“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上篇),和“天之道,人之情”所说的那样,是道家的同时又是成为道义性基础的自然法的道。
这一点在《版法解》和《形势解》中更加明显。在《版法解》中,版法是“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有“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还有“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和“圣人法之,以烛万民”等。《形势解》“法”的主张不一定很强,但也有和规矩、尺寸一起说明法数的地方,与此同时还强调了“明主配天地者也”和“明主法象天道”的说法。在古佚书的《经法》等四篇中有很多对天地自然秩序起模范作用的语言,对此可参见拙文(22)参照拙稿《有关古佚书〈经法〉等四篇》135页以后。。然后这里列举的《经法》的《四度篇》的“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在《管子》中《外言》的《重令篇》也可以看到“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这样类似的语言。在《管子》中有很多与古佚书类似的语句,《短语》的《势篇》和《杂》的《九守篇》,其重复的状况如唐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23)唐兰《〈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与其它古籍引文对照表》(原载于《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经法》收录)。,其中也有“天极而亡”讲自然和人的协调。作为道法折衷的文献,古佚书与《管子》中的以上诸篇有密切关系,几乎可以断定,其贯通了以自然秩序为中心的一种天人相关的思想。
这一思想,和对《区言》的《任法篇》等进行了考察而讲客观法至上的韩非的立场不同。将之和《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主道》《扬权》四篇合在一起,构成了讲道法折衷的资料群,可以认为形成了与韩非的思想有不同传承的一派。一般认为《解老》《喻老》等篇是韩非以后的折衷思想,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说以《管子》的《外言》为中心的诸篇以及古佚书《经法》等,全都是韩非之后的东西。《管子》的每个篇章便有着不同的色彩,从中可以看出其成立情况的复杂情况。在古佚书中,《经法》的成立很早,在考虑到其是战国末期、前三世纪中期成立的话,《管子》中的这些资料也可以大致可以认为是从那个时期起到秦汉之际的作品。
五
如上所述,《外言》以下和“法”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为两部分的话,《牧民篇》以下的《经言》诸篇的法思想大致分为三类。第一,以“令必行”为中心的符合实际应用的朴素阶段(《经言》诸篇);第二是在道法折衷的立场上对“法”进行自觉的反省(《外言》《法法篇》);第三是在韩非式的法至上的立场上强调客观法(《区言》的《明法篇》)。而且,从和相对古老的《经言》的关系来看,第二类显然更接近一些。《经言》里虽然没有第三类的纯粹法家思想,但第二类的折衷性同样看起来很浓厚。《形势解》和《版法解》都是以《经言》的句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当然与其有很深的关联。
这样看来,《管子》法思想的特色,首先是从《经言》看到的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然后从中发展产生出一种法思想,其继承了原有的现实折衷性而作为道法折衷的一派而存在,但也可以说受到了韩非法思想的影响。而且从《管子》书中可以看出,这个展开大致可以认为是以齐稷下为中心开始的。说稷下之学具有横跨儒、道、法的折衷性色彩,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稷下的全盛时期跨越威王、宣王。威王的即位是在公元前357年,宣王死于公元前302年。被认为讲自然法的势的思想的慎到出现在这年末。道法折衷,与其说是道家和法家都没有的一种政治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既重视现实的法令和法制的施行、又以传统的自然法的秩序为根本的思想,恐怕这与慎到的出现有关系。因此,《经言》诸篇以前的文章,恐怕是稷下前期编成的。尤其是卷首的《牧民篇》特别古老,战国初期以来,作为各国进行的富国强兵变法运动一环的田齐的活动,可以看到其主旨(24)虽然这是需要详细说明的问题,但是时间不够了。另外,《牧民篇》的内容之所以不能上溯到春秋时期,是因为它折衷了儒家思想,有讲“省刑”“禁文巧”等 。。战国初期,魏国有李悝的活动,继承此法的商鞅在秦国活动并被处以死刑是在公元前338年,正好是稷下前期。商鞅变法的惊人成果引起了各诸侯国的关注,作为法思想的自觉反省在此之后便活跃起来,但是在齐国稷下,传统的自然法观念仍然很强。在这种自然法观念的基础上对法秩序的考察和商鞅的技术性法律观的追求,是贯穿战国末期的法思想的自觉展开。一个是齐国,另一个是以三晋和秦国为中心。以客观法为主的法至上的韩非思想,其核心当然是从后者的发展而来的。
本文仔细推敲了《管子》中法思想的资料,发现其中大致有三种资料,并探索了其思想史意义。虽然还应进一步叙述和法思想展开的关联,但由于已经超过了字数的限制,只好以后另起一篇(25)1980年夏,我在台湾举办的国际汉学会议上以“先秦法家思想之演变”为题进行了发表,论述了整体的思想史的系谱。预定在近期付印(译者注,载《集刊东洋学》第47号,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