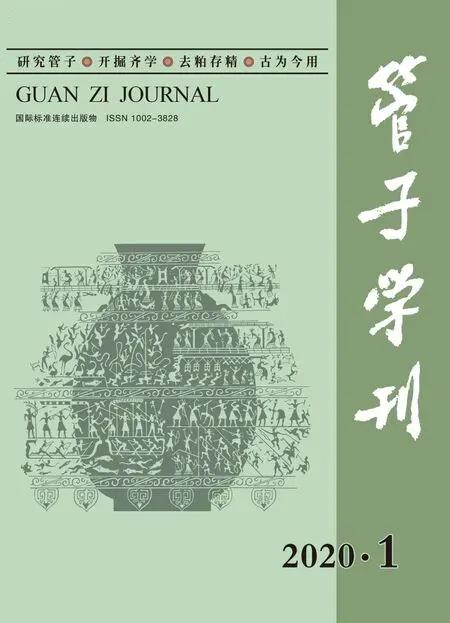方东美视野下的庄子哲学
郭继民
(宜宾学院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 宜宾 644000)
现当代哲学家中,研究道家哲学者可谓多矣!若谈及特色与洞见,方东美(1899—1977)先生的道家研究可谓独树一帜!方氏认为,老子开道家风气之先,其以惟惚惟恍、生天生地的大道根基,以无有,有为无为,本体超本体等概念来阐释人间的规则,建立起一道独特的玄学风景线,并与儒家相抗衡。殆至庄子,尤以创造性著称,其独特的思维、奇异的想象、浪漫的艺术品性及特有的诗意表达不但解决了老子因“语焉不详”而留给后人的困惑,而且把道家哲学推向极致。
方先生之所以更推崇庄子,在于庄子不但化解了老子哲学中的“矛盾”(1)注:方氏认为,老子哲学中的矛盾主要是“无”的用法过于混乱。在老子文本中,存在不同的“无”,既有类似道体(超本体)的无,又有次层级的与有相对的“无”。然而,在老子那里,并没有得到恰适的区分。,而且庄子还“将道之空灵超化活动历程推至‘重玄’(玄之又玄),然在整个逆推序列之中并不以‘无’为究极之始点;同时,亦肯定存有世界之一切存在可以无限地重复往返,顺逆双运,形成一串双回向式之无穷序列。……将整个宇宙大全化成一‘彼上是因’,‘交融互摄’之无限有机整体”(2)方东美:《方东美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无疑,整体、有机哲学之模式,亦是方氏追求的理想构架。
方氏认为,“庄子之所以能有如许成就,乃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个道家,而且受过孔孟相当影响,同时也受到那位来自名家阵容的契友惠施之影响”(3)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42页。。大凡对庄子有所研究的人当知,在《庄子》三十三篇中,涉及到庄子与惠施、庄子与儒家对话辩论的场景绝不在少数,即便拿《庄子》内七篇而言,亦如此。如《齐物论》中的精彩论辩,彰显严谨的逻辑(受名家影响);《应帝王》则隐喻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情怀——自然,其“平天下”的方式与儒家不同。除此之外,庄子哲学中还有墨家“节葬”思想之痕迹,他甚至还受到兵家思想的影响,如庄子与弟子关于死后丧葬的对话即带有墨学色彩;《大宗师》中“故圣人之用兵也”一段则多少涉及兵学思想。由此可见,庄子善于吸收、借鉴他者的思想!
方东美对庄子的探索,既忠于文本,但又不简单地停留于文本,而是深具问题意识,始终围绕中国哲学所特有的三大特质即“殊道异论”“旁通统贯论”“人格超升论”展开,他既以“双回向”的方法圆融地解读道家哲学,同时还将道家哲学综合并融汇于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
一、殊道异论:对“无”的再理解
“殊道异论”,主要通过比较儒释道三种哲学之异同,彰显其特质。按方氏理解,道家的主要特征及殊胜处在于一个“无”,庄子的哲学的殊胜之处在于通过种种譬喻厘清了老子的“混沌”之无。兼于此,我们亦须从“无”之角度去切近方东美视域下的庄子哲学。
(一)对“无”的理解
谈及“无”,一般道家研究者倾向于从平面角度入手,这是不够的。方氏认为,关于“无”的理解,一直存在混乱。原因在于老子的文风过于简洁,且未能处理好“一词多义”的关系,结果造成词语的误用乃至词义的混乱。譬如,老子之“无”,既有超本体论意义上的“无”(即超越有、无相对概念之上的“无”),又有与“有”相对意义上的“无”;此外还有其他的含义,如“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九章)之“无”,则是动词意义上的用法。然而,后人将老子的“无”或者定位于“虚无”层次而消解了“无”的丰富性;或者定位于本体论层次,乃至将“无”视为实有形态的本体论,以至于造成“无中生有”的悖论。关于此,牟宗三先生亦认为,不能把道家之“无”看作实有的本体论形态,“把道家的‘无’看成是个本体宇宙论的本体、客观的本体,而且是有能生性的本体。这样看好像没有人反对……这些话从表面看,你很容易从客观形态意即实有形态去了解道家的道,但这是不对的,讲不通的。”(4)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牟氏认为,应将道家之“无”看成“境界形态之形上学”,这实际上同方氏所主张的“超本体论”主张相一致。方氏的超本体论之“无”,应解释为无限,实质上亦是从境界意义上理解“无”(此即立体的理解)。当然,孤立地理解老子超本体论之“无”似乎证据不足,若结合庄子哲学做综合理解,那么问题则明朗很多:“老子哲学系统中之种种疑难困惑,至庄子一扫而空。”(5)方东美:《方东美集》,第292页。那么庄子到底如何解决老子关于“无”的困惑呢?
方氏认为,《庄子》的《天下篇》乃庄子理解老子的关键。庄子指出老子思想之精义在于:“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6)王夫之:《庄子解》,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7页。在方东美那里,句读为建之以常、无、有。如是,庄子视野下的道家之终极原则是“常”,是绝对价值,而不是虚无;这个“常”,是恒常、恒有,约略类似老子的超本体论之“无”(乃无限义,或大写的无)。“常”后的有、无则处于具有相对价值的层次,属于本体论。关于此句读,大多注庄、解庄的学者将之解读为常有、常无,以“常有”“常无”相对待的层面理解“道”。方东美则反是,他用“无对待”的“超本体论”去建构老庄之绝对价值。细思来,方氏所诠释的“无对待”之绝对价值倒颇契合庄子,庄子即以“无待”作为通往逍遥之不二法门。
如此看来,此“常”是更高层次上的“无”(即道),它是脱离了有、无相对待的“无”,意味着超本体论,即立体的“无”。只是一般人常将老子的开创的“无”之哲学误解为“空无”,其实不然。牟宗三先生对此平面意义的“无”亦有所批评,他认为,在平面意义上理解“无”,将导致“无中生有”的悖论,试问,本体之无(空无、虚无)如何生“有”?牟先生主张,须从作用层面理解“无”,“无”表征的乃是无为之作用,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不干涉主义”。方先生则从“超本体论”的层面理解之。他认为,老子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超脱万有,成立一套“超本体论”。倘若依据老子“玄而又玄”的辩证法,精神不断地向上发展,向上追求,直至追求宇宙后面最大的秘密。这种探求宇宙秘密的途径是通过层层否定完成的,老子最终要“无以为之用”,把一切都点化成了“无”。倘如此,就有可能陷入绝对虚无之境地,陷入佛家所谓的顽空、断灭空之中。庄子看出其潜在危险,故提出“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的观点。“从他看起来,‘空虚’——用平常的话说——就是无。然而‘万物’,这就是概括万有。可是庄子认为在老子思想里面,我们不要走这条路。假使我们从万物之有走向道的秘密——本无,就会陷到毁灭那一条道路上面去。”(7)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台北:黎明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71页。庄子的“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之理念可谓医治“老子之无”可能导致的顽空与断灭空,因此必须有超越有无相对的“常”存在。
以笔者蠡测之见,方东美之所以有“建之以常、无、有”之句读,大抵以“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为证据,否则,就很难解释了。排除了“无”之虚无乃至顽空、断灭空的危险,庄子之“道”就绝非纯粹的幻想之物了。依庄子言,其作为“无”之道不但时时刻刻存在于万物之中,正如《知北游》中庄子所谓“道在蝼蚁、在瓦甓、在屎溺”之所言;而且它(“无”之道)还担负着绝对价值的厘定权、裁决权(即“超本体论”)——当然这个绝对价值不是人为的、武断的,而是用现象学的方式来裁定“是非”的,用庄子的话就是“莫若以明”,关于此问题,下文将论及。
(二)“无”所开显的超越时空
言及至此,人们自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假若将“无”定义为超本体论或绝对价值论,那么这个“无”应居于何处呢?换言之,绝对本体论或价值论可否存在于时间的流变之中?
方东美以为,此问题恰恰是区分道家与儒家的分水领。方氏认为,道家“致于‘寥天一’之晶天高处,而洒落太清,然后再居高临下,提神而俯,将永恒界点化之,陶醉于一片浪漫抒情诗艺之空灵意境。嗣后,道家遂摇身一变,成为典型的‘太空人’”(8)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34页。。 方东美之所以将道家称之为“太空人”,即含有道家有提挈时空之意。在儒家看来,时间是由某定点奔向未来的过程,这在易经哲学表现得非常显明:“孔子在易经哲学里俨然以时间在过去固定开始或始点,只是向未来奔逝无穷。”(9)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42页。于是,始有“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之感叹。儒家的时间是变易、流变的时间,于是需要圣人出现,于时间之长河中与时偕行,“参赞天地之化育”。道家尤其庄子的时间观则大异其趣,《齐物论》中庄子有“有始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之妙论,一反儒家将时间固定某点的做法,而是依照老子“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之原理,把时间看作绵延不绝、变化无已的自然过程。这样就把宇宙的解释者、创始者在理论上给取消了,它不需要一个圣人或君子去管理世界。不仅时间如此,空间亦同样如此,因为整个时空乃是无限且绵延的。基于此立场,方东美认为,庄子“以其诗人之慧眼,发为形上学之睿见,巧运神思,将那窒息碍人之数理空间,点化之,成为画家之艺术空间,作为精神纵横驰骋、灵性自由之空灵领域,再将道之妙用,倾注其中,使一己之灵魂,昂首云天,飘然高暴,致于寥天一处,以契合真宰”(10)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42页。。由此,道家乃是艺术性的空间存在,是诗意的存在,亦即不受时间制约与粘滞的存在,此即方东美将道家定位于太空人的缘由。
于是,庄子之“无” ——作为绝对价值的“无” ——跳出时间的链条而达到无限的空间(化有限时间为无限空间),庄子的“逍遥游”也将因此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亦须说明,这种“太空人”的品性,是超越时空但又不脱离时空,是“即时空”而超越时空,是“即人间”而逍遥,按现代新儒家的说法,是为“内在超越”。由此,亦可以理解庄子“道在屎溺”之哲学内涵。
二、上回向:逍遥人格的理论构架
庄子哲学追求逍遥的人生,追求真人、至人、圣人的境界。此不断精进的人格追求即方氏所倡导的人格超升论,又因人格逐步超升,故方氏借用佛语将此渐次精进表述为“上回向”。
庄子以《逍遥游》开篇,拈出“逍遥”二字为其哲学鹄的与终结,自有深意。然而,世人对逍遥及其途径的看法历来见仁见智:魏晋郭象持一看法,东晋支道林持另一看法,唐人成玄英亦有一家之言。方先生学贯中西,以诗性眼光重新审视,创造性地提出趋向逍遥的三原理,精辟地概括了庄子之精义。基于方先生所提炼的“三原理”体现的是人之精神渐次解放进程,故笔者以“上回向”名之。
(一)个体化与价值原理
“个体化与价值原理”,是人超脱解放的起点。此原理针对郭象所注《逍遥游》而来: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11)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页。
庄子在《逍遥游》中,曾以蜩与学鸠之言嘲讽鲲鹏,“我决起而飞,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难为?”庄子本意当然是以蜩与学鸠之浅陋反衬鲲鹏之博大,殊不知,郭象却从中读出了庄子的吊诡与矛盾:倘若道法自然,万物顺乎本性自然,则尽道也,又何必以鲲鹏之性而蔑视蜩与学鸠之性呢?正所谓“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方氏认为,郭象所注,固有其理:无论蜩与学鸠还是鲲鹏,皆体现一种生命存在,皆有其价值。然而,倘若仅停止于此,胸怀则未免小了,所谓逍遥的生命将因此受到束缚,甚至导致新的危机。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物种若实现其生命意义与价值,皆须凭藉外在条件,“如果他的生命中心只陷在他狭小的观点里面,他就不能把握也不能控制住他生命所必须凭藉的外在条件,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庄子所谓的‘物于物而不能物物’,他的精神从自我充足的情况,一下子变成了不充足、不圆满”(12)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45页。。由此,个体解放之路(即“个体化与价值原理”)就必须进入超越性原理。
(二)超越原理
超越性原理,即对拘泥于“小我”境域而言。仍以蜩与学鸠为例,其“决起而飞”也好,其“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也罢,看似逍遥,然若扩大心胸看开去,它们并非真正获得逍遥,因为它们既受制于视野,又受制于外在的条件。《逍遥游》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秋水》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以道者,束于教也”,此等论述,即言任何个体皆受制于外在诸自然条件。以此观之,外在自然条件自身构成近乎“二律背反”的作用:一方面,它是万物得以生存的基础,万物须依赖它、顺从它,方可享受到存在的价值,有所谓的逍遥;另一方面,诸自然条件又是个体难以逾越的屏障,甚至成为其生存的枷锁。这样郭象对“蜩与学鸠”的逍遥注解,就走向了问题的反面。因此,方氏认为,生命逍遥固然起于个体化价值,但必须要超越个体,进入更高的层次,即为超越原理。这个更高的层次,不是纯粹的自然环境,亦非纯粹的物质,而是意味着精神的超越。须在精神层面拓宽其生存领域,“把外在的条件都收到生命本位上来,变作其内在条件:经后自己拿一个解放的精神,又可以第二度做个精神主宰”(13)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56页。。
(三)自发性自由原理
经过精神超越,个体通过精神的自我解放拓展了其视野和生存空间,然而却还需进行又一次的提升,以解决个体与“外在”的关系。依超越原理,个体之精神固然得以提升,提升之精神并非立于“虚空”之中,仍须与外在相抵触、摩荡,有接触就有限制——接触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限制和束缚,那么提升了的精神应如何应对外界呢?答曰:“无待。”
历代解庄著作中,方东美颇赞同东晋支道林之注解,他认为支道林既吸收了原始道家的精髓,又深得大乘佛学精神,故其对庄子逍遥注解为“无待”(而非郭象所谓“事称其能,各当其分”)更有说服力。今人解释中,章太炎对逍遥的注解亦有新意,他尝言:“《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二字。他以为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不能算数,在饥来想吃、寒来想衣的时候就不自由了。就是列子御风而行,大鹏自北冥徙南冥,皆有待于风,也不能算自由。真自由唯有‘无待’才能做到。”(14)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53页。方东美颇赞同“无待”观点,并可能受到章太炎的影响(15)注:方东美多次谈到章太炎先生所注《逍遥游》《齐物论》篇,且赞同其以唯识论解释《齐物论》的观点,方东美受其影响自不待言。。他认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获得自由,必须“无待”。无待,按庄子的话讲,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须指出的是,方先生对“无待”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容。首先,个体涵游于无限宇宙之中,化解了与万物“相对待”的敌意,从而与万物无有任何分别、界限;其次,达成无待的个体在精神上转变为造物主的化身,取得自作主宰的真人、至人、圣人之地位,达到自作主宰的精神自由。这样看来,当个体逐步提升其精神至一定高度时,其精神之转变就变成了宇宙之转变,变成了整个世界之人共同的精神转变,而不仅仅若儒家那样“外在地”与天地参。这种完全融入宇宙万象的精神转变避免了儒家的“人格优越论”,因为庄子的“个人的生活,就是指整个宇宙的生活,亦即同宇宙一同波动。因此,在这种境界,只有平等感而没有优越感”(16)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60页。。
方东美所提炼的三原理,实则按人之境界的逐次提升而展开,个体化价值原理是针对自足自乐、“拘于一小天地”的境界而言;超越原理针对意欲“突破外在的桎梏与拘束”的精神提升而论;“自发性自由原理”则针对“提升了的精神之最后归宿”而来。三者呈现出渐次提升与超越的关系,构成了方东美庄子“人格超升论”的“上回向”的主体内容。自然,这种上回向的超升仍然停留在理论上,欲达到真正的逍遥尚须从“下回向”即在生命实践上下功夫。
三、下回向:理论的旁通统贯与途径的选择
庄子的“上回向”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同“下回向”(17)注:“下回向”同上文中的“上回向”皆为佛学用语,“上回向”主要解决人如何通过修为、层层超越而成佛的问题,下回向则通过以普度众生的情怀重返并救助“世间”。联系在一起,二者亦难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此尤其体现于“自发性自由原理”中。以方氏之见,“自发性自由原理”乃个人同宇宙相互融合,并有望达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境界。这种“浑然中处”、不分彼此的态势实则凸显了道家天人合一之理念,亦即方氏所谓“道家的旁通统贯”思想。“旁通统贯”,实则以有机哲学的方式解决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即:“总是要说明宇宙,乃至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体”(18)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45页。.。
方氏认为,儒释道皆追求完满人格,其最终皆须通过“下回向”的具体落实方可证成。以道家言,老子偏重于上回向的自我超升,然而却很难返回人间,结果就有可能从世间逃逸出去;庄子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此偏颇。庄子的逍遥人格,固然是不断经过精神的提升,而逐次达到“寥天一”的极高处;然而,真正的至人、神人、圣人并不停留在“寥天一”处——倘若他继续在“寥天一”处,就意味着他仍然有所拘束、有所执着,同井底之蛙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并没有获得真正的逍遥:“大鹏神鸟绝云气,负苍天,翱翔太虚,其观点所得之景象,固永胜地上实物百千万倍不止,然以视无限大道之光照耀宇宙万象、形成统摄一切分殊观点之通观所得,则又微不足道矣!”(19)方东美:《方东美集》,第297页。真正的逍遥须是经过上回向的三层次方可达成——尤其体现在第三原理中“个体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圣人境界,“真正圣人,乘妙道之行,得以透视一真,弥贯天地宇宙大全,一切局部表相,无分妍丑,从各种不同角度观之,乃互澈交融,悉统汇于一真全界整体。一切分殊观点皆统摄于一大全瞻统观,而‘道通为一。’”(20)方东美:《方东美集》,第297页。此种互摄之有机境界即为方先生所醉心的“旁通统贯彻论”。由此,亦知真正的理性人格是必须“下凡”的,而不可停留在某一高妙处“与世隔绝”。那么追求无待、逍遥的庄子如何才能“下凡”,如何才能完成其理想的真人人格呢?庄子的答案为:须忘我、齐物。不同的是,在庄子那里是需要“斋戒”,需要若颜回那样“虚一而静”,用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方式完成(虽然间以理性的分析)。方先生的贡献在于其以独特视野对之进行了精致与深邃的理性分析,于学术发展大有裨益。
(一)忘我
“忘我”语出庄子《齐物论》,庄子借南郭子諅之口道出通往逍遥的必经之途——“吾丧我”。“吾丧我”即“忘我”,忘我即为去掉“小我”之固执,跳出“小我”的圈子,走向“大我”的境界——“大我”乃天地之我,不受拘束的“无待之我”。那么,要忘掉哪一个“小我”呢?方东美将“小我”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小我”可分为三种意义:第一种代表身体百官的“我”;第二种代表执行心灵功用的“我”;第三种是“统一的我”或“以‘我’为思想中心的‘我’”。
第一种肉体上的“小我”是在时空中处处充满滞碍的“小我”,因为凡“我”举手投足处,皆占有一定空间,从而与他人发生障碍,这种“我”可归结为局限于外部“物理世界”的我,此躯壳之我是阻碍人之精神人格超升的质碍。若以佛家思想对照,躯壳之我,应约略似对应由“地、火、水、风”所组成的色蕴;
第二种“心灵功用的我”则是受制于自身功能的我。人体器官之功能各不相同,形成又一种质碍,如眼能观色而不能辨味,耳能闻声却不能察颜。此言每一器官各有特殊功用,倘若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认识,则各各皆局限于自己的功能内,是为心灵功用之“小我”,此构成走向逍遥的第二重障碍。此种器官功能约略对应于佛家的“前五识”,即眼、耳、鼻、舌、身之功能性觉见;
第三种为“统一的我”,即把我作为思想的中心,比之于物理之我、心灵功用之我自然层级最高,因为此“我”能对外物作理性的思考,能将诸杂多统一起来进行理性分析(类似康德所谓的自我统觉)。无疑,此“我”由于受制于前两重自我之限制,对宇宙万物所作的结论往往如一孔之见而陷入自以为是乃至自我主义之窠臼,是谓“心机”。此亦是形成“我执”的关键,约略佛家的第七识末那识。佛家认为,第六识有“思”的作用,而第七识则是执着第八识阿赖耶识的见分,第八识则又受制于前六识,为染污识。污染了的第八识为第七识所执着,形成我执,加固了“小我”的空间,误把“小我”当做“大我”,故而始终处于轮回之中而不得解脱。
既然三种“小我”,并非真实意义的逍遥自我,而是“集结而成为妄我”。因此只有把三种意义上的“小我”清除之后才可能达到“大我”之境,所谓“妄我丧尽,乃登智境”(21)方东美:《方东美集》,第300页。。这个“大我”在方东美那里有两种说法,即“或指自发精神之本性,是即理性之大用;或指永恒临在之‘常心’,冥同无限大道之本体”(22)方东美:《方东美集》,第300页。。说法虽不同,其义一也,若用庄子的说法就是“灵台”——一种自觉性的自我:一方面能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另一方面亦能把自我的狭隘之心化掉而逐步提升至于“天地与一”的境界。庄子之“灵台”约略似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亦约略为佛学的“阿摩罗”(第九识)或清静如来藏。要之,皆为一种涵盖宇宙且为人人得以体验的普遍的精神。以此观之,作为绝对心灵与普遍精神的“大我”体现的是一个“通”字,通天地、通万物、通心灵:举凡天地间,大我无所不在,无所不通。假若到达“吾丧我”的“大我”的境界,或曰达到“通”的境界,其视野自然不同,若以“大我”的视野去看待万物,宇宙万物则应如何体现呢?循着这个思路,自然要过渡到齐物论了。
(二)齐物
以庄子思路,“齐物”既是“忘我”所达到的开阔视野,亦是“逍遥”的必要条件。没有“齐物”,则“小我”之“我执”没有破除,依然有某种成见在,“成见”乃是制约逍遥游的障碍。那么如何齐物呢?方氏同样给出富有洞见的解读,他认为,“齐物”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向上看齐”,一种为“向下看齐”。人世间无非有两种世界,一为世俗世界,一为高尚的理想世界。西方哲学将两个世界割裂看来,使得上层和下层互不通气,上帝自是上帝,臣民自是臣民。中国哲学则不然,以庄子为例,上层世界必须和下层世界沟通、平齐,必须通过“下回向”的过程,才能真正完成道家的卓越人格。于是就出现了上文中的“两种平齐”。如果将哲学家视为上层世界代表的话,那么就出现方东美所谓的两种平齐的对立。对此,他论述道:“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对立的;当然也可说一个精神解放的道家式的哲学家,与在现实上面平凡的人,彼此在那里呼唤。然而其间之不同,乃在于哲学家的呼唤是要现实的一切人‘向上看齐’,世俗世界的人站在现实世界上,却又呼唤哲学家要下来,要‘向下看齐’,与世俗世界看齐。”(23)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60页。两种看齐,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平等观,“向上看齐”体现了一种人格逐步超升的真平等,而“向下看齐”则代表了一种虚假的伪平等,因为拿世俗世界“本来的不平”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其结果自然是不平等的,此即庄子在《列御寇》篇中所论的“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之义。
既然“向下看齐”不可得,势必走“向上看齐”的道路。“向上看齐”是道家人格不断超升的过程,但此处却不能仅将其看做“上回向”,因为“向上看齐”涉及的是“真平等”的问题,也关乎“下回向”乃至方法和途径的问题。这个看齐,乃是“齐物”。关于“齐物”,章太炎颇有洞见:“今人所谓平等,是人和人的平等。那么任何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已经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庄子临死有‘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语,是他平等的注脚。”(24)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3页。从方东美对章太炎“齐物释”的赞同性评论来看,二者对庄子“齐物”的认识上,可谓“心有戚戚焉”!
“齐物”前提必须“忘我”,若有机心、固执之“小我”在,就难以齐物。然而,即便没有了“小我”,到达充盈宇宙间的普遍心灵的“大我”,终归是一个人的“孤往式”的“伪逍遥”,又岂能做到“与天地为一”式的“无待”之逍遥?“与天地为一”即必须把个人寓于宇宙之间,转化宇宙,转化他人,进而与万物“通”起来,于是庄子的“齐物论”就是以种种说理的方式破除他者的“机心”,以成见破除成见——倘若“齐物”本身也是一种成见的话。故而,就此而论,“齐物”并非取消万物自身的差别,仍是针对“我执”而谈。方东美明确指出:“庄子立说之真正动机及本意,乃在于为人类万般个性之天生差别谋致调和之道,而和之于大道之无限丰富性,并化除漫无目的、意义贫乏之单一性或表面上之平等性。是即建设性哲学之批导功能,而出之以后设或超哲学之层次者也。”(25)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99页。方氏此论,可谓精辟!
四、对庄子“齐物论”的“现代解读”
关于齐物——破除机心成见——的方法,庄子本人在《齐物论》中谈得较多,后世学者亦多有发挥,除了以道家立场诠释外,亦不乏以佛学理论注释者,譬如近人章太炎即作此理解。方先生凭藉其深厚的西学素养,对“齐物”做了更为别样的解读。
(一)对语言的分析
一如庄子的“齐物”从“大知间间,小之炎炎”之语言着手批判一样,方东美亦同样在语言层面上展开“齐物”的探索:“我们不仅仅要能够运用灵活的思想,而且还要灵活地运用适当的语言,来表现我们灵活的思想。而不能只以为语言指示实在。庄子认为这种‘图像语言理论是一种偏见’。”(26)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99页。方氏认为,庄子对言说的批判,实际上批判的是一种“图像语言”,即以语言代替实在,殊不知,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为了更好的破除“图像语言理论”的偏执,方东美对庄子“齐物论”中涉及到语言与实在的部分进行了扼要的分析。他认为:(1)庄子反对“简单心灵图像语言”,人们对某物虽然有言,但“言”未必就是实在,庄子所谓“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庄子·齐物论》),即然;(2)庄子反对素朴的实在论,名(语言)不一定代表实在,掌握了“名”未必掌握了实在,此应为庄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同上)及“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同上)流露出来;(3)庄子反对“言必尽意”的看法。语言与实在无必然之对应,语言不能代表实在,甚至也不能把握(说出)“实在”。正所谓“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也。”(同上)通过逐步分析,最后得出“言辩而不即”的结论。方东美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庄子的语言分析上,而是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的相关理论,将问题进行了深层的推进,从而深刻的彰显庄子的“齐物”之说。
方先生认为,克就人类哲学史而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无非有三:一则以定义、概念来厘定万物;二则以因果关系来厘定万物;三则以“实体”来推证万物。然而这三种认识方式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偏执。
“下定义”的方式来认识万物固然有其效用,但若深究下去,则并不究竟。因对同一物,站在不同的立场皆有不同甚至无穷的定义,方东美以数学基数“一”为例,一既可看做两个零点五之二倍,亦可看做二的一半,乃至无穷,那么究竟以哪个概念为准呢?此其一。其二,采用定义、概念法,则势必将概念推至无穷。譬如,当定义一种事物时,势必用其他的概念来表达,而其他的概念则来自于更远的概念,如此追寻下去,无有终极,甚至陷入循环论的窠臼。方东美以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物理世界本质》中的例子进行反驳,可谓入木三分:“比如说,要问什么是物质?就答说是质量。那么什么是质量呢?又答说是质波。那么质波由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则又答是因为物质的本性是质量。”(27)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70页。以定义、概念认识事物的谬误由此可见一斑。
以因果关系论证事物,亦势必陷入“死地”。因为在任何一个演绎系统里面,都必须有其前提(原因),按照无限追溯的方式,作为第一因的“原因”是无根基的,最终则可能或回到独断论的“设准”或回到循环论证。当然,对于第一因的“设准”固有其意义,如罗素就是依靠设准来保证知识的有效性。但从终极角度而言,未免不究竟。对于因果关系最终陷入循环论分析,方东美的论述更是精彩。他借用英国哲学家洛克的例子精辟地进行了论述:洛克看到某墓碑上刻有“地”字,就问“地”安排在什么地方?答案是“地”安排在墓碑上。于是又问墓碑安排在什么地方,答案是安排在一只乌龟背上。又问乌龟安排在何处?乌龟安排在岩石上。岩石安排在哪里?安排在地上?“地”又安排在哪里?答案“地”(这里是作为概念指称的“地”)是安排在墓碑上。自然,若从逻辑推理的方式,无疑存在偷换概念的嫌疑,即以概念之“地”换取了“实体之地”。然而若从因果关系的“无穷后退”的角度进行考察,则“因果关系”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死地。
以“实体”厘定万物,亦面临“不可知”的困境。无论概念(定义)、还是采取因果,最终都面临终极因(第一因)的问题,这个终极因就是无因之因,按洛克的说法就是“实体”。然而,什么是实体呢?“洛克说:‘从哲学与宗教上面看,假如我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话,实体就是我们的未知之物。’”(28)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73页。既然实体是未知之物,又如何能将其作为第一因呢?
通过上述抽茧剥丝式的论证,方东美以现代哲学的视野强化了庄子论证“齐物”的逻辑力量,把人们带入庄子自身的语境进而追问这样的问题:既然语言、概念、思辨乃至实体皆不能达到对象,在语言层面上导致不可说、不能说,甚至不可思议,那么人们对万物应采取何种态度呢?
(二)“莫若以明”的态度
语言层面的“一切不可说、不能说”(此与后世之禅宗相类,后人常以“庄禅相通”,固有其理)固然含有“齐物”的成分——因为万物对个体而言都是处于“无言”的地位,在这点上,确实有“齐一”的成分。但庄子的“齐物”绝非止步于此,否则世界真“难可了知”了,其构建的“道”亦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庄子认为道不可说、不能说的缘由在于人们“说出的”不过是个人的成见而已,并非真理系统,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人们的知见有无数,但以“道”观之,皆非最究竟的,只不过是一些边见甚至偏见,只是人们习惯于以一种偏见去否定另一种偏见,在相对系统里转圈子,甚至还有把相对系统无限扩大的趋势。譬如,庄子谈到的两人辩论代表两种观点,彼此不服,寻找第三者以裁判之,假如第三者契合于前两者的任何一方,亦不能代表其正确;假若第三方不同意前两者的观点,势必又加入了一种新观点,如此无限推演,观点越来越多,让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那么,应当如何对待这种种知见呢?答案是:“莫若以明。”
方东美对庄子的“莫若以明”认识可谓精辟之至!“庄子深知一切运用文字去陈述对真理的了解,都是构成相对系统。何谓相对系统?指这个叫做‘是’,指那个叫做‘非’,‘是’是这一个,‘非’是那一个,然后‘是’‘非’对照,便产生彼此对待。换句话说,所谓‘莫若以明’,就是指一切哲学真理的诉说,都是相对系统,在相对系统里,你不能拿‘此’来否定‘彼’,也不能拿‘彼’来否定‘此’,却必须容忍、容纳、承认别人对这于这一个问题,也同样的有权利和自由去表达,去形成一个理论。”(29)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76页。“莫若以明”同庄子所谓的“两行”其实是一回事,庄子深知人间存在诸多“知见”,但却非一棍子打死,亦非走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神秘之境,而是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对待诸种不同的“相对真理系统”(知见),以无私之“大公心”平等地对待各种言说。这个“公心”,就是各种相对真理的共同核心,即为“道枢”。若以庄子之言,即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关于“道枢”的理解,后世学者不免长篇大论,见仁见智。相比之下,方东美对道枢“图解”则清晰、简洁,方东美划了一个圆圈即解决了困扰人们的难题(此源自庄子)。方东美认为,圆心即为道枢,圆周则是由种种不同的观点组成,由圆心处看各观点,无有偏私之分(若以集合观点,即半径相等);同时,圆周各观点又是“道”的具体呈现——不同的场合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道无二至,不过是在不同的人那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而已。倘若以一己之成见为中心,则引起时间纷争,永无宁日。倘若以“那个核心为无穷系统的中心,以之诶大道的系统,才能把一切相对价值的真理都消解在那个无穷的真理系统之中”(30)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79页。,才能真正不偏私、心无凝滞,做到真正的“齐物”。
方东美所描绘的圆心(道枢)还意味绝对真理系统(即老子所谓的道、无),任何圆周上的系统只有和圆心联系起来,才能保持价值的“效用”,这个“效用”即是指不粘滞、不执着的自然逍遥状态。
要之,通过对达成逍遥的途径——坐忘、齐物——的分析,方东美既准确地理解了庄子哲学的精髓,同时亦藉此完善了其关于原始道家哲学的“双回向”理论,同时也侧现了方东美所谓的“旁通统贯”与人格超升论,较完满地展现出其旁通统贯论、殊道异论、人格超生论的中国哲学特色。无疑,这种全新的解读不仅继承并综合前人之所论,更以深厚的西学素养对庄子进行了创造性地解读,从而又超越了前人之见,无论对道家哲学研究还是对中西哲学会通皆有着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