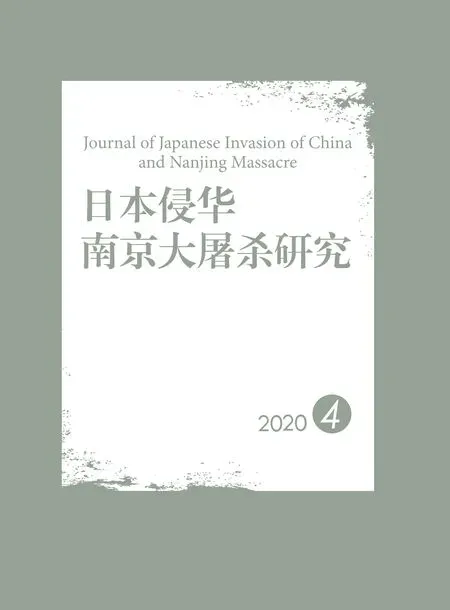全球化、抗战博物(纪念)馆与民族国家*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抗战记忆空间的构建
马 萍
随着中国提出共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写入中共党章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已成为中国新型外交战略和全球治理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的,以和平发展为内涵及宗旨的“全球观”,也是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下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
历史是构建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素材。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中,凸显中国人民基于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理念的抗战记忆,是讲好中国故事、有效传播这一新型价值观的重要文化素材。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战争存在着共同的苦难记忆与革命信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4日,第2版。然而,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环境中,任何一种新型全球价值观的构建,都考验着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叙事的文化能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新型全球观,考验着中国承载媒介在全球化语境下诠释和传承的能力。
抗战博物(纪念)馆是构建和传承抗战记忆的重要空间,也是中国传播和推广新型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由于承载着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抗战博物(纪念)馆一直被赋予培养和凝聚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记忆之场”的功能。集体记忆的构建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是构建主体合法性及最广泛社会认同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集体记忆也会不断重新构建。在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语境下,如何让抗战博物(纪念)馆这一典型的民族国家记忆空间,顺利转型为传播新型价值观的世界主义记忆空间,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从民族国家记忆空间到世界主义记忆空间
美国学者贝拉·迪克斯指出:“现代公共博物馆不只渉及储存藏品,而且是关于知识、身份和文化等级秩序及发展历程等重要现代概念的展示台。”(2)[美]贝拉·迪克斯著,冯悦译:《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中国学者俆贲亦指出:“没有博物馆,现代民族主义就会失去一个重要舞台。”(3)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尽管16世纪末17世纪初,私人珍藏品橱柜开启了博物馆的早期意象,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却是伴随着19世纪初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正如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所比喻的,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中,博物馆承担着“柔性意识形态机构”的职能,它通过相关的视觉形象和空间符号,实现观众对历史的再体验,成为国家对历史重塑、想象和动员的记忆空间。(4)[英]托尼·本尼特:《作为展示体系的博物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2年第1期。
与其他类型博物馆相比,以战争、大屠杀等创伤历史事件为主题的战争类博物(纪念)馆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尤为重要。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战争与死亡是锻造伟大国家最有效的途径,它们不仅构成了一个民族最基本的心理基础,也是塑造民族国家自我意象的最好素材。因此,战争类博物(纪念)馆也是构建“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空间载体。
在中国,抗战博物(纪念)馆是博物馆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其展示的是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凝聚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学者黄兴涛指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普及和认同的基本形成,也都是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1935年日本入侵华北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才得以实现的。”(5)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5页。因此,以书写和传承抗日战争历史为重要目的的抗战博物(纪念)馆,也成为我国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最为重要的“国家记忆之场”。据中国博物馆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在全国抗战博物(纪念)馆中,绝大多数都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深远的影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对人类的杀戮,使战争不仅成为各国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素材,更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创伤记忆的核心主题。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灾难、战争创伤等为特点的“记忆潮”席卷了全世界。此次“记忆潮”促使人们开始从人类整体视野出发,深刻反思战争、大屠杀、核爆炸和恐怖袭击等创伤事件。这使战争记忆的内涵得以拓展,不仅包含过去所强调的涉及群体或国家间利益之争的政治维度,更蕴含了以人性、道德义务等为核心概念的伦理维度。
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是较早提出“记忆伦理”概念的学者之一,她认为“与‘记忆政治’所强调的‘可利用性’不同,‘记忆伦理’强调不得不共同担当的责任,和共同面对、修复人性的破损,以及共同筑造理性的未来”。(6)[以]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著,贺海仁译:《记忆的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8页。换言之,“记忆伦理”要求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确保记忆被保存下来。俆贲进一步将这种聚合力解释为:“人性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7)俆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2页。美国学者丹尼尔·列维和那坦·齐奈德首次使用“世界主义记忆”一词来统称这种以“记忆伦理”为核心的普适性记忆类型,他们认为“人性”和“道德责任是世界主义记忆的两个重要核心内涵,“而世界主义记忆,这样一种由全球性记忆联盟促成的人类道德共同体,不仅包含了每个特殊个体的感知界限或主观性,而且也体现了一种集体意义上的文化同一性。它让全球性事件变成地方性本土经验的一部分,以及日渐增长的人类群体的道德生活世界”。(8)Daniel Levy and Natan Sznaider,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 The Holocaust, Memory and Trauma”,Topoi,2006(2).可见,世界主义记忆的提出和普及,使得战争、大屠杀等创伤记忆开始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民族和国家,具备了与人类普遍体验相融合的普适化认同视角。迄今为止,犹太大屠杀集体记忆被公认为是全世界范围内被构建得最为成功的世界主义记忆。它通过符号的泛化和去语境化,使曾经发生在特定历史情境,标志着种族仇恨、暴力与战争的事件,转化为代表人类苦难和道德堕落的普遍性象征符号。
美国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指出:“正是藉由人类共同的创伤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家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才不仅会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以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9)[美]杰弗里·亚历山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陶东风、周宪文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5页。正因为如此,出于建立一种新型人类关系和共筑理性未来的美好愿望,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世界记忆”项目,将以战争记忆为主的创伤记忆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与此同时,有关国际组织还成立了良心遗址国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国际公共犯罪受害者纪念博物馆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和国际和平博物馆联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useum for Peace)等。这些以战争、杀戮和恐怖主义等为主题的博物(纪念)馆组织,纷纷将“把本土经验转化为世界记忆,以此建立起世界性记忆联盟,实现‘坚持不允许战争再次发生’”,作为其运营的主要宗旨和目的。
记住战争创伤及战争中受难者的苦难经历已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更是全人类的普遍道德义务。因此,全球化语境下战争博物(纪念)馆所构建的记忆空间也开始不断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而更加具有全人类视野的普适化情怀。伴随着对战争创伤记忆理解的不断深化,战争博物(纪念)馆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经验,而与人类普遍体验相融合的阐释视角。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和平记忆空间
今天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人们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但粮食安全、心理冷漠、资源短缺、环境变化、普遍安全等却仍然威胁着人类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基于此,中国适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强调唯有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寻求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才能和谐相处并共同发展,因此,“和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关键词。与西方传统安全治理理念所认为的和平就意味着没有战争,意味着没有有组织的军事暴力不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和平”不仅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更是一种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一系列具有公共利益的共同体,在整体意义上呈现出的积极、持久而有意义的状态。被誉为“和平学之父”的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指出:“即使没有战争,也可能没有和平。这是因为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像战争冲突等显性暴力形式外,还包括像自然暴力、文化暴力、结构暴力和时间暴力等其他形式。与显性暴力形式不同,其他形式的暴力虽然无形,且看似呈现出一种稳定状态,但一旦发生质变,也同样会引发战争或冲突。”(10)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1969.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和平,强调的是一种整体性意识,它要将“和平文化”广泛渗透于意识形态、法律、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2018年9月,在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世界”为主题的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上,习近平致贺信指出:“和平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期待与殷切向往。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可贵,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11)《习近平向2018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致贺信》,《人民日报》2018年9月20日,第1版。“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景观的全球化流动都必须依赖并借助于媒介的构建与传播”(12)[美]阿尔君·阿帕杜莱著,刘冉译:《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上海三联书店2012版,第47页。,因此,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有效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就需要抗战博物(纪念)馆在构建具有世界主义记忆内涵的战争记忆空间基础上,增添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强调“记忆的伦理”。记住战争和暴行,并不是简单地追诉战争的发动者和施暴者的罪行,而是要警示世人,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记住战争和暴行还要突破地域和特定群体的局限,超越民族情感,在全球意识的基础上,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站在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维度来思考,而不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受害者的惨痛经历上。不仅如此,在“记忆的伦理”基础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和平话语,更强调全人类每一个个体在维护和平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唯有每一个个体都铭记惨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思人类曾经的暴行,时刻保持道德自省,并承担起自身的道德责任。只有这样,在面对新的战争时,才有可能做出合乎人性的价值判断和抉择,并对群体施加积极的正面影响,以避免群体行为偏离正确的轨道。
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13)[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时指出,平庸之恶隐藏于每个社会、每个人之中,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少数人。那么,如何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独立意识,以保证未来不陷入对战争的麻木之中呢?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要“在任何条件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因为只有每一个人都建立起对现代文明内部发生阻碍和平因素的反思、批判和警醒,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诉求。”(14)[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杨渝东、史健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由上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抗战博物(纪念)馆,不仅仅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仪式化空间和情感性空间,也不仅仅是具有世界主义记忆内涵与表征跨文化认同的伦理空间,更是一个致力于传播和平理念与呼唤个体道德责任的和平文化空间和批判反思空间。
三、新语境下中国抗战记忆空间的构建
近年来,面对世界主义记忆的发展潮流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新要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抗战博物(纪念)馆不再囿于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而是力图与国际接轨,在世界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2015年9月17日,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共同发起的“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在北京成立,参加该协会的有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韩国、意大利、日本、乌克兰、斯洛伐克等11个国家的35家博物(纪念)馆。该协会旨在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传承历史记忆、维护世界和平。2017年11月28日,来自18个国家近百名反法西斯战争博物(纪念)馆的负责人聚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形成了《南京共识》,与会者通过这份文件表达文博机构促进人权事业发展肩负的重要责任,并发出呼吁,全人类应以史为鉴,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人人得享和平、发展与尊严的美好家园”。(15)《加强交流合作 促进人权保障——第三届人权文博国际研讨会综述》,《人民日报》2017年11月30日,第9版。
毋庸置疑,这种发展路径契合当前国内外相关语境的变化,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任何一种新型全球价值观的形成与传播,都将考验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世界上的文化叙事能力。若抗战博物(纪念)馆真正实现从民族国家记忆空间迈向世界主义记忆舞台,成为构建、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媒介,就不能仅靠吸引更多的国际观众来馆参观,而更需要记忆空间内涵的深化,以及真正能够获得跨民族、跨文化认同的记忆群体的扩大。
就全国而言,虽然有了标志着中国抗战博物(纪念)馆历史记忆转型的《南京共识》,但从整体看,许多抗战博物(纪念)馆的记忆重构和转型仍然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总体而言,现阶段重塑中国抗战博物(纪念)馆这一承担着爱国主义教育职能的民族国家记忆空间,可借鉴国际战争类博物(纪念)馆发展转型的有益经验,在记忆空间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适时增加“伦理”话语,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重点关注和强调每一个个体的道德责任。
首先,增强以人性共生记忆的微观视角。与“民族国家”话语所强调的宏大、客观而一元的历史叙事视角不同,“伦理”话语所强调的人性更加注重多元而感性的个体微观视角。正如美国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所认为的:突出以人性价值为核心的个体故事述说是犹太大屠杀记忆得以顺利普适化构建的关键,“这种人格化的方式还原了犹太大屠杀的精神创伤以及受害者的形象”,其既“没有采取宏观的历史视角,也没有聚焦于意识形态。相反,它们从小团体、家人朋友、家长子女、兄弟姐妹的角度出发来描绘这些事件。”(16)[美]杰弗里·亚历山大, 周怡等译:《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相较于宏大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内容的单一化和导向性,唯有战争中个体的真实生活、生命体验和心路历程,才是真正能够与人类普遍体验相融合的叙事视角。因此,以人性共生记忆的微观视角不仅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形成一种与自我体验、经历共鸣的记忆,而且可以激发人们感同身受的情绪体验。正如美国学者丹顿所指出的:“今天,世界上很多博物馆对于战争死亡的描写都不再像过去那样赞颂为了伸张正义而作出的种种牺牲,而是更加专注于描绘战争受难者的苦难,尤其关注战争中作为个体的人的悲剧命运,通过对他们的缅怀来探讨现代性究竟为何会导致如此系统性的残暴。”(17)Kirk A.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m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60—78.
纵观国际上很多战争类博物(纪念)馆,几乎都设有系统收集受害者身份信息的纪念室。如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就在一间特殊的纪念室里,把受害者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出生、死亡日期都投影在墙上,同时,该馆还收集了上万份受害者遭受迫害的详细的个人和家族历史资料,供观众阅览。再如柏林犹太人纪念馆(Jüdisches Museum Berlin)在展示每一件受害者遗物时,都要添加该遗物的个体化信息。为此,美国学者詹妮·弗汉森—格吕克利希在评价该馆展陈时认为:“该馆在每一件遗物的说明牌中详细标注物品所有人的姓名、身份信息和它背后所发生的故事,以此呈现给观众一个个多元、丰富而立体的个体故事。让受害者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或空洞数字,而是能以清晰的形象实现与观众的互动和情感上的共鸣。”(18)Jennifer Hansen-Glucklich, Holocaust Memory Reframed—Museums and the Challenges of Represent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4, p149—172.
其次,提供包含多元观点的创伤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抗战博物(纪念)馆,致力于构建一个传递和平理念、呼唤个体道德责任的和平文化空间。然而,和平并非仅靠高呼口号即可实现,它需要的是每一个个体对和平的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建立。“平庸之恶”潜藏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内心,因此无论是和平态度的形成抑或是和平行为模式的建立,都需要每一个个体对战争的本质进行思考和反思。这就要求战争类博物(纪念)馆不应仅仅满足于如教科书般只让观众了解战争中发生了什么,更需要通过专业的深层次剖析和多元观点的提供,让观众理解、思考战争和人性的复杂性,让人们了解战争发生的背景、战争中各类人群的态度和遭遇,以及战争中任何一个决定将导致怎样的后果等等。
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话语的权威性和主导性,往往使得战争叙事具有一元及宏大的特征。这种采用宏大叙事框架去解释本身就非常复杂的战争和人性,虽然有利于特定历史观的传递,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批判性思维的形成。因此,新语境下的战争叙事尤其需要强调多角度的诠释。以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为例,虽然该馆自筹办以来就一直与美国视角和美国利益紧密相连而备受批评,但纪念馆却在很多方面尝试通过多角度的诠释来促使观众独立思考。如该馆在展示一幅美国空军在1944年5月拍摄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照片时,就将一封时任美国主管战争的副国务卿拒绝世界犹太人委员会请求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采取行动的来信予以并列展示,该信的说明牌称,美国空军本可以在1944年就对奥斯维辛采取行动,但美军却对死亡集中营未采取任何行动。这和热衷于将美国塑造为世界上与邪恶势力斗争的纯粹正面形象不同,该馆试图通过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照片和拒绝信的对比展示,将美军的冷漠态度这一迄今仍存在激烈争议的话题引入展览之中,以此向观众更全面地呈现战争和人性的多元复杂面相。
再次,打造“交互主体性”的记忆图景。“集体记忆不仅是被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的构建结果”。(19)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在传统的民族国家记忆空间中,记忆的传递模式往往是线性的、单向性的。在这样的记忆图景中,作为观众的个体会被制约在博物(纪念)馆生产的记忆框架和逻辑中去认知和体验。战争记忆需要的是世界上每一个个体对于整个现代性的反思和警醒,因此,需要博物(纪念)馆在原有记忆图景中对观众“被接受”和“被灌输”的角色加以调整,赋予观众更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此,英国学者沙伦·麦克唐纳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战争类博物(纪念)馆展陈理念——“世界主义展示理念”(cosmopolitan mode of representation):“世界主义展陈理念注重‘交互主体性’的观众体验。其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个体记忆的形成,而非历史知识的灌输。即战争类博物(纪念)馆既要提供给观众沉思的空间,也要充分调动这些记忆行动者在其中展开记忆实践的能动性。”(20)Macdonald,Sharon, Difficult Heritage: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Routledge,1998,p139.在这种展陈理念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战争类博物(纪念)馆开始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对话平台,而非对观众单向度的历史叙事空间。显然,“互动”已成为这一新型记忆图景中的关键词。
以美国宽容博物馆(Museum of Tolerance)为例,该馆是一个以互动而著称的高科技、参与式、实验性博物馆,其最具特色的便是还原了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餐厅场景,在餐厅的“菜单服务”平台上,有包含战争、仇恨与欺凌等不同选项供观众选择,当观众选择其中某个主题后,系统就会通过高科技手段还原这些情景。在视频播放完毕后,博物馆还邀请观众继续对刚刚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并鼓励观众将这些观点输入系统平台之中,之后,系统就会随机将观众的评论和观点制成表格,以供其他观众阅览。可见,这样的展陈方式让“菜单服务”平台本身成为一个可以启发人们思考和多元阐释价值的展品,其在吸引观众积极参与历史对话的同时,也允许并鼓励个体记忆嵌入集体记忆的构建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互动并不是高科技的代名词,“交互主体性”记忆图景的形成并不仅仅依靠新媒体技术来增进展览与观众的互动交流,它强调的应该是博物(纪念)馆与观众之间对于知识教化和自我体验的主体性对话。以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为例,该馆运用了大量当代艺术作品,以达到“交互主体性”记忆图景所追求的与观众的对话,以及新语境所强调的促使观众进行自我反思的效果。
四、民族国家记忆与全球意识构建关系的再思考
新语境下中国抗战记忆空间的历史叙事,应强调人性的微观视角,它不从情感上“绑架”观众,而是力图采用立体化、多维度的叙事方式,传递多元观点,由此向观众呈现客观的史实,并鼓励人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批判和自省的主体性思考,确保观众在自身作出价值判断的同时,也能反思战争的本质,以此真正承担起每一个人的道德责任。
然而,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心理构图” 的概念表明,记忆心理具有倾向性。当出现一个新的故事时,过去的固有心理倾向会对创伤经验的再现或表现形成一定的情感预设或情感期待。此时,文化心理的倾向会让记忆图式的转变十分困难。而从社会文化学层面来看,中国抗战记忆是重要的民族国家记忆的核心之一,因此,要让众多的个体展开自主性创伤书写,让战争书写呈现出更具丰富多元观点的立体叙事形式,有时不得不与民族情感相冲突。
英国学者沙伦·麦克唐纳曾指出:“尽管博物馆具有能够综合甚至是跨文化‘看的方式’的能力,但是,如何避免对民族的叙述,以及历史发生的因果论和进步论,毫无疑问仍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21)[英]沙伦·麦克唐纳:《博物馆、民族、后民族和跨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年第2期。纵观那些在致力于构建世界主义记忆空间方面享有盛誉的国际战争类博物(纪念)馆,也都或多或少地服从于国家利益,这不免会遭到来自各界的批判。如有学者批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通过获得近似于宗教般的神圣地位,为以色列国家的政治存在提供道义上的合法性。也有人批评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运用当代方法,把德国历史中的重要时期转化为美国人的想象与记忆,由此为美国改造世界提供依据。
对此,美国学者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形成的关键就在于民族国家是否成为具有世界普遍人类基本生活的秩序。”(22)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中国学者李昕进一步指出:“全球化进程中的力量博弈更趋隐蔽和复杂,只有民族国家自身强大才能保证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享有平等对话的权利。只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全球意识才能真正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主义教育是构建全球意识的基础和保障。”(23)李昕:《构建人类共同记忆:后申遗时代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的转向与深化》,《学海》2017年第6期。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微妙关系告诉人们,对于任何一段创伤记忆的构建,如果脱离了“民族国家”的叙事阶段,是根本无法直接进入“世界主义记忆”并最终完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书写宏愿的。因此,世界主义记忆与传统的民族国家记忆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那么,如何在这一曾经典型的民族国家记忆空间中适时增加“伦理”话语,并平衡好“民族国家”和“伦理”双重话语之间的关系,是顺利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舞台的关键,而“和平”这一包含所有国家和民族共同利益诉求的关键词,便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平衡好“民族国家”和“伦理”双重话语之间关系的核心。因为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承担起维护和平的道德责任,这不仅仅是激励人们在铭记历史的基础上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爱国情怀,更是促使人们形成放眼未来的道义感召力,让人们用更加宽阔的视角来认识自身发展与人类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在构建全球和平意识的同时,找准自身定位,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面对国际上世界主义记忆的发展潮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中国的抗战博物(纪念)馆这一典型的民族国家记忆空间,其内涵需要深化、功能需要拓展,适时增加“伦理”话语,并以新语境所强调的“和平”来平衡好双重话语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意识的关键,也是中国抗战博物(纪念)馆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