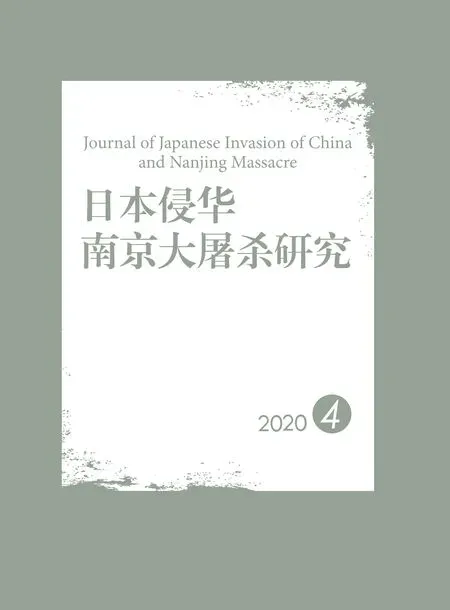衡阳保卫战的宣传塑造与记忆生产(1944—1949)*
郭 辉 傅伟男
战时宣传兼具军事与政治双重性质并贯穿整个抗日战争。美国政治学家、宣传政策研究奠基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将宣传定义为“它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1)[美]哈罗德·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简言之,以各种形式操控表述并试图影响大众的行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颇重视战时宣传工作,并先后出台《抗战建国纲领》《战地宣传方略(密件)》《战时宣传技术》及《如何使人民坚定抗战建国的信念》等文件。蒋介石在文件中明确指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宣传重于作战”,强调“今后军事胜利之前途,有赖于宣传之力量者至巨”,(2)《战地宣传方略(密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9年,第1页。尤其要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3)《如何使人民坚定抗战建国的信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0年,第1页。
衡阳保卫战的“抗战典范”塑造是战时宣传的经典案例。该宣传实践,引导社会民众形成某种倾向性记忆,衡阳保卫战被誉为“抗战史诗”,守城将士被称为“抗战的灵魂”,衡阳被打造为“抗战纪念城”。学界对衡阳保卫战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4)参见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陈长河:《衡阳保卫战与方先觉投敌》,《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柯育芳:《论长衡会战第二阶段战役》,《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记忆生产的角度回答这场存在投降嫌疑的战役缘何逐渐被神化。(5)关于方先觉等守城将领投降的问题尚有争议,大致有“投降说”“被俘说”“停战协议说”三种。回到历史现场,不难发现,衡阳保卫战具有符号聚焦的能力,并非后见之明的预判,而是国民党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6)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这些运行规则便是抗战宣传的效用,能揭示衡阳保卫战对国民党乃至中国抗战的特殊意义。
一、战前窘境: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
衡阳保卫战始于1944年6月23日,由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领,前后决死抵拒日军三次大规模进犯,直至8月8日拂晓,苦战四十七日的衡阳城终因兵疲粮缺、援军阻隔而陷落。作为历史事件的衡阳保卫战,经过守城官兵的英勇抗击与伟大牺牲,沉重打击了日军,延缓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计划”进程,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历史记忆的衡阳保卫战,其抗战地位的水涨船高,既由战时宣传所触发或衍生,亦在于战役之前国民党政权遭逢严重的“军事及政治之危机”。(7)林秋敏、叶慧芬编订:《陈诚先生日记》(一),(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579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渐趋危殆,于是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实现与印度支那半岛陆上联络,尤要摧毁衡阳与桂柳昆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防本土再遭轰炸。1944年1月24日,日本天皇发布“一号作战”诏谕,三个月后对河南中牟正式发动攻势。日军投入兵力约占中国派遣军总兵力的80%,约51万人,马匹约10万匹,火炮1550门,汽车约1.55万辆。这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规模的兵力投入。此次作战,分豫中会战与湘桂会战两个阶段,旨在贯通中国南北,全程达1500公里。
战前日方便已明确作战计划,为易于向衡阳、桂林突进,必须在开战四个月内击溃60个师的中方军队。(8)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豫中会战中,汤恩伯与蒋鼎文所部被日军闪电般击垮,国统区被截成两半,河南几乎全线崩盘,日军成功沟通平汉路南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判断,“敌鉴于马绍尔群岛失陷,及懔于海运船只吨位不足,知海洋交通不可必恃,乃变策略,以库页岛之利饵苏联,订(日苏)中立协定,移关东防苏兵力于我中原湘北各战场,欲以重兵急掠粤汉路,进而打通湘桂路”。(9)薛岳:《湘北湘南阻击战》,《正面战场·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于是,湘桂会战爆发。5月,长衡会战打响,第九战区调集第三十、第二十七、第二十四3个集团军48个师,4个挺进总队,总兵力约30万,抵抗日军。
由于衡阳正处粤汉与湘桂铁路的交汇点,上通武汉下达两广,既是进入桂、滇、川、黔等省的门户,也是湖南的经济重镇与物资集散中心,战略地位显要。日方认为“战局的关键”在于衡阳与长沙之间决战。日军试图一举拿下长沙,引诱中国军队对日采取攻势,以在衡阳决战时“尽量围歼重庆军”,为桂柳作战扫除障碍。(1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第13—14页。
经过长沙三次会战与常德会战,第九战区薛岳所部元气已伤,此时主力又调至印缅战场,各军还抽调1师到后方整训,番号虽众其战斗力削弱。在战略方针上,薛岳不顾参谋长赵子立的反对,囿于前三次长沙会战经验,对日军强大火力预判失误,执意在长沙决战,以致“由新墙河战斗开始至长沙失陷,将近一个月,而长沙的战斗仅占一天一夜多”。(11)赵子立、王光伦:《长衡会战》,《正面战场·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26页。至此,国民党军事危机遽升,“殆为武汉陷落以后之最”,(12)《王世杰日记》第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343页。“战局全变而大坏”,(13)《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并引发一系列政治危机。
一方面,军事上的溃败不仅使国民政府丧失土地及大量财政来源,更暴露了军队诸多弊端,军纪不良风纪败坏。河南尚未从1942、1943年干旱饥荒中恢复,便遭汤恩伯军队横征暴敛,百姓称之“河南四荒,水、旱、蝗、汤”(14)《长沙失陷后的危机》,《解放日报》1944年6月24日,第1版。;长沙作战时,长官假公济私以饱私囊,而士兵擅闯民房攫取财物,军民矛盾严重。(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四军参加长衡会战作战经过报告书(1944年9月)》,《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下),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9页。军队战斗力低下。军事检讨会上就有官员指出,事前疏于防范,部队斗志低落,且将帅不和指挥不统一,长官部形同瘫痪;抓来的士兵挨打受骂、饥疲不堪,临战一哄而散全无斗志,作战时平均六七人才能抵敌一人,作战能力可见一斑。(16)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台北)“国史馆”,1994年,第365页。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想念前途悲痛无已,几至绝望”。(17)《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另一方面,军事的失败使国民党的形象一落千丈。美国对蒋介石丧失信心,国内舆论亦纷纷指责。如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评价说,国民党与蒋介石“不能有效地抗战”“不能再代表这一民族了”。(18)《抗战后期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对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危机的片段评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1979年,第334—335页。甚至罗斯福提议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事令蒋介石备感侮辱,托词说“须有一准备时期”。(19)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北)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页。他后来致电华莱士称,中国战局“并未有如阁下在各地所得报告之危险与绝望之程度,此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20)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556页。国内方面,以中共为代表的民主化浪潮高涨,认为当时的局势为“抗战七年来所未有”,军队溃败的根源在于独裁与腐败,因此必须改弦更张,否则“战事必继续失败”“各种危机必将日趋尖锐”。(21)《长沙失陷后的危机》,《解放日报》1944年6月24日,第1版。国民党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政权合法性与抗战领导地位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都感到宣传工作之棘手,“愿辞职”。(22)林秋敏、叶慧芬编订:《陈诚先生日记》(一),(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579页。
于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衡阳保卫战的特殊地位就显露出来了。国民党政权选择于衡阳决战已是箭在弦上。战略上,衡阳为粤汉与湘桂铁路的交汇处,该战关乎日军能否打通粤汉路进犯广西;政治上,该战关乎国民党能否“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重获美国信任;民意上,该战关乎国民政府能否一洗前耻重塑形象。蒋介石亦称“今日惟一要图为如何固守衡阳”(23)《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并紧急调拨军队驰援,诫勉方先觉勇赴国难,亲下手令制订“连坐法”整饬军纪,甚至多次约谈梁寒操商讨宣传工作事宜。(24)《徐永昌日记》第七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368页。严重的军事政治危机令国民党精神紧绷,衡阳保卫战已被赋予诸多期待,这些均为战时衡阳保卫战的宣传埋下伏笔。
二、战时宣传:文字与活动的策划运作
战时宣传旨在以各种宣传方式灌输政治理念、坚定胜利信心,动员社会民众巩固统治抵抗日本。国民党宣传政策的规定相当细致:宣传对象上,要注意区别一般民众、农民、工人、商人、学生、妇女、士兵、敌军、伪军等,针对不同人群其宣传方式与要点不同。一般民众要使明了“国民公约各条之意义”,农民要使明了“农产品生产助长国力之重要”,士兵要使明了“不成功则成仁之军人精神”等。(25)《战地宣传方略(密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9 年编印,第8—13页。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因人因时因事因地采取合适策略展开宣传,可分文字(宣言、谈话、报纸、期刊、传单、通讯稿、壁报等)、活动(举办展览、演习、访问与慰劳、献金捐物、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口头(演说、座谈会、讨论会、谈话等)、艺术(戏剧、电影、文艺、歌咏、弹词说书、化装游行讲演、图画、照片等)四大类。(26)《战时宣传技术》,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出版时间不详),第28—37页。
衡阳保卫战的宣传则以文字与活动为主。文字宣传以报纸或通讯稿为主,是国家政策、战事讯息向社会传递的重要媒介,也是后方群众了解前线战况、军事动态的主要渠道,更是某些重大事件的记忆载体。本文围绕《中央日报》如何刻画衡阳保卫战进行,以观察国民党的宣传策略。
衡阳保卫战始于6月23日,《中央日报》6月26日即以“衡阳东北外围展开猛烈战斗”开始正式报道。8月8日,衡阳陷落。8月11日,《中央日报》宣布“守军牺牲殆尽衡阳沦陷”。有关衡阳保卫战的集中报道长达近两月,反反复复使用某些形容词刻画其战况进程、歼敌战绩、将士表现等,以烘托紧张局势、映衬将士英勇。大量铺叙使守军的抗战精神得以形塑,鼓励人们同仇敌忾。
战斗打响之初,《中央日报》即将衡阳战役定义为“恶战”,此后类似“恶战”“惨烈”“猛烈”等词汇几乎在每次的通讯稿中皆有出现,反复强化成为直观记忆。如经常出现的“惨烈空前之恶战”“全面阵地恶战”等用词用语。还有更具体的表述,如日本“此次屡攻衡阳不下,更复用尽其一切残忍手段,如不断施放大量糜烂性毒气及以飞机投掷烧夷弹”。(27)《衡阳市郊战斗极度紧张》,《中央日报》1944年7月5日,第2版。战争之惨状正是通过新闻报道予以呈现,如“我与敌往复冲杀凡八次,互有进退双方伤亡均重”,(28)《我军果敢拼战歼敌》,《中央日报》1944年7月31日,第2版。“与敌反复搏杀,不下十余次”,(29)《敌更番冲锋被击退》,《中央日报》1944年7月30日,第2版。这种“凄绝人寰”“惨烈空前”之血战,使得全城沦为焦土。(30)《敌称对衡阳发动总攻》,《中央日报》1944年8月7日,第2版。这些文字利用艺术手段对战场情形进行描述,不仅能真实地呈现战场,也能用艺术情感感染社会。文字既可深入描绘敌人的残暴,激发人们对敌仇恨,(31)《如何使人民坚定抗战建国的信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0年,第16页。又可引起受众对激烈战场的即视感,营造扣人心弦的紧张氛围,“恶战”叙述为将士的英勇表现作铺垫。
《中央日报》在士兵称谓、抗战决心、作战士气等方面精心刻画,以塑造将士形象凸显抗战精神。士兵称谓方面,言必称“忠勇”或“英勇”,诸如“我忠勇官兵”“我守备部队之忠勇将士”“我保卫衡阳之英勇将士”等不绝于耳。抗战决心方面,突出士兵决死奋战视死如归的精神,将士们“咸具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誓死拼战”(32)《衡阳城郊我军奋战》,《中央日报》1944年7月1日,第2版。,并且,“以迭挫敌寇凶锋之威力,愈益发扬革命军人之精神,不计牺牲,誓死拼斗”。(33)《我击溃犯耒阳以南敌》,《中央日报》1944年7月6日,第2版。作战士气方面,也极力展现士兵越战越勇的高涨气势,衡阳虽“被敌环围,但我士气则极端旺盛”,(34)《衡阳恶战继续正殷》,《中央日报》1944年7月2日,第2版。即便“血战八昼夜,我官兵虽受伤,仍不后退,士气极为旺盛”(35)《衡阳续制敌猛犯》,《中央日报》1944年7月9日,第2版。,秉持“果敢无畏之精神,不断向敌施行猛烈之反击”。(36)《衡阳攻防战发展至最高潮》,《中央日报》1944年6月30日,第2版。
战地报道为紧跟战场动态和进展,一般会涉及作战双方军队的伤亡数量。具体到衡阳保卫战,官方通过强调歼敌数表明己方取得的战果。对此,《中央日报》以两种方式加以呈现。一是频频使用模糊性语言表述战绩,如“杀敌甚众”“敌死伤惨重”“敌被我击毙极重”“歼敌甚众”。一是使用较具体的数字表明歼敌量,如“我阵地之前敌遗尸遍地,至少在一千一百以上”“先后歼敌共达六千余,内有敌高级部队长一人”“又于郊区歼敌八千余”“先后歼敌共达一万八千余”。歼敌数被强调的同时较少提及己方伤亡。就具体歼敌数而言,各方统计也有出入。方先觉声称最后歼敌数多达三万余,(37)谷光宇编:《子珊行述——方先觉将军哀荣录》,(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71页。官方媒体宣布“衡阳血战四十七日歼敌二万”,(38)《忠勇守军誓死报国》,《中央日报》1944年8月9日,第2版。日方则载死伤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余人。(39)李守孔:《民国三十三年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作战之背景——美国战略之歧见与衡阳保卫战》,(台北)《近代中国》1984年第42期,第48页。中方避而不谈己方最终伤亡数,强调歼敌众多激励士气,回应民众的期待,正是“从已获战果证明抗战必胜”宣传的实践。(40)《如何使人民坚定抗战建国的信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0年,第5页。
衡阳因其抵抗日军四十七日被誉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41)郑一禾:《衡阳颂》,《新闻天地》1945年第1期,第23—24页。《中央日报》从战役之初即有意进行包装宣传。6月29日,首称“衡阳安静巍然雄峙”。8月8日,仍强调“迄晓,敌未获得寸进”。前后类似“巍然雄峙”的表述多达24处,如“衡阳城仍屹如山立”“敌卒未能撼动我衡阳”“但敌仍未能丝毫撼动我阵地”等用词不绝如缕。7月20日的《中央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屹立不动的湖南战场”,肯定衡阳雄峙无恙,打击了敌人狼奔豕突的气势使闪击战转为持久战,壮大了历久弥壮的士气和百折不挠的民心,并最后将这一切归功于统帅部处心深虑的用兵作风。(42)《屹立不动的湖南战场》,《中央日报》1944年7月20日,第2版。衡阳这座城市安如泰山、坚若磐石可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比肩的描述,实则反映官方试图坚定民众抗战信心的强烈愿望。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8月7日,衡阳守军方面发表“最后一电”震撼人心:“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43)《忠勇守军誓死报国》,《中央日报》1944年8月9日,第2版。该电使整个衡阳保卫战的前后宣传浑然一体,将衡阳守军的抗战精神推向极致。
除文字正面积极宣传衡阳保卫战外,国民党还发动社会群众献金捐物、签名慰劳,也及时展开嘉勉授勋等,彰显出衡阳保卫战的价值和意义。活动是有力的宣传方式,也是社会记忆传播的手段,可以利用群众聚集之机,或现场宣讲或当场捐物以形成热烈氛围,颇具时效性与感染力。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国家和政权都该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对‘想象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44)[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衡阳保卫战进行之初即成为国民党利用和包装的对象,试图解决时局危机并进行精神动员。
社会活动作为抗战宣传的重要内容,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团结各界民众,包括振作敌忾同仇之心,坚定抗战意志;滋长民众爱护国家,拥护政府之感情与决心;激发人民普遍效死疏财,学习与国军之联络合作。另一方面,就前线战士而言,“申明军民一体与军民合作之要义”“说明人民对抗战将士之钦仰,国家对抗战将士之酬庸”“说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理由”,以鼓舞士气,激发抗战决心。(45)《战地宣传方略(密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9 年,第11—16页。所以,当时开展有各式社会活动,以营造热烈有序的团结氛围。
捐款献金活动。衡阳保卫战爆发后不久,正值抗战七周年纪念,全国慰劳总会为发扬民气鼓励士气,发起“慰劳湖南将士的捐款”与“七七扩大劳军献金”。献金活动分三部分并有具体安排,包括献金大会集体献金、一餐饭运动、自由献金。(46)《陪都各界七七扩大劳军献金节目》,《大公报》1944年7月2日,第1版。活动结束后,全国慰劳总会向民众公布献金数,褒奖献金较多的单位或个人,批评成绩欠佳者。(47)《内江献金超前》,《大公报》1944年6月30日,第3版。还有征集物品签名慰劳活动。衡阳受敌人两次总攻后,守城官兵伤亡惨重,城区一片焦土给养困难,蒋介石致电予以关怀,称“切不要让士兵们露宿”。随后,全国慰劳总会发起“捐献实物慰劳衡阳将士”运动,呼吁向劳苦功高的衡阳将士捐献急需物资。首先,该会宣告三日内送往航空委员会专机运至前线。其次,要求7月28日下午2时至29日下午6时完成捐纳。最后,发动重庆各界签名。签名共分三处,不分男女老幼均可前往,亦可附上慰劳将士之语句。(48)《请市民捐献实物慰劳衡阳将士》,《大公报》1994年7月28日,第3版。此后,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响应,仅重庆便有20余万市民参与。衡阳守军在前线艰苦卓绝的奋战感动了大后方的善良群众,展现出军民团结、众志成城的温暖画卷。衡阳将士的光辉形象在大规模献金捐物、签名慰劳运动中得到褒赞和宣扬,以有助于抗战动员,使“衡阳”在人们心里留下深刻记忆。
官方在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支援前线的同时,也通过嘉勉授勋对衡阳守城官兵予以褒赞。衡阳抗战的困难表现在阵地争夺战上,守城官兵作出极大牺牲,多数连队几乎全部阵亡,其英勇精神值得赞誉。因此,越是抗战艰难时刻,越需要对随时涌现的出色表现及时奖励,越是关键战役,越需要利用仪式树立英雄典范。6月26日后,敌军发起第一次总攻,第30团被重创,第7连张德山带领全连与敌拼至最后一颗手榴弹,全连官兵阵亡令人震撼。军事委员会为激励士气,授予团长陈德坒忠勇勋章。7月8日,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恢复张家山阵地有功,特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并记大功一次,其他作战的连长、排长等也获得忠勇勋章。(49)《国府命令 授葛先才等勋章》,《中央日报》1944年7月25日,第2版。7月13日,第3师师长周庆祥亲赴新街前线督战,将突入的敌人全部消灭,使阵地转危为安,特颁给青天白日勋章。(50)《周庆祥师长新街歼敌荣获勋章》,《中央日报》1944年7月19日,第2版。8月14日,中国空军节,国民政府对空军周至柔、张廷孟、高又新等授予青天白日勋章,黄镇球被授予二等云麾勋章等等。(51)《今日中国空军节 国府对空军将士授勋》,《中央日报》1944年8月14日,第2版。嘉勉授勋既为抗战树立了英雄模范,也给予前线官兵莫大心理安慰。
衡阳保卫战日后为民众广为传颂,固然功于守城将领自身之决心、士兵之用命,也得益于战时舆论的积极宣传。衡阳保卫战的记忆显然是有意宣传和策划的结果,从惨烈战况的描述到将士誓死拼杀的刻画,从辉煌战果的渲染到英雄授勋的操演,尤其是守军的“最后一电”诠释出军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至高武德。国民党官方媒体利用宣传话语配合战地新闻,以此“适应人民的心理”,(52)《如何使人民坚定抗战建国的信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0年,第16页。营造“在现场”的即视感,动员群众献金捐物、签名慰问等。当然,媒体报道背后反映出国民党的战时宣传政策,试图改变因河南战事形成的国军腐败不堪的丑弱形象,当时还期待通过“打几个胜仗,扭转国际观感”,(53)《徐永昌日记》第七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383页。这一切皆只是临时策略,未能形成长期影响,或许从另一面也体现出国民党本身的某些弊病。
三、战后反响:社会舆论的话语塑造
衡阳陷于敌手之际,外界多不清楚城内情形,且因“最后一电”臆测衡阳守城将士多已壮烈殉国,当时无论国民党抑或共产党均予衡阳守城将士较高评价。王世杰认为,衡阳一役“士气重于武器”“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54)《王世杰日记》第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365页。为衡阳陷落叹惋不已。唐纵为此“不禁黯然神伤,热泪夺眶”。(55)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解放日报》谓“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56)《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解放日报》1944年8月12日,第1版。但几天之后,日伪报纸宣称,以方先觉为首的将领悉数投降,(57)《日本大本营昨发表攻陷衡阳所获战果:渝军将领及士兵颇多投诚》,《申报》(上海版)1944年8月12日,第1版。国民党高层内部开始议论纷纷。然而,考虑到“最后一电”的舆论导向及多日宣传塑造出的军队形象不能因此土崩瓦解,蒋介石竭力排斥“投降说”,认为其系敌伪伎俩,笃信方先觉“决不至乞降”,(58)《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欲将衡阳保卫战树立成抗日模范,电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时为衡阳殉难军人举行默哀仪式,并致悼文誉其为“革命军人以身殉国之楷模”“足垂我民族成仁取义,千秋万世之光辉”。(59)蒋中正:《衡阳失守敬悼文》,李祖鹏编:《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国民党通过官方媒体宣传与仪式活动运作对衡阳保卫战进行典型刻画,将其作为记忆符号加以塑造,社会舆论的赞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形象。
衡阳沦陷后,有媒体称“衡阳的战绩是永在的”“打安了全国的人心,打高了国军的士气,更打稳了国家的地位。”(60)《衡阳的战绩永在》,《大公报》1944年8月12日,第2版。衡阳城虽沦陷,但其功不可没,有人称该战“写下了震惊环宇光昭千古的史迹,不但已令强敌丧胆,使我国军民益坚胜利在握之信心”,(61)《衡阳守军辉煌战果展》,《新福建》第6卷第1期,1944 年,第5页。且“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推衡阳之首”。(62)龙德柏:《方先觉不愧张睢阳》,《扫荡报》1944年12月18日,第2版。甚至高度赞誉“给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添了万丈光芒”,也“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吐了一口闷气”。(63)《扫荡报向衡阳守军致敬书》,《扫荡报》1944年8月6日,第2版。舆论称颂衡阳保卫战在艰难之际提升了抗战胜利信心与民族凝聚力,反映出现实政治的需求。
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将士所体现出的精神,重塑了国军形象。国家危难之际英勇牺牲、孤城奋战、忠肝义胆等精神甚为重要,媒体挖掘出这些精神内涵后,将其与国民党党国教育相联系,称其贯彻“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及信愿“若与总理‘军人精神教育’相对照,不成功便成仁热血染红了党史,死有余荣”,并被视为“国父大人无畏军人精神教育的实践,也是总裁‘军人魂’训练的结果”。(64)《衡阳守军忠义表天地》,《万象周刊》1944 年第61期,第2页。衡阳保卫战本为失败的战役,却被宣传成精神胜利,更把它包装成国民党教育实践的成功。如此言说无非为失败推卸责任,转移人们注意力,为重新塑造国军形象提供资本。
世界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场一路高歌猛进,国内正面战场则每况愈下,此时出场的衡阳保卫战却以衡阳的沦陷收场,于此,只有强化战役之外的意义和价值。社会舆论通过强调该战役的国际地位,以弥补战争失败的观感。因衡阳保卫战使“衡阳一度成为全世界注视中心的城市”,(65)《欢迎衡阳守将归来》,《扫荡报》1944年12月20日,第2版。且“敌之骄将堕兵,为之震栗,国际视听,因之改观”,(66)《不怕死精神之伟大表现 特向苦守衡阳之方先觉将军致敬》,《苏讯》1945 年第57、58期,第3页。衡阳“比之于史达林格勒,同其悲壮,同其灿炽”。(67)郑一禾:《衡阳颂》,《新闻天地》1945年第1期,第23—24页。衡阳保卫战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东条内阁之倒,我衡阳守军的苦打硬拼,实有其功”,(68)《衡阳的战绩永在》,《大公报》1944年8月12日,第2版。并且“为中华民族争回军人之气节,树立盟友们敢死军人之典型”,(69)宁墨公:《衡阳保卫战之史迹的检讨》,《民治》第1卷第1期,1944 年,第2页。甚至“奠定了我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70)《衡阳守军誓死报国》,《中央日报》1944年8月9日,第2版。衡阳保卫战体现出旺盛的战斗意志,其英勇牺牲精神乃抗日战争以来所少见,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经典之战。无论国民党抑或普通民众,皆希冀通过衡阳保卫战展现中国军人战斗意志,提升国际地位争取更多话语权。
随着衡阳保卫战传递的信息持续发酵,光环愈加灿烂,“四十七天”成为神圣的名词,成为光荣的标志,战役也被誉为“伟大史诗”。(71)郑一禾:《衡阳颂》,《新闻天地》1945 年第1期,第23—24页。其精神“永远彪炳千古”,丰硕战果“可与名城共垂不朽”,(72)根:《衡阳陷落与今后战局》,《新知识月刊》1944 年第4期,第4页。守城将士成为时代楷模。因为“以衡阳无险可恃的危城能够坚守苦打到四十七天之久,则何处不能守?又何处不能打?”(73)《衡阳守军忠义表天地》,《万象周刊》1944年第61期,第2页。如果“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74)《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大公报》1944年12月13日,第2版。因此,抗日战争“惟有发扬全民族不怕死之牺牲精神,始能争得最后胜利,以奠我国永久生存之基”。(75)《不怕死精神之伟大表现 特向苦守衡阳之方先觉将军致敬》,《苏讯》1945 年第57、58期,第3页。衡阳保卫战被称为“伟大史诗”,并要求人们以衡阳守军为榜样,本质上也反映出国民党能够被称颂的战役甚少。
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既被守城官兵的伟大牺牲感动,也被国民党宣传机器的政治话语引导。人们敬佩于衡阳守军敢打敢拼的精神,表达崇敬之情的背后,也是极度失望于国民党长久以来溃败无能丧师失地,如“久旱逢甘霖”般被激发,共同将衡阳保卫战书写成“神话”。
即便如此,也无法否认衡阳保卫战是一场失败的战役。虽然,官方认为其功劳“已达成最高战略任务”,(76)《军委会发言人谈 衡阳保卫战功劳已达成最高战略任务》,《中央日报》1944年8月12日,第2版。仍未能阻挡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步伐,此后的桂林战役一如既往地挫败。
随着衡阳保卫战中被俘将领陆续逃回重庆,无论国民党当局如何隐瞒回避,投降的事实也会不胫而走。于是,国民党面临的难题由如何挽回河南战役的颜面转为如何维护来之不易的政治资源,即衡阳保卫战的象征价值。
四、记忆强化:“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筹建
12月11日,方先觉返回重庆。次日,蒋介石即专门设宴招待予以礼遇。(77)《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大公报》第一时间以“苦战衡阳的英雄回来了”为题进行报道,并以“揭破衡阳敌谣之谜”否认投降说。(78)《苦战衡阳的英雄回来了!》,《大公报》1944年12月13日,第3版。重庆各界还举行大规模欢迎活动,在街上打上标语横幅称颂方先觉等为“抗战的灵魂”“抗战的精神”。然而,国民党内部颇有微词,中共则直接撕开国民党的假面具,严厉地指出“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79)《方先觉投敌经过》,《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5日,第1版。事已至此,蒋介石无路可退,惟有继续辩驳。
国民党深谙宣传运作的规则,从“破”与“立”两方面来维护形象。“破”在于澄清“谣言”。1945年2月,蒋介石授予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力斥党内异见。1946年7月,督战官蔡汝霖在方先觉授意下出版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其文再次否认投降事。1947年2月,投降一事依旧受时人关注,《申报》载“记者顷以日前报载方先觉被俘一事,询国防部有关方面,据称:此乃谣传,绝无其事”。(80)《方先觉被俘不确》,《申报》1947年2月16日,第1版。《大公报》也称“方先觉被俘说,国防部称不确”。(81)《方先觉被俘说国防部称不确》,《大公报》1947年2月16日,第2版。“立”则体现在充分运用衡阳保卫战的符号价值,利用已形成的某些共同社会记忆制作成某种纪念空间,以起到长期维护抗战话语及政权合法性的作用。纪念空间的内容是历史,指向则是唤醒记忆。(82)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打造即是为了维护和凝固社会记忆。
事实上,“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最初提议直接源于衡阳灾后重建的现实需要。衡阳保卫战使整个城市毁于炮火,百姓流离失所,加之瘟疫流行、旱魃为虐,其导致的灾荒为“亘古所未见”。(83)《衡阳灾荒亘古未有 发起商人节食运动》,《申报》1946年5月23日,第4版。地方政府电请紧急救济与灾后重建。然而,重建费用高昂,湖南省政府的财政亦甚匮乏。如此背景下,衡阳市议长杨晓麓、副议长欧柄堃等5人于是组成“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希望通过请愿来获得国家财政支持。1946年10月20日,请愿团从衡阳启程,并邀请“中央新闻社”跟踪报道。10月31日,到达汉口,拜访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并致电行政院、国防部等重要官员。11月6日,抵达南京,受到湘籍民众热烈欢迎。12月5日,杨晓麓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征得舆论支持。12月10日,杨晓麓一行正式向国民政府请愿,递呈请愿书及建设计划。请愿团活动颇受社会关注,且多将衡阳残破现状与衡阳抗战精神联系,以此激发人们对衡阳保卫战的记忆并博得同情。
当然,“衡阳抗战纪念城”提案最后能顺利通过,既是杨晓麓等通过宣传造势获得舆论支持的结果,亦是其所呈理由契合当时国民党的需求:其一,抗战胜利后中国跃为五强之一,“矧兹空前抗战之成果,可无纪念以资观感”;其二,衡阳为抗战贡献巨大,国民政府应“轸念衡阳之破坏而特于建设,否则无以慰已死三十余万之英魂,劫遗一百六十余万之喁望”;其三,外则列强角逐,内则各党争鸣,“如不提高民族意识,万一再遇事变,将何以固人心而御外侮”。(84)罗铁恕:《衡阳抗战纪念城定名的由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衡阳文史资料》第四辑,1985年,第64页。蒋介石收到呈文后于12月15日亲自召见杨晓麓,18日颁发电令核准“衡阳抗战纪念城”的命名,并准由国民政府一次性拨款200亿元。1947年1月,杨再谒蒋介石,请求命名典礼时颁发训词并题颁“衡阳抗战纪念城”碑文,再次获得答允,整个过程几无阻碍。(85)《衡阳抗战纪念城 蒋主席题颁碑文》,《申报》1947年2月4日,第2版。蒋深谙衡阳保卫战的记忆价值,不仅可借此回应他人质疑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更能以此维护并加强自身统治地位。
“衡阳抗战纪念城”的请愿得到国民党中央首肯后,衡阳便成立筹备委员会开始准备。首先,要确定命名典礼的选址问题。筹委会为凸显抗战纪念城的重要地位,经多方讨论最终选址岳屏山。该位置具有重要历史与象征意义,作为衡阳保卫战主阵地之一,日军68、116师团于此遭受毁灭性重创,寓意衡阳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杰出贡献。其次,抗战纪念城应铸造标志性纪念空间。在岳屏山山腰上先后修建了纪念塔、纪念堂、纪功亭等,打造出一座胜利公园为命名仪式奠基之地。其中,纪念塔高18米,塔碑镌刻蒋介石所题“衡阳抗战纪念城”七个大字,以此作为仪式空间的中心。碑座为八方须弥座式,取八方和平、永无战事之义。(86)杨安:《父亲杨晓麓的故事:“衡阳抗战纪念城”建设始末》,《文史参考》2010年第5期。塔后是抗战纪念堂,四壁镶有民国政要与社会贤达、各团体所赠共46件题词碑刻。附近的纪功亭旁,立有章士钊所撰“衡阳纪功碑铭”等。建筑既是思想与精神的凝结,也是权力意识的表征。这些建筑群建立于山腰之上,显示出“抗战纪念城”的威严与神圣,其错落有致的空间布局让人油然而生景仰之情。
1947年8月10日,命名典礼在岳屏山山巅举行。仪式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具有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功能。衡阳保卫战蕴含的象征意义内附于仪式,仪式所形成的社会记忆通过操演又得以宣传,(87)郭辉:《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本质上是政治权力与社会意志希望通过某些手段保存社会记忆的结果。典礼场地搭建有高大牌楼以营造庄严气氛,杨晓麓主持命名典礼并面向各界群众宣读蒋介石所颁训词。其训词名为“以‘仁者无敌’之义为国人告”,肯定衡阳保卫战为“全世界稀有之奇迹”,亦是“中华固有道德精神之表现与发扬”。(88)《衡阳抗战城命名典礼 蒋主席特颁训词》,《申报》1947年7月20日,第1版。仪式中宣读训词,抗战纪念城得以正名,成为国民党政治意志的体现,“抗战纪念城”之名被赋予政治合法性。训词将衡阳保卫战誉为中华道德精神的体现,为抗战精神的再构。“只有仁者才能无敌”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意味着衡阳保卫战的意义蕴涵也由抗战精神的象征升级为民族道德的典范。
自命名典礼后,国民政府内政部遴派专家莅临衡阳视察,湖南省政府成立市政技术小组,市政府成立抗战纪念城设计委员会,纷纷商讨计划,加快推进建设进程。其中,时任衡阳市工务局长欧阳鸣提出具体方案:首先,须明确建设的一般原则。衡阳应建设成富有纪念抗战意识的近代化都市,发展工业扶植其经济地位。其次,区域划分要因地制宜,应对工业区、商业区、农业区、文化区、公园区、平民住宅区、公墓等做细致划分,契合城市实际。第三,市中心区道路建设要系统化。应对江西岸道路系统、南北向四干线、东西向干线、平行铁路、干路人行道、车马道、林荫大道等做具体规定,统筹兼顾。第四,自来水及下水道要有详细规划。应针对人口数与用水量等安放自来水厂的位置,下水道明沟与暗沟要做互用等,考虑经济实效。(89)欧阳鸣:《计划中的抗战纪念城——衡阳》,《市政评论》第10卷第8期,1948年,第9—10页。这些措施致力于衡阳重建,思考细致周密,可将衡阳城建设为30万人省级规模的工业城市,反映出时人重建衡阳的热烈期盼。
此外,全城范围内修建一些有关抗战的纪念性建筑更是题中之意,欲使衡阳打造成真正的“抗战纪念城”。欧阳鸣在工业城市建设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纪念性建筑的构想。一、城之外围为两岸之林荫大道,两大道围成一炮弹型,以石鼓咀为终端,湘江铁桥为其底,全城平面即为一抗战纪念品。二、两林荫大道,西正名为抗战大道,东为胜利大道。沿江东西两路,分别易名为叔章路、船山路。上下长街易名为澹庵路等。三、在已修建抗战纪念碑塔之岳屏山上,加建船山图书馆,搜罗船山遗著以及抗战史实充实之。四、江西岸南广场,建阵亡将士纪念塔一座,北广场建自由神一座,胜利大道之南端,建蒋介石戎装跃马铜像一座,北端建凯旋门一座。五、接龙山建自由钟一幢,纪念式喷水池一座,每年守城纪念时开放,以象征烈士精神永生。六、恢复石鼓书院,嗣胡(澹庵)周(濂溪)两先贤。七、黄茶岭设遗族学校一所,飞机场附近,建纪念营房两幢。八、建抗战纪念大厦一幢,作大集会之用。(90)欧阳鸣:《计划中的抗战纪念城——衡阳》,《市政评论》第10卷第8期,1948年,第9—10页。这些设计围绕“抗战胜利”的主题,运用隐喻、联想、暗示等艺术手法展开空间布局,修建相应建筑,从而表达空间的纪念性价值,彰显衡阳整个城市具有抗战纪念意义的独特性。
“衡阳抗战纪念城”的出台缘于城市重建的迫切需要,命名及设计方案的顺利通过,则得益于杨晓麓等地方官员的切实努力,也包括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官员的价值考量,这是国家权力介入公共空间的过程,也是地方意愿与国家意志合奏的结果。根本而言,衡阳成为抗战纪念城在于衡阳保卫战体现出的精神价值,其象征意义超过了军事战略上的作用。衡阳保卫战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战斗意志、与阵地共存亡的牺牲精神、保家卫国的民族气概等,在抗战纪念城的建设话语中全部凝结成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而这些纪念碑塔、牌坊地标等以不同形式叙述着这座城市过去的历史,成为湖南乃至全国人民共享与展示的记忆载体,为民族和国家提供认同资源。
上述宏大计划的美好愿景并未能如期实现。一方面,建设款项迟迟未下,后来杨晓麓虽向蒋介石再次呈请此事,但行政院也仅“先行核发四十亿元”。(91)《建设衡阳抗战纪念城 蒋主席准先拨四十亿》,《善救月刊》1947年第28期,第15页。另一方面,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生死决战后,建设计划搁浅。
衡阳抗战纪念城的建设前后历时两年,也曾一度热闹,未能起到真正维护国民党政权的作用。但衡阳抗战纪念空间的命名及其修建的部分建筑却可唤醒与维持人们对衡阳保卫战的记忆,历史记忆反过来强化空间的纪念性,二者相得益彰。新中国成立后“衡阳抗战纪念城”碑文改为“衡阳解放纪念塔”,衡阳人民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记忆逐渐取代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记忆,受日本侵略的创伤记忆与中共伟大的解放记忆得以凸显。原有的记忆被覆盖叠加,“衡阳保卫战”的记忆书写进入沉寂期。
结 语
宣传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从建构主义视角而言,记忆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重新建构,宣传的目的是希望受众能沿着既定方向形成某种记忆或价值认同,当记忆得以强化则可巩固宣传的效果。国民党政权在遭遇政治军事的重大打击后,除增强军力部署外,还充分发动宣传机器巩固自身的权力话语。无论原来发生的事情真相如何,宣传所形成的公共记忆能起到关键作用。只要它能满足权力运作的现实需要,哪怕牺牲一般军事伦理,权力运作者也可有意识地筛选事实,对其进行夸大或遗忘,重构事件试图在社会中形成符合其所希望的某些观念,再通过某些纪念仪式固化这些观念与记忆,达到维护政治合法性的目的。
衡阳保卫战成为“抗战典范”,其中有关投降的问题被遮掩,便是受到这些政治运行规则的影响。战争发生时,国民党利用官方媒体集中报道战事进程,书写惨烈的战况与将士英勇的表现以图重塑国军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动员社会民众进行献金捐物、签名慰劳等仪式操演以营造军民团结,树立抵抗日本的信心。衡阳沦陷后,社会各界赞誉有加,称颂其伟大功绩,将之描述成“伟大史诗”,甚至为投降辩护者,短短两年内逐渐被塑造成罗兰·巴特所指的“含有各种意象和信仰的神话系统”。(92)[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各种象征符号及隐喻的社会记忆最终凝聚成抗战纪念城。
综上,国民党政权利用各种方式书写事件并制造记忆,以引导与控制人们思想倾向。但因为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色彩,其威权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民族危机压力得以缓解,其宣传政策与独裁理念再也难以奏效。(9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人民大众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不再屈就于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选择了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