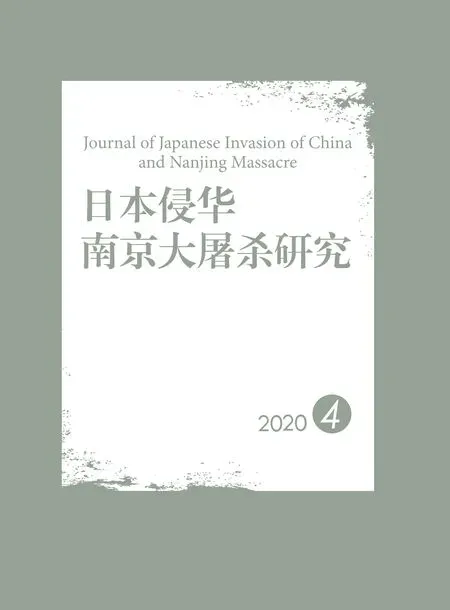《南京事件:日本48名目击者证言》及文本分析*
杨夏鸣 王晓阳
作为“虚构派”在英语世界“外宣”重要内容和最新成果,《南京事件:日本48名目击者的证言》 (TheNanjingIncident:JapaneseEyewitnessAccounts—Testimonyfrom48JapaneseWhoWereThere)(1)日文版书名为《“南京事件”日本48人的证言》。2017年在“传播历史史实协会”( Society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官方网站发布。(2)参见 Society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 at http://www.sdh-fact.com/index.html.与“虚构派”的其他著作和论文不同,这是一部具口述史性质的史料书籍,值得分析和研究。本文将探讨英译版原本的起源及其作者的背景与写作立场,概述48份证言的内容,并对摘要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分析不同版本内容的变化和否定率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尽管阿罗健一是带着预设立场进行采访的,并且在证人选择、证言取舍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受访者之口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由于存在着受访者审阅书稿和仍然健在的制约因素, 1987年版的35份证言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参考意义,其英文版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未必会达到作者所希望的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预设结果。
一、英译版原本及其作者
《南京事件:日本48名目击者的证言》的作者阿罗健一,1944年出生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东北大学文学部毕业后,1966年春入职皇声唱片(King Records),但在1984年离职,其时他40岁,成了自由职业者。20世纪80年代初,他常以笔名发表政治评论性文章,但他似乎不满足停留在评论性文章的撰写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了职业生涯向近代史研究的转向。
1984—1986年,阿罗健一采访了一批1937—1938年曾去过南京的记者、军官、外交人员及艺术家,并整理了他们有关南京的证言,1986年5月到1987年5月间,陆续在《正论》杂志上发表。(3)此前,部分证言以其他题目在《世界与日本》杂志上发表。1987年,又以《纪闻·南京事件——日本人所看到的南京屠杀事件》为题,在图书出版社出版,内容为35名相关人员的采访录,外加补遗。
2002年,经过若干增减,阿罗健一以《“南京事件”日本48人的证言》为题,并以文库版的形式由小学馆出版。与1987年版相比,该版本删除了松本重治的证言,增加了南正义等3人的证言,另外,新增了11位当年没有接受面对面采访,但对其信函提问进行了简单书面回复的部分内容,以这种方式,阿罗健一将提供证言的总人数增至48人。该版本对1987年版证言的内容也进行了部分删减。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删减并非简单的再版修改,而是别有用心的,本文第三部分对此将进行数据分析。
专业转向后,阿罗健一的学术头衔从政治评论员变为了近代史研究者,并担任了“百人斩诉讼支援会”会长、“要求撤出中国抗日纪念馆中不当照片的国民之会”会长等社会职务。此外,还担任了“为了恢复主权之会”“田母神论文与自卫官名誉思考会”的顾问。显然,他的历史研究提高了他在日本的知名度和地位。
2017年,作为虚构派在英语世界“外宣”的重用组成部分和最新的成果,该书的英文版(TheNanjingIncident:JapaneseEyewitnessAccounts—Testimonyfrom48JapaneseWhoWereThere)在“传播历史史实协会”( Society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官方网站发布。(4)参见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 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t http://www.sdh-fact.com/index.html.
在英文版的前言中,阿罗健一对其采访的情况也有一简单的介绍。他称找到了67名去过南京并还活着的军官、记者和外交人员,并与他们进行了联系。“在这67人中实际采访了35人,并与11人进行了信件联系。其余的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联系。在采访过的35人中,有的见过一次面,有的见了10次。但一般情况是两次听他们陈述,一次核对我的手稿。在出版前还请他们不仅核对他们自己陈述,而且核对了全书”。对阿罗健一整理的书稿,“有一半人同意,四分之一要求我改变用词和更正误解,另有四分之一人要我根据他们的意见重新写。”(5)Ara Kenichi, 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ra-Nanjing , g-1 p.9 at http://www.sdh-fact.com/index.html.这一信息对本文第三部分的文本分析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从表面看,通过采访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对还原历史真相的确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些证言是重要的一手参考资料。日本记者樱井在英文版的导言中溢美道:“了解事实(南京事件)最有效的路径就是聆听当时在场者的陈述。阿罗健一在这本书中采用了这一方法——最直截了当和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视角。”(6)Ara Kenichi, 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ra-Nanjing,g-1,p.3.然而,从采访对象的选择上看,阿罗健一却并非想真正地了解和还原历史真相。日本学者秦郁彦曾批评,“很明显,可以看出他(挑选采访对象)的策略是回避那些会给出暴行证据的人,而选择那些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人,因此,得出没有发生违法情况的结论。”(7)参见秦郁彦『昭和史の謎を追う』、文藝春秋、1993年。为了回应批评者的指责,在英文版的结尾处,阿罗健一特地列出了包括福田笃泰在内的18人名单,称由于生病或是死亡,他与这些人进行了联系,但未能得到回复。
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对比了《世界与日本》《正论》所刊载的证言文本及1987年版和2002年版书的内容后指出,“阿罗删除了对自己不利的采访记录”,并列出了多处被修改或是删除的内容,如“单行本删除了佐佐木元胜采访记录”“记录被删除的理由是因为佐佐木清楚地说‘发生了屠杀,绝不能否定它’”。(8)[日]笠原十九司著,罗翠翠等译:《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7—99页 。实际上,采访者一些提问的倾向性也十分明显。如采访足立和雄时,阿罗健一试图引导他否定其他几位报道南京暴行的记者(本多、报道“百人斩”的浅海等);采访桥本登美三郎时,试图通过桥本来诋毁报道过南京暴行的今井正刚和守山义雄的意图十分明显。(9)如阿罗健一问桥本登美三郎是否了解今井正刚和守山义雄,在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阿罗健一补充道:“今井正刚写了《南京城墙内的大规模谋杀》的报道,称有两万人被屠杀。守山义雄没有写任何东西,但有人说守山告诉他人发生了大屠杀”,希望以此来启发桥本。桥本回答说:“我没有直接从他们那里听说过,因此不知道它的真伪,(但)这两位记者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接下来,阿罗健一又问桥本是否记得今井正刚凭借想象写报道情况,如在入城式发生之前就写好了入城式的报道,目的是通过污名化今井的职业操守来否认其有关南京暴行的报道。
另外,通过梳理阿罗健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10)阿罗健一:《虚构的南京大屠杀证据——“崇善堂”之谜与真相》,《正论》1985年10月号;《反日宣传中使用的日本“谢罪金”——村山原首相撒出的钱去哪儿了》,《正论》1999年6月号;《纪闻·南京事件——日本人所看到的南京屠杀事件》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雅加达黎明之前——为印度尼西亚独立而拼命的人们》,劲草书房1994年版;《“南京事件”日本48人的证言》,小学馆2002年出版;《如今必须纠正的“南京事件”——日本人48人的证言之“真相”》,《SAPIO》2002年2月27日号;《〈南京战·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中的胡说八道》,《正论》2002年11月号;《百人斩诉讼报告书——等到恢复名誉的那一天为止》,《正论》2003年12月号;《为中国的南京“屠杀”宣传打开新风口》,《祖国与青年》2003年2月号;《南京“事件”研究最前沿——日本“南京”学会年报2005·2006年合并版》,展转社2005年版;《“再检证”究竟在南京发生了什么》,德间书店2007年版(本书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蒋介石战时宣传的工作所捏造”);《日中战争为德国所谋划——上海之战与德国军事顾问团之谜》,小学馆2008年版。,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对南京暴行目击者采访的立场是预设的,即希望通过当事人之口,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如早在1985年,其调查采访工作尚未结束时,阿罗健一就在《正论》上发文,标题的定性词语就用了“虚构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2002年又以48人的证言为依据,得出“如今必须纠正‘南京事件’”的结论,但通过这些证言,人们果真能得出这一结论吗?
二、目击者证言概述
为了便于了解英文版《南京事件:日本48名目击者证言》全书的内容,下面是48位目击者证言的概述。(11)本章所有资料均源自Ara Kenichi, 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t http://www.sdh—fact.com/index.html.摘要的原则:一是围绕发生在南京的屠杀或是其他暴行这一议题进行,无论是肯定或是否定都是概述的重点;二是有关日军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而其他内容一般省略;三是根据受访者当时的职业归类证言。另外,为了方便分析,根据采访内容,笔者将阿罗健一编撰的证言分为三类:肯定、否认和中间。所谓肯定,是指受访者在证言中没有明确否认有大规模的屠杀;承认在其活动的范围内目睹或听说屠杀中国人或是中国俘虏的场景,包括在江面射杀泅渡过江没有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目睹平民尸体及日本军人对平民犯下诸如强奸、抢劫、纵火等暴行。所谓否定,是指完全否定南京发生了屠杀或其他严重暴行。所谓中间,是指受访者称没有看到“大屠杀”,但看到或听说过屠杀俘虏或是看到江边的尸体;看到或是听说过强奸、抢劫、纵火等暴行。
1. 记者
山本治大阪朝日新闻社上海支局成员。1937年8月15日撤离南京,9月底去上海。坐飞机来南京报道入城式,在南京数天,后去杭州。看到城墙周围中国士兵尸体,在中山门看到市区多处冒烟。没有看到或是听到大屠杀。报社里从没有人提及过此话题。宪兵不允许他进入安全区。没有看见平民的尸体。看见红卍字会的人员在清理战争受害者(遗体)。在上海读到中国报纸“血战光华门”的报道,但从没有看到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人们可能用平时的标准描述战争,称其为大屠杀。
足立和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12月14日到南京,在南京大约10天,看见日军射杀十几名中国人。他们挖了壕沟,让中国人排成一行站在沟前,向其开枪。这事是当着妇女和儿童的面做的。记不清确切的地点。也许在其他地方有更多的中国人被屠杀,总数可能有几千人。城里的年轻人被认为是便衣士兵,日军的目的是清除“便衣兵”,但他们也许做过头了。
桥本登美三郎朝日新闻社上海支局次长。七七事变时,任南京支局负责人。淞沪战役爆发后,成为上海支局负责人。日军进攻南京时,协调记者(50人)报道,并待在十六师团司令部。受采访时表示从未听说过“南京事件”,私下也没有。如果有的话,记者会提出这个问题,或是委婉地表达。因此南京没有大屠杀。
金沢喜雄《东京日日新闻》摄影记者。经历光华门的战斗后曾在南京四处行走,在南京待了一个月。从未看到或听到能够被称为大屠杀的情况。但有尸体,可能是日军射杀的,并扔进江里。江面漂有尸体,在通往南京道路两旁的河里也有。城里有战斗,不否认可能一些难民也被射杀。对同事浅海一男(认为发生了大屠杀)的评价:与自己一样有点古怪,但是一个好人,在南京,他没有对自己提过这事。
佐藤振寿《东京日日新闻》摄影记者。在常州拍摄了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照片。认为由于他们职务(副官和炮兵中队长)不大可能进行“杀人比赛”。并暗示由于他与廖承志是同学关系,浅海一男不愿说其“百人斩”的报道是“小说”。讲述了其同事(记者)盗窃中国文物。在88师司令部前面,看见日本士兵屠杀中国士兵。在安全区,一位说英语的中国人要他告诉日本士兵不要屠杀中国人。12月16日,看见中山路站满了从安全区抓出来的“便衣兵”,他拍了照片。没有看见大屠杀,日本报纸都没有提到过大屠杀。听说3000中国士兵在下关排队被重机枪屠杀。他拍了那张日本士兵用童车运行李的照片,称并非是抢劫的物品。
五岛广作《大阪日日新闻》随军记者。1964年出版《南京作战真相——第六师团战史》,与谷寿夫关系密切。12月13、14日,日军进行了扫荡行动,但没有发生大屠杀。采访时多次否认。
铃木次郎《东京日日新闻》记者。1971年曾在《丸》杂志发表了“我所见证的南京悲剧”。他在南京停留了3天,看见城里多处着火。目睹日军在中山门屠杀中国士兵,在励志社入口,用镐杀害俘虏及另一个地方屠杀中国士兵。在光华门、下关有尸堆,目睹被汽油焚烧的尸体。相信“百人斩”是真实的,但非亲眼所见。
二村次郎《报知新闻》(读卖新闻报系)摄影记者。在南京期间,从未看见大屠杀这类事情。战后常有人问及此事,但他没有印象。与奥斯维辛不同,没有指定杀人的地方。东京审判时第一次听说,仔细回想进城后曾看见一个 20×30×1米的大坑。这可能与大屠杀有某种关系吧,但这只是猜测。在白天看见俘虏被捆着排队行走。南京可能有数百俘虏被屠杀原因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如果能找到押送俘虏的士兵,可能可以了解所谓大屠杀的一些情况。听到许多记者说他们看到长江里漂着无数的尸体,但自己没看见。高大建筑里面被洗劫一空,看见日本士兵在房屋里点火。
田口利介《报知新闻》(读卖新闻报系)记者。进入南京看见两三具尸体。曾进入总统府。当时没有听过大屠杀,没有人提及。就其所见,十六师团没有大的纪律问题,但在前往南京的路上,一个军士声称将用军刀杀100名中国人。这名军士沉迷于报复,但是一个胆小鬼。他的同事岩田岩二后来乘船来南京,在接近南京时看到长江上漂浮的尸体。
樋口哲雄《读卖新闻》摄影记者。从中山门进入南京,在南京待了一个多月。无论是否发生,他不知道大屠杀这件事。没有看见大屠杀的痕迹。中山陵没有被洗劫。在战争的情况下,你不杀人,就会被杀。有人说这是大屠杀。不知南京是否存在慰安所。
森博《读卖新闻》摄影记者。12月15日或16日到达南京,19日离开。1938年1月再次前往南京。在南京时,听日本士兵说过他们将俘虏带到江边,并将释放他们,但最终将其全部屠杀。还听说江边都是尸体。屠杀的原因是没有粮食和地方关押俘虏。听说许多中国士兵被屠杀。屠杀的命令是来自小队长这样的下级军官,但高级军官了解情况。几年后,他亲自见到低级军官屠杀中国俘虏,并问他:“你为啥不试一下?”这些人在陆军中是少数,但败坏了陆军。没有负罪感。他听说过屠杀的情况,没有看到,但看见日本士兵故意烧房屋,因为中国士兵会使用它们。不仅士兵,记者也在偷窃(抢劫)食物和其他东西,没有负罪感。记者们知道屠杀这事,但战争时期屠杀不是新闻,也不允许拍尸体照片。
新井正义同盟通讯社记者,同盟社上海站负责人。松本重治写回忆录时,向当时在南京的3位记者了解情况,其中前田雄二(每晚写日记)说看到了南京大屠杀。他看到士兵的尸体或者是“便衣兵”的尸体,他没有核对整个南京,但估计有30000—40000具。日军进入南京后,战斗时有发生。估计有160000中国残兵。在郊区的朝香宫司令部受到袭击,他前往报道,朝香宫说:“一个可怕的夜晚”。15日他前往位于金陵女子大学附近的原同盟社办公室,学校负责人过来抱怨:“我们接受的是女性难民,日本士兵侵害妇女,你们能帮助我们吗?”他们向日军司令部报告了这一情况。他没有看见屠杀,他的同事崛川在下关看见了射杀和尸体。他的同事前田雄二12月16日在陆军学校看见了处决。他不否认有一些死亡,但20万或更多不大可能。
浅井达三同盟通讯社电影部摄影师。拍摄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多场战役的纪录片。他的同事前田雄二每晚写日记,他记录了一些当时无法告诉陆军的严肃事件。在前往南京的途中,目睹一家银行被炸开后,一些士兵用中国纸币来煮饭。进入南京后看见多处失火。在他的《摄影机与人生》中前田雄二提到大屠杀。他看到数队中国士兵被押走,有不少穿着便装,也有逃难的农民。手腕晒黑的被当作逃兵抓走。他不想拍摄尸体的照片,即使看到也不拍,也不摆拍。他与石川达三很熟悉,认为他写的都是真实的。战后,他拍摄了东京审判的全程。他认为对松井的指控是合理的。
细波孝同盟通讯社无线电技师。在汤山镇附近看到有一万多中国俘虏。战地记者也收集赃物、文物。在下关看到了屠杀的痕迹。子弹宝贵,将俘虏关在碉堡里,浇油后点燃。不仅工事里,长江边也看到尸体,一些被捆着。看到中国俘虏被押走。估计很多尸体被江水冲走。后来听说有两万俘虏被屠杀。
南正义《新爱知新闻》(现为《中日新闻》)记者。没有大屠杀。没有人说过和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战后中国编造这个故事。有一些士兵失去了理智,但这是战斗。战场上往往不遵守规则。日军粮食不够。日军中没有“俘虏”的概念。不杀俘虏是国际法后来的概念。有人说杀死穿平民服装的士兵是大屠杀,这是不对的。1986年,来南京参加南京——名古屋友好城市活动,与南京市市长等在南京大桥上慢跑,当时没人提南京大屠杀。
三苫干之介《福冈日日新闻》记者。在乌江遇到桥本欣五郎。12月13号下午从下关进入南京。在水西门外遇见鹿儿岛小原大队。第二天一大早,吃惊地看到路边有500-600具中国人的尸体。在宝庆银楼找到十八师团的司令部。(12)被采访者记忆有误,原文如此。占领南京后,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过有任何大屠杀。但在入城式后就去了上海,故无法评说。1939年,作为支局负责人返回南京,在南京待了6年,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
小池秋羊《都新闻》(现为《东京新闻》)记者。12月9日,到位于马群附近的十六师团司令部。听说南京部署了25—30万中国士兵,但攻城时5万士兵留在南京。13日,从中山东路进入南京,南京死一般的寂静,没有战斗的迹象。在中山路和中正路的交界不远的地方,有一场大火,并迅速蔓延,没有人救火。有外国人驾车路过、拍照。后来得知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了日军的暴行。在安全区,看到抓“(中国)士兵”,其亲属哭诉他不是士兵,但还是被抓走。一组有10—20人被抓走,估计被带到郊区枪杀了。在新街口附近的一幢未完工的建筑地下室,看到了尸体,地下室的水被鲜血染红。挹江门有一具被碾扁的尸体。离开下关时,看到码头下有不少尸体。看见十六师团的士兵抢东西。军官对此视而不见。马渊逸雄(13)1929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先后在步兵第三十四联队、近卫师团司令部、第七师团司令部、陆军省、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任职,1937年11月晋升为步兵中佐,1939年3月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长,同年8月晋升为步兵大佐,后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兼报道部长,1940年12月,任大本营报道部长。试图在城门拦截外国记者,但他们已经返回上海。不少报纸刊登了相关消息。如果有人说有南京大屠杀,他说他无法反驳。但数字被夸大。
箭内正五郎《福冈民报新闻》记者。12月18日,重新找到六十五联队司令部,听说了俘虏的事。猜想是释放了俘虏。在当时除了将俘虏赶走没有其他的选择。1938年出版《支那事变乡土部队写真史》是基于事实,与新闻检查无关,但地点、部队名称不能在报道中出现。战后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使他再次想起了这些俘虏,《沾满俘虏鲜血的白虎部队》的作者秦贤助没有去过中国。当时弹药供应紧张,不会用来射杀俘虏,除非他们暴动。在南京江边没有看到尸体。没有大屠杀,是战后传播的谣言。
2. 陆军军官
吉永朴第十军参谋。为了迅速到达上海派遣军的后方,第十军现地征用(抢)粮食是不可避免的。从上海到南京,第十军推进迅速和(作战)勇敢,一些人将勇敢和大胆行动与纪律问题混淆了。进攻南京时,第十军的司令部在洪蓝埠。他于13日从中华门进入南京,将司令部选在朱雀路和建康路交界之处的上海储备银行。在城堡附近看到了尸体,看起来很凄惨。在去银行的路上,遇到一个落魄的家庭,他给了他们他的名片,并在上面写了“让他们自由通过”。在下关码头江边,看到数千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有许多穿着平民服装的尸体。还看到悬吊的穿着平民服装的尸体,看起来他们是被绞死的。没有大屠杀,因为大部分中国平民逃走了。另外,杀死数十万人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冈田酉次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参谋(负责经济事务)。 12月13日下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在城堡附近没有太多的尸体。他是第一个进入交通银行的日本人。银行周围也没有很多尸体,保险柜开着,里面没有账本和钱。中国银行也是空空如也,因此,他对中岛日记中记载的日本士兵抢劫银行的说法表示怀疑,不过南京有许多银行及分行。除了视察银行外,另一个任务是如何处理军票。在离开南京前,看到军票在城外的文物(赝品)和香烟交易中使用,但往往是日军强迫买者接受。他认为,“大屠杀”是将非武装民众聚集在一起,然后射杀或者是类似的情况,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看到逃兵和“便衣兵”被打死,他们的尸体后来被认为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一些日本士兵为了报复可能失去理智,屠杀了一些中国士兵。
大西一上海派遣军、华中派遣军参谋。 1938年,任南京特务机关负责人。从未看过和听过长勇(14)1928 年日本陆军大学40期毕业,1929 年任步兵第四十八联队中队长,后入参谋本部中国课。1930年成为樱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参加编写《国家改造案》。1933年8月任台湾步兵第一联队大队长,1934年8月任第十六师团留守参谋,1935年12月成为参谋本部员支那课中佐课员兼陆大教官,参谋本部附汉口武官。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派遣军参谋兼华中方面军参谋。12月任朝香宫鸠彦王指挥下的情报主任参谋。1938 年3月任朝鲜军属下的第十九师团步兵第七十四联队长。同年7月晋升大佐。下屠杀令。角良晴说,长勇是给第六师团下命令的,但第六师团隶属第十军,这是不可能的。没听说过长勇在华中方面军担任过参谋。“不接受俘虏”的意思是收缴他们的武器,让他们走。陆军从未下过屠杀的命令。松井批评中岛“烧中国人的房子没有问题”的言论,由他传递给其参谋。原来决定由第九师团驻守南京的,但参谋长中川希望返回上海打扫战场,所以只剩下十六师团。守备司令佐佐木到一是中国专家,但喝酒后行为有问题。12月13日,去挹江门,道路两边堆满尸体。12月18日,去下关,看到江中有许多尸体。没有听说过大屠杀。他自己驾车巡逻过,看到一起强奸案。抓了现行,是十六师团的士兵。发生多起强奸案。军队开始反对建立慰安所,看到多起强奸案后,决定建立一个设施。日军的确要求红卍字会掩埋尸体,且是掩埋主力。自治委员会也掩埋了一些,但不多。当时从未听说过有崇善堂这个组织。
冈田尚上海派遣军松井随员。在前往汤水镇的路上,看见日本士兵在河堤上刺杀中国俘虏。数千名俘虏被迫坐在空地上,里面有女兵。他们将数名俘虏在河堤上排队,并刺死。村上中佐下车说这太残忍,指挥官(少尉)说,他们不能浪费一粒子弹,只能杀死中国俘虏,继续向南京推进。进入南京印象最深的是到处都是丢弃的军装。因为如果他们穿着军装就会被日本兵杀死。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悬挂着许多绑腿。城内商店空空荡荡,被士兵洗劫。没有对普通人群的大屠杀,城里没有尸体。有一些强奸或抢劫案子,但不多。受害者会向日本领事报告。大量的房屋被烧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听说在将俘虏送过江时发生了骚乱,他们射杀了俘虏。一些俘虏和逃兵,包括逃入安全区的一定是被屠杀了,日本士兵没有精力照顾俘虏。他怀疑这是否应该称之为大屠杀。下关有许多尸体,松井和他都看到。在司令部讨论过俘虏问题,长勇说过一些疯狂的话,但这不是命令,他只是一名参谋。
谷田勇第十军参谋。松井与柳川属于日本陆军的不同派别,两人关系不和。柳川的照片被高层禁止刊登,在入城式的照片中,他的脸部被损坏。除了在杭州湾登陆阶段外,部队在供给方面没有什么困难。没有听说第十军有纪律问题。第六师团没有进行任何大屠杀。一一四师团的战斗详报说他们收到了旅团长屠杀俘虏的命令,他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命令。战场上没有出现(处理)俘虏的问题。第十军司令部于14日中午从中华门入城,几乎没有尸体。在下关码头看到2000—3000具尸体,有一半尸体穿军装,其余是平民尸体。他们应该是逃出城被十六师团包围射杀,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大屠杀。在莫愁湖和其他三个地方看到尸体,现在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14日经过挹江门,没有尸体。长勇也许向下属部队的参谋发过口头命令,但发布正式命令不大可能。12月19日离开南京,之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金子伦助第十军参谋。进城后没有看到尸体,也没有听到枪声。在南京待了一晚或是两晚。对南京没有特别的记忆,这表明没有发生什么事。
冈田芳政内阁企划院事务官员。1935-1936年,在南京任职,1937年底至1938年,在南京。12月24日乘船到南京。在江面看到了十几具漂浮的尸体。他们听说有更多的尸体,但漂走了。他们通过挹江门坐车进入南京。接他们的军官说日军在挹江门周围包围了中国军队,所以有许多尸体,但他只看见一些。第二天,特务机关的佐方繁木作为向导,他们去了光华门、中华门和城北。看到了日本士兵、平民和记者,一些房屋被烧毁,有一座还在冒烟。在金陵女子学院里有难民,也许是门卫认识他得以进入。只在挹江门外的江边看到一些尸体,在市内没有看到。他猜想是被清除了,但在十天时间里只能清理数百具或是数千具尸体。占领南京前后他都在南京,因此他相信“南京事件”是中国人的宣传。在宣传战中日本失败了,只能是这样。
谏山春树参谋本部总务课长,大佐。1937年12月底被派往上海,新年时前往南京。不是为了视察纪律问题而是为了了解部队情况。在南京时看到一具妇女的尸体,仅此而已。但塚田攻(15)日本茨城县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日本陆军大学第26期。 1935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后任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参谋本部附,是对华战争扩大派的决定人物之一。1937年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松井石根,参与指挥了攻占南京的战斗。后为陆军大将、第十一军司令官。告诉他,松井对日本士兵犯下的暴行感到非常担心。这不是具体所指,如大屠杀或是类似令人震惊的事情。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出现过大屠杀的报告,没有掩盖情况的命令。中岛日记中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接受俘虏”指的是缴械、释放。日本人不认为自己会被活捉,因此他们没有做俘虏的想法。当时根本不知道有“南京事件”。
大槻章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编制班参谋、华中派遣军参谋。1937年12月底,作为军务局军事课编制班的参谋视察了南京。没有看到大屠杀的任何痕迹。在司令部与参谋官员讨论了许多事情,他们根本没有提到大屠杀的事。他相信大屠杀的故事是一个谎言。1938年,他作为华中派遣军的参谋去了南京,也没有听到任何这类消息。命令大屠杀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如果有大屠杀的话,当他去南京时,作为参谋他应该听说过。他是在畑俊六将军手下,他与他有多年的交集,如果听说了大屠杀的话,他会坦率地告诉他。
三国直福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长。12月15日,到达南京,22日离开。在师团司令和参谋长那里没有听说纪律的问题。下级的报告中也没有特别的事件。他进城时,南京有些可怜,空荡荡,街道上可能有尸体,但他没看见。他没有时间仔细观察。他视察了他下属的战斗地区,没有看到大屠杀后留下的尸体。1938年,作为第十五师团的参谋长,返回南京驻守江宁。没有听说大屠杀的事情。1940年,成为南京特务机关首脑,接触了各种中国人,他们没有说过大屠杀的故事。不知道高冠吾在东郊掩埋3000尸体和立碑的事情。
小柳次一陆军报道班成员,自由摄影师。1938年3月,他拍的在南京处决一名间谍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1月2日,离开上海,4日晚,到达南京站。从挹江门入城,映入眼帘的是城墙上挂着许多绳索。城门的右边竖着一块大的木质纪念碑。当时没有尸体了,但他听说占领时,城门两边堆满了尸体。日本军舰使用了所有的火力向企图渡江的中国士兵开火。据说尸体很多。他们到达南京的晚上,发生了一场大火,据说是“便衣兵”放的火。第二天开始拍照,街道上没有姑娘行走,他试图在金陵女子大学为姑娘拍照,但卫兵不让他进去,说任何人都不许进入。南京很平静,没有看到日本士兵做残暴的事情。没有听说过大屠杀的传言,但听说有300多人在江边被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到江里。根据他在南京很长时间的经历看,大屠杀指的是战场上的尸体。
3. 海军军官
寺崎隆治“势多”号炮艇舰长。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在镇江龟山遭到中国炮兵的猛烈攻击。在南京遭到来自乌龙山及江对面炮火攻击。在长江分汊处(八卦洲或三汊河),发现许多中国士兵坐舢板或木筏漂浮在水面,“势多”上有四挺25毫米机枪,他们向他们扫射。长江上到处都是中国士兵,有的就抱着门板,他们向他们开火。在向下关码头行驶时,有中国士兵误将其当作中国船只,向他们招手,他们向中国士兵射击。“势多”号并没有像《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送外国记者去上海,17号后才离开南京。在下关没有看见处决中国人。14日,他派关口去视察南京,他回来后报告南京很平静,没有特别的事件。根据命令,他们夺取了江对面的一家硫酸铵工厂。参加了入城式,去了紫金山和中华门,没有看到尸体。下关和浦口的岸边有4000—5000具尸体。那是战斗,混乱中他们向中国士兵开火,里面可能有逃难的居民。
土井申二“比良”号炮艇舰长。11月 10日开始,从上海沿长江前往南京。在镇江停留了几天,掩护天谷支队过江。在入城式前一两天,到达南京的中兴码头(宝塔桥),那里有许多军事物资。在保国寺,看见有6000—7000名难民。看到十多具尸体。在下关到挹江门的路上,看到五六具尸体。在离开宝塔桥前,他们清理了街道,重建了桥梁。还征募了红卍字会的陈汉森掩埋尸体,他也是难民营的负责人。1938年新年,土井等带着药品和粮食再次来到中兴码头,陈汉森及市民用鞭炮欢迎他们,陈汉森还给他们感谢信。
重村实海军新闻处上海海军武官府报道负责人。12月17日,乘飞机前往南京参加入城式,当天返回。南京一切正常,路上没有看到尸体,也许尸体已被清理。在城外机场附近,看到数名中国人进入私人房屋偷东西。他在南京只待了一天,但没有看到什么异常。听到一些传言。在上海时,他看见一日本士兵抓住一中国人,他问该士兵如何处理中国人,士兵说“如果这个人可疑,将杀了他。”他问如何判断中国人是否可疑,该士兵说取决于他的外貌。今井正刚(写过南京屠杀的报道)是《朝日新闻》的最好作者之一,也是他的好朋友,没有听说过他写大屠杀。返回上海后,重村听说松井将军在纪念仪式上向部队发出过警告。他认为日本部队做一些很坏的事情,也就是松井最讨厌的事情。海军的确在下关用机枪扫射中国士兵,但这是战斗,伤亡也不大。海军训练有素,但陆军都是被征召入伍者,命令往往得不到执行。
源田实第二联合航空队少佐参谋。航空队误炸了“帕奈”号,不是故意。他们没有想到美国炮舰会在那里。他感觉外国人留在南京是为了激怒日本人。击中“帕奈”号的是春田重治。入城式后,他驾机到南京。日本在机场附近建立了司令部。每天往返于两地,并开始轰炸南昌和汉口,不了解南京市区情况。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就海军而言,这种行为是违反武士精神的,永远也不会发生。他警告他手下的人,不许杀俘虏或是任何不能抵抗的人。如何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住谷磐根海军从军绘画通讯员。乘坐炮艇前往南京。靠近南京时,看见南京在燃烧。在距南京1500-2000米的地方,看见中国士兵坐着小船或门板试图逃往浦口。炮艇向他们射击,由于距离只有四五米远,都被打死。看在城墙上挂有许多绳索。从兴中门进入南京,地上的血很滑。看见十几具尸体。几天后,他骑自行车在城内闲逛,并画了一些素描。没有看见中国人,日本士兵也不多。几次日本士兵差点把他当作中国人而向他开枪。返回兴中门时看到一队中国士兵(俘虏)在缓慢地行走。在下关码头,看到20多名日本士兵在砍杀中国士兵,然后将他们推入码头下面的水中。他想打开手电筒,仔细看,但日本士兵警告他会沾到鲜血,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一大早起来去看尸体,有800多具,有些人还在动或发出声音。他相信这就是所谓的南京大屠杀。
4. 外交官
渡边义雄外务省情报局摄影师。外务省决定拍摄展现日军形象的照片和纪录片向美国和世界传播。1938年1月,前往上海和南京拍摄宣抚班帮助难民的活动。拍摄团队共六人,由一等秘书小川领导。他们乘扫雷艇前往南京,船上有作家、诗人和战地画家。他们到下关时,一个士兵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进行砍头行动,然后将尸体扔到江里,称“很快江水将变成红色”,并建议他们去观看。但他们没有去看。一些摄影师拍照片,目的是揭露和谴责,但他没有这种想法。这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看,为什么不拍照?”他从来没有想隐瞒。他们充满仇恨,为了复仇,没有任何负罪感。没有监狱,也没有食物,(杀俘虏)没有选择。到南京时,街上所有的商店门都是开着,橱窗是空的。当晚,在大使馆过夜,使馆没有食物。他们在使馆待了两天,每天都有人来报告日军犯事(抓妇女)。看见尸体被丢在两条大路交叉处转盘的树丛里,一具前额有刀伤,另外几具的头被从后面砍过,脸上全是黑色的血,非常可怕。去难民营,拍了日本兵分发给难民食物的照片。晚上,可能有士兵溜进难民区,做这类事情(抓妇女)。1938年新年,再次来到南京,难民仍然在难民营里。偶然听到中山陵方向传来的枪声。他拍的照片在三越百货商场展览过,题目是“南京——上海新闻图片展”。他将这些照片寄给外国、外国外交部及《生活》杂志,但没有被发表。1945年3月9日美国轰炸(东京)时,他拍的照片全部被烧毁。
岩井英一外务省领事馆补、中国问题专家。1937年12月31日,离开东京,陪同外务省情报局长河相达夫视察被占地区。在南京被占领数周后,他们在那里待了几天。南京是一个战场,看起来也是。没有看到或是听到任何有关大屠杀的情况。他怀疑河相达夫访问南京的目的是亲自调查传言。1938年2月28日,他到达上海,担任副总领事,他想再次说,之后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大屠杀的情况。
粕谷孝夫外务省领事馆补。上海的日本大使馆和总领馆位于同一建筑内,职责也没有明确划分。在上海,他从未直接听说与南京大屠杀有关任何情况。他不阅读《纽约时报》或中国报纸(所以不知道相关报道)。也没有听说过南京外国人抗议信件经上海转寄到东京的情况。1938年1月,去南京任职,同年10月离开。日本南京总领馆有田中正一、福田笃泰和代理总领事福井淳,后来花轮义敬接替了他。日本总领馆有办公区和住宿区,他就住在里面。南京的局势平淡无奇,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商店开门,有不少日本商人。没有大屠杀这样的情况。在南京,他的职责是与外国领事联系和谈判。他不知道拉贝和贝茨。听说过阿利森事件,他会说一些日语,他似乎并不很记恨这一事件。
5. 没有接受当面采访,但书信简短回复者
吉川猛华中方面军参谋。1937年12月,他们司令部进入苏州后,松井召集了负责后勤的参谋二宫和他(负责总务),并严厉训斥他们处理尸体方式,即“得体”地处理了日本方面的尸体,而忽视了中国士兵的尸体。松井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寺田雅雄第十军参谋、中佐。由于淞沪战役陷入僵局,大本营派遣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第十军的战略是迅速推进,因此无法从后方得到补给。这就是他们不得不设法在任何地方获取食物的原因。就纪律问题而言,据说在当地征用粮食是错误的,但他不认为第十军的纪律特别糟糕。在当时,他从未听说过“南京事件”。
仙头俊三第十军参谋(国崎支队)。1937年12月12日,他们到达浦口。他估计长江两岸漂着的敌军尸体有数百具。江中间几乎看不到尸体。他看见下关的江边岸墙附近的水已经变成了红色,尸体的手脚似乎被捆绑着。当时对大屠杀一无所知。就国崎支队而言,不存在纪律的问题。
后藤光藏第十军武官,中佐,随第十军进入南京。南京是一座空城,没有人。他住在一所空房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冈村适三上海派遣军宪兵。当时没有听说过“南京事件”,就军纪而言,他没有从上海派遣军宪兵司令横田昌隆中佐、第十军宪兵司令上砂少佐和副司令藤野鸾丈那里听到任何特别的情况。他听说日本军队的行为傲慢。
屈川武夫同盟通讯社记者。随十六师团进入南京。有关你问的(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他没有看见或是听见任何特别的情况。
藤本龟《朝日新闻》记者。他想告诉你在他随军报道时,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特别的情况。
浅海一男《东京日日新闻》记者。他希望不要加入否定20世纪南京大屠杀的军国主义大合唱中去。
西野源《大阪每日新闻》记者。他是从《大阪每日新闻》在名古屋的支局参军的。随第九师团从中华门进入南京。没有听说你提到的情况(大屠杀),战场上总会有毫无根据的传言,这很常见。
大谷光照西本原寺住持。1937年11月,访问上海,参加南京的入城式。并主持了第二天的悼念仪式。14日晚上,他到达南京,住了4天。没有看到大屠杀,也从没有听到过传言。当时战斗已经完全结束了。南京很平静,也没有市民。没有发生大屠杀的环境。日本军队住在城内外休息。
石川达三作家。1937年,《中央公论》杂志派(他)到南京。12月21日,离开东京,访问了上海、苏州和南京,1938年1月底,返回东京。当他进入南京时,已经是入城式的两个星期后了,没有看到大屠杀的痕迹。两个星期清理数十万具尸体是不可能的。他从未相信过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现在也不信。
三、证言的文本分析
除了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年龄、记忆、个体在时间及空间所具有的局限性(如金子伦助和重村实在南京只待了一天或一晚,对南京没有特别的记忆)等因素外,不少受访者对“大屠杀”概念理解的偏差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上海派遣军特务机关参谋冈田酉次对大屠杀的认知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我认为,‘大屠杀’是将非武装民众聚集在一起,然后射杀或者是类似的情况,没有看到这种情况”。(16)Ara Kenichi, 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ra-Nanjing , g-5, p.13.另外,在短时间里一次屠杀十多万人,也是不少受访者对大屠杀的固有概念。显然,这与我们所定义的南京大屠杀——包括了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等各种暴行,而且是一个持续相当长的过程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实际上,不少受访者的证言正是对大屠杀的片面理解而否认其存在的。在文本分析时,这是一个应该考量的因素。
根据阿罗健一自述,他实际面对面采访了35人,而且在出版前还请他们核对各自陈述的文本,其中有一半人认同了文本内容,有四分之一的人要求改变用词和更正误解,另有四分之一的人要求根据他们的意见重写。因此,相对而言,这35人的采访文本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受访者原意和表达,换言之,阿罗健一不敢或不便明目张胆地篡改采访者的原意,特别是在这些人大部分尚健在的1987年更是这样。但到了2002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既有15年后这些受访者几乎全部不在人世的自然因素,也有采访者思想进一步右倾化的原因,对比这两个版本,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变化。
英文版是根据2002年出版的《“南京事件”日本48人的证言》翻译的,与1987年版相比,这一版删除了同盟社上海支局局长松本重治的证言(17)松本重治证言承认南京发生了大屠杀。,增加了《新爱知新闻》的记者南正义、参谋本部总务课长谏山春树大佐、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编制班大槻章少佐的证言。同时还增加了包括石川达三和浅海一男在内的11位简单回复的内容,这样将证言总数拼凑到48人。
由于删除了松本重治的证言,前面提到的接受面对面采访,并由本人核对过采访文本的人数减至34人。(18)阿罗健一在英文版书的前言里,没有说明新增加的三人的采访文本也经过本人的审核。这样,48人的证言中有34人的采访文本经过本人审核,3人为2002年版增补的,11人拒绝接受面对面采访,只是以书信方式进行了简短的回复。实际上,从英文文本上看,这11人的陈述往往只有寥寥数语,完全没有上下文的语境, 且未经本人的审核,不符合采访者意愿的内容是否被省略或篡改不得而知,操控空间巨大,但我们通过以下个案分析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以石川达三为例,作为由日本中央公论社派遣前往南京采访的特派记者,抵达上海后乘火车于1938年1月15日进入南京。在南京,石川达三对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进行了8天的实地采访,后又在上海对其他日军部队进行了4天补充采访,依据采访内容于当年2月上旬撰写了题为《活着的士兵》的纪实性报告文学。由于描述了侵华日军的活动及暴行,在日本国内被认为是危害皇军威信的作品。《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刊载时,虽然自主删除了描述日军对非武装平民和妇女的杀戮、以及侵华日军官兵在野蛮血腥的战争中的心态等敏感内容,这些内容约占原稿四分之一的篇幅,但是日本内务部还是以“诋毁皇军、扰乱时局”为由,在发行当天查禁了《中央公论》的当期刊物。随后,作者、编辑和发行等三方被以涉嫌违反《新闻报刊法》第41条(扰乱社会秩序)而被公诉。石川达三受到监禁4个月缓刑3年的有罪判决。
在其作品中,石川达三写道:勇敢而温情的西泽中队长“只下了杀尽数千俘虏的决定”,在南京城内的扫荡战中,“看情形终于很难单独处分真正的部分”。(19)秦郁彦教授著,杨文信译:《南京大屠杀真相——日本教授的论述》,(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页。显然,在石川看来,集体屠杀行为绝不是个体士兵的自发行动。战后,石川达三在回答国际检查局的调查询问时明确表示:“我之所以根据在南京发生的事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国家不报道真相”。尽管他没有目睹,但他从日本士兵那里听说了被关在挹江门附近楼房里的中国俘虏被烧死、日军在中山门附近的机场用机关枪屠杀俘虏、在长江堤岸砍杀俘虏等。(20)《石川达三询问调查书》(1946年5月11日),王卫星编:《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0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538页。但在阿罗健一的书中,石川达三的陈述却变成了“没有看到大屠杀的痕迹”,并补充道,“我从没有相信过南京大屠杀的故事”。(21)Ara Kenichi, 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 —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ra-Nanjing , g-9, p.16.这与其作品的内容和问询调查书的陈述自相矛盾,倒是更像是阿罗健一的话语。
另外,同盟通讯社的新井正义、浅井达三和细波孝在采访中对大屠杀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同样是同盟通讯社,并在南京时与其同事在一起的屈川武却在书面回答中说“没有看见或是听见任何特别的情况。”(22)Ara Kenichi, 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ra-Nanjing , g-9, p.14.这也明显地违反常识。
阿罗健一自己也承认由于增加证言的数量,所以删减了之前版本中证言的内容。以佐藤振寿为例,在英文版证言中,佐藤只是简单地提到,“在88师司令部前面看见日本士兵屠杀中国士兵。”但在几乎与《纪闻·南京事件——日本人所看到的南京屠杀事件》同时出版的其回忆录《步行行军》(1987年)中,佐藤振寿却详细描述了屠杀的过程:
到了目的地(88师司令部),那儿有一扇大门,两侧都有步哨,我先照了一张全景。进门一看,里面一座兵营式的房子,房子前面是广场。广场上坐着一百来人。他们被反绑着手,像是被俘虏来的伤病员。他们面前已掘好了两个五平方米大小,深约三米的大坑。
右边坑前的日本兵举着中国军的步枪,让中国兵跪在坑边,枪口抵住后脑,扣动扳机。枪声响起的同时,中国兵如表演杂技一般,一倾身,向着坑底翻落下去,成为一具尸体。左边坑前的日本兵光着上身,举起上刺刀的枪,叫着“下一个”,将坐着的俘虏拖起来,命令他们走到坑前,然后“呀”地大喝一声,猛地将刺刀扎进中国兵的背部,中国兵即刻跌落坑中。偶尔有个中国人在向坑边走的时候会突然转身全力奔跑,试图逃走。察觉不妙的日本兵便迅速将其击毙。开枪的地方距我不足一米,子弹就擦着我的耳边飞过去。那一瞬实在是危险至极。
实行枪杀与刺杀的日本兵们脸部都扭曲着,难以想象他们是正常人。他们似乎极为亢奋,已进入了一种疯狂的境界。在战场上杀敌,是在一种被迫的条件下进行的——不去杀人,就会被人杀。但在杀害手无寸铁、毫无抵抗力的人时,如果不拼命将自己的精神提升到近乎疯狂的状态,恐怕是难以下手的。
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23)佐藤振寿:《步行随军》,王卫星编:《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0册,第 470—471页。
很明显,出现这种叙述差异不大可能是由于佐藤的记忆所造成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对阿罗健一不利的证言细节被其删除了。
根据摘要统计,在1987年版接受面对面采访的35人中,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有12人,(24)包括承认大屠杀的松本重治,在2002版中他的证言被删除。占34%;中间有14人,占40%;否认的为9人占25.7%。也就是说没有否定大屠杀或看到或听说屠杀俘虏或是看到尸体以及其他暴行的占74%。考虑到前文提到的不少受访者对大屠杀的概念存在着认知上的偏差,否则这一百分比会更高。
2002年版增补的以通信方式简短回复的11人(减去一人)中(25)在这11人中,华中方面军参谋吉川猛只提到苏州处理尸体的情况,没有涉及南京,故统计中将其排除。,肯定的为1人,占10%;中间为1人,占10%;否认8人,占80%。而增补的南正义、谏山春树和大槻章三人证言的否认率为100%。
这三组数据的否认率分别是25.7%、80%、100%,也就是说,阿罗健一新增证言的否认率为84.6%,换言之,否认率从1987年版的25.7%,到2002版就增加到了44.6%(英文版的百分比相同)。否认率几乎翻了一倍,对阿罗健一而言,补救的意味十分明显。实际上,这些文本变化的本身就是最好的自供状,耐人寻味。
从受访者职业来看否定的百分比,海军军官最低为0;外交官最高占比为66%;记者和陆军军官相似,分别为33%和36%。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海军是从长江下游抵达下关。一方面海军参与了射杀渡江逃亡的中国士兵,另一方面江边是重要的屠杀现场,存有大量的中国人尸体。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一定会在证言中呈现。
外交官的高否认率显示了口述史的特点——个体经历和活动范围的局限性及易受到价值观和个体好恶的左右。阿罗健一只挑选了三位外交官(其中渡边义雄是一名摄影师,由日本外务省情报局挑选前往南京拍摄照片以供外宣之用)进行了采访,这三位没有一位是1937年12月13日随日军到达南京使馆的外交官员(如田中、福田、福井)。另外两位外交官都是在1938年1月到达南京的,其中岩井英一在南京只待了几天,存在着没有目睹或是听说日军的暴行的可能性。而粕谷孝夫在南京任职了10个月,但他在证言中描述道,“南京的局势平淡无奇,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他还强调“我不阅读《纽约时报》或中国报纸。也没有听说过南京外国人抗议信件经上海转寄到东京的情况。”(26)Ara Kenichi, 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ra-Nanjing , g-10, pp.7-8.这多少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这三人中只有渡边义雄由于摄影师的身份和摄影工作的需要见证到了日军暴行。
另一个原因是不同职业受访者人数差别过大导致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阿罗健一在证人选择和证言取舍上的倾向性。正如前文所引日本学者所言,“他(挑选采访对象)的策略是回避那些会给出暴行证据的人,而选择那些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人”以及后来在发表或出版时“删除对自己不利的证言”。考虑到这些策略和方法,阿罗健一采访目击者和出版这些证言的目的一目了然。之所以早期的版本中会存在着阿罗健一所不愿意看到的内容,很显然,主要是因为受访者要求对书稿进行审核及他们当时仍然健在这些制约因素。
余 论
尽管阿罗健一是带着预设的立场,即希望通过当事人之口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来进行采访以及在采访对象的选择和证言取舍上也存在着倾向的问题,但由于前文提到的制约因素,这些证言并没有如采访者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一边倒的否认大屠杀的情况,而是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因而具有了独特的史料价值。
由于受访者的身份——日本人、在现场,这些证言呈现出了一些其他史料所没有的细节,或者是进一步证实了一些广为流传的史实。如海军从军绘画通讯员住谷磐根回忆:“在下关码头看到20多名日本士兵在砍杀中国士兵,然后将他们推入码头下面的水中。我想打开手电筒,仔细看,但日本士兵警告我会沾到鲜血,我就回去了。第二天我一大早起来去看尸体,有800多具,有些人还在动或发出声音。”(27)Ara Kenichi, 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ra-Nanjing , g-9, p.5.这些细节非在现场的人很难看到,是其他史料中所没有的。
又如外务省情报局的渡边义雄讲述道:“我们到下关时,一名士兵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进行砍头行动,然后将尸体扔到江里,称‘很快江水将变成红色’,并建议我们去观看。但我们没有去看。”如果不是出自身临其境的日本人之口,“江水变红色”一般会当作写意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证言具有其他史料所没有的细节,因而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在这些证言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在否认的证言中多次出现在“战争的情况下,你不杀人,就会被杀”“ 战争时期屠杀不是新闻”“战场中不遵守规则”“没有粮食和地方关押俘虏”“日军没有俘虏的概念”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战争的状态下,杀人放火,屠杀俘虏不是犯罪,因而不存在大屠杀。实际上,这反映了阿罗健一的想法,抑或是其形塑的结果,阿罗健一在2002年版的新后记特别强调“日军在南京只有对军人的‘处刑’而没有对平民的犯罪”。(28)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3页。
换言之,与其他大屠杀“虚构派”一样,他们都使用了各种借口,力图使日军对屠杀放下武器的俘虏合法化和将俘虏的概念模糊化,(29)仅以东中野修道为例,他企图用各种理由,包括战争法来论证中国俘虏不是战俘,进而论证发生在南京的屠杀是合法的。参见Higashinakano Shudo, The Nanking Massacre: Fact Versus Fiction, A Historian’s Quest for Truth, Tokyo: Sekai Shuppan, Inc., 2005, pp 125—148.但是阿罗健一似乎忘记了他采访过的第2联合航空源田实的证言。他以海军的优越感和对陆军的一些不良行为的不屑口吻说道:“就海军而言,这种行为(屠杀俘虏)是违反武士精神的,永远也不会发生。我警告我手下的人不许杀俘虏或是任何不能抵抗的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30)Ara Kenichi, The Nanjing Incident: Japanese Eyewitness Accounts—Testimony from 48 Japanese Who Were There, Ara-Nanjing , g-8, pp.23-24.他强调了屠杀俘虏或任何不能抵抗的人都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其隐含的逻辑是这种行为就是犯罪。包括阿罗健一在内的“虚构派”对此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政治目的而故意设法使其合法化。
耐人寻味的是,英文版中并没有“日军在南京只有对军人的‘处刑’而没有对平民的犯罪”的内容,可见,至少阿罗健一完全知道屠杀俘虏有违国际法和世界主流文明的价值观,不利于他们自己,所以省略了这些内容的英文翻译。毫无疑问,屠杀俘虏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