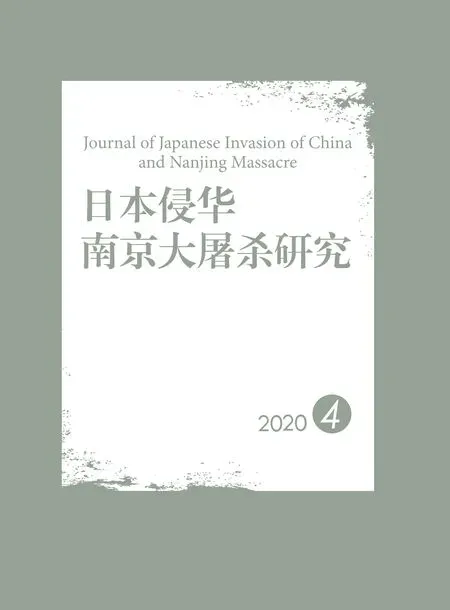个人·家庭·社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中的历史记忆*
马雪萍
1960年代初,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曾编著过《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当时,该小组组长高兴祖老师等访问了部分亲历的幸存者,以获取口述资料。(1)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序言”,第1—2页;吴世民:《关于国内第一本纪述南京大屠杀的书》,《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4期;张生:《“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发生之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逐步展开。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作为“活证据”,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从1984年开始,南京地区曾多次开展调查寻访活动,访问幸存者千余位,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10余部幸存者口述资料,总字数逾百万。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被应用到口述采访实践中,大批幸存者受访的音像资料被保存下来。
在口述采访实践大举进行之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研究也随之展开。论者在口述采访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南京大屠杀对幸存者的影响,研究了幸存者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探讨了幸存者在大屠杀之后如何进行自我修复等问题。(2)郭冠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研究:台湾的四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其记忆的研究》,《“多元视域下的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11月,第210—222页;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许书宏:《恐惧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心路历程》,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也有学者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广岛“原爆”被爆者的口述做了对比研究。(3)杨小平:《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与广岛原子弹爆被爆者的口述史对比研究》,《第三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17年11月。但是,相比于口述采访实践的大规模进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研究并未充分展开,这一课题之下相关论著相对较少。
记忆是口述史研究中的核心议题,正如英国口述史学者Lynn Abrams所言,“记忆如同口述史家的面包与奶油。经由一段口述史访谈联通过去,或者说某些版本的过去,无论在神经学或社会意义上,其经过皆仰仗对记忆的加工”。(4)[英]Lynn Abrams著,汪正晟译:《兼为材料与研究主题的记忆:口述史的变迁》,《口述历史》2016年第14期。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研究中,记忆同样是中心问题。如果广泛阅读幸存者口述文本并重点对比同一幸存者多次受访而形成的多个文本,就会发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交杂着个人记忆、家庭记忆、社群记忆三种记忆成分。
一、个人记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接受口述访谈时,通常最先讲述其个人记忆,即亲身经历并保存在其大脑中的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对这类亲历事件的回忆,构成了他们口述文本的主体内容。然而由于人类记忆的选择性,个人所能记住的只是其生活中发生的部分事件。尽管人类大脑的容量非同寻常,但也只能选择性地记录或保存个人的部分经历。因此,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而言,他们在大屠杀期间的全部经历并非都会被保存在其个人记忆之中。他们能够记得并向访谈者讲述的,同样只是其部分经历。由此值得关注的是,哪些经历会被保存在这些幸存者的个人记忆中?以及为什么是这些经历被保存下来?
每一位幸存者的经历见闻各不相同,其个人记忆的具体内容也迥然有别。但是,在接受口述访谈时,幸存者们所回忆的事件类型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即以他们亲身受害的经历及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为主要内容。
一般而言,幸存者在接受访问时,首先回忆的即是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亲身受害的经历。这类经历通常伴随着身体疼痛或生命威胁,因此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身体疼痛是一种与现存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有关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体验。(5)贺丹军主编:《康复心理学》,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亲身受害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或遭受日军枪击,或被刺伤,或遭殴打,无一例外都承受了严重的身体疼痛。在当时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许多幸存者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与护理,伤口往往要数月或年余才能愈合。更有甚者,部分幸存者因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创伤而留下了终生残疾。对这些幸存者而言,南京大屠杀期间遭受日军侵害的经历是他们永远无法忘却的。
幸存者马金义生于1909年,1937年家住南京铜坊苑五号。大屠杀期间,他在家中被日本兵强行带至三坊巷一处日军驻地内,并被视作“中国兵”而遭到毒打。1984年接受采访时,马金义即重点回忆了这一亲身受害的经历,他讲道:
他们(指日军——引者注)解下我的腰带套在我的颈子上,两个日本兵一头一个,同时用力拉,待我昏死过去时,他们就松一下;等我醒来时,他们又用力拉。就这样一紧一松,使我几次昏死过去。
天快黑时,我苏醒过来,身上盖着一张芦席,躺在电报局后面的花园里,周围到处都是死尸,令人毛骨悚然。不久,有两个日本兵拿着两张芦席走来,向我踢了两脚,一脚正踢在我的左眼上,我忍着疼痛没敢动,他们以为我死了,就转身走了。
天黑了,四周听不到人声,我才慢慢爬到围墙边,墙外通高家巷四圣堂,靠墙的一棵大树下放着一个粪桶,我扶着树站在粪桶上爬上墙头逃了出来。(6)《马金义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99页。
1986年9月18日,马金义再度接受了军旅作家徐志耕的采访。在这次访谈中,他主要讲述的仍是上述死里逃生的经历:
日军……用裤带在我脖子上绕了一圈,一人抓住一头,勒得我喘不过气,就啥也不晓得了。
到了下午,太阳偏西了,耳朵嗡嗡响,人醒过来了,只见身上盖着芦席。朝四周一看,尽是死尸!横七竖八像山一样地堆着。这时天还没黑,我想:怎么办呢?不跑没得命了,跑也没得命。来了两三个鬼子,一下掀开我身上的芦席,我闭上眼,憋住气。突然,一个鬼子飞起一脚,踢在我的脸上!只觉一阵钻心的疼痛,眼冒金星。我咬着牙,一动不动。“没气了。”鬼子说完,就走了。我慢慢睁开眼,面前一片模糊,只见前面有一片灯光。我吐掉了嘴里的血,心想,不逃肯定死路一条。要跑,一定要跑!我翻转身,脸朝下,一点点向围墙边爬,旁边都是尸体。到了墙边朝上一看,围墙很高,手够不着。墙上插着碎玻璃。幸亏边上有棵大树。我咬着牙齿硬撑着站起来,想爬树,但爬不上去。忽然发现墙边有两个粪桶,我把粪桶翻过来底朝天,站上去后双手扒住墙头,使劲一窜,窜上墙头后连滚带跳地翻出了围墙。(7)《马金义》,徐志耕整理:《幸存者说——南京大屠杀亲历者采访记》,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徐志耕是著名军旅作家,为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一书,1986年8月至11月,他穿街过巷,四处奔波,采访过80余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考虑到口述文本整理者对口述稿的修饰后,对比以上两版口述文本,不难发现,两次所述的基本经过相差无几,细节处也大体能相互印证,反映出这段经历在马金义脑中印象深刻。日军一脚踢在马金义的左眼上,导致他的左眼失明。彼时,马金义尚不满30岁,正值少壮之年,但其余生却都要在一眼失明的痛苦中度过。在这种延续性创伤的刺激下,幸存者很难忘记南京大屠杀期间遭受日军迫害的经历。当他们接受口述采访、回忆南京大屠杀惨案时,这部分经历自然成为最先讲述且记得最为准确的内容。
除去亲身受害的经历之外,幸存者在大屠杀期间目睹的日军暴行也因其恐怖性与残酷性而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构成了幸存者个人记忆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此外,日军肆意屠杀之后,遇难者尸体遍布南京城内外各处,不少幸存者都曾目睹死尸枕藉的惨景,这也成为他们受访时较常讲述的内容之一。
在现存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文本中,见证日军屠杀暴行的案例俯拾皆是。在这种情景中,遭遇生命威胁的虽非幸存者本人,但直接面对近在咫尺的屠杀与死亡,这种恐怖的体验也足以让他(她)们终生难忘。
幸存者陈家寿在1999年受访时曾回忆过自己目睹的一次屠杀事件:
正搬着货物,有个姓谢的门卫听到卡车声,从门卫小屋里伸出头来。卡车上的日本兵盘问了他,叫卡车停下,把姓谢的捆了起来。日本兵硬说姓谢的是中国兵,叫他跪在那个地方,其中一个人拔出军刀,对准姓谢的头猛地砍了下去。可怜姓谢的被砍了后脖子,朝前倒下。别的日本兵用军靴把姓谢的身体踢起来,让他脸朝着天。姓谢的好像还有口气。看到他不动了,日本兵若无其事地离开了那里。(8)[日]松冈环著,沈维藩译:《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陈家寿亲眼所见的上述惨景无疑给他造成了强烈的刺激,这一事件被稳固地保存在其个人记忆之中。2002年,时隔三年后,在另一次口述采访中,他再度对访谈者讲述了这一经历: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惨景:有一天干完活回来,走到长山公园门口,一个姓谢的门卫听到有卡车声音,就探出头来看了一眼,正巧让车上的日本兵发现,他们立即跳下车把老谢绑了出来,让他跪在地上,其中一人抽出军刀,恶狠狠地向他头上砍去。可怜老谢脖子后面被砍断了,前面还连着一些皮肉,趴在地上的时候还未完全断气,日本人又抬起皮靴,把他踢得翻了个个儿,然后扬长而去。这位姓谢的人就这样活活地被砍死了。(9)《陈家寿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陈家寿亲眼目睹了日军砍断谢姓门卫的脖子,又将其尸身“踢得翻了个个儿”,之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日军残暴无理,屠杀手段极其残忍,中国平民命如草芥,凡此种种,都让陈家寿对这一情景印象深刻。由此,该事件也成为他的个人记忆中的重要内容,在两次接受采访时,他都曾回忆并讲述了这一事件。
幸存者余昌祥也曾回忆过他亲眼所见的日军屠杀中国士兵的情景,他讲道:
当时我在门缝里看,不敢出去。2号(指门牌号——引者注)里面住着四个中央军,来了两个日本人,他们跑进去,一个人一手拖一个,四个人就被拖出来了,鬼子用刺刀往人脖子处捅进去,再一搅,血就一喷。正好我在门缝里看到了,吓得我跑掉了。(10)《余昌祥口述自传》,张建军、张生主编:《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余昌祥曾多次接受口述访谈,几乎每一次采访中他都会讲述这一事件。日军在他眼前屠杀“中央军”“刺刀往人脖子处捅进去,再一搅”,这“一捅”“一搅”的动作给他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使得他终生难以忘记这恐怖的一幕。
强奸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的另一灭绝人性的罪行。对日军强奸暴行的记载广泛散见于各类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之中。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见证日军性暴行的人亦为数甚多。幸存者彭善荣曾回忆道:“当时日军强奸不是什么稀罕事,大家都经常看到听到。”(11)《妇女藏身的房子里被强奸,在别的日子里也曾被迫观看轮奸》,[日]松冈环著,沈维藩译:《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第290页。
彭善荣在1999年—2002年间,曾多次接受口述采访,并留有三个口述文本。(12)彭善荣的三个口述文本分别见于:《妇女藏身的房子里被强奸,在别的日子里也曾被迫观看轮奸》,[日]松冈环著,沈维藩译:《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第287—290页;《彭善荣口述》,张连红、戴袁支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中)》,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6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525页;《彭善荣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第477—479页。在这三个口述文本中,他除了回忆自己被日军刺伤及被抓差的经历之外,还讲述了他目睹的几次日军强奸妇女的情景。
南京大屠杀期间,彭善荣曾躲进安全区避难,亲眼见到日军强奸妇女。在接受日本学者松冈环采访时,他回忆道:
两天后,另一个日本兵扛着上刺刀的步枪来了,在他问“有女人吗”的时候,和我一样住在房间里的熟人的太太突然露出脸来,结果被发现了。日本兵把我们全都赶到外面,锁上门,强奸了她。十分钟后,日本兵系着皮带出来了。那个太太害怕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13)《妇女藏身的房子里被强奸,在别的日子里也曾被迫观看轮奸》,[日]松冈环著,沈维藩译:《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第288—289页。
上述情景为彭善荣亲眼所见,被强奸的又是熟人的妻子,因此他对此事印象深刻。当他接受访谈,回顾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时,这一事件即会被忆起并讲述。2000年,在接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采访时,彭善荣亦曾回忆了这一经历:
一天,一个日本兵来找“花姑娘”,我们说没有,碰巧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出来,被那个日本兵看见,他便将我们几个人赶出房间,关上门将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强奸了,当时她哭得很伤心,我们都劝她。(14)《彭善荣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第478页。
大屠杀期间,彭善荣曾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日军强奸妇女。1999年及2002年,在他接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访问时,他还回忆了目睹的另一次强奸事件:
一次我去水西门的菜园拔菜,在水西门看到一个姑娘被日本兵强奸。有的姑娘躲在棺材里,日本兵都能找到。(15)《彭善荣口述》,张连红、戴袁支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中),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6册,第524页。
在2000年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采访中,彭善荣也回忆了这一事件:
城里面没菜吃,一天,我与几个人一起到水西门外找菜,被日本兵抓住,威逼我们与他们一起去找“花姑娘”,一个女的躲在一个棺材旁边,被他们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轮奸了那个妇女,日本兵还不让我们走,逼我们在一边看。(16)《彭善荣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第479页。
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甚至还逼迫彭善荣等人在现场观看,此举不仅伤害了那位妇女,更是对在场的中国男性同胞的羞辱,这种交杂着恐惧、难堪、屈辱的体验对彭善荣而言无疑是颇为难忘的。
除此之外,日军大规模屠杀后,遇难者尸体遍布各处的惨景亦是幸存者个人记忆中的重要内容。绝大多数幸存者都曾在其口述中提到过目睹遇难者尸体的情景。生活在战争年代的人们经常面对死亡与尸体,但是,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者尸体数量之巨,分布之广,死状之惨烈,完全超出了人类想象的极限,这种强烈的感官刺激显然让幸存者记忆深刻。
幸存者沈锡恩曾参与过“南京回教掩埋队”(17)南京大屠杀期间成立的宗教慈善团体,专门负责掩埋被日军杀害的回族同胞的尸体。的工作。由于掩埋队必须往来于南京城各处找寻回族遇难者的尸体,沈锡恩因此得以看到城内尸山血海的惨景。其中,九华山下、乌龙潭内,弃尸甚多,堆叠情形格外惨不忍睹,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1983年底,在接受日本记者本多胜一采访时,时年76岁的沈锡恩回忆说:
九华山脚下。在现在的煤气公司所在地,有一个围绕山丘的半月形大坑。这个坑宽五丈、长八丈(一丈约三米三十厘米),坑里尸体满满的,坑有多深不知道。尸体的样子很惨,有的头没有了,有的还被绑着手脚,周围弥漫着强烈的臭气,因为尸体已开始腐烂……
乌龙潭。乌龙潭是个水塘,在汉中门的龙盘里,宽二十米、长三十米左右。……那时这个水塘完全被堆积的尸体填满,尸体就像泡在红色液体里的腌菜一样。(18)[日]本多胜一著,刘春明等译:《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龙盘里”为“龙蟠里”之误。
这种惨烈的情状,他人即使只阅读文字,也深感触目惊心。而沈锡恩亲眼目睹此景,无疑更是终生难忘。1984年、1986年时,沈锡恩还曾接受过另外两次访谈,并留有两个口述文本。在这两次采访中,他都曾讲到了九华山下、乌龙潭内遍布尸体的情形。(19)《沈锡恩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第429页;《沈锡恩》,徐志耕整理:《幸存者说——南京大屠杀亲历者采访记》,第19页。
南京沦陷前夕,幸存者秦杰与家人从上新河镇逃到了放生祠难民营(20)秦杰所言位于三汊河附近的“放生祠难民营”应指“慈幼院难民收容所”。南京佛教慈幼院位于南京汉西门外三汊河法云寺,寺内建有放生池,原为一“念佛放生道场”,因此被难民称作“放生祠难民营”。。南京沦陷后,他们一家又从放生祠难民营回到上新河镇。1990年代初,秦杰曾提到过他在回程中看到尸体的惨景,他回忆道:
沿途还看到已被日军烧成焦黑色跪地姿势的尸体、江东桥已断,河水很浅,河底用尸体垫成一条路,上铺门板,我们都是从这上面走过的。门板两边,一边看到是头,另一边看到的是脚。在江东门河边,还看到一具女尸,光着全身,已被河水泡得浮肿起来,乌鸦就停在尸体的脸上啄食眼球,一路景象惨不忍睹……(21)《秦杰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第296页。
“焦黑色跪地姿势的尸体”,江东门的尸体桥,光着全身、被乌鸦啄食眼球的女尸,这些惨象无论何人看过恐怕都终生难以忘记。尽管幸存者们在已经见惯了屠杀、尸体、鲜血,但是这样强烈的感官刺激显然让他们记忆深刻。
如前所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亲身受害的经历,亲眼所见的日军屠杀、强奸暴行及遇难者尸体是其个人记忆中的重要内容。诚然,幸存者在其间的经历见闻并不仅止于此。但是,多年之后,当他们接受访问并回忆南京大屠杀的情形时,上述事件成为他们个人记忆中最为鲜活、生动的内容。那么,为什么是这些经历被记录与储存在幸存者的大脑中?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对幸存者而言,不论是亲身受害,抑或是亲眼目睹日军屠杀、强奸暴行及遇难者尸体,他们在经历这些事件时通常伴随着极端强烈的恐惧、无助、绝望等情绪。而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认为,情绪对记忆的编码和提取都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个体经历的具有高度情绪唤醒水平的事件更容易被长久地记住。这些具有高度情绪唤醒水平的记忆,“即便是在很久之后被回忆仍然可以产生‘身临其境’,‘恍若昨日’的感觉”(22)尹璐、毛利华、冯胜闯、叶香、史煜才:《自传体记忆系统及其神经机制》,《心理学进展》2013年第4期。。幸存者之所以对上述事件记忆深刻,与他们经历这些事件时的高强度情绪体验密切相关。这种伴随着强烈恐惧情绪的经历,一般能够绕开生物学常规限制而直接进入个人长时记忆,牢固地保存在幸存者的大脑中。(23)[美]埃里克·坎德尔著,喻柏雅译:《追寻记忆的痕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82页。
二、家庭记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个人记忆是其口述的主体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幸存者受访时所讲的内容并非全部来自其个人记忆。如前所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中交杂着个人记忆、家庭记忆、社群记忆三种记忆成分,除个人记忆之外,幸存者还讲述了其家庭记忆及社群记忆中保存的内容。
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也是最普遍的一种社会群体类型。“家庭伴随人类的起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一种群体形式,对家庭记忆的保存与传承一直是人类重要的使命。”(24)郭德泽:《大众传媒对家庭记忆的社会表述与意义重构——以央视〈客从何处来〉节目为例》,《新闻界》2014年第17期。纵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家庭记忆在其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幸存者在接受采访时,除了回忆个人在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之外,还会讲述其家庭记忆中保存的有关内容。
家庭记忆的形成与家庭内部的沟通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国学者安哥拉·开普勒(Angela Keppler)、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inzer)等人的相关研究表明,家庭中的回忆性沟通对家庭记忆的建构至关重要。(25)安哥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家庭)历史的沟通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在谈话中共同制作过去》,[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121页。以讲故事的形式进行回忆性谈话的这种沟通实践是所有家庭史和家庭记忆的基础。(26)刘研:《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树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4页。幸存者及其家庭成员通过不断的对话沟通交换着彼此的个人记忆,进而建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家庭记忆。这种家庭记忆一经建构,即由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并通过代际传递机制由家庭的下一代继承。
幸存者路洪才生于1933年。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之前,路洪才的父亲带着他和十五六岁的大舅舅逃出南京城避难,奶奶留在家中看守两间草房,外公、外婆、怀孕的母亲、两个小舅舅、妹妹在家中挖的地洞里躲避日军。南京沦陷后,日军闯入路洪才家中,枪杀了躲在地洞中的6位亲人。逃难在外的3人获悉家中惨剧之后,赶回南京城,从幸存的奶奶那里得知了6位亲人遇害的经过。路洪才回忆道:
当时我奶奶看着两间房子,日本人来了以后看见我奶奶,就问——大致意思是——你们家这么大房子,怎么没有人,人都到哪里去了?我奶奶又不会说,又回答不了。他就一把火把房子烧掉了。烧掉了以后就到外边找,一看有一个土堆,这个土堆跟平常的土堆不一样,上面都是新土,也没有多少草,这明明是一个藏人的地方,就把盖子掀开。掀开以后,大人小孩在里面哭着、喊着、叫着,在里面一塌糊涂。日本人就喊他们出来,谁敢出来啊。日本人来气了,就开枪。这里面六个人,等于七条生命,就打死了。为什么说是七条生命?因为我母亲大着肚子,快临产了,走不动路。(27)《路洪才口述自传》,张建军、张生主编:《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第227—228页。
从1982年开始,路洪才即作为南京大屠杀见证人多次接受采访,控诉日军暴行。他的口述中较少提到大屠杀期间的其他见闻,6位亲人被日军残忍杀害一事始终是他口述中的核心内容。奶奶亲眼目睹了家中6位亲人惨死的经过,之后将具体情形告知了父亲、大舅舅、路洪才3人,在这一过程中,奶奶的个人记忆转化为路洪才家的家庭记忆,由全体家庭成员共享。
一般而言,家庭记忆的内容是非常丰富驳杂的。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特殊事件如婚丧嫁娶,家庭成员的脾气秉性、经历遭际,家庭内部的思想观念等,都可以成为家庭记忆所保存的内容。而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家庭成员的死亡、受伤以及家庭成员见证的日军暴行通常是家庭记忆的主要内容。
对个体家庭而言,家庭成员的死亡通常是家庭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任意屠戮,无数家庭遭遇惨祸。父母姊妹等亲人被杀,给幸存的其他家庭成员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痛,因此也成为幸存者讲述的家庭记忆中的重要内容。
幸存者陈德寿生于1932年,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日军在城内四处放火,陈德寿家居住的古钵营一带亦被焚烧,他的父亲和邻居在赶去救火时被日军抓走。父亲被抓的当天,一个日本兵闯进陈德寿家中,企图强奸陈德寿的姑妈,姑妈不从,被日军刺了6刀,最终伤重而死。陈德寿曾回忆道:
……一个鬼子拿着一支长枪来到我家……要“花姑娘”,到处找。当时,姑妈抱着两岁的小表妹,手搀着四岁的小表弟,鬼子见了就要拖她,她是个有文化的人,死活不从,她把小表妹放下,让奶奶抱着,她与鬼子推推搡搡从房子的第三进推到第二进。鬼子恼羞成怒,在枪上装上刺刀,对她就是一刀,连续刺了6刀,然后扬长而去。
姑妈倒在地上,由于流血过多,她说心里难受要喝糖水,奶奶刚从后面房子里端水过来,她就没气了。(28)《陈德寿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第155—156页。
除姑妈被杀外,陈德寿的父亲被日军抓走之后,也被杀害。与父亲一同被抓的邻居在逃回之后向陈德寿一家讲述了其父被杀的经过,陈德寿在其口述中也完整转述了邻居所讲的父亲被杀的情形:
我们街坊的皮匠告诉我祖父,说我父亲被鬼子杀了。那天,我父亲被抓后,鬼子要他跟着走,我父亲说家中有老有小不能走,另两个被抓的人也不愿意,那两个人一个被刺死,一个被砍头,我父亲也被戳死了,刺刀是从太阳穴心刺进去的,胸口也被刺了一刀。(29)《陈德寿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第156页。
20世纪90年代后,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德寿曾接受过多次口述采访,仅笔者搜求所得即有四个口述文本留存。(30)陈德寿的四次口述文本分别见于《看到婶子因抗拒强奸而被刺死》,[日]松冈环著,沈维藩译:《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第239—242页;《陈德寿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第155—157页;《父亲、姑妈被日军用刀刺死》,李晓方:《13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4页;《陈德寿口述自传》,张建军、张生主编:《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第2—10页。对比这四个文本,可以看到,父亲和姑妈之死作为重要的家庭记忆,在历次访谈中都被着重讲述。对于陈德寿而言,这只是灾难的开始,由于家中主要劳动力丧失,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困苦不堪。1940年,陈德寿的妹妹和祖母先后染病去世。为筹钱安葬祖母和妹妹,陈德寿的母亲被迫改嫁。之后为减轻家庭负担,祖父不得不将姑妈的一儿一女分别送到孤儿院与亲戚家,后来表弟、表妹也都相继死去。原本的八口之家,最终只剩下祖父与陈德寿相依为命。父亲和姑妈之死在带给陈德寿无尽精神创伤的同时,也几乎改写了他的人生。这种延续一生的创痛使得他对悲剧的开端——亲人死亡的记忆更为刻骨铭心。
除家庭成员的死亡之外,家庭成员受伤的经历亦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庭记忆中的重要内容。在家庭内部的沟通交流中,受伤而未死的家庭成员讲述自己遭受日军侵害的经过,由此,其个人记忆成为家庭记忆中的一部分。
南京大屠杀期间,幸存者余昌祥与家人躲在一座防空洞中避难。他的舅父余必文认为男人留在外面不会有危险,因此不愿躲入防空洞内,结果被日军刺成重伤。余昌祥在其口述中详细地讲述了舅父受伤的经过:
我的舅父被他(指日军——引者)捅了七刀,打了两枪,肠子都出来了,腰间腿上都戳。戳了之后,日本人看到他好像还在动,就补了两枪,一枪打的手心,他一挡,就打穿了。第二枪把牙打脱落了,没打到脑袋瓜子,还算不错,但还是打昏过去了,他认为自己死了。到夜晚的时候,流血流多了,嘴也干,想要喝水,到处找水没有,最后摸啊摸地回到家里面。我家离粮行大概不超过两百米,绕一个小巷子就过去了,但就这点路,他爬回家,爬了两个小时。没有什么水,就用淘米的那种小缸,过去住过中央军的每家都有,弄点淘米水喝。喝好以后进门,就跑到房里的床头底下,过去床都有帐子,躲在里头,一直躲到第二天早上。他肚子饿了,又想吃饭,肚肠子流到外面,又没办法了,又爬到地洞里面喊开门。(31)《余昌祥口述自传》,张建军、张生主编:《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第91页。
舅父受伤之际,余昌祥并不在现场,上述对其受伤经过的详细回忆显然是来自舅父本人的讲述。经由舅父的讲述,这段经历为所有家庭成员知悉,并由舅父的个人创伤记忆转变为家庭创伤记忆。
家庭成员的死亡及受伤给个体家庭带来了深重的创伤,因此被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所铭记。除此之外,其他家庭成员见证的日军暴行也在家庭内部的日常交流中被不断谈及,因此亦被保存在家庭记忆中。南京大屠杀期间,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并非时时刻刻都在一起活动,因此他们所目睹的日军暴行也各有差异。在家庭内部的沟通实践中,不同家庭成员交换着彼此在大屠杀期间的见闻。通过这种沟通交流,不同家庭成员直接见证的日军暴行通过幸存者口述向家庭外部成员展现出来。
南京大屠杀期间,幸存者马惠玲与母亲躲在金陵女子大学,她的父亲与弟弟在鼓楼五条巷中避难。马惠玲曾在其口述中讲到弟弟目睹的日军集体屠杀:
和父亲在一起,比我们早回到家的弟弟,在五条巷看到了大屠杀。家的后面有个大水池,他说看到日军把大批中国人捆着双手,让他们站在池边,机枪声“哒哒哒哒哒”的接连不断地响起,把他们打死了。他说有非常多的人,被打中的中国人一个个倒进池子里,剩下的人也被日本兵扔进了池子里。第二年三四月份从难民区回家时,我也见到了这个水池,但尸体已经被收拾了。母亲比我早一步离开难民区,她说那时大批尸体还是照原样在水池中漂着。(32)[日]松冈环著,沈维藩译:《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第131页。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弟弟目睹了日军集体屠杀的情景,母亲看到了漂浮在池中的尸体。马惠玲从难民区回家之后,只看到了水池,但她从弟弟和母亲的讲述中知道了水池边曾发生过集体屠杀,以及池边曾经漂浮着大量尸体。经由家庭内部的沟通交流,弟弟和母亲的个人记忆转化为家庭集体记忆,“水池边的集体屠杀”也成为马惠玲家庭所特有的南京大屠杀记忆。
在绝大多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家庭记忆都是重要的记忆成分之一,幸存者与其家庭成员是在“谈话中共同制作过去”(33)[德]哈拉尔德·韦尔策:《在谈话中共同制作过去》,[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105页。,经由家庭内部的沟通实践,不同家庭成员的个人记忆汇聚成为家庭的集体记忆。一般而言,家庭记忆的内容是纷繁芜杂的。但是在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时空中,不同的家庭共同面临着日军无差别的暴行,因此多数幸存者的家庭记忆表现出相同的结构,即以家庭成员的死亡、受伤以及家庭成员见证的日军暴行为主要内容。
三、社群记忆
一般而言,社群(community)是指“特定的人们基于一定的情感、习惯和记忆,以及血缘、地域和心理而形成,从而拥有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或共同信仰、价值目标、规范体系、关系稳定而持久的实体(或社会有机体)”。(34)敖素:《同一还是差异——社群主义的“社群”与传统儒家的“群体”之比较》,《人文世界》2011年第4期。在中文语境中,家庭、邻里、村落、城市等都属于社群形式。正如家庭内部成员在沟通交流中建构家庭记忆一样,邻里、村落、城市内部也在其成员的互动交往中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社群记忆。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逐步平息后,在幸存的民众中间,这场浩劫成了最重要的话题。幸存者姜永和在其口述中回忆道:“世面安定之后,只要碰到人,讲的都是那个人被强奸后自杀了、那个人被杀了之类的话。”(35)[日]松冈环著,沈维藩译:《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第181页。杨秀英也讲到她从难民区回到家中之后,“从邻居那里经常听到日军屠杀的事情”;(36)[日]松冈环著,沈维藩译:《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第153页。幸存者胡伟在回忆了大屠杀期间目睹的日军暴行之外,补充说道:“我自己直接见到的就是这些,但关于日军的暴行,我从熟人那里听到过很多。”(37)[日]松冈环著,沈维藩译:《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第233页。正是在这种邻里、熟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中,个人及个体家庭的遭遇为社群内其他成员所熟知,幸存者的个人记忆、家庭记忆在社群成员中传递,进而成为社群共享的记忆。而幸存者在接受口述访谈、回忆南京大屠杀时,除了讲述其个人记忆、家庭记忆之外,还会提及这些在社群中传递的记忆。
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城区幸存者与农村地区幸存者讲述的社群记忆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相较而言,在城区幸存者口述中,社群记忆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多数城区幸存者多是在讲述了个人记忆及家庭记忆之后,简略提及曾听说过的左邻右舍受害的经历。以幸存者石秀英为例,日军攻占南京之前,石秀英一家逃往安全区避难。南京沦陷后,石秀英的父亲在安全区被日军抓走杀害;她的哥哥也在去“茶炉子”(38)“茶炉子”,南京人又称为“老虎灶”,指的是卖开水的店铺。买水的途中被日军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因此在石秀英的口述中,父亲和哥哥的遭遇自然被着重讲述。除此之外,她也简单讲述了后来听说的邻里成员受害的情形。在安全区躲避了数月之后,石秀英与母亲、弟弟等人回到了七家湾的家中。在口述中,她也讲到了回家后了解的邻居们的遭遇:
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前面的半间房子……后面住着一个姓李的小姑娘。当时,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家里赶快给她订了婚,结了婚,结果还没有一个月,她的丈夫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
像附近的阿訇家的媳妇就被日本人糟蹋了,后来就死了。过去在草桥,一拐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道。有的人被日本人发现了,就钻到地道里头,里面都是日本人进城之前没跑掉的人。结果日本人把门一堵,他们想跑都跑不掉了。当时,地道里面还有一个姓马的,是挎着点心篮子做小生意的,他老婆正怀着小孩。日本人进地道以后一发现,就把她戳死了。(39)《石秀英口述自传》,张建军、张生主编:《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第211—212页。
日军暴行肆虐时,石秀英一家躲在安全区,上述邻里受害的情形是回到七家湾后才听说的。李姓小姑娘的丈夫被抓走、附近阿訇家的媳妇被强奸以及地道中发生的惨剧都可是七家湾社群中流通的集体记忆,身在这一社群中的石秀英也分享着这部分记忆。在受访时,以上来自社群记忆的内容亦会被讲述。
相比于城区幸存者,农村地区的幸存者口述中,社群记忆是更为重要的记忆成分。农村地区的幸存者“从父母嘴里一遍一遍地听说过村里发生的种种往事,形成了自己的记忆”(40)费仲兴:《城东生死劫》,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7页。。对他们而言,世居的村庄类似于一个扩大的家庭,村庄内每一位成员在大屠杀期间的遭遇都作为社群集体记忆为多数村民所熟知。在口述过程中,几乎每一位农村幸存者都频繁地使用“我们村”这样具有凝聚力的代词来讲述村庄的集体记忆。长期从事南京东郊汤山地区大屠杀幸存者寻访工作的费仲兴教授曾指出:“农村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弱,老人长期定居在一个村子。通常找三四个老人,就能把一个村屠杀的情况摸清楚。”(41)《“把同胞受的苦还原出来,我就这点能耐”》,《新京报》2014年12月13日,第A06版。访谈村庄内的三四位老人,即可摸清整个村庄遭受日军暴行的情况,正说明了在访谈中,多数老人并非只回忆个人及家庭在大屠杀期间的遭遇,而是会讲述整个村庄有关的集体记忆。
西岗头是现属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作厂社区的一个自然村。1937年时,该村共有村民42户。该年12月7日,日军第十六师团进驻汤山炮校。此后,位于汤山炮校东北1.5公里的西岗头村经常受到日军侵扰,村中房屋先后三次被烧,大部沦为废墟。该村村民在日军打来之前,纷纷弃家“跑反”(42)旧时指为躲避战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1938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九),“跑反”在外的部分村民回村搬粮,恰逢日军进村,日军以诱骗的方式将村民带至村内社堂小学,其中22位年轻人被逼令跪成两排,之后开枪扫射。22人中有2人为外地人,除村民陈万有死里逃生外,其余全部被杀。该村除19人被集体屠杀之外,还有16人在“跑反”期间被日军枪杀及迫害致死。
陈广顺是西岗头村的一位村民,当时14岁。日军在西岗头村社堂小学集体屠杀村民时,陈广顺亦被带至屠杀现场,但日军只是强令其观看,并没有杀他。因此,陈广顺见证了此次屠杀的全过程。此外,陈广顺的三哥陈广寿当时也躲在村内家中,听到社堂小学传来枪声之后,在惊惶中逃往村外山上,但不幸被日军发现并射杀,陈广顺同样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
2003年8月,陈广顺接受南京炮兵学院费仲兴教授的访谈,讲述了他关于1937年冬至1938年春的“跑反”记忆。从口述文本来看,陈广顺始终是自发地将自己视作西岗头村的一员,他所讲述的不只是其个人记忆及家庭记忆,而是整个西岗头村关于“跑反”的集体记忆。
陈广顺首先讲到了日军占领汤山炮校后,在各村大肆放火的情形。“日军占领炮校后,就派兵到各村点火烧房,见人就杀……我们西岗头先后被烧了三次,绝大部分房屋都被烧光了,只剩下一些断墙残壁和烧焦的梁、柱”。(43)《陈广顺口述》,费仲兴、张连红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下),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5页。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南京城内大肆放火焚烧,许多市民住所被毁,城区幸存者在回忆时通常只会提及个体家庭房屋被烧及财产损失的情况。而在陈广顺的口述中,面对村庄外部的成员——采访者费仲兴教授时,他对日军纵火焚烧情形的描述并非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而是以讲述村史的方式回忆“我们西岗头”受害的情况。这种讲述方式并非只出现在陈广顺的口述中,西岗头的另一位村民陈万堂在受访时,同样并未提及个体家庭的受害,而是回忆了日军纵火给整个村庄带来的灾难,“村上的房屋,有一大半被烧光了,都是有钱人家的好房子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哭啊、喊啊,谁会想到呢”。(44)《陈万堂口述》,费仲兴、张连红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下),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册,第1099页。
陈广顺亲眼目睹了日军在西岗头社堂小学集体屠杀村民,因此,此次屠杀事件也成为他口述中最重要的内容。在口述过程中,陈广顺详细讲述了此次屠杀的全过程,并为访谈者列示了20余位被杀的西岗头村村民的名字。屠杀发生之时,陈广顺尚属少年,他是否能在当时即列出被杀村民的姓名不免存疑。依笔者浅见,这份名单更可能是屠杀发生之后,在西岗头村村民内部的沟通交流中被确认下来的。因此,陈广顺向采访者列出的名单未必是调取自其个人记忆,而更可能是对村庄集体记忆的转述。
对一个仅有42户人家的自然村来说,20余位村民同时被杀,无疑是影响较深的重大事件。因此,该事件也成为西岗头村重要的村庄记忆,并为村庄内部成员共享。在村民陈万堂的口述中,社堂小学的集体屠杀也是最核心的内容,除了讲述这次屠杀事件之外,他并未提及“跑反”期间的其他经历。同时,陈万堂的口述还提示了此次屠杀事件是如何被建构为村庄集体记忆的。陈万堂讲道:
两个鬼子,一人扛一挺机枪,说是要拉网捞鱼,让人去喊。躲在北面小树林里的小伙子以为没事,就出来了。23个人,在社堂前小学里集合,排成两排。鬼子叫他们跪下,他们就跪下了。后来鬼子用机枪一枪一枪地打,把他们打死了。只有一个人死里逃生,叫陈万有。鬼子打第一枪,前排的人倒下,他也趁势倒下,人家的血流到他身上,他就昏过去了,中间动了一下。日本人上去补刺了几刀,都没刺中要害。鬼子走了,他才从死人堆里逃出来。这段经过啊,他给村上人不知讲过多少遍。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45)《陈万堂口述》,费仲兴、张连红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下),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册,第1098—1099页。
正如陈万堂所言,在西岗头村关于社堂小学集体屠杀的社群记忆建构的过程中,亲历者陈万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陈万有一遍一遍地重复讲述中,社堂小学集体屠杀的经过为村民所共知,成为西岗头村关于“跑反”的重要社群记忆。
除了回忆目睹的日军在社堂小学的集体屠杀之外,陈广顺还向访谈者简述了西岗头村其他几位村民的遭遇,限于篇幅,此处只部分引录:
除了上面讲的这些以外,我们西岗头还有好多人在别处被鬼子打死。
裔建和:“跑反”时在宝华山南面的东葛庵被鬼子一刀砍死,死时约50岁。
陈小四子:我的家门侄儿。刚“跑反”时,他就和他妹妹逃到句容练城。他在那里被鬼子一枪打死,死时约17岁。
陈治富:“跑反”期间,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家门前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日本人叫他下塘敲冰摸鱼,他没下去,被一枪打死,地点就在我家墙角处。他是个极其老实的人,死时约60岁。
陈广发:鬼子刚来时,他想躲到地主家牛舍的大门上头去,因没有梯子,没爬上去。鬼子发现后,在牛舍拐角处用刺刀把他戳死了。死时有四十来岁。
刘贤春:60岁左右。他在自家大门口走路,因耳聋,未听到日本人喊,仍自管自地走,就被鬼子一枪打死。(46)《陈广顺口述》,费仲兴、张连红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下),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册,第1107—1108页。
如上所述,裔建和、陈小四子、陈治富等人遇害之时,陈广顺并不在现场。但是作为村庄的一员,他在村庄内部的沟通交流中了解了以上几位村民的遭遇,并自然地将其视作西岗头村历史的一部分。当他面对村庄外部的访问者时,以上来自社群记忆的内容也理所当然地被讲述。
裔文钊是费仲兴教授在西岗头村采访的另一位幸存者。1937年“跑反”时,裔文钊6岁。当时为安全起见,裔文钊一家十余口人分奔三地避难,他与爷爷、奶奶一起躲藏在宝华山南的东葛庵中。南京沦陷后不久,日军来此地搜查,逼问“中国兵”的去向无果后,杀害了裔文钊的爷爷裔建和等数人。此外,裔文钊的两位叔叔也在社堂小学集体屠杀中被日军杀害。1946年,裔文钊离开了西岗头村,此后他辗转在南京市区、乌鲁木齐、阿克苏等地工作,直到1990年代才回到南京市定居。尽管裔文钊从15岁起就离村外出,此后一直不在村中长期居住,但是他依然维持着对西岗头村强烈的社群认同。在他的口述中,“我们西岗头”的表述不时出现,他所讲述的,同样是整个西岗头村在“跑反”期间的遭遇。裔文钊并未亲历社堂小学的集体屠杀,但是经由村庄内部的沟通交流,他也熟知这一事件,并在其口述中向访谈者讲述了概况。同时,他并不将自己视作这一事件的“局外人”,相反,他一直致力于调查日军在西岗头村的暴行,并曾表示:“我还打算在西岗头国民小学旧址前再竖一块碑,纪念遇害的23位同胞,让子子孙孙永远牢记这段历史。”(47)《裔文钊口述》,费仲兴、张连红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下),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册,第1110—1111页。国民小学即社堂小学,是西岗头村村民对同一地点的不同指称。
长期以来,西岗头村35位村民被日军杀害的记忆只是在村庄内部口头传承。直到2005年,在裔文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西岗头村在村内竖起了一座“西岗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在此碑背面刻上了1937年冬至1938年春日军攻占汤山之后西岗头村遭受劫难的情形,这段惨痛的历史才有了文字记录。碑文如下: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农历正月初九),本村被日军集体枪杀的二十二人中,仅有陈万有一人死里逃生。死亡二十一人:李小三、李永华、李克俭、金怀生、赵小三、周正根、陈广林、陈广泉、陈万松、陈万夏、陈万宽、陈朝良、莫庆文、莫庆武、裔建昌、裔景华、裔景富、曹友恒、董老大、外地二人。
另外,还有被日军枪杀及迫害致死的十六人:李克本、李连才、刘贤春、吴宝才、陈治富、陈广寿、陈广聚、陈万慧、陈道法、莫庆元、张在寅、裔建和、刘方氏、裔景妹、陈朱氏及女儿。
当时全村仅有四十二户,遇难者除外地二人外,本村共计三十五人,被烧房屋九十一间又二十六间厢房,损失粮食、衣、被、禽、畜等不计其数,损失惨重。为了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国耻、牢记悲惨的历史教训、弘扬爱国主义、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本村全体村民,自发捐款,建立此碑,以慰亡灵。
通过竖立纪念碑并刻写碑文,西岗头村的社群记忆以文本的形式被固化下来。若将碑文的内容与陈广顺的口述对照,则可以看出两者所述的基本事实并无二致,陈的口述可以看作是对碑文所传达的社群记忆的个性化讲述。陈广顺的个人口述与西岗头村村史文本之间这种不谋而合的相似性,或许正体现出,农村地区的幸存者是以讲述村史的方式回忆“跑反”经历的,在他们的口述中,社群记忆是最为重要的记忆成分。
四、结语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交织着个人记忆、家庭记忆、社群记忆三种记忆成分。这三种记忆共同构成了幸存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其中,个人记忆指的是认知心理学层面的记忆,即幸存者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后,保存在其大脑中的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家庭记忆和社群记忆则指向的是记忆的社会维度,它们展示了家庭共同体或社群共同体如何回忆南京大屠杀。家庭记忆的形成有赖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在家庭内部的沟通交流中,家庭成员交换彼此的个人记忆,进而建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家庭记忆。家庭记忆一经建构,即由全体家庭成员所共享。社群记忆同样是藉由人际交往和语言交流得以构建及维持的。在社群内部的互动交流中,社群成员讲述并交换各自的个人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所在社群的集体记忆。
如前所述,家庭记忆及社群记忆都是通过其内部成员交换彼此的个人记忆而形成的。因此个人记忆是家庭记忆与社群记忆形成的基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家庭记忆及社群记忆并非是其内部成员个人记忆的总和。群体成员的个人记忆在转化为家庭记忆或社群记忆时,难免会出现信息的缺漏、增补乃至讹误。家庭记忆及社群记忆是在其内部成员个人记忆的基础上建构的,而非是对群体成员个人记忆的完整复制。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访谈活动的开展由为已久,至今已出版了十余部口述资料集,同时也保存了大批幸存者受访的音像资料。面对如此丰富的幸存者口述史料,可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各版口述文本并不完全一致,其原因何在?考察幸存者的生理、心理因素如何影响其个人记忆应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此外,在口述资料整理阶段,不同整理者面对同一份原始口述资料时,所整理的口述文本也有不同。分析整理者的意志如何影响最终生成的口述文本的面貌,亦能为幸存者各版口述文本因何不一致提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