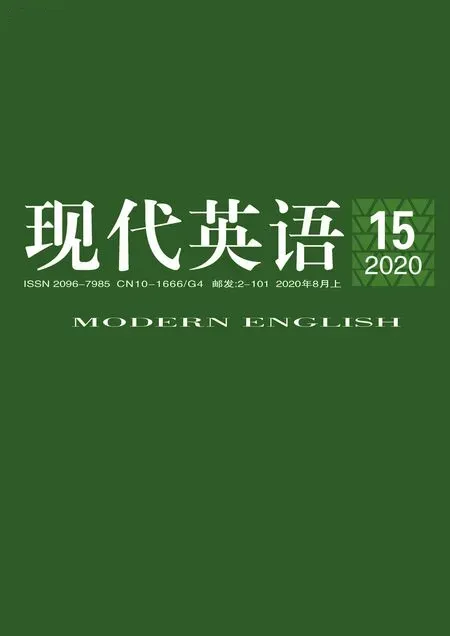从释意理论看国产电影片名的英译策略
冯 芸
一、 引言
释意理论(又称达意理论)是20 世纪60 年代末产生于法国的探讨口译与非文学文本笔译理论与实践的理论。 该理论最早由塞莱斯科维奇提出。 释意即解释意义,该理论认为翻译的最终目标不在于词义和句子层面的语言单位的对等,而在于整体交际效果的等值,即译文对读者产生的效果能复制重现原文对原读者产生的效果。 文章基于此理论,将以中国电影片名的英译为例,探析释意理论对英语翻译的指导作用。
二、 理论概述
释意理论的核心在于区分语言意义和非语言的意思,“一种是词汇语法方面的,另一种是概念方面的,即非语言方面的”(Seleskovitch,2001)。 译者的任务不是传达语言符号的意义即实际写出或者说出的内容,而是话语中所表达的非语言的意思即原文的意图。 语言符号只是交际者在某一个交际场合中试图表达的意思的载体,对这个交际意思的确定需要考虑到认知语境、讲话人的身份、听众的身份等因素。
电影片名的翻译虽然看似笔译,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质更倾向于一种口译。 一般文学作品的文本材料可能因为不同年代或者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与读者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像口译场景中那样密切,因为作者意图表达的意思可能因为年代和文化的变迁而模糊不清;而电影片名的翻译是对电影内容的承载,所有观影人都在场,他们都享有同一个时间空间,也拥有电影中涉及的话题的相关知识和信息,也可以根据电影中的情节、人物表情动作,甚至配乐等感知非语言意义。 所以研究者认为可以用释意理论处理国产电影片名的英译问题。 影片片名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并不是重点,电影的主题和思想才是焦点。 世界各地的观影者观看电影,通过电影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国情、领会电影试图传达的情感和观点。 所以在释意理论中,针对外国电影市场的片名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电影中的信息。
三、 译者应具备的知识
(一)语言知识
对外语语言的专业把控应该是对译者最基本的要求,在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二)认知补充
即译者对语言之外的、对现实世界和通过对原文的解读所获得的知识。 理解是当新信息与相关知识联系在一起时发生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种知识,新信息将被忽略。 对电影片名的翻译者来说,电影的情节和内容作为“认知结构”中的“认知补充”和原文使用的语言符号结合之后,便产生了意义。 电影内容提供情景语境和认知语境,融合译者的语言知识和相关背景知识,译者可以实现从源语到目的语的意义对等。
(三)讲话人
这里的讲话人主要指中国电影的制片方的立场和观点,他们试图用原文片名传达什么交际意义,达到何种目的。
(四)听众
听众指海外市场的观众群体。 译者的终极任务是让听众产生自己预期的交际效果,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的应用保留交际意义,获得预期的听众反映。
四、 翻译策略
释意派学者将语言分为了三个层次:语言、言语和语篇。 与之相对,翻译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语言层面的翻译,力求实现词与词之间的对应;言语层面的翻译,可能会忽视了语境和交际情境;语篇层面的翻译,解码从语言意义和认知成分中衍生出来的意义。 前两个层次属于语言翻译或代码转换,而最后一个层次是解释性翻译,是真正的翻译。 在可能实现对应的情况下,译者可以寻求语言和言语层面的对应,实现等值翻译。 如果失败,译者则应该从语篇中探寻原文内容,也就是意义,并寻找其在目的语中的对等表达。 下文试图将电影片名英译技巧划分为追求语言和言语对应的音译和直译,以及寻求语篇意义对等的各种其他翻译技巧。
(一)音译和直译
事实上,在翻译以人名为影片名的时候,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比如菊豆(Ju Dou);翻译中英文的文化意象不冲突的影片名时,经常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比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Hero),姜文的《让子弹飞》(Let The Bullets Fly),宁浩导演的黑色喜剧片《疯狂的石头》(Crazy Stone)。 就连《卧虎藏龙》也被直译为(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 严格意义来讲,《卧虎藏龙》的英译明显不符合西方文化对龙的负面认知,但是由于释意理论要考虑到讲话人,这里主要指导演李安,他拍这部承载着自己对东方武侠的热爱的电影就是希望将中国博大精深的武侠精神传播到全世界,让外国人感受中国文化中的龙虎精神。 所以,直译保留源语中的用词和搭配,正是考虑到讲话人的意图以及以期达到的效果。 但是释意翻译不等同于乱译,当李安执导的《饮食男女》被翻译为Eat Drink Man Woman 时,便未能有效地传递交际意义,无论是从语法角度还是语义层面都让人不知所云。 因此,当直译行不通的时候,就必须用意义等值方法表达,这就等同于求助了语言外知识,采用了释义。 因为释意最重要的是传达与原文相同的信息,而不是追求使用和原文一样的单词和句式结构,所以改变原文形式的改译法就顺势而生。
(二)改译
释意理论认为翻译是释义,即根据原文的语言符号意义,结合自己的认知补充,对原文做出解释。 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之后,需要分析原文的语言含义和认知结构,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翻译影片片名的交际含义,最后用目的语再度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 也就说在音译和直译不可取的情况下,可以对电影内容提供的认知信息加工处理,和原文片名的语言信息一起为在目的语中的重新表达提供有机平台。 释意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是语篇层次的翻译,电影内容恰恰提供了语篇知识的补充。
比如剧情犯罪片《误杀》便抛弃了字面形式,改译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在电影当中,羊多次出现。 羊羔代表赎罪,谦逊,仁爱。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可以理解为督察长的儿子没有家长的约束指导迷失了自我,也可以隐射双方家长出于对自己孩子的爱和保护,迷失了自我。 所以英译的电影片名对于西方观影者来说更贴近他们的文化信仰,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这部关于爱和救赎的影片。 这样的改译便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影片内容中的认知信息,改变了源语言字面形式,完成了交际意义的传递。
类似的例子还有《鼠胆龙威》(high risk),《少年的你》(Better Days),《甜蜜蜜》(Comrades:Almost a Love Story),《春光乍泄》(Happy Together),犯罪悬疑片《烈日灼心》(The Dead End)等。
释意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勒代雷指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语言的声音发动认知记忆的内容。 当其出现在即时记忆中,认知机制就构建意义;当意义出现,即时记忆就不再保留语言形式——声音首先消失;然后它所唤起的义素消失;最后意义单位也终有其生命限制;一个接着一个进行融合,组成话语的基本意义”(Lederer,1981)。 译者可以积极主动地调动自己的认知,在观看完影片之后会对影片的意义有自己的理解并印象深刻,实现了从语言分离出来的意义获取阶段,因此在对影片的内容和意义有了定位和认知之后,译者便可以在目的语中以自然的方式重新表达意义。 翻译的本质便是意义的提取,而摆脱源语形式的束缚便是改译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三)转换视角
释意翻译本质上是一种从语言到意义,再从意义到语言的翻译技巧,它要求译员从一种语言中提取意义内容,并将其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而不是将一种语言模仿成另一种语言。 翻译的目的是把话语或文本的意思以恰当的形式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视角的转换便诠释了译员如何在理解话语或文本的含义之后,脱离了源语外壳,用另一种语言自然地表达话语或文本意义。
巩俐主演的亲情电影《漂亮妈妈》并没有直译为Beautiful Mom,而是用转换视角的方法翻译为Breaking the Silence。 因为影片讲述了女主角孙丽英生下了一个先天性耳聋的男孩,丈夫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和她离婚,这位单身母亲独自抚养儿子郑大,为了能让儿子听得见,不会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中,她吃苦忍辱,终于给自己的儿子买来了新的助听器,打破了包围着儿子的寂静,最后儿子也终于学会开口说话。 所以“漂亮妈妈”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对这位伟大母亲的评价和赞美,而Breaking the Silence 则是以女主角的第一人称的视角,表达她对生活和命运的抗争,为儿子赢得机会的全力以赴。
另一部剧情片《我不是药神》 的英译片名为“Dying to Survive”。 同样,中文名《我不是药神》是从药贩子程勇的角度出发,但一语双关的英译名却是以那些濒临死期、垂死挣扎、渴求生存的患者的视角出发。
电影片名英译的目的是对观影者传递意思,即交际意义。 译者不应该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的约束,而应该把整部影片的整体内容作为语篇层次的翻译内容,通过解释性的翻译把影片所传递的信息内容予以再现。 正如在口译中译者并非对原文逐字逐句地刻板直译,而是把原文所要表达的交际意义加工之后,用目的语重组还原。
(四)套译
释意理论认为翻译就是在正确理解信息的基础上,将信息从源语传递给目的语的接受者。 这绝不是不同语言之间简单机械的词汇转换,而是实现的语言意义和认知补充构成了意义。 翻译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语言,更是意义的传达,需要译者关注语境,而语言在翻译中只是一种工具。 所以了解翻译受众的语言习惯对电影片名的翻译工作极具指导性,能顺应目的语观众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要求的套译更是不得不提。
《陆垚知马俐》(When Larry Met Mary)是由文章执导的爱情喜剧电影。 中文片名里面既包含了陆垚和马俐两个主人公的名字,又谐音“路遥知马力”,点题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是日久见真情。 如果完全追求字面层次的对等,那么很难把日久生情、兜兜转转找到自己的真爱这层内容传递出去。 所以根据释意理论的原则,果断抛弃措辞,保留信息中的主要概念、想法才是译者的主要任务。 不可否认,《陆垚知马俐》在很多方面和另一部美国爱情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 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相识多年的男女最初并不认为对方适合做自己的男女朋友,他们并不愿意步入恋爱关系而打破和谐的朋友关系,他们有过争吵,在失恋的时候也互相依靠,在不断的错过中最终发现对的那个人一直在原处。 “When Harry met Sally”是1989 年的一部非常有知名度的美国电影,可谓家喻户晓,所以用套译的方法翻译《陆垚知马俐》可以让外国观众倍感亲切,也能有效地传递这部爱情电影的思想和主题。
五、 结语
在目的语中寻找源语的字面对等词或短语并不是译者的任务,将语篇层面的意义在目的语中表达出来,寻求意义的对等才是译者的最终目标。 也就是说,翻译不仅仅是从源语到目的语的单向解码过程,而是重新呈现目标语言意义的过程。 直接转换语言编码只是表层的机械转换,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翻译。 通过以中国电影片名的英译技巧为例,研究者认为综合考虑讲话人意图和听话人的接受度,用释意理论调和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形式差异,以内容和接受度为首要任务,指导翻译工作是值得译者借鉴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