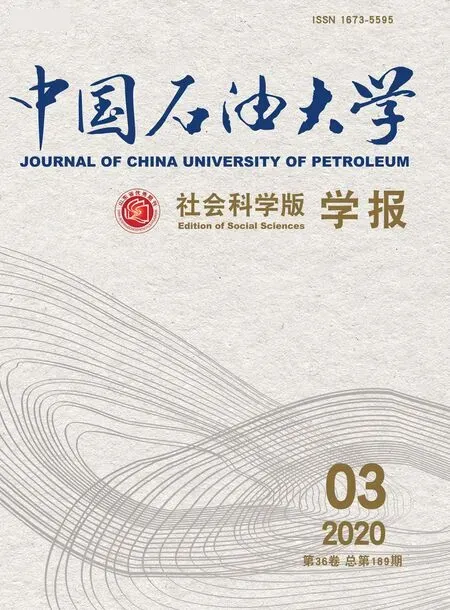理论、路径与价值:论文学地理研究应有的三重自觉
葛 永 海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从季札观乐、《诗经》国风中南北地理之探讨说起,文学地理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成果虽日趋丰厚,但长期以来大多聚焦于实证研究,相比而言,理论建设颇为滞后,对文学地理研究的内涵、路径、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学理性思考不足,学科理论体系认知模糊。有鉴于此,20世纪末以来,围绕着文学地理学理论内涵的讨论此起彼伏,在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广度与深度上,都呈现出明显的递进之势,而在研究推进中,关于“文学地理学”如何成“学”的研究最为抢眼,也最具深度,体现出对于文学地理学立学之本体属性的理论思辨。随着近年来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理的多部著作问世[1-3],相关的理论体系已逐步形成,基本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渐自明确,概念体系和核心意涵已被研究者清晰指认①,其研究范畴和方法亦获得研究者的认可。众所周知,处于正名状态的学科领域,大多经历了一个前学科的状态,其学术探索由隐而显、由散而聚,历程大多遵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螺旋式递进过程,理论指导的意义在于研究者可以在已然明确的研究框架内选择论题,用具有建构性的工具性概念形成对话。那么,当下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就应当完成从不自觉状态的文学地理实证研究到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集中建设之后的第三次跨越,即重点推进开展自觉状态的文学地理实证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开展自觉状态的文学地理研究?文学地理研究应具有怎样的学术品格?这正是本文拟将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重新出发的文学地理研究至少应具备理论、路径和价值的三重自觉。
一、理论自觉
文学地理研究首先应该有清晰的理论自觉。文学地理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无到有,从散到聚,从争鸣到共识,亟待系统性理论的引领与指导。笔者与梅新林教授合著的《文学地理学原理》专注于原理探讨,系统梳理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自问世以来,为学界同仁所推重,有研究者称之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奠基之作、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创新之作、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4],其理论的集成意义颇为彰显。
理论的创新引领,乃是任何一个学科建设的灵魂,是事关这一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文学地理学原理》重在“原理”,其所关注的正是文学地理之为“学”所应有的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与通则,其最为本质的要求是指向理论探索的原创性,该著作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系列能够自成体系的论断和概念。主要论断包括:(1)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2)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4)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除了以上基本论断外,《文学地理学原理》更多地彰显了文学地理研究应有的本体自觉,这种自觉涵盖了理论渊源的自觉、理论体系的自觉、理论概念的自觉等多个方面。
(一)理论渊源的自觉
通观中西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中希发轫、中国轴心、西方轴心与中西并盛四大时段,最终形成法国、美国与中国三大学术中心。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率先宣告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中心,由“空间批评”带动了文学地理学的全面繁荣与内在深化,那么重构不同于西方的“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使命当由中国本土学界来承担。中国本土文学地理学研究由于长期以来普遍侧重于实证性研究,而缺少相应理论创新的引领和支撑,所以在重构不同于西方学术传统的本土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方面一直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而且,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费雷《文学地理学》(1946),皆侧重于法国地域——区域文学研究,严格地说尚未深度触及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更没有完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建构,并且从中西学术交流的维度来看,由于两书一直没有中译本出版,所以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持续高涨与学理探索,与以上两书奠定的西方文学地理学传统并不存在直接的学脉承传关系,这是两种产生于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文学地理学。因而中国本土学界有必要明确提出“新文学地理学”这一全新的理论命题。
《文学地理学原理》提出的“新文学地理学”这一理论命题基于19世纪“地理学—新地理学”与20世纪“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历史经验,从“地理学—新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的历史逻辑走向21世纪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学理逻辑,其完成了不同于以往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重构。重构的“新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以概念界说、学科定位、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作为四大支柱,为文学地理学新体系的创建实现理论奠基。“新文学地理学”之“新”,目标在于彰显了新的理论价值,尤其是通过“学理”“学科”与“学派”三重学术指向,为“新文学地理学”后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前景。
(二)理论体系与概念的自觉
《文学地理学原理》凝炼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其中,对于研究实践最具启示意义的是三组概念,即四种地理、四重空间和三原理论,试简要析之。
其一关于“四种地理”。我们认为,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应包括四个层序:(1)作家籍贯地理,(2)作家活动地理,(3)作品描写地理,(4)作品传播地理。此四层序 “地理” 的提炼极具概括性与涵容性,可以说涵盖了我们所主张的文学地理研究的所有范畴,一切文学地理问题皆莫能脱离此“四种地理”之外。通过对这四个层序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文学家的生活环境,复原文学家重构的时空场景,揭示隐含于文学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而且还可以由此探究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特殊规律。“四种地理”说无疑为文学地理研究的对象指认和路径导引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二关于“四重空间”。对于文学地理学而言,艾布拉姆斯的“世界、艺术家、作品、欣赏者”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可以为重构“世界——客体空间”“艺术家——主体空间”“作品——文本空间”“欣赏者——传受空间”的四重文学地理空间提供整体理论框架。“四重空间”的内在学理关系表现为:“世界”是文学活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指向文学活动所反映的物质空间,即文学地理的第一空间——客体空间;“艺术家”不单是创作作品的人,更是将自己独特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主体,指向文学生产的主体空间,即文学地理的第二空间——主体空间;“作品”作为显示物质世界的“镜”和表现主观世界的“灯”,指向经由作者建构的文本书写空间,即文学地理的第三空间——文本空间;“欣赏者”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也是通过作品进行更新意义层面的精神沟通者,指向文学作品传播——接受空间,即文学地理的第四空间——传受空间。文学地理的四重空间之间,彼此并非孤立或静止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总体而论,是以作家的主体空间与作品中的书写空间为中心,同时协调与物质空间、接受空间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以作家作品的地理属性为中心的空间系统。“四重空间”说重在系统解析文学地理研究中“空间”的本质属性以及内在交错的相互关系,进而呼应:文学地理学研究即主要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属于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的研究。
其三关于“三原论”,也是我们所主张的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核心建构。《文学地理学原理》由地理学所要关注和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受到启示,同时融合“地图批评”的“内层空间”与“外层空间”的“双重空间”理论,最终熔铸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三原”论乃成为“新文学地理学”最核心的理论引领与支撑。
所谓“守正以出新,弘道以致远”。一种理论建构得以完成在于正本清源基础上的创新性建构,对于理论体系的创新性、完整性和成熟度提出很高的要求,而守正出新的最终目的则在于弘道致远,即我们如何将这些理论概念行之有效地运用于研究实践,我们需要观察并思考,这些理论框架与工具性概念在学术实践中将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学术视野,它们能否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指导性并在多大程度上更新我们的论述框架。
二、路径自觉
文学地理研究的理论自觉是与明确文学地理研究基本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备了此种自觉,也就理解了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涵盖面,比如将“四种地理”作为判断标准,那么,与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有关的研究即可归为文学地理研究,反之则不是。那么,明确之后,如何着手开展研究?我们认为,路径自觉中最重要的是路径适用的自觉。
路径适用是文学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所面对的学术论题属于文学与地理空间的关系问题,第一直觉即认定是探讨文学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地理空间问题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无可回避;二是地理空间是论题中的因素,但并非重要因素,引入文学地理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可以对现有文学研究的问题有所发覆、拓展和提升。下面对这两种情况分别加以解析。
(一)文学地理研究的“当然”论题
一般情况下,那种与地理空间紧密联系的文学论题,属于文学地理研究的“当然”论题。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由于作者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本位立场以及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应对策略,主要路径可以从“空间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空间”两方面来展开讨论,也可简要概括为“由地而文”路径论与“由文而地”路径论。
“由地而文”路径论中涵盖了多种学术命题,包含地域文化对于文人、文风乃至文本、文体的诸多影响。地域文化特质对于文人的影响,我们不妨以江南文化对于区域内文人的影响为例做一个系统探讨。
梅新林教授认为江南文化精神乃是刚柔并济,即具“剑与箫”的双重特质,六朝时期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的精神演变,即表现为亦“剑”亦“箫”的二重组合与变奏,具体乃为先“剑”后“箫”、南“剑”北“箫”,最后集中表现为内“剑”外“箫”。这种地域文化特质于江南文人文风影响深远,其形态特征亦颇为多样。对于这一观点,不少研究者形成不约而同的呼应。有研究者认为是“一地兼二体”,比如20世纪初上海文学之发展即对应着这种“剑与箫”的二重变奏。近代以来上海的城市文学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城市文学的开始。在20世纪初,上海文学主要是沿着两条主干线索发展演变:一是言情文学,一是时议文学。前者主要是通过编织悲欢离合的婚恋故事,来迎合广大市民对于风月言情的天然爱好,以商业文化为支撑,突出世俗性,符合追求言情的市民趣味。而后者主要是突出城市作为舆论中心的功能和意义,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言情显示出城市叙事的感性化和欲望化,时议则代表着城市理性。时议与言情的交织发展贯穿着上海文学的现代历程。[5]也有研究者指出“一户兼二体”的案例,典型如绍兴周氏兄弟。有研究者将吴越文化归结为“激烈”与“冲淡”两种不同的人文精神,鲁迅与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是在相同环境、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同胞兄弟,由于个性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对吴越文化中“激烈”与“冲淡”两种不同人文精神承传与吸收的差别,一为“猛士”,一为“名士”,由此形成了其为人为文的迥异。[6]
若将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再加以演绎,甚至可以见出其对于作家个体精神的影响,似乎也有“一人兼二体”的典范样本,比如近代杭州文坛巨擘龚自珍。“壮烈”与“婉约”正是龚自珍诗词意象的两种集中表达,他选择的也正是“剑”与“箫”两种意象。龚自珍《漫感》:“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湘月》词:“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丑奴儿令》词:“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秋心三首》诗其一:“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己亥杂诗》之九十六:“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又忏心一首》诗:“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在龚自珍笔下,“剑”为狂放,“箫”喻缠绵,由此构成诗人壮怀报国之剑胆与幽怨抒怀之箫心的神奇组合。以地域文化之特质传承集于一地、一户、一人之文学研究,江南文化庶几可为范本矣。
当然,关于“由地而文”的研究话题还有许多,江南如此,其他地域文化对于文人、文风的影响也可以以此类推,比如:楚文化对于《楚辞》的影响,秦文化对于文学陕军的影响,齐鲁文化对于鲁地文学的影响,城市文化对于历代城市竹枝词的影响,等等。不同地域文学之间也相互影响,比如江南文学与岭南文学的互动,“自古文人皆入蜀”与蜀地的精神磁场效应,等等。这些研究案例所指示的路径对于其他研究者而言,皆具有启示意义。
再就是“由文而地”路径论。简单地说,就是文学表现地理空间,即文学作品除了表现各类自然与人文地理景观、城市节点、行走路线等,还对地理空间加以重构。我们接续前面关于文学江南的话题,来看“文学中的江南”,比如六朝文人如何书写江南。先秦至六朝的江南意象发展进程,概而言之,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其一偏重于感物。地域意识的觉醒,大体经历了一个由物到情再到审美的过程,江南方物因进贡制度而为博物典籍所记载,进而又被引入文学篇章。所谓“感物”,意指由方物到对地域的情感。其二偏重于审美。在晋室南渡之后,江南意象由感物而至于审美,由萌发而至于蓬勃。南朝士人竞相吟咏,遂为大观。诗歌中的“江南”指称以及与此呼应契合的具体名物意象,逐渐形成特色独具的审美系统。其三偏重于体悟,此乃为审美之延伸。比如南北朝之庾信、王褒等人因为阔别江南,比之齐梁诸人的纯粹诗情,在北思南,更生空间暌违之念,其中又糅杂了极为丰富的生命体验,江南意象在被叠加了更多生命体悟之后,获得了文化内涵上的拓展和提升。正是以上这些,尤其是后两种情形的江南意象不断被塑造和强化,表达出文人们对江南地域一往情深的情感皈依,而情感皈依又不断激活与创造出新的审美表达,这种基于感物情怀又超越魏晋的深度审美演绎,丰富并拓展着江南意象,逐步走向地域审美意识之纵深,最终使“江南”作为经典之意象符号而广泛流传。
六朝文学对于江南的表现,是由各种因素综合塑造的,其中颇为重要的就是文人的空间移动。检视秦汉至六朝,随着国力消长与政权更迭,江南与北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博弈,形成了一系列由地域审美视角引发的文化互动,其演进链条大致可归纳为:在北观南(秦汉)—入北怀南(由吴入晋)—入南观南(西晋到东晋)—在南化北(东晋、南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演进之中,随着江南本位意识的初步建立,在“在南化北”成为日渐自觉的文化策略之后,一种可称为“江南认同”的文化心理开始逐步萌发,并对其后中国文学之江南书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7]
在以上这一文学表现地理空间研究案例的反思中,我们发现研究的着力点,不仅在于文学表现了怎样的地理空间,更重要的是文学为何如此表现,这种表现意味着什么,文学作品中的江南意象,从先秦到六朝呈现出从方物审美到山水审美的演进之迹,这就超越传统作品中地理书写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场景还原,突出了作家的空间移动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通过对在北观南、入北怀南、入南观南、在南化北等一系列文化姿态的分析,解读由文学中心转换所带来的文人主体心态的巨大变异,从而创新性地重构六朝江南文学的生态系统。“由文而地”的研究路径,不能局限于单一的作品描写地理,而要还原其多样性,在立足作品描写地理的基础上,更要讨论与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以及作品传播之地理的密切关系,才能最终复原时空图景,重构文学生态。
概而言之,“由地而文”“由文而地”的二元研究路径,正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两者最大公约数是由“地文互释”与“文地互释”臻于“对话关系”的建立,这是双方趋于内在融合以及在融合中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相互增值的前提条件,也是双重路径论从“文地规约”“文地协同”进而走向“文地重构”的内在动力。
(二)文学地理研究的“或然”论题
一般性文学论题中的空间视角选择,属于文学地理研究的“或然”论题。对于这类论题,要注意运用辩证与平衡的思维,一方面探索空间阐释的可能性与意义,另一方面要注意空间视角的适切性。
比如从地理空间着手对于陆游的诗歌进行研究。在陆游的笔下,并置着不为以往研究者所关注、精神内涵却颇为丰富的两大意象空间,那就是“大散关”空间和“沈园”空间。对于这两大空间,我们必须用彼此映照的思维来加以分析,这两大空间是对于江南文化特质的一种承继和发扬,前者指向壮烈,后者寄寓哀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中提及的大散关,自乾道八年 (1172) 首次出现在陆游诗作 《归次汉中境上》中,到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210年1月26 日)陆游辞世的 38 年之间,20 余次出现在陆游诗中。[8]这期间,陆游自南郑辗转嘉州、蜀州、成都、山阴、严州、临安等地,到晚年再回山阴。无论世事变化与身份转换,大散关一直都是陆游诗中永恒的话题。有研究者称大散关“不仅被用作指涉从戎生涯的语词,从其上向下俯瞰关中平原的视角更从此成为陆游爱国诗作中的代表视域”[9]。与这种终其一生念念不忘的抒写相一致的还有陆游笔下的沈园。陆游20岁(绍兴十四年)与唐婉结为伉俪,琴瑟甚和,不料唐婉为陆母所不喜,种种哀告不许,最终棒打鸳鸯,两人被迫分手,后陆游再娶王氏,唐婉也改嫁“同郡宗子”赵士程。在分手六年之后的绍兴二十年,陆游于山阴城南禹迹寺附近的沈园,与偕夫同游的唐氏邂逅。陆游饮后乘醉赋词,将那首著名的《钗头凤》题于园壁,唐婉亦有《钗头凤》相和,词中难掩悲伤之情,其归家后不久即抑郁而终。沈园自此成为陆游一生念念不忘的牵挂。63岁触景生情,陆游题二绝句云:“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泌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68岁时陆游重游沈园题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陆游75岁时曾居于沈园不远处,“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作绝句《沈园二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79岁再次在梦中游沈园,作诗二首:“路近城南己怕行,沈家园里最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82岁作《城南》:“城南亭榭所闲坊,孤鹤归飞只自伤;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84岁作《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如此高频次地歌咏一方地理空间,念念不忘,几乎至死方休,放眼世界诗歌史,亦为罕见。正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所评:“无此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10]
类似研究思路的还有关于“吴中四才子”研究,在一般意义上,对于吴中四才子的生平交游、作品艺术特点和思想内涵等的研究都已经极多,如果从文学地理出发,引入空间视角,当如何思考?四才子籍贯地在苏州,却又有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四人不同的人生版图中,他们如何交集,如何看待他们交集的意义?他们的作品中书写了苏州之外的哪些地域?如何书写的?苏州在明代文人的精神时空坐标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带有地域特征的文学群体,这种空间视角的研究对于各个时代的文学群体研究其实都有启示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强调研究路径自觉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研究路径的误区加以反思,力戒空洞化、平面化、虚幻化的倾向。一是影响论之泛化。研究者在讨论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时过于笼统,由于缺乏清晰而连贯的材料加以印证,作家所受的地域影响往往是碎片化的、不成系统的、抽象的,这类的空间视角往往过于宏观。二是反映论之简化。作品描写地理是新手研究者乐于选择的学术论题,其特点在于论题直观,上手较快。但这类选题的通病也比较明显,研究者在分析作品中关于地理景象的描绘时,依据文本但未能超越文本,未能从文本空间进入主体空间,对于精神内涵的探讨浅尝辄止,使较为复杂的文本空间投射、主体空间建构的过程被简单化处理。三是适用性之虚化。并不是所有的空间都是“有意味的空间”,空间并不必然产生意义,我们在面对“或然”的文学地理研究时,如未能采用适切性原则,生硬造文,空间视角的意义则会被人为地放大。要避免以上的诸种弊端,最重要的是必须证明:地理空间对于文学而言,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化的;这种学术理路是清晰的、可以确证的而不是空泛的。
在研究实践中,具体研究路径的选择会大致形成几种模式:作家籍贯地理+精神探原,即如绍兴周氏兄弟的探讨,从作家籍贯入手来探讨其精神内涵;作品描写地理+精神探原,即如陆游笔下的“大散关”与“沈园”,既是人文空间,又是精神空间;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精神探原,即如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六朝,在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时代,文人都通过南北游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江南想象”,其“江南情结”引人深思,凡此不一而足。各项研究大多不约而同,不乏殊途同归,其落脚点都指向了版图复原以至于精神探原。那么,我们的追问是,文学地理研究是否有着明确的、共同指向的价值落点,这需要从文学地理研究的价值自觉说起。
三、价值自觉
文学地理研究究竟价值何在?这个价值指的是文学层面,而非地理层面。对于这个带有目标指向的话题,我们明确提出“三原论”予以回应,即版图复原、场景还原和精神探原。这是关于文学地理研究之价值意义的核心命题。
1. 版图复原
版图复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与“外层空间”相对应。“版图复原”说,版图之“版”,意为户籍,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版与图组合为版图,即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及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等。文学版图之“版”即“户籍”,也就是文学家的“名册”;而文学版图之“图”,就是文学家的活动空间舞台。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的“户籍”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所在。文学家群体处在哪里,流向哪里,文学活动与创作成果就带向哪里,文学地理的中心也就转向哪里。文学家的“名册”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活动之中的,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的文学版图也就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与传播地理的分布与流向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图景,而这也正是“版图复原”说的要义所在。[2] 313
2. 场景还原
场景还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双向互观,将“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相贯通。“文学场景”与影视的“场景”概念具有内在相通之处,主要是指人物活动的空间情景,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不可替代也不可重复的空间图景,旨在强调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鲜活样态还原,并通过不同时空的场景链接而走向动态化、立体化、集成化与虚拟化。杨义先生就曾使用“生命现场”这一概念以阐释文学地理学的本质,他指出:“研究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时间的维度,进入到具有这么多种多样因素的复合的地理空间维度,进行‘再复合’的时候,就有可能回到生动活泼的具有立体感的现场,回到这种现场赋予它多重生命意义,就可以发现文学在地理中运行的种种复杂的曲线和网络,以及它们的繁荣和衰落的命运。所以,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它的生命现场,进入它意义的源泉。”[1] 8“场景还原”的主旨导向集中体现在三个“回归”,即回归生命现场、回归鲜活样态、回归人文精神。
3. 精神探原
精神探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价值追问,与“内层空间”相契合。“精神探原”特别关注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精神探原”具有自身独特的空间矩阵结构,即以“诗性空间”为逻辑基点,中经“文化空间”的开放性和“原型空间”的深刻性,最终指向本体追问的“终极空间”。
如上所言,文学地理研究之价值自觉的核心内涵在于,要使“精神探原”成为文学地理研究的最终落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仅“精神探原”中的空间矩阵难分彼此,比如“诗性空间”与“文化空间”“原型空间”的边界很难区分,在专题讨论时,“精神探原”与“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也常常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三原”的价值目标与意义指向往往是贯通式的。许多典型研究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精神探原”的生动路径。
有的研究案例关注“精神探原”的强度。比如,洪文莺、梅新林在研究东晋时期的东—西“文学走廊”时就指出,该“文学走廊”东起扬州治所兼首都建康,西迄荆州治所江陵,既是借助长江水道地理优势与“荆扬之争”历史机遇双重支撑的产物,也是两晋易代迁都之后中国南北文学中心历史性转换的结果,在建构建康—江陵两大文学中心以及重构整个东晋文学版图中都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11]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重点在南—北文学中心迁移与交融,而忽视了东—西文人群体的双向互动及其深远影响。事实上通过对这个东—西“文学走廊”形成机缘、文人互动与文学交融的还原与探索,不仅有益于重新认识这一东—西“文学走廊”本身的重要价值,而且有助于深入诠释东晋文学版图的内在结构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研究之后,最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对于会稽—寻阳两大文学原型空间及其深远影响的阐释。该研究认为,由东晋初期建康文学轴心地位的确立以及南北文学重心转移的完成,到东晋中期会稽、江陵两大文学亚中心的崛起,再到东晋后期归结于寻阳文学亚中心,实际上也是对东晋百年文学版图时空演变的总结。其中最具文学原创精神并最具持续影响力的是会稽、寻阳两大文学亚中心,前者经“玄学—山水”的“山水玄化”,同时吸取江陵文学亚中心“地志—山水”的“山水诗化”,一同铸就了相对成熟的山水文学。后者一方面在山水文学上,由慧远在东、西部“玄学—山水”的“山水玄化”与“地志—山水”的“山水诗化”的两相交融中另行融入佛理与禅趣,不仅是对中国画“以形写神”理论的有力提升,同时也开启了后代山水诗、画合一的先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派的开创,陶渊明另辟蹊径,从此前的登临游览山水直接转化为躬耕田园生活,从感悟自然山水的玄远意境走向田园风景的质朴意趣,这无疑是陶渊明之田园诗不同于此前山水诗的崭新创造,这一“开宗立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寻阳文学亚中心,也远远超越了作者所处的东晋时代,更是直贯唐宋以后的田园诗脉而历久不衰。研究最后指明了这两大精神空间的原型意义:“我们不妨将重点孕育和催化中国山水诗、田园诗的摇篮与圣地——会稽、寻阳两大文学亚中心,视为最具原创意义与最具持久影响力的两大文学原型空间。”[11]113在此研究理路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从“场景还原”“版图复原”到“精神探原”的演进之势,并最终在文学精神的探讨中突出文学原型意义的深刻性。
有的研究案例则关注“精神探原”的广度。我们尝试通过唐代诗歌作品对于各类城市歌咏的分析,来描画唐人的“精神地图”。②唐代疆域辽阔,出现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城市,比如:号为“世界首都”的长安、富贵闲适的洛阳、风月长生的扬州、富庶安逸的益州,等等。城市歌咏乃是唐诗的重要题材,不少名城秀美卓异的自然风光与意蕴深厚的人文景观往往为诗人们所辗转追忆、真情歌咏。鉴于唐诗歌咏的各层次的城市极多,我们将研究的对象聚焦于唐代最为重要的一级城市行政建制——州城。唐诗中有大量关于州城的描写,以郑州大学《全唐诗库》的网络检索系统计算,仅题目中包含“州”的诗歌就达2590余首,若计上内容中包含州或州所辖区域的诗歌作品,数量更为繁多。本研究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数据检索选取相关的城市,以检索统计的方法,筛选出在诗歌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城市,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关于唐代城市的整体认知和城市方位、类型、特色等因素,筛选出一定数量的研究对象;其次将所研究的城市加以分类,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通过分类以凸显其城市的独特性;最后通过对城市类型的综合分析,探讨唐代诗人的城市情结,最终推演出诗人的精神地图。
就学理而言,此项研究即从客体空间出发,以文本空间为依据,探讨主体空间的情感特质。就“三原论”而言,即通过诗歌分析,完成各个城市歌咏的、局部层面的“场景还原”,再到组缀形成的全时代、全空间层面的“版图复原”,在划分不同的精神板块之后,进而推导演绎一个时代文人的“精神地图”,其研究之主旨即归于“精神探原”。
四、小结
文学地理研究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无论在个案研究的微观方面,还是在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与价值。[12]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文学地理研究,重视空间维度,重构时空关系,在传统论题之外,时空贯通,另出手眼,别开生面。我们呼吁“三重自觉”之后的再出发,乃是希望研究者全面提升理论研究的本体认知,明确自己在研究什么、为什么这样研究以及研究的目标方向、价值意义,从而明确主旨,重建框架,掌握概念,运用方法,不断砥砺学术品格,提升学术品质,使得文学地理研究一步步从外在转向内在、从宽泛走向纯粹、从浅表迈入深邃。
当下的文学地理研究的优秀成果体现了国际视野、本土情怀、时代精神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我们应当以立足世界、超越中西的学术视野,进一步展现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理论创新。伴随着当代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学术也逐步走向了世界的中心舞台。中国学术在很多学科领域已摆脱长期以来的“跟跑”状态,而与西方形成“并跑”之势,时代更为之提供了反超进而“领跑”的历史契机,比之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学地理学更具潜质。相信当代学人共同努力,通过理论奠基、体系创建,进而聚焦重点、多维透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不断提升学术视野与学术品格,定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地理学学派。
注释:
① 《文学地理学原理》梳理并总结了系统的概念体系,重点围绕“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历史变迁、多元复合与整体界说三个维度,将“文学地理学”概念体系归结为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以及地理诗学的复合概念系统之说。
② 此为本文作者及其团队所进行的关于“唐代诗人的城市情结及精神地图”研究,其相关成果2019年被复旦大学收录于《文学与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