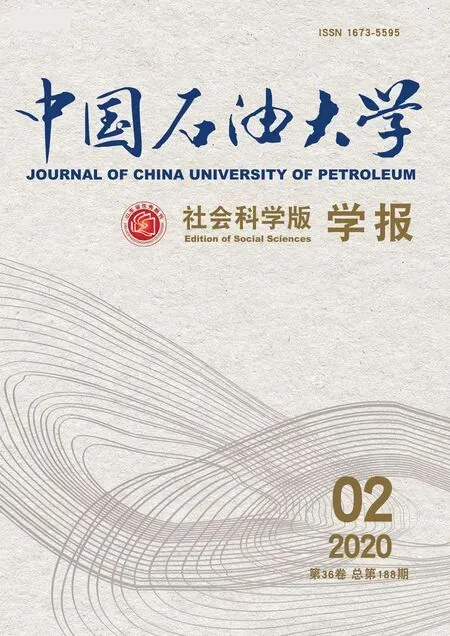他乡人视域下《寿宁待志》的独特民俗
张 丹 丹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号吴下词奴、墨憨斋主人等,明末清初,“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县”[1]56人。冯梦龙一生大部分时间活动于苏州地区,明代苏州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生活衍生出多样的民俗,正德《姑苏志》即言苏州地区“其俗可谓美矣”[2],这也使得冯梦龙长期浸染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之中。此外,冯梦龙尚有两段较长的寓居在外的经历:一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前后于麻城授业,二是崇祯七年(1634)至崇祯十年(1637)于寿宁为官。《寿宁待志》即是冯梦龙知寿宁令时所编撰的县志,成书于崇祯十年(1637)。
在《寿宁待志》之前,张鹤年曾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主持修撰《寿宁县志》,知县戴镗曾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主持修撰《寿宁县志》,均佚。冯梦龙之后,赵廷玑亦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主持修撰《寿宁县志》,今尚存。相比他志,《寿宁待志》为冯梦龙实地考察寿宁后所作,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县志,一方面,该书记录了晚明寿宁地区政治、经济、地理、风土民俗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书中大量篇幅以第一人称“余”进行叙述,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体现了他乡人冯梦龙对寿宁独特民俗的关注。
寿宁县设于明景泰六年(1455),地处福建东北部,主要为山地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对外交通不便,由此保留了一些独特的民俗。康熙《寿宁县志·风俗》载:“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淳薄异性,俭奢异习,农末异趋,质文异尚,服食异宜,若泾渭然不可推移,物之情也。”[3]345直接阐明了寿宁地区风俗之异。冯梦龙于《寿宁待志》中曾言:“吾乡人有札至,问寿人何状。”[1]可见,苏州人对寿民亦充满好奇感。冯梦龙由浙入闽,在接触寿宁风物时,下意识会联想起苏州老家,如《寿宁待志·风俗》论及寿宁吏惯于用扇,言“若苏杭真金扇,虽荐绅大家间有之,无轻用者”[1]29,即将寿宁用扇之风与苏杭之“无轻用者”进行对比。由此,他乡人身份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便凸显出来,使得寿宁独特民俗成为冯氏笔下的关注点。
一、衣食住行习俗
由富庶的苏杭之地进入寿宁地区,寿民的吃穿用度是初来乍到的冯梦龙最直观感受,这种感受带来的强烈新奇感,引发了“搜罗奇事韵事,不余遗力”[4]的冯梦龙的关注。由此,相比其他县志,《寿宁待志》所载的寿民日常衣食住行等方面习俗,不可谓不详细,体现了作为他乡人的冯梦龙对寿宁独特民俗的关注。
(一)服饰习俗
寿宁服饰款式独特。《寿宁待志·风俗》载:“寿人男女衣服微分长短,领缘无别。其相反者有二:男子必服袴,而女既嫁则否,寒则添裙,有添至三四者。男子无长幼,无凉燠,必以布兜其胃,恐触寒气。而妇人虽暑月亦不蔽乳,此其故不可解。”[1]31冯氏此处所言“相反有二”:一是明代寿宁已婚妇女只着裙装,不服袴;二是男子四季以兜肚为常服,而妇女夏季炎热时则存在“不蔽乳”之举。此种服饰习俗的形成,应是当地地形与经济综合影响的结果。明代寿宁基本采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方式,寿宁多山,男子经常在外务农,下身着袴便于行动,恐触深山寒气而以布兜其胃;女性长年居家,很少出门,受寒气侵袭不严重,为了节省布料,故只着裙装,夏季暑热,上身甚至不着衣物。古代中国素来将服饰与仪礼联系起来,从而赋予服饰一定的伦理意味,尤其是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礼仪、阶级观念和伦理道德。冯梦龙是春秋学大家,对儒家思想有较深的认同,寿宁女子的穿着无疑违反了儒家服饰伦理规范,故引起冯梦龙的关注。此外,冯梦龙长期生活在文化高度发达的苏州,惯见苏州女子“靓妆炫服,堕马盘鸦”[5]56的奢华穿着,看到寿宁女子连基本遮羞都不需要,“其故不可解”[1]31。
明代寿宁服饰风俗之异,还体现在小儿蓄发、冠者脱帽上。《寿宁待志·风俗》载:“寿俗,小儿才数岁即为蓄发。其冠者,居恒脱帽,甚则并不裹帻,以此为适。儒生在途,亦多短衫露顶,各不相诧。”[1]32古代中国男子有蓄发之俗,到了一定年龄则束发加冠,“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6]。嘉靖《吴江县志》载:“童子年十二或十四始养发,发长为总角,十六以上始冠。”[7]685可见,明代苏州一带,男童十几岁才开始蓄发,故冯氏有“小儿才数岁即为蓄发”之语,“才”“即”二字,尽显其新奇之感。有明一代,冠履被视为男子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时,男子二十而冠,多于冬至或元旦束发加网,士戴方巾,民戴圆帽”[8],这是儒家正统的服饰仪礼要求。而寿宁成年男子,则不戴帽不裹帻,甚至儒生亦然,并以之为常态。此种现象一则出于寿宁湿热的地理气候,带帽裹帻容易增加不适感;二则因寿宁物资匮乏,且男子受教育程度低,儒生亦是“文风不振,科第绝响”[1]5,对儒家正统服饰的认同感不如苏州等地区强烈。
冯梦龙对这种服饰习俗表现出强烈的新奇感,虽有所不解,但尚能欣然接受。其《寿宁待志》有言:“吾乡人有札至,问寿人何状?余答曰:‘寿人甚易识,比他处人,不过多一个兜肚,少一顶帽子耳!’虽戏言,实实录也。”[1]32冯梦龙用“戏言”的轻松形式点出寿民服饰特点,又可见其乐在其中。
(二)食、住、行习俗
作为对外交流较少的山中小邑,明代寿宁的食、住、行习俗深受地形、气候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寿宁的饮食习俗与别处不同。《寿宁待志·风俗》载:“民间三餐俱饭。好食线粉,粉米为之,鬻者最多。贫家乏米,或用粉竟日,取其便也。”[1]30昔时寿宁三餐以米饭为主,甚至用米养猪,后因“邻境多饥,奸民往往阴与之为市”[1]30,导致米价渐贵,家贫者出于米价上涨及便利因素,食粉竟日。此外,由于寿宁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加之地形以山地为主,湿气严重,“晓起,触山气易病”[1]30,因此,寿宁百姓多于晨间饮酒。
寿宁多山,建屋“取材于山,立屋颇省”[1]30,因而筑房屋四墙时,“四围垒土,或用木板”[1]30,甚为容易。而屋顶的建造因“瓦(泥瓦)最难致”[1]30,故村落多有使用陶瓦为盖者,然“团沙为质,手擎可碎”[1]30,陶瓦所筑房屋质量极差。因寿宁建房成本低廉,有搬家者则“空之,还复葺”[1]30,导致了房屋盗卖之风盛行。又因山中平地甚少,房屋又有“制度狭小,多重屋而少广厦”[1]30的特点。
寿宁百姓出行主要依靠步行,“城中绝无肩舆之迹”“乘舆张盖者稀有”“远行用小兜,与民家同;间有暖舆,亦甚简陋”[1]29,轿类的使用非常稀少,即便是乡绅与有司的谒见,或赴宾筵者等,也多徒步前往。这与寿宁多山,且寿城占地面积小,“东南相距不半里,举足可周”[1]29紧密相关。
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明代寿宁日常生活习俗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寿宁待志》对明代寿民日常衣、食、住、行习俗着墨甚多,可谓他志所不及,这与冯梦龙作为他乡人的身份息息相关。细究《寿宁待志》所载衣、食、住、行诸方面习俗,可以发现,这些风俗都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显然是冯梦龙感知上受异乡民俗冲击,因而详细记之,多暗含与冯氏先前在苏州一带惯见的生活经验相对比,如写宴会上的鸡鸭“带血登俎,韧不堪嚼”[1]30,这与其先前饮食习惯或相关,表现了他乡人在接触寿宁本地习俗时的文化隔阂。此外,寿宁一些衣、食、住、行习俗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正统仪礼相悖,这也引起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冯梦龙的关注。冯梦龙著县志以《寿宁待志》为题,其中“待”之一字,不乏对后世为官者能够移风易俗、纠正寿俗不甚合理处的期待。
二、婚丧习俗
婚丧自古被视为人生大事,“冠昏丧祭,民生日用之礼,不可苟也”[9]。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各朝各地形成了一定的婚丧习俗,且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色彩。寿宁“城囿万山之中,形如釜底,中隔大溪”[1]1,交通极为闭塞,经济亦相当落后,因而其婚丧习俗在受时代因素影响的同时,更多地保留了地域独特性。
(一)婚俗
婚俗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礼俗之一,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嘉靖《吴江县志》有载:“男女议婚,大率以门楣为重,亦互择人而兼决于命卜。”[7]685-686可见,冯梦龙居住过的苏州地区,婚姻对门户有一定的择取。而《寿宁待志》载寿宁“婚礼不甚择门户”[1]30。这种习俗后面,伴随着寿宁乃至福建地区婚俗的一大弊病——婚姻论财,明代何乔远《闽书》即载寿宁地区“姻缔论财,要责无厌,贫则弃之”[10]。
《寿宁待志·风俗》对寿宁婚俗进行了详细记载:“聘单开自女家,盒担如干,聘礼如干,男家从之,乃始成好,最费不过五十金。女家奁盛者笼二十担,牛十头,以次而杀。或贫甚,则男家预扣奁资若干。其聘以饼为重,如江南之用茶枣,粤中之用槟榔也。女既许字,其家制衣俱不给价。将出阁,男家自非赤贫,必有挂帐之礼专劳衣匠,多至十余金,少或一二金,听女家随意自犒。”[1]30冯梦龙对寿宁婚俗的关注点不是婚俗仪式,而是围绕着婚姻的花费进行记载,看似客观,实已有一定的价值判断。据载,男方聘金“最费不过五十金”,而给衣匠的酬劳可“多至十余金”,可见“五十金”在明末寿宁价值并不高。男方聘礼“以饼为重”,而女方“奁盛者笼二十担,牛十头”,聘奁轻重悬殊之大颇为可观。反观苏州地区,虽婚俗尚奢,“自行聘以及奁赠彩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期贵重,又求精工”[11]146,但其俗为聘礼重于嫁妆。《陈文恭公风俗条约》有载:“有女家多索男家,延挨不但子女怨旷,更至酿成强抢硬娶之事。”[11]147与寿宁形成鲜明对比。寿宁重奁轻聘婚姻陋习的形成,与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观念相关, “闽俗重男而轻女,寿宁亦然”[1]30。而寿宁此种婚俗又产生一大后果,即当地存在严重的溺婴现象,“寿民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1]31。究其原因,与担心养女出嫁难以置办嫁妆不无关系。
与寿宁婚俗紧密相关的是寿宁家庭男女关系。受重男轻女观念、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低下,缺乏独立性和生存保障,这些都促成了寿宁的婚姻陋习。一是随意休妻。《寿宁待志》载:“大家非大故不出妻,小户稍不当意如弃敝屣。”寿宁地区以经济为缔结姻亲的先决考虑因素,经济实力差的妇女被休乃为常态,“下民一有缓急,即儿女满膝之妇,去之不顾”[16]944。二为随意典妻。《寿宁待志》载:“或有急需,典卖其妻不以为讳。或贷与他人生子,岁仅一金,三周而满,满则迎归。典夫乞宽限,更券酬直如初。亦有久假不归,遂书卖券者。”可见,明代寿宁地区,女子更多地被视为夫家所属物品,可以随意以低廉的价格典妻、贷妻,借给他人生子。三为丧中即嫁。《寿宁待志》载“孀妇迫于贫,丧中即嫁”,《闽书》亦载“贫妇,夫死未几辄嫁或赘”[16]944,表现了寿宁妇女对男子的强烈依附性。四为帮老。《寿宁待志》载:“甚有双鬓皤然尚觅老翁为伴,谓之帮老。”寿宁女子极低的社会地位决定,她们离开男子无法独立立足于社会,故即便年老,为了生存亦可能寻觅伴侣。
对寿宁重奁轻聘婚俗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溺婴、婚姻陋俗,冯梦龙直接发出感叹:“微独轻女,女亦自轻,悲夫!”[1]冯梦龙“三言”、《情史》等作品皆表现出了对弱势女性的关怀,明代寿宁这种把女子置于极低地位的观念,大大触发了冯氏的感慨,“悲夫”,二字于县志中直抒胸臆,表现出其对此陋俗的悲痛之情。
(二)丧葬习俗
自古以来,丧葬不仅是为单纯安葬死者,还被作为衡量孝顺与否的标准,“孝莫重乎丧”[12]。由此,丧葬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丧礼也理所当然被视为“礼之大本”[13]。丧俗是由丧礼中发展出来的相对固定的丧葬习俗,具有地方性与时代性交融的特色。
寿宁的丧俗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火葬及停柩。古人出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伦理观念,认为破坏身体完整性的火葬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普遍采取 “亲死棺殓,入土为安”[11]146的土葬方式,乾隆年间《陈文恭公风俗条约》中,把火葬视为“忘亲灭礼,莫此为甚”[11]146的大逆不孝行径,并列出“有子孙之亲,棺毋许火化”[11]146的规定。麻城亦是“坐夜择地营葬”[14]卷十第十一叶的土葬方式。因此在冯梦龙眼中,“寿多火葬”[1]32显得尤为奇特。
停柩之风,有较强的普遍性。明清之际,随着卜宅兆葬之说的盛行,“葬必择地”的风气愈加兴盛,没有择到吉地吉时的丧家则久停不葬。加上厚葬习俗盛行,财力不足者多选择停柩以塞流言。停柩之风在苏州一带也相当盛行。同治《苏州府志》载:“温饱者惑于风水,久不厝不葬,反以速葬为耻。甚至数年几代均不肯葬,漏屋停棺,到处浮厝。”[11]146然而,在冯梦龙眼中,寿宁停柩之风的成因与苏州一带截然不同。 “寿多火葬,非惑西方之教也,其停柩亦非尽信堪舆之说也”,而是 “土之稍平者屋之,山之稍浮者亩之,地几何而堪宅鬼”。[1]32寿宁少平地,凡地势较平者都作盖屋和耕地之用,不足以营坟,此是造成火葬和停柩之风盛行的根本原因。这与康熙《寿宁县志》“惑西方异教,而火化亲尸;信堪舆僻说,而停顿亲柩”[3]345的记载迥异。
三、岁时节俗
岁时节俗是庆祝岁时节日而衍生的相对固定、代代相传的民俗活动。寿宁因地处较为封闭的山区,其岁时节俗有相对独特之处,正如康熙《寿宁县志·风俗》所言“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3]345。同样在他乡人的冯梦龙眼中,这些岁时习俗彰显了寿宁独特的色彩,也因而,冯梦龙《寿宁待志》将岁时风俗单列《岁时》篇以详细记载。
(一)迎春民俗
立春作为农耕社会的一个重要节日,在古代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因而衍生出各种迎春活动。迎春牛作为迎春活动的重要仪式,历来广受关注。明嘉靖《姑苏志》即载:“迎春日……竞看土牛,集于卧龙街,老稚走空里。”[15]372在苏州地区迎春牛活动乃是盛典,明代唐寅《江南四季歌》之“满城旗队看迎春”[16],当可窥之。冯梦龙《寿宁待志》云:“迎春……迎土牛,居人竞以砂砾掷之,中者新年有采。虽呵禁,不止。比至县,牛无完肤矣。”[1]34可见,明代寿宁地区立春时亦有迎春牛活动,而较他处有所不同的是“居人竞以砂砾掷之”。
“鞭春牛”之举,民国前苏州地区不见记载,福建则多地有之,应是受山地地形影响,更好地保留了前代风俗。“鞭春牛”本意是要把冬休懒散的耕牛打醒,让它振奋精神投入春耕。闽中、闽北地区又有“向牛乞土”的风俗。乾隆《宁德县志》载:“‘立春’前一日……儿童各以竹竿粘彩丝,打土牛身而拾其剥落之土,谓得土多利田畜也。次日行鞭春礼,奉芒神于邑城隍庙。”[17]卷二第四叶宁德县以春牛身上落土为吉祥意,但在寿宁,该习俗演化为以砂砾掷牛。牛作为主要畜力,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很长时间内被统治者严禁宰杀。《大明律·厩牧》即载:“凡私宰自己牛马者,杖一百……若故杀他人牛马者,杖七十,徒一年半。”[18]为了保护耕牛,一些地区乃以土造假牛充鞭春之用。寿宁这种肆意伤牛的习俗引起了冯梦龙的反对,其“虽呵禁,不止。比至县,牛无完肤矣”之言,表现了对此陋俗的不满及劝诫无效的无奈之感。
(二)端午节
“端午”原作“端五”,即五月初五。《岁时杂记》载:“京师市廛人,以五月初一日为端一,初二日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午。”[19]冯梦龙久居苏州,苏州端午之俗“五日,治角黍,悬艾,饮雄黄、昌阳酒,缠缕制符以辟邪”[5]57。而明代寿宁一带,以五月初四为端午。冯梦龙《寿宁待志》载:“端午以四日为之。”[1]34冯梦龙对此风俗进行了追溯:“相传国初,民与兵争市肉至相杀,自是,民间先一日作节。而旧志云:避闽王死忌。未知孰是?”[1]34冯梦龙此处对初四过端午风俗的考证相对审慎,参考了民间传说和旧志材料。乾隆《宁德县志》载:“‘端午节’,俗传五日为‘闽王忌辰’,皆以四日为节。”[17]卷一第五叶乾隆《福建续志》载谢在杭言:“闽人以五月四日作节,谓王审知以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年谱,审知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20]卷八第十七叶可见,闽地传说因避王审知忌辰而四日为端午的,不在少数。康熙《寿宁县志》亦载:“俗传五日为闽王死祭,皆四日为节。”[3]345除了五月初四过端午,冯梦龙亦关注到寿宁端午无赛龙舟之俗,并追溯原因“溪水浅而溜,且多石,故不设竞渡”[1]34,此无疑是受寿宁地形影响下的独特节俗。
(三)中秋节
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节有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其中又以赏月、食月饼、分瓜等流传最广。光绪《苏州府志》载:“十五日为‘中秋节’。作月饼相饷,祀月。陈果于庭,镂瓜如锯齿式,焚香斗,食新栗、银杏,聚饮。夕则结伴出游,名‘走月’。”[15]370光绪《麻城县志》亦载:“八月中秋,作饼相送,具菱藕、瓜果为赏月之宴。”[14]卷十第十二叶类似记载亦多见于明清多地县志。
明代寿宁的中秋节俗有鲜明的独特性。《寿宁待志》有载:“县无鲜鱼,惟中秋节各村俱涸泽取鱼,荷担至城。虽贫人典衣亦必市鱼一块,为过节之需,晴雨无间。过十五求市中一鳞,不可得矣。”[1]34寿宁中秋之际,人们即使典卖衣服都必须买鱼,可见寿宁中秋食鱼的节俗之盛。寿宁地处山区,“溪鱼仅二三寸,亦为珍馔。鳇鱼从宁德来,甚艰,非大寒之候,色味俱变矣”“魦鱼干鳗谓之常馔,猫亦食惯,偶以鲜鱼投之,摇尾而去”[1]30,在一个鲜鱼如此罕见,被视为“珍馔”的山区,中秋必求一鱼,当地人对中秋节的重视不言而喻,正如《寿宁待志》所载“四时惟端午、中秋二节最盛”[1]34。中秋必买鱼而不置月饼、瓜果等,展现了明代寿宁中秋节俗之独特,无怪乎冯梦龙多用笔墨尽绘买鱼之热。
(四)重阳节
关于重阳节的记载历时已久,以登高、佩茱萸、饮酒为主要节俗。汉刘歆《西京杂记》即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21],梁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中又有“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22]的相关记载。此种节俗相对固定地流传下来。万历《长洲县志》记载:“九日,登高,采菊,佩萸。”[5]57-58光绪八年《麻城县志》亦载:“九月重阳,登高,扫墓,民家酿酒。”[14]卷五第三叶可见,冯梦龙寓居过的苏州地区,重阳登高乃为常俗。而《寿宁待志》载:“重阳在家庆节,不登高。”[1]34冯梦龙写及寿宁重阳节俗时,关注点置于其“不登高”这一特色,此处以无入载,明显是与先前惯常“重阳登高”的经验作对比。寿宁地处山区,“踞一郡最高之处”[1]32,故重阳实无登高远眺的必要。
明代寿宁的岁时节俗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如端午节不赛龙舟、重阳节不登高等,多是受地形影响。当然,也有人文因素影响下形成的节俗,诸如五月初四过端午;更有甚者,寿宁百姓出于认知的缺失而产生迎春伤牛的陋俗。
四、小结
“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仍不可避免地渗透于作品之中,从而为我们从小说文本反观地域风尚提供了可能性。”[23]冯梦龙作为话本小说家,曾编撰“三言”及民歌《挂枝儿》《山歌》等通俗文学,采风问俗是其内在关注倾向,这也影响到冯氏对《寿宁待志》的编撰。《寿宁待志》详细记载了明代寿宁习俗的独特之处,其涉及民俗的篇幅为康熙《寿宁县志》的六倍之多,二志笔墨多寡悬殊,足可见冯氏对寿宁习俗的关注。与康熙《寿宁县志》及其他方志对风俗的记载相比,《寿宁待志》具有明显的独特之处。
首先,《寿宁待志》对民俗的记载虽以真实为准绳,但角度的择取具有主观性。一般志书强调客观、全面地记录民俗,而《寿宁待志》却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根据冯梦龙关注点集中载录其独特之处。如,记载寿宁丧俗时,并无如他志般言明丧礼流程,而是着重写“火葬”“停柩”之风形成的原因;状寿民服饰时,笔力集中于与别处“相反者”;同是记载端午节俗,康熙《寿宁县志》载为 “各取菖蒲艾草插门户,裹角黍祀祖先、遗亲故,饮菖蒲酒以辟邪气”[3]345,而《寿宁待志》则集中笔力记载寿宁五月初四过节及不设竞渡两种节俗,而对插艾草、裹角黍、饮酒等与他处相同的节俗,只字未提。可见,冯梦龙记载寿宁岁时节俗时,所关注的恰是寿宁民俗独特之处,表现了冯梦龙作为他乡人,对明代寿宁民俗充满新奇感。
其次,《寿宁待志》在记载寿宁民俗时,具有对民俗成因追根溯源的突出特点。如《寿宁待志》载冬月,贫儿“手必提竹炉烘火”[1]31,冯梦龙以“尝闻闽人手寒,吴人足寒,陕人头寒,北人腰寒”[1]31释之;如“端午以四日为之”[1]34,冯氏追溯原因为 “相传国初,民与兵争市肉至相杀,自是,民间先一日作节。而旧志云:避闽王死忌”[1]34。
《寿宁待志》所载风俗,展现了冯梦龙作为他乡人视角下寿宁民俗的真实特色。这种他乡人的身份,使得冯梦龙能够以超越地域局限的视野,更理性地看到寿宁民俗的独特之处。可以说,《寿宁待志》所载的风俗不仅是明末寿宁独特民俗的真实呈现,更浸润了一个渴望福泽百姓的县令对寿宁民众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