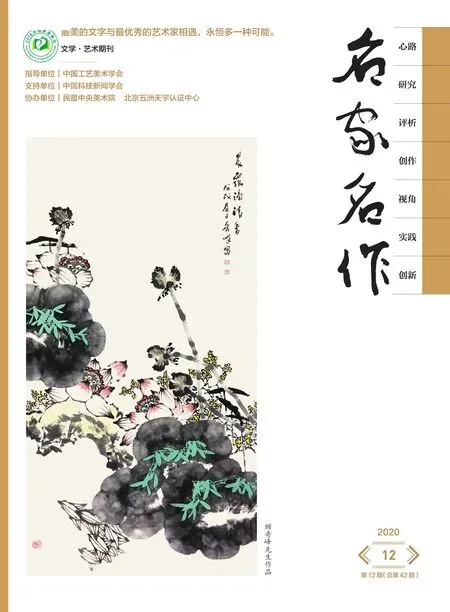论《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性成长的困境
金 哲
一、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蚀
白人通过学校、文化机构、大众传媒等手段传播并强化他们的文化价值观。这些手段建构了他们充满种族歧视的白人霸权意识:白人崇高而美丽;黑人堕落且丑陋。不幸的是,这一点被那些与自身文化疏远的黑人所认同,因此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受到了双重控制。黑人的无能表现恰恰反映了白人文化霸权的地位,这种霸权阴险而毒害着黑人的生活。通过这种方式,白人对黑人实行有效的统治。
学校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在影响学生对自己、家庭、社区和国家的看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和操纵成为社会支配者向被支配者灌输思想的有力手段。在《最蓝的眼睛》中,狄克与简的故事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文化的一个经典版本,通过学校初级课程,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某些章节的标题,白人文化为克劳迪娅·麦克蒂尔的故事提供了背景。在小说中,莫里森也把焦点转向好莱坞和流行文化作为白人展示种族优越思想的渠道。她揭示了戈宾诺的学说是如何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化形象中被具体化为身体美的表现。音乐公告牌、杂志、洋娃娃、秀兰·邓波儿的电影充斥着《最蓝的眼睛》。好莱坞强化了18世纪与19世纪种族主义的束缚,并含蓄地阐述了戈比诺的学说,即白人种族在美的方面优于其他种族;人类群体在美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永久并不可磨灭的。莫里森用秀兰·邓波和主人公佩科拉的对比来强调黑人经历的讽刺。由于渴望成为邓波,佩科拉否认了自己黑人的身份。一个黑人小女孩渴望获得一双蓝眼睛,而她内心深处对社会的恐惧感慢慢被这种幻想所超越,最终在她的成长历程中埋下邪恶的种子。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黑人女性波莉同样对于成为白人影星的幻想越发强烈。在《最蓝的眼睛》中,对非裔美国人与黑人女性特定历史的否认,主要是因为大众文化产业对白人流行文化与形象的普遍湮灭,或者说是对这一现象的忽视。从电影之中,波莉吸收了种族主义者对于女性美的看法,在她把电影中白人的身体美评判为美的唯一标准时,波莉剥去了自己的民族思想,束缚了自己对黑人种族的认知,并逐渐积累了幻想心理。同时,虚幻的电影给了波莉一种无法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心理满足感。波莉用好莱坞银幕上的白人女性取代了年轻时彬彬有礼的自己,而对自己黑色肤色的否定也增加了她对自己女儿佩克拉的厌恶,也间接导致佩克拉成长过程中的悲剧。
二、黑人身份认同的缺失
对于黑人女性而言,黑人社区构成了她们追求自我身份认同的归宿,对她们构建身份认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刻画了多个黑人群体中的角色,旨在关注黑人群体内部的关系对黑人女性成长历程中的影响。
在小说中,主人公佩克拉生活在一个深受白人价值观影响的社区。在这种个性严重扭曲的环境之下,肤色较浅的黑人会被认为优人一等,更容易被主流文化所接受,而肤色较深的黑人会受到歧视和排挤。当黑人在社区中得不到认可时,他们开始在自己的身体里塑造白人的一些特征来寻求安慰。杰拉尔丁是一个皮肤较浅的黑人,与其他黑人时刻保持距离。在她眼中,佩科拉是肮脏、无知与贪婪的化身。她屡次对佩克拉施加拷打,把责任推到佩克拉的身上。皂头牧师基于优化血统的目的,对后裔们的学业与言行举止都予以干涉,以便摆脱黑色人种的身份。黑人对自己固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摒弃源于他们固有的奴役心理。小说中悲剧家庭的命运变迁有一个分界点,当乔利与波莉北迁之前,两人拥有过一小段亲密时光。然而当迁移至一片被白人统治的区域后,两人各自的心理都受到了影响。波莉越发想从他人的赞美肯定中获得自我认同,一方面被更加复杂多样的外部信息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主流意识进程即白美黑丑,也导致波莉的防御心理被攻破,加快了白人主流价值观的内化。另一方面波莉的北迁之旅并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转移,也代表着自己即将摒弃自己的种族根基与传统。例如波莉慢慢憎恶黑人家庭用的盆子,意味着她开始放弃带有黑人特色的生活方式。脱离黑人固有传统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将是彻底抛弃了种族认同感,打破了植入在种族根基的防御系统,进一步巩固了白人种族权威意识。佩克拉的成长过程也遇到了黑人种族内部冲突的阻碍,而这种内部冲突源于他们对白人文化的痴迷与对白人价值观的崇尚。由于黑人社区内部深受白人文化的影响,他们对自己肤色以及黑人身份的认同感日益缺失,致使对身边黑人的憎恶感日益强烈。而身为土生土长的黑人女孩,佩克拉不但未能从社区获取任何温暖与关怀,还遭受到社区内部的不公平对待与无休止的歧视,也让佩克拉的成长环境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黑人女性摆脱困境的反思
在《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在白人统治的规训机制下,逐渐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沦为一个个被顺从的躯体。但是小说中依然不乏有像克劳迪娅一样敢于抵抗白人种族势力,在白人主流文化圈中勇于发声,维护自身种族自信的黑人女性。在佩克拉放学后被黑人男孩语言欺辱时,是弗里达上前保护佩克拉并驱赶了欺负她的黑人。与佩克拉截然相反,克劳迪娅对白人明星秀兰·邓波一点都不感兴趣。在小说中,克劳迪娅亲手毁掉了圣诞节收到的蓝眼睛、白皮肤的洋娃娃。而她毁掉的并不仅仅是一只洋娃娃,其本质上是一种抵抗白人种族话语权的标志。《最蓝的眼睛》所讨论的正是黑人种族面对整个白色阶层压迫欺辱时究竟用什么去抵抗。从二元论的角度上,当具有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特征的白人在自己的主流文化里确定衡量美的标准时,它是合理的;然而当上升到另一个层面,变为判断所有有色人种包括黑人的价值观与美的标准时,它就转变为不合理且扭曲的价值观。
在小说中,克劳迪娅对洋玩物的拆毁是白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下少有的黑人民族意识觉醒。克劳迪娅从来没有在圣诞愿望里奢求过洋娃娃,而她真正渴望的圣诞礼物是静坐在厨房的角落里,品味着仙桃,身上布满丁香花,欣赏大伯给自己演奏的小提琴音乐。克劳迪娅像她母亲麦克迪尔一样,欣赏黑人的布鲁斯音乐,喜欢倾听艰辛与苦楚岁月的歌曲。母亲麦克迪尔即使面对社会的困苦不时发一些牢骚,但她依然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仁慈的麦克迪尔母亲在佩克拉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时,不仅给予了她温暖的家,还在佩克拉经历初经之际,清洗她的衣物,扮演了其母亲的角色,这让佩克拉感受到来之不易的母爱。作为黑色种族文化的继承者,麦克迪尔母亲是一位和善的母亲,她的血液里依然保留着黑人人性的美。在她的影响下,两个孩子克劳迪娅与弗里达也绝没有因为自己的肤色而感到自卑。麦克迪尔母亲对于后辈的关怀、对黑人音乐的继承,都凸显出她捍卫黑人种族地位的决心。麦克迪尔一家人对于白人统治话语权的挑战,在当时的大环境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四、结论
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通过黑人女孩佩克拉的凄惨遭遇以及悲惨的结局,向读者揭示了种族主义话语权与白人统治意识形态依然潜藏在黑人的思想领域当中。虽然奴役制度早已废除,法律也明令禁止种族迫害,表面上看白人对于黑人的统治阶段已经结束,但黑人们仍然未能得到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以及经济能力,仍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之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白人对于黑人的思想统治,具体表现在美国大众传媒以及社会所引导的白色人种价值体系与价值观。在白人对黑人种族扭曲的精神压迫之下,黑人种族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白人的种族认同。这种认同的不平等性导致的后患就是社会结构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美国社会的长远发展。
综览整篇小说,莫里森力求表达的,并非是让黑人能意识到白人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强势进而做出妥协,而是想唤起黑人自身意识的觉醒,并呼吁黑人能够理性判断,不盲目崇拜,能够保留自身的种族文化,在面对扭曲的价值观入侵时,能够维护好自身独有的种族身份。黑人群体更是需要团结一致,增强黑人种族文化认同感与种族自信心。然而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黑人群体内部里的相互歧视与彼此冷漠。佩克拉成长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在白人文化冲击下家庭成员的漠视以及黑人社区的歧视造成的。莫里森对佩克拉的遭遇以及黑人群体的冷漠深恶痛绝,甚至感到绝望。然而正是有了像麦克迪尔一家一样充满对自身种族文化的自信,能够维护好自己黑人身份的角色,让反种族歧视道路重现曙光,这也是《最蓝的眼睛》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