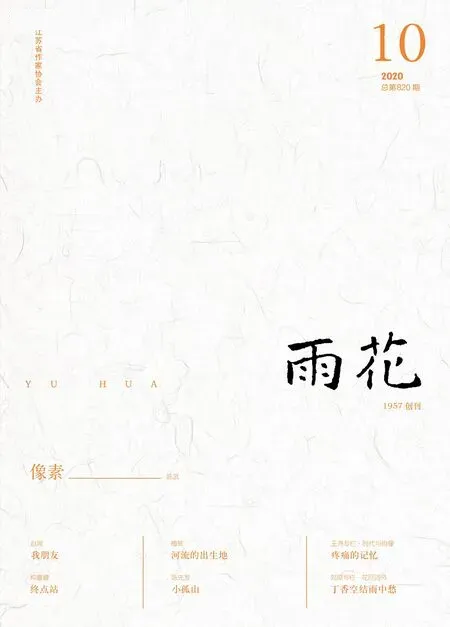山水与人的解放
这一年,时节刚到五月,广州的酷热便像山火一样将人使劲烘烤。这种情形,数年未有。广州即便到了夏季,那种热也总是不乏潮湿,很少有干燥如火之热。再加上年初新冠病毒肆虐至今,人人深居简出,坐在家中,犹如困兽。
诗人黄礼孩来信息,相约去从化山中一聚,如同缝隙中有了光线,我立刻应允。
当天清早,在天河公园附近,和诗人世宾、黄金明汇合,一路谈天说地,看着窗外的楼房渐渐低矮,直至一个多小时之后出现了绿色的田野,方才感到城市的控制开始松动。路过山脚的一个村落,传言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后,他的后人为避战乱迁到了岭南,先在南雄珠玑巷,后迁至广州从化钱岗,也就是眼前的这个村落。历史的烟云细节无从考证,但这个传说意味深长,这是一种身份的寄寓,是对历史的一种想象性的联系与延续。
东南沿海对于大宋王朝的最后眷恋,也是边缘对于中心的一种永恒渴念。这种渴念变成了挽歌,在隐秘地传唱。我这个从西北内陆到东南沿海的人,时不时总能够听见,每每听见,情绪总是变得绵延而恍惚。
车向山坡上驶去,爬上了一个陡坡,转弯后,停下。我下车活动一下身体,看到一座小楼守着一个小广场,一只疲惫的狗躺在树荫下。
保安走了过来,我们说:“是莫先生的客人。”保安点点头,让我们在原地等着,会有车来接。因为我们的小轿车底盘太低,没法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
等待之际,我独自迎着一侧的山峦走去。山峦仍在远方,那是等会要去的地方。但进山之后便不能眺望,只有站在山下,才能看清山的轮廓。我的前方,有一道低矮的堤坝,不确定在它的后边有什么。每走一步,堤坝与远山之间的空间都越来越开阔,直至走在近前,发现那巨大的凹陷,是一片近乎枯竭的巨大湖底。近堤坝一侧还有浅水,其余则如同茂盛的草原一般,长满了葳蕤的绿草。从堤坝到湖底少说也有十数米,因此完全是山上苍鹰俯瞰草原的视角。
一辆车停在远处,犹如甲虫般渺小。两位女子从中走出,想在这年轻的草原上漫步,结果滩涂松软,一位女子陷了下去,另一位女子赶紧去拉,两人嘻嘻哈哈的声音回荡在空间之中。目睹这样的场景,我心头为之一振。被新冠病毒压抑数月的情绪忽然松绑,我摘下口罩,这个柔软的嘴巴刑具。我和世界之间不再有阻碍。
在远山和转瞬即逝的笑声中,平远空旷的境界从中抽象了出来。我想起了宋代马远的名画《踏歌图》。《踏歌图》中,远景是奇峰耸立,近景是山间小路,上边行走着几位神态各异的人,他们手舞足蹈的样子,令人不免想象他们在共唱着一首歌。“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画上的诗句给予了提示,但我总觉得多余。此画的高妙之处,在于画面的中心是远景与近景之间的一片留白,那是无尽的虚,也是无尽的意蕴所在。
画于南宋的《踏歌图》改变了北宋绘画中的“远观其势”,构造了一种“近观实质”,逃出那种全景式的近、中、远三景,仅选近景和远景来呈现。这已经不仅是绘画,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我们更愿意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世界又是如何呈现自己的?《踏歌图》激起的追问我一直难忘,此刻又被激活了。那《踏歌图》跟我眼前的景分明是一样的:远景是山的寂寥清寒,近景是人的欢歌笑语。
矛盾吗?冲突吗?好像又不,好像又非得如此不可。
留白何在?在这湖底上方的空中,那里曾经是水的世界,现在已经失去了踪迹。那踪迹只在望者的心间。
我是一个望者,一个以望作画的人。
我又一次听见了大宋的幽微回响。既然如此,宋就没有真正消亡,宋比元更持久。从这个意义上说,挽歌比杀戮更持久。
车来接了。
车驶进了山间小道,每到转弯之际,都令人心脏收缩。容易晕车的人,怕已经开始忍受呕吐的冲动。
手机信号格开始变弱,直至没有了信号。这对于手机的奴隶们来说,并没有感到自由的快感,而是陷入了茫然与焦虑之中。
前面的山坳里,停着几辆车,看来是会合地点。我们下车,有几位朋友坐在石头上休息。有人说莫先生上山了。我坐了一路车,也想上山走走,活动下筋骨,看看山内风景。我和几位朋友沿着山道,慢慢向上走去。浓密的绿色植物让人心情愉悦,不时还能看见鲜艳的野花。我忽然意识到,假若没有电子产品,在生活中要经常看到这么鲜艳的自然色彩,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约走了半小时,就开始返回。俯瞰谷底,发现有些树木之高大是超乎想象的,它们几乎有数十米高,生命的生长性得到了完美体现。我在看这些树的时候,朋友给我介绍了莫先生的计划:将这上千亩的地方,做成一个让人可以安心投靠的栖息地。比如,有养老院,有学校,有度假地,类似一个社区,人们居住在这里,重新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这倒是一个宏大的想法。
走回到山坳,人都齐了,莫先生也回来了。他身形瘦小,行动灵敏,眼镜后的目光时常有很明亮的色泽。那个宏大的想法就在他瘦小的身体内滋长,驱动着他。简单握手之后,他就招呼大家去吃饭。几辆车组成的车队,在崎岖的山路上跌跌撞撞,缓慢爬行,然后到了一个山间平台。那里烟火缭绕,原来是烧烤炉已经支起,牛羊肉块、鱼类和各类蔬菜被穿在竹签上,只待放在火上烤。
众人坐在小方桌前,便有山泉沏的绿茶端上。在此间隙,莫先生说了自己的想法。原来他是以做教育为本的,认为有六种教育对人的生命至关重要:“艺术陶冶人,体育健康人,科技发展人,生活培育人,心育愉悦人,生态影响人。”而他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融汇在一起,而这一切的核心,他称之为“天人山水”。他说完之后,还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个谦虚的玩笑。他说,他叫莫道明,就是讲不明白。我暗暗想,他的名字很奇特,有多重解读:要说讲不明白,自然大道也是讲不明白的。
将生命的能量用在改造世界上,最直观的莫过于与自然的斗争。将山丘夷为平地,将湖海填成平地,逆造化之力而行动,是人的力量的巨大展现。莫道明先生打算把余生用在这上边,他的雄心壮志像是生命内部的大海,波涛汹涌,时刻准备溢出他身体的堤坝。大自然是需要发现的,没有人的发现,大自然只是沉寂在那里,什么也不是。是人的目光照亮了自然,进而是人的行动改造着自然。在这个过程中,难道自然就没有改造人本身吗?当然,这是相互的,人也被自然所改造。人终究是自然的产物。
烧烤的食物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大家一边吃着烧烤,一边继续听着莫先生的讲述。这是他理想的提前实现,我们也在他的言语中想象着这里的未来。
他提到自己为了规划这块地方,曾去印度的一个实验社区考察。那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社区,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进入。他在里边还看到了不可描述的奇迹。奇迹,是个人化的,在这里恕不具体提及。
我没有向他求证具体的社区名字。我想起了印度建立于1968年的国际社区“曙光城”,那里有着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两千七百多位居民。它的愿景是成为一座世界之城,让所有国家的民众都能在和平与进步的和谐中生活。超越一切教派,一切政治,一切国界,实现人类大同。在那里,人们尝试着摆脱现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主流生活,探索一种更加符合自然灵性的生活。有位村民面对采访,说出了让人震惊的话:“有时访客们会感到困惑,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实现梦寐以求的乌托邦?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认为重要的不是我们没有取得的成就,重要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醒来都愿意继续尝试。”
也许,生活就在于这种不断的尝试。
莫先生规划的社区与曙光城有无关系,这并不重要,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试验对现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有所矫正。
现代生活已经被批评得太多了,现代生活当然不是一种完美的生活,但古代生活又何尝是完美的?古代人对于古代生活的怨言是如此稀少,他们反而总是在向往更加古老的时代,这其中的意味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生活需要矫正,古代生活就不需要矫正吗?如果古代生活没有被矫正,何来今天的现代生活?置身生活内部而尽力对生活进行改造,这本身就体现了生命的一种伟力,而生活以及无数生活构成的历史也需要这样的改造,以实现更多的可能性。
历史已经没有可能性,也正因此,历史在行进的过程中格外需要可能性。
吃完饭,从小平台搬到了下边一个洼地,其间有树可以遮阳。有古琴悦耳,还有年轻人组成的乐队演奏,一点也不违和。如果有人愿意上前朗诵自己的作品,也悉听尊便。众人各搬小凳,随意排列坐好,面前小桌有新鲜水果奉上。我全然放松,生出“雅集”之感。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雅集,毫无疑问,是兰亭雅集,王羲之的书法名作《兰亭序》不用多说。其实,我对《兰亭序》的内容,也是念念不忘,就对心灵的冲击而言,甚至大于书法本身。
那是一种生活美学,将日常生活的相聚变成艺术。后世相聚,仰望兰亭,也不必自卑于风骨与才华的不足,重要的是,有了兰亭雅集以及《兰亭序》带来的文化想象,中国人的每一次相聚都有了一种想象性的空间。它不是一种参考,不是一种标准,而是一个出口,让眼前的相聚不止于眼前,而是尝试着与历史相接。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兰亭序》中的这句话,极为沉痛。所幸,兰亭雅集的文化想象空间延续至今,而今天又在此玄妙空间中找到依据,并继续展开。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也是在文化想象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真正理解。人必须突破自己的狭隘与盲目,而与更大的事物构成谱系,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就像唐人张怀瓘称赞王羲之的《兰亭序》时所言:“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一个人的“神功”,依赖于“造化发灵”,实际上就是人对于造化的深沉领会。每个人都可能领会到自然造化的“发灵”,但总有人领会得更深刻、更彻底。
山间鸟鸣,与人声唱和。几乎每个人都上前发出了声音,大山默默吸纳了这些声音,永远不会吐露秘密。只有洼地的末端,有小溪在流淌,仿佛将人声转换成了水声。
有山有水的地方,确实令人感到踏实。中国古人将大自然称为“山水”,这是极具智慧的。山水,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中,构成的人文意蕴之富厚是超乎想象的。文化对于生命的塑造,于审美上最关键。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自此,智慧与仁德便是中国文化试图兼容的两个方面,并化入到中国人骨子深处的美学当中。明代影响极大的文人袁宏道说:“意未尝一刻不在宾客山水。”内在的精神被山水所俘获,竟然每时每刻都与山水关联,山水已经成为生命的骨血。清代的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把山水分了类,意味着山水对于生命的一层层渗透。
在这里不得不提中国原创的两种思想: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它们为中国人的生命样态设定了两种状态,要么“入世”,要么“隐逸”。入世是儒家的范畴,道家倾向隐逸。隐逸,太难了,甚至可以说,没有将入世作为前提的隐逸,都是对隐逸的误读。否则,为何只有陶渊明的乡野生活是隐逸,而山野樵夫的普通生活就不是隐逸呢?
就像平日里来山中,就不如新冠病毒肆虐之际来山中。这其中的滋味便包含某种精神的探询,这山便不再是土石的堆积,而成为山本身。
老子说:“道法自然。”这其中便有太多可以领悟的东西。道与自然之间并非是完全等价的事物,而是大道要向自然本身去探询。这就意味着,道不是先验的,更不是给定的,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当中。
听着音乐,凝视周遭山林水石,忽然就被融化了,仿佛那个被肉身承载的我,渐渐不再狭隘,而是与目光合一,进而与目光所及之物合一。天人合一的感觉,就是以此刻这样的感受为基础的。
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八个字:“山沓水匝,树杂云合。”这是自然景观的呈现。在这句话后面,跟着八个令我极为难忘的字:“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目与心的关系,构成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通道。这个通道并非敞开的通衢,而是藉由艺术的创造而呈现和生发的。比如山水画,比如诗,比如文章,比如音乐。唐代大诗人王昌龄《论文意》中如此谈到诗在生命中的发生:“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这个看法正好与刘勰的看法构成互补。刘勰说的是从目到心,而王昌龄恰恰说的是从心到目,要将心的力量通过目光投射出去,这个力量是极大的,是“击”,而不是“触”,并“深穿其境”。两种说法不仅是互补,也是抽象与具象、发生与发声的互补。刘勰看重的是写作在人类精神与自然能量交换过程中的大尺度,而王昌龄所说的是“写”的穿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之思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然的能量。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太能理解王昌龄所说的意思了。那是一种随时准备好的状态,如同箭在弦上,等待着一个微小的扰动,箭矢便如电射出,如果能够射中那个扰动的目标,并且洞穿扰动的原因,那么,这样的写作将会是极为有力量的,是强悍的。
人的自由为何与艺术、与写作有关,就是因为人唯有在这个过程中,才深刻理解了自然,理解了人自身。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都提醒我们要注意人本身的自然属性。我们时常会忘记这样的自然属性。马尔库塞说:“解放最终和什么问题有关,亦即和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人自己的本性与外界自然的新关系有关。”解放就是获得自由的过程。从来不曾存在百分之百的自由,人类的自由是靠着解放的过程而缓慢获得的,这种获得不是物的给予,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精神的领悟。所以,自由才是珍贵的。
当我们发现了山水的时候,发现了山水当中的超越维度——天,发现了山水当中的生命维度——人,我们就是在领悟自由,就是在缓慢地实现人的解放。
黄昏毫不迟疑地降临,日暮时分,天气没有凉爽,暑气反而被热透的土地释放出来。再风雅的集会,也会有曲终人散之际。就像永和九年那场让王羲之写出了天下第一行书的聚会,已经散场了一千六百多年,这个数字注定还要增长下去,直至文明的终结。还有更多的雅集,已经无法追溯,消失于时间的幻象当中。
莫先生没有再说些什么,在音乐声中,他应该想了很多,但有太多的话只能藏在心底,无人能说。放眼广州从化的这一片山水之地,不能说这是桃花源,更不能说这是庇护所,只能说,这里有可能实现人对自身的安放。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总和投入到青山绿水当中,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可靠的、稳固的边界。
足矣。
车出大山,手机信号重新恢复。从此一瞬起,那山水便不再是那山水。回复一些俗世信息,然后发布这里的山景照片,配上一句实实在在的文字:“逃入大山,一会儿古琴,一会儿蔡琴,好像瘟疫已经结束。”微信朋友圈的热闹开始了,有多少人渴望着逃离,正如我。
而此时,车掠过了山下的村落,那个传说住着陆秀夫后代的村落。来时,心心念念要去走走,可回时,就这样平淡路过了。
心底默念着白沙先生的诗,如同宗教信徒默念着经书上的圣文:
“江山几处堪还我,泉石边头合有人。高著一双无极眼,闲看宇宙万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