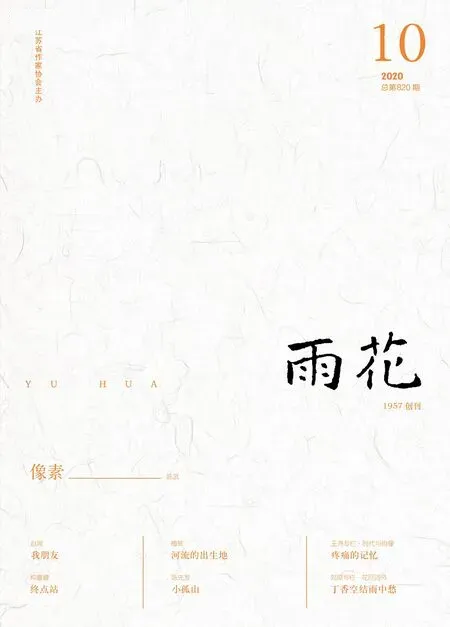我朋友
1
我朋友所在的小区翻新时拆了所有的违建,施工方为每一户人家更换了门窗,修缮了破损的墙体和路面,最后还装了几个监控探头。其他的项目小区居民都很配合,但是装监控时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自己的隐私权或受到侵犯。他们找施工方交涉,要求停止安装监控探头。施工方根本不理会,说老旧小区翻新改造是政府工程,装什么不装什么是政府有关部门决定的,自己只是按规定施工,大家有意见可以去找政府……这几户人家找到社区,刚提出自己的担心就被挡了回来。社区工作人员说,监控是市里有关部门统一规划的,市区任何一个死角都必须覆盖到位,这一点没有商量余地。
监控探头就此安装完成。它悬于小区大门的一根灯杆之上,圆鼓鼓像一颗大眼珠子(360°的覆盖范围),冷冷地直视人间。接下去一段时间居民们开始不淡定了,进出小区时总觉得有一只贼溜溜的大眼睛在一眨不眨地紧盯着自己,盯得他们全身冒汗内心发毛,忍不住想干点出格的事一般。出于某种自我防护的意识,许多人路过探头时都不自觉地把头扭向一侧,有人还额外为自己增加了一些遮挡物;女的会用一条大围巾把整张脸蒙得只剩下两只眼睛,男的或戴上墨镜或戴上口罩……有一个刚搬来不久的中年人更是夸张,每次出门前都要乔装打扮一下:戴一顶宽沿礼帽,走过探头前时故意把帽檐拉得很低,让探头找不到自己的脸;或者粘一副假胡须,脸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装扮成一名学者的模样……有一天他甚至装扮成了一个老太太,戴上一顶白发苍苍的发套,弯腰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探头前走了过去。以前大部分邻居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做什么的,见识到这一波骚操作后好奇心骤起,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一个演员……
众人面对监控探头时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不确定它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另一方面又无力拒绝它的存在。他们面对探头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奇异行为和略显夸张的招数其实都是一种自嘲之下的自嗨;好比一个人给自己讲了一则笑话,原地就把自己逗得乐不可支哈哈大笑起来了。
监控探头出现在小区居民尚未有心理准备之际,很多人躲避它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挖掘它身上可能的实用功能。然后宾利出现了。
2
宾利是一辆车,它是一天凌晨突兀地停到我朋友小区里来的。
那天上午我朋友起床后简单吃了一点东西就坐到了电脑前——忘记交代了,我朋友也是一个作家。每天上午是我朋友固定的工作时间,从上午一直要写到午饭时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吃中饭并不以饥饿程度决定,而是以一天的工作量是否完成决定;每天一千字是我朋友给自己定的工作量,正常情况下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即可完成,而只有完成一天的工作量之后他才会吃饭。当然这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遇到非正常情况那就说不准了。我朋友曾经有过从上午七点到晚上九点在电脑前坐了十四个小时且一个字都没写的经历。那天上午我朋友刚在电脑前坐下来,门铃突然响了。他起身开了门,门口站着的是邻居丁大爷。
在家呢?
大爷有事吗?
丁大爷说,不好意思!我来问一下,院子里的小车是你的吗?
我朋友有点蒙圈,问,什么车啊?
你出来看一下吧!
我朋友所在的小区不大,一共就三幢楼,呈U字形排列。我朋友住在U字最底部那幢楼的一楼。那天,他跟着丁大爷出了单元门拐过楼道后,果真看见一辆小车沿着墙边静静地停着。就是说,这辆小车是停在我朋友家的山墙边上的。几个邻居看见他就问,是你们家的车吗?
不是啊。我没有车的。
邻居们就抱怨,这是谁家的?真不像话!把车停到这里我们还晒不晒衣服了?
我朋友所在的小区很小,可利用空地有限,也就U 字中间那巴掌大的一点地儿。其中靠近大门位置是小区主要的进出通道,基本没有利用价值,剩下的U 字底部的一点空间则被一些大爷大妈拉上了晾衣绳,一没事就把家里被褥拿出来晒,冬天晒夏天也晒,空地就被被褥、衣服、床单给占据了。当没有邻居晾晒衣服被褥时,偶尔也会有人把车子停在这里,基本都是某户人家的亲戚朋友过来临时停一下,过不了多久就会自行离开。多年来大家相约成规相安无事,所以今天看到有一辆车突兀地出现在小区里都觉得恼火……
邻居们还在叽叽咕咕地对着这辆车发泄着不满。我朋友的注意力却被这辆轿车吸引了。虽然我朋友自己没有车,但是对各种品牌的车子并不陌生:奥迪、讴歌、现代乃至中低配置的宝马、奔驰等等。但是眼前的这辆车却有点特别。首先它是一辆新车,新得无与伦比,几乎是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车身光洁锃亮一尘不染,轮胎上的纹路清晰饱满,看不出有任何磨损的痕迹;车型的设计尤为新颖,线条流畅动感十足,即便静静地停在原地,也像在平稳而快速地前行……车头上的金属标志是一只展翅的雄鹰,中间是一个红色的字母B或是数字8,做工精致鲜艳夺目,仿佛当这辆车向前疾驶,那只鹰就会展翅飞去……
车子前后都没有牌照,不是临时撤下的样子,应该是还没上牌照……
一辆轿车突兀地出现在小区,仿佛一根鱼刺扎进了食道,扎得一众邻居百般不快万般不适。他们楼上楼下挨家挨户地询问,一圈问下来,没有一个人承认是自己家的车。大爷大妈就去找社区工作人员反映情况。社区工作人员过来看了一圈也束手无策;车主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没办法通过有效的渠道联系到车主,同时车子也没有牌照,基本堵死了通过车牌寻找到车主的可能性。工作人员就说,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我们也没办法。
邻居们急了,那我们怎么办?
社区工作人员说,要不你们报警吧,让派出所查一下监控。
一语惊醒梦中人。有人掏出手机报了警。十多分钟后派出所的管段民警小宋和一个辅警到了。小宋和大家都很熟悉,一见面就大爷大姐地瞎打招呼;他把大爷叫大爷,称大妈为大姐,你说说这情商!大清早地晒太阳呢?他笑眯眯地问。
大爷大妈就喊,小宋快来帮帮我们,七嘴八舌地把事情诉说了一遍。
小宋绕着车子观察了一下,摇头,这没法查。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不是有监控探头吗?你们查一下监控不就一清二楚了?
小宋笑眯眯地说,大爷大姐你们也真会开玩笑,这点小事就报警,当我们整天没事做呀?再说了,监控虽然装好了,现在还没正式开通呢。转脸对一旁的中年辅警说,老胡,我们走。
说完甩手走了,留下一地蒙圈的群众。老半天才有人反应过来,一蹦三丈高地朝小宋的背影喊,没开通怎么不早说!一想到自己跟一个假探头斗智斗勇好几个星期,每个人都很愤怒。
这天虽然最终没能解决这辆车的问题,但是缓解了众人因监控探头产生的紧张情绪,众人不咸不淡地又发了一阵牢骚后便偃旗息鼓了——与大多数时候一样。
3
每天下午两点一过我朋友就烦躁起来,时间越往后这种烦躁感越强烈,直到等来一个邀约饭局的电话——
喂!还在忙吗?
还好。
晚上没事一起坐坐吧!
——只有等来这么一个电话,困扰着我朋友的那种烦躁感才会烟消云散。每天一场饭局既是他的病也是他的药。这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已经记不清了,却像鸦片一样在时间中延续下来。无论如何,饭局对于每一个城市人来说都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聚会,它是脆弱的生命损耗了一天之后自我充电的机会;一群朋友围坐在饭桌前,喝点酒聊一聊人生苦短儿女情长,间或互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再犯个浑抖个机灵啥的。所以饭局从来不是几个熟人聚在一块儿吃一顿饭这般简单,它是人们为自己生命续费或充电的一种方式。
电话一般会在下午四点之前打来,而我朋友的期待从中午之后就会展开。如果电话四点后才打来,即便再想去他都会委婉地拒绝——迟到的邀约基本上属于补缺性质,这对于被邀请的人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何况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止一个“续费点”,除了饭局还有酒吧、KTV、茶馆等等,他并不是非此不可。
今天的电话四点半才出现,在此之前我朋友暗暗发誓,下面无论谁来电话他都会一口拒绝的,然后电话就响了。是老陈。
老陈是一个摄影师,他们是在一个摄影展上认识的。
老陈啊!有事吗?
是这样。我有一个亲戚从北京来,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我朋友一愣,说,你和亲戚吃饭是家宴,我一个外人不便叨扰,我们还是另外再找机会聚吧。
老陈说,别呀!我这个亲戚也是艺术圈的,跟你还认识。
我朋友好奇起来,他也是写小说的?
不是,她是电影导演。
我朋友快速地在记忆中搜索了一下,说,我不认识北京的导演啊!他叫什么名字?
老陈哈哈笑起来,她在我边上,不让我说。你来吧,见了面不就知道了?
我朋友六点准时到达饭店,老陈和北京来的导演已经到了。导演竟然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笑眯眯的一脸佛相。看见我朋友进来,没等老陈介绍便躬身迎上来,是赵老师吧!我是兰艺。
兰导好!
今天吃饭的人不多,就老陈两口子和这位导演,另一个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我朋友进来后她一直在埋头玩手机,女导演捅了她一下,她才放下手机站起身叫了一声:赵老师好!看样子是兰导的助理。我朋友注意到她的个子似乎很高。
服务员开始上菜。几个服务员轮番上场,极短时间内一桌菜就上齐了。老陈拿着一瓶白酒要给我朋友倒酒。我朋友伸手捂住杯子:昨天喝多了到现在头还晕,就不喝白的了。
老陈说那不行,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边说边用瓶口顶着我朋友的手想把他的手挑开,我朋友死死捂着不肯就范。
在一旁的兰导说,要不就给赵老师喝点红的吧!说着便拿起桌上一瓶红酒走过来给我朋友倒了小半杯,回到自己位置上却没给自己到,端起面前的半杯茶水说,我以茶代酒敬敬赵老师!
我朋友说,不对啊兰导,酒桌上没有这道理吧?
兰导说,不好意思!我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不能沾酒。我朋友还没说话,身边的老陈端起酒杯说,我代兰导先敬赵老师一杯,一仰头把一杯白酒“咕嘟”一声灌下去了。我朋友只得喝了这一口。
整个席间兰导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朋友瞎聊,话题宽泛。有一段甚至聊起了中国足球。
开始我朋友还惦记着要跟导演多聊聊,记得老陈在电话里说她和我朋友以前相互见过,但是兰导始终不提这个话题,我朋友也不好硬聊。也许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例修辞,是别人对你的一种客套,在乎你就傻了。一念至此我朋友就放下身段专心喝酒了。我朋友后来瞄上了女助理。他一直对她的身高很好奇,借一次敬酒的机会问她有多高,女助理调皮地说,赵老师愿意猜一下吗?
我朋友那时已经有点晕了,浅薄地问,我猜中了有什么奖励吗?
女助理一歪脑袋想了想:那我们打个赌,如果你猜中了我喝一个满杯,如果你猜错了你喝。
我朋友说,行啊!
兰导在一旁笑眯眯地对助理说,别没大没小的!
没事,我们就玩个游戏,不会让他喝多的。
兰导微笑着没再说话。
女助理站起身抓起酒瓶倒了一个满杯,然后把酒杯放在转台上静静地看着我朋友。我朋友有点紧张了,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说,能请你站起来让我目测一下吗?
女助理大方地站起身,还离开座位走了两步,然后落座。
我朋友思考了一下,脱口道,一米七六。
女助理的脸上显出一丝诡异的笑意,我朋友顿觉不妙,刚要改口,一旁的兰导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鼓掌,赵老师厉害!赵老师太厉害了!
女助理疑惑地看了兰导一眼,微微一笑站起身,我输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兰导使劲地鼓掌,好!好!端起水杯招呼大家,我们一起喝一口吧!
女助理拿起酒瓶走过来添酒时,悄悄把嘴贴在我朋友的耳边说了一句,我一米八二……
我朋友顿时尴尬不已。兰导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情绪,笑着说道,孩子不懂事,赵老师见笑了!
我朋友说没事、没事。突然反应过来说,她不是你的助理?
兰导说,这是我孩子。看了她一眼补充了一句,她是三瓶红酒的量。
这一句话让我朋友顿觉人生无趣,硬着头皮没话找话道,兰导那么年轻孩子都这么大了,好福气啊!
兰导娇笑道,快五十了,不年轻了。赵老师孩子应该也不小了吧?
我朋友说,我没孩子,停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我没结过婚。
兰导面露疑惑,这么些年怎么不找个人呢?
我朋友叹了一口气说,也不是刻意不找,最初觉得还年轻,玩心太重,等反应过来已经晚了,也可能是错过了本该遇到的某个人,然后就一路被时间诅咒了……
这个话题似乎激起了兰导的兴趣,侧身问我朋友,赵老师在南京大学读过作家班是不是?
我朋友说,没错,又半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出于虚荣,我在公开场合一般只称自己是南京大学毕业。
那2005年4月28日那天下午的事你还记得吗?
我朋友一愣,这我哪能记得呀!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是周四。下午你们作家班有两堂计算机课。任课老师叫姚松。你们两点钟上课,四点钟下的课。你大概四点二十分左右出的汉口路校门。你那天上身穿一件黄色长袖T恤,下身穿一条旧牛仔裤,脚上穿一双白色旅游鞋;牛仔裤右边膝盖处已经破了一个窟窿。出了校门后,你沿着汉口路向东走,正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路上的行人不多,你走得很慢。那时的汉口路两侧有一些旧书摊。你在一个旧书摊前逗留了一会儿,没发现有自己喜欢的书就离开了。刚走出两步,在旁边书摊上看书的一个女学生突然追了上来问,同学你是南大的吗?你停下脚步说,是的,有事吗?女孩儿说,我在那边一个书摊上买一本书,差五块钱。我能不能用南大的菜票跟你换五块钱现金?你就给了她五块钱却没要她的菜票;你是走读生,上完课都回家吃饭,所以菜票对于你没有意义。女学生似乎有点过意不去,非要把菜票塞给你……
我朋友惊讶地问,这事你从哪儿听来的呀?
你先说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朋友挠了挠头,这我真的不能确定。不过有一个点倒是属实,我在校的那几年南大校门口的确有一些旧书摊。我那时穷,买不起新书,所以经常会逛逛旧书摊淘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书。至于你说的那个女生拿菜票换现金的事我记不清了,只依稀有点印象。你既然说得这么具体,应该是真的吧!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兰导:你怎么不关心那个女生究竟是谁呢?
她谁啊?
4
这顿饭一直吃到快九点半才散。和兰导一行分手后,我朋友没有打车,沿着大街向前走着。这天他还是喝多了,主要是在饭局的后半部分他与兰导的女儿较上劲儿了,他不相信一个娇弱的女孩子会有三瓶红酒的量,跟她连干了三大杯,兰导拦都拦不住……
夜晚的大街空旷安静,街道比白天显得宽了不少。偶尔有车驶过,会在空旷中溅起一阵轰响,汽车过去后又迅速熄灭了。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朋友进了一条地下过街通道,他要到街对面去。沿着阶梯刚下到地下就听见有歌声传来,拐了一个道口后看见了一个卖唱的小伙子;小伙子用一个移动音响放着伴奏,自己举着麦克风卖劲地唱着,周围还围着三五个听众。我朋友本来要拐向另外一个方向的,也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竟然放弃了原路线,循着歌声走了过去。让我朋友感兴趣的一点可能是小伙子唱得实在太差了,要嗓子没嗓子要乐感没乐感的那种。人打扮得倒是挺文艺的,一身的牛仔衣,一头长发,精瘦精瘦的。如果不唱歌还挺给人好感的,可是一亮出嗓子那一切都不对了。这种水平的歌手也能出来骗钱?这着实令我朋友不快。
我朋友走到近前时恰好一首歌曲结束。围观的人纷纷鼓掌,有人还掏钱往他脚下的一个纸盒里扔,唱歌的小伙子礼貌地欠身致谢。一圈互动结束后,小伙子重新举起话筒:为了感谢大家,下面我再演唱一首《掌心》。众人再次鼓掌,前奏响起,小伙子把麦克风移到嘴边,略一运气刚要张嘴,我朋友大叫一声:等等!
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到我朋友身上。小伙子错愕地看着他,把话筒放下了。你好这位先生!有什么事?
我朋友说,我能不能点歌?
小伙子迟疑了一下,解释道,我的曲库不是很全,你要点什么歌?
《天堂》。
这歌不太好唱,要不你点一首别的吧。
就这首。我朋友缓了一口气接着说,我点的歌不是要你唱,是我自己唱。
小伙子疑惑地问,你想在我这儿唱歌?
是的。
小伙子面露难色,大哥我是靠这个吃饭的,别挡路好吗?
一股酒劲冲上脑袋,我朋友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拿在手里“啪啪”甩着响儿,一百块钱唱一首,你就说干不干吧。
话音未落,小伙子一把把钱抓到了手中,快速把话筒塞到我朋友手上了;生怕他不接,话筒塞进手中后还用手包住我朋友的手用力握了一下,另外一只手顺势摁响了前奏……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嗯安),碧绿的草原,那是我的家……
一开始我朋友稍显拘谨,还唱错了两个滑音。唱到副歌部分时人已经完全放开了,最后只用了一口气便完成了难度最高的哼唱部分。
一曲歌罢掌声骤起,众人一边鼓掌一边叫好。一对年轻的情侣显得尤为激动,女孩儿站在原地一蹦一跳的,扭头跟身边的男朋友说了一句什么,跑到我朋友身边求合影,男朋友冷冷地举着手机。我朋友就对女孩儿说,要不把你男朋友也叫上吧!
女孩子说别管他。朝男朋友喊,快点拍,多拍几张。
在我朋友和女孩儿摆姿势准备拍照时,卖唱的小伙子乘机把话筒从我朋友手中拿走了。拍完照女孩儿兴高采烈地回到男朋友身边,这边卖唱的小伙子举着话筒说,感谢这位先生为大家演唱,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爱情歌曲《心雨》……
拍照的女孩儿喊了一声,我们不要听你的,指着我朋友,让那位大叔再唱一首吧。
她的提议引来围观的人一致赞同,对!让他再给我们唱一首。
卖唱的小伙子蒙了,站在原地无比尴尬。我朋友顺势剥下他手中的话筒,举着话筒对大家说,谢谢你们鼓励和支持!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天路》。
大家热情鼓掌。小伙子脸色不好看了,杵在原地没动弹。我朋友举着话筒准备开唱,等了半天发现没有音乐,转过头对小伙子说,麻烦给一下音乐。
小伙子满心不情愿地打开了音乐,我朋友咬着前奏最后一个音唱起来:清晨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第一句便博得了一个满堂彩,然后越唱越来劲,此前觉得难度较大的段落也能轻巧把握,到最后几近忘我状态,所有的现实困厄、喜悦甜蜜都远去了,只有音乐从灵魂中升腾并弥漫。围观的人被我朋友的情绪感染,随着节奏齐声高唱,歌声像一只肥胖的野兽在地下通道里四处乱窜,余音四溅。
那天我朋友一连唱了三首歌,感觉像开个人演唱会一般酸爽。围观的人最高峰时有二十多个,黑压压的一片。等唱到第三首时,卖唱的小伙子说什么也不让我朋友唱了,给钱也不行。他快速地收拾了一下,提着音箱就走。走出很远了,我朋友发现地上收钱的纸盒子他没拿,就朝他喊,你的盒子没拿,你的钱没拿。
他走得更快了,一溜烟地拐过道口,消失了。
围观的人还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鼓励我朋友继续再唱,清唱。我朋友却突然没了兴致,掉头离开了。
5
这天晚上是几点钟到家的我朋友已经记不清了,从地下通道出来后酒劲上来了,刚开始还有点意识,后来就彻底晕了……等他从睡梦中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他是被窗外唧唧喳喳的嚷嚷声吵醒的。忍着剧烈的头痛打开窗户,发现一群邻居围着那辆宾利车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我朋友好奇地问了一句,大家伙儿干吗呢?他的意思是如果没事就别在这儿瞎吵吵,耽误自己睡觉。
邻居七嘴八舌地说起来,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我朋友好奇起来,穿上衣服走了出去。原来那辆崭新的宾利车不知被谁砸了。现场满地的碎玻璃,几乎所有车灯都被砸了,车身更是凹凸不平,靠外侧的前轮胎也瘪了,下跪一般瘫在地上……
我朋友问,谁干的这是?
邻居说不知道谁干的。早上一出门就发现车变成这样了。
虽然没人承认是自己干的,我朋友猜大概率还是小区里的某个(或某几个)邻居所为。原因大概是看着不顺眼。想想也是,自己小区的车都进不来,某个不自觉的家伙招呼不打一个就偷偷把车停到这里来了,的确让人心生不快。还是一辆宾利。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自己不痛快就把别人的车砸成一堆废铁肯定也不厚道。
我朋友说,这车坏成这样车主该心疼坏了。这可怎么是好?
邻居说,你是作家,你给大伙儿出个主意吧。
我朋友说,依着我还是得报警。
几个邻居一起说,监控还没开通,报警也没用。
我朋友说,报警不是要找出肇事者,而是要让警察想办法把车给拖走。总不能永远停在这里吧?
邻居热议起来,有的赞成报警,有的认为反正不是我们的车,被砸活该,管它呢!
看他们的样子一时半会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我朋友就回去继续睡觉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非常急促没礼貌的那种,有仇似的。我朋友没好气地问,谁啊?回答他的是更加激烈的敲门声。我朋友气急败坏地起来拉开门张嘴就要骂,一看见门外的人立刻怂了——门口站着三个警察,除了小宋另外两个不认识。三个警察神色凝重,其中一个领头模样的问,你是某某某吧?
我朋友说是。
他看了我朋友一眼,请你把衣服穿好,跟我们走一趟。
我朋友彻底蒙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小宋堆起一脸笑意道,没什么,请你去问个事,一会儿就好。
小宋这一说我朋友稍稍放松下来,返回房间穿好衣服。不过临出门前他还是耍了一下小聪明,装作找不到钥匙的样子对小宋说,我的钥匙找不到了,去你们那时间长不长?时间如果不长门就不锁了。
小宋淡淡说了一句,无所谓。
我朋友就不知道该如何判断了。
那天我朋友进了派出所后,三个警察旁敲侧击跟他瞎聊,一副你已经犯了事你自己心里有数的架势,我朋友被唬得心里像有十五只吊桶打水……脑子里飞快检讨了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哪里犯了什么事儿,一点一点地在记忆里抠,把自己从小到大干过的所有不着调的事情都过滤了一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心里一动,忽然想到,该不会遇到冤假错案了吧?此前媒体报道过多例这一类的案情,最惨的一个人被关了近二十年。我朋友就怕了,觉得自己坐几年牢倒也罢了,万一被枪毙了那就太不划算了,自己连婚都没结过……然后各种伤心纷至沓来,最让他担心的是如果真被枪毙了,自己生前常用的QQ、微信、微博、邮箱会落到什么人的手里呢?他们会偷看自己的各种信息吗?会向外散播吗?我朋友吓坏了,浑身颤抖涕泪横流。就在我朋友即将崩溃之际,警察亮出了底牌。原来他们把我朋友抓来是为了那辆被砸的宾利车。简单地说,他们认为是我朋友砸了那辆宾利车。证据是监控录下的一段视频。他们后来给我朋友看了那段视频。在视频中,我朋友拿着一个榔头对着宾利车一顿猛砸,最后还跳上车顶,用一只脚使劲跺着车顶棚……
看到这个视频我朋友整个傻了。虽然他觉得这事不应该是自己干的,但是监控实实在在放在面前——这显然是自己小区的监控录下的,令他百口莫辩。也许这是自己醉酒之后在无意识状态下做出来的,只是自己记不得了。一想到自己竟然会是这样一个恶棍,他几乎无地自容……
一旁的小宋说,没冤枉你吧?
小宋的话让我朋友浑身一激灵,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小区的监控不是还没开通吗?这个视频是假的,一定是假的。
小宋冷冷地说,你们那片区域的监控昨天晚上六点正式开通的。你撞枪口上了。
我朋友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开始后悔了,后悔昨天不该去喝那顿酒。管他什么导演不导演的,跟自己有个屁关系!
小宋说,现在那辆车的车主是谁尚不明确,我们也不难为你,只要你承诺负责以后一切可能的赔偿责任,你就可以回去了。
虽然已经没有掉脑袋的危险,我朋友还是觉得心有不甘——毕竟那也是一辆四五百万的宾利轿车,真要自己赔怎么着也得大几十万上百万的,自己上哪儿弄这笔钱呀!?我朋友搜肠刮肚想啊想啊,脑海中一道闪电划过,突然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他大声说,不对!不对!
小宋不耐烦地问,又怎么不对了?
我朋友问,监控上我砸车的时间是几点?
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开始的,持续了十分零三十五秒。
我朋友的心鼓一般咚咚咚地急跳起来,颤抖着声问,鼓楼地下通道有没有监控?
小宋被他问愣了,你说什么?
我朋友说,我就想问一下,鼓楼广场的地下通道里有没有监控?
小宋说,那是公共交通要道,十年前就装了监控。没什么奇怪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朋友哈哈大笑。他记得昨天晚上自己离开酒店时已经快九点半了,沿着中山北路走到鼓楼少说也要二十分钟,然后在鼓楼地下通道还唱了两首歌,再从鼓楼走回家,无论如何自己也不可能在九点四十五分出现在小区的。一念至此,他不由得开心大笑起来,且越笑越开心。
三个警察被我朋友笑得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开心,那个领头的警察猛一拍桌子,你给我老实一点!
我朋友越发地大笑不已……
6
最后的结局很简单。警察们调出了当天晚上鼓楼地下通道的监控录像,看到了当晚九点四十五分时我朋友正在那里纵情歌唱。时间恰巧与砸车时间重叠……
数日后小宋领着一个辅警上门向我朋友致歉,说现在已经查清楚了,小区的监控因为刚开通,系统不稳定出了技术故障,造成一些小误会。现在可以确定宾利车被砸与你无关。
我朋友就问,既然跟我无关,那录像中怎么会有我出现?
小宋说这是机器故障导致的。
如何导致的?
那就是技术问题了,需要找技术人员咨询。
我朋友被气得差点笑起来,说,好吧!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宾利车被砸是事实吧?既然不是我砸的,那又是谁砸的?
小宋说这个我们还在排查,有些情况目前不方便对外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