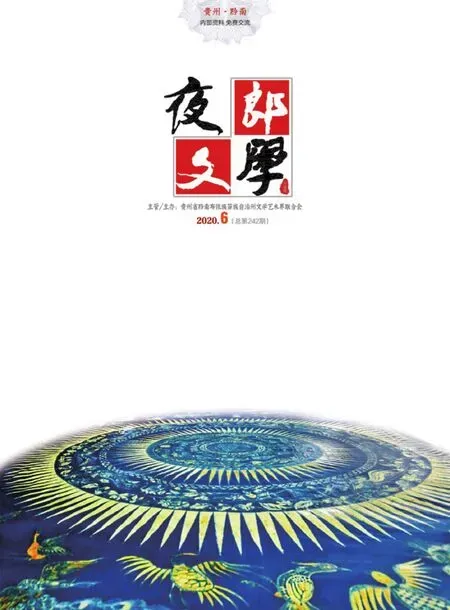乡野的秋天
郭其昌
时序流转,秋去冬来。故乡总是在时光起起落落的另一端守望着我们。
一、黑公鸡与黑母鸡
这次回家,最先迎接我的就是家里一只黑公鸡与三只黑母鸡。他们还是在门前我种下的那棵大柳树下,看见我来,便作鸟兽散了。
母亲在家里,每年都会喂有几只鸡,说是在家没事了,也有个念叨的对象。其实母亲并不吼骂它们,而是贵宾一样的待着。每早上都会抓些麦子、苞谷喂它们。鸡们也知道回报,每天都会下几个蛋。这样,小侄女的好生活也就有着落了。
几只鸡除了爱去吃邻居家的小白菜而外,其他的没什么不好。母亲说,我们难得回家,就让抓一只来杀了吃。我说算了,它们一起好好的,为什么要杀呀。母亲说,这几只鸡几乎不回家睡的,每天都呆在圈门上,说不准哪天就被别人捉去吃掉了。我说这是太平盛世的,谁还做那些捉鸡捉狗的事呢。我还给母亲说,梁大叔家那条狗因为前些天抓了张家的鸡,被主人告上门来,今天不是就被敲来待客了吗。这会一帮人正在煮水去毛呢。我说,得把这个故事讲给村人听听,看看谁还敢来抓我们家的黑鸡。母亲知道我在开玩笑,她也笑了。
第二天,我在园子里摘菜,看到我们家的黑公鸡带着三只黑母鸡,在菜地里扒得欢,还不时咯咯咯地叫着。我就知道,这是他正在讨好女士来着。自从家里把几只鸡养在一起来,这只黑公鸡就混得红光满面的,成天妻妾成群,在每一个他认为舒适的地方肆意妄为,吃穿不愁,而且还有人保命,过得与皇帝老儿无二啊。呵呵,想一想,我都向往哦。但有一点我敢保证,在家的几天里,我们家的黑公鸡一直很本份,每天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不对其他母鸡斜过眼。我亲眼看到,隔壁黄二叔家的一只红公鸡也想过来讨好几只母鸡,结果被这只黑公鸡一脚踹出老远,只得落荒而走。呵呵,还真有几下子嘛,活该你享受。
在家的几天里,都是黑公鸡叫醒我们的。离开家时,我还特别叮嘱母亲,喂好黑公鸡和黑母鸡,他们很谐的,没必要给他动刑。走出了老远,黑鸡还在咯咯地欢叫,像是在向我道别。也是啊,如果不讨好我,万一我动了吃心,它不就过不成皇帝生活了吗?
二、老花猫的幸福生活
花猫和我们一起生活有些年头了。
花猫前胸一片白毛直延伸到下颌,身材称不上健壮,在猫界应当是个苗条的女士。大约在2000年,我们都在外边工作,母亲一个人在家,觉得无聊,便养了一只黑狗与这只花猫。当年黑狗很听话,长得也相当可爱,一身黑毛油里发亮,看家本领一流,对家人极尽忠诚,所以颇得家人喜欢。大家也都没有特别注意这只花猫身上。
没过两年,黑狗不在了,家里就只剩下这只花猫。记得2002年回家时,我开始对这只花猫有了印象。正值杀年猪过大年,花猫成天就吃肥捡瘦的,正月没完就胖得肚子都差不多拖地了。大家一边笑这是一只笨猫,一边赞这只猫有福气。女朋友看见了,更是觉得吃惊,她说从未看到这么胖的猫。
过完大年,我们离开家后,肥猫便也开始劳碌起来,捉耗子一点也不含糊,一逮一个准。旁边几户人家都被她管得滴水不漏,因此她在邻里很有好人缘。有时母亲到县城来小住,她就到邻居家去吃喝。她知道,每一家都为她备有一个饭碗,随到随吃。
但花猫还是恋着家的。听母亲讲,有时干农活回来,听到家里有了人,她就从外边跑来,一边叫着一边挠着母亲的脚,十分可爱。有一次,我回家,猫也过来围着脚转,表现得格外友好的样子。母亲说,大家都在家的时候猫也回来了,真热闹。等我们一离开家,猫又到邻居家赶热闹去了。听起来多少有点伤感。
每年过年回家,花猫都会吃着肉,长胖一回,走起路一摆一摆的,煞是可爱。有一年回去过年,不见花猫,觉得奇怪,便问妈妈。妈妈说花猫生宝宝了,就在邻居黄幺公家。我们都担心花猫是不是也像往年那样吃到很好的肉,于是大家都“喵喵”在唤着。不多时,她居然出现了,还是那样可爱,但明显瘦多了。捡来瘦肉,她也吃,只是一会又跑出去了。大家都知道,她肯是去看猫宝宝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起床洗脸时,花猫居然从楼板上向我们喵喵地叫。母亲上楼时才发现,花猫在昨天夜里把三只还不能睁开眼睛的小猫搬回家来了,把新家安在我结婚的电视机纸箱里。妻子取来旧衣服,给小猫垫上,看着几只还不能睁眼的小家伙,我们一家高兴不已。
当我们又一次回到家时,看到只是花猫一个人了。母亲说,那几只可爱的小家伙都被邻居拿去养了。因为家乡有个习俗,家养的猫猫狗狗不能白送,所以三个小猫有两只就象征性地收了6块钱,有一只是远房的大奶用一包食盐换走的。
后来,老花猫又生了几次小猫,每次满月后都是这样被送给邻居家的。也不知道那些重新安家落户的小家伙,可曾抽空回来看望过它们这尽责的母亲。
有一次,中秋回家,花猫就睡在门前的柳树下。见到我们的到来,她还是起身来喵喵地叫着,只是不再围着大家的脚挠了。花猫看上去老了许多,虽然不是很瘦,但走起路来明显不如当年轻巧。见到花猫,倒是乐了三四岁女儿、侄儿、侄女。个个都争着抱起照相,有时你拉脚,我抱头地抢,让人于心不忍。但老花猫也不抓不咬,只是本能的躲逃。看着她那副温顺的样子,我责令孩子们不要乱来。要知道,这可是我们家的宝贝猫。没有了她,该会有多单调。在家里住了两天,老花猫总是安静地躺在脚边,呼噜噜地打着瞌睡。
临回县城上班了,我又拿起相机,给花猫拍些照片,看着她安恬地躺在扫帚旁边,甜甜地睡着,任房前的光影兀自流走,也全然不顾相机闪光的干扰,心下一时涌起了一股暖流。
老花猫,你是幸福的。
三、门前的小路荒了
记得小时候,临村有一个姓杨的算命先生,成天在村子里转悠,遇到谁家没事,就凑上去闲聊,有时候也会有人请他算上一算。灵不灵不知道,只是大家都会乐呵呵的迎他来,送他走。
有一次,正值农闲,老杨路过门前,父亲开玩笑说,老杨,过来帮算一卦。老杨也凑过来说,好,今天就给你家三个公子算算婚事吧。听说要娶媳妇了,我们三兄弟一下子聚了过来,围成一圈。说到我时,老杨说我要绕过门前那条半围着大田的小路,才能找到媳妇,而且我的媳妇在北方。那时好像才七八岁,但我就记下了,我要绕过门前的路,向北方去才能找到我的媳妇儿。
老杨算过命,抽了烟,说些闲话,就回家了。门前的小路还是我每天放牛、游玩的必经之道,也把娶媳妇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偷懒,天还没有黑就把牛赶回来,于是只好在门前的小路上让牛儿再啃一会,拖到天黑。小弟常去给妈妈告状,妈妈也并不生气,只是故意逗我“哟,小昆在看哪个是他的媳妇呢”。
读完初中,我就离开了家,也离开了那条小路,真的向北去了。我那时开始想,咦,是不是算命的很准啊,我向北求学,是不是会遇见传说中的媳妇呢。一连回家的几个假期,有时在夏雨初晴傍晚,我会一个人来回徜徉在门前的小路上,听牵牛郎在晚霞中唱着牧归的孩子,看着邻居们在炊烟里荷锄而归。小弟从园子摘菜回来,一脸坏笑,还用手指着北边,“哎,北方,北方”,把一腔的闲情逸致,搅得横七竖八的。呵呵,好像我就真是在那儿等我的媳妇一般。
再以后,门前的那条小路也渐渐少走了。随着大家对便利交通的向往,我们家的很多邻居都选择向公路边搬迁了,原本我们家的中心地带也正在开始边缘起来。中秋节回家,当我抱着女儿艰难地走过小路,到对面的园子去看看菜园时,我才发现,那已经不能叫做路了。两旁的野草、野花繁茂地展示着一种荒芜的美。倒是女儿对路边开得星星点点的雏菊花格外地感兴性,央着我给她采了一大把。回到屋里,妻子用水瓶子将花插起来,放在桌子上,还真有几分味道。
四、记忆中的白菜苗
每次回家,都会经过村前的一坝稻田。
家乡的稻谷收进屋后,田野里开始落秋雨了。家乡是山区,秋雨一下,整个季节就会变得枯败起来,那些山岭上曾经金黄一片的草林,一下子也灰暗了许多,就连房前屋后飘起的炊烟也变得濡湿粘稠。
翻犁板田种小麦油菜尚有时日。村人们都三五一伙地聚在屋檐下。男人抽着旱烟,女人们则纳着布鞋底。大家各做各的一份事,说说笑笑,打发着一年里不多的几天清闲日子。任山村的第一场秋雨润沁着几欲龟裂的劳苦,垛在田里的稻草堆星星点点地散在烟雨里,静默无声。
不出一星期,太阳便会准时地照在每一个早起的山村汉子们的肩上。他们荷着犁,赶着牛,爽朗地投向田野的怀抱,展开健壮的双臂,翻犁着清香扑鼻的稻田。泥块带着露水,从牛蹄空隙里的铧尖上翻滚而出。小村的人们得在寒流到来之前把小麦、油菜、胡豆种下去。当来年春天满野的黄花红叶把田野打扮得温馨可人时,山村的人们便可以美美地享受着自己为自己播种下的春天。
挥鞭赶犁是男人们的活,女人们帮不上什么忙,于是都在家里收拾锅灶。秋收季节是山村一年中最富足的日子。小村的女人们也会在这个样的时节里,弄出一些好吃的饭菜,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红光满面。最先搬上灶台的当属新打出来的糯米。主妇们把刚刚长块的姜与肥壮的蒜苗洗干净,切成碎沫与小截在热油里轻轻一炸,再把淘好的白米倒进锅里,在大火上的油锅里翻炒。三下两下,大米就泛起了浅浅的嫩黄,加适量的水与盐后,合上锅盖,小火焖干水份。直听到米粒细细地炸响才退去柴火,一家人的主食就做好了。
在秋雨到来之前,小村的妇女们都会在自己家的园子里先挖出一片空地来,分了沟畦,施了肥水,再撒上些白菜籽,密密地铺上一层梳理干净的金黄稻草,便又下地忙活了。秋雨适时而至,把地里的白菜从土里唤醒,牵引着它们钻出黄色的“草被子”。这时才刚好长出两三片叶子来,嫩嫩的,长长的。
主妇端着盆,从稻草上轻轻地将菜苗拔出来,因为有稻草保护,菜叶上一点泥斑与虫口都没有。不一会,就可以拔上一大盆。放到井水里轻轻一淘,棵棵菜苗依然保持精神抖擞,茎叶无损。
主妇回到火堂前,汤已被火苗烧得翻滚。往汤里放入一两片姜叶子,再把洗好菜苗放入锅里,轻轻一翻,汤又翻滚起来。这时火得退去。
退了柴,火堂里就是红红的明火了。主妇趁着这通红的明火,将大把的刚刚晒好的干辣椒炮煳,再从门前的篱笆上摘下两三只西红柿,一起烧着。炮糊的辣椒并不入水清洗,就吹了灰放在大海碗,冷脆后夹在掌心稍一搓揉便化成了清香四溢的辣椒面。把搓好的辣椒面装在碗里,加上食盐、味精与烧好的西红柿拌成蘸水,再切上一把刚刚冒尖儿的小葱,撒进蘸水里,才算大功告成。
主妇们做好饭菜,太阳也高高的挂上了村头。男人们缓缓地放下手中的犁与鞭子,拍打着一身阳光与稻草屑,完成上午的活儿。
清炒的糯米饭,散发着浓浓的姜味与蒜香,吃在口里爽滑不粘,加上糊辣椒蘸水与清汤白菜苗,吃起是辣味实足,清爽到家。
至今我都坚信,那是我记忆中最想吃的东西。
五、偶遇山里月光
秋天回家,如果我没有听到秋娘的的鸣叫,是有些感到寂寞的。
记得在几年前,也是秋天,屋后的秋娘喳喳地叫个不停。月光从小窗里透进来,妻子睡不着,问是什么叫得这样厉害,我说是秋娘。过了秋天,秋娘就不知去向了,她得珍惜这有月的短暂时光。然而今年的秋天,当我如期而归时,却没有听到她那灿烂的叫声。难道是秋天已过?还是我来早了一些。
还好是中秋,月光极好。入夜就能看到月亮从对面的山垭口升起,随即便会高挂在我们家门前的柳梢上。柳树是我10年前栽下的,如今已高过房顶,长成大树了。取来相机,准备透过柳枝,拍下满月照屋的意境,顺便诠释一下儿时语文课本中“有时挂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个圆盘,有时像把镰刀”的儿歌。但却拍不出点意思来。也罢,这么好的月光,应该是可远赏而不能近取的。
还记得小时候过中秋节,妈妈把炒好的南瓜子当成中秋最好的食物。分给我们每人一包,几兄弟就坐在院子里,一边听山村里磨玉米的石磨此起彼伏,一边听草丛里的秋娘欢唱,偶尔可以听到天上有飞机飞过,仔细寻找还能看到一闪一闪的灯。
那样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没转眼就早已飞逝而去。倒是有些中秋的食物越来越丰富,但内容却越来越单调的味儿,就连那些平素的声响也不如当年那样丰富多彩了。
夜渐深,家人都睡去的时候,我依然没有睡意。我在寻找,也在等待,希望能多有一些声响陪我度过这个让人畅想也让人伤感怀的节日。月光还是从后墙的小窗上布满了被子,我可以看到妻子与女儿均匀呼吸的动静,甚至看到了我两手紧握的失落在慢慢地捋着月光,搓揉着一点点仅存的希望。总想,不会吧,一年这大好时光,怎么连声虫叫也不赐给我呢?
不知什么时候,我又走出了屋子,打开后园的小门。月光已偏西,但很明,直把屋后的瓜架子与山上的高树照得清晖四溢,像清豆浆浇过的一般。但也静极,几乎连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风,月光凝固了。没有太吠,小村全然安睡。天空如一面空旷而清远的大镜子,但极其悠远,以至于无法看到自己在其中的成像……无论我在原地等待多久,天空依一片靛青。
或者是真的太远了,就连我现在看到的月光,也是她在飞逝中的某一瞬发出来的呢,而她其实早已流向他方了吧。光于我,只是一次周期的偶然而已?
这么说来,今夜虫鸣亦不会再伴我入睡了,因为,偶遇注定只在别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