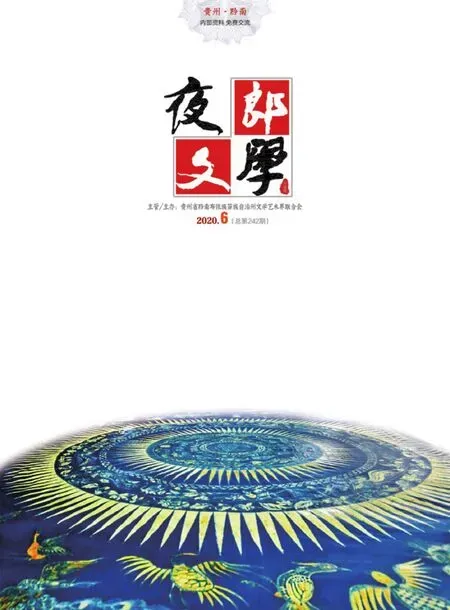窃听者(短篇小说)
王剑宁
他站在苍茫的人群里,惶恐地等待着最后的结果,生活却走出了人群,离他一步步远去了!
1
夜里,张从政又开始做梦了。
梦里,他来到了一个路口。半夜里刚下过一场雨夹雪,寒冷的感觉正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扫荡着白杨树上残存的几片枯叶。他站在那个路口,就好像站在事关生死的门槛上。
他的命运,也到了一个重要的结点。他站在这个结点上,感到无所是从,身心交瘁。
那个路口隐藏在厚重的雾中,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怪兽,张着大嘴,在等待着食物。而他,恰巧就是准备送到它口中的食物。当一个人失去了自我、无法看清自己,甚至自己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时,你所拥有的,就只有恐惧。
他现在就陷入到了这样的一种恐惧中。
为此,当他打起残存的一点精神、鼓起最后的勇气从那个路口走进去时,他的脚步显得那样艰涩、无助、乏力。他不相信一切,包括单位里所有的人,即使打扫卫生的那个李阿姨,他都会无端的怀疑她是谁派来监视自己的暗探。当他从路口走到巷子的尽头时,绝望地发现,巷子竟然是个死胡同。
他又一次从梦中惊醒了,绝望地在黑暗中喘着粗气。说起来,那些梦,都与那个该死的位子有关。
2
入秋的时候,部里的秘书处处长调离了,处长的位子空了出来。说来有些可笑,这个位子没空出来的时候,处里很多年都风平浪静,大家相安无事,按部就班,日子在浑浑噩噩中不知不觉地度过。这个时候,那个位子空了,突然间,就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所有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像极了发现猎物的猎犬。即使坐在办公室里,耳朵也都没有闲着。大家比先前显得更加沉默了,但那种沉默的背后,是一场厮杀爆发前的片刻安静,安静的有些反常,甚至有些瘆人。说实在的,谁又不想当那个处长呢?在单位里,谁又愿意甘居人下呢?这个时候,不争行吗?
张从政当然也想争。
张从政在这个单位工作已经二十年了,在秘书处副处长的位子上也熬了近十年。过去,那个位子没空下来的时候,他还显得心安理得,安静地干着分内的事。现在,处长的位子突然空了,他突然就有了危机四伏的感觉,想法也多了起来。按常理,他是副处长,转个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关键是,处里有三个副处长,这就有了危机。从资历上来说,大家都差不多。他也暗暗盘算过,单论工作,他绝不输给那两个。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干工作,业绩有目共睹。但是,他却没有一丝底气。
说到底,他没有关系。
他是个农村娃,考上大学后,总算留在了城市。但他骨子里依然流着农民的血。他自小家庭生活就十分贫穷,是父亲用种地的汗水供出了自己。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父亲就曾反反复复叮咛着自己,咱种田人没有什么本事,靠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事。这句话深埋在他的心底,与流淌的血液融合在了一起,已经不可能把它们分割开来。他在单位里除了工作,很少有别的心思。
但他却清楚地知道关系的厉害。
另外两个副处长,一个叫吴良新,据说是他们这个市副市长的亲戚,这层关系的厉害,当然不用言说。另一个,也与老处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老处长临调走时,就传出话来,已经在部里推荐了那另一个。老处长虽走了,但人脉还在,想来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唯有他,一个农民的孩子,离各种关系太远了。
晚上下班时,张从政的内心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失落感。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眼前依然晃动着同事们冷漠的眼光。此时,秋意渐浓,路旁的杨树叶子已经微微泛出了些黄色。一阵风吹过,枝叉中有一片叶子就很不情愿,又不得不离开似的,飘落到了地上。随着风的摆弄,叶子无可奈何的翻滚着,终于被卷到了一滩肮脏的泥水中。他突然感觉到了更大的无助,好象那片被遗弃的叶子就是自己。这使他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了同事们眼中的那种冷漠。
为什么人到这种时候,就都会变得冷漠了呢?
回到家时,妻子正在做饭,看到他进来,并没有做声。好像已经很久了,妻子就是这样默然无声。记得刚结婚时,妻子并不是这样,对他,还是有些笑脸的。久了,他和妻子的各种差异就出现了。他的话很少,除了写作,没有更多的爱好。妻子却不然,喜欢攀比。久而久之,他和妻子的话就不断减少,直到无话可说。
说到底,他和妻子还是不同的。妻子是城市人,而他,是农村来的。
吃饭的时候,妻子依然不言不语,这使他感到极不适应。他停下筷子,仔细地端详着妻子的脸,他想从那张依然年轻的脸上看到一丝温柔,哪怕是一时装出来的,也足以安慰自己那颗失落的心。然而,没有!妻子只是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冷漠地看了他一眼。是的!冷漠。那一刻,他的眼前再次掠过了单位同事们的眼神。妻子的眼神,和那些眼神是何等的相似啊!
张从政突然有些愤怒。
这是怎么了?自己到底得罪了谁?为什么自己的妻子,也要用这样的眼神看自己。他恼怒地把饭碗推到一边,歇斯底里地吼到,你们都怎么了?!妻子却依然不紧不慢地吃着饭,眼神更加冷漠。他终于有些按捺不住,呼地站起身来,推门而去。
屋外,已是夜色飞扬。
张从政低头走在苍白的街道上,背影有些孤独。隐隐约约,从黑暗笼罩着的一棵大树中,传出了一阵鸟的叫声,尖利而又满含怨恨。他想,那一定是两只鸟夫妻在吵架。少顷,一只鸟飞出了树丛,拍打着翅膀显示着愤怒。他想,那只飞走的,一定是一只雄鸟。
很久以前,张从政心里就明白,自己的那个家,早已名存实亡了。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昏暗的街灯下,他的影子时而被拉得瘦长,时而又变得矮胖。看着自己的影子,他若有所思地想,影子就是自己,而自己就是影子,如果影子也有生命的话,那么,这两个须臾不离的生命,到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影子的世界里,到底都有些什么?人了解影子多少?影子又知道人是什么?呵!在这个氤氲的世界里,理解为什么就这样的难!想来想去,他始终无法理出个头绪。于是,他摇摇发胀的脑袋,幽幽的想,也许,如果能当上那个秘书处处长,一切或许就解决了。
他决心争一下。
3
张从政开始行动了。
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他掏钱买了两瓶酒和两条烟。他想,既然要争,总得有所表现。于是,等到天黑的时候,他抱着烟酒,向部长家走去。在他的认识中,现在送礼,都是要在黑夜进行的。他不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是谁制定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规定,自有他的合理性。然而,在他幼年的记忆中,送礼原本并不是这样的。那时,送礼总是光明正大的。在农村,谁家的苞米熟了,就煮上一锅,笑着送给邻里;谁家的果子熟了,就赶快摘上一篮,与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他考上城里的这个单位后,村里的赵阿奶第一个赶来道喜,麦子还没有磨成面,她就将刚刚打出的麦粒炒熟后送了来。直到现在,他的唇边,似乎总有那甘醇的麦香在飘逸。
然而,现在,他却在黑暗中一步步向部长家走去。
他看着自己身后的影子,不觉有些可笑。他暗暗揣摩,也许,送礼本就是需要真诚的、不带任何杂质的。那种怀有某种阴暗心理的送出,本就是要在黑暗中进行的。还未到部长的楼前,他脸上就在微微发热。背后,竟然有了一些汗水。毕竟,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在黑暗里送礼。他突然发现,这种送礼,竟然比写一篇万字的稿子还要困难的多!
部长的房子在三楼,当他站在门前时,猛然有些气喘。
看着门铃,他突然犹豫起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件看似顺理成章的事,自己做起来为啥这么难!其实,对于部长,他还是有些亲近感的。他依稀听人说,部长也是农村出来的,只是不知道是真是假。部长对他的工作也是十分肯定的,记得去年的年终总结会上,部长就专门点到了他,说他踏实肯干,部里就需要这样踏踏实实干工作的人。他能当上副处长,据说也是部长在会上力争的结果。那时,部长还是副部长。可现在,副部长变成了部长,时过境迁,人还是那个人吗?
他伸着手,却怎么也摁不下去。
难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可是,明明自己并没有做错!想来想去,他觉得,问题的症结就是因为自己太老实了,只知道拉车,不知道看路,现在这个社会,这样怎么能行?再不能这样了,要想使那个副变正,自己就必须先得改变自己,走出这一步。
想到这里,张从政的手终于狠狠摁了下去。
还未等张从政在铃声中回过神来,门开了。迎接他的,是一个女人。女人先是看了看他的脸,好像并不认识。又看了看他手中的礼品,方才回头说了一声,老王,有人找。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耻辱感,难道,在那个女人的眼中,自己的存在,还不如那两瓶酒?随后,他就走了进去。
他的头有些发懵,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去的。
直到部长站在了面前,他才猛然清醒过来。他头一次觉得自己的表达能力是这样的差,这之前,他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表达能力,再难写的稿子,他都可以搞定。今天,他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看着他手中的礼品,部长似乎早已明白了他此行的目的。
部长微笑着,笑得很勉强。笑容里,似乎藏着些什么,显得很高深,让人无法揣摩。部长用手拍了拍他的肩头,淡淡地说,咱农村人,不兴这一套。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象一条狗,正在等待着主人手中的食物。那食物是什么?不就是一个位子吗?
他突然有了一种想哭的感觉,为什么而哭?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从部长家出来,张从政的双手仍然抱着烟和酒。并不是自己不想送,而是部长没有要。走出去很远后,他的脑袋才渐渐清醒过来,这才记起部长送他出门时说的那句话。看来,部长真是农村出来的。可是,农村人又怎么了?农村人就不会变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又有什么会一成不变?
随后,更大的失落又潮水般涌来。
部长拒绝了他的礼品,也就是拒绝了他的请求。这就说明,他的那个处长的位子,已经没戏了。他早就听人说了,现在办事,没个八万十万的,门都没有,他的那点东西,谁能放在眼里?
走在回去的路上,他歇斯底里地长笑几声,声音凄厉而无助,在黑暗中传出了很远很远!
4
从那以后,张从政就陷入了一种无法抑制的焦虑中。
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张从政无意中碰到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以前他只在侦破电影里见过,却从没有真正触摸过,那是一个叫做窃听器的东西。
那天他来到西门市场,百无聊赖的转悠着。这时,一个陌生男子若无其事地走到他跟前,撩开衣襟神秘兮兮地对他说道,哥们,要吗?他狐疑地看了看男子衣襟里绑着的东西,却并不知道是些什么。
他问,这是什么?
男子狡黠地凑到他的跟前,小声对他说道,窃听器!
窃听器?听到这个名字,张从政吓了一跳。毕竟,他是一个公职人员,对这样一件东西,还是十分敏感的。他还真的未曾听说,在这样一个看似风平浪静的城市,竟然会有窃听器这样的东西!
是真的窃听器吗?他好奇地问男子。当然是真的,不信你买一个试试?便宜着呢,男子自信地回答道。
那天,莫名其妙地,他竟然掏出了一百块钱,买了那个叫做窃听器的东西。当他真正拿到那个东西时,突然感觉有些紧张。如果这家伙是个真的,他要它是为了什么?又能有什么用呢?
返回家中后,他立刻就试了试那个所谓的窃听器。
那天,他乘着家人不在,将窃听器安在了儿子的卧室,并打开了电脑,制造了一点轻微的声音。带着一种莫名的冲动,他等待着奇迹的发生。关上门后,他带着耳机,在离卧室较远的客厅试了试,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于是,他一步步接近儿子的卧室,当贴近墙壁时,突然就听到了儿子卧室断断续续的声音。
竟然真的听到了!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却仍然可辨。
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个普通人了,他拥有了一个窃听器。拥有这样一件东西的人,还会是普通人吗?说起来,当时他的心态十分的奇怪,拿着那个似是而非的窃听器,竟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或许这个仿造的东西,会派上什么用场?
后来,那个窃听器果真就被派上了用场。
5
不久,部里的风声更紧了。
有人放出风来,说张从政要调出部里了,到大西沟工作。据说,放出这股风的人,就是副处长吴良新。谁不知道,大西沟地处偏远,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到了那里,再想出来就难了。
几天后,部里有关他要调出的风刮得更紧了。
每天一到单位,这股风就开始围着他转,就像来自坟墓里的鬼火,搅得他魂飞魄散。虽然,他极力躲在自己那个烟气弥漫的办公室里,那块属于自己的阴暗潮湿的地方,很少出去,但那股风却总是如影随形,使他无法躲避。每时每刻,他都心惊胆战地猫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等待着噩耗的降临,惶惶不可终日。那些日子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苍蝇,只要露出点头,就会被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拍子打得粉身碎骨。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已经完全失控了,正一点点地被一种什么力量揉捏着、挤压着,濒临破碎。这使他惶恐到了极点,精神到了就要崩溃的边缘。
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吴良新的脸。
这个时候,因为那个处长的位子,他和吴良新似乎已经成了仇人。每次,当他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得不走出办公室,面对那张脸时,他的头脑都会一片空白,说话也语无伦次。他觉得吴良新那张脸根本就不是人的脸,揭开敷在面上的那层皮,藏在下面的一定就是一个十足的恶鬼。
他也更不愿见到部长。如果说吴良新是鬼的话,他觉得部长更加难以琢磨,看到部长,自己就会有种掉到十八层地狱的感觉,全身发汗、毛骨悚然。
有一天,部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最近,部里要对今年的几个重点工作做些调研,你的文字功底好,这个调研材料,就由你来写。部长说这话时,眼里有些许期待,声音却很严肃,使他无法分辨部长对待自己的态度。部长又说,你是农村出来的,对咱农村比较了解,调研要触及农村的实际,我相信,这篇调研材料,你一定可以写好。他听出来了,部长在说“农村”两个字时,语气显得特别亲热,这就使他心里也是一热,部长到底是农村出来的,对自己还是亲近的。
然而,部长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又让他彻底凉了下来。部长说,特别是大西沟村,要作为这次调研的重点,明白吗?
从部长办公室出来,不知怎么的,他的腿突然一软,差点就滚到了楼道下,像中风了一样。部长提到了大西沟,为社么单单提到那个鬼地方?难道,自己真要调到大西沟去了?张从政的头皮一阵阵发紧,汗顿时就冒了出来。
那以后,张从政变得更加神经质了。
他不相信任何人,也不敢面对所有的人,他在极力回避着,因为他无法面对自己被他们掌控着的命运。一个人的命运,一旦掌握在了别人的手里,还能怎样呢?他的下场一定会是可怜和悲惨的。
那个窃听器,就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有一次,当吴良新走进部长的办公室时,张从政鬼使神差地贴在部长办公室的门上,极力地偷听着里面说话的内容。他总是觉得,只要吴良新在部长的办公室里,就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或者就是在密谋怎么处置自己。后来,他还发现,部长和吴良新聚在一起,大都是在下班后,在夜幕将临时。每次,他们都将办公室的门关得严严的,在里面窃窃私语着。在黑暗里,又能干什么好事呢?
张从政断定,他们一定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些勾当,一定与部里的人事变动有关,也一定与自己有关,与自己的命运有关。这使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窃听欲望,他必须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说自己?他们说的到底又是什么?他必须要知道这些,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做好垂死挣扎的准备。
也就是在这时,他想到了那个窃听器!如果能把窃听器装在部长的办公室里,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6
此后,张从政开始盘算着如何将窃听器装在部长的办公室!
为此,他极力寻找着机会。他发现,部长办公室的钥匙除了他自己有一把,另一把在内勤的手里。因此,想要打开那道门,除非破门而入,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他没有那样的胆!没办法,只有见缝插针、乘虚而入了。
为了寻找机会进入部长的办公室,每天一上班,他就将门打开一条缝隙,躲在阴暗里,做贼般观察着部长的活动情况。是的,那时他的样子一定像极了一个贼。这之前,他一直觉得干这事的都是特工,不是保密局的,就是共产党的卧底。但每次当他趴在门缝间向外看时,他的腿都在不停地颤抖。说到底,他没有特工那样训练有素,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再也不能平凡的普通人。
但是,为了改变命运,他别无选择,必须做殊死一搏。
后来,他发现部长是个极其谨小慎微的人,只要他离开办公室出去办事,就总是要把门锁上的,根本就无机可趁,这使他十分的沮丧。然而,就在他快要泄气的时候,突然发现,机会也并不是没有,部长在上卫生间时,有时就不锁门。但是,很快他又发现,这个部长的排泄功能似乎特别的强大,每次到卫生间后,很快就会出来,速度快得惊人,根本就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他想,也许部长本就不是人,而是一个其他的什么动物!他暗地里算了算,按照部长上卫生间的速度,如果他进到他的办公室,并安装窃听器,很有可能就会与部长不期而遇,事情就会败露。他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面?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然而,机会还是来了。
有次他再次趴在门缝观察时,发现部长从办公室急匆匆的走出来,手里提着文件包,快步向外走去。他判断,部长大概是有什么紧急会议要开。当他准备退回去时,突然发现部长办公室门上的钥匙竟然没有拔掉。看来,这家伙是走得太急了,竟然忘记了钥匙。这是个天大的意外,当然也是他张从政天大的机会。张从政明锐地发现,如果自己错过了这个机会,或许就从此再难得手了。他鼓足勇气,蹑手蹑脚地推开部长的办公室,终于将窃听器装在了里面。
随后,他就开始准备实施窃听了。
那时,他被自己的壮举激励着,一种就要揭穿真相的兴奋感时时刺激着我,令他欲罢不能。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简单。问题就出在距离上。那个窃听器毕竟是仿造的,功能根本就不能和正规的比,以他和部长办公室之间的距离,要想听到点什么动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开始后悔,他担心时间拖久之后会被部长发现,那样他就彻底完蛋了,他的恐慌在不断加剧,以至于每天都在做着恶梦。在梦中,他总是看到部长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他甚至在噩梦中发现,部长那张脸根本就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随时准备刺杀他。
就在张从政濒临绝望时,希望却再次出现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打扫卫生的李阿姨从部里的小会议室里出来,且没有锁会议室的门,而那个会议室,恰巧就紧挨着部长的办公室。于是,下班后,趁人不备,他就潜入会议室,开始实施窃听了。那一刻,他就像是一个真正的特工,戴着耳机,紧贴着墙壁,在极力捕捉着隔壁极其微弱的动静。那天,吴良新刚好又一次走进部长的办公室。两人坐在办公室里,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话。由于声音还是特别微弱,他没有听到全部,但他仍然听到他们提及了自己的名字!这使他的恐慌达到了极点,
他们提及我,能是什么好事吗?
7
又过了几天,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当张从政再次躲在会议室窃听时,他突然发现窃听器里没有任何的动静。怎么回事?怎么会没有了动静?他的心在狂跳,他的呼吸眼看就要停止了,他预感到了危险的降临,已经嗅到了浓烈的火药味!当他带着这些惊悚的疑问走出会议室的时候,他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自己的行踪,一定是被部长发现了!
他惊恐地断定,那个窃听器,现在一定就在部长的手里!
这天夜里,张从政又做起了梦。这个梦,可怕极了。梦里,他被关在了一座黑屋子里。坐在那个密不透气的地方,他似乎看到了一副冰凉的手铐,悬在半空里。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知觉,快变成了植物人,每个器官都废了,脑子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身上的肉,似乎都可以闻到腐败的恶臭。随后,他的精神也开始出现变异,思维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他觉得周围的空间越来越小,不断地挤压过来,压得他胸膛都要爆炸了。四面墙壁也在剧烈的晃动着,似乎发生了地震,随时可能倒下来,将他掩埋。
他在这种极度扭曲的状态下,感觉真的生不如死!
他瘫坐在地上,目光无力地看着窗外。夜色已经很浓了,寒气挺重。透过窗玻璃,可以隐约看到不远处的半个月亮。四周格外安静,他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狂躁的心跳声。他害怕这种静。这种可怕的静将他紧紧包围着,压迫着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他感觉自己的血液在那种压迫下已经停止了流动,全部淤积在了脑袋上,剧烈的头疼强烈地冲击着他,使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囹圄。
最初接触这两个字,他并不认识。他翻阅了词典,才知道是“监牢”的意思。身陷“囹圄”,就是指被关进监牢的意思。汉字是很有些玄妙的,要么形似,要么音似,往往两个相同的字,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就像人,虽然都说着人话,但肚子里的心思,却是永远难以琢磨清楚的。他仔细研究了这两个字,他觉得除了那两个密不透风的“口”外,其余都和“监牢”没有什么关系。
“囹圄”和“囚”,到底有什么不同吗?
他觉得,如果都是监牢的意思,那“囚”,不是更形象些吗?人,被封闭在四道墙里,严丝合缝,阴森逼仄,戒备森严,暗藏杀气,多么贴切?又是多么令人生畏?人一旦变成“囚”,就和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了。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囚”,他还没到那个地步。
那么,就是“囹圄”了。
或许,“囹圄”和“囚”还是有所区别的。“囹圄”,起码还有那么点空间和余地。“囚”,却是不可救药了。但他认为,从根上来说,这两个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就是身陷囹圄了,困在黑暗中,比“囚”好不了多少。他在梦中苦苦挣扎,却怎么也无法走出那间形似监狱的小屋。
第二天,梦醒后,张从政害怕极了。如果窃听的事情真的暴露了,自己会不会真的坐牢?
当然,他无法知道,那个窃听器其实并没有被部长发现,只不过是由于粘的不牢,掉在了地上,恰巧被打扫卫生的李阿姨给扫到了垃圾池里了。
一连几天,张从政每夜都是噩梦,精神紧张到了极点!
这天,他在单位看到部长时,发现部长的目光是那样不可思议,那样怪异。这家伙似乎已经掌控一切,早已把他的把戏彻底看穿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再次想到了那个梦,想到了“囹圄”。或者,自己真的要身陷囹圄了。想到这里,他的眼前一阵发黑,头剧烈地疼,猛地摔倒在了地上。
他得的是脑溢血,医生说,虽然还不至于没了性命,但将来就是半个植物人了。
出院后,他从此失去了意识。
当然,张从政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是,自从秘书处处长调离后,部里早已开过了会,他是那个位子的唯一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