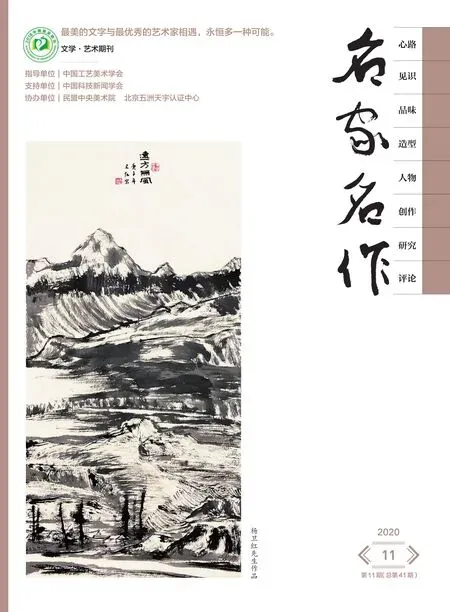中国古代士人阴柔艺术审美心理研究
姚 羿
一、“诗缘情,情绮靡”
(一)阴柔之始,魏晋先行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异常重视血亲文化在家族内的传承,与西方人强调个体价值的家庭观念相比,表现出倾向于中和淡然的伦理偏好。这种偏好使得中国人极其重视家庭内部的情感和谐,崇尚“贵柔守雌”的处世之风,追求心灵深处的安逸与自在。这份恬静雅致体现在诗歌创作上,即是推崇阴柔婉转的审美意趣。
老庄思想可以看作是此种阴柔审美偏好之滥觞。老子在《道德经》中以自然界的大量物象暗喻“古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的为人之道,训诫后人应同水一般具有以柔弱胜刚强的品质,正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所言之“水”实是阴柔之美的象征,在他看来,连派生万物的“道”都具有阴柔之属性[1]。
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玄学的建立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研究庄学的高峰,亦是阴柔审美盛行之始端。时局的激变与朝代的频繁更替使魏晋士人阶层深感无力,驱使他们相继摒弃了繁缛的儒学礼教,寄情于山水,沉醉于追寻生命本真的价值之中。这时老庄哲学中的隐逸思想无疑为士人们迷情于山水之色提供了上佳的理论支持,一时间,饱含清逸之风的隐逸诗、山水诗风行起来。清丽婉约、柔情百转是这些诗作独有的美学特质,大量自然物象的运用更为其独添了一份超逸之美。士人们将无限的柔情赋予那些曼妙辞藻的诗句之时,也凸显出自身对阴柔之美的审美偏好。
譬如魏晋山水诗人谢灵运,其诗作深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诗境空灵细腻,悠然闲适。在其一生所作之山水诗中,与“水”相关的意象出现近百次[2]。谢氏咏水一来是为了一抒胸中向往田园归隐生活之理想,二来则是慨叹水流之畅达幽远一如道家仙境般难得寻觅。自幼在“靖室”修行的经历亦使他得以对作为道学最高理想载体之“水”有着难以割舍的心灵羁绊。在五言诗《过白岸亭》中,谢氏借溪涧之端柔一表对那“水”之禅境的神往:“拂衣遵沙垣,缓步入蓬屋。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3]
实际上,以“水”作为展现阴柔美之意象并非魏晋时期士人之首创。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先民们就对“水”“月”等意表阴柔的物象充满依恋之情,可谓是阴柔审美最早的萌芽。譬如《诗经·蒹葭》中水之意象与热恋男子意中人的联结及《诗经·月出》中月之意象与清丽女子之联结等,皆表露出先民对阴柔之美的推崇与喜爱。至南北朝时期,刘勰于《文心雕龙》中首次为阴柔美正名,将其作为独立的审美范畴与阳刚美一同划分入文学批评的领域之中[4]。
(二)万类诗篇只一柔
魏晋南北朝时所流行的隐逸诗和山水诗可以大致归为写景抒情诗的范畴,而诗歌按照题材划分还存有咏物言志诗、即事感怀诗、怀古咏史诗、边塞征战诗等数大类。无论是哪种题材,阴柔之美均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譬如晚唐诗人李商隐可谓是咏物言志诗写作的杰出代表,其对人生悲情的慨叹使他的诗作中处处涤荡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在写作物象的选择上,李商隐擅以纤弱、秀美之事物作为寄托情愫的载体,这些事物包括但又不限于野菊、蝴蝶、微风、细雨、残灯、夏蝉、月色等。如在《桂林道中作》中,诗人以蝉为物象,感时伤怀,寄托了自己孤身一人以四海为家的失意之情:“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晖。空余蝉嘒嘒,犹向客依依。”又如在《滞雨》中借摇曳的烛光袒露出的浓浓旅愁:“滞雨长安夜,残灯独客愁。”抑或在《为崔从事寄尚书彭城公启》中依托“皓月”“悲风”等慨叹命运之不公,抒发空有一身抱负却生不逢时,无力施展的悲凉心境:“皓月圆时,树有何依之鹊;悲风起处,岩无不断之猿。”[5]简言之,李商隐所作之咏物言志诗绝大部分都是他本人彷徨迷乱之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主观理想与残酷现实的背离促使他不断地在诗词歌赋中寻求精神慰藉,以文人的一种特有的阴柔心态回应造化弄人的世事,算得上是一种“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式的温柔反抗。
除了“应物斯威,意物吟志”的咏物言志诗外,唐人还好作以点滴琐事生发而出之即事感怀诗。所谓即事感怀,人生体悟、思乡赠物、逸致闲情等即兴而发之情愫皆大抵可归为此类。此类诗作不拘于特定题材,事体情理无论大小主次皆可入诗。可以是雨后的闲庭信步:“夜凉喜无讼,霁色摇闲情”(皎然《酬乌程杨明府华雨后小亭对月见呈》)[6];可以是独居时闲来无事的信笔挥毫:“未得青云志,春同秋日情。花开如叶落,莺语似蝉鸣。道合和贫守,诗堪与命争。饥寒是吾事,断定不归耕”(杜荀鹤《春日闲居即事》)[7];抑或是静虑坐禅时所焚的一炷檀香:“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8]简言之,士人们大多借此类诗体畅言那些一过性的诗意情愫,从而为闲适的生活增添几分情趣。而在这份闲适中,却也有些不为人知的心酸愁绪在里面。真是“零丁洋里叹零丁”,个中悲味谁人知!
至于怀古咏史诗与边塞征战诗,二者看上去似乎与“阴柔之美”没有太多联系。实际上,怀古咏史诗、边塞征战诗与写景抒情诗、咏物言志诗、即事感怀诗在情感抒发的载体上别无二致,它们全都是借用某种“第三方”的存在来较为委婉地表露自己的心声,往往带有文弱书生特有的书卷气。而单就这一点,便为阴柔美在诗中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如在以悲戚肃杀诗风闻名的李商隐那里,其在咏史怀古诗《陈后宫》中大量用典,极尽讽刺之能事,并将自己一贯的悲情作风代入诗境之中:“玄武开新苑,龙舟宴幸频。渚莲参法驾,沙鸟犯钩陈。寿献金茎露,歌翻玉树尘。夜来江令醉,别诏宿临春。”[9]李商隐借陈后主行事之荒淫无度来警示当今皇帝切勿贪恋酒色,全诗看似气势凛然,但由于其诗境全无向上阳刚之气,全然充满了闺怨般的悲情,遂体现了作者虽心怀愤懑却无力改变现状的凄苦心境。再如中唐诗人令狐楚所作《从军行五首》中表达出的强烈的厌战情绪和思乡之情:“荒鸡隔水啼,汗马逐风嘶。终日随旌旆,何时罢鼓鼙。孤心眠夜雪,满眼是秋沙。万里犹防塞,三年不见家。”[10]在唐代,以“从军行”为题材的绝句、诗词不胜枚举,世人都道边塞征战诗皆应呈现出一派金戈铁马、斗志昂扬之态,却甚少留意其中亦存有铁汉柔情的阴柔之美。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古代士人们既无铁肩扛起那沙场的噍杀之气,也便只有以逸士之心吟诗作赋排遣内心的苦闷作罢了。
二、“音之流华,水月相和”
(一)以“悲音”为美
儒道两家崇尚内敛、端柔、中和的思想对古中国人的艺术审美心理起到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举凡在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等审美活动中,古人皆被要求以一种克制的、隐忍的、合乎中庸之道的态度来指导一切情感的抒发。长此以往,这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审美要求逐渐成为具有社会群体性质的心理偏好,并呈现出尚悲、阴柔的美学特质。施咏将有尚悲倾向的音乐作品划分为政怨、闺怨、士怨、暮愁、别恨、离愁、悲秋、夜怅等八类[11],足可见古人对阴柔美之偏爱程度。
在笔者看来,政怨、闺怨、士怨、别恨、离愁之情感皆因“人”而起,可粗略归为一类;而暮愁、悲秋、夜怅则皆属因时移世易,自然风光变幻而产生之离愁别绪。两类情感形式虽殊途同归,末了都为表达对国家社稷及个人命运之慨叹,但又因二者“触媒”不同,故由此生发而出的音乐作品之情感也有着不同的色彩偏重。如宋代音乐家姜夔所作琴歌《古怨》,其曲糅杂了作者对时局动荡而忠士不得重用的不安与惶惑。全曲采用燕乐调式写作而成,曲调和婉悠长,曲辞如怨如慕,字字流露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作者借金谷园(为晋代石崇的私家园林)中佳人薄命之典故哀叹国之大厦将倾,感慨再美好的事物也不过昙花一现,终将同园中奇珍异草般在生命的末途零落成泥,消失在时光的滚滚洪流之中。正是“过金谷兮花谢,委尘土。悲佳人兮薄命,谁为主。岂不犹有春兮,妾自伤兮迟暮。发将素”[11]。《古怨》创作之时正值南宋的前中期,统治者的软弱无能使得外族频频进犯中原,国家政权风雨飘摇。姜夔身为一介书生,眼看家国有难,却因仕途不济而无法尽一己之力,忧愤之情溢于言表。他在词中叹息:“欢有穷兮恨无数,弦欲绝兮声苦。满目江山兮泪沾屡。君不见年年汾水上兮,惟秋雁飞去。”[11]个中怅惘困顿之情可见一斑。
《古怨》之配词风格实为骚体,不似一般诗体有节有章,结构上亦不似传统诗歌句式囿于四言体,其诗句长短不一,五至七言均可,并含大量用以咏叹的语气词。姜夔采用骚体作词,一来是不必过度考虑诗句结构上的严整性,合乐时音符与词句间的匹配将更加自然。二来是使用此种文体可以突破传统抒情诗刻板的情感表达方式,使词句间语气更加哀柔婉转,很容易抒发深层次的哀怨之情。《古怨》词曲所具有的独特意境使其更偏重于表现政怨、士怨这类带有群体性质的情感,此类作品通常以宏大的时代背景为烘托,借用典来表露某一特定群体对时政、风俗、封建礼教乃至某些社会现象的愤懑与不满。与以《古怨》为代表的偏重于抒发群体性情感的音乐作品相对,以“暮愁”“悲秋”“夜怅”为表现主题的音乐作品则更偏向于个人情感的阐发,此类音乐作品之代表作有姜夔自度曲《杏花天影》抑或《扬州慢》。作者在夕阳西下之时,睹物思情,为自己的过往和前途命运发出慨叹,叹息万物终有时,就如同那漂泊于江面上的扁舟,不知“移舟更向何处”。
(二)女性化审美偏好
在长期的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大环境影响下,中国人“缺乏海之超越大地的限制性的超越精神”(黑格尔语)[12],其精神内核更趋向于一种安稳恬淡、顺应自然、“与天道合”的独有特征。而这种追求安定美好的内敛式生存愿望促生了一种“场域依赖型”的审美偏好,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观点来说,即是一种偏重女性化特质的审美心理。
就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其乐思多纤巧柔美,乐音的组合方式倾向于二维展开,不同于西方交响乐多立克柱式结构般充满竞争欲与力量感。在旋律的搭配和使用上,也未发展出西方音乐结构繁复的和声思维,而是在线性思维的指导下,以单旋律作为主要的音乐表达方式。中西方这种音乐表现手段上的显著差异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两种文化间截然不同的音乐审美心理结构:东方智慧更注重内容或情感的细腻表现,西方文明则更偏向结构、形式的堆砌和逻辑表达,相对削弱了情感的表达空间。我们不能说二者相较孰优孰劣,只能从中窥见中国传统音乐审美心理感性化、女性化表述的渊源所在。
中国人女性化音乐审美的形成除了上述要素之外,亦和社会因素息息相关。作为引领古代音乐文化潮流的关键群体,士人阶层的命运通常是每个封建王朝音乐精神内核的风向标。加之受儒、道、佛三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该阶层历来便是封建礼教热忱的贯行者,均梦想着“暮登天子堂”。于是,统治者的一颦一笑便时刻牵动着他们脆弱的心,社会政治氛围的变动也会实时反馈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13]。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中,士人群体的心理亦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们一方面在精神上高度渴求自己的才干能被当朝者所重视,另一方面则是梦想一旦破灭,便隐于世外桃源,饮酒作赋。心中虽有不甘与愤懑,却因封建文人既无力改变固有的体制,亦忌惮历代所兴修之“文字狱”,故而忧愁与哀怨只能同涓涓细流般借莺啼燕语之口倾诉于笔下了。
这样的“借物抒情”从本质上来看实属一种被动、消极的情绪发泄方式,是某种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畏惧统治者绝对权力的威压,没有勇气与“属阳”的皇权直接对抗,从而选择了一条“属阴”的道路避其锋芒。所谓女性化的审美偏好即可看作是长期高压统治或社会动荡下的妥协产物,时代环境对士人阶层的压迫越重,这种倾向就会越明显,例证如下:
其一,魏晋时代。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出仕不再是士人的必要选择。文艺领域盛行清谈之风,音乐多“以悲为美”。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隐士们不再追求政治理想,转而长啸山林,沉湎于作诗吟赋。这时的音乐风格极大地受到老庄玄学之风的影响,或恬静雅致,或傲物不羁。雅致者有如嵇康所作之“嵇氏四弄”,傲物者有如阮籍作之《酒狂》。嵇氏抚琴多为表其高洁之志、自清之态,曲风多清雅秀丽,一如其与世无争的自在之心;阮籍则借酒佯狂,以酒为号,一抒“己道与世之不合”的悲凉心境。二者一收一放,虽然外在意境略有不同,但实质却殊途同归,其精神内核皆透露着一种女性般的哀愁与隐忍,一种失意文人踌躇满志却愿景成空的不甘与无奈。
其二,元帝国时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元统治者跋扈专横,所谓“九儒十丐”即是形容元代士人阶层在等级制度下艰难求存的真实写照。社会大环境对士人的放逐使其在精神上失去依傍和方向。与魏晋风度影响下的士人不同,元代文人不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清谈生活,而是将关注点放在同样受到阶级压榨的穷苦百姓身上,这其中,尤以对女性的关注为甚。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秩序下,女性鲜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她们很容易就会沦为各种权力倾轧的牺牲品。而同样处于颠沛流离命运的元代士人们极易对这些美貌端淑的“解语花”产生“我见犹怜”式的共情心理,这一点在音乐创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以元代广泛流行的元杂剧和元散曲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元杂剧现存247 部,相关作家百余人;元散曲达3853 首,相关作家二百余人[14]。在这些反映元代普通民众世俗生活的音乐作品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将女性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这些女性形象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她们可能是待字闺中的少女或初为人母的少妇;抑或是久居深宫的奴婢和烟柳花巷的妓女。身份角色产生了千差万别的个人遭际,而这些正是剧作家发挥其共情能力的立足点。他们在哀叹被压迫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不公世道的反抗与嘲弄。如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所作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通过对崔莺莺与张生间自由爱情的歌颂,将一记重拳砸向了腐朽落后的封建伪道学,并为生活在封建体制压抑下的广大妇女赋予了进步独立的思想,鼓励她们冲破旧道德的精神枷锁,勇敢地反抗夫权和父权,从而彻底掌控自己的命运。《西厢记》只是元代士人在时代大背景下以女性视角进行创作的一个缩影,他们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寄予在这些弱女子身上,以细腻的音乐语言将笔下的女性形象描摹成富有独立精神、不畏强权的进步个体,使之具有论文承载作为反抗封建强权统治急先锋之象征的独特价值。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细腻端柔的心理特质为女性化音乐审美偏好的产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而作为外因的专政统治,民族压迫等亦加剧了古代中国士人以女性化视角及话语写作音乐的倾向。士人们在秉承自身“尚悲”之音乐理想的同时,也为封建时代女性独立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一丝曙光。
三、“画之境者,冲虚贵柔”
(一)“士大夫写意画”之阴柔
“文人画”亦称“士大夫写意画”,是中国古代士人群体所独有的一种绘画形式。其滥觞于唐代,经宋元进一步发展,兴盛于明清。唐代诗人王维最早提出了“引诗入画”的概念,被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奉为中国文人画之鼻祖。文人画亦同山水诗、士大夫音乐相仿,皆为古代文人群体所创造之精神家园的一部分。唯一有所区别的是,文人画更近似于某种“综合艺术”,它将文学、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在创作风格上更加飘逸自由。从总体上看,文人画呈现出一种隐逸阴柔的美学特质,这与老庄哲学对士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说,老庄哲学对诗歌与音乐的影响多少还停留在“只可意会”之阶段的话,那么就绘画而言,这种影响则显得更为直观。
众所周知,绘画作为一门空间艺术,其表情达意的功能主要通过视觉来呈现,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绘画作品中线条、构图、用色这类表征来判断画家本人的审美偏好。如唐代王维所绘之《袁安卧雪图》,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就此画作点评:“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15]芭蕉本生于南国,性喜温不耐寒,而王维却“不问四季”,反其道而行之,将芭蕉作为物象引入画中,真可谓奇哉怪也。实际上,王维受老庄思想影响之深刻,不仅体现在他所创作的诗词里,亦表露于这些信笔挥毫而就的文人画之中。且王维生前“精禅上理”,仕途的无望、达则天下之心的泯灭更使他晚年虔敬修佛,以至于身后得到“诗佛”的称谓。故此,“雪中芭蕉”并非时兴之作,而是在儒道佛禅思想浸润下的一种对人生的慨悟,表现一种跳脱于尘世之外的旷达心境。作者选用芭蕉在佛经中亦是肉身脆弱的象征,《维摩诘所说经》有云:“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16]而以脆弱的芭蕉来暗喻人生之多舛,这本身就体现了王维崇尚“悲美”的审美偏好。有了王维的铺垫,后世文人画创作的整体基调大都以冷色阴柔为主,而这其实也是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在封建社会戕害下悲凉心境的真实写照。
王维“悲美”的阴柔审美偏好为文人画之精神填充了底色,而作为“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其高逸的画风掀起了明清数百年“仿倪高士”的热潮。倪瓒性情孤傲,一生未出仕,年少时家境优渥,广为交际,二十八岁后随着长兄离世,家道崩殂。中年后典当家产,漂泊海内,不为名利所累,世人敬称他为“倪高士”。倪瓒的山水画可谓是他一生心境的写照,由于自幼受儒、道、佛三教思想之浸染,在他的作品中时常透露出一种“大道至简”的出世之美。不与俗世相争,孑然傲立于世的人生态度造就了他“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水墨追求,而这八字亦是后世文人争相礼颂倪瓒的原因之一,只因它一语道破了文人画之精髓。倪瓒作画,不求奇技淫巧,一味堆砌画技,但求寥寥数笔,即能勾勒出所绘之物之精气神韵,使之气韵高古,宛然不可近也。这种“生人勿近”的距离感源于他独创之“一河两岸”式的三段构图法,亦源于他在画中鲜少绘出人物,只因“今世那得有人”。如此高冷到几乎不近人情的绘画风格正是倪瓒“悲美”阴柔偏好之体现。诚然,这样的“悲美”较之王维实际略有不同,王维之悲尚存俗世烟火,以他的人生际遇来看,其悲苦之情主要源于仕途上的不得志,他本人对统治者仍抱有一定幻想;至于倪瓒,其“尚悲”的根源则要纯粹许多,他既没有对政治的热情,也不对世俗生活抱有太多奢望,是真正的“为己而悲”。从曾经年少时所拥有的无忧虑的美好心境,到最后至亲至爱相继离去的凄苦之情,倪瓒饱尝了人间苦味。这样的人生经历反映在他的绘画创作上,体现出的是一种类似禅宗“色空”的“冲淡”之美,一种了无牵挂、参透一切机巧之后的平和恬静。
远山、近岸、几棵杂树,即构成了倪瓒简约阴柔的绘画世界,这个中滋味正对应了苏轼“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文人理趣。王维、倪瓒作为文人画创作的领军人物,为后世皆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水墨财富。
(二)黑色崇拜——阴柔审美偏好的成因
文人选择水墨作为表情达意的艺术语言并非偶然,中国先民实际上从远古时代便有崇尚黑色的传统。《韩非子·十过篇》有云:“尧禅天下,禹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而材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17]黑色在远古时期已是尊贵的象征,在《易经》中该色被认为是天空的本色,而古人以天为尊,自然对黑色格外器重。此外,古人将五行、五色、五味、五方等一一对应,而黑色正对北方,五行中北方属水,亦与天官五兽中的玄武相对应。玄武本身又由龟蛇组合而成,五行主水,象征四季中的冬季,在道教信仰中被奉为“真武大帝”“玄天上帝”。道家向来常以水喻道,水的阴柔特性及由此衍生的水崇拜便因此得以大力推崇,这在以儒道佛为文化根基的古代中国无疑会对整体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如此,黑色与道教信仰及以阴柔为美的水崇拜之间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黑色本身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演化成为阴柔内敛、冲淡平和的精神象征。
黑色直至秦朝时基本保持着主色的地位,但在汉代以后,其主宰地位逐渐为黄色和赤色所取代,赤色更是成为唐代、宋代、明代等几大王朝之主色。但对黑色之外颜色的偏好毕竟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皇室内部的喜好,这种喜好并没有淡化黑色在民间之受宠地位,文人画的出现即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何以言之?首先,古人讲究书画同源,中国汉字的字形本身即具有抽象和象形的特点,写字的过程亦同绘画的过程。而唐代亦是书法发展的一个巅峰时代,怀素与张旭的草书模糊了书法与绘画间的界限,为文人画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士大夫们在酒酣尽兴之时很容易利用手头的白纸黑墨信笔涂鸦一番。其次,禅宗的影响。禅宗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兴盛期,士人群体与隐匿于山林中修行的禅师多有交集。禅宗讲求空寂淡然,追求精神世界的升华与顿悟,而这种静虑参禅的思想在士大夫阶层颇为流行,并间接导致了山水画由丹青向水墨世界的渐变过程。诚然,水墨的玄黑除了可以更好地表达远离凡心、脱离现实的境界和目的之外,还可以唤起士人们心中对文化底色的回忆,而这种回忆的刺激源正是禅宗本身。禅宗发展至唐代,早已与儒、道、佛三家在精神层面合而为一,兼收并蓄地传承和发展了它们的一些固有传统,三教信仰的核心部分亦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佛家的觉悟皆被禅宗吸纳为空寂幽玄的禅理,同样被吸纳进来的,还有和老庄思想相联结的尚黑传统与阴柔倾向的审美观。如此,禅宗的精神追求与包含有阴柔尚黑审美的美学内核促进并发展了文人水墨画,使之在漫长的时光淘洗中逐渐去伪存真,日趋成熟,成为文人在绘画中展现其阴柔审美观的首选艺术形式。
四、结语
古代士人阶层可谓是封建社会中自我意识觉醒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淫威下汲汲营营,却又苦于无力突破强权所带来的精神枷锁,故此不得不另寻旁路解决个体在集体无意识制约下产生的孤独与彷徨。在追求自我意识解放的征途中,士人们选择以先圣阴柔美学的核心思想作为指路明灯,在诗歌、音乐及绘画创作中皆贯之以阴柔尚悲的审美准则。这种准则的普遍应用促使士人心中的女性意象“阿尼玛”(anima)得以被全然释放出来,在自己所塑造的艺术领地中尽情挥洒着自身女性化的一面对士人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更是一种原始欲望的回归与艺术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