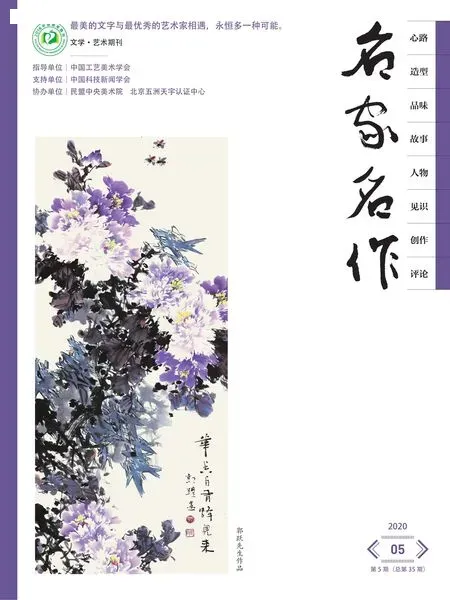浅析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王晓蕊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小说作家,其在先锋文学时期所撰写的一系列作品在扎根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又具有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往往以社会生活底层某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生活经历为缩影,使读者进入他所构建的语言世界中,进而观照到整个社会民众的现实生活状况,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是中国作家常常应用到的。余华的一系列小说,如《活着》《兄弟》等均运用大量笔墨塑造了许多经典男性形象,大部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视线聚焦于性格各异的男性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余华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刻画。在余华的小说中,女性作为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虽在当时时代下并未能摆脱作为男性附庸的形象和思维,但是其以忍辱负重的姿态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压力和苦难的折磨,在生活的磨砺之中展现出了较大的包容性和忍耐力,体现出了女性在温和、柔弱外表下隐藏的巨大力量和母性光辉,亦值得后来人在阅读鉴赏的过程中进行人物特征的细致剖析和人性特点的深刻感悟。
一、聪慧明理的家庭女性——《活着》中的女性角色家珍
余华小说《活着》主要讲述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浪潮下,农民福贵在他的一生中、在命运的翻云覆雨中经历了种种苦难,身边的所有亲人在变故中一个个离去的故事。福贵这一男性形象,在屡经磨难之后仍然坚韧地活着,这其中自然映射出他在一次次悲剧命运打击下所形成的看淡世事、超然物外的精神,但同时也包含妻子家珍的包容信任。《活着》中的女性形象家珍是封建社会下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小说里,家珍的每一次出场,几乎都伴随着福贵人生道路和命运上的不如意。福贵在给母亲看病的途中不慎被国民党军人掳去当兵,当他多年后重返家中,母亲却已在等待和遗憾中去世;这时的家珍宽慰福贵:“我不想再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能给你做一双新鞋。”由此可见,在飞来横祸和福贵多年的杳无音讯面前将所有的抱怨和苦水都一一咽下,劝说福贵带着家庭的责任和希望继续生活下去。后来,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家中越来越贫困,也是家珍拖着饱受疾病折磨的身体,到娘家带回了一小袋米,解决了家里的燃眉之急。从这些生活细节可以看出,家珍这位家庭女性虽然在性格上具有软弱的一面,未能摆脱封建思想的保守,未能跳出家庭对女性的束缚;但她依然是聪慧、明理的女性,以包容和牺牲个人幸福成全家庭的完整。从家珍身上,读者能够看出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特有的坚韧与善良。
二、挣脱父权枷锁的母亲——《第七天》中的女性角色李月珍
小说《第七天》的写作手法充满了瑰丽奇特的现象,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杨飞在死亡七天后的所见所闻,以杨飞进行回忆的视角,带领读者了解了其一生的坎坷经历。在关于“第三天”的叙述中,作者讲述了杨飞的身世,即杨飞从小被母亲遗弃在火车站中,被名叫杨金彪的扳道工捡回了家中,将其当作亲儿子一般抚养;虽然杨金彪为了杨飞这个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终身未婚,但在杨飞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角色却从未缺席。小说中关于这位“母亲”做过这样的描写:“‘我’生下来的第一天喝的就是李月珍的奶水……在父亲上夜班、有事的时候,‘我’吃住在她家,我的童年很多时间都在她家度过。”因此,在杨飞的心里,亲生母亲给予了他生命,但于生父生母的家庭而言,他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外来人,李月珍才是给予他在成长过程中所需的爱与陪伴的“真正的母亲”。李月珍这一角色,不同于以往余华小说中传统的母亲形象,即常常被父权所牵制和压迫,不是作为男性的附庸,便是缺少自身独立人格的表露,她既与杨飞没有血缘关系,与杨飞的父亲杨金彪也无任何羁绊,在物质和精神上也都是独立存在的。生前,李月珍指导杨金彪养育孩子的方法,带给了童年的杨飞不可替代的温暖体验;故去后,她的灵魂看着丈夫和女儿消失在眼前,在伤心之余,她看到了二十七个孤独飘零的婴儿,这些孩子激发了她内心的母爱,使她带领这些并非亲生的婴儿穿越生与死的边境线,最终踏入了没有等级、没有压迫、没有悲伤与仇恨的永生之地。可见,李月珍的一生均保持了作为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挣脱了父权的枷锁,并利用其内在的能量与情感感化了更多人。
三、从父权视野下看待女性的命运
(一)在压迫下苦苦挣扎
在人类文化史上,从父权视角看,女性长久以来被作为男性释放欲望的对象或男性美好想象的载体。从男性的思想意识上看,女性似乎不可脱离男性而独立存在;男性往往将顺从、规范、“以夫为天”、符合其理想状态的女性塑造为贤妻良母或贞洁烈妇;将不安于现状、具有新派思想和独立意识的女性定义为“妖妇”“祸水”。正如《活着》中的女主人公家珍在嫁给以吃喝嫖赌为乐的福贵后,只能默默承载来自丈夫的无情、漠视和夫家生活的重担,连请求流连赌场和烟花场所的丈夫回家,都只能默默跪在一旁,聆听斥责和奚落而无语凝噎,悄然吞咽下心中的苦水。又如《在细雨中呼喊》的女主人公的“母亲”便是父权文化尺度标准下典型的贤妻良母,这位母亲不但在分娩时没有得到丈夫的关爱和陪伴,还因为无法及时为丈夫送饭遭到粗暴辱骂,此时的“母亲”不但没有自伤身世、缘分伤怀,还能继续容忍丈夫的恶行,并一如既往地向丈夫展示出全部的体贴和善解人意。由此可见,在父权社会下,女性不但没有话语权,甚至也没有抒发怨愤的出口和挣脱牢笼的意识,便只能在男性的压迫下或自我麻醉、或苦苦挣扎。
(二)女性的话语权的丧失
在父权社会中,男性作为一家之主,不但占据极高的家庭与社会地位,与女性相比,也在话语权方面存在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在遇到问题、困难和他人批评时,往往能够清晰、明白地发现他人的问题,但很难客观地从自身进行反思,进而寻找到自己的问题并予以纠正;这一点在余华的小说中也有所体现。男性形象更倾向于将自身缺陷、生活不如意的根源以或粗暴或冷血的方式加诸女性身上,而女性由于话语权的丧失,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倾诉自身的哀情与无奈。由此可见,在父权的压迫之下,女性难以彰显出自己的信仰、内心的独特感受,更无法抗议来自外部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在小说《现实一种》中,当男主人公山峰因为痛失爱子迁怒于妻子,甚至对妻子拳脚相向时,山峰的妻子面对丈夫的欺凌和殴打竟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在被殴打伤重的过程中,她只是轻轻地点头或淡淡地摇头证明自己还活着,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动作。从读者的角度而言,我们自然可以想见山峰的妻子失去儿子之后与丈夫别无二致的痛苦心情,但在小说中,她并没有歇斯底里地表达自身的哀痛与对现实的怨愤,反而还要默默承受丈夫的怒火和发泄。即使余华的部分作品,如《在细雨中呼喊》中,作者给予女性开口说话、表达自身积累情感的机会,诸如冯玉青等女性角色,但关注具体的内容,发现即使女性开口,也并非辩解或为自己在生活中争取更多有利地位,述说自己对家庭、社会付出的种种不易和心酸等,而是用父权社会下为男人提供的侮辱女性的词汇、话语来攻击其他女人,主动伤害与自身性别相同、命运趋同的其他女性。这种女性的失声,正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下女性与男性的从属关系,也告知读者,父权意识如同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女性的肩头,不但约束住了她们的行为,更禁锢了她们的思想,让她们在屈辱的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权利。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和觉醒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自身社会行为和情感的支配者,在客观世界中形成的对自身地位、社会价值的自觉意识;是指女性能够以独立的精神和姿态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实现人生价值,而不必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在余华的小说中,部分女性缺乏对自身的全面认知,只能将自己代入某一个社会角色之中,不带有情感色彩和自主意识地完成自身的社会任务,但依然有一些女性角色在父权的压迫下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如《第七天》中的李月珍,不但努力挣脱父权枷锁,还主动承担了杨金彪恋爱的指导者、陪伴杨飞成长的另一位母亲等角色,她不完全是余华小说中被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传统女性,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遵从本心地完成一系列行为,完成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从以李月珍为代表的女性人物上,读者亦可看出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们首先冲破了父权对思想的束缚,能够在意识层面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特点,认为女性并没有一定要担负的家庭责任或历史使命,而是同男性一样,能够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获得肯定。从行为上,这类女性渐渐摆脱了男性乃至“家庭妇女”这一角色的束缚,希冀一种可以按照自我想法勇敢冲破男性压制、掌控自身行为和命运、重构自我的人生。
综上所述,余华的小说中既有以男性为生活中心、几近失去自我的女性形象,亦有从思想和行为上逐渐摆脱传统道德束缚,以全新社会角色定义自身的新时代女性。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变化,读者亦可窥见在时代的变化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余华对女性的定位及其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