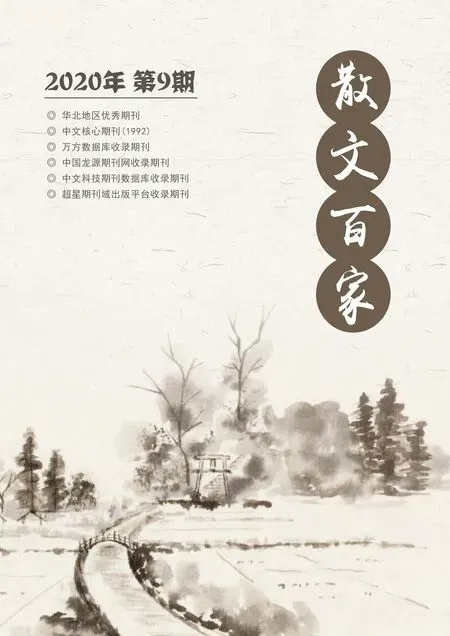寓言与童话
——萧红和迟子建的儿童叙事视角对比
王 睿
曲阜师范大学
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1]作家以儿童别样的眼光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间,能够在作品中展现出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别样面貌。萧红和迟子建虽然都运用儿童视角描写儿时记忆中的自然家园,但是她们对于世界的体认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感悟。
一、儿童视角下的自然家园
儿童是天真活泼的,他们凭借单纯稚嫩的思维与自然本能地亲近,这种本能地亲和,使得人与物的界限模糊而朦胧,自然界的万物在儿童的感觉范畴里都富有了生机和灵气。在萧红清新自然的笔致下,后花园里“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2]在儿童的眼中,自然万物都是活的,一切都是自由的。在迟子建这里,生命盎然的菜园中,“草丛中的蚂蚱蹦得欢,蝈蝈也叫的脆生了。傻子满足得直尥蹶子,小鸡们不停地刨着湿乎乎的土”。[3]大自然中的一切,在孩子们的眼里,有了灵动的气息,呈现出活泼的生命,而且都带上了儿童特有的生机和情趣。儿童率真可爱的举动,使得故乡的回忆中充满童真趣味。
《北极村的童话》小迎灯眼中的晚霞,大红的像炉膛的火,粉红的像小猫的舌头,金黄的像大公鸡的尾巴。细细的雨丝像一根根银色的绣针,一股脑地扎向地面。雨落到地上冒起好多水泡,像踢毽子用的铜钱。这些新奇的想象与比喻打破了人与物的天然界限,是儿童视角和儿童感觉的文字呈现。此外,儿童的感官听觉是分外灵敏的。特别是在寒风冷冽,冰雪覆盖的东北,儿童对于冷和热的感知更加敏锐。小萧红能够听到小狗被冻得夜夜叫唤的声音,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了一样。礼镇上的天灶和他的小伙伴,好像不怕冷似的,穿着大棉袄厚棉裤,冻出清水儿鼻涕,也快乐地在冰上抽冰嘎,月亮出来的时候,清脆的“啪啪”声离着很远都能听到。在北极村小迎灯的感知中,天旱的不光让人难耐,连小泥人的胳膊都烫掉了,老母猪趴着晒大肚皮,小鸡小鸭也猫到了阴凉处。
在萧红和迟子建的笔下,儿童的听觉是真切的,眼睛也是明亮的,能够感知自然中的生灵万物,正因为儿童心灵的稚嫩与视角的晶莹纯净, 使文本的叙事口吻体现出单纯稚嫩活泼清新的气质。正是源于作家贴近自然,感悟生命的人生经历,所以描绘出生动可感、万物有灵的家园画卷。
二、儿童视角下的风土人情
儿童视角的单纯与好奇,使得他们将生活中的表象进行详细地展现。同时,好奇的本性也使他们愿意去追寻生活中的任何可能被忽视的细节。细节化的呈现是儿童观察世界感受世界的方式。萧红生在呼兰河小城里,从小就能够感知到小城的风土人情,比如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人人欢欣鼓舞,这份热闹是为着鬼神,而不是为着人的。女子去拜神,在她们眼里,子孙娘娘也不过是普通女子,也怕老爷打,所以做出特别温顺的样子。“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4]人们守着愚昧,麻木地面对生活中的苦痛。单纯无知的儿童视角,愈加强烈地展现出农村千百年来人们在沉默中安于现状,在畸形中不求改变的生活状态。
在小城人的平凡卑琐的实际生活中,跳大神成为了精神上的盛举。跳大神多是为了给病人驱魔治病,“我”亲眼目睹了给小团圆媳妇跳大神治病,在“我”的眼中小团圆媳妇是一个爱呵呵笑,充满活力与朝气的女孩子,只是走路很快,为什么就要挨打呢?明明好好的为什么要说她病了呢?萧红借助儿童单纯稚嫩的思维,使得内在原因的揭示更具深度。从娘娘庙大会到跳大神,从小耳濡目染接收到的民间传奇,自小滋养了萧红的心灵,这些经历也使得萧红的心思更加敏感细腻,加深了其对于人的关注,呼兰河小城里人按照千百年传下来的传统和规律生活。借助儿童的口吻,“大泥坑”和“跳大神”是萧红讲述的一个又一个的寓言故事,对底层民众愚昧思想进行更“深”与“真”地揭示。
在迟子建的小说《清水洗尘》中,也有本土风俗。礼镇的人每到腊月二十七要放水,每个人都要痛快地洗澡迎接新年。天灶从八岁就开始负责给全家人烧水、倒脏水,但是他总是借别人洗过的水凑乎洗一次,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一盆清水。而在天灶眼中不只是放水,过年也没什么意思,天灶讨厌过年繁重的礼节和要遵守的规矩,在他的眼中“年仿佛被鬼气笼罩了”。[5]即使被妹妹用话语揶揄,使唤他烧水干很多事情,天灶依旧妥帖地做了,手足之间的情谊在吵嘴和动作中得到了完整的展现。同样,当女人的眼中钉蛇寡妇因为澡盆坏了,来请天灶爹去帮忙时,心里再别扭不情愿的母亲,因为淳朴的本性,也让父亲去了。厚道的父亲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帮完忙后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赶了回来。农村人内心的朴实善良在日常小事中得到彰显。在古老的风俗映衬下,人情变得愈加浓厚。在儿童的视角下,农村人的质朴敦厚,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相惜,使得迟子建的小说中充满了温暖和爱意。
无论是萧红还是迟子建,她们的作品中都描写了乡村特有的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迟子建在描绘了北极村和礼镇的人事人情,展现底层民众的质朴与根子里的善良,力图呼吁人性美好的回归。萧红内心敏感,心思细腻,同样也关注底层乡村的人与事,展现出其不同的思想深度。陈思和曾评价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认为她“在坚持启蒙立场,揭发民间的愚昧、落后、野蛮的深刻性与展示中国民间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6]到了《呼兰河传》中,萧红清新雅致的散文化写作,似乎将《生死场》中浓烈的压抑与痛苦驱散了,但萧红的锋利仍在,即揭示底层民众身上落后、蒙蔽的“顽疾”。萧红使自己愈加贴近底层,以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悲悯去唤醒沉默的底层人民。
三、儿童视角背后的荒凉与温暖
萧红总是说我的家是荒凉的,因为在这个“家”里,男女关系不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祖父是唯一的温暖。在她的回忆中,只有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她就向着“温暖”和“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在小萧红的眼中,有二伯始终难以融入“我”的家,小团圆媳妇总是吵着要回家,他们的家在哪里?儿童认知的有限和天真无邪的目光使他们更愿意观察,而非评判他们所不理解的成人社会的人与事,文本也就呈现出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特征。
呼兰河小城里卖豆芽菜的王寡妇,独子到河里边洗澡,掉河里淹死了。王寡妇就疯了,但还晓得卖豆芽菜,静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发疯,在大街上或庙台上狂哭一场,但哭过之后,还是平平静静地活着,仍是得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儿童不解的是人们的反应,从当时似乎轰动一时,家传户晓,不久也就平静下去了。就连她的亲戚朋友也都把事情忘记了。人们的冷漠令人感到心寒,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薄至此。关于人生的定义,呼兰河小城里的人奉行着“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的生存哲学。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逆来顺受的惯了的,粉房里边的人,天天唱着歌,漏着粉。冯歪嘴子日复一日地摇着风车,独自一人拉扯着孩子长大,活着的人依旧在挣扎,有韧性、有力量的努力活着。以儿童世界反衬成人世界, 也就在深层上揭示出了成人世界的病痛。
迟子建曾谈及喜欢采取童年视角讲述故事的原因,“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那一瞬间,它们已经自成气候”。[7]儿童是纯真美好的,不会像大人一样带着审视当代目光去打量世界。即使在别人眼中,通向北极村中苏联老奶奶家的小道是“一具僵尸”,小迎灯依旧热情勇敢地走进了她的世界,俩人成为了忘年交。还有《清水洗尘》中的天灶,母亲帮他倒掉了剩水,他最终拥有了一盆清水,全家人也开始注意到天灾的需求,开始去了解一个儿童的内心。生活中的苦难在迟子建的笔下得到消解,温情的释放使得小说字里行间充满温暖。
苏童评价迟子建:“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温”。[8]因为迟子建始终放低自己的姿态,贴近民众,贴近苦难,带着悲悯情怀去贴近被遗忘的自然角落和生命群体,同样,萧红对民众的感同身受,对作品中的人与事有着透彻的洞察力与深厚的穿射度。萧红怀着悲悯之心去同情与理解苦难中的人民,她的这份人道的情怀和热肠,植根于对底层人民细致的关怀、对家园深切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
四、结语
鲁迅评价萧红是一位“孩子气”[9]的女作家,她的一生都保持了儿童的天真烂漫,特别是顽童爱自由的天性与顽皮,幽默。迟子建从小被母亲认为是淘气的、爱说的、不听妈妈话的孩子。正是由于她们从儿童时期就显现出来的灵动与个性,使得她们更近一步的去感知生活和体悟生命。目光敏锐的张爱玲曾经谈到,对小孩是尊重和恐惧的,“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怎样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把长辈们大大的吓唬一下”。[10]儿童是聪明又敏锐的,萧红和迟子建选择运用儿童视角去展现自然家园的生动美好,以儿童好奇单纯的眼睛去关注生活中的细节,借助他们质朴单纯的原初生命体验,还原生存世界的本来面目。迟子建以温情的目光,讲述一个温暖动人的童话,消解生活中的苦难,给予尘世中的人们贴心的关怀。而萧红笔下的“我”,正如张爱玲描述孩子的眼睛时所说:那么认真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她以冷静客观的目光,以启蒙的姿态,带着体恤底层大众的悲悯之心,讲述着主题是严肃而深刻的寓言故事。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