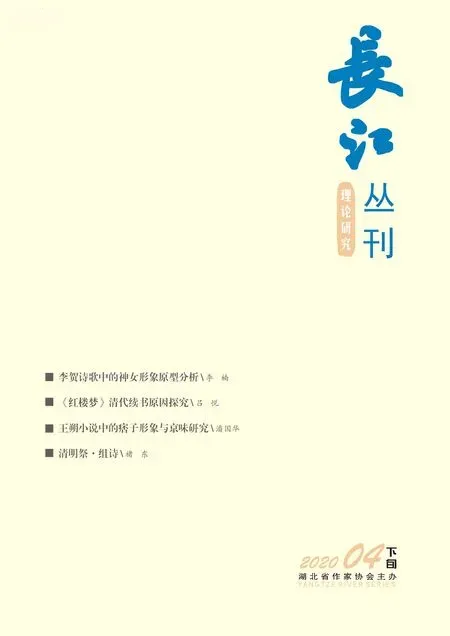递归思维透视翻译症候,隐喻认知促进语言转码
■王枭君 戚亚军/湖州师范学院
“翻译症”即“洋化”的汉语,译文忠实于原意但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如今,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号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语言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认同、共识与默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类共同行动的前提。翻译作为跨语言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语言活动,是不同语言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融合,实现“语言互通”显得更加尤为重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往往得益于翻译[1]。因此,强化自身的对话本领是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剖析翻译症的根本原因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首次创新地写出翻译症的英文“translationese”。他认为‘翻译腔’又称‘翻译体’,是指源语的语言形式,表达方式,句法结构机械性地移植到目的语中,从而造成译文不符合表达习惯,不具接受性与可读性。
翻译症主要表现在译文拘泥于原文的语法语序;不变换词性;直译定语修饰词造成译文中一连串的“的”和不调整状语顺序造成逻辑颠倒这四个方面。首先,没有联系语境:初涉翻译的学生往往停留在词义的表面,同时,译文脱离语境使其概念不清,指代不明。其次,语义搭配不当。最后,文化缺失:缺失文化的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则失去了灵魂。
(一)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象[2]。 我们的思维决定了我们的语言。反之,在基本的句法翻译活动中,语言也支配着我们的思维,也决定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和思维结果。
学生用英语思维理解源语言受到英汉思维原生差异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源语言句法结构的影响,即“思维定式”。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不仅支配着我们的语言,还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往往将人作为出发点与立足点,强调人自身的价值与素养;而西方文化崇尚“主客二分”,探究客观世界,遵守客观规律。由于施事行为主体性,我们一般使用主动句表达想法,在英语中由于施事主语的不明或省略,被动语态成为了英语中常见的语法现象和表达习惯,进而促成了“被字句”的思维定式。
(二)认知转换能力的不足
初涉翻译的学生常面临不会转换英语隐喻句的语造成看不懂无生词句,翻译无从下手,译文无法完全忠实原意的困境。隐喻是英语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一种抽象认知。Lakoff提出,隐喻是建构在经验现实主义上的抽象认知图式,此认知基于人类身体经验,从具体域到抽象域的隐喻投射。人类身体的经验即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介,Srorou认为,认知是语言和客体世界之前存在的一个夹层,而且每一个客观范畴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3]。 词汇亦源于经验,中心义项与边缘意思兼而有之,而边缘意思指代被联想的客体。同时,认知决定语义模糊造成英语中模糊词的出现,也是认知模糊性在语言上的外在表现。
汉语搭配动词遵循泛指对泛指,具体对具体。而英语动词不对称的搭配,如“do laundry,make sense”等,要从语用的角度翻译这类泛指动词。且英语是黏着语,若逐词翻译或逐一翻译从句及修饰成分,译文既生硬啰嗦又不通顺,更不具有可读性,这归根结底就是学生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在语言和文字的转换上不够熟练,并且在联系语境补充省略成分的能力有待提高。
(三)创新变通思维的缺失
翻译症多见于翻译初学者,无关学生的知识储备,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应试教育与母语负迁移造成学生思维固化和创造性思维缺失,译文盲目追求形式对等,打破它需培养求异思维。所谓求异思维,即开拓型的创造性思维,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诱导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问题,“多辟蹊径”,一问多答。
思维固化下盲目追求形式对等主要表现在词义对等、词性对等以及语序对等这三个方面,学生翻译时受到英汉词义对照和源语言句式结构的影响,认定词语的中心义项而忽视其他边缘义项,不取舍意义累赘词,不结合语境,不增词补充于省略成分等,这也再次反衬出学生语言转换能力的不足。尽管部分学生在翻译时意识到了这样的译文存在语病,但依旧拘泥于源语言的句式结构,既缺乏创新思维,又不敢打破句子框架,将各个语言成分加以重组和变通。
二、克服翻译症的有效途径
(一)利用递归思维进行灵活转换
所谓递归思维,是指客观事物内部存在循环或可逆的递归性。汉语中部分动作的概念化呈现出双向可逆特征,而英语却表现出单向不可逆特征;汉语对时间的表征具有二维空间性,而英语却对其则呈现出一维线序性[4]。英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造成二者时空性思维差异。在无法改变源语言语序的情况下,可调整目的语语序、语态来实现表达方式的变通。
英汉的思维差异在句法和型态上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句子结构与形式不同;二是主被动的表达习惯差异。从语言表达型态看,英语是向左扩展,句首开放,句尾封闭;而汉语恰好相反。英语句子一般只有一个主干句,主次分明,结构严谨并且逻辑性强,使用从句修饰其他成分来表达复杂的思想,长句的整合使得思维逻辑更加严密;而汉语是语用型的语言,旨在于意义通顺,注重语感与变通,且以短句居多,组句自由度更大。以事件为中心的汉语有着严谨的时间先后逻辑顺序,主动语态的句法构造使英文更具有可译性,此外,英汉翻译涉及到空间大小,心理上的轻重缓急以及事理上的因果等。
(二)通过隐喻映射进行认知重组
维特根斯坦提出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破旧立新,融合文化、历史、社会条件等因素归纳人们认知客观事物的变化过程,产生一词多义——隐喻认知思维演变的产物之一,也是在不同语境下心理表征的外在表现。在翻译时,要结合文化、语境,联系生活,找到认知上的隐喻对相似的抽象物体建立关联,充分挖掘词汇边缘义项,在词的翻译上避免思维定式,严谨措词。
[例1]The sight of the fish suggested a brilliant idea for submarines.
人们看到鱼,便有了潜水艇这样一个伟大的设想。
suggest:建议,提议;显示,表明;推荐;暗示,暗指;使人想起,使人联想到;考虑某事物。
通过分析suggest一词的义项可以看出演变出来的义项之间存在联系,并且都与中心义项存在关联。“由建议”到“暗示”,再到“启示”与“使人想起”体现了词义的演变过程。 此处suggest为某人想到某事:come to somebody's mind,occur to somebody。
就英汉翻译词类转换而言,常见的词类转换有名词化,动词加副词译为名词加形容词等。
[例2]“I suppose boys think differently from girls,”he says.
他说:“男女有别,想法不同。”
动词加副词结构中,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应转换成名词加形容词。但汉语力求语言简洁与结构对等,译文需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
(三)语言文化视角下的功能对等
思维与认知的不同大多可以追溯到语言在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往往导致语码转换过程中的意义流失或内容扭曲,随之产生翻译的功能对等问题。所谓功能对等,是为了让读者更加有效地接收信息,把握文化语境,适当借助文字变换来有效传递信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功能对等翻译更加注重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联系,更加注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从而使得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可以实现有效沟通,防止出现语义脱节的现象[5]。
[例3]Man proposes,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此处God译为“天”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功能对等是信息和文化的融合,将原语文本的读者理解和欣赏方式与译语文本的接收者的理解和欣赏方式加以比较[6]。
文化不分良莠。在大力推行构建人类命运体的新时代,认识文化多样性与尊重文化差异,顺应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文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并维护良好的国际关系,有效避免国际误会及妥善解决国际争端。社会文化心理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形成和积淀,具有长期性、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又处在不断变化、创新和发展之中,具有阶段性、创新性和动态变化性[7]。 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介质,应顺应时代潮流,在继承中发扬与创新,成为推进全人类友好相处及合作共赢的中坚力量之一。
三、结语
翻译超越学科,高于技术,是跨越文化的桥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流下,翻译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专利,更切身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翻译的前提是了解东西方文化认知差异,翻译的过程是不断打磨并形成认知机制上隐喻思维,不断培养递归思维作用于翻译与实践。在中国不断屹于世界之林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继承与发扬中国文化。当翻译不再是机械性转换语言输出和移植句法结构的工具,而是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的通行证时,翻译症也不再有机可乘。言语的排列组合千变万化,但只有掌握了翻译的真谛,才能理解翻译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