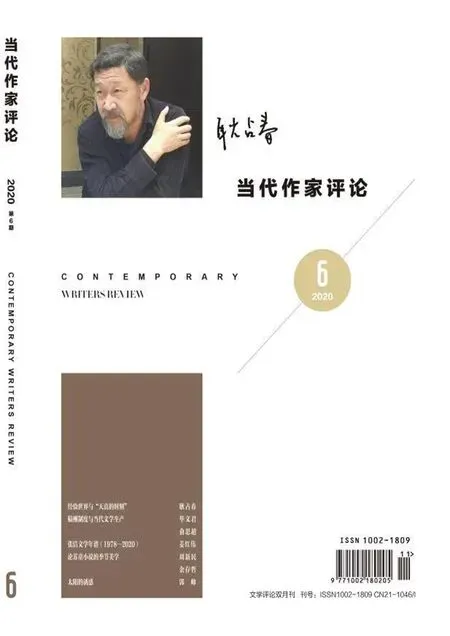童年生命感与“根性”精神的共振
——孙卫卫儿童文学创作论
李 琦
在“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孙卫卫的创作是颇具个性与辨识度的。20世纪90年代,他凭借散文创作初登文坛,完成了从“文学少年”到“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转变。此后,孙卫卫在儿童文学的园圃中默默耕耘,一方面在他擅长的散文领域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小小孩的春天》(2012)、《爸爸小时候》(2018)、“孙卫卫·少年心”系列(2020)等作品;另一方面他也力图拓展自己的文学疆界,在小说、绘本等体裁领域积极探索,贡献出儿童小说《胆小班长和他的哥们》(2003)、《一诺的家风》(2017)、《装进书包的秘密》(2019),幻想小说《会说话的书》(2017)以及绘本《回老家过年》(2019)、《爸爸,出发!》(2020)等多部品质稳定的作品,呈现出“多面开花”的创作态势。
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深刻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娱乐化、同质化作品的大量涌现,使儿童文学的深度写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在此时代语境下走上创作道路的孙卫卫则自觉与“泛娱乐化”保持距离,始终以“修辞立其诚”的创作姿态写作。孙卫卫在创作中力图平衡接受主体与创作主体间的关系,既反对忽视儿童性的训诫式写作,也对一味取悦儿童的创作倾向保持警惕。具体来说,他的创作一方面带有明确的读者意识,重视对儿童心灵和思维的理解与表达,作品呈现出鲜活的童年生命感;另一方面他重视创作主体的作用,以儒家文化精神作为“文化根脉”,以经典文学作为“精神根底”,致力于创作富有“根性”精神的作品。童年生命感与“根性”精神相互渗透,彼此激活,共同组成了孙卫卫个性鲜明而又风格多样的文学图景。
一、沿“小儿之目”:复活童年生命感的文学表达
“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是周作人1913年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中对安徒生持有的儿童心性的赞扬。对于成人作家来说,童年生活已经远去,如何最大限度地葆有儿童心性、贴近童年生命状态,是创作中需要时刻面对的课题。
阅读孙卫卫的儿童文学作品,常常有种童年的“在场感”,仿佛有位率真可爱的男孩,正在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的生活趣事。男孩面容清爽、稚气未脱,话语间还带着一点羞涩,一点执着与一点调皮。如此稚性的文气,与作家“少年心”的葆有休戚相关,保持“少年心”的秘诀不仅有赖于他对当下儿童生活的自觉接近,更来源于自身童年生命经验的激活。在他的创作中,童年自我与成年自我从未割裂开来,而是以“记忆”的方式自然勾连,由此唤醒的不仅是回忆里渐行渐远的人与事,更有尘封在成年生命体内的童年感觉。较之于抒情,孙卫卫的散文更喜欢以叙事的方式对童年旧事娓娓道来,并将童年生活的真实感受融在细碎的日常书写中,使文章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质感和情味。记忆中的美食、家乡的节日、童年的恶作剧、少年时的文学梦……这些作家的专属回忆尽管与当下的儿童生活存在着明显的距离,但叙事中所传达出的纯真童心、生动童趣以及儿童的隐秘心理却是可以跨越代际隔膜与现在的儿童读者对话的“情感联结”。值得一提的是,在具有自传性质的散文写作中,作家沿着“小儿之目”看到的不只有童年的纯真面向,有时还有更为复杂的生命本相。面对偷钱、虚荣心、对异性的懵懂好感等处于童年“中间地带”的往事,他亦能够以坦诚的姿态解剖心灵,并通过成年视角的介入完成对“不完美”自我的修正,这样的书写正是“以自己为标本研究生命”的典型写照,同时也为读者展示了“成长”的可能。作家通过记忆的复现点燃自身的童年感觉,使散文呈现出真实、饱满的童年生命感,与读者之间的心灵通道也由此打开。
在儿童小说方面,熟悉孙卫卫的读者也会在典型人物、情节设置等方面捕捉到少年“孙卫卫”的痕迹。童年经验的滋养,使作家在进行虚构性文学的创作时,也能够保持生动的写作感觉。《胆小班长和他的哥们》中有一段关于竞选班长的精彩描写。“我”在哥们儿赵小帅的建议下,把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改造成了自己的竞选词,并在竞选当天把演讲稿放在文件夹中捧读,造成一种庄严宣誓的神圣感,读来令人捧腹。对成人活动的模仿和向往,是一种深层的童年心理机制,班马在20世纪90年代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并将其称为“儿童的反儿童化”。他认为:“吸引儿童读者的魅力所在,并不在于对儿童状态的反应,而恰在于对儿童状态的摆脱。”(1)班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第36页,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作者对儿童心理的深度把握,与其对童年回忆的文学转化密不可分,“赵小帅”这一令人捧腹的“机灵鬼儿”形象在作者的生活中就有着现实的原型。陈思和曾这样表述作家在创作中“复活童年”的意义:“通过童年记忆来挖掘和激发自身具有的儿童生命因素,也许这种因素早已被成年人的种种生命征象所遮蔽,但是仍然具有活力。通过记忆把自身的童年生命因素激发出来并且复活,通过创作活动把它转化为文学形象,那是儿童文学中最上乘的意象。”(2)陈思和:《儿童文学:尽可能地接近儿童本然的生命状态》,《文汇报》2019年9月23日。因此,记忆成为了孙卫卫深入童年心灵深处的有效通道,他的创作也因此显示出对儿童心理的深刻理解。
除了童年记忆的调动,语言的智慧运用也是孙卫卫作品富有童年生命感的重要质素。作家对“浅语”艺术有着自觉的追求,他无意于辞藻的华丽与雕琢,而是在创作中选择简洁、朴实的语言进行叙事,这样的语言正是林良所说的“浅语”。林良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应懂得“运用儿童所熟悉的真实语言”(3)林良:《浅语的艺术》,第17、20页,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进行写作,他进一步解释道:“儿童所使用的,是普通话里跟儿童生活有关的部分。用成人的眼光来看,也就是普通话里比较浅易的部分。”(4)林良:《浅语的艺术》,第17、20页,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孙卫卫经常采用一种近乎于原生态口语的笔调进行叙事,他在散文中回忆童年时的“慢生活”,那时候交通尚不发达,出门主要依靠走路:“经过人家门口,都有狗向我吼叫,我家也有狗,狗是我的好伙伴,我并不怕它们。”(《走路》)当谈及自己“胆小”的性格特点时,他这样写道:“我想游泳,我妈妈总是说,不要去不要去,水库里淹死过人。我想上树摘桑葚,我妈妈说,不要上不要上,你没看你的叔叔上次从树上摔下来成了骨折。”(《我的胆小》)这些口语化的叙事口吻看似普通,不事雕琢,却是儿童在生活中使用的真实语言,也是最为贴近童年生命感觉的语言。此外,儿童文学的语言是否贴近儿童天性与语句的组合也关系甚密,孙卫卫善用短句,且在早期创作中,他常通过语意的“重复”增强叙事效果。如在《班长上台》中,作家写“我”对萧老师的喜爱:“当然了,萧老师也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而不单单是相貌好看。萧老师才貌双全,这一点是无疑的,不需要证明的,一看就知道的。我这么啰嗦,只是想强调,萧老师是一个有才气、又很漂亮的人,我没有骗你,也不想骗你,我知道骗人不好。”这段独白的叙述者是作为小学生的“我”,词汇量有限,表意重复正是这一年龄阶段儿童正常的“童言童语”。因此,这种看似“啰嗦”或“赘述”的话语实际是作家巧妙运用儿童语言的生动体现,也正是孙卫卫作品中的“语言味儿”。
二、扬“传统之髓”:儒家文化精神作为内在质地
五四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被放置在相对立的话语框架中,因为“当时的儿童文学并未独立或未完全脱胎于成人文学或成人视角下的文学”,(5)王海峰、季捷、汪愉翔:《中国当代儿童绘本的前行之路》,《艺术广角》2020年第3期。诞生于这一历史语境下的儿童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新文学“反传统”的文化基因,但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实际上是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面对启蒙艰难性所采用的一种话语策略。如今,在重估“传统”的思潮下,儿童文学与传统文化间的关系也被重新思考。虽然“传统文化”的内涵极为驳杂,但儒家文化思想无疑是其中的主体部分。在孙卫卫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清晰可见,可以说,儒家文化精神作为一种价值信念和精神资源,构成了他创作中的“文化根脉”。
“自省”是儒家修身之道的重要内容。“自省”即“对自身的仔细观察和审视”,(6)王立皓、汪凤炎:《西方的元认知与儒家的自省:概念比较》,《现代教育管理》2010年第3期。“吾日三省吾身”的自省意识在孙卫卫的创作中有着许多显著而具体的表现。在儿童散文、序跋、书话等纪实类作品中,常常可见作家经过岁月淬炼、阅读思考后的生命体悟,其中不乏对自我品格修养的要求。例如,回忆式散文《偷钱》以坦诚的自我剖白对儿时所做的错事真诚忏悔;《做人比做文重要》中,作者对自己年少时急于发表文章的功利心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并为自己树立起“做人”先于“做文”的准则。自省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心性修养,对于孙卫卫来说,这是修身的需要,也是“为文”的基础。自觉的“自省意识”使得孙卫卫创作中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得以与虚假的说教保持距离,呈现出“以诚动人”的文学力量。
孙卫卫的儿童文学创作常蕴含着对儿童教育、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展现出对儒家“文以载道”传统的认同。他曾在创作谈中多次谈及创作的初心:“真正的儿童文学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写出来的,写作者首先要对孩子有一种责任感,写出的作品,应该对他们的成长有益。”(7)孙卫卫:《推开儿童文学之门》,第290、102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我希望我的文字可以影响正在成长的小孩,哪怕影响一两个人,这是我可以做到的。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有别人,还有小鸟小虫和花花草草。公平和正义比生命都重要。”(8)孙卫卫:《推开儿童文学之门》,第290、102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对于儿童文学的“载道”问题,人们有一种常见的误解,那就是将“教育性”置于“儿童性”的对立面,认为“儿童本位”的作品就是“只要儿童的心理,不要大人的世界”,(9)朱自强:《由高向低攀登的艺术——谈李少白童谣》,《文艺报》2016年8月31日。这种看法其实是将“教育工具论”与“教育功能说”混淆的结果。实际上,优秀的儿童文学并不是要废弃“载道”的功能,关键是要对“载什么道”以及“如何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辨析。在孙卫卫的创作中,“载道”绝非是以成人的规训压抑和框范儿童,而是通过饱满的文学性,激活蕴藏在儿童生命体内的人性光亮地带,这包括乐观坚韧的生命意志、诚实朴素的精神品质和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等。同时,孙卫卫也注重处理“道”与“文”之间的平衡关系,力图使二者呈现出“盐之溶于水”的状态,他以抗击疫情为题材的绘本《爸爸,出发!》就很好地展现了这种“融合”。绘本以小男孩“我”的视角展开,讲述了疫情背景下,作为医生的爸爸参加抗疫支援行动出发前的故事。“爸爸,出发!”这句口令在绘本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父子间的游戏之语。爸爸平时会和“我”玩“发射火箭”的游戏,当一切准备就绪,“我”扮演的指挥官会向爸爸扮演的士兵发出“出发!”的口令;另一次出现则是在临别之际,爸爸再次以士兵的口吻向“我”汇报:“报告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这一次“我”喊出的口令“出发!”成为了现实中的告别语,孩子本能的不舍、懵懂的理解和大爱的感染在此处交融,文本的意味也由此晕染开来。这一叙事细节的设置,使文本对英雄主义的表达注入了亲情的温度,从而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孙卫卫还从儒家人生观与伦理观中汲取有益部分,为探索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提供精神资源。儿童小说《装进书包的秘密》将目光放置在了“童年苦难”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学主题上,并通过对典型人物姜听棋的塑造,表达了对儒家“刚健有为”人生观的认同。“刚健有为”是儒家哲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作为儒道思想起源的《周易》将其概括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装进书包的秘密》中,主人公姜听棋原本拥有安稳平静的童年,然而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妈妈的双腿,也使小家庭的命运急转直下。但姜听棋没有因磨难而陷入怨天尤人的悲戚情绪,而是坚强地照顾弟弟,安抚妈妈,展示出克制、坚韧、乐观的精神品质。小说《一诺的家风》以儒家学说中的“诚信”观念为思想资源,建构出清正明朗的人际关系图景。儒家文化重人际关怀,追求社会群体之间的仁爱和谐。可以说,在儒家伦理观念中,“诚”是天地人伦的至高原则,正如孟子所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小说既谈“家风”,便离不开成人形象的塑造:无论是一诺妈妈宁愿失去工作也不愿为公司造假的“诚实不欺”,还是一诺爸爸对于归还养女的“言而有信”,或是小卖部老爷爷帮助一诺妈妈找工作时的“言出必行”,都在无言处践行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儒家文化精神。小说中成年人的守信品质对儿童的影响不是通过强势的说教来完成,而是以细节处的言行滋润着童年的心灵,激发儿童在内心深处产生向善向真的愿望。可见,作家通过对代际影响的思考,传达出一种大写的教育观,即成年人对儿童的“教育”,首先是以“自我教育”为前提的。如果说,儿童文学担负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重任,那么除了“儿童性”与“文学性”外,“感召力”也应被纳入儿童文学的批评标准中来。所谓“感召力”,简言之就是作品所具备的对于现实儿童行为、性格、人格等方面的影响作用。虽然文学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很难开展实证性研究,但已有大量社会学研究证明,现实或象征性的“榜样行为”会影响儿童的行为习得。从这一层面讲,孙卫卫创作中真实可感的“正面形象”无疑为现实儿童生命状况的提升提供了可效仿的对象。
三、承“经典之脉”:阅读滋养与文学风格的生成
孙卫卫的文学成长之路离不开阅读的滋养。“爱书人”是孙卫卫自身十分认同且喜欢的称谓,对他来说,“书就是生活”。(10)孙卫卫:《喜欢书二编》序,《喜欢书二编》,第3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5。刘绪源曾将“爱书人”的阅读与“普通人”的阅读划分开来,认为“普通人”将阅读视为学习、工作的需要,而“爱书人”的阅读则与日常生活糅合在一起,难以剥离。孙卫卫显然属于后者。在《书香,少年时》《喜欢书一编》《喜欢书二编》这些关于淘书、买书、读书的书话集中,可以清晰见出作家的阅读旅程和精神成长。在作家广泛而丰富的阅读谱系中,经典文学的阅读、吸收和转化塑造了他的“精神根底”,使他的写作显示出“纯正”的文学趣味和持续发展的潜能。孙卫卫曾在创作谈中多次谈及喜爱的作家,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孙犁与汪曾祺。两位作家的文学风格虽不能以流派简单概括,但他们在心性气质、文学思想、创作志趣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语言的考究、文体间的互渗等。孙卫卫以上述文学旨趣为艺术上追求的目标,并在创作实践中裂变出具有创作个性的多样景观。
“真诚”是孙卫卫儿童文学创作的突出特征和稳定品格,这一特质的形成离不开他对孙犁文学观的自觉追崇。孙卫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孙犁“追随者”,他曾多次谈及对孙犁为人、为文的感佩,其中令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孙犁对待文学的“真诚之心”。孙犁把真诚视为作家创作的基本原则,他曾说:“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11)孙犁:《晚华集》,第19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孙犁的创作大多源自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情感的流露也出自创作时的真实性情。比如,面对自己后期风格的变化,孙犁坦诚地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12)孙犁:《秀露集》,第1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孙犁“修辞立其诚”的创作理念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后来者孙卫卫的创作。无论是纪实类作品中追忆童年的情感涌动、自省自悟后的心灵成长,还是虚构文本里优缺点并举的儿童形象、崇高与平凡共生的抗疫英雄,孙卫卫的儿童文学创作可以说始终以一个“诚”字贯通。周作人曾说:“个人所特别真切感到的事,愈是真切也就愈见得是人生共同的。”(13)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迅风编:《现代散文随笔选》,第13页,上海,太平书局,1944。可见,作家对自我情志的表现越是诚实,就越接近人类共通的思想或情感,其文字也就更容易跨越时间、代际、文化的隔膜而唤起读者的“共情”。
语言风格的生成是作家写作风格成熟的重要标识。孙卫卫的文学语言在不同文体、不同时期里既有稳定的“守”,又有自我突破和沉淀后的“变”,在二者之间,作家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且具有辨识度的语言风格。纵览孙卫卫的小说创作,不难见出其语言风格的嬗变轨迹。在他早期的校园小说《胆小班长和他的哥们》《男生熊小雄和女生蒙小萌》《班长上台》中,语意重复是显著的语言特征,通俗来说,就是以啰嗦、饶舌的话语方式模拟儿童的生活语言。这样的写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语言的童稚感和趣味性,但作家也清醒地意识到,若一直延续这样的语言风格,创作道路会逐渐窄化。因此,从《一诺的家风》开始,孙卫卫的小说创作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叙事上更加重视写实和白描,语言也走向了简练、朴实。比如小说《装进书包的秘密》结尾处写男孩姜听棋终于等到妈妈有了苏醒的迹象:“妈妈经常说,如果是难过,泪就是咸的,如果是幸福,泪就是甜的。姜听棋觉得自己的眼泪,有点甜,又有点咸,似乎又都不是。”此处作家以最简练的文字道出了姜听棋交织着悲、欢、喜、哀等多种情绪的复杂心理,也写出了儿童在苦难中成长的生命力量,这正可谓是孙犁所说的“朴实无华,而真情毕现”。(14)孙犁:《耕堂读书记》,第99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
散文是孙卫卫最为喜爱的文学样式,也是他自步入文坛以来至今始终坚持创作的文体。在散文创作中,语言的“平淡”是孙卫卫一贯的艺术追求。所谓“平淡”,“是指称一种素朴自然、平和淡远,无涉于刻意雕造的艺术风格和境界”。(15)汪涌豪:《范畴论》,第12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对孙卫卫来说,这一语言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孙犁、汪曾祺等前辈作家的影响。“大道低回,大味必淡”是孙犁十分崇尚的文学境界,他曾说:“我写文章从来也不选择华丽的词,如果光选华丽的词,就过犹不及。炉火纯青,就是去掉烟气,只有火。这要有阅历,要写得自然。”(16)孙犁:《尺泽集》,第12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而汪曾祺也曾对苏轼“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文学追求表达过由衷的欣赏。同时,“淡”并非是寡淡无味之意,而是以“平淡近自然”的文学语言提炼出日常生活的“色”与“味”。孙卫卫写小时候物资短缺,每逢家里做油饼都不敢向邻里声张:“妈妈似乎知道我要大声叫起来,她一下摁住了我,差点要把我弄倒。我笑了。我知道必须保守这个秘密。妈妈也笑了。”“叫”“摁”“笑”等单音节动词的使用,为看似普通的生活场景增添了俏皮、生动的韵味,也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心思与期待的喜悦表现得恰到好处,趣味盎然。他也写生产队分西瓜的场景:“男的都特别着急,好像不及时吃就会被别人抢走,几下就啃完了。女的,一口一口,吃一半,剩下的给孩子。瓜子也舍不得吐到地上,都攥在手里,吃完西瓜,再嗑瓜子,这些瓜子,可以在嘴里嚼大半天。”这看似朴素的白描,却不着痕迹地将生活的本相展示出来,毫无雕琢之气,其中滋味留给读者品味。与早期创作对比,孙卫卫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在“平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了语言的留白和暗示性。《我小时候》是作家于2020年出版的又一部儿童散文集,在这部散文集中,可明显见出作家在语言“节制美”方面的努力。《小河弯弯》一文写童年时代家乡的小河以及与它有关的童年往事,在结尾处作家这样写道:“从小,那条小河就是我心目中的大河。”对于一“小”一“大”的含义,作家没有继续解释,而是将童年的意义留给读者去补白。这样的处理,正是对孙犁所提倡的“弦外之音”的遥远呼应。
大多数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都会受到经典作家的影响,在文学史上,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前辈名家厚重的思想、高妙的文学技法自然会为后来者的精神世界打下经典的底子,但对于后来者来说,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话题。对孙卫卫而言,孙犁、汪曾祺等经典作家着实对他文学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他并未以“刻板”的模仿姿态跟在前辈作家的身后亦步亦趋,而是将真诚的文学理念、平淡朴实的美学追求等经典气韵与他的个体生命经验、乐观入世的精神信念相融合,绽放出富有创作个性的花朵。
结语
整体而论,孙卫卫的儿童文学创作既重视表现童年独特性的生命状态,也看重儿童文学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作用,显示出儿童观上的“鲁迅方向”。五四时期,周氏兄弟对现代儿童观的建构深刻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周作人偏重儿童“自然性”的“儿童本位论”相比,鲁迅关于“人之萌芽”的儿童观则更具有思想内涵的辩证性,即一方面提倡对幼者生命状态的尊重,另一方面也看到儿童的心灵并非全是天真,因此需要帮助其发展人性中的真善美,警惕和修正恶的萌芽,使其成为“社会的人”“完全的人”。但这一儿童观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究其原因,多是出于颠覆“成人本位”文化惰性的需要。在当下,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读图时代”的到来,视觉媒体与成人读物对儿童的吸引力不断增强。面对这一时代语境,鲁迅儿童观的深刻性被重新认识。而孙卫卫的儿童文学观正是接续了“鲁迅之脉”的结果,他的创作始终怀着对“未来之人”的赤诚之心,将儿童文学创作视为以生命点亮生命的神圣事业,这对于消费主义语境下“儿童本位观”滑向“儿童至上论”的偏颇态势是一种富有力度的校正。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