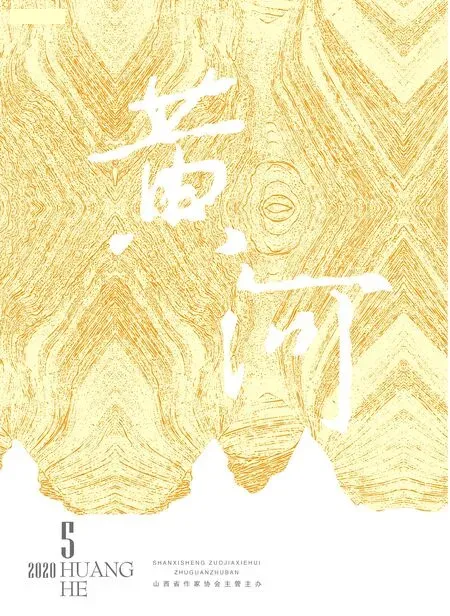小说的律法与伦理
曾攀
一
新的时代精神状况,必然带来新的历史语法,而新的生存秩序与生活诉求如何得以确立,并在适当的表述中形成自身的形式话语,意味着个体的精神延伸在一个律法愈发完善的历史时段中,如何得以探询新的落脚点,并于焉形成新的伦理支撑,这是时至今日,当代中国小说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进一步说,随着社会政治的逐步深化与生活实际趋向精细,更需辅以法律的规训与惩罚,这也是后革命当代需要追及的问题。可以说,法制化的当代中国开始不断涌现新的文化规制与生活法则,在这种时代境况下,小说文本内外的律法与伦理发生了深刻的勾连与纠葛。
自新时期尤其是到了21 世纪前后,中国对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修订、 颁布和执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通过并于次年施行,2018 年进一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1995 年通过,于2012 年修正,原1957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条例》废止;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发布且于2013 年实施;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此外,《反贪污贿赂法》《个人收入申报法》等也不断颁布,不仅如此,各级反贪污贿赂机构、纪律监察委员会等也逐步设立并发挥了广泛的社会效用。可以说,无论是从社会结构、体制机制,还是在社会常识、时代观念方面,都形成了新的规训机制,并且影响现实的行为规范、文化旨归、生活习惯等。反映在小说中,则不仅涌现了新的公检法题材,官场小说、反贪小说、刑侦小说等类型文学层出不穷;而且在传统的纯文学叙事中,同样融入了新的价值判断、生活伦理、精神倾向,在人物的主体性与主题的倾向性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样态。
不得不说,在当代中国,小说在情、理、法等方面展开的多重探索,使其在文本中不断发生摇摆摩擦,并由是出现新的价值伦理困境。也就是说,小说越来越多地涉及关乎情与理、情与法的交汇,多重向度的价值取向,熔铸了小说情节结构的环环交互,其中不仅增强的是戏剧性的推演,而且也内在于叙事本身的推动力,形成文本新的当代性;另一方面,小说的律法与伦理之间的复杂互动,不只是出于区分简单的善恶好坏,而更注重当代人及人性发抒中的罪与罚,以构成小说内部丰富复杂的层次。
当然在这里并无意于移置现行的法律条例,也不局限于二元论视阈中的善恶区分和道德判断。在小说的叙事空间之中,生存境况与生活意志、精神法则与观念结构、社会常识与情感伦理等诸种维度,不断充实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叙事映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小说更深层次的叙事伦理。因而,在现实的律法规约与小说的精神伦理之间,实际上喻示的是爱与恨、情感与理智、罪恶与宽恕等不同面向之间的现实协商。
周梅森的长篇小说《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直至后来因改编为电视剧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人民的名义》等,以及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常书欣的《余罪:我的刑侦笔记》等,在善恶分疏明晰的当代官场小说、反腐小说、刑侦小说等类型中,相对二元分立的正义、善良、光明得以声张的同时,也时常透露出对情感和伦理的同情深化。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世俗化的小说叙事在设立基本的政治法律和规约常识的同时,始终高悬的情感判断和人性尺度,在法与理中不至于损伤人性的质地与生活的原味。然而曲折之处在于,规则与法律及其实施的过程,也是警察、法官、纪检人员等执法形象作为小说文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叙事形象产生并发挥效用的过程,这些人物形象及其背后所携带出来的特定法则,与小说所闪烁的人性与情感,往往存在着龃龉甚或是冲突,也就是说,内在于小说深层的人的罪恶、欲望,人性的游移和两难,伦理层面的错位等,简言之,小说所意欲铺陈的庞杂主体与驳杂现实,与单一的意识形态律法及国家机器之间,势必难以调和。这样的境况一方面反应在情节结构与叙事进程中,事件/案件真相的一再延宕,甚至叙事者根本无意于惩恶扬善的价值探寻,而更多地挖掘人/事之中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另一方面,在人物形象上,警察、法官等执法者的出现,同样需要建构自身的人性层次,破除对人物直接生硬的单一理解。
因而,当代中国小说不断涌现的律法与伦理的周旋中,新的人物形象及其背后的时代语法,编入了事件与结构的讲述序列,同时纳入生活的认知和情感的认同,不仅构成个体日常的底线与常识,而且糅杂了丰厚的美学格调与人性色彩。两者一般而言是彼此呼应的,但在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叙事中,国家与社会之法,往往让位于生活之法、人心之法。宕开一处说,在文学界域中,与其说这是一种法的迷失,不如将之视为内蕴于形象表达的精神之法、灵性之法与存在之法,这个法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基于/超乎现代律法之上的,个体与群体共同分享的生存/生活意志,现实之法根植于精神内在之法,前者不断规范制约后者的存在,而后者则可以拓宽前者的概念与范畴,也就是说,小说的律法与伦理之间的彼此融合冲击,往往能够促成新的精神法则。
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天体悬浮》等小说,从讲故事的角度而言,作者不在乎营构波澜起伏的情节,但却在意丰富复杂的人性世界,写出人心的回环转换,更呈示他们的灵魂坚守;然而,田耳小说往往能够通过耐心的铺垫深层次的精神伦理,并于小说将近终局之际,不经意地点缀几笔,将人物在世俗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寄寓其间的精神与灵魂之高下,揭示殆尽。如是这般表面上仿佛无所作为的叙事手法,实则有其欲有所为的深层意图。在《一个人的张灯结彩》中,哑巴小于倾心罪犯钢渣,然而最后钢渣被捕,而小于依旧保持初心,“一个人张灯结彩”,守候恋人。田耳叙事不携带价值立场,即便面对为非作歹的罪犯,但叙事却不入道德评断,从而建构出惊心动魄的情感世界。
不仅如此,小说的偶发性伦理旨向在普遍性与强制性的规约面前,除了遵从基本的常识原理,其更关注的是被遮蔽的边缘和失语的存在,当代小说内在伦理总是倾向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与群体,让他们不被湮没,不被压制,使他们的声音得以记录和发抒,尽管他们的声音扭曲甚至不无罪与错,甚至充满着生命的黑暗与卑微,但这个过程却因人性的复杂、情感的丰厚、欲念的声张等非理性的诉求,反证了小说存续的价值和意义。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叙述了京漂一族的生活史与精神史,小说集最后一篇《兄弟》,讲述北京西郊上演的一场场械斗并致人死亡,执法者开始彻查并清理西郊京漂人口与出租屋;而另一头的小人物戴山川来到北京为寻找“另一个自己”,却最终在执法队的推土机下,“抢救”出了鸭蛋的弟弟“鸡蛋”的照片,如是这般的带着同情的理解,让他舍生忘死地助人,而也就是这样的“壮举”,让他真正找到了“另一个自己”,那个得以弥补他童年创伤的更为完满的饱满的自我,因为这样有情有义的伦理表达,代表着小说内在的新的精神法则,在叙事中被有意强化,从而得以在小说中不断掘进人物深层的内心世界。
二
现代以来的中国小说,警察形象几乎是隐匿的。无论是清末民初租界的印度巡警,还是国民革命时期镇压学生与工人运动的警察形象,又或者是当代中国50—70 年代多有出现的执法者与违法者兼在的革命者……可以说,20 世纪以来中国革命与启蒙起伏的历史中,执法者以及法律规则的形象往往难以彰示。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段时间以来,律法与执行者形象则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便是以无关紧要的寡淡无聊的形象,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作为背景与烘托而存在。总而言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律法与执法,都不作为文本叙述的中心与重心,文学叙事不考虑他们自身所承担的功能,也没有展现其中不同层次的主体性。
然而随着中国法制化的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警察等相关执法者形象及其主导的案件和事件背后,同样隐现出了文学的现代性和人性的当代意义。尤其在违法与执法案件中,社会环境的更新及其所承载的复杂人性表象,透露出越来越多的现代性经验,其中深刻之处,往往层层剥开当代世界真实伦理道德的内在肌理,不断映射人性的欲望、罪恶,并为其中的情感结构所包裹。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的法律规则与国家机器开始不断进入小说视野,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好的小说而言,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粗暴的干涉,也不是直截了当的植入,而是在迂回曲折的叙事结构中,与现代性的经验交互,彼此映衬和参照,互为解答与可能。
此外,法律与规约与后现代叙事伦理之间,往往还呈现出更为隐晦复杂的精神指向。格非的《傻瓜的诗篇》中,莉莉在父亲去世之后,陷入深刻的自我谴责,随后去派出所自首。遇到了一个中年警察,警察的行为与身份的落差,成为小说人性和欲望对抗的重要关节,格非对人物幽暗心理的把握非常精准,不仅将伦理困境推向深处,而且由此审视律法的存在及其权力的施行。
弋舟的短篇小说《出警》将笔墨沉入当代民警的日常世界与内心世界,在城市中,在生活的深处,作为“人”的执法者与作为“人性”的幽暗寂寥,一一涌现。 “小吕出门时替我关了灯。外面旋转着的警灯把斑斓的光投射在天花板上。我举起手,光着的胳膊被照进的彩光裹缠,红红绿绿,像是纹了身。这一刻,我又想到了我们农大‘解民生之多艰’的校训。随后,我也感到了那大水一般漫卷着的孤单。 ”小说在意的是警察内在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伦理,并且在极为日常琐碎的生活表达中展现警察的困惑与迟疑、坚忍与韧劲。相较而言,周凌云的《所长小超》则直击派出所的工作日常,凸显普通民警的英勇机智和果断担当,小说通俗自然,警察作为职业身份,更作为人的主体形象得以展现。
黄咏梅的小说《父亲的后视镜》写父亲寻常而不普通的生活遭际,写到后来,父亲被赵女士诓骗,“她还把父亲衣柜里那些值钱的东西都变走了,包括:两只夏家祖宗传下来的金元宝、一对母亲的玉手镯、一只瑞士老手表以及那架还装着风景的莱卡照相机。父亲找遍了衣橱、壁柜、床底,甚至每一只抽屉,赵女士都不在里边。父亲坚决不承认赵女士是个女骗子,他为她做过许多设想,他想得最笃定的就是赵女士被老胡抓走了,没收了手机,软禁起来了。那么,老胡在哪呢?这个一度被父亲当成邻居却从没出现过的人,随着赵女士的消失,遥远得成了一个没有形状的黑点,甚至,一个点都不是,是一团白色的浮沫,逐渐消散。我们劝父亲报警,父亲死活不同意。他说,这绝对不是入室抢劫,哪里会有这么一个贼,先帮主人打扫卫生,然后再拿东西的?赵女士不是贼。 ”值得注意的是,显而易见的骗局面前,父亲仍然不忍心报警,因为如果出动了执法者,那么赵女士所作所为的性质就大不一样了,父亲显然压抑了自己的理性而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情感。可以说,当代小说在处理正义与罪恶的过程中,已不再仅仅是板起脸来露出公正无私的姿态,其中固然也守护着秩序、正义、公平,但人性与情感判断,不断延宕甚或修正既定的审判。
凡一平的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中,围绕着乡土世界上岭村的刑事案件,凸现了两套价值系统的冲突,也即传统乡土的道德伦理与现代的法制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其中代表了前现代与现代的生存意识与是非观念,更由是造成了人物的偏离、悲剧与苦难。小说在上岭村的人际场域中上演了一出合谋与献祭的好戏,设计杀死韦三得的黄康贤, 由韦波顶罪得以脱身……小说前两部分可以说是乡土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村民合谋除恶,伦理模糊了法律,仇恨超越了规则。小说中有一段,专门提及作为执法者的刑警周龙拿筷子敲着桌面,像打快板一样说道:“刑警是最没有生活规律的人。刑警是用没日没夜的工作染白了自己满头黑发的人。刑警是用自己的胸膛挡住罪犯枪弹和尖刀的人。刑警是懂得没有自己社会就会乱套的人。刑警是在卧底时最像罪犯的人。刑警是知道自己出发并不一定能回来的人。刑警是在电视上出现时用‘马赛克’处理过脸面的人。刑警是和女友恋爱时经常迟到和爽约的人。刑警是和朋友聚会时经常中途退场或者‘挂空档’的人。刑警是妻子数落时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多家务劳动的人。刑警是自认为有愧于家人又不改正的人。刑警是最容易产生家庭感情危机的人。刑警是公安机关平均年龄最短的人。刑警是整个社会最不了解的人。刑警是人们认为警界最坏的人……”显在的执法者刑警的形象不断得以铺设并走向自身的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周龙等刑警形象不仅作为案件的现实逻辑推断,而且背后同样隐现着一种传统乡土的叙事伦理,他们不得不受到宗族的、情感的、关系的人物间性的制约,后者不断干扰甚至左右律法的判断实施,而作为执法者,在诸种挤压与抗斗中,艰难地推动着整个乡土世界走出幽暗的隧道。
三
如前所述,尽管文学伦理可以自有一套系统,自成一重规则,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与社会常识并不是完全相悖的,而且一定程度而言,小说在虚构的状态中,更需要寻求现实支点,这不仅是小说得以成立的事实性来源,而且也是情节推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逻辑性存在;更重要的,小说无论在阶层、人群、性别等层面输出再多的文化话语,也需要回到常态、常识与常理,也即,再虚拟的想象世界,也不得不回到善恶美丑的时代性判断,并且尊重外在的人、人文、人性。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通过陈金芳的人生沉浮,重新开启了对于阶层性征与人性弱点的考察,在小说中,陈金芳也许作为底层出身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同情与理解,但是到了收尾时,陈金芳被捕,而她加害于乡亲而造成的恶端也被揭露出来,故而这个在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丰富复杂的人物身上,寄寓了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小说固然可以创造新的经验世界,但不代表能够模糊和篡改起码的人文判断,最基本的尤需引入基本善恶伦常的维度,对于如陈金芳般为非作歹、草菅人命的部分,同样需要施以必要的价值判断,也即在道德决断与律法判定之间,维持理性的平衡与判别,否则小说的叙事将坠入迷雾而不自知。
具体说来,小说所结构的虚拟世界与律法所施行的现实世界必定有所区别,小说也可以一定程度地含纳“恶”的存在,尤其是人性之恶与内在的暗,但这个过程需要有所区分,如《世间已无陈金芳》,叙事的伦理固然可以倾向于对底层女性出身的陈金芳本人的同情与悲悯,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也必然需要顾及基本的社会常识,尤其是对于人物主体施以他者的良善或罪恶,需要重新厘定和审视,也就是说,再值得理解的人性和个体,其身上的“暗”与“恶”如若致害于人,则会演变为另一个层面的法律与规则统摄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律法与伦理是彼此纠葛的。也就是说,对于小说而言,无论阶层与性别、人性与欲望如何彰显,文学的内在伦理需要一杆秤,尽管这杆秤不需要做出如法律判决般的断定,也未必如武侠精神般惩恶扬善,但是其中的价值疏理和善恶知觉是应当分辨的,否则,当一个立体的丰富的复杂的人树立起来时,基本的常识与是非却倒了下去,那未免得不偿失。
王昕朋的中短篇小说《金融街郊路》《第十九层》《北京上午九点钟》等,包括长篇小说《漂二代》,叙述的是京漂一族的生活镜像和情感迂回,在城市挣扎的他们,在规则面前生如蝼蚁,然而却不时自我排挤与互害,从而将人性与世俗的恶推至更引人深思的层面。在王昕朋的中篇小说《金融街郊路》中,大桂和小桂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她们出身寒门,从乡下进城,在大都市北京摸爬滚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格局”——事实上也只是寻得一处谋生之所, 在停车场当收费员。 《金融街郊路》塑造了“有文化、有头脑”的小桂,她来自乡土底层,在贫乏无奇的停车场岁月中,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与同在金融街郊路看车的老伍合谋,最终挤走了对其有恩并一直照顾她的大桂,成全了自己。人固然要回到世俗,这里谈及的世俗,并不带感情色彩,没有什么先在的褒贬之辨,甚至说世俗到骨子,亦不指向偏颇和极端,因为世俗更多的是涵纳着个体内在的理念、态度和价值。小说最后,“小桂在孩子满百天后就回到了北京。她不是在停车场看车收费,而是在大桂曾看见她和老伍吃饭的羊杂汤馆当了店面经理。一个月后,小桂开上了一辆价值七、八万的小轿车。每天把车停在老伍那边。老伍每天都给她留着位子,对别的司机说,这位子是人家包年的。 ”而姊妹大桂却出乎意料地被老板辞掉了,所幸得胖姐帮助,在大楼的十九层做保洁工作。 “大桂开始想得头都疼了,怎么也想不明白。后来,她就索性不想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大桂,看到自己原来的职位被老伍挤占,而小桂则一跃成为餐馆经理,并且过上了比以前丰裕富足的生活,大桂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但欲言又止,有苦难诉。小说到了最后峰回路转,让人心里突然咯噔一下,体验到世俗的冷酷。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 ”小桂对大桂的残忍与冷酷,由于大桂的懵懂、纯粹以及终不得已的释然,反而更为放大。鲁迅所诉及的最坏的恶意,显然是将人心之恶指向无穷的限度;而之所以会至于如此糟糕的境地,便也是源于世俗伦理的无所限定。不消说,利益至上的世俗姿态,俨然已经成为资本与欲望世界驱之不尽的鬼魅。在王昕朋的小说波澜不惊的叙事中,透露出来的,是无处不在却又隐而不彰的人性的险恶和卑微。
周瑄璞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讲述了中国传统乡土世界中两个女孩的起伏升沉,两人高考失败之后,从乡村来到城市谋求生存,然而,甄宝珠经过短暂的停留后回到乡村,过上了普通日子,也经受着生活磨难,可以说在她身上代表着传统的乡土伦理的延续;而罗锦衣则被物欲与情欲所驱使,未达目的不择手段,以身体为筹码,无所不用其极地换取物质与地位。甄宝珠的寻常甚至平庸,与罗锦衣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备受生活挫折和法律制裁的罗锦衣,在小说最后回到了生之养之的村落北舞渡,与甄宝珠再度相认相处,“黄昏前的最后一缕天光和北舞渡的灯光交融,老妇皱纹堆积的脸,苍凉而慈悲。锦衣和宝珠转头对视,心里一惊。 ”综观甄宝珠和罗锦衣两人的生命轨迹,可以见出小说内在的伦理在罗锦衣身败名裂只身返乡之际,便以显露殆尽;而另一头,一世朴素淡薄的甄宝珠,与遍体鳞伤的罗锦衣最后并立而行,走在她们儿时曾经游戏的田埂乡间,精神的坦荡与凄惶同样分而并立,致使两人灵魂的阻隔已至千山万水,由是而观,小说的叙事伦理甚至价值评判的倾向昭然若揭。
因此,“世俗”的与人性的小说伦理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现实存在,诠释的是千重人生,也构筑了万般活法,其中固然无所谓规定性的限度。然而,“世俗”伦理却又必须牵连人世的精神和价值,这个层面也理应成为世俗人生始终坚守之所在,否则,如若任其随处漫漶,最终将失落道德礼义,也将失却世道人心,从这个层面而言,小说的伦理在现实的法则面前,万不可失却其中必要的精神与文化限度,换句话说,小说的伦理势必需要内外律法的某种适恰规限,如是才不至于令叙事显得凌空蹈虚并滑向虚空邪祟。
更值得深思的是,当文本面对卑下甚至低俗的人物情态时,所采取的不置可否的甚至是无可奈何的叙事态度,一旦逾离虚构的世界,进入实在的世俗世界时,如小桂和老伍这样平静而不动声色的诡黠诈伪,冷漠却理所当然的损人利己, 在世俗的滚滚洪流中,往往显得那么司空见惯,在予取予夺中,贪婪、险恶、自私,仿佛信手拈来,毫无沉重之感与歉疚之态。如此联想,不免令人多少悲从中来。在这样的境况下,便需要小说伦理在内在的发抒中引入法律和规则的视角,通过语言、结构、修辞等层面,建构内部的伦理与法则的多重判断形态。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小说出场评断,而是在文本收束之后,仍然渗透出未为或已的伦理剩余物。
总而言之,小说叙事可以不作出显性的价值判断,但是内在的伦理倾向却应当树立并有所透露,否则,叙事的伦理在做出或隐或显表达的同时,却颠倒了是非黑白,倘若如此,小说叙事内部的光泽难免被藏污纳垢的外在表象所掩盖,更遑论文学的批判意识在面对善恶时理应持有的立场与伦理。文学的伦理是一种虚设与想象的建构,同时也存在着甚或说肩负着更为合理的判定功能以及价值引导,这是作为精神与灵魂意义的小说存在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