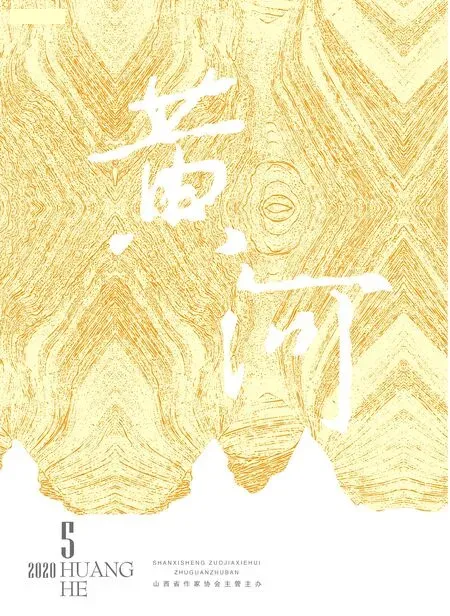一觉醒来人走了
徐春林
朝着那扇木门的裂缝往外望,我似乎看见了那个女人的背影,扁扁的拉得很长。我看见了她脸上那颗熟悉的黑痣,那双长扁的眼睛,长发在风中荡着,还有她走路时的样子,像是脚踩着树叶,一片片朝着远处飘,叶片又一片片掉落在地上,掩埋她的行踪。
我每天站在门的背面偷偷看着,那个时候,村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所有我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扁长的。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到处乱窜。我听见有人在喊我,那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像是躲在翻虚的土地里,听不清楚声音的方向。这时,我看见人和老鼠打架,村外的大片荒野开垦成棉地,老鼠的家园被摧毁,就跑到人的地里来争夺粮食。
早晨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在喊,“起来,走了。”窗台上隐约着一丝光,我搓揉着睡意朦胧的眼睛爬起床,一闪一闪地跟在大人后面,朝村外走。我害怕他们回头,所以走得特别小心,害怕他们见着我跟在身后,会扔石头打我。“赶紧回去,不然石头砸死你。 ”大人是不允许孩子跟着的,害怕走出村就再也回不来。十多年前,村子里有个小孩走到村口,就再也没有回来。谁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朝哪个方向走的,去了什么地方。
那年夏天,我不知道,那是一场怎样的梦,女人是风吹来的,也是风吹走的。她来的时候,村子里刮着大风。她就站在我家地场上。她走的前夜,村子里还是刮着大风。后来我想想,她本来就不属于这个村庄,只是一个稍作停留的过客,但她的到来给村庄和我的梦增添了许多色彩。我习惯了听她说话,觉得她说话的样子好看,尤其是那双深得不见底的眼睛,我特别喜欢。可一切都像是树上的叶子被风刮得不知所踪,“不要再做梦了。 ”我已经成了村子里多余的人,所有的人都想扔掉我,把我丢在村子里,而我呢?还时常能听见她说话,但听不清楚她要去哪,往哪走。
我总感觉她就在我前方,隐隐约约的,也许只要喊一声她就会停下来,可我费尽了气力都没法喊出声来。在梦里,我的声音被风堵在咽喉处,看着她的影子越走越扁,慢慢地变成一束炊烟。
黄昏的时候,我等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听见有脚步声从远处慢慢移来,却只看见一片浩浩荡荡的风,像是风把她带到了另一条路上。我开始反复梦见我们见面的情形。我的个头太矮,踮着脚跟努力地望着远处时,老槐树也探着头帮我眺望,可它看见的是大片的黑压下来。黑夜落在老槐树上,我走几步,又停下来,蹲在地上听一会,夜静得发麻,然后我趴在村口田野的草垛上,很快又睡着了。在梦里村子还是以前的样子,她蹲在地上“叮叮咚咚”地干着事情,敲打声传遍村子的角角落落,“珊,你这凉席到底凉不凉?”“躺下去就知道哩! ”说完她用袖子擦额头的汗。她的手艺特别精巧,做出来的东西也很好看,她在村子里干了两年,做出来的凉席村民也很喜欢。
我担心有那么一天,她会走掉。每天晚上,我总会蹑手蹑脚地摸进那个半开着门的院子,里面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灯,我听见自己的脚步碎碎的,我不敢进门,爬到院子旁边的草垛上闭着眼睛,听见她躺在床上均匀的呼吸。有时我会赤裸着身子站在院子里,她见着我,好奇地把我拉进屋里。“姐姐,我想听你唱歌。 ”她笑起来。我是在她的歌声里进入梦乡的,醒来时我的脸贴在她肚皮上,突然有种冲动想把手伸进她毛衣里,她一扭身差点把我甩到床底下。
有一个夜里,我听见一场呼啸的风吹进村子,看见她在屋子里收拾东西,收拾完后走出屋子。我看她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转到草垛的地方又转了回来。那时我不在草垛里,我躲在另一个暗处,她不知道我的方位。那天晚上,我蜷缩在草垛里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出村了,我不知道她要去哪,偷偷摸摸地跟在身后,想喊住她,却喊不出声来。我以为她还会回来的,跑进她的院子,门是敞开着,除了她睡过的床,和一些用过的物什,没有任何与她有关的东西。从那天开始,我一直在村子里等。我再也长不大,我还是个少年,活在女人出走的早晨。我就这么等着,看着村口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黄昏村子上空的炊烟,听着锅碗瓢盆的响声,鸡鸣狗吠相闻,觉得她还活在村子里。后来我跟在大人背后,远远地跟出村子,但很快他们就把我甩在村口。我躲在村口的草丛里睡觉,当他们走回来时,我感觉丛草在不停地抖动,他们挑着的担子很重,扁担叽叽喳喳地响。这时我来不及拍打身上的草叶,又跟在他们后头。我不敢肯定这些人是不是早晨的那些人,看着谁都是陌生的,没有见着他们的脸。我长久地被他们扔下,不敢咋声。
我发现,我再也没有按照正常人的生活进行。本来我该下地种田了,该去镇子上挑米了,可我还是不见长大,就连拿把铁锹铲土,我居然都不会。我停在那个女人出走的早晨,所有我该做的事情我都推掉了。无论村子里发生了什么,我都活在那个早晨,一动不动的。“快来,我教你唱歌。”她的声音好听,带着沙哑,感觉声音一点一点地朝天空挤去。有时候她也会和我讲故事,故事讲到一半她的声音突然停在那里,“接着讲嘛!”有时候她讲得入神的时候也会泪流满面。
她是来村里干嘛的呢?我知道她不是村里人。她来的那年我还是个小屁孩,刚满五岁。我见她躲在屋子里写文字,父亲说她是个不会劳动的女人。村子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没有不会干农活的,一个规定好的动作一百年没有变。不需要练习,生下来就会的。各自都在自我的局限中生活,谁也不会去读书识字,仿佛一生注定就是和土地打交道,成天操着锄头下地。天黑时,又从地里爬回来。
自从她来到村子里后,我的心就落在她屋子里。她住的地方是一间牛栏改造过来的,用石头砌了个围墙。不过围墙挺高的,一般人爬不进去。那时,她也就十七八岁吧?她不会烧火做饭,好在会做凉席。那段时间她在我家搭伙吃饭,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和她特别地熟。我喜欢她身上的那股味道,那个味道和村子里的味道不一样。我总是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梦境般的感觉,感觉那个让人讨厌的破牛栏成了村里最美的风景。
当然,我毕竟还是个几岁的孩子,不会有村里男人那样看女人的眼神。村里的姑娘都很土,这些外来的姑娘让人见着就心惊心动。
父亲梦想着我长大成人,可我让他失望了。我不想让自己长大,以为那些都是别人的事,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因此别人站在高处的时候,我就站在低处。想着法子不让自己长大,我害怕自己长大后,她就会不和我一起玩了。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的身子在不停地拔高。我开始害怕,自己哪天长大后混迹在人群中间,她再也认不出我来了。
某天晚上,我听见村子里人说,得搬出去,不搬出去这些大龄男人都会打光棍,哪家的姑娘愿意嫁到这穷山沟里来。“搬出去是搬到哪里去呢? ”“当然是城里。 ”说是上面来了政策,移民搬迁进城有补助,每个户头补二万,每个人口补三千五百元。这可是个不错的待遇,村民在这个寂寥的山角落里算是熬到了头。 “得把握这个移民的机会,错过就再也没有了。”村主任说。大家都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村民们在村里过着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身上的味道特别浓,人、牲畜、果木混合在一块,洗都洗不掉。坐个车得走十几里山路,车挤得紧,左右摇晃着,夹着的气味也左右摇晃着。 “能出去还是出去吧! ”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后来村子里再也没有了人。
几年的时间,一个热闹的村庄变得寂静起来,女人做的凉席,也被抛弃在荒草上晒太阳。进城的生活,得狠心抛弃乡间的破铜烂铁。想想,那又会是另外的一种日子。
村民们都离开村子的时候,我也跟着离开了,如果说人有灵魂的话,我的魂还留在村子里。我觉得我只有活在村子里不会成长,即便是长大了,可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孩子。我喜欢躲在昏暗的墙角里睡觉,歪着头,打着呼噜,不用在意别人的表情。在村子里,我会忘记白天,把夜晚扣在背上。那些夜里我穿行在村子里,不知道白天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里全是她的影子,我不知道她去的地方,听说回了广州,也有人说她嫁人了。也有传说,她去广西支教去了,再后来在支教的路上发生了意外。她来村子里时大学刚刚毕业,是来边远山区社会实践的。听着这些传言,我就像丢了魂似的,见着鸡狗都唉声叹气。她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怎么寻找就是找不着。梦是会认识人的,多少年后它还会记得你的样子,即便是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可还是会记得年少时的梦,那个梦一直会在村子里,等着她。现在呢?每次回到村子里时,我依然和那个早晨一样,我在离村的路口停住了脚步。她在村子里时我没能占到便宜,可我那时还是个少年。也有人拿我开玩笑说,木,珊那么喜欢你,长大把她娶了。
每个夜晚我都能听见孩子的脚步声,他在村子里跑。我没有见过他,听见他的脚步声,我朝着那个影子不停地追赶,可没能追赶上。但我听见他在白天和夜里不停地喊叫,那声音传遍了村庄的每个角落。我在夜里追赶时,那声音仿佛又在另一个白天。我追赶不上,没法走到他们中间。很多时候,我觉得那孩子就是我,我又偷偷地闯进那个院子,我看见一只老鼠追着另一只老鼠跑。自从女人走后再也没有人住进来,院子里满是枯草,那扇门早已没有了,里面是尘土,黑黑的,房顶上是一片星空。
村子里来过的外地人非常少,来一个人会热闹好一阵子,走一个人会让村民惦记好久,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说她的事情。何况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呢,一个从孩子记忆中走丢的人,多少年后还会寻找她的去向。我以为,这是孩子最天真的地方。
好些年没有人聚在一起了,他们商量着好像是要把我扔在村子里,也许我会是那个经常在村子里走的人,还会惦记起有关她的事。因为村民的习惯已经打破了,他们搬到城里后分散在小区内,很少再相互聚在一起讨论村庄,外面世界有说不完的新鲜事,每一件似乎都比村子里的精彩。
现在村子里的老鼠越来越多,它们不用偷偷摸摸地生活了,一个院子里到处是鼠窝。村民们落在村子里的碎食,够它们吃上几个季节。
我突然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现她已经走远了。我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可我闭上眼睛就会看见村子,看见老鼠不分胜负地打架,看见她在村子里走。
每个人走同一条路就会合成一个村子,那时所有的人又都会回来,所有的夜里星星都会到齐,一起聊着过往的事情。
风跟着村子的季节一起变化。人一辈子看路的时间比看啥的时间都长,一个村子里的人走到哪都可以从脚印里看出来,他们把更长的身影投向大地,村子里的人还会回来干活。其实,他们和我一样哪也没去。
一个人出走,很多时候不会再回来,她会不会再回来,我不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