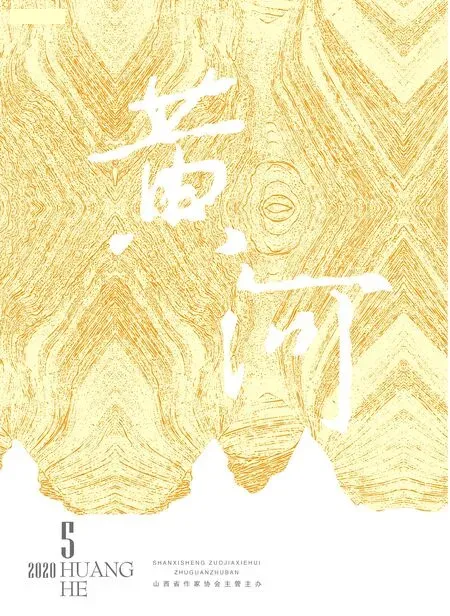掏鸟行动
刘勇
二野鬼单手叉住我后脖颈,老鹰抓小鸡似的,从河边白色的沙滩,把我一直提溜到河滩那棵歪脖老柳树的阴影里。
他让我蹲下,自己站着,捡了根三尺长的枯树枝当指挥棒,指点着树下那片白色的盐碱地。
今天晚上有大行动,和你狗的说下作战方案。说这话时,他脸皮绷得像面鼓,显得军官似的一本正经。地上没有沙盘,只有树影的光斑胡乱晃动。我感觉这情景顶多像敌后武工队的架套,他却硬要摆出正规军的阵势。我瞅了一眼他的军用球鞋,后跟永远是踩倒的,露出黑脚后跟蛋。他哥捎给他的这双鞋,好好的,硬是让他糟蹋了。
好臭,比臭咕咕还臭。
我用手扇了扇,不顶事,只好用手捏紧鼻孔。
臭咕咕大名叫得胜,和我的大名叫得胜一样。二野鬼每次说起臭咕咕,就会强调自己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好像只有说起臭咕咕,才会想起自己的大名。全村无论大人小孩,都二野鬼二野鬼叫,冷不防有人喊马得胜,他总会愣怔一下。
他告我臭咕咕一窝就六颗蛋,一颗也不会多,一颗也不会少。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带我去了废砖窑。臭咕咕窝比茅坑还臭。他扭过头,一手捏着鼻子,一手去掏,果然掏出六颗。他先分给我两颗,停了一下,又不情愿地捏给我一颗。蛋皮也有股刺鼻的臭味,可我经不往蛋皮里内容的诱惑,又怕他反悔,只好忍着臭,咬破一颗吸一口,咬破一颗吸一口,咬破第三颗彻底吸尽了,又将前两颗重吸一次,真觉得实在没什么内容了,才将蛋皮一起扔进窑口。 臭咕咕在窑顶气得发疯,“”一声,稀屎像水枪一样射向我们。那臭真叫臭。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么好看的鸟,为什么那么臭,好看的东西都臭么?它的冠和尾比公鸡不知好看多少。
刚才我还在不远处的芦苇后面。那儿有一大片白色的沙滩,斜插进水面,水波像狗舔食一样,“哗啦哗啦”吃进泥沙,又“哗啦哗啦”吐些小树棍和羊粪蛋过来。
放暑假了,半前晌我在沙滩上躺着。阳婆暖烘烘的,挑逗着河泥的腥味。光线白的刺眼,河关关不知哪儿歇凉去了,沙鸡鸡不知哪儿歇凉去了,蟋蟀也不知哪儿歇凉去了,都歇凉去了,天蓝得连一丝云也找不到。大队的高音喇叭听不清广播什么,离吹收工号还早着呢。躺了一会儿,觉着背下细沙流走,温热的水气湿漉漉的,再躺得时间长了会洇湿衣裳,我才坐了起来。
滹沱河还没到发水的季节,静静地流淌着。看久了也没啥意思。蝴蝶大概不分男女,都独自飞舞,二野鬼那块手绢上倒是两只一起飞,可我总觉得那是画的人没好好观察。男蜻蜓真不要脸,趴在女蜻蜓的背上,飞来飞去,就是不肯下来。我好像想到了什么,浑身突然发热,喉咙发干,就在沙子上画了一只竖着的眼睛。有一只河关关飞来了,它斜身俯冲,几乎触到我的头顶了,“叽叽叽”地叫,想看我画了什么。不知怎么的,一激灵,裤档里的小寸就硬了,身上好像虫虫乱窜,痒痒的,说不清难受还是舒服。
就在那一刻,二野鬼的军用球鞋踩在了白色的沙滩上。
二野鬼比我大好几岁,我念一年级时,他就排在四年级的队尾,常看见他在男同学的背上贴纸人人,或者扯女同学的辫子。我升到四年级了,他还蹲在四年级,在教室最后排独占一桌。二野鬼是个夜游鬼,他不睡觉,四处游荡,夜里发生的任何事他都晓得。一上课就瞌睡,下课铃一响,他就醒了,摇头摆尾,好像游鱼入水,等悄悄靠近聚在过道里的同学时,冷不防尖叫一声“掏小寸”,手猛地伸向男同学的裤裆。教室“轰”一下炸了,他的眉眼和嘴就全笑飞了。
二野鬼是全校有名的差等生。期中考试刚完,他一个人在过道大声宣扬,哎呀,语文和数学了不敢吹,常识肯定是高分,全是判断题,瞎猫哇还愁碰个死耗?边说边把脖颈探到班里最袭人的女生牛艳花脸前,盯紧人家看有什么反应。牛艳花撇下嘴,鼻孔“啍”一声,满脸的讨厌和看不起。
班主任尤老师师范毕业分配到村里好几年了,想调回崞县城,不知让什么人卡住了,调令一直下不来。尤老师满身散发着一缕一缕香气,走哪儿哪儿香,我一直认为她是花精转生的,只是分不清究竟是哪种花。到夏天了,尤老师穿着白裙,赤腿赤脚。二野鬼手挡在我耳边说,你发现了没,香气是从裙底走出来的。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香气走出来时,还拽着一丝腥。
尤老师在教台上宣布各科成绩。马得胜,语文37,全班同学两腮鼓起了猪尿泡。数学6分,所有的猪尿泡“噗噗噗”全破了,教室漂满了唾沫星。二野鬼站了起来,尤老师,常识,快说常识。尤老师走下讲台,过来问他,看把你着急的,是不是估计常识考好了?二野鬼狠狠吸了两口气,肯定哇,要么对要么错,空空里全打的对勾,至少也能打50分哇!尤老师将卷子立在他脸前,你自己念。二野鬼眉眼集中成一堆,咋才39?全班同学更憋不住了,擂桌子敲文具盒,笑声震得顶篷尘土直往下掉。二野鬼缩脖坐下去,说那也是常识最好。
二野鬼经常眯着眼吸气,夸奖尤老师屁股圆,奶大,好像那些东西就在他眼前似的。他说他听见工作队队长老王和民兵连长说灰话了。我问灰话还能让你听见?他说巡夜时,他俩从校园出来后说的,工作队队长老王一路叨叨,蚕沙老婆黑脸汉,说起……二野鬼问我,你晓得说啥?我知道说灰事,可又不全明白。二野鬼觉得我好奇了,又问,民兵连长还说了句,老王你就脸黑,你晓得这又是说啥?二野鬼见我发愣,认真瞅了瞅我的脸,一下笑了,小沱,你狗的脸也挺黑的……我后来也观察过,工作队队长老王脸的确黑,但和我脸黑又没牵扯,脸黑的人多了,又不是就我一个。二野鬼有些话我确实听不懂。我不大留心尤老师的屁股和奶,只是觉得她鼻子两侧如果没有那些蚕沙,应该还是很好看的。我喜欢闻尤老师的香味,说尤老师真香,也学二野鬼的样子眯了眯眼。
自从二野鬼缠上我,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从班里的一二名退步到了中等生。尤老师好像在我妈名下交不了账,将罪过全怪到了二野鬼头上。她找二野鬼谈过几次话,奉劝他别拉拢腐蚀好同学,否则吃不了兜着走。二野鬼褪下裤子让我看屁股上教鞭抽的红血印,小沱你他妈不就是校长的儿子吗?今后你离我远点,省得跟上你挨打。我妈也教训过二野鬼好几次,但怎么教训的,他一个字也没对我说过。我妈说二野鬼会装,哭不出来,就偷将口水抹在眼底,装委屈,装可怜。我觉得我妈每教训他一次,他就会缠得我更紧。不单教我上树掏鸟,还教我下河耍水捞鱼虾,还带我到崞县城看《卖花姑娘》,还给我贩弄一些类似《品花宝镜》《绿野仙踪》之类的书。我特别爱看书里有小姐丫鬟的插图,盯着想一些不能说出去的心思。我觉得二野鬼比课本有意思多了。有次听见尤老师和妈分析我,说孩子正在性朦胧期,这个时期过不好,会影响终生。我妈明令禁止我和二野鬼接触,我只有在她去联校或教育局开会培训的时候,才敢公开和二野鬼耍,其余时间都转入了地下,有接头暗号和地点,比台湾特务那一套还神秘。
白色的盐碱地上,二野鬼先画了一个小长方形,又在长方形的右侧画了一个大正方形。他还把枯树枝当指挥棒,指挥棒点在长方形和正方形上面,小沱,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说咱们学校哇?
我们学校过去是大财主牛孝远的宅院。长方形小四合院里东西南三面房舍做了五六七年级教室。北面五间正房,外面四间教师集体备课,里边一间曾是我妈的办公室,后来教师多了,将隔墙拆通,全用来集体备课了。正方形场院里的伙房、库房、长工屋和车马棚,改造成了一至四年级的教室,外乡教师的宿舍也全安顿在了这里。二野鬼在正方形的西侧画了一根竖道道,怕我理解不了,用指挥棒指了指头顶歪着的树冠。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那棵紧贴墙的钻天杨,就点了点头。二野鬼是掏鸟摸蛋的高手,村里河滩的树没他上不去的。一般情况下,只要双手能抱住,他都能上去。学校后面的钻天杨,是全村最粗最高的树,树皮又光又滑,树身一个人只能抱住一多半。有一天放学路上,二野鬼和同学吹牛,说能将上面的喜鹊蛋掏了。这话刚好让后面的牛艳花听到了,她无意中撇了下嘴,一副不相信的神情。星期天,二野鬼约了我和几个男同学在树下等。他不知从哪儿找了一整条废自行车外胎,对折后,一手抠住一头,盘在树身上。他将趿着的黄军用球鞋踢到一边,赤脚蹬紧树皮,双手用力一拽,腰身借势往上提,自行车外胎就向上挂了半尺。他腰身一伸一缩,屁股一坐一颠,“哧溜哧溜”,十多个回合就上到了第一个树杈,悠闲地坐在那儿抠脚趾缝。同学们先惊得不敢说话,这时才叫喊,快下来,快下来,危险。喜鹊窝在树冠的顶端。他一直向上攀,快接近窝了,手脚大展开,整个身体都随树枝摇来晃去。大家心顶得嗓子眼疼。他拉长身体,一只手终于探进鸟窝里,摸索了好长时间,好像摸到了什么,将摸到的东西塞进了嘴里。
几片羽毛从树叶间慢慢往下飘,他和我们招手。
星期一上课,牛艳花发现书槽里有一颗鸟蛋,双手托着惊呼,快看快看,鸟蛋鸟蛋。不知情况的同学围过去,见她掌心真的有颗鸟蛋,比鸡蛋小,灰白色的,蛋皮上有褐色的斑点,比尤老师鼻子两侧蚕沙深了些。
阳光从树叶间筛下来,有风吹过,大小不一的斑点在长方形和正方形组成的学校平面图上胡乱跳动。
头顶的这棵歪脖柳树,算是河滩上最大的一棵,树上原来有好几个乌鸦窝,都让二野鬼拆了。那些天,乌鸦们围着树飞起去落下来,“哇呀哇呀”呼天抢地惨叫,后来觉得没指望了,黑压压齐落在不远处的小老树上,轮流着一声接一声咒他。二野鬼才不管这些呢,他用镰刀将树杈周边的几根树枝砍下来,再利用留下的树杈,或斜或正搭成一个平面,将乌鸦窝拆下来的细枯枝铺在上面,又让我去河边割了几抱芦苇,一个门板大小的铺面就完成了。我和他挤在上面躺着,晃晃悠悠,白天看云彩和鸟,晚上看月亮和星星。有时他一高兴,就坐起来大呼小叫要掏我的小寸。闹够了,我就问他,你说崞县城的人叫麻雀就叫麻雀,为啥才五里远,咱们村的人却把麻雀叫成小寸?他说,还不是因为“除四害”改的,这四害本来叫苍蝇、蚊子、蟑螂、小寸!我觉得有些道理,又问他,那小寸是小寸还是小虫?我怕他分不清,将寸和虫分别写在他的两个掌心里。他哈一声,说你把裤子脱了!我说你干吗?他说你不脱我脱给你看。他真的露了出来,软绵绵的像条毛毛虫。我说晓得了,那应该是虫子的虫。他说不对,你看。他叉开拇指和食指在毛毛虫上量了量,然后将手指固定住,举到我眼前说,看看,也就一寸多一点,所以应该叫小寸。我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麻雀不也就一寸大小么。之后心里就默认了,将麻雀和裆间的小虫都正名为小寸。
不远处小老树的树杈上,乌鸦们又重新搭建了自己的窝,一根又一根衔树枝和茅草,我有些可怜它们,那得费多少时日。乌鸦们发现我们又来了,全守在窝边,不断派出侦察兵,在我们头顶飞上飞下,“哇哇呀呀”叫着,传递消息。
二野鬼见我走神,用指挥棒敲了敲我的头,小沱,你狗的咋了,今夜我们这个行动很大很大,你狗的听好了。我问究竟干啥呀,弄得真打仗似的。他把高举的指挥棒又当做冲锋的指挥刀,朝前方劈下去:今夜去掏尤老师的燕窝!
我们学校燕子特别多。燕子恋旧,喜欢到富贵人家垒窝。牛财主宅院没收做了学校后,一群一群的燕子每到春天,都会准时飞回来,各入各的窝。我们读课文、唱歌、做游戏,燕子垒窝、觅食、生儿育女。我们什么鸟窝都掏,就是不欺燕子,不捅燕窝,不掏燕儿。村里谁家檐下燕子垒窝了,全家老小都喜眉笑眼,会觉得马上就要富贵了。有时燕子屎拉头上,也不恼不怒,像钢儿掉头上一般欢喜。打记事起,村里老人就告诫,谁捅燕窝,会得红眼病,会烂眼珠。燕子和人相安无事,谁也不敢把燕子列入“四害”。
我知道尤老师宿室门顶上也有一窝燕子,放假时,看见白色的窝口露出了一排金黄的小嘴,燕子爹妈叼着小虫喂食时,发出“叽叽叽”的叫声。
我站起来说,二野鬼,你狗的不怕烂眼珠?是不是常识没考好,记恨尤老师?二野鬼把眼光抬到天上,我咋会那么小心眼,就是没养过燕儿么,想试着养一只。我说,反正我不去,你又不是不知道,椽眼里有蛇。二野鬼打了个寒战,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蛇。
我们村新戏台上的木料,全是从文庙上拆下来的。可能是檐口没封好,“麻雀战”漏网的小寸,好像全躲藏在了戏台屋顶。它们习惯了锣鼓铜器,不惊不慌,飞来飞去,和村人们一起看戏,经常扰乱剧情的正常进行。一次白毛女正唱到“北风那个吹”,一只刚学飞的小寸儿“扑扑棱棱”落到了白毛女的长头发上,村人收回眼泪,忍不住都笑了起来。小寸的冒失行为,严重地伤害了大家的无产阶级感情。大队长当下登台发出号召,“麻雀战”要打持久战,务必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在这场人民战争中,二野鬼大显身手,扛着梯子一个檐口一个檐口去掏。一时间,小寸的羽毛像灰色的大雪。鸟蛋稀里糊涂,东一摊西一摊。粉团团的小寸儿扔在戏台上,张大嘴惨叫。有人拿了套鸽子的网杆,随便在戏台周围一挥,就能网住三五只。大家正在兴头上,突然听见二野鬼惊叫了一声,他整个人雷击似的僵在了半空。后来,好多人都说,一条丈数长的白蛇,冒一股青烟,腾空而去了,还说一堆小黑蛇没修炼成,纷纷坠落在戏台上,眨眼功夫不知全钻到哪里去了。我当时的确看见一条黑乌乌的蛇盘在二野鬼的脖子上,红着眼直往他嘴里钻。他抓住蛇尾,像扯一条围巾一样,将蛇甩了出去。由于用力过猛,他和梯子一起向后倒去,谁也没看清怎么回事,在倒下的瞬间,他将梯子和自己一起翻转了过来,手撑梯子面朝下,台下众人赶紧伸手去接,他竟连肉皮也没擦破,只是裤裆湿淋淋的,两腿直筛糠。
众人反应过来,都回家找了黄裱纸烧。
这件事发生后,二野鬼再也不敢到房檐底掏鸟了。蛇喜欢钻洞,早年间村里也有个孩子去庙上掏鸟,脚踩在梯子上,一顶一顶用力,一直往里探臂,仰着头,嘴一张一合,好像触到软绵绵的东西了,以为是鸟,嘴一直大张着,就在这时,一条蛇“唰”地窜进了他嘴里,那孩子双手抓着蛇尾使劲往出拽,怎么也拽不出来,脸由红变黑,生生给憋死了。老人们说,蛇身顺着光滑的如涂了油,逆着却粗糙的像鱼鳞,入了人嘴,拽断也拽不出来。这故事很瘆人,我后来经常做这样的恶梦,觉得喉咙里塞满了东西,怎么也出不上气,连救命的呼叫声也发不出来。
二野鬼拖着那根指挥棒,围着我转,边转边在白色的碱地上画了个圆圈,将我和长方形、正方形以及竖道道标示的钻天杨全圈了进去。圈内,阳婆黑白相间的光斑一直胡乱晃动,让人眼花瞭乱。他自己跳出圈外,军用球鞋的臭气全留在了圈内。
小沱,尤老师门顶的燕窝在檩外,不会有蛇的。我说那可说不准。他用指挥棒划拉一下天空,说肯定没有,戏台上的蛇是寻着庙上旧木料的香味去的。我说,尤老师可比那旧木料香多了。他说,那香和尤老师的香不一样。蛇不会寻这香,尤老师的香早让工作队队长老王吸光了。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放假了,校门锁得黑铁铁的,我可进不去。
他用指挥棒又将圆圈反复描,说这你不用发愁,我会想办法让你进去的,放假前,我早把梯子从伙房搬到墙根了。我让他转的头昏,就说,那我也不去!二野鬼突然停下,和我面对面,从口袋里掏出几页发黄的纸。你要答应,这个就给你。他将那几页黄纸展到我的眼前。我看见纸上有十二回,相思和风雨等字。我跳了起来,二野鬼,你啥时把我姥爷的《石头记》撕了,你和你爷一样,是四类分子反革命。我去抢那几页黄纸,他用指挥棒顶住我胸脯,我无法抢到那几页黄纸。那会儿,我像被拴住腿的鸟,他牵着线的一头,我只能在地上胡乱扑腾,却飞不起来。他眼里伸出两道凶光,小沱,我警告你:你敢不听老子的,就把你狗的看黄书,让我耍你小寸的事,全抖露给你妈!我趷蹴了下来,手背上一大摊泪水。二野鬼看出已将我拿死了,抬起脚用臭军用球鞋将画的那个圆圈踢开一个口子,说声,回!
这时收工号响了。
二野鬼其实对我还算好,有时和同学争吵或者打架,他都一直护着我。他对我好,应该和我妈是校长有关,他对我好是有意的,我一直这样以为。
经常是晚上,工作队队长老王会从崞县城亢三的熟肉铺割半斤猪头肉,挑七八个兔头,再到我二姨的蔬菜摊拣几个青椒和茄子,然后将这些东西吊在车把上,晃晃悠悠地推进我家的院子。老王在部队做过首长,冬天披军大衣,夏天穿军上衣,有四个兜的那种。前来吃喝的人不外乎这几个人:大队长老肉、民兵连长和会计。喝酒夹菜间,免不了谈些学校的事情。有一次就谈到过二野鬼的问题。大队长老肉说,这娃年年蹲班,这可咋办呀?老升不上去,这可不行。我妈在锅台边炒青椒边回过头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我们不能把不合格的学生推向社会,这小子调皮捣蛋还在其次,主要是好搞阴谋诡计。
窗户外闪过一个黑影,我嗅到了一股熟悉的臭味。
会计说,他家成分就不好。工作队队长老王说,对他爷那样的反革命,必须斗倒斗臭斗垮,而对二野鬼这样的小顽劣,还是以教育挽救为主。再过几年,把他送部队算了,放到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炼炼,废铁也会变成好钢的。我妈叹了一声,臭咕咕生下的还是臭咕咕。工作队老王拢了拢大背头,也不能唯成分论,他哥和家里划清了界线,不也成了革命军人。
玉米地里非常燥热,各种蚊虫成团成片乱飞,地埂上蚂蚱、瓢虫、毛毛虫,见一个往死踩一个。我肚里憋着怨气,十分希望一条蛇窜出来,钻进二野鬼的屁眼。我叫了声,蛇!他踩在牛屎上一般,后跳一步,尖声问我哪儿?我说刚才从你脚后跟蛋那儿窜过去了。他很快明白了过来,小沱,你他妈别报复我……不过咱们还是绕远点,走道儿吧。
从眼前这条田间小道上,能清楚地看见村庄的房屋和东倒西歪的炊烟。去年暑假,二野鬼神秘兮兮地拉我到供销社买了一块印着两只蝴蝶的小手绢。我问送牛艳花呀?他斜过眼,说你瞧好吧!那段时间,他嘴里一直念叨:燕子低飞蛇过道,燕子低飞蛇过道……拖着根长棍,拉我到大路小道来回走,两眼像日本鬼子的扫雷器。后来他发现燕子不低飞,蛇也不过道,就改了主意,转移到河滩、乱坟堆,废,用长木棍四处拨拉敲打。
那天中午天气非常热,地面上所有的东面都在向上扭动。在两座坟之间的草地上,一团乱麻绳似的东西缠绕在一起,越缠越紧,发出“咝咝”的怪声,上面雾气腾腾,下面好像一堆燃烧的炭火,连周围的空气也烫人。二野鬼两眼放绿光,呵呵呵,就是这了,就是这了,可找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花手绢,展开挑在棍尖上,小心地,慢慢地,一步一步靠过去,将手绢轻轻地抖落到那堆乱麻绳似的东西上,然后迅速跑开。他躲在我身后,双手搭在我肩上,嗦嗦发抖。我不知道他是兴奋还是害怕,只觉得肩头水洗过一般。过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夕阳西下,那团乱麻绳才冷却下来,上面的雾才慢慢淡了。乱麻绳终于松动展开,我看见两条黑乌蛇,曲里拐弯,相跟着窜入了乱坟后面的蓬草中去了。二野鬼跳大神一般腾挪过去,食指和拇指捏住花手绢,对着吹了口气,念念叨叨做法。
夕阳的光线穿透手绢,两只蝴蝶在飞舞。
开学第一天,牛艳花发现了书槽里的花手绢,她像举着一面小旗一样惊呼:谁的花手绢?谁的花手绢?二野鬼走过去,脸绷得像面鼓,说这花手绢是他的,并让我做证,就收回了。牛艳花傻傻地笑,立马变得十分听话,变了个人似的。后来二野鬼和众男生说,牛艳花再也不嫌他学习不好了,只要抖抖花手绢,牛艳花就羞地像一朵刚开的花,眼光痴呆呆地粘在他的身上,他走哪牛艳花就跟他哪,让她做啥她做啥。
我们一前一后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知道那块花手绢叠得方方正正,一直在二野鬼左边的裤兜里。高年级有同学想借去用用,他谁也不肯借。有次问我你借不借?我说你狗的晓得我没用才借的。他说又不是借给你,拿回去给你……他把后面的话咬断了,眼光向天上抬起,自言自语,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
那天的形势有点特殊。我和二野鬼回村后,路过戏台,看见各种颜色的标语贴的到处都是,原本定在晚上召开的批斗大会,提前到下午召开。一个排的民兵全副武装,子弹袋里鼓鼓囊囊,押着村里的地富反坏右游完街后,在戏台上当众把他们五花大绑了。二野鬼他爷马有顺个子最高,像踩了高跷,民兵跳起去往下压他的头,每压下去一次往起抬一次,像浮在水上的瓢。他给上面写过一封检举信,牵扯了省里和行署的大官,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二野鬼说他爷是冤枉的,他爷是为了革命。我把马有顺从台上拉出来,将二野鬼替换进去。我全副武装,狠狠用脚踢他的屁股。二野鬼和我说过,每个民兵就分配6颗真子弹,其余子弹袋里塞得全是饲养处牛棚里的玉茭圪节。我找出子弹袋里的真子弹,“咔嚓咔嚓”上了膛,枪口抵在他的后脑勺上,再让你反动,“啪啪啪啪啪啪”,六颗真子弹全打在了他头上,让你狗的再逼我掏尤老师的燕窝。
批斗会全体社员参加,全体教师参加,全体学生参加。我妈早上说去县里开会,晚上不回来了。尤老师不在教师队伍行列,因为是外乡教师,放假回家了。我心里稍微轻松了些。大会隆重而热烈。工作队队长老王上身依旧穿着军装,一手叉腰,一手挥舞,列数地富反坏右的罪行。当数到马有顺的罪行时,我看见二野鬼两只拳头攥得紧绷绷的。台下高呼口号,二野鬼没有振臂,也没高呼。他嘴碰着我耳朵说,白蛇已回到戏台顶了,小沱,你瞧好吧,不知哪天白蛇会探下头来将工作队队长老王咬死。我本想扯扯他袖子,让他别瞎说,可转念一想,让他去说吧,让他大声说。我高声喊,你大声点,我听不见。二野鬼胆敢将我看黄书耍小寸的事告我妈,我就把他刚才说的话报告工作队队长老王。
天擦黑批斗会才结束。二野鬼没有马上离开会场,他摸到工作队队长老王的身后,假装擦鼻涕,掏出那块印着两只蝴蝶的手绢,在工作队队长老王的后衣襟拖了一下,捂住自己的鼻孔念念叨叨做法。民兵队长发现他不对劲,喝道,你小子干吗?二野鬼迅速收起手绢,还不让人感冒擦鼻涕?民兵队长瞪了他一眼,说你一个长小寸的,怎么大闺女似的,还用花手绢?
那天晚上天特别黑,看不到一点白色的东西。二野鬼两眼泛着绿光,一手晃动着一只河里发大水捞浮财用的三爪,一手叉住我的后脖颈,将我提溜到了校园墙外的钻天杨下面。我说尿紧了。二野鬼说,看你狗的那怂样。我说,还和过去一样,我瞭哨,你打主力。他呸了声,不就掏个燕儿,还用我亲临前线?我眨了一下眼,他已经站在墙头上了。
手!他探下手来,用力一拽,我没站稳,骑在了墙头上。这时才发现,校园外低里高,墙角黑漆漆的,像深沟。二野鬼松开绳子,将三爪顺墙探下去,动了几动,好像勾住了,用力向上提,躺在墙根的那架梯子便搭在了墙上。骑在墙头上,隐约看见尤老师的宿舍就在斜对面。校园的房屋比天还黑,黑的让人害怕。我说你揣我这手,又湿又烧的,燕儿烧爪了,活不成可不能怨我。二野鬼说不怨。我再无话可说。路上还思谋,妈去县上开会了,尤老师也放假了,这行动就好完成些。我顺着梯子下到了墙根。扛梯时不小心撞在了墙上。
谁家的狗耳灵,“汪汪”了两声,黑锅底似的村庄裂开了缝。
这架梯子真沉,为什么没想到这个理由?我用足了吃奶的劲,扛着梯子往尤老师的宿舍挪步。校园十分安静,蚊虫这时也好像全闭了嘴,每走一步都发出巨大的声响,头皮一阵阵发紧。快接近尤老师那间屋时,脚底滑了一下。泥地上有水,水还没干,能嗅见淡淡的肥皂味。
我顾不上细想,轻轻将梯子斜向尤老师宿室门顶的一侧,梯子落在檩条上“咚”地一声巨响,“扑扑扑”两个黑影从窝中飞出。我知道这是燕子的爹妈,但感觉头顶盘旋的黑影比乌鸦还大,发出的叫声“哇呀哇呀”的,也像乌鸦的咒语。那一刻,我突然怀疑这窝里住的究竟是燕子还是乌鸦。
什么声音?好像有人……
我轻手轻脚往上爬,听见屋内有人说话,声音十分熟悉。我的头“嗡”一下炸了,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我蛰伏在梯子上,大气都不敢出。我妈早上明明确确说她去县上开会,晚上不回来的,是我听错了?还是二野鬼施了什么法?我脑子里剧烈地晃动着那块印着两只蝴蝶的花手绢。我吸住气,想再听一句,好确定自己的猜测。头顶的燕儿探头探脑,“喳喳喳”惊恐不安,它们和我一样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木头窗棂糊着纸,下面的方玻璃拉着窗帘。
没事,燕子……
另一个声音划开了窗户纸和玻璃。我想,是不是在研究工作,说不定还有老肉和民兵队长,这可能是一次秘密性很强的会议,要不为啥连灯也不开。头顶燕窝里的燕儿不出声了,全缩回了头,好像也在等待更多的声音。
我要掏你的鸟……
我要捅你的窝……
没有更多的声音,只有两种声音,这声音曲里拐弯,像缠在一起的黑乌蛇。
怎么会是……怎么回事……燕子窝里飞出了乌鸦。
我想哭却哭不出来,不想尿却尿出来了……
不可能是……可能不是……
墙头上突然站满了人,一道又一道的手电光像探照灯。众人纷纷跳下,手电光柱胡乱交叉在一起。校园里所有的燕子,好像都变成了乌鸦,在天上“哇呀哇呀”乱叫。两个民兵将二野鬼燕子别翅押到了梯子跟前。民兵队长冷笑了一声,我就觉得你小子今天鬼鬼祟祟不对劲,说!你小子究竟想搞什么破坏?一个民兵将我从梯子上拉了下来,所有手电的亮光都堆在了我脸上。小沱?民兵队长吃了一惊,深更半夜你干啥?二野鬼,二野鬼让我给他掏燕儿,他说他要养……二野鬼抬起头,两眼放着绿光,说是这是这,说完又疑惑地问了句,小沱,是不是尤老师宿室有人说话?民兵连长一刮扇他脸上,你小子尽胡说,放假了,校园鬼都没一个。
那一夜,全村的狗一直叫到了鸡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