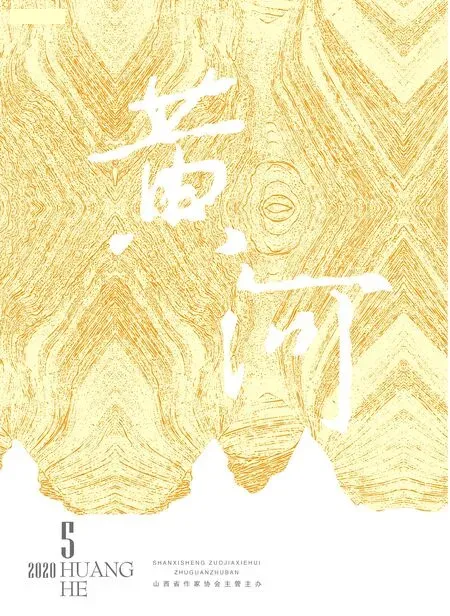犹豫不决的时刻最接近文学
草白
在我的电脑里,有两个小说都叫作《河水漫过堤岸》。最开始完成的那个《河水漫过堤岸》是个中篇,后来被我归入废品行列。因为对这一题目的念念不忘,又动笔写了一个《河水漫过堤岸》,便是眼下成稿的这一篇。
这个题目来源于一个梦中意象。在那个梦里,我回到故乡,梦见洪水、祖母、鹅、鸭子,还有堤岸。梦醒的那一刻,我嘴里念叨出的就是这个题目:河水漫过堤岸。这是一种很奇异的感觉,我居然可以梦见一个小说题目。那一刻,我便决定要以此为题做个小说,尽管兜兜转转之后,最终完成的已不是当初设想的那一个,但这种感觉依然美好,不可言喻。
不用说,这是一个先有题目后有内容的小说,类似于填字游戏。表面上看,这个小说的内容与梦并无关系,但实际上,还是有着那么一种隐秘的联系存在,尤其是在小说完成之后的今天,再次追溯过往梦境,我想到的是胡安·鲁尔福的一个短篇《都是因为我们穷》,里面写到洪水把“我”姐姐塔霞的嫁妆——一头母牛卷走了,导致她走向堕落之途。小说几乎没什么特意推进的情节,却像暴虐的洪水给人惊心动魄之感,究其原因还在于作者对环境氛围的成功营造。
胡安·鲁尔福在这方面真是造诣非凡,不论是他的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还是后来的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都给人强烈的“身临其境”之感,作为读者不仅能闻到闷热的树荫下腐烂的阿莫尔树的气味,还能听见来自死人世界的嗡嗡声。
具体到《河水漫过堤岸》的写作,如何营造一种幽微而独特的氛围,便成了我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它应该从文本内部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的,就像冬日河谷里弥漫的雾气。主题是什么不是不重要,但找到与此相关的语气语调,显得更为迫切。这个小说使用的是相对幼稚的少年人的视角,以此去表现残酷的生存主题, 这之间自然会产生一种错位——恰恰是这种错位感的存在使整个小说渗透出一股芜杂的气息。
一次访谈中,有记者问胡安·鲁尔福:你都是通过环境和气氛找到装备你的人物的材料吗?胡安·鲁尔福说:不,比这个还要复杂。我必须虚构一个主要人物,然后酝酿他的性格,最后寻找让他表现的方法。 ——他说的是《佩德罗·巴拉莫》的写作。在胡安·鲁尔福那里,连死去的村庄也可以成为人物,那里的气氛、声音、光亮都是这个人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河水漫过堤岸》里,有些东西是虚构的,但最大、最重要的虚构是小说的氛围。我必须把人物置于那种氛围里,才能让他(或她)行动起来,去发展和表现自己,或者什么都不表现。 ——我这么说好像氛围和人物是可以分开的,是有先后次序的。其实,氛围从来不是外在的。好的人物带来氛围,景物也能起到部分作用,关键要有统摄全篇的“气”,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这时候的写作便顺其自然,顺理成章,有些接近于写作的“生理性”了。
很多年前,我曾以情感热线女接线员为题材,写过一个类似的作品。但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我经常想,对于一个小说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真的会越来越清晰吗?只能说《河水漫过堤岸》是此刻的我所能写下的作品,它所谓好坏,至少在那一刻,它是真实的——无限接近当下的我所能抵达的真实。或许,一些年后,还会有另外版本的《河水漫过堤岸》问世,那时候它大概不叫这个题目,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表达。这是时间流逝带来的好处,让写作者对写作永远充满期待。
一个耐心而诚实的写作者,总能认识到自身局限性,并以此局限为出发点,或者说画地为牢也可,去接近她所以为的“真实”。真实并不面目狰狞,但也绝非让人可以轻易靠近。这虽然是一篇关于已完成作品的创作谈,但我真正想谈的还是那些影影绰绰、没有成型的东西,它们是脑海里闪烁的碎片,是夜晚窗玻璃上移动的光影,是雨天里灵魂的美妙勾留和短暂出窍。
那些台风天、月光明亮的夜晚或罕见的下雪时刻——总让我感到自己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城市里,而是隐居于深山老林之中。无独有偶,当写作者顺利进入虚构的世界,当那个世界发生的一切足够真实,也会体验到这短暂的出离感以及时空错置所带来的恍惚感。
无论什么境遇下,我们都应该有想象生活的能力,拒绝“现实生活”的干扰与绑架,更不要去管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距离,所有的想象都是我们的现实,它有自己的逻辑,也有应该遵循的规矩。
荷尔德林曾说,在踌躇的时域里,存在一些持久的东西。哲人旅途中的那份盘桓、犹豫不决以及凝思性的逗留,无疑更接近文学。文学永恒的表达对象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要认真地生活,真实地面对自己,心无旁骛或心如死灰都是一种境界。我们的生命与写作始终都处于同一场域里,从来没有另外的人生或另外的写作可以让我们安然无恙地泅渡过去。而今,除了一天天地纸上劳作下去,我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接近写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