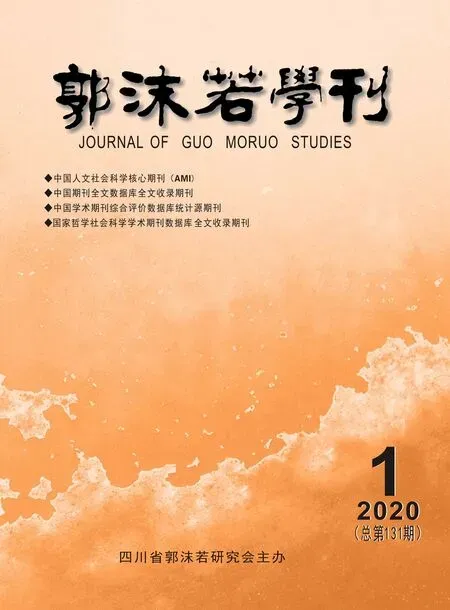怎样才算“替”胡适“恢复名誉”?
——向宋广波等先生请教
王锦厚
毛主席逝世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版不少回忆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场合与不同人士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书信、读书笔记、批语……其中涉及到《红楼梦》和《红楼梦》研究,涉及到胡适的功过……给我们如何研究《红楼梦》、如何研究胡适作了一次又一次的示范。
在写作这本小册子时,作者尽可能去寻觅这些材料、学习和研究这些材料,并从中受到极大启示……
著名的鲁迅研究权威、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唐弢先生,在回忆毛泽东主席1956年2月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的文中写到:
那时正在批判胡适,席间曾提到这个问题,毛主席说:
“这个人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
有人插话,声音很低。
“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毛主席说:“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
又有人插话,我听不清楚。
“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主席说着笑了。(唐弢:《春天的怀念——为人民政协四十周年征文作》,《唐弢文集》第四卷(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是怎么一回事呢?朱庄在《毛泽东眼中的胡适》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56年9月16日,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周鲠生,到瑞士出席“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利用这一机会,他辗转向胡适传达了有关的信息,劝他不要乱说。周鲠生1949年前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武汉大学校长,与胡适颇有个人交情。在瑞士会议结束后,他又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的邀请赴伦敦访问。在伦敦,周鲠生会见了创办《现代评论》时期的老友,同时也是他执掌武汉大学时的下属陈源(陈当时在武大英文系任教)。周鲠生代表周恩来,劝陈源回大陆看看,同时通过陈源动员在美国的胡适也回大陆。陈源依老友之托,于9月20日致信胡适,将周鲠生的原话转告:
“我说起大陆上许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适评判’。他说有一时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
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的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
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在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然而,胡适并不相信周鲠生所说的话,他针对陈源的信中所说的“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一句话,在下面划了线,并在一旁批注说:“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胡适与共产党的对立,主要是在思想、信念上,他深知自己的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是无法沟通和相容的,因而也就不可能相信来自共产党的任何劝说。
对于此事,1962年3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上发表的李青来《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一文中也有所披露:“在前几年‘共匪’大鸣大放的时候,‘共匪’曾派人向美国的胡适先生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先生听了便哈哈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朱庄:《毛泽东眼中的胡适》,刊于1999年第1期《人物》)
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胡适之所以如此顽固,原因就是要捍卫并推行他的“思想”。什么“思想”?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再造文明,将中国变成一个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国家,实质上就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早在1929年7月1日,复信李璜、常燕生时就说过:“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纵这个思想上的敌人。”(《胡适往来书信》上册)50年代批判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思想是无法清算的东西”,“感谢他们在铁幕里替我宣传我的思想”。可以说,从20年代起,他就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他思想上的最大敌人,不惜一切地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为敌,不但绞尽脑汁散布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由“小骂大帮忙”,迈向“过河卒子”,直到与蒋介石狼狈为奸。即使如此,共产党、毛主席还是千方百计争取他,挽救他……即使批判他的思想也留有余地。
1939年2月,毛泽东有三封长信给陈伯达,对陈关于诸子哲学的论文提意见。内中有一段话说:
“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和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的危险。”章,是章太炎,梁,是梁启超,冯,是冯友兰,胡,就是胡适。毛泽东要求作者申明:“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郁文:《毛与胡适——大书小识之二十四》,刊于1995年5月号《读书》)
1954年前后,毛主席曾亲自发动并领导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批判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最终把矛头指向了胡适,也主要是指向他宣扬的杜威的实验主义,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的规模之大,参加的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毛主席不但于1954年10月16日亲自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陆定一、习仲勋、胡乔木、凯丰、张际春等分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冯雪峰、何其芳、林默涵等文艺部门的负责人,认真对待这次批判工作,而且还亲自审阅报刊发表的部分按语,并进行修改。如对冯雪峰起草,经中宣部审阅过的在《文艺报》上发表李希凡、兰翎文章时的编者按语,就亲自作了修改:
……
编者说:转载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两句“更深刻……”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分别批注:“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陈晋:《毛泽东文艺生涯》下卷,1949—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对一些人所写的批判文章作了修改,如艾思奇批判胡适哲学思想那篇文章,等等。可见,毛主席对这次批判运动的重视,亲自掌握运动的每一个环节,避免出现偏差。1957年2月16日的一次谈话时说:
我们开始批判胡适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都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陈晋《毛泽东文艺生涯》下卷(1949—197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谈到《红楼梦》时,他说:
《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郁之:《毛与胡适——大书小识之二十四》,刊于1995年5期《读书》)
批判胡适的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禁区,红学研究出现了很多新气象,取得了不少的新成就,诸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成立,研究《红楼梦》的专刊《红楼梦学刊》的出版,国内国际召开了多次关于《红楼梦》的会议……出版了不少的“红学”研究的专书……其中就有“替”胡适“恢复名誉”的。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对胡适的“成就”不但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他的错误的东西还加以宣扬,甚至还欢呼:“又见当年胡适之”了。(沈治钧:《又见当年胡适之——评宋广波编辑〈胡适批红集〉》,刊于2010年2月《博览群书》)什么样的胡适之?他们说:
作为“新红学”的开山大师,胡适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胡适之所以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情有独钟,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学,要为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所以,“新红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胡适在“新红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是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与方法引入《红楼梦》研究之中,从而将“红学”纳入学术轨道,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纪元。从此,“红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现代学术。这种研究具有“新典范”的意义,“为中国青年学者运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进行考证与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本”。众所公认的,“新红学”的影响与贡献,不限于《红楼梦》研究领域,其对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亦具有深远影响。(宋广波:《胡适批红集·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这不是叫人见到的那个拼命地“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与方法引入《红楼梦》研究之中”,“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纪元”……“具有‘新典范’的意义”、“为中国青年学者运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进行考证与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本”的胡适么?如果真的以胡适用杜威实验主义思想和方法写成的《红楼梦考证》做“教本”去培养青年,不知要把青年引向何方???
杜威的实验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
《胡适口述自传》的译者唐德刚先生作了这样的回答。他说:
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是因为他是个什么“实验主义者”。实验主义者在中国说穿了只是一些早期留美学生带回国的美国相声。一阵时髦过去了,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只能做做注脚,是不值得多提的。(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这个回答形象而又通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当年的胡适到底是什么人?研究者说:“是在五四运动中暴得大名。”(陈漱渝、宋娜:《胡适与蒋介石》,北京:团结出版社,2019年3月)“踏着中国人民心血结成的彩虹似的桥梁,进入了大学的高墙,坐上文化第一把交椅”(引者注:即北京大学校长)。“又是一个口头上标榜‘不谈政治’,但实际上却有浓厚的政治情节的人。”(《胡适与蒋介石》)“一个最高明的入世者”。(唐德刚:《胡适口述历史》)他由“小骂大帮忙”到“过河卒子”,到“反共骑士”,“高参”……《红楼梦考证》是他“政治情节”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不但是抛向蒋介石的敲门砖,而且是他用以推行杜威实验主义,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重要手段。
胡适就是这样一个人。直到晚年,遭蒋介石打压,还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出谋划策……所以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最终将矛头指向了他是自然而然的事。……后来,三联书店从这些批判文章中选录了一部分,编成十本《胡适思想批判》出版。应该承认其中有价值的批判文章还是不少的。
读读当年领导这场批判的文艺界的两位主要领导人的文章吧!
郭沫若在《三点建议》中,重点批判了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说:
这是把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学是允许假设的,科学当然更着重实证。假设是什么?假设是从不充分的证据所归纳出来的初步的意见。它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假如积累了更多的证据或经得起反证,它有成为定论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郭沫若:《三点建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最初发表于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后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中则着重批判了胡适运用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红楼梦》的唯心主义。他说:
胡适对《红楼梦》及其它中国古典作品的研究,却是完全从美国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作出正确的真正科学的评价。首先,他对古典作品的考证和评价,完全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其次,他对古典作品又单纯地只从它的语言形式,即白话来着眼,而不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他认为《红楼梦》的“真价值”只是在它“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周扬:《我们必须战斗——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最初发表于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后收入《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样的批判如何?!
“典范”、“新典范”,“活生生的教本”,论者请再去好好读一读耿云志先生所列胡适1947年到1960年间利用文化问题,特别是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反共的文章:
1947年8月1日,在北平讲演《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1948年9月4日,在北平电台播讲《自由主义是什么》;
同年9-10月间,在南京讲演《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同年10月4日,在武汉讲演《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次日讲演《自由主义与中国》;
1949年3月,在台北讲演《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1950年12月4日,在美国加州大学讲演《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存在价值——在中国思想与文化中哪些东西是不会为共产主义所摧毁的》;
1953年1月3日,在台湾新竹讲演《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
1954年3月5日,在台北讲演《从〈到奴役之路〉说起》;
同年4月1日,在《自由中国》杂志十卷七期发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
同月,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演《中国思想史上的怀疑精神》;
1955年12月,开始写《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
1958年3月14日,在耶鲁大学主办的修姆博士基金会上讲演《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科学治学方法的发展研究》;
同年6月13日,在台湾大学讲演《从中国思想上谈反共运动》;
1959年7月7日,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宣读论文《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同年7月16日,同地讲演《杜威在中国》;
1960年7月1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讲演《中国的传统与将来》。(耿云志:《胡适思想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1版)
请注意:这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简表。
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胡适的什么全集、全编,其实都是不全的,就是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反共的文章、讲演、书信……还多着呢!如他的《〈自由中国〉的宗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宣言》等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圣人……”。从学理上说,“胡适这个‘但开风气’的‘启蒙大师’哪有‘批不倒’之理?”(转自吕启祥:《史家风范作家文采——我心目中的唐德刚先生》,《红楼梦会心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版)因此对胡适的评价免不了争论,昨天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明天还将如此。
“替他恢复名誉”是必要的,应该的,此项工作已经有人做过而且还有人在做。但到底如何“替他恢复名誉”,恢复什么样的“名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下功夫去研究。我们以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实事求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学术上,有功,也有罪,一定要让青年明白,决不能含糊,也不允许含糊,这就要如鲁迅先生早先教导我们那样:“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题未定”草》《且介亭杂文二集》)
“替他恢复名誉”,恢复什么样的“名誉”?我以为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那就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否则一定会误入歧途!
二○二○年一月于成都川大花园
注:这是作者撰写的《吴宓演讲〈红楼梦〉追踪》的后记。该书分三个部分:一、《吴宓的〈红楼梦〉研究》,二、《吴宓与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三、《沈从文的“讥诋”与吴宓的“反击”》。这里所用的标题是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