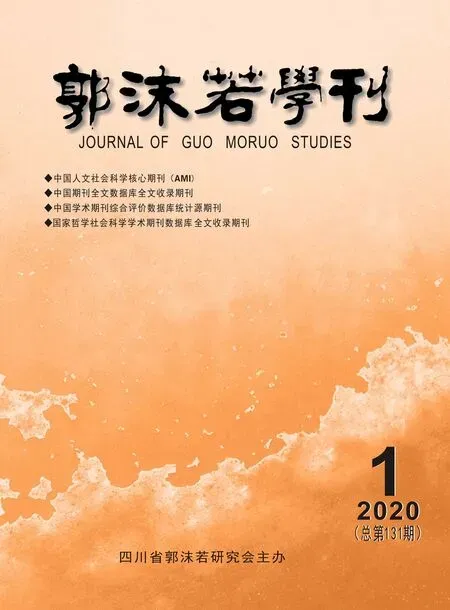《孔雀胆》的主题意识和演出效果
司空痴
剧作者:郭沫若,演出者:演剧二队,地点:天津励志社:
《孔雀胆》的主题意识,在去年春天读剧本的时候便知道郭沫若先生和许多人都讨论过了。而且也似乎曾引起了一阵论辩。《孔雀胆》的故事是大众皆知的历史题材。而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可以统括的说:全是以历史事件来作为现实社会的反映。这中间当然要含蕴了剧作者卓特而正确的思想与见地。李广田先生将创作的动机分为四种:有一种称为“由事实出发的创造过程”;另有一种称作“由寓言故事出发的创造过程”。《孔雀胆》的故事可以视作一段历史事实;也可以视作一个历史故事。无论视作事实或故事,总是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批判像酵母一样的揉合到事实或故事里,使死的事实死的故事活化起来,因此才使戏剧艺术的教育工作如蒲伯英在《戏剧之近代的意义》中所说“像再生一样,不像别样死教化,占据在人脑海的,就不容易抽换”。《孔雀胆》的创作动机我们由郭先生自己的话中知道郭先生的本意,最初是要将故事的重心放在阿盖公主的身上,而一个重点是在民族团结,这凝结成为阿盖的爱,和这对立的是车力特穆尔①“车力特穆尔”原文作“车里特穆尔”。的破坏。段功呢,则是把他放在副次的地位上。但是这一点却又如同看过演出以后的郭先生也承认的,在演出上使观众得到的不是作者最初的创作动机,而却在另一方面领受了深重的教育意义。郭先生说“在演出上,段功却成了主人,因而主题也就更加隐晦了”。
正如所有的悲剧一样的发展与结局,以宽大为怀,道义为本,主张“释放一个人可以表示恩德,杀掉一个人不足以表示威武”的段功,因为他太把人当作人了;这种自以为是的善念,当然要造成自身的倾覆与灭亡。但是我们要作再进一步的追问,那将会毫不客气的指摘段功的宽大与慈悲完全是一种动摇份子的妥协主义。因为他被梁王的伪善与阿盖公主的情爱这两条彩绳捆绑住,使他像他的好友杨渊海对他所下的批评说:“池塘里的荷花表面虽然开得异常繁荣,而它的根却陷在深厚的泥潭里。”因此,他的自以为成功的错误观念却正是造成本身颠覆的因素。
郭先生说徐飞在《〈孔雀胆〉演出以后》的恳切批评是替他将孔雀胆的故事提醒了主题,又介绍徐飞先生的话说“造成这个历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是的。在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之下,一切妥协主义论者终究是将自己造成一个悲剧的人物而已。这种提示与批判的确是给观众们一个明晰的正确的提醒。当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间,我们敢很肯定的说是有着很多很多的人抱着妥协友善的政策,以企图感化异族侵略者的正义与良心。但是在现阶段的今天,我们更要申明而且强调一点,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欲望不是不仅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和刁诈,而且应该强调对一切统治者来表示这一种观点的。即使是非妥协主义者的杨渊海却为了另一种顽固的错误的观念而陷于相似于段功的同样的悲剧命运,但是这种以身殉友的忠诚我们也要视作另一种的妥协,因为本身自命为反对与恶势力合流同污,主张与一切新的有生力量(故事中是指长江南北的一切义军)合流的非妥协论者,但是我们要负责任的追问,为什么当一件艰辛重大的工作完成之前,轻轻的殉友来逃避开工作的岗位。
是的。“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脚印,这脚印说明着过去也提示着未来的路”。当我们读完《孔雀胆》的剧本和看过《孔雀胆》的演出以后,我们承认我们领悟到《孔雀胆》的主题意识的指示。
现在我们就演剧二队的演出作一个检讨。
我们首先要反对演出者对于原剧的任意删改,这一点我知道是由于天津市的宵禁提前而作不得已的节删,在现阶段的恶劣环境之下是应该作退一步想的原宥,但是这一次的删节,容易使观众产生一种误解,也可以说是对主题意识的模糊观念。例如第三幕中段功杨渊海审问提到的刺客,而暴露了统治者的阴谋,第四幕中在通济桥旁行刺段功前一刹那化装后的铁知院对阴谋的态度,这一点对于观众的教育意义相当浓重,因为就演出上说,给神经错乱的阿盖公主清醒剂的化装和尚,在观众意象中是很容易淡薄而疏略的。
就演员的表现技巧方面来说:饰王妃的张今呈似乎典型性格的不太适合,因此对于王妃的狠毒未能表现到淋漓尽致,王皇和罗泰都能将段功的沉毅①“沉毅”原文作“沈毅”。“王妃”原文作“王姐”。和杨渊海的忠义表现得恰到好处;饰阿盖公主的梁国璋和饰车丞相的袁敏也确能把握住剧中人物的典型性格,尤其是梁国璋能将阿盖公主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为观众的脑海里镌刻上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是在服装方面,阿盖公主和施宗施秀好像应该有显著的差异,例如施宗无意间偷听到车丞相和王妃的阴谋的一场,很容易使观众认为是阿盖公主(虽然第三幕中阿盖自己有一个说明),开幕闭幕时灯光不能配合,象征火焰的效果不逼真,这一些后台的问题是更特别需要顾及到的。
(原载天津《益世报》1947年11月24日第6版《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