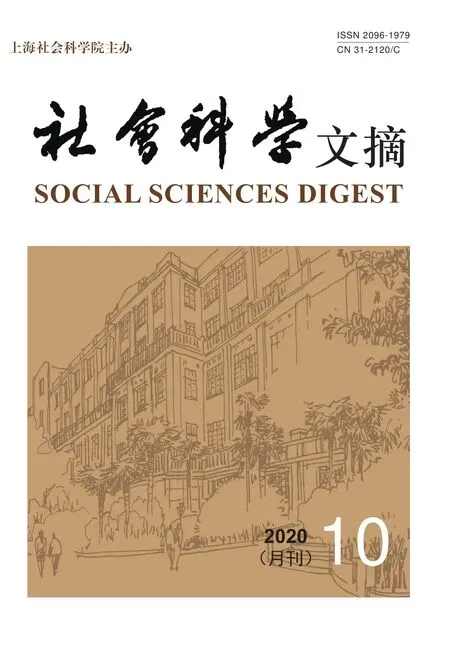政治学话语分析的类型、过程与层级
文/郭忠华 许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如何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问题也日益为学术界所感知。当下有关中国学术话语的研究成果尽管不少,但大部分停留在本土学术话语的反思和建构上,有关学术话语的基础理论研究屈指可数。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对学术话语的原理性知识缺乏理解,有关本土话语体系的反思和建构也就失去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出于加强本土话语建构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目的,本文希望引入话语分析方法来提升本土话语体系建构和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自觉性。本文从“话语类型”“话语过程”和“话语层次”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阐明话语分析的主要策略。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话语分析”
从兴起的背景来看,“话语分析”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韦伯的诠释社会科学思想,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有关语言与存在的论述,以米德、温奇等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以索绪尔、雅各布森等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以及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传统等,都与“话语分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中晚期,在英国高校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话语”研究的学者,他们从“话语”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致力于建构起系统化的“话语社会理论”。在这种背景下,话语分析开始成为一种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最先兴起于语言学领域,但随即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结合,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法。
将话语分析延伸至政治学领域,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在中国社会社会科学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很少被关注。在政治学领域,尽管可能已经出现有关政治话语研究的成果,但话语分析显然还没有成为一种明确的方法。近年来,随着方维规、孙江等学者回国任教,他们倡导的“概念史”研究在我国渐成气候。但是,概念史研究并不等同于话语研究。尽管概念史研究所选择的大多是政治概念,但它们主要关注单个概念或者以单个概念为基础的概念家族。尽管概念是“话语”的构成要素,但后者表现出诸多差异。首先,在分析资料上,话语分析主要以“文本”和“对话”为基础,而非特定的概念。其次,在研究重点上,概念史侧重于对概念语义的研究,即通过理解概念在上下文中的涵义来理解“历史”;而话语分析尽管也研究话语文本,但更侧重于通过理解文本的生产、分配、消费等来理解“权力”关系。最后,在研究进路上,概念史研究主要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侧重于对文本的占有和诠释;话语分析则有诸多不同的进路。
话语类型与话语分析
在不同的情境下话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类型。从本质上说,话语的类型呈现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权力,言说者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不同,话语的表达形式也存在差异;二是知识,说话者拥有的知识专业度不同,话语表达形式也体现出差异。根据“权力”和“知识”两大标准,可以区分出四种话语类型:指令性话语、游说性话语、专业话语和日常话语。
在权力的维度上,话语可以区分为“指令性话语”和“游说性话语”。“指令性话语”主要体现在命令、要求、威胁和管制性话语上。它们表明,话语发出者拥有某种被法律和制度所赋予的权力,句子形式主要以命令式和祈使句为主,主要见之于正式工作场合中上级对下级的谈话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所发布的文件中。在这种话语类型中,话语发出者与话语接受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后者基本上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与之相对,“游说性话语”主要体现在凭借理由、证据等反复向话语接受者灌输,使之相信话语的内容,它表明话语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权力接近于对等,利益引诱在这种话语形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权威人士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此种话语形式来达到其目的,甚至可以起到比指令性话语更好的效果。
在知识的维度上,话语可以区分为“专业话语”和“日常话语”。“专业话语”主要体现在专业知识精英所建立的话语体系上,例如天文学家有关新发现星星构成状况和运行规律的说明,它们不仅在形式上迥异于日常话语,而且在内容上远远超出常人的理解能力。与之相对,“日常话语”表明的则是知识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话语形式,尽管很少涉及专业知识,但同样表明了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
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话语划分为上述四种类型。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并非彼此排斥,而是通常结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话语表达的效果。例如,地方政府为了在特定地点建立核电站,邀请了部分核电专家对发电厂的选址问题进行论证,专家们先是从专业知识角度表明有关核电站建设的要求,并从土壤、风向、天气、潮汐等角度说明选址的合理性。凭借专家给出的理由,政府再从能源短缺、经济发展、政治需要等角度说明建立核电站的必要性。通过这两套话语的有机结合,有关核电厂选址的话语似乎变得科学合理和无可反驳,从而大大增加了核电站选址的可接受度。
作为话语分析的策略之一,话语类型及亚类型的区分可以使我们对话语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首先,话语形式以相应的情景为转移。话语分析必须考虑到空间和情境因素,不同的情境以不同的话语类型作为主导。尽管并非绝对,我们可以大致总结为:在严肃公共场合,指令性话语具有主导地位;在日常生活领域,日常话语变得盛行;在专业知识领域,专业话语具有主导地位;在经济生活领域,游说性话语十分重要。其次,话语类型的资源相关性。话语类型的分殊最终取决于政治和权力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以不同类型的资源作为基础。比如,指令性话语以正式的组织和制度为基础,所依托的主要是“组织资源”;专业话语以专业知识作为后盾,所依托的主要是“知识资源”;游说性话语建立在说服和利益诱导的基础上,所依托的主要是“经济资源”;日常话语以血缘、友情等社会关系作为基础,所依托的主要是“关系资源”。
话语过程与话语分析
“话语过程”体现在特定话语情境下参与要素所形成的顺序排列上,它主要建立在话语主题、话语轮次和话语方式三种要素的基础上。其中,“话语主题”指谈话过程中所涉及的主题,一般而言,话语在一个时间点上只能围绕一个主题进行,但可以根据时间改变;“话语轮次”则指围绕同一个主题所进行的交流回合,同一个主题可能有相当多的轮次交流,甚至成为单次谈话的唯一主题,但也有可能一个主题只进行一轮次交流;“话语方式”则指交谈过程中所采用的话语类型和话语语气,话语类型体现在前文所区分的那些分类上,话语语气则体现在强调、疑问、感叹、反复等语调上。
话语过程分析主要集中在日常话语,这看似与政治学关联度不高,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政治和权力因素通常渗透在话语过程的主要环节。由于所有话语都是高度情境性的,情境具有“封闭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能轻易地分辨出谈话参与者的主次地位。例如,在权力高度不对等的情境下,掌权者通常可以有效地控制进入谈话的机会、选择或者变换谈话的主题;与之相反,处于从属地位者则很少有这些权力。权力因素同时体现在谈话轮次上。在通常情况下,掌权者占据着明显更多的谈话时间,从属者则相对只能占据更少时间。话语方式上同样体现着权力因素。谈话者如何根据情境安排来选择话语类型,或者如何根据情境变化来调整谈话语气,这些都不是随心所欲和自由选择的事情,而是对自身进行“情境定位”的结果。这种“定位过程”本质上是参与者所处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的体现,其中蕴含着一系列特定的特权和责任,在谈话过程中参与各方既会充分利用这些特权或者承担责任,也会充分履行好与该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角色定位。从这一意义而言,即使是在最日常和最随意的话语交流中,也与更加广泛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联系在一起,其中贯穿着政治和权力线索。
话语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使用”。话语过程在“口头语言”中潜含着政治和权力因素,但其在“书面语言”中也具有大致类似的功能。一般而言,“话语主题”“话语轮次”“话语方式”在各种类型组织(尤其是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书面交流中大致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比如,在主题选择上,必须以符合公共议题的主题作为话语对象,必须选择符合公共议题的话语方式,不同层级组织之间必须选择适合于自己层级的话语语气,必须以公共议题的需要来决定话语轮次等。可以想象,在政府公文中,如果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使用“指令性话语”类型,或者上级组织对下级使用“说服性话语”类型,很可能导致话语接受者不能理解话语的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过程要素对于话语效果所具有的重要性。
话语层级与话语分析
“类型”和“过程”角度倾向于对对话进行“单一层次”的分析,即以既定的话语文本为基础或进行类型划分,或进行过程分析,从中阐释话语所表达的“意义世界”。这两种分析策略体现出相对“扁平”的特征。与之相对,“层级”角度倾向于从“多层级”的角度进行话语分析,它不仅关注话语的文本本身,而且关注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从而体现出相对“立体化”的特征。
具体而言,“层级”角度的话语分析以三个层级的划分为基础:一是“话语文本层级”,这一层级的分析具有典型的语言学属性,主要聚焦于话语的文本要素,包括词汇、语法、一致性、结构等;二是“话语流转层级”,这一层级的分析具有福柯的话语功能分析属性,主要聚焦于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背后所潜藏的权力因素;三是“话语政治层级”,这一层级同样表现出福柯话语分析的特征,主要聚焦于意识形态、政治领导权等要素的分析上。
“话语文本层级”主要包含词汇、语法、一致性和结构等要素。具体而言,“词汇分析”主要涉及对单个词汇的分析,主要表明选择该词汇的理由、词汇在表达意义世界时的功能等。“语法分析”主要处理分句与分句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分句都是一个观念或意义表达单位,分句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连接成复杂句。文本作者凭借这些单位和它们之间的联结来表明其对意义世界的看法。“文本一致性”主要考察句子之间的连接方式。尽管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内在连贯和独立的小型意义系统,但只有实现句子与句子之间的一致性,意义的表达才能变得更加充分和系统。“文本结构”则涉及更大范围的组织方式,类似于文本的总体设计书。
“文本流转层级”尽管仍然以文本作为依托,但已不再针对文本内容本身,而是侧重于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文本的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文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主要考察两个问题:一是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文本生产的视角之一是考察这些文本如何通过协作而被生产出来;二是考察文本生产的机会,这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不论在哪一个社会,总是有部分文本得到广泛的生产,有些文本则很少得到生产的机会。文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机会分配贯穿了接下来将要谈到的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因素。除偶然谈话之外,大部分文本都涉及或简或繁的分配方式,对于书面文本尤其如此。比如,部分文本作为机密文件被严格控制在范围很小的官员群体内部;部分文本则作为教育和宣传材料被广泛分配到普通社会成员手中。总体而言,文本流转层级较为偏重于分析决定文本走向的权力性因素。
“话语政治层级”主要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权角度来分析话语。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套有关现实世界的精神表象,但这一表象必须被建构为体系化的“话语秩序”。围绕话语秩序所进行的争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问题处于核心地位。领导权通过与其他社会力量结成同盟而凌驾于社会之上。意识形态是维护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寻求改造和整合从属阶级的思想以赢得后者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它构成了领导权问题的敏感区域。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总是内在稳定和平衡的,而是内在充满矛盾和张力。反映这种矛盾和张力的最重要指标是话语秩序的巩固、重述和新生。作为话语分析的最后一个层级,它的目标在于通过对话语文本的内容、流转方式及其动态变化的解读,以透视意识形态争夺和领导权斗争问题。
结语与讨论
话语类型、话语过程和话语层级三种研究策略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区别又内在依存的关系。三种分析策略存在着不同的关注点,类型分析所针对的是对作为整体的话语所作的分类,而话语过程和话语层级所针对的则是特定话语,话语过程侧重于话语进程中的要素分析,话语层级则侧重于话语形成背后的逻辑挖掘。但同时,三种策略彼此依存,每一种分析策略都依赖于其他两者,政治和权力因素是这三种分析策略背后所隐含的核心要素。
如果说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话语体系业已成为我国政治学界的共识,那么,上述三种分析进路可以为本土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何种启示?我们认为,须将上述三种分析进路贯穿于两个层面的努力:一是对于现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检视;二是关于中国政治学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里仅以话语类型为例进行说明。如前所述,话语体系总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因素关联在一起,外来话语体系也会对本土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形成规训,从而限制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我们当前所使用的许多政治学话语很可能反映的是西方思维而非中国的政治现实。比如,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西方政治学者先后使用了“绝对威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竞争威权主义”“选举威权主义”等词汇来描述中国,“威权主义”似乎成为中国难以摆脱的一个政治标签。由于这种话语规训的结果,国内甚至也有部分学者援用威权主义来分析中国政治。要建构真正反映中国政治现实的话语体系,显然必须审视类似威权主义的话语标签。关于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压制性话语与说服性话语是话语类型中的另一对分析性范畴,国际话语权的取得显然无法通过压制性话语的方式来获得,而需建立在说服性话语类型的基础上。这说明,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话语须重视国际交流的一面,只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能够为来自他国的学者所理解和接受,才能真正赢得国际话语权。这提醒我们,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需要关注他者的话语构建原理和话语准则,在理解与掌握话语建构规则与规律的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与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