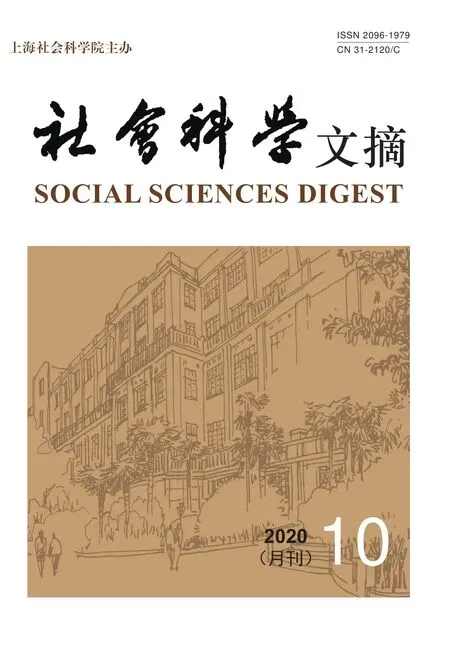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路径反思与理论建设
——基于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写作互动关系的考察
文/郭冰茹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权运动中产生,强调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是其核心特征。中国近代虽然没有独立意义上的女权运动,然而亟待启蒙的女性意识和社会生活中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文本中不断浮现,这使女性主义批评在当代中国的衍生获得了适宜的土壤。不过,在中国,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存在,女性文本即便涉及性别议题,也很难抽离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很难就性别而论性别。若女性主义批评单纯强调性别,很容易使本土的批评实践忽略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以及自身女性写作的特殊性而造成误读。因而,正视语境的差异,重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国化过程中的特殊性,才能对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作出符合历史逻辑的阐释,也才能充分认识到女性主义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是建立在女性写作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反思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旅行历程,调整既定的理论批评范式以适应并促进女性写作的发展,建设生长在中国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
一
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知识界落地生根,中国的妇女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发展到壮大、从被忽略到受关注的过程。作为妇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也在这一历程中发展和成熟起来。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是在20世纪60年代妇女争取女权的社会运动中,随女性文学的产生而出现的。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一种表达方式,女性文学在女权运动中应运而生,文学评论为女性写作进行积极的理论探索,继而逐步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并成为学院的一种知识生产。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形成过程说明,明确的性别意识是其理论建设的基础。
女性主义批评所倚重的性别立场和性别意识对文学研究,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研究者以性别为切入点重新清理文学史,使许多对中国文学作出贡献的女作家走出了尘封的故纸堆,也对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论的女作家作出了性别立场的重新评价,成为“重写文学史”的积极尝试;另一方面,批评家以性别意识介入文学批评,肯定女性经验的权威性,分析女性文本的主题、结构和创作心理,总结女性写作的特征和规律,成为建构女性文化或者女性美学的一种努力。不过,伴随这两项学术工作的逐渐展开,对“性别”的强调所带来的问题和局限,也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呈现出来。这不仅反映在“性别”对女性写作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遮蔽,也反映在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批评对“性别”的不同认知,以及“性别”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发展空间的限制等诸多方面。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作为文学现象的女性写作是由女性主义批评催生的。在性别视角的观照下,新时期初年的许多女性文本都被解读出性别意识,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视野中,比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谌容《人到中年》、戴厚英《人啊,人!》等。从性别角度看,这些文本都折射出了女性在情感、家庭、事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困境。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和女性写作生成的初始阶段,这样的分析阐释无疑是必要也是必须的,然而只关注性别却悬置此类文本产生的语境,忽略文本的整体结构和意义,很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现实中,女性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发展和成熟,女性文本中的性别意识被有效开掘和深入解读,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强化的性别意识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或改变了男权中心的文化现实。但是,单纯以性别意识作为理论视角的研究无法兼顾女性文本的多元性,也会使女性文本的多重意义,尤其是性别议题之外的意义被忽视。事实上,新时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文本很难被纳入只强调性别意识的话语实践中。活跃在当代文坛上,受女性主义批评关注的许多女作家的创作,都是既有包含女性主题、性别视角的写作,也有超越女性主题,不囿于性别视角的写作。张洁、张抗抗、王安忆、方方、池莉、徐坤等,还有更年轻的一批女作家,比如鲁敏、乔叶、黄咏梅、笛安、张悦然等均是如此。性别视角当然是女作家观察世界的视角,但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女作家进行文学书写时的唯一视角。相应地,性别意识、性别视角、性别立场也不应该是衡量女性文本的唯一标准。
女性主义批评强调性别立场和性别意识,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强调是否能与文本产生的语境以及文本内部深层的意义结构相协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对性别问题的处理也并不完全契合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性别”的认知。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所有的父权制都只是男性力比多机制的投射,女性要摆脱父权制中沉默或缺席的境遇,就必须通过压制对方才能在象征秩序中获得意义,女性文本却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比如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张洁的《红蘑菇》,她们的处理方式一方面说明女性写作并不认可这种以暴易暴、仅仅在象征秩序的权力结构中施行简单的位置互换而不触及结构本身的“夺权”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性别问题有自身存在的语境,西方的批评理论并不能与中国的性别问题完全对应。
事实上,在我们讨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时,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该理论庞杂的体系中,关于“性别”或“女性写作”的认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伊莱恩·肖瓦尔特曾大致概括了涉及女性写作的四种不同的批评样式: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女性批评(gynocritics)、女性本原批评(gynesic criticism)和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批评对“性别”的认知过程是其批评的重心从“女权批评”逐渐过度到“性别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该理论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每一种批评样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中国知识界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但接受的路径与该理论在西方通过不断反思逐步推进的过程非常不同。换言之,中国知识界是在功利主义的推动下,共时性地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成果。因而,我们在清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时,就不难发现女性写作并不是完全按照女性主义批评设定的轨迹渐次展开的,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女权批评”与“女性批评”也共时存在。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功利性的接受,女性主义批评在借助“性别”分析研究女性文本,追溯清理女性文学传统时行之有效,在结合本土语境与创作实际反思理论局限、推进理论建设方面却乏善可陈。
二
与其他文学理论不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其产生本身就是为了服务于女性文本。当然,女性主义批评也只是一种阐释方式,从性别角度进入文本不可能呈现出女性文本的全部意义空间,但是清理近20年的女性写作,我们也不难发现,如果女性主义批评只关注性别意识和女性美学建构,其能为女性写作提供的理论支持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限。这是因为孕育女性写作的文学秩序和文化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写作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虽然仍在处理个人经验的表达、性别主体性的确立以及女性历史的建构等女性主义批评比较关注的主题,但是女性经验已很少作为结构文本的核心事件,性别意识也很少成为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根本动力。这些变化表明女性写作所包含的“性别”问题远比批评实践所关注的性别立场和性别意识复杂得多。换言之,女性写作本身正在突破既定的理论框架,女性主义批评如果不作出相应的理论调整,将很难适应变化了的女性写作。
强调个人经验的书写是女性主义批评建构女性美学的方式之一,建立在个人经验上的“身体写作”尤为女性主义批评所重视。20世纪90年代,林白曾以极端的“身体写作”备受女性主义批评的青睐。单纯将身体经验作为书写对象也只能使写作变成一种自我复制的体力劳动。林白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开始主动将自己的文学世界向社会空间敞开。虽然《万物花开》(2003)、《妇女闲聊录》(2004)、《致一九七五》(2007)、《北去来辞》(2013)依然能够成为关于女性意识和性别立场的批评实践地,但这一文本序列显然包含了比性别问题更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相对于身体经验,一个人的经历、情感、思考、认知可能更具有“个人性”,更关乎个人的性别认同与身份建构。虽然乔叶《最慢的是活着》、魏微的《寻父记》、金仁顺的《梧桐》等带有个人体验的文本触及了关于现代女性心理、情感和身份认同等诸多问题,这些已远远不能为性别经验所囊括。
如何改变女性在象征秩序中被动的客体位置并确立其主体性是女性主义批评立论的起点。王安忆曾在《逐鹿中街》(1988)中讲述了一个关于改造和失控的故事。30年后,裘山山的《失控》(2018)讲述了一个几乎同样的故事,只不过主角换成了男人。如果说《逐鹿中街》讨论的是性别问题,是在男/女、主体/客体、主动/被动这一二元对立的权力模式中,思考女性如果僭越了规则,获得了主体或主动性的位置,是否能够抵达平等或者解放的彼岸;那么《失控》则否定了男性作为创造主体的权力位置,直接拆解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前提。这意味着男女两性,谁都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或改写另一性,由此,《失控》讨论的问题超越了性别本身,直接指向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主体性的确立。
改变女性在历史长河之中“物”的处境,让女性扮演叙事者的角色也是女性主义批评重要的学术工作之一,因为女性主义批评认为,历史经验并不完全属于男性,女性可以通过书写、通过表达、通过叙事进入历史,构建出有别于男性传统的女性历史。但是,21世纪以来叙述历史的女性文本大多没有沿着这一轨迹继续深入,反而不再以建构“女性历史”为叙述目的,也不再以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来认识历史。比如王安忆的《天香》、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铁凝的《笨花》和范小青的《灭籍记》等。从这些文本实践可以看出,尽管女作家们在叙述中仍然借助性别视角,但性别视角并非进入历史的唯一视角,性别问题亦非讲述历史时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便是关于性别经验的书写,也安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中。这种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已经超越了女性主义批评对“女性历史”的理论设计。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相比,21世纪的女性文本在处理个人经验、社会生活、历史想象等方面都有了更多元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本实践立足于性别,但并不囿于性别,拥有更深广的表达空间。女性写作的这些变化显然需要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作出新的阐释和概括,从而充实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三
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写作相伴相生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其理论建设无法脱离具体的文学实践而独立展开。一方面,女性写作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批评理论作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处理性别问题的策略和方法也为批评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某种方向性的维度。因而,调适两者在互动过程中的矛盾与分歧,有助于女性主义批评抛开成规,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
我们认可女性主义批评之于女性文本的阐释价值,就必须正视囿于性别立场带来的阐释局限。就女性主义批评而言,女性主义理论的建设必须要有性别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有一种立场,而且性别立场本身与其他立场也并不矛盾。正如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两性关系一样,女性写作所处理的材料也不可能仅仅指向性别,而女性文本中超越性别意识的表达,同样也不是以否定性别本质为前提的。相应地,女性主义批评强调的性别意识只是女性写作的一种路径,更何况性别意识鲜明的文本也是在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中产生的。丰富多义的女性文本已经提示女性主义批评无需自我设限。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在调适与女性写作的互动关系时,非常有必要以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将性别问题放置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去考量,在性别立场上叠加或者兼顾包括民族的、国家的、民间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等立场,而不是从复杂的文本中仅仅抽离出纯粹的性别问题进行解读和理论归纳。
女性主义批评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是建构女性美学,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通过强调性别差异,为女性在既定的权力秩序中争取平权,在被漠视或者忽视的文化传统中建构女性文化。但如果文学批评只是简单地将女性写作与女性的性本质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写作应该是细腻的、日常的、繁复的、“女性化”的,或者男性的写作应该是粗狂的、宏大的、简约的、“男性化”的,无疑是偏狭的。事实上,女性主义批评自身也对单纯强调性别差异的女性批评进行了反省,因为界定女性文本的独特性是非常困难的,无论这种差异来自风格、文类、经验还是阅读过程,其标准都很难确立。
其实,关于性别本质以及由此引发的性别差异的争论,不仅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议题,也是推动该理论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1929年弗吉尼亚·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借用柯尔律治的说法“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婉转地表达了男女平等、相互交融、和谐共存的文化诉求,并借此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写作权利。新时期以来大量将性别议题与其他议题相交织,包含性别却不局限于性别的女性写作,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建构女性美学的思路。这些女性文本提示我们,批评理论可以在“双性同体”基础上构建女性美学。只不过,这种“双性同体”的文化想象是建立在充分肯定和尊重女性性别本质的前提下,这意味着女性美学的创建需要既重视女性的性别本质,也兼顾蕴含在性别本质中的模糊性,既尊重作为性别群体的普遍性,也肯定女性作为个体的特殊性,从而为女性美学的建设赢得更广阔的理论空间。
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的发展轨迹来看,虽然研究女性文本是其始终如一的任务,但其理论建设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在为女性文本提供有效阐释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人类认识世界、了解自身的知识体系,或者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在西方,“性别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在文学、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也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联系中国女性写作的实践,女性主义批评也完全可以以性别为方法来讨论中国问题。当我们将性别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相联系,性别才不仅成为分析女性文本的视角、立场和眼光,同时也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法,进而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