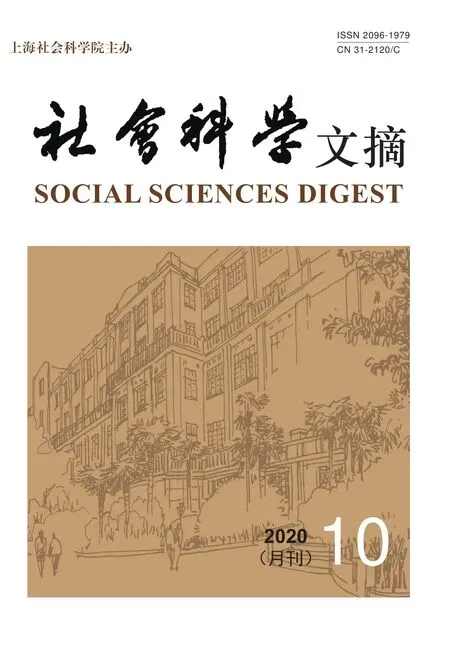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对“人的文学”的再思考
文/李春雨
文学是人学,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文学的本质是写人、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写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也不是一个新的结论。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虽然从根本上改变甚至颠覆了以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它改变不了文学写人的这个本质。在书写人在重大变动下的生存方面,文学从未缺席,也无法缺席,这既是文学关注人的命运的天然本性,也是文学对时代社会肩负的重要使命。这一点,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现实也正在证明,未来还将继续证明。从“文以载道”到“人的文学”,从“人的文学”到“时代的文学”,从“人”到“人类”的升华,这些命题贯穿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与关注。
从“文以载道”到“人的文学”
“五四”以来,百年中国文学的根本主题就是“人的文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主题是在“五四”新文化对几千年来“文以载道”传统的质疑中诞生的,这是“人的文学”命题得以出现的一个历史逻辑。“人的文学”是否意味着对文学载道传统的彻底扬弃?我们有必要对文以载道和人的文学都作一点重新的辨析。
第一,文以载道,载的是什么“道”?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柳宗元倡导的“文以明道”,韩愈践行的“文以贯道”,周敦颐推崇的“文以载道”,虽然各自所指之“道”不尽相同,但根本上强调的是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一种传统:文学不仅是审美、艺术上的追求,而且必须承载思想层面的价值、理念,它既可以是对社会、国家的批判,也可以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看,“文以载道”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学和文化关注现实、关怀天下的一种文化自觉,而绝不仅仅是哪一个具体朝代、哪一种具体制度下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理念。简单地把“文以载道”理解为某一种政治理念、伦理制度的“文学工具论”,是非常狭隘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长河里,我们很少能找到哪一部著作是“纯艺术”的,它们背后都要有所载之“道”。
第二,“五四”新文化反对“文以载道”,是反对文学的“载道”功能,还是反对传统文学所载之“道”?“五四”的现代化转型是在反传统的语境下拉开大幕的,作为古典文学核心命题的“载道”自然当仁不让地成为新文化运动者攻击的靶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就是反对载道的文学,恰恰相反,新文学不仅不反对“载道”,反而充分利用起文学的“载道功能”,用来载“启蒙”之道,用文学唤醒民众的觉醒,这种使命意识本身就是对“文以载道”的延续。这事实上也意味着“五四”新文学反对的是以一种“道”规范、钳制所有的文学,而不是反对文学的载道功能。
第三,“人的文学”,“人”到底指什么?“五四”是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学自然发展而来的,更是世界性文化及文学相互渗透、撞击和融合的结果。这意味着鲁迅的“立人”、陈独秀笔下“最后觉悟之觉悟”的国民想象、李大钊想要再造的“青春之我”、胡适心目中的“新人格”、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实际上都是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个人觉醒与社会批判结合的产物。在笔者看来,这些提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是对新文学主体的现代化想象,所涵盖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层面,个人之人。在“五四”发起之时,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压制,就不得不依靠个性解放来张扬个人的价值。我们今天确实也能看到“五四”时期所留下的很多“个人化”的书写,比如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热烈地追求着个性解放,是一种火山喷发式的情感张扬,《天狗》每一行都以“我”开头,仅仅29行诗歌中出现了39个“我”字。这种对自我的崇尚和对自我力量的认可,是几千年文学没有出现过的崭新面貌。
第二层面,自然之人。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对“人”的定义“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在这里,周作人的观点其实包含了两个要点:一是“从动物”进化的,二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其实也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逻辑:只有对自然、生命本身的高度推崇,个体之人才能够存在。
第三层面,社会之人。个体觉醒是“人的文学”的出发点,但不是落脚点,“五四”确实因为西方文艺影响,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四”是一场“个人化”的运动。郭沫若看起来是那样地浪漫抒情,但他也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样高度清醒理性的政论文章;郁达夫再如何私语,如何个人,他也有《广州事情》这样犀利的社会批判。高度浪漫,高度关注个性,但又高度关注现实,高度回归社会性,这两点的融合才是“五四”最大的特点。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标志,在张扬人的个性、文学的解放方面具有长久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否全面、准确?这是值得反思的。一方面从事实上看,周作人所谓的“人的文学”,从来都不是只强调个人性张扬、人性解放的文学,它是一个包含了个人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复杂思想体系,是从“自然”生命里发现“个人”,从“个人”觉醒达成“社会”的启蒙的逻辑命题;另一方面从理论上看,“人的文学”的概念也不应该被狭隘到仅仅对“个人性”的理解。从历史到“五四”再到今天,“人的文学”的概念从来都不只是个人性的突显,而是个人性、自然性与社会性三个层面的共同融合,这才是“五四”留给我们的真正伟大而深刻的命题。今天看来,新文学确实以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新面貌横空出世,但这种“新”依然是相对性的,它并没有改变中国自古以来文学的根本本质,那就是文学不可能离开社会性、不可能离开时代性、更不能离开人和人类而存在,其实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将来也不可能改变。
从“人的文学”到“时代的文学”
如果说“五四”初期更多是在理论上建构了一个“人的文学”,那么“五四”以来的一百年历史进程则用实践来证明:人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可能依靠抽象的人性解放,只有融入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中才能得以实现。
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一个最集中的表现就在于灾难叙事的频繁出现。丁玲的《水》、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等,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灾害。有的是旱灾,有的是水灾,有的是明明丰收了却还是迎来破产的“丰收成灾”。为什么这些作家执着地写这样一个题材?写灾难是为了写灾难背后的人祸,只有在极端的情景下,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得到更为真实的暴露,这是一种时代的文学,更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的文学”。茅盾在成为著名小说家之前,更是一位批评家和理论家,他能够在1933年就创作出《子夜》这样的现实主义巨著,就得益于他长期在文学理论上的积累和沉淀。但这样一位精益求精的理论家和批判家,却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很多“未完成”的创作残篇。《虹》《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于二月花》《锻炼》等作品都没有完成茅盾最初的构想,在主题和情节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就匆匆结尾。何以至此?茅盾过于想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社会的主题,因此他需要长篇小说的体量来容纳时代的方方面面,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突变的局势下,长篇小说显然又不具备能够时刻贴近时代脉搏的灵活度。茅盾焦虑地想要用文学反映时代、记录时代、解剖社会,但又无力真正地掌控,这难道不是那个时代里更加真实的“人的文学”吗?
进入新时期之后的文学依然如此,作家以空前的热忱关注个体在时代面前的迷茫、反思和追寻,这既是对个人的关注,也是对时代的一种反馈和回音。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说起来写法并无多大的独特之处,却为何能在当时产生震撼效应,并直到今天依然拥有大量的读者?就是因为作家对现实的热切关注,他站在同时代人中间,却有着比普通人更为深切的感知和更为清醒的理智,因而作品直接戳中了时代的痛点,引发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共鸣。余华也是如此。余华的创作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尤其擅长直面人生悲苦的一面,在人性最柔弱的地方扎上一刀,把痛苦作为人生的“常态”来描写;第二,他又始终把这种悲苦紧扣在时代社会变革的节点上加以表现;第三,他总是力图通过对个人不幸的思考达到对人类命运的理解。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写的既是一个人的苦难史,也是一个时代的苦难史。福贵的命运其实是经历了国共内战、土改、“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的那一代人苦难的浓缩。许三观一生靠卖血度过了很多难关。我们发现,小说写的是许三观一次又一次卖血,但其背后都是鲜明的时代、社会印记。余华的作品里有不少夸张、戏谑的东西,但更多的是真实的、现实的东西,这些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余华作品的根本特质,即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互为表里,互为因果。莫言常常被称为“中国的福克纳”或“中国的马尔克斯”,他自己也并不回避对这两位作家的学习和借鉴。但是莫言作品的根本生命力,是在中国的土地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莫言之所以能够真正地走进世界的视野,并不是在于他魔幻的表现手法,更不是他迎合了西方的审美,而是在于他在作品里描写的依然是中国人在一个世纪以来所经受的生活、精神的变迁与苦难,这才是莫言作品根本的精神资源。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转型,我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迎来经济、社会、政治、哲学、道德等众多方面的迅速发展。回望历史,唐宋元明清虽然也有着时代内部的更迭,但总体来看,它们更像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内核影响着我们,但是“五四”以来的这一百年,工业革命、商业革命、智能时代,人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的精神日新月异。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迅速地变成了现实,人类的命运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与时代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与时代的关系会更加密切,这种密切不是简单的相加、绑定,而是在更高的层面达成融合和升华。
从“人”到“人类”的文学升华
人和人类这两个词看上去相差很大,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往往会想起自己,但当面对人类的时候,却往往觉得这个词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从历史到当下,无数的文学经典都生动地演示了这一点。
历史曾经告诉我们,个人与人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回顾历史经典,个人命运与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就是一个永恒不衰的话题。个人与千百万人的命运相牵连,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了战争、瘟疫等重大灾难降临之时。这些灾难的爆发,就像一个个即时炸弹,迅速地中断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并把各种不同的人生拉入一个共同的命运漩涡。小说《鼠疫》深刻地表明了想要避免瘟疫,不过是人类的美好愿望罢了。《鼠疫》继承了加缪创作一贯的主题,即世界的“荒诞”,以及人对“荒诞”的反抗。所不同的是,小说中面对来势汹汹的鼠疫,个人的反抗已无力回天,人人团结、直面灾难、共同反抗才获得了最终胜利。在这部小说里,加缪对“反抗”的呈现,其重点已由个体的反抗上升为更有广度、更有力度的人类行动。医生、记者、政府职员、病患,这些平凡的普通人面对灾难时突破自我,从狭隘、利己走向崇高,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值得赞颂。《鼠疫》出版于1947年,小说中所描绘的情景,却与当下由新冠疫情带来的世界性灾难有着惊人的相似。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人类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实际上自然界早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类发出了警告。在全球化越来越成为趋向的当下,面对大自然给我们的挑战,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明哲保身,整个人类的安全和利益都已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绑定在一起。
现实正在提醒我们,个人与人类依然是水乳交融的。全球化、世界化加速的不仅是科技的共享、经济的合作,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依存。“核威胁”是科技的悲剧,更是人为的灾难,它潜伏于人们生活中,随时可能给整个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2013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晚年样式集》,在2011年发生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再次表达了对人类潜在的“核危机”的深切关注。大江健三郎一直走在“反核”“反战”作家的前列,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曾连续出版了《广岛札记》《冲绳札记》等具有轰动效应的纪实性随笔作品,并多次在“反核”集会上发表演讲,而在《晚年样式集》中,他又将福岛与广岛、冲绳因为同一个问题而联系在一起。这些直面“核威胁”的作品,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人类该如何避免核灾难的重演?当灾难从历史事件变成正在生活中上演的现实,我们也逐渐变成历史的见证者,成为灾难攻击下的世界的一部分。现实已经一再用伤痛警醒我们,人类永远不要试图因为现代科技的发达、文明的发展而漠视自然,凌驾自然之上,否则承受痛苦的必将是人类自身。
未来同样警示着我们,个人与人类永远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当面对着更加不可知的未来世界,作家关心的更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而充满着对人类整体命运何去何从的思考。当我们去看待这一类描绘未来、想象未来的作品时,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就出现了:作家对未来的想象似乎总围绕“世界末日”“人类绝境”“种族灭亡”这样的话题。拿科幻小说来看,刘慈欣的《三体》写的就是当面临着更加高级的三体文明,人类应该如何生存?《流浪地球》更是直接描写了太阳毁灭之后,人类带着地球一起流浪的故事。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已经不存在个人式的英雄,甚至也不存在民族的英雄,不同国家组成联合政府,共同应对着未来世界的巨大挑战。只有这样的文学想象,才能触发一些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根本性思考。科幻之所以成“文学”而不是科普,就是因为这种未来想象与现实生活的勾连,因为这种宏观世界朝向微观生命的关怀与思考。
眼下这场全球范围的疫情,生动而深刻地突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意义。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意识到“人”自身的根本价值,意识到人与人类密不可分的、休戚与共的依存关系。在疫情面前,科学的治疗、政策的规约等是十分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人的精神健康、心智的健全和思想的成熟。人类不仅在“常态”下生存,也会遇到类似疫情这样的“非常态”状况,如何在复杂的状态下生活与发展,这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文学无可替代的主题与责任。越是在复杂和困难的状况下,文学越是应该在场,必须在场,这是中国文学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并将不断延续的悠久传统和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