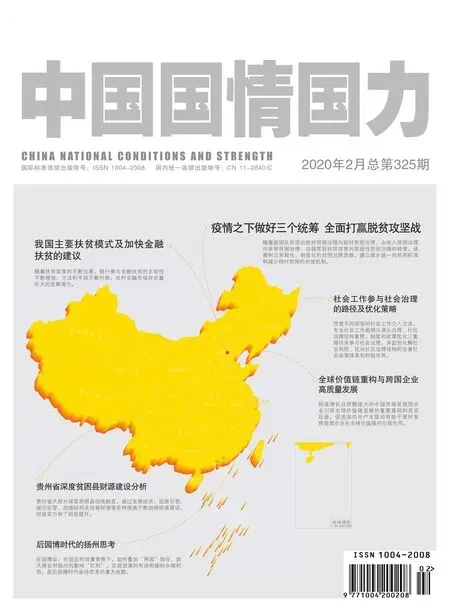新时代员工四种转向特征
李然 李海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与此相适应,中国现代企业及其员工必须跟上时代。因此,与新时代相配套,必须“打造时代员工”,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
什么是时代员工
1.从技术革命看
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一是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叶,以蒸汽驱动机械设备制造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蒸汽时代”。二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以电力驱动大规模生产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时代”。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大规模运用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自动化时代”。四是21世纪以来,以虚拟现实、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大规模开发应用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智能化时代”。鉴于此,不同技术发展阶段对员工的技能、素质要求各不相同。
2.从制度变革看
当今社会,由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与智能经济深度融合、相互叠加,导致员工定位和角色各不相同:一是员工定位于被管理者,其角色为“工具人”。二是员工定位于自管理者,其角色为准主人。三是员工定位于自创业者,其角色为合伙人。四是员工定位于自组织者,其角色为社会人。员工定位角色不同,不仅引致企业运行机制的重大差异,而且引致国家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以此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发展人”。
3.从企业转型看
当今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企业及其技术、产品、产业要分别转型为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打造时代企业及其时代技术、时代产品和时代产业。与传统企业转型为时代企业相适应,传统员工须转型为时代员工。
为什么要打造时代员工
1.新发展的要求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变化:一是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即从重视速度型、数量型、外延型和牺牲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重视效益型、质量型、内涵型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二是从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解决“从大到强”的根本问题。三是在国际上从“跟跑”发展转向“并跑”“领跑”发展,包括在部分产业领域制定标准规则和掌控话语体系。这一转型发展的微观基础及具体实践在于广大产业工人队伍。目前,整体来看,无论从理念、技术还是素质、操作来看,现有产业工人队伍还不适应新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现有产业工人队伍亟需一场“脱胎换骨”式的革命。
2.新技术的要求
当今社会,新技术革命加速推进,出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终端;ICT、DT、CPS,VR、AR,区块链;识别技术(指纹、语音、人脸)、无人技术(无人驾驶、无人工厂、无人银行……)、3D技术、5G技术、量子技术等。概括说来,这一技术革命的大致走向是: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从物联网到智联网,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它不仅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冲击着人们的工作方式,更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现有产业工人队伍亟需一场“更新改造式”的革命。
3.新动能的要求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所在。“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更多依赖人的“智力产出”,而其关键在于研发人员。我国产业工人队伍长期以来呈现的多是“人口红利”“数量红利”而非“研发红利”“质量红利”。也就是说,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土地及资金等,现在经济发展更多转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综合创新,它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结晶或智力性劳动成果,一旦形成,可以无限次地重复使用。因此,现有产业工人队伍亟需一场“转型升级”式的革命。
打造什么样的时代员工
1.从重复性体力型员工转向创造性脑力型员工
当前正在推进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其重要特点是“机器换人”,机器不仅可以代替人的绝大部分体力劳动,而且可以代替人的一部分脑力劳动。针对产业工人队伍,此举意味着人的发展必须从1.0、2.0向3.0、4.0演进。其中,人的发展1.0,人口——纯消费者,处于非生产者阶段;人的发展2.0,人力——以体力劳动为主,重复性工作,处于人力资源阶段;人的发展3.0,人才——以脑力劳动为主,创造性工作,处于人力资本阶段;人的发展4.0,人格——又红又专、德艺双馨,处于人格资本阶段。这里,打造时代员工,不仅是单个企业的事情,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2.从他组织管理型员工转向自组织管理型员工
过去,员工要么附属于机器设备,被物管理;要么服从于等级权威,被人管理。总之,体现为被管理者,属于他组织管理。目前,随着去等级化、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的发展,员工已经由被管理者向自管理者甚至自创业者、自组织者发展。这里,首先体现为自管理者,属于自组织管理。所谓自组织管理,从个体看,自我导向,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从整体看,自驱动性,自增长性,自优化性,自循环性。需要指出的是,自组织管理是由脑力劳动的复杂特点所决定的。
3.从遵从企业文化员工转向遵从职业文化员工
过去,员工隶属于某一单位,固定性强;现在,随着在职员工向在线员工的转变,员工由“单位人”开始转向“社会人”。即通过借助“新技术群”,个体可以零时间、零距离、零成本地对接工作需求,“去组织化”整合社会资源,实现自身价值。从生产者看,企业开始转型发展,一方面把在职员工变成企业创客,让其自主创业、自主发展;另一方面把社会创客变成在线员工,一则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二则大大降低用工成本。这种新型劳动关系的变化,使得企业文化的作用越来越淡化,而职业文化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将来,不论员工岗位如何灵活、弹性,遵从职业文化是其首要选择。只有具备工匠精神以及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操守、职业技能等职业文明的员工,才能立足于各个行业、各个工作和各个岗位。
4.从工作-家庭失衡型员工转向工作-家庭平衡型员工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统计,2018年末,中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9%,中国已成为超老龄化国家。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大量独生子女,以及近几年来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情况,这代人的家庭负担尤其沉重,工作-家庭关系失衡,不仅影响工作状态,而且影响家庭和谐。今后,转向工作-家庭关系平衡,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技术的使然。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导致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边界模糊,人们既可以在工作场景中处理家庭生活,也可以在家庭场景中处理工作事务,从而使工作-家庭关系由对立走向统一。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利用移动办公、在家办公等在线办公形式,自由配置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以此提升时间利用效率。
打造时代员工需要哪些配套政策
1.教育培训
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引致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正在重构全新的生产方式。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新技术群”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整合,导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面感知、可靠传输、精准决策、智能处理的全新时代。传统知识体系加速折旧,新型知识体系亟需重构。增加员工教育培训时间,使其彻底从重复性体力型员工转向创造性脑力型员工,构建人机协同工作方式,是当前摆在国家面前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必须早打算、早安排、早实施。
2.工作时间
“机器换人”的未来场景可描述为“机器干,网在看,云在算”,最终结果则是,人们工作时间缩短,休闲时间增多。也就是说,生产方式革命导致生活方式革命。总体上看,闲暇时间增多,一方面,人们可以利用更多闲暇时间处理家务,老人孩子照顾好了,家庭和谐幸福,从而对创造性工作更加投入、更加专注,以此把社会领域问题和经济领域问题融合起来一并打通解决。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广泛从事学习培训、自主研发,挖掘创意灵感,培养创新能力,从而活跃整个社会自主创新氛围。加快推动形成闲暇和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奠定打造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国家的深厚基石。
3.灵活工作
工作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增多,近期可能影响人们的整体收入水平。鉴于此,一是人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释放多样能力。作为旧时代的员工,大多固守一个职业、一个身份和一个工作;然而,作为新时代的员工,可以从事多个职业、多个身份和多个工作。在新时代,零工经济、夜间经济形态日益成熟,建议国家适时出台政策,像医院多点执业医师、高校教授多点授课那样,鼓励工商企业员工利用闲暇时间从事与自身专长、兴趣相关的第二职业甚至第N职业。二是利用闲暇时间复制核心能力。员工在某一领域具备核心能力或专业特长后,不仅可为本单位服务,更可为全社会服务,做一个“U盘式员工”“即插即用,用完即拔”,由此成为社会共享员工。由于其专用性、专长性人力资本在社会中被各个主体无限次地重复使用,既促进了社会价值增值,又提高了个人收入水平。
4.社会保障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特别是“五险一金”主要是由雇佣关系决定的。只有进入“单位”,与“单位”建立了雇佣关系,才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特别是“五险一金”待遇。如果脱离单位,即失去了享受“单位人”员工的社会保障,特别是“五险一金”资格。鉴此,社会政策需要做出根本性的转型。除基本收入由工作关系决定外,社会保障待遇全部应由“公民身份”决定,即以社会权利的名义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不仅如此,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社会保障范围、内涵、水平和质量也应逐步提升,旨在实现全民共享“时代红利”,践行“普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