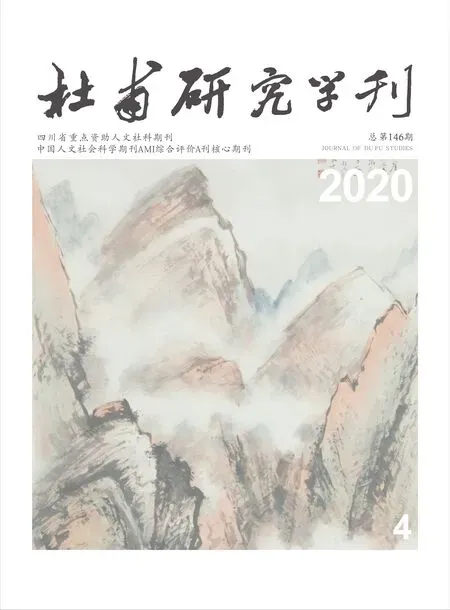一部开拓杜诗学研究新进境的力作
——评张家壮《痛切的自觉:明末清初杜诗学考论》
胡永杰
一
家壮君的“新”著《痛切的自觉:明末清初杜诗学考论》近日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我有幸获赠奉读,深感快慰,也不禁想表达一点儿读后的感受和收获。首先需指出,之所以把“新”字加上引号,因为这是他博士论文的增补修改本,从2009年论文完成至2019年12月出版,之间经历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仅于此,即可见家壮君笃厚严谨、精益求精学术态度的一斑,这与我多年来和他交往中获得的认识是一致的。
关于此著的研究目的和思路,家壮说他意在“对杜诗学所寄寓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注家的个体生活经验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心理’的考察为线索,寻绎其作用于杜诗学的种种进路,由此呈现明末清初一百多年间杜诗学发展的大致脉络”(第18 页)。表明,他是紧扣时代的、历史的、注家个体的综合背景来考察认识明末清初杜诗学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脉络。从方法上言,乃是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研究杜诗学①。
知人论世,是包括杜甫研究在内的古代作家作品本体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在杜诗学这一学术史研究领域,总体而言其运用还谈不上深入。家壮君之所以取此路向,我想主要原因应有两端:其一,由于杜甫在后世历史上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杜诗学的意义并非文学研究或学术研究自身所能涵盖,它往往还是时代文化精神“对象化”之攸集、治杜者人生价值之寄托所在。他深知,仅仅关注辑注、评解这些“学”的范畴,尚不足以完全揭示杜诗学的价值。就如他在著中所论:“正是这等空前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还有清醒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使明末清初的杜诗学对于明末清初那一段历史如此地贴近,因而杜注也就近乎成为注家与时代关系的表达式。此外,以历史巨变为普遍背景,在沉重艰难的生活情境下,杜注中还融合着注家较为个人的,也更为细腻的人生体验。”(第16页)其二,受其师林继中先生的影响。林先生多年来提倡“将文学置诸‘文化域’这一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视界,做整体的动态的考察”,提出“文化建构文学史”“文化诗学”的概念②。而作为杜甫研究专家,杜诗学正是他实践这一方法、思路的主要对象③。家壮君此著应该说是对林先生研治杜诗学道路的继承和拓展。
以上是对家壮君此著研究目的和思路的整体性概括。那么,具体研究中所达到的效果、取得的实绩如何?我认为他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在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的系统性、深度、广度、具体问题的深化诸多方面,都体现了杜诗学研究的新的进境。
二
关于研究的具体取径,家壮君说:
探询明末清初杜诗学的整体进程,必须建基于对杜集具体(而非笼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各个杜集之间纵横交错的异同关系,从而勾勒出这个阶段杜诗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样一来,就要求每个个案在被我们作为“细节”研究之后有可供提取的“整体” 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即“在具体研究所有细节时,必须始终铭记整体”。我们认为,所谓“始终铭记整体”,不应该只是一种意识,还要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以贯之的关照模式,亦即在某个视角支配下的研究方式。因为所谓“整体”,亦不过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不同的关照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整体。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想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将是困难的。(第18-19页)
可见,他是欲采取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以贯之的关照模式”,在此“观照方式”下从“细节” 中寻绎“整体意义”,从而勾勒把握明末清初这一段杜诗学的历史脉络和整体风貌。这个“观照方式”就是“杜诗学所寄寓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注家的个体生活经验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心理’”(第19页)。
著中分为三篇,上篇对此时期杜诗学者做整体考察;中篇以王嗣奭《杜臆》、金圣叹《杜诗解》、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六家著作为中心做具体讨论,这六家著作两两为一阶段,兼有个案研究和发展脉络及历史进程梳理两重意图。这样的结构安排,正与他“建基于具体研究”而“始终铭记整体”的思路相合。上篇即是着力探求这一“观照方式”。他首先从明末清初杜诗学者的地域分布考察入手,揭示他们的籍贯分布主要在以江浙为主的江南之地这一现象。而江南之地正是以“以省身克己砥砺名节为教,而最留意于当世之务”(第46页引梁启超语)为追求的明代及明末清初东林党、复社、几社等党社活动最为活跃之地,杜诗学者们也多属党社成员。从而,他总结出了这时杜诗学者的主要特征:因地缘、党社、师友、亲缘等关系及便利,他们具有联系紧密、相互激励的群体关系;因党社宗旨、时代环境的激发,他们具有“省身克己砥砺名节”“痛切的自觉”等群体精神;他们的身份多为儒者而非一般纯粹文士。无疑,这样的群体特质,加之独特的时代环境,必然会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杜诗研究。如他所论:“杜诗学在明末清初的再度兴起,很大程度上缘于这一代士人的‘痛切的自觉’——既‘自觉’地发现自己与数百年前‘诗圣’的精神感应:从社会意识、民族感情直至个人的悲剧感受,从而也‘自觉’地加入到杜诗诠释的队伍中来。”(第15页)“儒者注杜不但促成了杜诗学者总数的量变,而且其活动方式、共同的学术追求更酿成了杜诗学界风貌的质变。”(第51页)
于上述视野下不难想见,明末清初这一代杜诗学者自然不会满足于对前人阐释中的杜甫、杜诗“拿来”,而是欲建立自身也是时代所需要的杜诗学。而“新建”之时,必然会对前有之杜诗学有所破除,有所承续;在这些破、立、承续、恢复等诸多的路向下,无疑将会衍化出既丰富多姿、异彩纷呈,又有其内在共通性的一代杜诗学。家壮在中篇正是带着这样的“观照方式”去深细而敏锐地考察这时具有代表性的杜诗学者和他们的杜诗注解,在整体脉络的把摸和具体问题探究上,都提出了不少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比如,他分析王嗣奭《杜臆》的“以意逆志”解杜法,乃紧扣王嗣奭与杜甫之间“家国之痛”这一相似的处境,指出王氏解杜虽尚有胎息明代杜诗学风尚的痕迹,但他是在恢复被明人抛弃的“知人论世”这一环节基础上“以意逆志”,实由明人的空疏走上了健实;而且他“以意逆志”之“志”还有“因诗悟道”的独特意指,乃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原始情景相暗合(第146 页)。对于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他在具体考察统计的基础上指出,“他们虽然猛烈地批评宋人的杜注,但又凭借宋人的成果进行新的整顿。与刘辰翁评杜之不但遭到他们的挞伐亦且被删汰至残存无几不同”,他们对待宋注其实是“辟之而又用之”,二者之间的紧张对立只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的解释上,而与注杜的基本范式无关(第186 页)。因而揭示,明末清初学者笺注杜集,其实是继承和重树宋人笺注中寓含的杜集具有经典性意义和地位这一传统,是经典本位批评意识崛起的表现,符合清初学术界告别“游腹空谈”,提倡“尊经复古”,回向以考据为中心的汉学研究路径的整体动向(第186 页)。他考论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集大成”意义,着重从仇氏注杜的思想根底、注杜方法之来源与其采择前人注杜成果之间的关系上着眼(第209 页),揭示其中通常所谓的“援据繁复”之外的深层内涵。即,意图上,意在为实现康熙“宏纳众流”的雄心尽一份为人臣者之力,“实属庙堂代言之作”;方法上,踵武朱熹《诗集传》注《诗》之义例,乃与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统制国家的做法同一机杼(第214 页);采集前人注解上,“决不是对诸家旧说的简单收集”,而是对旧说进行了一次“遴选”和“净化”,实融贯着仇氏自家的理念(第219页)等等。
总之,通观中篇中所考论,处处可见他“观照” 这一代杜诗学时宏阔独到的眼光、鞭辟入里的考辨、发隐抉微的见解。而把这些考论所得汇集一起,这一时期杜诗学“殊途同归”,具有共通性、整体性的精神风貌、发展脉络也就历历在眼、分明可见了。即,他们都是意在树立一个“伦理道德楷范”、一个“诗圣”形象的杜甫。他们或反拨明人“选隽解律”“评其细而遗其大,评其一字一句而失其全篇”的解杜之风,力图把握杜诗的全貌,解得杜甫的真精神;或恢复杜诗注疏之学,树立杜集的经典性地位;或维护杜诗、杜甫温柔敦厚、有益风教的“纯正性”;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指向这一目的,是根植于这一代追求“经世致用”的整体学术风气的。
可以说,家壮此著,不仅在深度、系统性、整体性诸方面,使对明末清初杜诗学的认识跃升至了一个新的境地;同时也通过从“细节”考论中寻绎出“整体”意义,和以“整体”意识照烛“细节”考论这两个向度上做出的实绩,有力地展示了“知人”“论世”这一“关照模式”对于研究杜诗学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三
此著下篇系专门考论明末清初的杜诗书写,这是杜诗学研究的一个创例,这里也应略作评议。笔者对书法一窍不通,仅从“杜诗学”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书法艺术,相对而言比较抽象,它和书者的情绪心理表里相连,但又难以明确对应;而且以前杜诗学著作都没有将此类作品或资料纳入。所以家壮君此举的得失,尚有待学界讨论,就如林继中先生为其所作序中给予赞许肯定的同时也曾谈到的那样:“(把杜诗书写纳入杜诗学范畴)甚有创意,亦可见其素养和胆识。……说到胆识,也流露出我的一点担忧。‘正宗’的杜诗学能接纳‘杜诗书写’为研究对象吗?研究它有什么‘现实意义’?”
但是,就如前所谈及,由于杜甫在历史上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杜诗学的意义实非文学研究或学术研究自身所能涵盖。从揭示杜甫在历史上的全部意义这个角度而言,家壮君的做法是诚可嘉许且有启发性的。如果从杜甫杜诗的学术意义、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等总体考量,“杜诗学”这一范畴的外延其实应该扩大一些,不应局限于文学研究的范围,抑或说“杜诗学”应该承担“杜甫学”的内涵④。这样来看,“杜诗学”的内涵就不应仅是“诗”之学或“学术”之学,而应为“文化”之学。其外延不应仅局限于杜诗的注解及整理,历史上凡和杜甫有关的文化现象,诸如有关杜甫杜诗的书法、绘画、石刻等艺术作品,有关杜甫杜诗的后人吟咏、论评、模拟、继和等诗作,有关杜甫的草堂、祠庙、冢墓等遗迹,祭吊等活动等等,皆可纳入其范畴。于此而言,家壮君之举可谓是对此的初步尝试和勇敢探索。
如果说其做法有可商榷之处的话,问题其实在于,“杜诗书写”只是“杜诗学”疆域开拓之一端,既非全面开拓,又非“体系”之整体构建,把“杜诗书写”置于全书的下篇,确有不伦之感。如作为“附篇”处置,则会比较妥当。
总之,家壮君此著,立意既高,又考辑扎实全面,论析鞭辟入里,不仅对于明末清初杜诗学,而且对于整个杜诗学而言,都具有纵向拓深和横向拓展之意义。称之为“一部开拓杜诗学研究新进境的力作”实非过誉之辞。
注释:
①对于此,家壮君在书中有明确表述:“亦即希望通过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观照方式贴近明末清初杜诗学的历史空间。”(第19页)
②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中唐——北宋)·导言》,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③参看林继中《杜诗学论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中所收录《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超越“以史证诗”——试从文化诗学的视角认知“诗史”》等文。
④今天已有学者采用“杜甫学”的概念,参看刘文刚《杜甫学史》(巴蜀书社2012年版)。